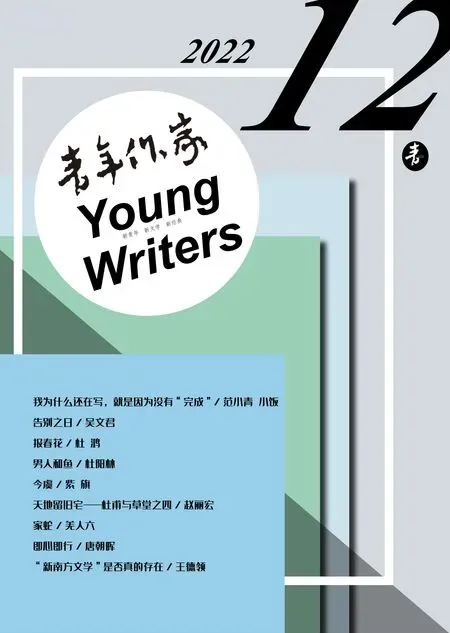旧 事
蓝格子
老 井
对于老一辈人而言,我所说的老井,并不够老。我记忆里的老井,不是大家所说的一个村子里只有一口的辘轳井,而是我老家,一家一户院子里的手压井。对于喝着井水行事的孩子,无论走多远、饮过多少他乡水,总也冲不淡家乡老井水的味道。
关于老井,还要从父亲讲起。父亲十一岁时,祖父病逝,迫于生活压力,祖母带着父亲和大姑母从安徽乡下逃荒至东北。后来,祖母改嫁,父亲相继又多了六个兄弟姐妹,一半是祖母在东北生养的,另一半是新祖父和前妻生养的,但最大的叔叔也比父亲小,父亲仍然是家族里父辈中的大哥。祖母改嫁时,新祖父就患有严重的咳疾,人又有些懒惰,叔叔姑母们年龄又小,家中大大小小的活计都落在父亲一个人身上。父亲只读了一年小学就辍学了,为养活一个十口之家。当时整个村子里的人共用一口辘轳井,没过几年,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多,一口井哺育全村人,已经显得十分吃力了。随着时代的变迁,开始有人在自家的院子里打井,村头的辘轳井也就逐渐废弃了。是年,父亲与母亲结婚,没有彩礼,没有房,更没有车,只有两小桶豆油。两个人,动手搭建起一间极简单的茅草屋,就这样有了自己的家。也是这一年,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父亲打了第一口井,在祖母和叔叔们的院子里。我没有亲眼见到父亲打井的情形,可我看到过他在炎炎烈日下铲地的样子:脸部和上身的皮肤被晒得通红,汗水沿着脸颊和脊背淌下来。我想,父亲当年打井的时候,大抵也是这样吧!
打一口井,不光是为了解决一家人的吃水问题,也是一家人在一个村庄生活的颜面。
父亲已经成家,独立门户,但叔叔们毕竟还小,再加上新祖父去世,养活整个大家庭的重担还是由父亲一个人承担。所以,到大哥出生两年多以后,父母亲才盖上了一间土坯房,在小院子里打了一口真正属于自己的井。一直到后来二哥和我出生,我们一家五口人,住在狭小的土坯房里,就是喝着这口井里的水度过那些艰涩而甘甜岁月的。因此,从我记事时起,老井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了,那时,我还没有露出地面的井头高。可能家中的老幺自然都娇惯些吧!两个哥哥又都比我大十来岁,所以,家里打水的活儿都由他们俩承担下来。我还记得,多数是黄昏时分,母亲在灶前生火做饭,两个哥哥轮流压井,然后用一根结实的木棍将满满一铁桶水抬进屋,再一起倒进缸里,我多半是在一旁充当看客。井水倒进缸里的瞬间,形成小小的瀑布,这样的场景在当时的我看来,极为壮观!哗哗的流水声,成了童年里最动听的音乐。后来,我长大一些了,他们也不让我帮忙,只有在我任性地自告奋勇下,他们拿我没办法时,才让我来压井。由于我力气小,压得比较慢,他们要在一旁等很久,自然也开始打闹玩耍起来。每当父亲看到他们让我来压井,便会心疼起他的小女儿,要把哥哥们训斥一顿。我却不知道为他们解围,只一味沉浸在压水玩儿带来的乐趣中。只要将井上那根铁棍向上抬起,再用力往下压,前面的拐脖处就会有清澈的水流出来,在一个孩子眼里,那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啊!夕阳西下,金色阳光把土房子粉刷得光亮,老花猫在墙根的阴凉处趴着不动,眼睛眯成一条缝儿,神态安详,院子里的鸭子在它身旁悠然自得地踱着方步。我用尽力气压出来的井水也被施以魔法,仿佛就是汩汩流淌的金水,此刻父亲和哥哥们也都像是镶了金边的人,我感到头顶的阳光和手里握着的井杆儿,同样温暖得让人沉醉不已。童年的天,总是特别高、特别蓝,每每炊烟升起,就好像乡村女孩手中舞动的白纱。
好日子,就在岁月无情的追赶中匆匆闪过。叔叔、姑母们相继成家以后,便渐渐地不再需要父亲这个大哥的照顾了。甚至于祖母去世,几个叔叔在他们的母亲下葬后就因为遗产分配的事,迅速打翻了兄弟情义,父亲依旧保持沉默,这样的事,他总是没有发言权。我看着他,蹲坐在台阶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按打火机的时候显得十分吃力,夹烟的手指看起来僵硬得像是扭曲的枯树枝,从我站的角度并不能看清他脸上的表情,只依稀看见他侧脸的肌肉在微微抽动,眼睛盯着祖母院子里那口早已锈迹斑斑的老井,落寞得像是冬日里一截没精打采的老树。这些年,在那个家里,他从来都只是干活儿养家,不多言语,除了结婚时的那两桶豆油,没有拿过任何东西。现在,祖母去世了,临终前一句话都没有交代,他作为异姓的大哥,眼睁睁看着他的兄弟们自相伤害,却尴尬地说不出一句劝阻的话。他怎么能够想得明白,那么一大家子人,多少年都是喝着同一口井水生活的,现在竟要弃血浓于水的亲情于不顾。后来他几次努力想将叔叔姑母们团结起来,但终究是白费了苦心。
流年似水,每一个人,每一种事物,也不断地向前走去,老井也不例外。逐渐地,村子里的压水井也大多被卸下去了,电水泵代替了老井。我几次提议说:“屋里都有了电水泵抽水喝,老井闲在那儿也不常用,还占地方,干嘛不拆掉它?”父亲都没有说话,他的眼神,深邃得像一口老井,只有那隐约的哀伤,好像祖母去世那年我看到的情形一样。母亲见状,连忙把我拉到一旁:“这么多年,他守着那口老井,习惯了!就让他守着吧!”于是,关于拆掉老井的事我再未敢提及。每到夏天,父亲就搬出一口大水缸,放在井头下,压好满满一缸水说:“放那儿晒着,饮牛不会凉,谁想洗洗手,也方便。”有时候,村子里停电了,家家户户洗衣做饭缺水,就来我们家,排着队用老井打水。这时,父亲总是微笑着去仓库里拿出两个干净的水桶,给乡亲们用,偶尔,还会亲自去帮忙压水。看他压水的样子,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脸上还不自觉地浮现出喜悦的神色。恍惚间,我才猛然惊醒,父亲执意保留那口老井,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家人洗手方便,另一层也是与人方便,那是他对于人情固执的守望啊!过了一会儿,乡亲们把父亲换下来,他却仍然站在井边,一动不动地看着井水哗哗地流到桶里,仿佛一刻不守着老井都不安心。正午的阳光明亮得有些晃眼,这么近的距离,我竟有些分不清站在不远处的是父亲还是老井,或许,他们早已合二为一了。
多少年了,老井经历过无数次风吹雨打,木头井架已经有些腐烂,固定井架的铁丝更是生了厚厚的一层铁锈,可老井的井杆儿,反而越磨越亮。去年夏天我从南方回家,一路上蒙了不少灰尘,手上也汗涔涔的。刚进院子,就看到父亲在用老井压水,我走上前,井头下面已经蓄了大半缸水。父亲说:“洗洗手吧!凉快!”我洗过手,就接过父亲手里的井杆儿,没有去拿杯子,就用一只手捧着喝,炎热的夏季,只有从老井里刚打出来的水才有这样的清凉与甘甜。我注意到,父亲已经将旧井架换过了,没有漆过,保留着原木色,让人看着如此踏实、舒心,老井,也是。这些年我一直在外面读书,村庄变得亲切而模糊,可关于老井的记忆,却时刻萦绕于心,它就像镶在我身体里的一根脉管,无法拔除。老井是我们这些乡下人的生命源泉,只要它还站着不倒,我们这些常年漂泊在外的故乡人就不会断了水源。
土豆
天上的星星总是让人仰望,地上的,也是。几乎每一个想家的夜晚都会梦到夏天里,一大片土豆叶子,被风吹成绿色的海洋,上面飘浮着白色、紫色的土豆花,就好像散落人间的点点繁星。
我的家乡在东北农村,小时候,生活条件不好,很少能够吃到新鲜蔬菜,尤其是在寒冬腊月。秋收以后,粮食装满谷仓,就要进行蔬菜的抢收,在降霜之前要把白菜、萝卜、土豆等全部收好,存入菜窖。此后,一大家子人就靠着这些蔬菜度过漫长的冬春两季。
土豆是北方人餐桌上的常客,炝土豆丝、炒土豆片,炖豆角、炖小鸡,哪一样都少不了它,有时甚至还将土豆做成主食来吃。一般来说,都会选用小一点的土豆,大的留着切丝切片。土豆洗干净之后,放到锅里,或蒸或煮,然后把外面的薄皮剥掉,蘸着自家打的大酱吃。酱香和土豆香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种近乎原始的味道让我迷恋。除了这些家常吃法之外,还可以制成土豆干。首先要将土豆去皮洗净,随后切成土豆片,放到清水里浸泡,泡好之后还要上锅蒸熟。最后,把蒸熟的土豆片和浸泡生土豆片的水一齐拿到院子里进行晾晒。土豆片和盆里的水分一点一点被阳光和风带走,盆里逐渐显现出白色的粉末状物质,这就是我们家厨房里自己使用的淀粉。而土豆片,则留下了养分和醇香。晒好的土豆干呈琥珀色,晶莹透明,不仅可以长期储存,而且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土豆干里的淀粉被事先漂出,因而变得韧性十足。土豆干在吃之前要先用开水浸泡,可以红烧,也可以与腊肉、干肠等一起炖食,口感劲道。在冬季缺菜的北方,这种食物变化带来的新口味显得尤为重要。
土豆不仅可以做菜,可以做主食,还可以做零食。童年记忆里,印象最为深刻的还要算餐桌之外的土豆。那时候,东北的农村,冬天还没有暖气,每家每户都是用砖头垒砌而成的炉子,烧柴禾。一到冬天,大人孩子都窝在屋里“猫冬”,烤土豆在这时候成了最好的休闲食品。一开始,都是把土豆放在火炭上烧,烧出来的土豆虽然足够香,但土豆外面会形成一层厚厚的烧焦的硬壳,不但造成浪费,还会把手弄脏。有时候,母亲看到我们因为贪吃,不注意,脸上也跟着抹了黑,就打趣地说:“这孩子,个个都跟烤土豆一个模样,成了‘黑脸包公’!”我对于这样的“嘲笑”总是可以置之不理,但大我几岁的二哥却不能。为此,他想出了一个堪称绝妙的解决办法,至今我还对他的聪明感到佩服。他先是找来一根新铁丝,洗干净,再把土豆一个个串在上面,形成一条“土豆链”,然后放进炉膛,悬空,把两端留出的铁丝放在炉盖上,再用烧水壶压住。我在一旁巴巴地看着,二哥自信地说:“你就等着看我的‘杰作’吧!”我对他的话感到半信半疑,然而,也还是乖乖地等着。等他把烤好的“土豆链”拿出来,我忽然崇拜起他来了!那些土豆不但没有变成“黑脸包公”,而且外焦里嫩,只需剥掉最外面一层极薄的皮,露出来的那一层就又香又脆,一口咬下去,就能看见淡黄色的土豆瓤上面泛着白沙,十分香软,北方方言把这种口感叫做“面”,与土豆干的劲道正好相反。窗外的雪下得不疾不徐,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看电视,一边享受着烤土豆的美味。从那以后,二哥就成了我们家每年冬天的烤土豆“专员”。
烤土豆虽然好吃,我却还不满足,非要二哥换换花样儿。而二哥,对于他这个任性小妹的“无理要求”,也总是尽量满足。那天,我在外面和邻居伙伴滑爬犁回来,正觉得饿。刚进屋,一股土豆的香味就迎面扑来,我连忙跑去厨房,只见二哥站在炉子旁边,一手端着盘子,一手拿着筷子忙着翻炉盖上的土豆片。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品尝新的美味了,一个劲儿催他快点烤,他看见我在一旁馋得直流口水,就大笑起来。大哥看见了,也跟着笑。我觉得他们在笑话我,说要去跟爸爸告状,他们才肯停下来。二哥把土豆片切得很薄,要烤至金黄色,才捡到盘子里,还要在上面撒上一层薄薄的盐,这种自制的“薯片”又香又脆,好吃极了!时隔多年,土豆的这些最朴素吃法仍然让我觉得回味无穷,那些平凡的日子,是我们兄妹在一起最快乐的时光。
后来大哥二哥外出读书,每封家书后面也总是惦记着他们的小妹在家听不听话。我每次读到这儿的时候,都一面在心里怨他们不相信我早已经变得懂事,一面偷偷地拿出他们的照片,看着看着就流下眼泪。现在,大哥、二哥都已经各自成家,也有了自己的子女,但家中早已没有了火炉子,侄子、侄女吃到的薯片或薯条,都是超市里买来的膨化食品,缺少了土豆的纯正香味,更别提烤土豆的乐趣了。似乎越是清贫的日子,人活得越是简单、快乐,我很庆幸自己生长于农村。
故乡虽然每天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属于故乡人独有的那些食物的味道却是历久弥新。在外面,无论吃多么美味的佳肴,也总难抵消家乡的味道。我每次和朋友们吃饭,都要点上一盘带土豆的菜,虽然也好吃,但我内心最怀念的还是小时候家里的土豆。行走异乡的日子,总觉得自己时时刻刻怀揣着一枚隐形的土豆,凝结着难舍的记忆,带着泥土的芳香,带着炉火的温度。
煎 饼
我小时候并不十分爱吃煎饼,嫌它太硬,不好咬。要知道,煎饼是最能考验人的咬合力的,它的韧性极强,以它为重要主食的北方人,身上也充满了这种韧劲儿。在外面读书这些年,吃过不少各地的小吃,但我最想念的,还是家里的煎饼。那金黄色的圆,成了悬挂在我梦里的一轮明月。
我所说的这种煎饼确切地说应该叫“山东煎饼”,因为它产于山东省东南部和西南部的临沂、泰安等地。我之所以能吃到口感纯正的煎饼是因为我的母亲是山东人,她十几岁跟随外祖母和舅舅来到东北时已经会摊煎饼了。现在,村子里年轻一些的婶婶摊煎饼的手艺就是从母亲这里学的。
每年四月是村里人摊煎饼的月份,每一家都要赶在春耕之前将这种易于保存和食用的主食备好,为的是农忙时做饭省些时间。摊煎饼之前要有一系列准备工作。首先,要把玉米、小米、花生等五谷杂粮去皮,淘洗干净,将其中的三分之二倒入桶里浸泡两日,另外三分之一放入锅中蒸熟,这叫做“熟饭”,然后再将这些原料搅拌均匀,磨成糊,也就是“煎饼糊子”。那时候磨煎饼糊子多数是用村里的碾磨磨制而成的,不像现在,煎饼糊子都是用电机磨出来的,石磨和石碾子早已成为乡村沧桑历史遗留下来的物证了。糊子磨好,就可以搭鏊子,生火摊煎饼了。
童年记忆里摊煎饼的时候,总是快乐的。在乡村,无论大人还是孩子,人与人之间,都格外亲近。农村人做什么事情都是相互帮忙,有什么活儿大伙儿都会一起干,摊煎饼自然也不例外。村里有鏊子的人家不多,我们家是其中一家。每一户人家摊一次煎饼要三四天左右,几家轮一圈儿,就要近一个月。婶婶们来摊煎饼,当然还会带上自家的丫头。这时候,大人们在屋里摊煎饼,我和小伙伴们就在院子里做游戏,有时跳皮筋,有时丢沙包,还有时跳格子……饿了就去煎饼房里要一张刚摊出来的煎饼吃。煎饼糊子从倒在鏊子上那一刻起,就被柴火的温度迅速加热,粮食的香味儿瞬时化成一团蒸汽,大人孩子都被包围其中。拿到煎饼的孩子又要跑到院子里玩儿去了!
如果天气暖和一点,野生韭菜就会长出来,我们便会提着柳条编制而成的小篮子,去附近的山上割,几乎每一个农村孩子很小就会使用镰刀去山上采摘野菜。从山上采回来的韭菜,韭菜味儿更浓些,不要说现在超市里卖的韭菜,就是农村自家园子里的韭菜也没它味道好。山韭菜是用来做煎饼合子的,作为一大家人的午饭。把洗好的韭菜切碎,打上五六个笨鸡蛋,再加上豆油、盐等调味品,拌好馅。将刚摊好的煎饼洒上些温水,使其变软,再把备好的馅儿放上去,一张一张地叠成方形,然后像烙油饼一样煎好即可。虽然时间不长,但在一旁等着的孩子可是已经心急如焚了!时不时从厨房跑到院子,再从院子跑回厨房,有时我们在院子里看到烟囱中飘出缕缕炊烟,仿若蓝色天空里游走的云,好像自己的家就在快乐的仙境!
任何一件美好的事情,都需要足够的耐心经营和等待。在乡村孩子们的童年里,摊煎饼时节值得等待的要数那最后一张煎饼。这最后一张煎饼并不是一般的煎饼,它应该叫油煎饼,是北方孩子尤其是农村孩子一年里难得的美味“零食”。每次一说摊油煎饼的时候,我就飞快地跑到厨房将白糖罐子捧到鏊子前,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属于我们的美味是如何炼成的。摊油煎饼的时候当然要先倒上油,再倒煎饼糊子,煎饼糊子要比摊普通煎饼时多,油也不是一次倒完的,需要三四次才行,还要加上白糖。因为油煎饼比较厚,因此摊制时的火候更难掌握,火大了,下面会煳掉,上面却不熟,火小了,鏊子的温度上不去,摊出来的油煎饼会潮湿粘牙,放凉之后就会变硬,咬不动。油煎饼要等到凉透了更好吃,酥脆可口,又香又甜。就连蒲松龄也要为煎饼的美味而倾倒,他曾作过一篇《煎饼赋》专门赞美煎饼:“圆如望月,大如铜钲,薄似剡溪之纸,色似黄鹤之翎,此煎饼之定制也……味松酥而爽口,香四散而远飘。”这真是对煎饼最恰当的描述了。
北方人选择煎饼作为主食绝对不是偶然。其一,北方的气候不似南方那般温润,物产也不如南方来得丰富,食物保存在这片寒冷的土地上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偏远的山村。早些年,农村的生活条件差,交通又不够方便,别说绿色果蔬,就是大米、白面这样的“高档”食物也不是家家能吃得起的。人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自家产的玉米、黄豆,煎饼顺理成章地成为北方人的首选主食。再者,北方也不仅仅是人们印象中广袤无垠的平原和一望无际的黑土,还有很多山区,由于地势不够平坦,地块面积也小,无法真正实现农业机械化,人力、畜力都无法完全得到解放。因此,到了农忙时节,农民们可真是要忙上一阵子。这时候,煎饼在庄稼人的生活中就发挥出了重大作用。干了一上午农活,回家炒上一个简单的小菜,忙了、累了的时候,不愿意炒菜,就用煎饼卷点儿咸鱼或大葱,一顿午餐就这样完成了。大葱蘸大酱,煎饼卷大葱,是北方人最爱的煎饼吃法。这种简单而原始的吃法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伴随着北方人走过了那些贫寒、艰涩的岁月,即使现在多数北方乡村都已经以米饭、馒头为主食了,但煎饼所包含的农作物最初的甘甜和北方地域的风土人情,还是常常让人们在以后的日子中念念不忘。
如今,在外地,也有一些地方卖煎饼,可我只吃过一次,虽然很薄,或许是由于为了口感劲道而加入了特殊材料,也或许是由于机制的原因,总觉得外面买到的煎饼缺少了家乡煎饼那种独特的谷物香味儿。然而我想,对于一个常年在外的游子来说,比一张煎饼更让人回味无穷的是关于故乡与故乡人的种种记忆。在时光的碾磨一点一点向前推动时,煎饼的香味儿,在一个又一个异乡的夜晚仍会飘进我的梦里,而我,就守在梦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