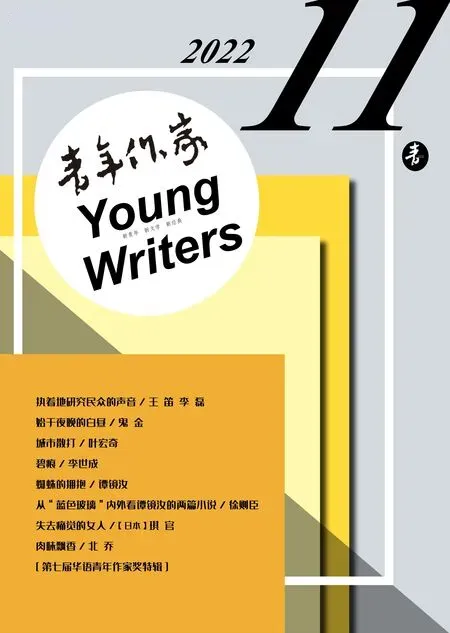肉味飘香
北乔
到临潭的第一顿饭,我就吃上了手抓肉。准确地说,是手抓羊肉,这也是我头一回吃手抓肉。
盘子是羊形的,一只白白的羊卧着,头稍昂起,盘子里有一条条肉,肥瘦相间,都带骨,宽度和长度与我的食指大差不差,那样子和猪小排有点像。没有我想象中的粗犷,反倒是比较精致,也能看出,厨师的刀功不错。我取了一条肥多瘦少的,一手捏骨一手扯肉,有些费劲,但还算顺畅。不是说到了高原,就要大口吃肉吗?好吧,我把整条肉塞进口中。麻烦来了,肉韧劲十足,我怎么嚼也嚼不烂。当着众人的面,我不好意思吐出来,更舍不得吐出来。为了遮人耳目,我左手捂着嘴呈倾听谈话状,表面上风轻云淡,口腔里牙齿与肉的战斗一刻没停,努力了好一会儿,我不得不放弃抵抗,硬生生地把肉推进了喉咙,狠狠地咽了下去。
来高原前,我着实做了一些功课,显然,功夫下得还不够,没有细细研究一下这手抓肉怎么吃。看看周围人吃得津津有味,我心头闪过小小的失落,当晚再也没吃这手抓肉的欲望了。临睡前,我想起了手抓肉,感觉这本身就是一个隐喻。我来到曾经的远方,纵然再努力,必然还会遭遇许多囫囵吞枣之事,甚至根本就无法嚼出味咽得下。
后来我才知道,这手抓肉还是人家特意为我们做的,肉煮到九成熟,切得齐整,而且是专挑的肋条肉。他们平常把一整块牛肉或羊扔进锅里,可以放些姜、辣椒等佐料,但许多时候就是单纯的清水煮,要的就是原味。肉只煮七成熟左右,最好带些血丝。用盆端上来时,边上会放一把锋利的小刀,现割现吃。吃肉,要的就是有嚼头,越嚼越香。他们说吃手抓肉,没什么窍门,放开腮帮子,手与牙都用上劲就可以。我见他们吃起来有滋有味,吃过的骨头呈惨白色,一点肉星儿都没有,我怎么也做不到。我喜欢肉烂一些,可人家说那有什么嚼头,不够劲,不够味。
在临潭,人们说牛肉,多指的是牦牛肉。与羊肉相比,吃牦牛肉更需要咀嚼之功。吃牛肉,完全是用刀,那藏式小刀煞是讨人喜。握起小刀,自己想吃哪里就割下来,这让我感觉到了游牧人传统的食肉方法。小刀割开肉,因肉只有七成熟,那血丝相当显眼,我常误以为是生肉。他们爱吃这样的肉,想来多是祖辈游牧生活的饮食基因还在。或许,他们也是以这样的方式致敬祖辈。锋利的小刀、鲜美的牛肉,在坚硬与柔软之间,可以有太多的想象。
处于高寒地带,牛羊生长得很慢,体格强健,肉质密实,那份韧劲,吃起来考验牙齿。大块吃肉,其实是吃下大块的肉,他们更在乎这吃的过程。煮肉之法,已至极简,只要锅放得下,肉就尽可能大。能在嘴里解决的,从不劳烦那些烹饪之道。这是极为朴素的吃肉之法,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吃出了肉的本真滋味。
来,弄块肉,大人割下一块特别筋道的肉递给孩子,吃下了,再来啊。这块肉真够孩子嚼上好半天。就这样,我们可以时常见到大人在桌上喝酒吃肉,小孩子在一旁玩耍,嘴里一直动个不停。看来,这吃肉的本领从小就开始练了。练的不只是牙齿的咬合力,更是一种吃的态度。或许,其中还隐含生活的教义。
搞点肉吃,或,屋里去,煮肉上。临潭人常说这两句话时,口气很寻常,很轻很轻,可端上的肉很壮观。一盆羊肉,一盆牛肉,一盆血肠,盆是大盆,瞬间把桌子挤得满满当当。现在许多人家用木质的托盘装肉,那往桌上一放,说是一座小山,真不为过。有了肉,别的菜,可以免了。事实上,临潭人有了肉,就算是席了,其他菜可有可无。亲朋好友聚在一块儿,常常就是吃肉。饭可以不吃,肉不能少。临潭人对肉执着而浓烈的需求,不由得让我赞叹。
有肉吃,是临潭人最低也是最高的生活要求。条件困难时,能吃上肉,这日子就算不错了。现在条件好了,能尽情地吃肉,这生活顶好了。能吃回肉和天天能吃肉,他们都认为是很奢侈的事。刚脱贫的农民和生意做得相当好的老板,都会说,现在日子好着呢,能敞开吃肉了。同样,待客怎么着都得有肉,有肉又是待客的最高礼遇。
牦牛,藏语发音为“雅克”,最早汉地人称牦牛为雅牛,后因形造出了“氂”字,该字本读“雅”,汉语中“氂”字有多音,又读“毛”,人们以牦牛全身长有长毛而形似,最后牦牛这个称谓就流传至今。据生物学家研究推断,早在200 多万年以前,野牦牛就与一些大型草食性兽类在青藏高原同生共处。就目前的研究,人类踏足青藏高原最早的年代在4 万年前,而人类驯化牦牛始于7300 年前。我们现在遇见的基本上都是畜养牦牛,野牦牛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视线之外。
在高原,牦牛可以撑起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部。牦牛肉、酥油、牦牛奶为食,酥油灯可供照明,用牛皮做靴子,牛毛搭帐篷,连牛粪也是最好的燃料。牦牛比马更有力,更抗忍饿,驮运、耕地,是强项。尤其是冰雪、沼泽之地,牦牛的行走能力,是惊人的。就连娱乐,骑牦牛也比骑马更刺激更有趣味。
牦牛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奇怪的是,如此的熟悉的牦牛,偏偏又给人极为神秘之感。牦牛是世界上唯一的源种牛,没有和其他牛杂交过,与企鹅、北极熊一样属于世界仅存的三种源种动物之一。古代藏族神话中,将野牦牛称为天上的“星辰”。牦牛远比人类更适应高原,千万年来,它们就是高原的一部分。或许正因为如此,它们有着与高原一样的神奇与神秘。日常性与神性,在牦牛身上得到完美交融。
遇见过牦牛打架,也算激烈,可在我看来那是两位身披黑裙的舞者。如果牦牛快速地奔跑,那静坐于肉体的野性会一下子爆发出来。这时候的牦牛,刚烈、威猛,浑身之力似乎足以驾驭茫茫的高原。只是这样的场景很少很少,多数时候它们与高原一样静默、平和。青青的草地、白色的羊、黑色的牦牛,如同白天与夜晚在沉默中对话。是的,它们很安静。安逸的生活,温柔地剪去了它们的野性。更大的可能是,它们学会了隐忍,像高原一样深藏我们无法感知的厚重。不问人间事,低头吃草,咀嚼,似乎是它们最专注的事,也可能是它们生活中唯一的大事。
时常会在路上遇见牦牛,不紧不慢,步伐从容优雅。我坐在车上,俯视那些黑得发亮的背,几乎看不到它们的眼睛。每到这时候,我有种不得而知的优越感。当我在草地上遇见它们,那眼睛令我不寒而栗。不敢过久地对视,不是恐惧,而是我看到莫名忧伤。那壮硕的体形,让我一下子渺小了卑微了。我总是有意与牦牛保持距离,靠得太近,我的世界就没有了。那天,我在山坡上闲逛,阳光很好,天很蓝,草很柔软,我就躺了下来。原先的糟糕心情一下子治愈了,闭着眼想象飞翔的感觉。待我睁开眼时,一头牦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这太意外了,我没看到山坡上有牛啊,它从哪里来的?不是夸张,那一刻,我的眼前是一座山,牛眼里卧着深潭。我下意识地半坐着向后挪动,那牛一动不动。最后,我落荒而逃了。
我更喜欢羊,虽然我总觉得它那挂在唇边的笑意,带着某种嘲笑之味。老家的羊,我可以上去抚摸,但高原上的羊,我从来未能接近过,感觉它们的防备心特别重。这些高原上的羊,表面上很温顺,但与我格格不入,不像我老家的羊,有朋友之感。
高原上的牛羊,呼吸纯净的空气,沐浴纯净的阳光,饮喝纯净的溪水甘泉,终身吃天然的野草。古老原始的放牧方式,依然在这里得以延续。人们给牛羊以一个舒适的家,给了它们安全、舒适及相对自由的生活。不再像它们的祖先那样受寒冷风雪之苦,时刻担心被野兽撕咬。牧人像对待孩子一样照料它们,每天陪着早出晚归。
这些年草场越来越好,牛羊的日子也是好多了。没有了凶险,一切都很安逸,只是无法终老。这和我家乡的水牛不一样。区别就在于牦牛成天在草地上边玩边吃,自在得很,而水牛一天到晚要干活,很辛苦又极不自由。水牛是家里的重要劳力,也是家庭成员之一,基本上都可以善终。牦牛的宿命是被宰,寿命有定数,但它们是否知道呢?更不知道的是,如果让牦牛和水牛自主选择,它们选现在的生活,还是互为对方,还是回到它们祖先那样的生活?
这个问题真不能往深处想,想多了,我们可能就不是在为牛想了。
吃肉最够味的,还当是浪山的时候。
浪山,藏语称“香浪节”。“香浪”是藏语采薪之意。每年农历六月中旬、藏历六月初九,甘南许多地方都要举办“浪山节”。过去寺院每年这个时候进山伐薪,因路途遥远当日不能返回,遂选择依山傍水处露宿野营,多则数日。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演变为广大农牧民群众喜爱的传统节日。据《夏河史话》记载:节日的前一天日出之前,人们来到有拉再(祭祀石塔)的山头上,煨桑祭神,祈求神灵的保佑。赛马、赛牦牛、摔跤、拔河,是人们欢迎的项目,男女老少踊跃参加。入夜后,能歌善舞的藏族同胞,在熊熊燃烧的篝火边,唱起悠扬动听的歌曲,翩翩起舞,尽情欢乐,直到深夜。
这时候的甘南,气候宜人,风景最美,人们可在草原、山间尽情地撒欢,吃肉喝酒自然少不了。在草地、在山坡上、在小溪边支起大锅煮肉,青烟蹿得很高,肉香飘得很远。家族团圆,好友相聚,小小的草地上,浓缩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所有,迸发了所有的快乐与幸福。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在演绎和回味那消失于岁月深处的远古生活。
临潭属于半农半牧区,汉族人远多于藏族人,其浪山更接近郊游和野炊,几乎没有与马有关的活动,至少我没有遇上过。过去放牧是骑马,现在基本是骑摩托。在人们的生活中,马越走越远。
古战乡拉直村,每年二月有赛马,周边县乡都有人来参加。多个民族的男女老少,马儿是从自家牵来的,比赛也简单,就是比快。山谷间的开阔地,飞奔的马儿卷起沙尘。
在冶力关天池的河滩上有马,是当地的农民用来做游客生意的。纯粹的娱乐性体验,马儿走得很慢,牵绳的农民控制着速度,以保安全。
浪山,是对曾经生活的追忆,更是当下生活的延伸。看不到马,听不到马蹄声声,但马的身影在人们心中挥之不去。
回到大自然中,以最舒展的情绪把自己完全交给湛蓝的天空、嫩绿的草地以及掩不住野性的微风。人们不再是当年那样骑马来了,小汽车就在不远处的路上停着。许多人手机不离手,拍照刷微信。是的,现代性的元素很多,可我觉得眼前的一切与我梦中的画面很相似。或者说,与我想象中的甘南草原是一样的。
许多时候,煮肉并没有专人,而是大家都在参与。吃肉,同样如此。肉在那儿,刀在那儿,想吃,自己上去割一块肉。孩子们喜欢弄上大大一块儿,乱啃胡咬,双手和脸上油滋滋的,就连笑容似乎都在冒油。有个六七岁的小男孩,远离人群,到一棵树下坐着,身边是他家的狗。刚开始,他咬一口肉,就撕点肉给狗。后来,干脆自己咬一口,递给狗咬一口。狗吃得很自然,他时而就冲着狗笑,时而在地上打滚,既是高兴,又是试图逗狗玩。狗还是在吃肉,不为所动。我很想上前参与其中,但终究没有,只是远远地望着。
我爱在草地上走来走去,走进水声里,走进花香里,走进肉香里,走进人们的笑声里。我走在人间,也走在天堂。有时,我还会选一高处坐下来。身后是树林,再后面是高山。眼前是开阔的草地,追逐的孩子,拍照的姑娘,再往前就是那口大锅和吃肉的人们,再往前就是一顶顶帐篷,最远处又是树林和高山。我的目光随意地撒向某一处,或者漫山遍野地乱晃,但总会时不时地看看那口煮肉的大锅。
坐上一会儿,我想起童年时躺在草垛上,跷着二郎腿仰望天空。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我还真是想不明白。
与一群牦牛和羊漫步在草原上,那是我向往的。
这天我到扎西家,想和他一起去牧场。我专门挑了这个日子,七月的草原,美得无法形容。扎西让上初中的儿子才旦一起去,可才旦不情愿。说这话的时候,才旦正在羊圈里收拾羊粪,干得满头大汗。这不应该啊,放牧能随处溜达,比干这脏活累活舒服啊。扎西的口气,没有商量的余地,才旦很不高兴地从羊圈出来。
我以为他们会带上生肉、锅之类,牧场比较远,中午不可能回来吃饭,在外野炊,蛮好的。不料,他们只是带了些熟肉、馍和一些水,我也不好意思提什么要求。扎西给我拿来一件羊毛大衣,我说我穿着毛衣毛裤,不用了吧。扎西说,带上吧,外头会冷的。
扎西家有39 只牦牛、161 头羊,牧场离住的地方有三小时的路程。距离其实不算远,从家出来有一段水泥路,后来就进入草地。翻过两个不算高但很大的山地草场,又走了个把小时,才到了扎西家的牧场。经过的都是别人家的草场,牛羊可不能吃。扎西一路上吆喝不停,但还总有个别牛羊不听话,动不动啃一口。才旦特别认生,很少和我说话。刚开始,我的感觉很好,高原的天,蓝得纯蓝,那云尽显浪漫之感。我问才旦,这么好的天气,到牧场多快活啊。他说,不好,还不如在家干活。这三小时,走得很慢,我才明白为什么不骑马或骑摩托了。
这块牧场很平坦,中间还有条小河。牛羊都聚到河边喝水,扎西和才旦随地就坐下了,我虽然有些累,但还是想走走。都说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里可不需要。草很矮,都到不了羊的膝盖。牛羊刚喝了一会儿水,扎西就赶它们去吃草,说是喝得太多,吃不下草,回去的路上,就得饿。
真没有想象的那样闲散,歇不多会儿,就得赶牛羊,不能让它们在一个地儿吃的时间太长,要不然,这草就全废了。
阳光很好,也没什么风。可待久了,真的很冷,我披上羊毛大衣。到了中午,扎西招呼我吃饭,还专门给我带了面包,说是担心我吃不惯馍。因为装在保温的袋子里,肉还不太冰,不过那馍确实很硬。扎西说,这天好多了,要是前几个月或者到了十月份,肉就成冰块一样了。
我说,你怎么不唱歌呢?扎西说,唱歌,你瞧瞧我这忙得,嗓子也快冒烟了,有点空,就坐着,哪还有劲。说着,他嘴上咬着肉又去赶牛羊了。
我逗才旦,这么多牛羊,以后你娶媳妇不愁了。才旦说,我才不要呢。天天陪着这些牛羊,还不如它们舒坦呢,烦死了。可我又不想学习,以后也只能像我阿爸这样了。他这样说,竟让我无言以对。
这地方,手机没信号,想看新闻刷视频打发时间,是不行了。实在是闲得没意思,我就和扎西一起赶牛羊。扎西总提醒我,你离远点哦,它们不认识你,惹急了,会来顶你的。
恍惚间,我突发奇想,这到底是人在放牛羊,还是牛羊在牧人。才旦说,一天到头,都是人在伺候它们,人过得没它们好。小小的青年,似乎悟出了牧民生活的本质。
傍晚,我们回去时,人和牛羊的步子都很沉重。牛羊是吃得太饱,我们三个男人是疲惫所致。路上,才旦和扎西说,明天再不来了。扎西笑笑,不来了,你再不来了。
放牧,真的没意思。
晚饭时,才旦见到牛羊肉特别兴奋,说好大吃一顿。我有些奇怪,平常不管够吗?扎西有些不好意思,哪能,全敞开肚子吃,这日子可就没法过了。我这才知道,今晚能有这么多的牛羊肉,是因为我来了。
临走的时候,才旦对我说,明天还来吧,我还陪你去。我知道,他心里想的是我明天再来,他晚上还能尽兴地吃肉。
我爱吃肉,尤其是红烧肉。
红烧肉,也是成年后才吃到的。成年之前,我有关吃肉的记忆并不多。那时,最羡慕人家过年的时候,门口挂个猪头,一个完整的猪头。现在谁家门口停辆再高级的车,哪怕是架直升机,也比不上当年那个猪头让我羡慕。红烧肉,一定是吃过的,比如左邻右舍红白喜事的桌上,比如年夜饭,但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年二十八,家里会煮肉,悄悄撕一块,蘸点酱油,那是最解馋的。还有就是肉丸。年二十九家里炸肉丸,我从不出门,一直围着锅台。用我妈妈的话说,这孩子眼睛掉进丸子里了,拔不出来了。在武警上海指挥学校那两年,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每周一次的大排。说是大排,其实也没半个巴掌大。
后来,真的是条件好了,我可以想吃肉就能吃肉,也就喜欢上了红烧肉。一周不吃,就觉得浑身不得劲,脑子也迟钝了。就是现在,我也时常放开了猛吃红烧肉,怎么着也得满满一大碗。有时,家人会劝我,少吃些,容易三高呢。我说,我从小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穿上皮鞋尽情吃肉,现在能吃上了,还是想吃就吃,要吃多少就吃多少吧。
牛羊肉,是好东西。可到了临潭,我从没有大吃海吃,反而是有意识地控制自己。从早到晚,饭桌上都离不开牛羊肉,到谁家去,也是牛羊肉当头,哪怕不是饭点,人家也会端上牛羊肉,盛情地让我吃上几块。我不敢多吃,我总认为我的饮食结构里没有牛羊肉,吃多了,害处太多,比如痛风之类。所以,我暗下给自己规定的是每两天,只有一顿吃上些牛羊肉。虽说有些实在是躲不过,但总体上还是控制得不错的。常有人劝我,以后离开临潭,可就没有这样原生态的绿色的特别好吃的牛羊肉了。
在临潭,想吃上红烧肉,还真有难度。就是猪肉,也不是很多。食堂里,饭馆里,不但是牛羊肉的主场,许多时候根本就看不到猪肉。大约到临潭快一年了,我才在县城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家店主营白煮肉。这把我高兴的,第一次去,要了二斤,切成片,装了满满一大盘子,我喝着茶,就干完了。后来,我平均一个月去一次,少则一斤,最多的一次三斤半。那真是吃得过瘾。想想,在临潭三年,我最过瘾的,就是这样吃肉。
回到北京后的近一年里,我吃红烧肉的次数和量,比以前多得多,好像是要把三年的损失补回来一样。
我喜欢吃牛羊肉,也知道离开临潭后,很难再有这样纯正的好肉,也不可能像在临潭时那样随时随地都能开吃。临潭这一方土地的文化,我再深入,也不可能完全走进去,不可能全部融进我的血液里。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更对临潭以及临潭的历史人文怀有深深的敬畏。
肉味飘香,我只能是匆匆过客。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