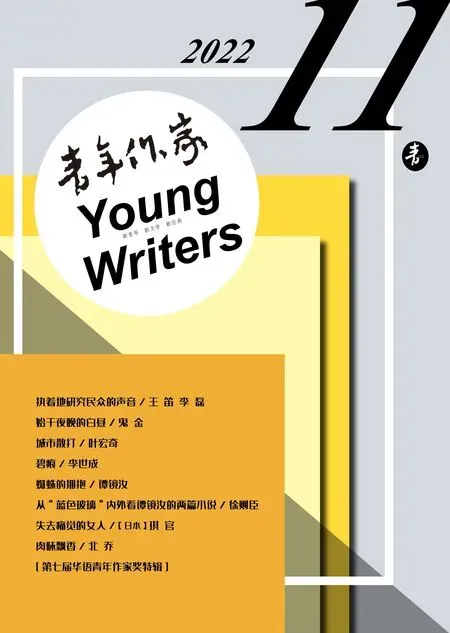幽 情
【加拿大】斯辰
我有点晕,飞机降落所造成的一股恶心让我不得不向窗外看去。骓原,这座我曾经上完高中就离开的城市,依旧葱翠美丽。骓原机场的跑道上奔驰着一群青白色骏马,鬃毛苍黑,像在不舍昼夜地追逐往来的风,我就看到了青春的样子。如果不是这次突如其来的悲剧,我还真没想到会这么快又回来。
上次回骓原是在不久之前,毕业十五年的同学会。那次人聚得真齐,包括我在内,好多国外的同学都回来了。看见终成眷属的刘瑞和Rachel,我不禁想起了十五年前那个闷热的下午。
那天二十三个班的各班大佬带着小弟们仿佛参加武林大会一般,纷纷走向校东的室外篮球场。他们故意放慢步伐,生怕走快了会被认为没见过世面。后来,各班女生也到了。在骓原中学,三个篮球场远不够二十三个班级用,便有了个不成文的规矩——想打球,就“拼场”——五个球,谁赢,场子就归谁。平时这里早已人满为患,可今天空极了,唯独在最远的场子里,有几个笨拙的土老帽,拍皮球般地玩着。可能是从来没有抢到过场子吧,他们脸上挂着憨傻的笑容,完全没搞懂形势。
我们班的李枫缓缓走到场边,场里的人纷纷给他让开位置。李枫扔了瓶饮料给场内的刘瑞,二人互相扬脖点了点头。刘瑞是我们班的中锋,他扫了眼站满场边的各班大佬,单手抓起球,爆起了小臂上的青筋。闷热的下午更闷了。
李枫东张西望,发现了站在三楼东角窗户边的我。这是间音乐教室,最早还是我们班的陈明幽告诉我的。因为学校忙着搞升学,音乐课便早停了。这儿偏安一隅,外窗正对球场,翻内窗便能进。室内墙壁上挂的那些德高望重的音乐家肖像被涂得面目全非。屋内课桌横斜,各样式的便宜乐器零散四方。在这灰尘漫漫的房间里,唯一干净的地方是黑板前的桌子,上面有个能放磁带的机器。陈明幽打从发现了这儿以后,常来这里放朴树的歌。
窗外的李枫龇着嘴,笑着给我比了个中指,让我下去。我还了他两中指。
我们八班的刘瑞和十九班的郝强同时疯狂地爱上了年级的级花——五班的Rachel。Rachel 人长得漂亮,成绩优秀,性格也高傲。我对她最大的印象就是她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刘瑞和郝强在久久得不到Rachel 的任何肯定下,双双认为对方是自己恋爱的最大阻碍,于是君子般地私下决定用篮球单挑。十一个球,谁赢了谁便获得追求Rachel 的权利,输家将退出,永生永世不得向Rachel 以任何方式示爱。就这样,我们永远地记住了这个闷热的下午。
裁判的一声哨响,单挑开始。
站在三楼音乐教室窗前的我,无心看球,而是看着场边的黄熠。我喜欢她,她是我们班的大美女,也是我们班篮球的第一女粉丝。我和她关系不错,但她却偏偏暗恋上了刘瑞,我想刘瑞单挑对她是复杂的,而我喜欢她的事,世上不超过三个人知道,所以在我、黄熠还有刘瑞这似有非有的关系里,我很纠结,也许这才是我选择远远地在三楼看球的原因吧。
单挑最终以刘瑞11 比7 的优势大胜而终。刘瑞巍峙在篮下,单手高抓着球,身后的阳光把他照得像特洛伊里刚捅死赫克托尔的阿喀琉斯。在这属于我们班的胜利的晕人阳光里,我的眼睛跟丢了黄熠。
“哎……”突然背后一声叹息。我以为这教室就只有我一人,惊慌回头,见陈明幽在我身后说,“Rachel 明天就要转学走了,说是要去美国。”
“你看到黄熠了吗?”我问她,边问边转过头看向窗外。功放机里响起了朴树的《且听风吟》:
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
又怎样放开我的手
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
在深夜收紧我的心
我转过头,陈明幽没了影儿,只留我一人跟着音乐哼哼。
胜利者刘瑞在众人的拥戴下,去食堂庆功。当他知道Rachel 转学后,当晚,我们谁都没见到刘瑞。次日,他如金刚一般,浑身泛着意志的光芒,走进班来对着全班说,“我要去美国。还有,以后不许叫我刘瑞,我的名字叫做Ray。”
Ray 和Rachel 后来在美国终成眷属,他们的往事也成了这次同学会的一个焦点。在大家等待Rachel 出现的望眼欲穿里,我偷看着黄熠。十五年过去了,她瘦了,高挑了,留长了黑发,十分漂亮。有人说她做了整容,至少是微整,但这些对我都不重要。这个从中学时代我就追求未果的女人,回眸对我宛然笑了笑。面对Rachel 的到来,她眼睛里有种势在必得的泰然自若。
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知为何,从美国回来的Ray 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了。他头发稀疏了不少,身子还胖出去了至少仨。他身边的Rachel,丰满、圆润,脸上是浓浓的妆。仍旧满口英文,但她的英文听起来不如当年那么悦耳了。最精彩的,要数Rachel 和黄熠的撞衫。冤家路窄,我们私下调侃,同样是一件黑色香奈儿的成衣裙子,那左肩的商标,穿在黄熠身上就是“香奈儿”,而穿在Rachel 身上就被扯成了“背靠背”。
同学会的焦点很快又回到了我们八班的三剑客身上。那时候李枫、Ray 和我三人华丽的三角进攻和联防,一直是年级篮球联赛中最华丽的风景线。除了篮球,我们还同住一个宿舍——这里是班里欢乐的源头。有一次晚上熄灯后,我们无聊,便原创起了成人文学,以打发又一个寂寞空虚苦闷的夜晚。Ray 的行文总是很直接,器官是器官,运动是运动,不修辞,不隐晦,属于典型的“提枪上马式”。而他的故事总是千篇一律,都是以他为主角,和欧美大妞上体育课。李枫嘲笑Ray 没有境界,说更有意思的应该是自己在纸窗外,透过小孔看见自己在屋里颠鸾倒凤。而我说李枫也不够境界。最有意思的应该是自己明知道自己在屋里颠鸾倒凤,可搁着纸窗,却怎么也戳不破。
在同学会一系列的喧嚣中,唯一的遗憾是没看到陈明幽。黄熠告诉大家,陈明幽工作上出了点意外,很遗憾不能参加。要不是黄熠那晚跟我说了一件令人费解的怪事,我真不会如此遗憾陈明幽的缺席。
陈明幽的葬礼是在同学会后不久举行的。带着复杂的心情和满腔的费解,我再一次回到了骓原。回来的同学里,男多女少。大家谁也没想到再次的相聚会是如此之近。听说,陈明幽脑子里生了肿瘤,很早之前本已做了次手术,结果没摘干净,后来又失察了,再治疗的时候已过了理想期。
陈家把陈明幽的灵堂搭在了家里。遗像上的她,笑得很勉强。一番礼数过后,陈家妈妈带我们几个同学看了眼陈明幽的房间。听她说毕业后上大学的陈明幽很少回家,工作后就更少了。屋内摆设,还基本是她高中时的模样。
参加完葬礼,我们几个同学没留下吃饭,而是单独找了个地方喝酒。在大家的回忆里,陈明幽瘦瘦的,长发及腰,爱穿黑色,写一手好字。那年篮球联赛前,她在板报上题下“制霸”二字,笔力遒劲,霸字中稍稍拖长的“月”字一撇,那叫一个秀逸酣畅。
十五年前的篮球晋级联赛中,我们八班打一班。面临这个只会拼死防守然后犯规的鸡贼班级,我、李枫和Ray 平时的华丽三角进攻熄了火。焦灼的比赛让我们越发吃力,最后一刻,我们落后一分,而Ray 双手杵着膝盖,早已没了体力回防。在这最后几秒,我不知哪儿来的劲儿,有如罗德曼一般奋力一扑,把球断了回来。我用尽最后力气,胳膊放开摩天轮,一记地传送给前场的Ray。他意外得球,上篮得分,比赛就结束了。我趴在地上,虚脱地看着前场。赛点绝杀的Ray,像尊古希腊战士的雕像。而黄熠已经扑到了他的身上,她搂着Ray,亲吻着他汗湿的脖子,像极了他的女友。
那天我们班在食堂的庆功我没去,晚自习我也没去,而是撬锁进了校南偏远的室内篮球馆。我手拿篮球,走到体育馆聚光灯的开关前停了下来。我退后数步,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凭意识,抡起右手便把球向开关砸过去。灯,就这样亮了。一片白光泛起,篮球反弹回来,我左手接过,运力怒挥,又把球砸回开关。灯,就这样又灭了。在这一来一回、一明一幽中,我宣泄着,一些想不通的事终究是没想通,直到开关烂了、电灯灭了,整个学校都跳闸了。
第二天的我,挨了处分也停了课,被禁足在老师的办公室里写检查。在办公室里,我敷衍写完检查后,在物理老师桌上看到了陈明幽之前被没收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扉页上有她一手好字,“永生永世”。我翻开瞧了几十页,看似是说一个男的对一个女人一辈子的追求,冗长复杂,我是没读进去。但其中有一段浪漫的伎俩,在那天给了我新的希望。书里写到男主角阿里萨喜欢在夜晚于一个穷人墓地里拉小提琴,通过辨别风向,让自己的华尔兹传达到远方心上人的卧室。(后来,在陈明幽的葬礼上,陈家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同学看陈明幽的卧室时,我又看到了这本书,扉页上还是她写的“永生永世”,我摸了摸那字,拿起书随便一翻,书就停在了阿里萨在墓地拉小提琴的这页。那刻我想,时间也来参加了葬礼。)受那段文字的启发,被禁足的我着了迷。后来下课前我跑去走廊,感受着风的强弱与方向,把铃铛摇得精妙,希望这风声和铃声能让黄熠知道。
同学会上,黄熠告诉我:“其实陈明幽一直喜欢的人是你。她跟李枫好,只是为了接近你。”这话来得唐突,我有点措手不及,只听她又说,“青春的时候我们都很傻,明知自己喜欢的人喜欢自己朋友,自己还能将人拱手相让。你别不信。”
我一脑门子雾水,黄熠说:“不信,你回去查你的同学录,陈明幽很少留字。她全班同学里,没给任何人写同学录,就连她的男朋友李枫都没写,却唯独给了你。”
同学会后,我带着疑问和好奇飞回了温哥华。在储藏室的旧纸箱里找到了当年的同学录。看到陈明幽这页,我呆若木鸡。我从不记得她给我留过同学录,这页怎么来的,我毫无印象。短短二十余字,是个预言,在我后来的生命里,像个要让我患上斯哥德摩尔综合征的索命徒,摧剥于我又温暖于我。
陈明幽真是有一手好字。简单的个人信息下,她在祝福栏里留了一行雷光夏的歌词:
用我的美好思念,与你的过去相逢,在下一个时间。
葬礼当晚,我扶着醉得“身不由己”的李枫,慢慢走出酒吧。我想,他和陈明幽之间应该是有真感情的。李枫酒量不差,上一次见他喝成这样,还是十六年前的毕业散伙饭。那顿饭前不久,李枫和陈明幽分手了,说是因为毕业后要去别的城市,要彼此自由。因为是和平分手,两人没闹,也都来了散伙饭。那晚大家为青春干杯,都喝多了。我记得陈明幽两手各拿一瓶啤酒,跟每个男生拥抱,吹瓶子。看那豪放劲儿,我们以为她是做出来给旁边桌李枫看的。反正这是散伙饭,李枫也去厕所吐去了,所以没有一个男生不配合的。陈明幽文绉绉的,跟每个男生喝酒前还得来段儿《兰亭集序》助兴,一晚上都醉念着什么“仰观宇宙之大,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又说什么“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这样听她说着,我们干杯,拥抱,再干杯,歌以咏志。轮到我,陈明幽晃晃悠悠地拿着酒瓶走过来,双手搂着我的脖子,就像篮球赛那天黄熠搂着Ray 的脖子一样,我还以为她要亲我呢,只听两个啤酒瓶在我耳后相撞,像一记清脆的风铃。她咬着我耳朵说,“幽情,他们懂啥。”
其实在同学会与葬礼之间,我试着联系过陈明幽。用以往一贯步步为营的套路,我委婉地、不戳破地与她聊天,就像同学会上跟黄熠一般,我希望窥探她心底的秘密。可是事实证明我完全失败了。经常是几天中我给她发了好几条短信,过了好几天她才回我。每次回复,写得跟王羲之打电报一样,半白半文。刚开始这让我非常不舒服,感觉自己挨了一记下马威被示众了一样,我甚至有些恼羞成怒想干脆不聊了。但过不了多久,我又跟个奴才一样码起了试探的语言。时间在龟速的交流中慢慢过去了,我也渐渐开始学会如何用说不清的遐想来伴随漫长的等待,不知道这是填补了时间的空虚,还是让时间更加空虚。
这一切直到陈明幽死后,我才理解,她并非不想与我频繁交流,而是当时复杂的治疗,实在不得时间。如今再看那些短信,每一次回复,分明都是病情恶化中她的呕心沥血。想到这儿,我鼻子酸了,后悔这些年跟她没有联系,后悔没有去医院看她,更后悔没有直接问她。可悔憾中,当我想到在她生命最后,我俩回归到了一种带着旧时代美感的方式,往来通信,能这样陪她走完了最后一程,至少对我,是个安慰。
这几篇屈指可数的短信,我不知道在后来的日子里读了多少遍。我把这些短信逐字抄录,并尽可能模仿陈明幽的字体。试想她曾经的样子,怎样在病床上写道:
迟复为谅。犹记骓原当年,一起何等快乐。未赴同学会,可惜了。有缘再见,故园行。
眀幽亲笔
迟复为谅。纵不遇,纵不念,纵生命匆忙,深情掠影,不与左右,却存其中。就让时间孤独地在深情里,美好地凝固吧。
眀幽亲笔
迟复为谅。也许话不说穿,才经得起时光荏苒。
眀幽亲笔
迟复为谅。我近来觉得,时间如河流,生命有涯,时间无涯。生命以有涯追无涯,故不息,故有来生。
眀幽亲笔
这些短信,后来索命般地消磨我。
李枫知道我要写回忆录,找了些老照片给我。我翻着他的相册,看到那年毕业前在宿舍里的合照,上面的我俩正巧都拿着同学录。他回忆,那天我俩去小卖部逛,连同学录都买成了一样的,可惜后来,他那本丢了。
会不会我和李枫的同学录搞混了?毕竟两个本子是一样的,而且都是活页的,就算本子没搞错,陈明幽这页也可能会弄错。我冷静地分析陈明幽给我留下的文字,而每一次冷静地分析,最后都是自己与自己青春期回忆的又一次直面相遇,这是浮光掠影所设下的陷阱——自己明知自己在屋里颠鸾倒凤,隔着纸窗户,却怎么也戳不破。
知与不知的斗争,让我从疑从悲中领悟了不少智慧。可又有什么用呢?带着阴霾,我游山玩水。在欧洲的火车上,我新认识了一个文艺女青年,我想学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里的男主角一样,来一段自己翻译的奥登的诗,“在头痛与焦虑间,看不透的人生,黯晦消沉。然时间,终将拥有它的范特西,今曾与共。”
同学录上的那句“用我的美好回忆,与你的过去相逢,在下一个时间……”仍旧不舍昼夜地伴着我。我不知道这是陈明幽让我去怀念她,还是说她会以某种形式再与我相见。若不是三十年同学聚会上偶然发现的一条线索,故事可能就结束了。
毕业三十年的同学会上人少了些,除了黄熠,核心分子还是都来了。可能我们是真的老练了,大家这次见面,台面上在追忆感情,台下面却暗较劲。不知不觉,我们都成了时间的敌人,都在秀,秀一切可以拿出来证明“时间不曾打败我”的东西。比老婆、老公、孩子,比学校、房子、国籍,比晒出的幸福,比脸上的皱纹,以及自己的精气神。我真不曾想到,骓原中学是如此一个有竞争力的学校。
Ray 和Rachel 这次也回来了。Rachel 胖得像一个美国大妈。听他们聊天,我突然发现Rachel 不再说英文了。她说现在国外,会说中文的才吃香,她这样做是为了好让自己的孩子也说中文。
李枫这次带了比他小27 岁的新老婆来同学会。大家夸他老婆年轻漂亮,整得他蛮不好意的。私下,他跟我说自己的新老婆怀孕了,他算了算,等这娃娃上完大学,他都七十多了。我笑着斟了杯酒祝他健康。
再没人提起陈明幽。
散场前晚,我提早回了房间。路上偶遇Rachel,她说困了,嗨不动了。我问她孩子怎样,她说老大今年刚上大学。也是有缘,孩子去了当年自己的大学,还住进了曾经自己的宿舍楼。在那宿舍楼里有个传统,就是每学年结束,要离开的同学都会摘下墙上的镜子,在后面暗槽里留下自己的物品做纪念。当年,Rachel 刚出国,关于这个镜子还写了篇英文博客《镜子后面的秘密》。她说那时我们班的陈明幽还在博客上跟她用英文聊了好久,说要把这个传统在骓原搞起来。时间飞快,她说孩子都上大学了,博客也没了。
我万万没想到最后一个关于陈明幽的线索居然会来自Rachel。同学会结束,我便去了骓原大学。时赶暑假,一番询问后,我听得几个还没走的高年级同学说他们之前好像听说过在镜子后面放东西的传统,与其说是传统,还不如说是传说。我思索了下,便雇了个清洁公司,以义工的形式去给骓原大学提供了免费的宿舍清洁。这个公司也算麻利,几天下来,把七栋楼的宿舍挨间打扫,镜子拆了又装,满满地给我收拾出来二十多个大纸箱的物件。清洁的人说,“都是镜子后面的。”
因为这些宿舍有些年住过男生,有些年住过女生,所以镜子后面的物件杂乱无章。我像考古一样,戴着口罩和手套,寻找着陈明幽。从这些与烟、酒、性相关的纪念品里,我考证出了那个早恋如霍乱的遥远时代。当我把这些箱子翻了个底朝天后,我终于找到了一张铅笔漫画。因是碳粉画的,画幸免于褪色。上面虽没署名,但我相信,这是陈明幽的,画里是我,一个中长发男生的背影,正在用力把篮球砸向墙上的电灯开关。
我赶着周末急忙回了骓原中学。三十年过去了,曾经Ray 单挑的那个室外球场上面起了两栋新楼,不分高矮,像两个还要单挑的巨人。我花了点钱,包场并租了个篮球。
担心身体,我开始做起几组热身运动。渐渐天黑了下来。用着身体的记忆,我再次把篮球砸向远处墙上的开关。一时间,白光乍泄,新的灯真是比原来亮了好多。我觑着眼,左手接球拿稳后,振臂长啸,又把球砸了回去。就这样,灯又灭了。在这一来一回、一明一幽中,我眼睛花了,墙壁越来越远,世界是蔚蓝的,世界又是金黄的。陈明幽在对面,接过我的球,又传给我。我俩没说话,就这样一传一接,那球带着温度,时高时低,时轻时重,亦此亦彼。对面的陈明幽自然地笑了。我真的有好久都没看到她笑了。后来,我们累了。她躺在木地板上,我侧卧着帮她捋了捋头发,亲了亲她的额头,有根乌溜溜的头发黏在她额头上,格外美丽。
那晚之后,我再不曾见过陈明幽。
我最后一次回骓原,是在与陈明幽相识的半个世纪后的九个月,正赶清明刚过不久。管理人员帮我查到了她的墓,他们说联系不上这座墓的家属,若再不补上管理费,可能就要被迁走了。我连忙补上费用。他们问我,要续费多久?我说,“永生永世。”他们笑道,“这没法儿办。”
寻到她墓碑,我看到这里管理得还不错,墓碑漆黑,干净,并孤独。我弓着腰,擦了擦墓碑,烧了些纸。天渐渐暗了下来,我开了两瓶啤酒,点了根烟,把它们放在碑前。五月的晚风轻轻拂来,沉醉中,我隐约在风里又听到了那悠扬的风铃,铃声里是半个世纪前的那首老歌《且听风吟》:
突然落下的夜晚,灯火已隔世般阑珊
昨天已经去得很远,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
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又怎样放开我的手
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
咿呀,时光真疯狂,我一路执迷与匆忙
依稀悲伤,来不及遗忘,只有待风将她埋葬
咿呀,咿呀,待风将她埋葬
咿呀,咿呀,待风将她埋葬
风铃中回响的歌声,带着情绪,每过几年总会随风吹来。最后一次,是在我74 岁的时候,那时我在国外的一所社区华人学校教书。一个练《兰亭集序》字帖的小孩子问我,文中“幽情”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男女爱情?我久久不答。他追问我到底是什么?我老态龙钟地弯下腰,从柜子里找出一本古董,一本一个世纪前于1979 年最权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中国第一版《现代汉语词典》。我教他用传统的部首查字法,终于在一千三百八十一页的左下角查到了相关解释,上面写着……
幽情:深远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