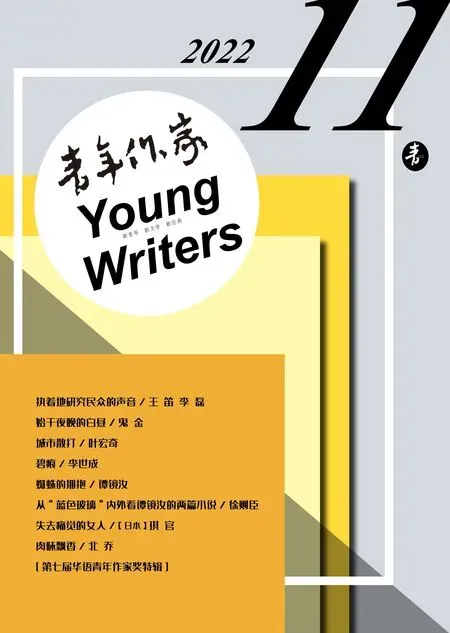银白之册
麦 阁
一
陆小曼。19 岁,花样年华,完成一生中由少女到少妇的身份转换,离开圣心学堂,遂父母之命与军人王赓结婚,没有几天便发现婚姻并不幸福,常常郁闷无处诉说。
21岁。出演《春香闹学》,结识诗人徐志摩,并与之恋爱,同年翻译意大利喜剧《海市蜃楼》。22 岁,与徐志摩的恋情升温,拜刘海粟为师,同年底与王赓离婚,当时已怀有王赓的孩子,为了能够使接下来的生活幸福得彻底一些,堕胎,从此没有机会再成为母亲。
23 岁。怀着不能再生育的极大痛苦,与徐志摩订婚、结婚(徐到死都不知道这个秘密)。与徐志摩南下上海,到浙江硖石小住,猜想这也许是她一生中相对快乐的时光。
28 岁。徐志摩飞机失事,她受尽谴责,没有人为她出来说一句,徐志摩坐邮政专机,一方面为了省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急着赶去北平,给林徽因的讲座捧场。她也不说,都按下了。痛楚的心不想多辩说一句。
30 岁。人全变了,本是得心应手的交际场中,再没见到她的身影。素颜,整理徐志摩的《眉轩琐语》,发表在《时代画报》第三卷第六期上;清明独自一人去浙江硖石给徐志摩扫墓,可这从头至尾,徐家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喜欢她接受过她。
58 岁。有一天孤单一人在上海的善钟路上散步,遇到阔别多年的老友王映霞,都已经老了。无限伤感的她对王说了这样一番话:过去的一切好像做了一场噩梦,酸甜苦辣,样样味道都尝了,如今我已戒掉了鸦片,不过母亲已经谢世了,翁瑞午另有新欢了,我又没有生男育女,孤苦伶仃,出门一个人,进门一个人,像你这样,有儿有女有丈夫,多好,多么幸福,如果志摩能活到现在,该有多好啊。
62 岁。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那一天是1965 年4 月3 日。
陆小曼,62 年的在世时光,尝尽了人间的繁华与孤独。
二
阅读的现实好处,有时不仅仅可以看别人写了什么、怎么写的,它同时还可以给我们振奋与力量,让已然有些绵软疲乏的自我,再次在阅读中感到被召唤与启迪。
感觉写作艰难,不知道写什么或写不下去时,就让自己静下心来阅读,不要硬写。时间宝贵,一个人的经历和经验必然有限,要相信,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来帮助我们聆听到自己内心更多的声音。在我的理解中,书写正是书写者倾听与记录自己心声的过程。
唯有书籍,永远给予我们实实在在的启迪。
三
面对这个世界,你不能麻木,你得投入自己的观察,观察得越专注越细微,你将越容易收获个人的发现。写下个人的发现是多么重要,甚至可以说,这简直就是你写作的意义所在。同时你也要知道,你创作时候投入的情感、心力与专注度,也会直接影响到你作品的面目——我这里所说的面目,并不是指写作水平的高低,而是说,你完成的作品一定无可避免会呈现你写作时的状态——每一个写作的人,都必须知晓并牢记这一点。
说来这个现象很神秘神奇——如何从心灵生发而来的东西,就会如何抵达心灵,这是我们应当理解的艺术的自身法则——艺术的自我恪守与尊严,恒久而毋庸置疑。
四
暗暗思忖写作中所说的天马行空。一匹神马,踩着云朵行走,那该是多么惬意与奔放、率性而自由。这个成语本身就是一种解放与异想天开。既然是这样,那么写作的人每写一篇文章,又何必还要一定去绞尽脑汁,想着在哪儿开始、哪儿结束,而不是任意开始、任意结束。老话所说的行于当行,止于当止,应该是写作中一个可取的路径——说出我们心里最想说的、最想表达的,感觉自己说完了,就收笔。以真动人,以情动人,再加上较为准确干净的语言,文章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
当我想象并尝试这样的写作,它带来的自由与快乐,令我多么欢欣和感激。我有时也会把“马”换成一只“鸟”,语言就是我写作时的翅膀,随时随地,任由我打开或是收拢,或升或降,在天空、山谷、流水间快意飞行。
五
我依然记得,小时候我在乡下,那一年弟弟七岁,我十岁。有一个刮着寒风的冬天下午,我和弟弟去山上放羊,风吹着那些草木,好像什么都在瑟瑟抖动,天气真是冷啊。我和弟弟一直在盼着太阳落山,因为父母说了,等太阳落山,就让我们牵羊回家。后来终于等到了那一刻,那一天为什么让我难忘,可能你们都无法想象,太阳几乎是在我弟弟的尖叫声中落下山去的,他叫我,哎呀哥哥,你快看,太阳在落山,太阳在落山,然后,我们就一起一言不发在风中看着太阳,飞快地移下山去。我真的在那一刻体会了什么叫作飞快,因为就是刚刚还在眼前的太阳,你能看得到它在下沉,然后转眼间就不见了。实在太让人难忘。
我从讲述者的眼睛里,仿佛也身临其境,看到了那一天的太阳飞快落山的一幕。他亲眼所见飞快消失的落日让他惊悚,难以忘怀。从他的讲述里,我也再次暗自在内心对时间的流逝之快感到微微恐惧。
每一刻来临的、逝去的,都是唯一,都永不再来。
六
写作是一个人的事,也只能是一个人的事。试想,纳博科夫写《说吧,记忆》、写《洛丽塔》之时,他俯身案前,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奇怪,我为什么脑海里冒出来的是他,如果是其他作家,不是也一样吗)。但当他一旦写完,作品面世,就不再是他一个人的事了。
对于写作,纳博科夫曾说,无论现代还是古典,优异的文学其实只有一个流派,就是天才派。是的,其实文学艺术与其他门类的艺术一样,都是为天才而诞生、由天才来完成的事业,不是天赋异禀的人算不上天才。艺术事业,仅靠后天的努力是没有用的,不过话说回来,光有天分、不付出后天努力也是同样没有用的。艺术就是这样一项既需要天才又离不开后天努力的不朽事业。
七
在时间里活过,倾斜是危险的,而平衡显得多么重要。于我,写作可以帮我达到这种内在的平衡。真心热爱并从事着,就是意义。很多时候,完全可以不必去想何谓“成就”,唯独享受阅读、书写的过程,就是价值。
八
诗歌于我,是一件既痛苦又幸福的事。我所写的文字,最先被变成铅字发表的是诗歌。我曾经想,诗歌像什么呢,后来我觉得,它像爱。因为只有爱,是让人又幸福又痛苦的,它带着神秘,你不知道是在什么时间地点,你发现它时它就已经存在了,但你又看不到也摸不到,那只能用心灵去感知的东西,无用却又美好。无论如何,它是美好的。有人说,美好本身就是用处。
我所理解的诗歌与爱相像,还有一层意思是说,它们都不是寻觅,而是可遇不可求;它们也从不强行给予。放到诗歌中,就是我们所说的不能硬写,就像爱所说的,强扭的瓜不甜,所以还是要“有感觉”,这样写出的诗,才会在文字以外生发诗意,给人回味。我以为,作为一个热爱诗歌的人,如果最深沉最纯真的感情不在诗歌里安放,那么便无处安放,这样的话,不写诗也罢。
好的诗歌写作应该是抒写者与她生命热力的深度相融,应该是一个生命在聆听自我心声以后的深情回应。诗歌写作最需要独到的发现,独行的姿态。
九
我一直这样理解,作家和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应该是他更关注精神与情感层面的东西,至少要比一般人脱俗与懂得悲悯。文学是人学,同时它永远是艺术,它应该是一种高于倾诉的表达,它一定可以稀释苦难,对抗人性里的恶与灰暗,唤起人心的温暖与善良,给心灵以慰藉、美好。文学是善,文学是美,文学是痛。
十
文学是艺术、是想象、是还原与呈现,并给不出具体的评判与结果。由此,你的叙述从哪儿都可以开始,结束也是,什么都可以是开头或结尾。
艺术到高境界应当是自由。导演阿巴斯在讨论电影时曾说,一部电影,如果越是忠于拥有开头、中间和结尾,我就会越抗拒。他说的是电影,电影用镜头讲述,文学用文字讲述,其法则是同样的。
十一
我最早接触外国诗歌的经历,至今都让我骄傲。那时的我还在江南小城宜兴的城郊生活,在县城新华书店,我十几岁的年纪,在那里被诗歌深深吸引,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分行的表述,我喜欢上了诗歌。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本橘黄色封面的《萨福抒情诗选》。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萨福是谁,《萨福抒情诗选》——打开第一页,在译序里,我看到:萨福是古代希腊抒情女诗人……记得当时,仅仅是因为这一句,我立即就在心里决定买下它了……对翻译过来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说,诗歌就是那个翻译的过程中流失的部分。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去看翻译过来的东西,我个人理解,因为每个人写下来的东西,都沾着自己的热血,是每一个书写者自己的发现、哭声或微笑,只属于他自己,那是他的呼吸与气息,像血型与胎记无法更改……基于此,读的过程,翻译当然是有好坏的,但无论怎样,我们也还是会搭到书写者的脉搏,可以辨别、倾听到他的灵魂与心跳……
十二
沉寂二字,沉是沉下心来,寂即静,在寂静中,或许我们可以发现更好的自己,更好地听到自我的心声。而写作,不正是记录个体生命心声的一件事吗?我这样理解,一个写作者在写作之时,是一个生命同时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安放肉身的外部世界,是形,在喧闹的世俗之声里;另一个,是他的内部宇宙。写作的一刻,在喧闹世俗之声里的那个形俯首案前,面向内心,拥有一个安静而又迷人的隐秘世界……那些即将要被他书写的东西是他内心的纷纷火焰,将它们捉来凝固到纸上的过程,多么让他激动、幸福,他全神贯注,一言不发,全力以赴……如果你自写作以来从来不曾体会过这些,那么我只能说,你对写作还不够由衷热爱。英国作家伍尔芙说:我写得好时,连忧郁都减弱了。由此看来,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已经选择了以读书和书写度时的人,就该自觉地与那份沉寂牵手,少说空话,多读多思多写,在沉寂中,写作就是你的通道与出口,可以成就你、治愈你。
十三
发硬的塑料封面上端,是两枝黑茎绿叶的荷,荷下方是三四条游荡的鱼,每条鱼的嘴边都吐着一个圆圆的水泡,可爱至极。黑色的字样是:上海日记。这是我的红色笔记簿的外观。显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所理解的人性情怀:温暖,向上,平和而又清澈。
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红色笔记簿留住了我遥远往日的稚嫩手迹。内容有我当年在有限的阅读中摘抄的篇章——有诗歌,有名人名言等等,都是那时的我所认可的;还有就是我生活与心情的一些片段,所以,我只能称它是红色笔记簿,而非纯粹日记本。
从抽屉里翻出它来,仿佛感觉是再次翻出自己十几岁的年纪,那些命运所给予我的青涩、挣扎、如梦的时光。
这些记录同时使我知道,自己对于文字的热爱,是那么早就开始的事。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所写作文每次都会被老师作为范本,在全班朗读。每次这样的时候,我的心情会有些害羞,但也总是喜悦而又兴奋。那是文字带给我的最初诱惑与快乐。
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是在1994 年左右。所写内容正是从我的红色笔记簿中得到启发。第一次在文学期刊上得以发表也是在那会儿。这时我才发现,曾经亲手写下的点点滴滴,已然融入了我的生命与血液,只要我稍做呼唤,它们便会蜂拥而来。我想,一个写作的人,首先是听从自己的内心,最初写下的,也总是自己的生活。
十四
我尝试着这样来记录写作时的感觉:我的身体犹如旷野,有时荒芜,有时馥郁。每当感觉荒芜的时候,我就什么也不想写,也写不出;反之,当感觉自己馥郁的时候,我则感觉心里“枝繁叶茂”,似有“花开”,甚至有鸟儿飞来喳喳啾啾,还可以听得到溪流水声潺潺……这种时候,就会清晰感觉到自己想写,通过文字,与时间擦肩而过,感知自己……
十五
真诚、认真的人才有可能是生动而吸引人的,文章亦是如此。
面对文学与书写,只有自己整个身心投入了,确信了,然后再把这种投入与确信传递给他人,那么从心灵到心灵,这种传递一定是具有意义和感染力的。
十六
于我个人,看书和翻书是有区别的。看书是要一字一句看仔细的,翻书就可以比较随意。今天是在翻书,从手上翻过的书有如下:
《一份私人档案——劳伦斯和两个女人》。也许是因为劳伦斯写下的文字大多与性有关,在家乡,他早年曾被贬为“地摊作家”,多年以后,骂名消失。在英国某处小径的岔路口,如今有着这样一块指示路牌,上面写着:注意,这里通往D·H·劳伦斯的故乡。是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对于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从他的肉身里流出了什么样的文字,最终贡献了什么样的艺术与文本。至于其他,到了终极,或许都不是最重要?
《独影自命》。扉页上,川端康成的特写照片,枯空的白发,光线照得进的丝丝缕缕,双眸的紧张、犹疑与莫名的警醒和惊恐。《独影自命》只是《川端康成文集》十卷本中的一卷。也许,有时买一本书,理由仅仅只是因为一张封页、一个眼神。
《从未描述过的梦境》。残雪的短篇小说全集。“某种深层次的东西力量要强大得多。”这个一只口袋里装着别人衣服尺码的裁缝作家一直都是那样自信。她常常用貌似远离人间的文字,为我搭建一条幽秘通道,只要我愿意侧身穿越其中,就会感受她带给我飞越常态的片刻体验。许多年,一直都喜欢着她的小说与一些相关理论,自觉地阅读她,有时并说不出多少足够的理由,仅仅是单纯喜欢与认可,喜欢她叙述的飞翔式自由,认可她的看似怪诞与匪夷所思……
十七
听孟庭苇唱《往事》。
“如梦如烟的往事,洋溢着欢笑,那门前可爱的小河流,依然轻唱老歌;如梦如烟的往事,散发着芬芳,那门前美丽的蝴蝶花,依然一样盛开。小河流我愿待在你身旁,听你唱永恒的歌声,让我在回忆中寻找往日,那戴着蝴蝶花的小女孩。”
记下这首歌的全部歌词,只是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心绪复杂。我从那里倾听自己的心声,穿过歌声我看到遥远童年的那些夏日,那毒日头下自己的孤单影子。
这是一支与我的童年紧紧相连的歌。
十八
阅读、思想、写作,对于这三者,这样的排列是经过我思考的。
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是一个有一定深度的思想家。不然,他的作品就会缺乏深度,也不会走得远。
思想的深度必然与一个人的学养有关。阅读让我们更多认识自己,让我们有话要说。写作,就是呈现自己的思想。
学问的深浅又可以决定一个人思想的深浅,由此再来看,学问与思想也是读书的条件——用已有的学问与思想来伴随阅读,而阅读又可以帮助我们不断累积学问与思想。
只要有兴趣与热爱在,慢慢来,从可理解的书开始读起,从写自身周围所见所遇开始写起,由简入难,由低到高。
中国还有一句谚语:不怕慢,只怕站。阅读、思想与写作,都可以积跬步,至千里。
十九
一个作家的作品要有个人面目、独特个性与辨识度。
拥有辨识度的文字,一定关联着写作者的生命质地。与写作者自身命运息息相关,连接着他的血地、童年与少年,他的成长环境。书写者自己无从选择,这是他命定要写下的那一份。就像一个女人刚生完第一个孩子,身体里自然生成的奶水,不言而喻的浓度与纯度,无从更改。
二十
写作的人在一起,就像是很多人在一起走路,而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
别总是看别人怎么走路,而忘记迈好自己的步伐,也不要觉得别人走路姿势好看,就去模仿。
归根结底,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想写的,找到自己的“走路”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