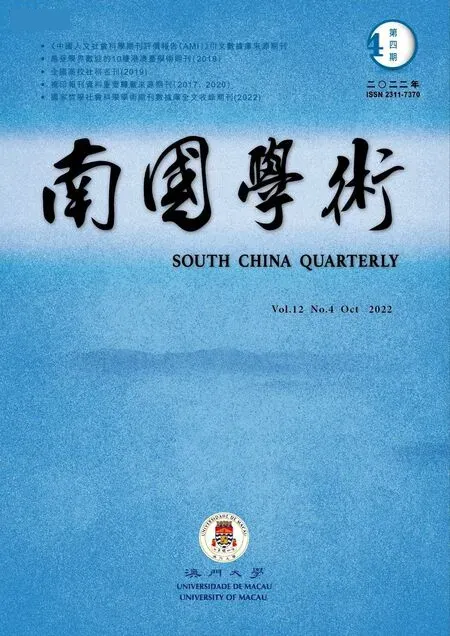一個被忽略了的話題:哲學始於驚異
戴茂堂
[關鍵詞]驚異 相通 自我意識 普遍性 張力
在今天的中國哲學界,人們耳熟能詳、記憶猶新甚至奉爲圭臬的話題不可謂不多,如“哲學是世界觀”“哲學是關於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一般規律的科學”“哲學的基本問題是物質和意識的關係問題”“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運動是有規律的”等等。在這些話題下,許多研究者把哲學“做成了”一堆抽象無比且神乎其神的概念,似乎怎麽說、說什麽,都可以與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了無關聯。①張世英說:“自柏拉圖到黑格爾,在西方哲學史上佔統治地位的這種概念哲學儘管與西方科學的繁榮發達有密切聯繫,但它又的確把哲學變成了蒼白無力、抽象乏味的東西,把人生引向枯燥而無意義的境地。”“驚異終止了,新奇也就結束了,世界衹是‘散文式’的,人們最終能達到的衹是一些表達客體之本質的抽象概念,就像黑格爾的由一系列邏輯概念構成的‘陰影王國’。哲學成了(除了在開端之外)遠離驚異、新奇和詩意的枯燥乏味、蒼白無力、脫離現實的代名詞。”〔張世英:《哲學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導言”第5、133頁。〕而那些不“做”哲學的人,似乎也産生一種錯覺或誤解,即認定生活於其中的“世界”可以與自身無關,也可以與哲學無關——沒有哲學,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照樣可以自行其是、自然而然地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成爲客觀對象物即客體,而人則成爲與客體對立的主體。這就是通常所說的主客二分。由於“世界”出了問題,成爲“客體”;哲學出了問題,成爲“冷門”,因此,事到如今,“做”哲學的人還要爲已經“存活了”幾千年的哲學的合法性給予證明,還在繼續爭辯哲學究竟是“有用”還是“無用”。
與那些耳熟能詳的話題相比,“哲學始於驚異”這一古老的話題卻沒有在哲學人中產生那麽多的記憶、那麽大的興趣。其實,這一古老話題擁有許許多多重要的思想信息,包含了真正的哲學秘密,甚至構成了人們反思和檢討乃至詮釋哲學諸多其他話題的絕佳“鏡子”和“武器”。重新拾起這一古老的話題,可以縮小人與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的距離、重建哲學與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的聯繫。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要去從事哲學的專門研究,但每個人與哲學都脫不了干係。衹有在承認哲學與生活其中的“世界”是相互關聯的前提下,哲學、人與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纔能回歸自身,纔能是其所是。
一 如何理解哲學“始於”驚異之“始於”?
“某某事情始於~~”這種句式,多是用來表達某某事情“始於”什麽時候,“始於”後面跟出來的是時間。例如,鴉片戰爭始於1840年。這個時候,“始於”指的是“從某個時間開始”。“哲學始於驚異”這個話題在字面表述上有些特別、奇特,“始於”後面跟出來的是“驚異”這個詞。“驚異”這個詞顯然不是用來標示時間的。這就如同說“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足下”這個詞顯然也不是用來標示時間的。所以,“哲學始於驚異”也不是想從定量角度或者時間維度討論哲學“從某個時間開始”,而是從定性的角度、邏輯的維度標畫或指明做哲學應該持有什麽態度、什麽立場。具體而言,“哲學始於驚異”這一話題表明,做哲學研究的人要有驚異感,即對這個世界的差異性的驚訝感或敏銳感。
“感”是一種內心態度、一種內在立場。驚異感描畫出的是做哲學的狀態、樣子甚至標誌——有對世界的驚異(感)或好奇(心)。衹有如此,纔能稱得上是在做哲學的研究。換言之,有無驚異(感)或好奇(心)是判斷有沒有、能不能、算不算甚至適合不適合做哲學的重要標準。鄧曉芒認爲:“驚異是一種超功利的興趣,具有精神上的超越性,它所激發的是一種純粹的‘愛’的追求。什麽是‘愛’?這是一種生命力的衝動,是生命對精神生活的一種向上的追求。”②鄧曉芒:“哲學起源於‘驚異’”,《愛思想網·專欄作者·鄧曉芒》2021-02-25。即哲學是超經驗的、純粹的精神性反思,也就是常說的“對智慧的愛”。田海平也認爲:“驚異是一種天真純樸的心靈狀態,它穿透一切爲人熟視無睹的事物的外表,將人從一種自然狀態或者日常性的漠視與遲鈍狀態中喚醒,去關注那遠大未思之物。哲學家的愛智慧如果缺少驚異,根本是不可想象的。驚異是未泯的童心,是思的開啓,是詩意的根源,是愛智慧成爲‘問題’的契機。”③田海平:《哲學入門——將愛智慧進行到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第21頁。趙汀陽則對哲學的純粹性給了一個解釋:“哲學的純粹性並不在於把思想表達爲無用的語言遊戲,這兩者並不必然聯繫。哲學的純粹性衹在於反思性。所謂反思,在於建構思想的‘元’(meta)層次,思想進入元層次,就超越了現實經驗,也就具有純粹性了。”①趙汀陽:“純粹哲學有多純粹”,《中國社會科學評價》3(2019):7。從根本上說,做哲學的狀態、樣子,是不能定量地去刻畫、描述的。做哲學與效用考量、理性算計無關,衹與對世界的驚異(感)或好奇(心)有關。歷史上,柏拉圖最早把哲學、哲學家與“thaumazein”(驚異、疑惑)聯繫在一起,他在《泰阿泰德篇》中說道:“疑惑感(thaumazein)是哲學家的一個重要標誌。”②[古希臘]柏拉圖:《柏拉圖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王曉朝 譯,第2卷,第670頁。亞里士多德也說過:“由於驚異,人們纔開始哲學思考。”③[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吳壽彭 譯,第5頁。
討論“哲學始於驚異”這一話題,很容易被誤導爲另一種情況,即這一話題字面上的表述好像衹是從時間上強調,驚異屬於哲學的開端,做哲學一開始要有驚異感。其實不然。驚異感應該是始終如一的堅守,一直貫徹到底的。一個人如果沒有驚異感、疑惑感,一開始就不能做哲學,以後也不適合做哲學。因爲,他已經丟棄了、失去了做哲學的標誌、資格和身份。也正是從這樣的理解出發,“哲學始於驚異”這一話題,不是說做哲學一開始要有驚異感、疑惑感,以後就不需要、可有可無了。哲學與世界究竟能不能夠建立起關聯,與有沒有始終如一的驚異感有關。從根本上講,哲學注定與令人驚異的東西“糾纏”在一起,脫不了關係。可見,這裏的“始”不能理解爲時間上開始的“始”,而應該理解爲邏輯上始終的“始”。在這個意義上,說“哲學始於驚異”,但“驚異”不能“止於開始”。如果準確地表述,應該說:“哲學始終相關於驚異。”也就是說,哲學在哪裏,驚異就在哪裏,驚異應該貫穿於哲學和哲學家的始終。驚異是哲學的“本”和“根”。哲學越本真,越令人驚異。哲學本質上就是指向驚異的,驚異感伴隨哲學從開端(過去)到現在直至將來的全過程,永不停息。張世英認爲:“說哲學開始於驚異,意思是:哲學本質上就是某種令人驚異的東西,而且哲學越成爲它之所是,它就越令人驚異。”④張世英:《哲學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第135頁。如此說來,“哲學”與“驚異”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指明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爲“驚異”不僅標識了哲學的誕生,而且也是理解世界、理解人、理解世界與人的關係的出發點和入口,包容、統攝了真正的哲學秘密。
之所以特別強調驚異貫穿哲學的“始終”,也是考慮到在柏拉圖之後,哲學發生了對“驚異”的遺忘。哲學誤以爲,驚異衹存在於哲學的開端,隨後哲學的目的似乎超出了驚異。哲學便以完成對世界的本質和本原的認識爲目的,不再需要驚異,不再秉持與驚異的緊密關聯了。⑤張世英:“談驚異——哲學的開端與目的”,《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1996):37、38。哲學前行的過程,似乎就是遠離驚異的過程,“推動知識前進的,不是驚異,而是否定性的力量”⑥John Sallis, Double Truth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 196.。如果說,在哲學剛剛開始的時候,“驚異”意味着從沒有自我意識狀態中驚醒,那麽,到了真正的驚醒狀態如精神的自我發展狀態則不屬於驚異,哲學與驚異也就很遺憾地漸行漸遠了。其實,人在世上從主客不分、沒有自我意識進展到主客二分、擁有自我意識會産生驚異,從主客二分進展到超主客二分即高級的天人合一同樣會産生驚異。⑦張世英:“談驚異——哲學的開端與目的”,《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1996):37、38。今天的哲學爲什麽不能建立起與生活其中的世界的緊密聯繫,爲什麽常常陷入那種抽象、枯燥的概念之中,很大程度上應歸咎於驚異從哲學中隱退了,歸咎於對驚異與哲學始終如一的關聯性沒有牢固的堅守和信奉。
二 如何理解“驚異”之“異”?
人們常常用“驚訝”來替換“驚異”,覺得“驚異”與“驚訝”大同小異。但在哲學視域中,相比於“驚訝”,“驚異”這個概念更好。因爲,“驚異”除了保留了“驚訝”之意外,還新增和突出了一個“異”。如果說,“驚異”的“驚”指的是“驚訝”“驚嘆”,那麽,驚異的“異”指的是“差異”“異樣”。對“差異”“異樣”的新增和突出,對於更好地詮釋“哲學始於驚異”這一命題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原因在於,在人類生活於其中的“世界”,差異性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在很多層面體現出來。
從自然界本身來看,萬事萬物互有差異。赫拉克利特說,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爲什麽?因爲既然是“兩”次,它們就不可能相同,不可能是“一”。萊布尼茨說,世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爲什麽?因爲既然是“兩”片樹葉,它們就不可能相同,不可能是“一”。赫拉克利特、萊布尼茨這兩位生活在不同時空的哲學家表達了一個相似的道理,那就是,萬事萬物彼此不同、互有差異。衹要你願意,萬事萬物之間的差異可以無窮、無限列舉下去。如果說,河流與河流之間、樹葉與樹葉之間,彼此的差異是相對的,比較隱蔽,不那麽直接,不那麽直觀,那麽,河流與樹葉之間,彼此的差異就比較絕對、比較顯明、比較直接、比較直觀了。由於自然界萬事萬物之間的差異多是看得見,摸得着的,所以,這裏的差異,更多是從事實上講的。
在人世間,同樣也充滿差異、互不相同。每一個人僅從外貌特徵上考察就互有差異。如白人與黑人、老人與小孩、原始人與現代人、男性與女性等等。如果進一步從文化信念、生活習慣上去考察,即便外貌特徵很接近,依然可以發現他們彼此之間的巨大差異。例如,同樣都是小孩,小孩甲可能很喜歡神話故事,小孩乙可能很喜歡電子遊戲,小孩丙可能神話故事和電子遊戲都不喜歡。這種愛好的差異不以實然的方式存在,在人的身上看不見摸不着,但卻確實存在。存在於何處呢?存在於甲、乙、丙的心底裏。由於心底裏的差異折射出來的是觀念差異、精神差異、思想差異,顯然,這裏的差異是從價值上說的。
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個世界最直觀、最絕對,當然也最複雜、最微妙的差異是人世間與自然界之間的差異。當人們強調這種差異的絕對性的時候,實際上是因爲已經明白,人世間與自然界的差異是兩個不同系列之間的差異,具有不可比擬性。這就像價值與事實的二分一樣。當人們使用“價值”與“事實”這兩個不同的語言概念去說明人世間與自然界無處不在的差異的時候,就已經默認了這種差異的絕對性。初步來看,差異性是世界的真相。沒有差異性的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不可想象。離開了差異,沒有差異,就沒有一切,沒有世界。而驚異之“異”,指的就是世界的這種差異。
三 如何理解“哲學始於驚異”之“驚異”?
人類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特別有趣、特別神奇的是這種“差異”具有重要的積極性。河流成其爲河流,樹葉成其爲樹葉,馬成其爲馬,牛成其爲牛,靠的是彼此的差異。就像白天不同於黑夜一樣,也就是因爲這種差異,白天纔成其爲白天,黑夜纔成其爲黑夜。可以推測,假若世上萬物之間沒有差異,萬物之間也就不能形成邊界,一個事物無法區別於其他事物,並最終成其爲自身。正是事物的差異,成就了世上的萬事萬物。由此可見,世界的差異不僅存在,而且需要存在、必須存在。這一點太真切不過了。
這種差異的積極性,在人世間更是突出。你與我不同,我與他不同,因此都非常神奇地成爲自己。常言道,你要成爲你自己,其實就是成爲與我不同的人、與衆不同的人,成爲與別人有差異的、獨立的自己。人是開放的、指向未來的、不可確定的。正因爲人與人互有差異,纔可以說,每個人都是奇跡。每個人都應當得到尊重的最高哲學理由,也因爲每個人互有差異,每個人都是奇跡。人奇跡般存在着,導致無法給人一勞永逸地下出定義來,導致人無法被先天規定。如果非要給人下出定義來,那衹能勉爲其難地說,人的定義就是不可定義。因爲,在自由意志的帶動下不斷地創造,就是人的本性。“人之爲人就在於他的不可規定性和無限可能性。人就是、必然是、並且永遠應當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東西,即‘奇跡’。人的本性就在於創造。人將要怎樣創造自己,這是誰也預料不到的,人不能憑藉自己天生的‘性’而對自己高枕無憂,而必須隨時提防自己、警惕自己,畏自己。”①鄧曉芒:《新批判主義》(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第166、338頁。你爲什麽恰恰是你?他爲什麽恰恰是他?這樣的問題永遠也給不出實證性的答案。如果非要作出回應,那回應也衹能是:也許,衹有給不出實證性的答案,你和他纔能作爲奇跡,與其他人一樣得到平等的對待和尊重。他恰好是他,你恰好是你,體現的正是人的不可置換的奇跡。這種奇跡反過來又會不斷喚醒人的驚異感或好奇心,喚醒哲學純粹的精神性反思。
由此可見,“驚異”說的就是萬事萬物不僅彼此存在差異,而且恰恰是這差異(及其表現出來的唯一性)使得萬事萬物彼此形成邊界、成爲自身。這實在是令人驚訝、令人驚喜、令人驚嘆。值得一提的是,産生驚訝、驚喜、驚嘆的原因就在於——萬事萬物之間的差異(及其表現出來的唯一性)恰好使萬事萬物成其爲自身。可見,“驚異”第一層含義就是:“驚”於“異”,即爲“異”所驚、因“異”而驚。這是一個被動式。“異”是“驚”的原因,“驚”是“異”的結果。差異居然具有如此神奇的力量,敏銳的哲學家能不驚訝嗎?始於驚異的哲學對於世界能熟視無睹嗎?
深入考察還會發現,差異不僅使單個的事物成其爲自身,而且成全了彼此的完滿和整全。如果世界是差異性的,而差異性的世界如果沒有相通性,那麽就會導致世界的孤單化、碎片化;並且,如果世界沒有統一性,世界的差異性很容易衍生出對立、對抗來;而衹要有對立、對抗,雙方要麽同歸於盡、要麽一方消滅另一方;最後的結局一定是,任何事物都不能成爲自身。因此,既要強調世界是差異的,還要強調世界是統一的;既要承認世界是差異性的,又要承認世界不同而相通。這是世界的深刻張力。這就像黑夜與白天不同,但黑夜與白天不同而相通,並且依賴這種相通,纔形成了完整的、圓滿的一天。一個衹有白天或一個衹有黑夜的世界都是不可想象的。一個衹有老師或一個衹有學生的大學也是不可想象的。正是老師與學生的差異,纔保證了學校成其爲學校,教育成爲可能。在學校中,互有差異的老師和學生獲得了統一性。一個衹有男性或一個衹有女性的世界同樣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男性與女性的差異,纔有了人類的綿延不盡的歷史,纔保證了婚姻成其爲婚姻、家庭成其爲家庭。在家庭中,男性與女性獲得了統一性。
人類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不同而相通,差異而同一。“同”與“異”之間神奇般地相通着。“一切東西之所以是同一的,是因爲它們都是有差別的,它們同樣有差別,在相互有差別這點上是同一的。”②鄧曉芒:《新批判主義》(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第166、338頁。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差異律就是同一律。惟其如此,纔會有世界的和諧、完整和圓滿。這一切就像硬幣的正反面,彼此不同,但又彼此成就。相比於差異性使得萬事萬物各自成爲自身所引起的驚異而言,差異性背後不同而相通所隱藏着的統一性更是令人驚異的!可見,更深的驚訝、更大的驚嘆緣於萬物“差異”的背後居然有“統一”的力量,顯示了差異更大的魔力。所以,對於“驚異”第二層次理解,應該是“驚”於“異而不異”。深刻地看,異而不異更是世界的本相。“異而不異”是“驚”的原因,“驚”是“異而不異”的結果。
四 驚異始於自我意識的覺醒
哲學始於驚異,那驚異從哪裏來?驚異感如何被喚醒?生物包括動物說不出“我”字,沒有自我意識,也不能區別出萬事萬物。當然,也沒有驚異感。自我意識其實就是“我”作爲人開始有能力把“自我”與“非我”區分開來的時刻。黑格爾說:“人如果還沒有驚奇感,他就還是處於蒙昧狀態,對事物不發生興趣,沒有什麽事物是爲他而存在的,因爲他還不能把自己和客觀世界以及其中事物分別開來。”③[德]黑格爾:《美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朱光潛 譯,第2卷,第22頁。在這個意義上說,自我意識就是差異意識,自我意識就是對差異的發現、敏感、驚嘆、驚訝。所以,說到“驚異”,免不了會追溯到自我意識上來。驚異本來就始於自我意識的建立。假如沒有自我意識的覺醒,恐怕也就不會有“哲學始於驚異”之說。
當人意識到自己是“我”、獨立的人、與其他不同的“我”的時候,他也就開始與非我劃清界限。沒有自我意識之前,人與世界之間混沌一片。有了自我意識,人就開始用理性之光照亮模糊不清的世界,突破原始的還沒有建立起個體意識、主體意識的主客不分。自我意識是對混沌一片和模糊不清的世界的“中斷”和“懸隔”。“人能夠具有‘自我’的觀念,這使人無限地提升到地球上一切其他有生命的存在物之上。”①[德] 康德:《實用人類學》(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鄧曉芒 譯,第1頁。“平常我們使用這個‘我’字,最初漫不覺其重要,衹有在哲學的反思裏,纔將‘我’當作一個考察的對象。在‘我’裏面,我們纔有完全純粹的思想出現。動物就不能說出一個‘我’字。衹有人纔能說‘我’,因爲衹有人纔有思維。”②[德] 黑格爾:《小邏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賀麟 譯,第82頁。人衹有事先擁有了自我意識,然後纔能在我與對象之間拉開無限遠的距離,纔能發現我是我,是獨立的個體,不是對象,纔能發現彼此的差異,纔能“觀”世界,纔能在把人與世界當成是相互區別的主體與客體的前提下,再把人與世界的關係問題確定爲哲學的基本問題。
西方哲學裏有一個影響巨大的“原罪”論。在《聖經·舊約》中有一個論述,那就是,人不配吃“知識之樹”的果實,那是上帝的專利。人類的祖先僭越了上帝的這一禁令,從此就犯下了原罪。以往的“原罪”論過多關注“原罪”直接牽涉出的人性之善惡的討論,而對於“原罪”背後隱藏的自我意識之覺醒卻缺少深入揭示。“原罪”帶來人的局限,帶來了人的罪性,帶來了墮落的痛苦、道德的淪喪,帶來死亡、暴力和欺詐,帶來了人永遠的、艱辛的贖罪,帶來了一切負面的、糟糕的東西,但這種“原罪”觀背後卻暗示出一條具有絕對積極意義的思想和主張,那就是肯定了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
從自我意識的角度看,所謂原罪,就是人從與自然混沌一片的狀態中覺醒了,驚喜地發現自己是人而不是自然,從而有能力與自然拉開距離,打破自然的圓融性,甚至褻瀆自然,向人的自然狀態發起挑戰。偷吃禁果不會發生在沒有自我意識的任何東西身上。因此,從本質上看,“原罪”必將帶來人與自然的分裂和對立。“原罪”衹能是在人驚訝地發現自己與世間的萬事萬物存有差異的前提下纔能發生。根本上說,“原罪”就是人的自我意識和自由意志的覺醒帶來的“果實”;同時,自我意識和自由意志的覺醒反過來又強化了“原罪”觀,似乎成爲原罪的“果實”。顯然,這兩個方面是相互循環、相互論證、相互支持的。在這裏,人們最爲關切的是有了自我意識和自由意志,就有了行善或作惡的可能。在這個意義上看,人有“原罪”,不是對人的貶低,而是對人的尊重。人有了“原罪”,人就高貴了。動物、植物都不可能犯罪,因它是由自然規律所決定的,沒有自我意識。“原罪”帶來的一切負面的、糟糕的東西,衹不過是人類前行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曲折,付出的“必要的代價”。從這種積極的理解出發,“原罪”更像是一個標簽,標識並且代表了人有了自我意識、有了自由意志,有了對差異的敏感。在這個意義上講,如果說,哲學始於“驚異”的話,那麽,驚異始於“自我意識的覺醒”。人如果沒有自我意識的覺醒,就不能産生驚異感。而人如果沒有自我意識的覺醒,進而沒有驚異感或好奇心,是不能做哲學的。
五 哲學的使命: 尋找“差異”與“普遍”的張力
沒有差異就無從鑒別。但如果衹有差異,世界上就沒有了溝通。所以,差異不能是漫無邊際的。不應誇大這種差異。而片面的自我意識,往往會走向對差異的誇大,進而走向對他者意識的疏忽。衹有自我意識,沒有公共意識,將會面臨偶然性和不確定性帶來的巨大困境。所以,一方面需要喚醒自我意識,另一方面又需要建立起他者意識,包括對他人的自我意識的接受和吸納。衹有如此,差異性纔與普遍性貫通,自我意識纔與公共意識貫通。最理想的狀態應當是,在差異性中呈現出普遍性,在普遍性中容納差異性,使差異性和普遍性總是處於一種彼此認同與接納的張力關係之中。在這種張力關係中,萬事萬物反而能更好地呈現自己的特殊性,並真正成其爲自身。
由此可見,差異性與普遍性並不是相互排斥、彼此對抗的①戴茂堂、葛夢喆:“論哲學的普遍性面向”,《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2021):83。。哲學的使命正在於,平衡差異性與統一性、自我意識與公共意識之間可能引發的緊張乃至衝突,尋找差異性與普遍性、自我意識與公共意識之間必要的張力。差異性與普遍性之間本沒有一道絕對的縫隙或裂口,“哲學之爲哲學,或者說嚴格意義下的哲學,乃是源於對世界整體性把握這樣一種最大最高的普遍性問題的驚異。或者倒過來說也一樣,有了對這種普遍性問題的驚異、好奇,就意味着哲學問題的提出和哲學的産生”②張世英:《哲學導論》,“導言”第2頁。,從而將哲學因始於驚異而産生的對差異性的關切與哲學面向普遍完美整合在一起。
長期以來,哲學界將普遍性等同於“絕對”、將差異性等同於“相對”,人爲地設置了普遍性與差異性的二元分裂,結果是找不到自我意識與公共意識之間的張力,最終使得哲學始於驚異也成爲一個可疑的話題。爲了重拾這一話題,並破解這一話題底下隱藏的哲學秘密,至關重要的環節就是解除差異性與普遍性之間的對抗,感受自我意識與公共意識之間的張力。而做好這一切的前提和核心,就是區分出兩種普遍性。
第一種是客觀普遍性。比如,墻面是白色的、黑板是黑色的,不允許黑白顛倒。黑與白是可以通過科學的手段檢測出來的。如果誰有不同的、差異性的看法,那就衹能推斷他是色盲。這是一個事實判斷。在這裏,墻面是什麽顔色,不是針對單個人發問,更不認可每個人站在自己的角度來給予回答。也就是說,不認可每個人支配問題本身,答案不隨着每個人的經驗而走。因爲,每個人的經驗千差萬別,如果答案隨着經驗走的話,必然會産生出漫無邊際的差異來。這種差異性反過來就會消解具有普遍性的答案本身。爲了追求客觀的普遍性,必須走向對差異性的放棄。對於墻面的顔色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可以表達個別性意見,也不允許兩個不同的回答同時爲真、同時存在。如果出現不同的答案或結論,那就必須展開爭辯,直至達成或取得普遍性共識。這樣的普遍性,實際上就是常說的客觀普遍性。很明顯,客觀普遍性是排斥差異性的。
客觀普遍性在方法論上是以心物對立、主客相分之設定爲前提的。這是一種獨斷論。在這個世界上,永遠不可能心物二分,永遠找不到主觀跟客觀相分開的東西,就像永遠想象不出沒有兩面的一枚硬幣一樣。所以,主客二分永遠衹是一個武斷的假設。然而,科學卻依賴這樣的假設。科學相信,人與自然(物)是一種彼此外在、主客二分的關係,自然在人面前是被分析、被征服的對象,人在自然面前是積極能動的主體。作爲認識者的主體與作爲被認識對象的客體彼此外在。這種主客關係思維模式是一種對象性思維方式。其基本特徵在於,把主體與客體看成是兩個彼此外在、相互獨立的實體。主體是一個能思維、能認識的思維者或認識者,而客體則是一個外在於主體的被思維、被認識的對象。於是,進入主客二分。人在世上從主客不分、沒有自我意識進展到主客二分、擁有自我意識,會産生驚異,這無疑是哲學發展邁出的重要一步。但是,哲學長期局限於主客二分,既會遮蔽人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又會遮蔽真實的人的存在。哲學必須從主客二分進展到超主客二分即高級的天人合一。在這種異而不異、萬有相通、萬物一體的生命體驗中,同樣會産生驚訝,並且是一種更加強烈、更高層次的驚訝,這就是人與存在的契合。在日常生活狀態下,人一般採取主客二分的態度看待世界,人會異化,世界也會非世界化。然而,人一旦感悟到了與存在的契合,就能聆聽存在的聲音或召喚,感到一切都是令人驚異的。在令人驚異之中,萬物不同尋常地敞開了本來之所是。人生並非衹是使用對象的活動。主客關係及其認識之所以可能,以萬物一體爲其本體論的基礎和根據。從本源上看,人與世界恰好是親密無間的。人生在世,首先是同世界萬物打交道,對世界萬物有所作爲,而不是首先進行認識。人在認識世界萬物之先,早已與世界萬物融合在一起,而世界也衹是一個人活動於其中的世界。人認識萬物之所以可能,是因爲人一開始就已經融合於世界萬物之中、生活並實踐於世界萬物之中。萬物一體是第一性的,主客關係和主體對客體的認識是第二性的,是在萬物一體的基礎上派生的。也就是說,主客不分先於主客相分,主客交融高於主客二分。①張世英:《哲學導論》,第63、118、231~253頁。哲學對世界的理解實質上不過是對人生意義的展露。反過來,對人生意義的揭示又能幫助人去理解世界的意義。人生的最高意義在於對萬物一體、萬有相通的體悟,而努力去避免科學認識所依賴的物我相隔、主客二分。
第二種是主觀普遍性。康德在《判斷力批判》“導言”中指出:“一般判斷力是把特殊思考爲包含在普遍之下的能力。如果普遍的東西(規則、原則、規律)被給予了,那麽把特殊歸攝於它們之下的那個判斷力(即使它作爲先驗的判斷力先天地指定了惟有依此纔能歸攝到那個普遍之下的那些條件)就是規定性的。但如果衹有特殊被給予了,判斷力必須爲此去尋找普遍,那麽這種判斷力就衹是反思性的。”②[德]康德:《判斷力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鄧曉芒 譯,第13~14、46~47頁。在他看來,規定性判斷力與反思性判斷力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斷力類型。前者與科學所追求的客觀普遍性相契合,後者與審美所最追求的主觀普遍性最投機。比如,莎士比亞的文學作品的美、達·芬奇的繪畫的美、貝多芬的音樂的美,這些都不是客觀的判斷,沒有辦法通過儀器檢測和發現;但讀過莎士比亞作品、看過達·芬奇繪畫作品、聽過貝多芬音樂作品的人,衹要沒有功利心、利害感,都會同意他們的作品很美。這個時候,人撇開了一切既定的概念,從根本上剝離了“經驗的雜質”,跳出了自我視界或自我利益,超出了世俗生活的“一己之見”,完全可以達到鑒賞的普遍性。之所以這樣,是因爲有一個最終的基礎性的東西爲審美提供了擔保,康德稱爲“共同感”(sensus communis)。這種共同感,基於每個人內心情感的先天共通性,“是一種不帶有基於客體之上的普遍性而對每個人有效的要求,就是說,與它結合在一起的必須是某種主觀普遍性的要求”③[德]康德:《判斷力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鄧曉芒 譯,第13~14、46~47頁。,能爲情感的普遍傳遞並引起共鳴提供保證。以審美爲契機,康德以主觀普遍性擴展並顛覆了客觀普遍性,巧妙地宣告——在差異性當中可以尋求到普遍性,差異性與普遍性之間可以貫通且應該貫通。
羅素認爲,“當有人提出一個普遍性問題時,哲學就産生了,科學也是如此”;“提出普遍性問題就是哲學和科學的開始”。④[英]羅素:《西方的智慧》(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崔權醴 譯,上卷,第6、14頁。不過,最終科學走向了“定義”,哲學走向了“反思”。科學的定義就是在差異性中抽象、概括、提煉出所謂具有普遍性的概念來,抽象的過程就是超出特殊性的過程、就是與特殊性拉開距離的過程。通過提煉,科學找到了普遍性,但差異性卻被淘汰掉了,衹剩下抽象的概念或客觀的普遍性。“一切科學的概念形成或科學的闡述的實質首先在於,人們力求形成普遍的概念,各種個別的事物都可以作爲‘事例’從屬於這種概念之下。事物和現象的本質就在於它們與同一概念中所包攝的對象具有相同之處,而一切純粹個別的東西都是‘非本質的’,而達不到科學的地位。”“科學概念的最後因素在一切情況下都是普遍的。概念之所以衹能由普遍的因素所形成,這衹是因爲科學所使用的詞匯必須具有普遍的意義,以便能爲大家所理解。”⑤[德]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塗紀亮 譯,第37~38頁。哲學之所以要面向普遍性,不是想要淘汰差異性,衹是想遠離“意見”,面向真理。在哲學看來,差異是普遍性藉以實現和豐富自身的條件與環節。如果沒有了差異,普遍性就成爲了空無一物的“虛幻物”。所以,哲學並不主張在普遍性與差異性之間形成對立和排斥關係。哲學的反思就是在差異性中體驗出普遍性來,體驗的過程就是融入差異性的過程、就是與差異性拉近距離的過程。由於普遍性是建立在差異性的基礎上的,越差異越普遍,越特殊越有共鳴。一個思想者,他有特別的才華,纔會有普遍的接受和共鳴。沒有差異,恰好不可能普遍。普遍性不是從差異性中抽取出來的,而是在差異性內部生長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