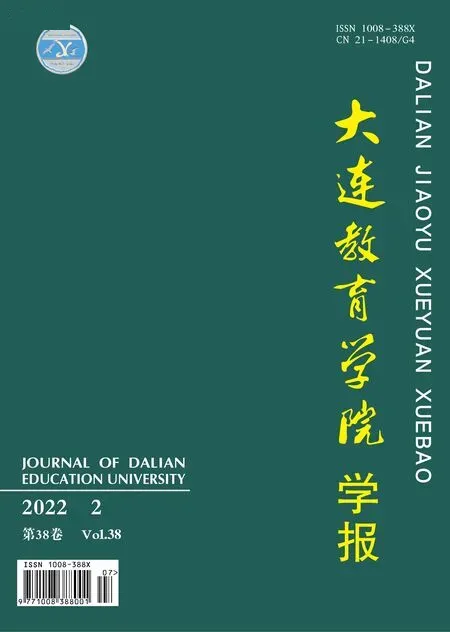论双雪涛小说东北地域图景
纪秀明,郑 玥
(大连外国语大学 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地理生态环境迥异使历史文化基因不同,从而形成区域文化。“它以世代积淀的集体意识为内核形成一种网络状的文化形态,风俗、民情、宗教、神话、方言,包括自然生态和种族沿革等等,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的系统”[1]。在作家作品创作中,“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形成一定稳态的审美价值和判断标准”[2],由此产生了风格迥异且极具民族特色的地域文化。
双雪涛小说东北地域图景由自然图景、城市图景和工业图景构成。东北自然图景以大风大雪为代表,创造了干燥严寒的冷峻雪国,自然变化更间接催化了小说本身的发展进程;东北城市图景概指小说中的辽沈印象、铁西艳粉街和红旗广场等城市坐标勾连出历历往事,它们不自觉融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为东北发展的见证者;东北工业图景指向那段锈色历史,工人工厂元素随处可见,父子两代人对火车铁路的感受对比出东北工业的迅猛发展。三者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双雪涛小说的地域图景。
一、冷峻雪国——东北自然图景
自然环境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它或显或隐地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法国理论家丹纳曾就气候对人性格等方面的影响有过具体的举例研究论证。他以居住湿腻闷热的平原为例,讲述荷兰人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坚韧生存的例子。“不断地重做,改善,筑堤防河防海……因为困难大得不得了……几百年的压力造成了民族性,习惯成为本能……使他成为一个埋头苦干的人”[3]。与丹纳论述相似,双雪涛小说也呈现了自然对人的性格、心理的影响。东北的雪作为自然意象之一,频繁现身于其多部小说之中,整体塑造了冷峻的雪国形象。严寒的天气造就东北人直爽的性格,雪的冰冷也使人性温情的一面更加柔软温暖。双雪涛的部分小说,没有明确指明东北,但是有关自然的描写大多指涉东北特色的地域景观。
1.雪的描写
双雪涛小说自然环境大多指向飘雪的东北。雪意味着凛冬已至,它是冷色环境的缔造者。《跷跷板》写冬天的深夜,“路上几乎没有人,路边时有呕吐物,一经冻成硬坨儿。树木都秃了,像是铁做的……煤炉上隔着水壶,墙上都结冰了”[4]18。铁色的环境将故事推向了冷彻严峻的走势,也为文末挖出骨骸埋下氛围上的伏笔。
不只环境的烘托,双雪涛作品中每一场雪都不尽相同。有绵绵密密的小雪,也有磅礴难辨的大雪,好像入冬以来雪从未停过。《飞行家》运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东北的几场雪。第一场小雪“是一个傍晚时分,不是很大,但是很黏,雪片不易分辨,如同粉末……雪已经停了,白得耀眼”[4]26,就连那一大片杨树林的“树枝上都挂着雪,风一吹摇摇欲坠”[4]28。第二场大雪来势汹汹,仿佛要淹没这个世界。“第二天傍晚,突然下起大雪,雪势之大,好像要把一冬的雪一次下完……(教堂里)几个男女身上还有雪花……”[4]44。“所有屋檐上都有雪,蓬松洁白”[4]49,层层积雪从侧面表现了雪量的庞大。沉重的积雪堆积在建筑物上,竟然把阁楼给压塌了:“大雪把光明堂压低了半截,阁楼的木头垮下来,搭在房檐上”[4]48。第三场雪下得更大更紧凑了,“雪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而且是越下越大……此时的雪已经如同铁幕一般,在身体周围降下,看不清”[4]73。细读全文可以感受,雪分割了故事,它宣告着叙事的暂时停滞,并开启叙事的新篇章。下雪的节奏让读者在故事的间歇,重新整理思绪,继而投入到新的叙事中去;它也间接催化了小说本身的发展进程,缠绵的小雪开启故事的首页,磅礴大雪压塌了教堂,预示着毁灭的现状和亟待重建的精神理想,最后天幕般的大雪,更是创造了与世隔绝的新奇世界,它昭示着现实主义叙事就此终结,一切怪异的事物将在此处发生。因此“我”与姑鸟在湖底接受“大鱼”审问,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2.雪的温情与救赎
雪的寒冷凸显了人与人之前的温情,在琐碎的日常中展现了东北人热络开朗的性格。《光明堂》多次描写白雪皑皑的东北景象,即便大雪纷飞的寒冷天气也掩盖不住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我”和姑鸟是在雪地里堆雪人相识的,“我”和姑鸟也在大雪追凶中,经历了更加严峻的友情考验。雪之大,似乎要将“我”和姑鸟吞没,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姑鸟,而是背着她在寸步难行的大雪里求生。“我”与三姑的初次相识,“我”的鞋子全是雪水。“我说,三姑,脚湿。三姑说,脱了暖气烤上。我把鞋和袜子放在暖气上,盘腿坐在三姑旁边,用军大衣盖着”[4]30。雪拉近了“我”和三姑之间的距离,平淡的语气中有普通生活中亲情的温暖。《跷跷板》描写“我”和女朋友刘一朵的父亲第一次见面,由于下雪,岳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关切到:“那你辛苦……路面有雪,开慢点”[4]6。即便下雪的天气再寒冷,但温情的呵护总能帮人度过难捱的严冬。
我国文学对雪的描写历史悠久。在古代诗词中,它或烘托氛围、暗含情感,如“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中征夫的思念悲痛;又暗喻祥瑞,“迎气当春至,承恩喜雪来”,寄托美好之意。在双雪涛的作品中,雪意象不仅写实表现出东北的苍茫冬景,它更以清冷孤傲的姿态,不断刺激着人们,在索求灵魂解脱之路上作出抉择。白茫的大雪在视觉上造成隔绝,形成天然屏障,促使青年人不断尝试寻找个体存在与获取救赎的可能性。
《无赖》里“我”拥有一盏好不容易修好的台灯。车间环境阴暗狭小,寒冷阴暗。而台灯的光昏黄温馨,是黑夜里最简单的依偎和陪伴。但是在一个普通的夜晚,台灯被保卫科理所当然抢走,据为己用。而他们对个人欲望外的事情全然不在乎,道貌岸然的权威掩盖虚伪贪婪的手段,纵使身单力薄的“我”想要抢回,却力不从心被甩在一旁,还被骂“看起来好像有点不正常”。年幼的“我”不谙人情世故,将希望投在那个玩世不恭的“无赖”身上。少年的手里并没有可以交易的筹码,只凭着一腔蛮不讲理与歇斯底里,将所有的委屈化在眼泪里砸向“无赖”,抓紧眼前的最后一根稻草。人人嫌弃的“无赖”,站起来看了我好久,拿起礼帽和一只完整的酒瓶,决定帮我讨回我的最爱。终于,下起了一场大雪。那晚的“雪下得真大,北风呼啸着,把雪吹得到处都是,一会向东,一会向西”[4]196,冰冷的雪花裹着风钻进“我”的衣领,但难压制沸腾已久的热血。“无赖”安静地走进办公室,微笑着与人理论,不出意外地迎来了办公室人的指指点点。他脱下礼帽,在雪夜里优雅极了。忽然他抡起酒瓶砸向自己的脑袋,像烟花一样飞溅着血花。车场的灯骤亮,所有事情都疯狂了起来,黑白的世界在这个磅礴的雪夜里点燃。台灯是“我”内心私人化和渴望的象征,然而生活的贫困和道德失范摧毁了“我”最后的精神原乡,“无赖”自残式的攻击则意味着弱势群体的绝望的反抗,即便机器的嗡鸣震耳欲聋,“我”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自由的灵魂在雪夜里跳舞,大雪解放了人性中的束缚,将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温情释放出来,在双雪涛的笔下,雪夜寒冷严酷,却也无比温暖。
二、辽沈印象——东北城市图景
对记忆叙事的情有独钟,是双雪涛的书写之殇。正如《天吾手记》的开篇引用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一句名言,“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其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也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期望的那样,东北与那段尘封的历史,就像一座座岛屿,永远沉静在双雪涛的脑海中,曾经企及,永不遗忘。
双雪涛笔下的辽沈印象以铁西艳粉街和红旗广场为主。铁西艳粉街的生活经历占据了双雪涛童年及少年的大部分时间,铁西成为他众多小说中说不尽的故乡和经验来源;红旗广场勾连出历历往事,不自觉融为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为东北发展的见证者。
1.铁西艳粉街
艳粉街位于城市和农村的中间地带,因清朝给皇家种过胭脂,故取名“艳粉”。比起如此香艳的名字,艳粉街本身则显得普通得多。大量的普通居民聚集居住在盘香似的窄巷子里,生活比较艰苦。成年人多忙于生计四处奔波,孩子就跟着爷爷奶奶,或者自由地野蛮生长。双雪涛曾在《朗读者》采访中表示,“艳粉街有一地儿好,就是玩的东西比较多,小伙伴比较多,父母都不怎么管,自己也变得可能野了一点,一玩玩到很晚很晚”。
艳粉街的整体样貌,被双雪涛形容为“圆的,从上面看像蚊香,一圈一圈的”[4]125。艳粉街“在市的最东头,是城乡结合部,有一大片棚户区,也可以叫贫民窟,再往东就是农田,说实话,那是我经常抓人的地方”[5]12。
双雪涛许多作品都有艳粉街的描写。人口密集是艳粉街第一个特点。作为城乡结合的交点,艳粉街人口复杂多元。受东北大下岗波及的城里人被迫逃到艳粉街暂时落脚,而渴望进城生活的农村人则把这里当作入城的缓冲带。鱼龙混杂是艳粉街第二个特点。它就像一个宽容的避风港,不论是刑满释放的犯人、妓女、无业游民或是落下残疾的病人,它都慷慨提供落脚空间。
《光明堂》的背景就是铁西区的艳粉街,廖澄湖给“我”的关键地图就画着艳粉街的全貌。而在廖澄湖的手绘地图上,标明着几个小图标:艳粉小学、煤电四营和光明堂等。这些城市坐标,一个个交错安置在双雪涛的小说中,构成了他记忆中的艳粉街形象。艳粉街鲜有高楼林立,工厂的烟囱就像是鹤立鸡群,傲然俯视着忙碌着的平凡人们。
艳粉街不如城市干净整洁,这里聚集了讨生计的男男女女。在双雪涛的小说中,藏污纳垢的环境描写比比皆是。《光明堂》写到艳粉街的豆腐坊和坊后的煤堆,“门口南流北淌,都是脏水和豆腐渣,有的已经结冰。许多人站在上面,排着队……豆腐坊的后身,雾气漳漳,有个煤堆,有些煤球都已经烧黄了,有的略微带点黑”[4]38。双雪涛笔下的艳粉街无论故事有多离奇精彩,而它一直安稳平和,藏污纳垢却又吐纳不息。
2.广场往事
一座城市的广场,往往可以反映这座城市的文化、民生状态以及历史往事。它就像一种文化现象,矗立在城市与文化之中。广场风格的变迁与建设,往往与这座城的历史、审美有关。在中国近代史上,东北是一片饱含血泪的深沉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肩负着新中国工业成长的伟业重担。双雪涛是一个非常注重责任感的作家,他曾表示,如果没有人写,那就自己来。带着这样的写作目的,双雪涛对历史频频着墨,小说中出现很多历史城市坐标,红旗广场就是其中之一。
《飞行家》以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为背景,以工人李明奇飞行家的梦想为故事基础,讲述了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挣扎与生存困境。红旗广场作为故事发生的核心地点,见证着李明奇的成长、追梦与毁灭。小说开篇就介绍了红旗广场的由来,“1967 年修的红旗广场。广场原是日本人修的,铺的大理石砖,据说是从阜新开山运来的大石……广场四周是日本人的银行和办公楼……1967 年在大理石广场上立了一座毛主席像……,就此成为‘红旗广场’,因为主席像的底下有一排士兵,为首的一个带着袖箍儿打着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4]124。小说结尾部分,二姑夫李明奇坐上自己的飞行器,预备进行无翅的飞翔。“我”随表哥李刚到红旗广场找二姑夫。红旗广场对于“我”来说是一段快要模糊的记忆。于是跟随“我”新历者的视角,描写了红旗广场的现状。“四周的老式八角灯都黑着。毛主席像立在正中,底下是一圈黑影。我抬头看了看主席像高举的右手,在黑暗中那手显得特别和蔼,平易近人”[4]174。双雪涛以两代人的视角描述了广场的历史变迁。尽管时光荏苒,红旗广场与毛主席像一起见证着城市的沧海巨变。
无独有偶,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也对红旗广场有着相近的叙述。庄德增承包了印刷车间,收购了曾经的卷烟厂自立门户。厂里的老退休工人因为不同意毛主席像被拆一事,去广场上静坐示威。书中这样描写“红旗广场的主席,六米高那个……我知道那个主席,小时候我住得就离他很近。老是伸出一只手,腮帮子都是肉,笑容可掬好像在够什么东西”[5]25。正如艳粉街是双雪涛虚构小说时的现实土壤,红旗广场以及广场中间的毛主席像,也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红旗广场就是现在的中山广场,它位于辽宁沈阳和平区,整个广场视野开阔,中心的主席雕像庄严肃穆,抬手指向前方。雕像下方簇拥着58 个战士,表情坚韧姿态各异,组成了中华儿女不畏艰难刻苦奋斗的群像。
广场就像是城市发展的见证者,它冷静地看着东北人民在它身边忙碌过活,不自觉地融入了城市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作为子一代视角,“我”对于红旗广场的印象就像是一个过路的旁观者,它的变迁兴衰、荣誉辉煌在我看来都只是一方城市的建筑。即便知道它曾经饱含历史的风霜,却只在路过时投入憧憬的一瞥。而父一代例如李明奇等人,他们的成长故事与广场息息相关,正如《平原上的摩西》中老工人回忆的那样,“夏秋的时候,我们在他周围放风筝,冬天就围着他抽冰尜”[5]25。那些曾经的激情岁月,那些感人的奋斗历史与毛主席像一样是熠熠生辉的峥嵘岁月。
三、锈色历史——东北工业图景
20 世纪80 年代末至9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却也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隐痛。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些工厂企业需要重组改制。工人和工厂、工业描写几乎在双雪涛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工业题材成为双雪涛笔下不可忽视的焦点。
1.工厂与工人
双雪涛童年时期的个人生活经历,在作品中产生举足轻重影响。小说以浓郁的现实主义手法,重新回望过去的年代,试图还原出琐碎生活,将记忆中的景象依次展开,勾勒出特殊时期传统工业艰难处境的真实图景。
《无赖》里“我”和父母挤在六七平米的工厂小隔间里。车间有“一条生产线,无数的车床、吊臂、工具箱、电钻、扳手、螺丝。一到夜里,硕大的落地窗洒进月光,机器们全都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5]138。《走出格勒》中我和老拉去煤厂捡煤块,“煤营四厂”的铁门斑驳,上边四个红字“像是许多年前刷上去的,好多笔画已经脱落”[5]245。翻过铁门,院内“有一段铁轨,铁轨上停着一辆煤车,四四方方,铁轨向前延伸,一直爬过一个土丘”[5]245。《杨广义》中早上的上班时间,“工厂大门拉开,喇叭里放起东方红”[7]86。《跷跷板》更是有大段的工厂环境描写。“厂区的中央是一条宽阔的大道,两边是厂房,厂房都是铁门,有的锁了,有的锁已经坏了,风一吹嘎吱吱直响……有的玻璃全部碎掉,有的还有生锈的生产线,工具箱倒在地上……车间的墙上刷着字,大多斑驳……一车间是装配车间,二车间是维修车间,三车间是喷漆车间,一直到九车间,是检测车间”[4]19。双雪涛小说中的工厂环境描写,带着老旧的气息。跟随作者的视角推开大门,仿佛有陈积的灰尘扑面而来,这是工人们挥洒热情汗水的土壤,如今流淌着压抑的气息。
工人是新中国工业发展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双雪涛《飞行家》《平原上的摩西》等小说集描写了一系列工人群像。
《平原上的摩西》中,庄德增被分配到卷烟厂任供销科科长,傅冬心在印刷厂上班,老李在小型拖拉机厂做钳工;《大师》里“我”的父亲是拖拉机厂的工人,负责看守仓库。《无赖》中,“我”的母亲是车工,每天要站着工作八个小时,喷漆工张师傅总带着一个工具箱,即使里面空无一物,打开“却散发出工人身上特有的汗味”[5]189;《杨广义》里赵静和“我”一样,住在厂里,“她妈是五车间的出纳,他爸是保卫科的干事”[7]81;《聋哑时代(序曲)》中,“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拖拉机厂工人,每天为如何更能省力地装卸螺丝而烦恼”[5]1;《跷跷板》里,“我是个工人……我父母都是工人”,和我要好的女人“是个钳工……年年先进,能做极好的炸黄花鱼”[4]12;《飞行家》里高立宽是市印刷厂的高级技师,“拿手的本事是古板印刷,一通百通”[4]124,高雅风在变压器厂做钳工,“每个月领二十多块钱工资,工龄比同龄人都长”[4]128,别人介绍起来说“车钳洗没得比……父母是双职工,都是老工人,根正苗红”[4]161,李明奇在军工厂上班,“具体工作不让说,但是总之就是造降落伞的”[4]142,高旭光“回城后分配到拖拉机厂”[4]143。
双雪涛笔下的工人是极具韧性的边缘人,为了全家的生存摸爬滚打,底层性和世俗性与往日工人“完美”的形象裂开。他们被时代高高簇起过,又未能及时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即使如此,《安娜》中“我”的父母下岗后卖茶叶蛋,“我”家的茶叶蛋是那条街上唯一用真材实料的红茶煮。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化初期,工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工业文明发展高度契合。而在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中,他们依然散发着人性的隐忍与善意之光。
2.火车与铁路
铁路和火车是现代化工业的象征。东北的铁路和运输相当发达。作为东北最大的铁路博物馆,沈阳铁路陈列馆宣传的每件铁路装备及火车展示,无不昭示着东北铁路工业的辉煌。在双雪涛的小说中,铁路和火车频繁登场。
铁路和火车作为工业象征频繁出现在双雪涛的小说中,充当故事的工业背景板。《光明堂》描写了“我”第一次看见火车的场景,“由北往南,一个黑点驶来,头上也如我般冒着热气。车厢大概十几节,窗户紧闭,将阳光折进我的眼睛。那是我头一次见到火车,硕大无比,隆隆巨响,如同天外来客”[4]28;《走出格勒》中提到“我”的捡煤经历,去煤场前必经一大片高粱地,火车呼啸而过。“我”听到“火车经过铁轨的声音,只听见隆隆的声响,听不清铁轮轧过轨道接缝的声音”[5]245;《聋哑时代》中“我”和刘一达的物理实验就是在铁路上完成的,“火车呼啸而过,猛兽一样想要碾碎所有阻挡它的力量”[6]36,“我”甚至会因为火车经过的震撼景象而“哑了半响”。
除了震撼的视觉冲击外,火车和铁路见证着孩子的成长。“我”在初中时常来到城郊的铁路旁,“躺在铁道旁边的草丛里,看天上的云变成那个女孩儿的模样”[6]36。高中毕业生“我”与《跛人》的相遇,直接在火车上发生的。文中不止描写了火车站环境嘈杂混乱、拥挤不堪的环境,还记录了火车上发生的趣人趣事。当“我”和刘一朵拼命挤上绿皮火车找到座位时,“火车已经驶出站台,把一栋栋楼宇甩在身后,窗户外面的景物也开始逐渐稀疏”[5]139,故事的最后,“我”和刘一朵分道扬镳,“我”独自在火车站睡了一晚才回家。《大路》也有关于火车站的叙述。火车站是“我”在这座城市的活动地区之一。“白天我就在火车站里睡觉吃饭,候车大厅就是我的房间……火车站只是我生活的地方,在哪里也找不到这么美妙的家,被无数的人包围,可没有一个烦你”[5]222。从双雪涛表述中,火车站是一个复杂但是包容的环境。它每天吸纳着来来往往的过路人,每一个人带着目的地而来,向着心中所想而去。
火车站不止参与了子一代的成长轨迹,它更是直接构成了父一代的回忆。在小说《光明堂》中,这种对比尤为明显。“我”第一次看到隆隆而过的火车,心里无比震撼。但是在父一代老赵的眼中,有关火车的描述则与直接经历有关。老赵对后辈讲述去北京的经历,提到“坐火车去看毛主席”的往事,还有曾经“扒火车”的经历,并感叹“现在的火车真快……过去我扒过火车,现在不行了,太快了”[4]67。值得一提的是,子一代柳丁也是在老赵的陪同下,第一次看到了火车。在《光明堂》中,父一代有关火车的描写带有回忆性质,与子一代直观性的冲击不同。对于老赵等人而言,火车的提速带给他们不同往昔的感受,在对比中表现东北工业的迅猛发展。火车与铁路也和故事中的人一样,不断发展,奔跑向前。
“地域文化……影响了作家们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内容、艺术风格”[8]。20世纪80 年代中期,作家开始把寻找“文化之根”作为新的探索目标。由此,地域文化作为小说创作的内在基底,成为文学新的生命之源。双雪涛诚实地书写了东北人的生活现实,以善良为导航寻找人性中美好。双雪涛作为生于东北长于东北的人,浓郁的东北地域文化色彩直接或潜移默化地融入了他的文学艺术创造中,散落在他作品中的隐秘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