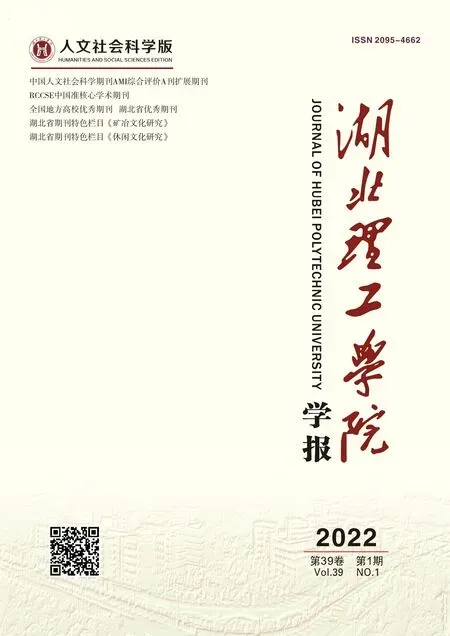贵州清水江文书俗语词考释六则*
杨小平 谢 蕊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贵州清水江文书,又称“清水江民间契约文书”,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数量最多的近代民间文书,跨越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个阶段。它是贵州清水江流域苗族及侗族人民创造和保藏的一种民间文献遗产,主要包括山林经营和木材贸易方面的民间契约和交易记录,详细记载清水江下游民间贸易、借贷、分家等活动,是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一地区历史文化的资料库。该文书具有内容丰富、口语化强、真实可靠、数量庞大的特点。
据考察,黎平、天柱、三穗、剑河、台江这五县档案部门收集的文书已达18万件,数量庞大,其中的俗语词数量更是不少。近些年来,有部分学者对其中的俗字进行了研究,有的文书史料汇编附有少量的疑难词语简释,也有部分学者撰文专门讨论词语的含义,比如肖亚丽《清水江文书词语释义十一则》[1],郑文慧《清水江文书套语词例释》[2]。检索发现,针对清水江文书中的俗语词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数量不多,其中一些词语未曾注解,或者注解未明。由此可见,学界缺乏对清水江文书俗语词的系统研究,因此针对这方面的研究价值极大。
俗语词,是流行于民间的并且带有一定方言色彩的通俗语词,也是典籍中字面普通而有特殊含义的口头语词。贵州清水江文书中出现“拆足”“后饭”“理落”“沙洋”“原本”“周牒”六个俗语词,意思费解,容易误判,形成清水江文书阅读障碍。《汉语大词典》、《辞源(第三版)》、白维国《近代汉语词典》等辞书多未收录。文章根据语境,结合传世文献,联系地域方言,分析俗语词的构成,探析其意义及演变,消除清水江文书阅读障碍,补充《汉语大词典》《辞源(第三版)》《近代汉语词典》等辞书未收词条或义项,提前滞后例证。所引清水江文书引文括注文书编号及书写时间,以便核对。
一、拆足
《□□□卖田契》:“其银拆足应(用),不少分厘,其田事卖之后,任(从)买主永(远)□□。”(《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09-27-001-027,道光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3]28
按,“拆足”一词,意思费解。《汉语大词典》《辞源(第三版)》《近代汉语词典》均未收录。
在清水江文书中,买主和卖主在证人的见证下,卖主在交易之后将钱如数取回,买主合法使用交易换回的田地、山木等其他物品。为防止两人交易不作数,还会相应地签订契约。查阅辞书,可以知道“拆”字在当时就有与钱有关的意思,《汉语大词典》:“拆,按比例算钱。”[4]472此义项的“拆”与钱有关,例证孤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太平天日》:“四人齐声曰:‘主不早说明,今晚主同我四人食饭,饭钱臣们同主拆。’”[4]472《汉语大词典》中“拆”与钱相关的例证不足,清水江文书中的“拆”字可作补正。“足”在《汉语大字典》的释义之一是“充分;完备;足够”[5]3929。结合文书语境,“拆足”二字可以理解为“账目结清,已然无误,完全拿回来”。
在其他文献中,也存在“拆足”的例子。
周为筠在民国时代编撰的《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中提到了“拆足”。《20年拆足了烂污》:“‘拆烂污’乃上海方言,‘烂污’者谓闹肚子的肠胃里翻江倒海之后忍不住一泻千里,所以,‘拆烂污’即北方人所说的‘拉稀’。”[6]179
《20年拆足了烂污》标题中的“拆足”并非一词,而是连接在一起的两字,与我们讨论的“拆足”并非一回事,也可以看到,计算机检索某些时候并非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清代《说唐后传·第三传》第四十七回《宝石基采金进贡·扶余国借兵围城》:“冒箭冲到营前,手起斧落,乱砍乱杀,有几个小番遭瘟,做了无头拆足之鬼,乖巧些逃往帅营去了。”[7]256
此处的“拆足”也并非清水江文书中的动词“拆足”之意,而是表示鬼的样貌,形容鬼折断双足。
可见,和文书中表示同义的“拆足”并未出现在其他文献中。
“拆足”一词,在清水江文书中,也说成“收足”“领明”“领足”“接足”等,他们常出现在“其……应用”和“其银……”句式中,都表示“(银两)账目完全结清、已然无误,完全拿回来”。
1)《谢乔生等卖山土字》:“其钱一并收足应用,其山任□买主永远管业耕种,卖主不得异言。”(《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09-28-001-028,道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3]29
2)《谢生保卖田契》:“其银亲手领明应用,其田任从买主永远耕管为业。”(《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09-30-001-030,道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3]31
3)《谢老□卖田契》:“其银亲手领足,其田任从子孙永远耕种管业。”(《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09-31-001-031,道光六年六月初九日)[3]32
4)《王林豹卖山柴土契》:“其银领明接足,其山谢姓畜禁,耕管为业,若后不得异言,立此卖字存照为(据)。”(《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09-36-001-036,道光十一年二月初六日)①[3]37
上述四则用例均表示(交易)所获得的银两清算清楚,完全拿回来,这和“拆足”是同一个意思。
二、后饭
《谢二长等卖地基柴山字》:“今凭地方头人保长倍有酒寔,不得后饭,若有后饭,自干罪戾,立此卖字清白为据。”(《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09-55-001-055,道光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3]56
按,“后饭”一词,《汉语大词典》《辞源(第三版)》《近代汉语词典》均未见收录,甚是费解。检索传世文献以及工具书引用的文献用例,可以看到“后饭”有不少用例。
1)春秋战国尉缭《尉缭子》卷一:“军井成而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舎,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8]3
2)春秋战国荀况《荀子》卷十三:“飨与享同,四时享庙也。用,谓酌献也。以玄酒为上,而献以酒醴,先陈黍稷,而后饭以稻粱也。”[9]137
3)《黄帝内经大词典》:“词组。饭后服用。〈素问·病能论篇〉:‘以泽泻、术各十分,麋衔五分,合,以三指撮,为后饭。’”[10]339
4)《中华医学大辞典》:“服药法。谓先服药而后食饭也(一说谓饭后服之)。《素问·腹中论》:‘以五丸为后饭。’”[11]571
在上述用例中,1)、2)两个例句的“后饭”不是词,而是连接在一起的两个字,与我们这里讨论的词组“后饭”不是一回事。“军食熟而后饭”解释为军队的食物煮熟之后再吃。“而后饭以稻粮也”中的“后饭”同样不是一个词,“而后”和“饭”是分开来说的,这里的“饭”是动词。例3)、例4)两部工具书所引两个文献例子中的“后饭”是词组,表示饭后服用。另外也表示涉及医学方面的专业术语。
由此可见,这些文献中的“后饭”和清水江文书中的“后饭”并不是一个意思,不能用来解释清水江文书中的例子。观察文书中的例子,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句式:“不得异言,若有异言”,这和“不得后饭,若有后饭”的使用位置和表达意义都一样。据此可以推测“后饭”与“异言”类似,表示不同意。俗语词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被大家口口相传,所以具有口语性、地域性的特点,“后饭”一词很可能就是当地群众口语的体现。南方人常常“h”“f”混淆,“饭”即是“悔”的音变,“后饭”即“后悔”。《杨正典等卖田契》:“其钱卖主亲手领足,不得少欠分文,字(自)卖之后,不得后悔,恐口无凭,立有卖字为据。”[3]131(《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10-130-002-060,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四日)与《谢二长等卖地基柴山字》例证表达类似。由此看来,文书契约中的俗语词极有可能是地域方言变体的结果,这也说明对文书中的俗语词研究是有益于近代方言研究的。
除了表示后悔、不同意的“后悔”“异言”“后饭”外,还有“翻悔”“后言”等词,《杨正典卖田契》:“其钱卖主领足应用,不得后言,恐口无凭,立有卖字为据。”(《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13-133-003-003,民国元年十月二十五日)[3]138
“后言”一词似当是“后悔”与“异言”组合的缩写形式。出于表达简洁的需要,将表示相同、相近或相关动作行为的两个词组合浓缩在一起。
三、理落
1)《谢老宏卖断房屋字》:“承买为业,卖主不得异言,若有内外不清,卖主上前理落,不干买主之事,恐口无凭,立有卖字为据是寔。”(《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11-165-003-035,民国五年十月初八日)[3]170
2)《谢文举卖地基字》:“其钱领足应用,买主不欠分文,来理不清,卖主上前理落,不关买主之事。”(《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11-160-003-030,民国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3]165
3)《邰名新卖田字》:“倘有抵当不清,边界不明,邰信卖主自行出钱,出头理落清楚,不与买主分毫相干。”(《贵州清水江文书》SS-84-1-039,光绪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12]40
按,“理落”意为处理、过问;承担、承当。清水江文书中存在大量的“理落”用例。《汉语大词典》《近代方言大词典》均收录。
根据上述契约内容可知,买主和卖主在交易完成后不得有任何异言,如果发生争执,就由卖主去处理或者承担这个事儿,与买主无关,所以“理落”意为:处理、过问;承担。
“理”在《汉语大字典》其中的一条解释为“操作、从事”[5]1194。“理落”中的“理”与“捋”同义。“捋”也表示梳理、整理之义。这和“理落”一词的整体意思相关,那为何“落”字会和“理”字合起来表示上述义项呢?“落”似当为“捋”的讹俗字,“捋”有两个读音,其中一个读音是[luo51],表示用手握住条状物向一端滑动。在川渝方言中,经常用“理[lo51]”一词表示清理、过问之义。
此外,其他文献中也有“理落”用例。
政协天柱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编《天柱古碑刻考释·下·清水江文书》收录《远口镇新市庵产碑》:“该碑放置在新市回龙庵门前的田埂上,碑的上半已折断不知去向,其旁有两片残石,其中一片有‘不惜叠次理落以复前人之’等11字,疑为该碑所裂开的内容之一。”[13]33
龙泽江、傅安辉和陈洪波共同编写《九寨侗族保甲团练档案》收录《吴万富等于家祠留宿女人赔错清白字》:“以后倘有外来人来历不清,居(俱)我等祠内并店主吴正荣与祠领钱人等一面承当理落,不与两寨团等相干。”(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二日)[14]289
“理落”一词在当时有着不同的俗写形体,如“礼落”“里落”。“理落”一词与“里落”“礼落”等同音。
1)《彭贵伍卖田契》:“亲手领足应用,并无下少分厘,不得议(异)言,若有末里不清,卖主上前里落,不干买主之事。”(《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10-110-002-040,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五日)[3]113
2)《刘必求等卖田契》:“倘有末厘不青,卖主上前礼落,不干买主之事,恐口无凭,立有卖契一纸,永远存照为据。”(《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11-132-003-002,民国元年五月初九日)[3]137
由文书中例子句式相同可知,“理落”“里落”“礼落”这三个词是同样的意思,“里”“礼”两个字是“理”的不同讹俗字。这和当时当地的契约文书有关。锦屏清代林契一般以纸契和石契两种形式出现。纸契几乎全部用丝棉纸、草纸,经过高温消毒、杀菌等一套完整的制作工艺流程,方才成形。由于在纸契上书写不便,所以在书写契约时尽可能简化汉字,也就造成了同字不同形的讹俗字。
四、沙洋
《谢文举出典田契》:“自己上门问到亲房人等,谢文举承典当面议定价沙洋二十万元。至典之后,不得易言。恐口无凭,至典后,议定三年上门续字积沙洋青促领出。”(《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13-248-005-010,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3]237
按,“沙洋”一词费解,《汉语大词典》《辞源(第三版)》《近代汉语词典》均未收录。传世文献也未见“沙洋”用例。
在传世文献中可以了解到,“沙洋”一词曾用来表示地名,“沙洋,镇名,在湖北省荆门县东南、汉江中游西岸。1960年曾设市,1961年撤销。公路东通武汉,西至宜昌,为鄂中物资重要集散地之一”[15]190。这显然不是文书中“沙洋”的意思。
清水江文书中有与之相似、出现在同一句式位置中的词语,如“价洋”“清钱”“钞洋”等。
1)《杨宗茂等各庵主卖田契》:“□□请中登门问到谢寨,谢三林名下承买为□,当日凭中人议定价洋壹拾八元零□□□。”(《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11-159-003-029,民国□□五年六月十五日)[3]164
2)《李胜耐等出典田赎退字》:“自己请中上门问到谢秀魁续约,当面议定价钱清钱三千八百文整。”(《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12-214-004-027,同治八年十二月初五日)[3]214
3)《谢文举卖地基字》:“自己上门问到亲房人等,谢文星名下承买当面言定价钱钞洋四百七十元八角正。”(《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11-150-003-020,民国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3]155
“价洋”“清钱”“钞洋”同“沙洋”一样,出现在固定句式中。“价洋”的两个语素都与钱有关,显然表示价钱。“清钱”指的是清代流通的铜钱,分官方铸造的制钱和私人铸造的私钱两种。《天柱古碑刻考释·上·清水江文书》中记录“钞洋”为钞票,属于纸币[16]140。
检索语料库发现,“价洋”“清钱”“钞洋”等词除了在清水江文书中广泛使用,还在其他地方档案中出现。
《〈申报〉宁波史料集7》中的《信客钞洋被劫》:“鄞县方桥马生财航船于前日有方桥龙台墩信客马春小雇该航船由甬开往庙堰头地方,驶至半途,忽来小船一只,内有匪徒四人,将该航船老大马和尚、阿林二人缚住,将信客马春小所带之钞洋九百余元一并劫去。”[17]3266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37—1945》中有一则标题:《工厂联合会请预交代购粮款各厂来会领粮函并附分配各厂粮数及价洋数额》[18]281。
由此可见,“沙洋”也和钱有关。“洋”字很好理解,《汉语大词典》解释为“洋钱、银元”[19]1182。“沙”字,不能从其字义入手,而应从其字形分析。从纵向的历时层面来看,“清钱”较“钞洋”和“沙洋”出现时间早,也就是文书最初写的是“清钱”,后来使用“钞洋”,只是在手抄过程中,“钞”受到原来“清”的偏旁“氵”之影响,“钞洋”于是写作“沙洋”。
五、原本
1)《谢乔生出典山土契》:“不得异言,在于典主向前理落,不干银主之事,以后归得原本上门续约。”(《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12-202-004-015,道光七年三月二十九日)[3]202
2)《王三毛出典田契》:“其田限至三月之内归得原本,上门续约,不得有误,若有误者,任从银主下田耕种收花,典主不得异言,若有异言,立有典字为据。”(《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12-218-004-031,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初九日)[3]218
3)《杨二禾出典田地字》:“其钱交与典主三年,耕种为业,遇相原本,上门续约,不得异言,今恐无凭,立有典是寔此据。”(《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13-238-005-001,民国十一年二月初二日)[3]228
4)《杨二木加典字》:“其田交与典主,一年之内归得原本,上门续约,不得异言,后说无凭,立有典字为据。”(《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13-298-005-002,民国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3]229
按,“原本”一词,清水江文书中多见用例。
“原本”,《汉语大词典》收录有这样几个义项:一指事物之所由起,根源;二指追溯事物的由来;三指本来、原来;四指第一次写成或刻成的书本;五指翻译所根据的原书[20]928。根据上述契约的语境,这几个义项并不能用来解释文书中“原本”一词。传世文献也未见“原本”的此种用法,《辞源(第三版)》《近代汉语词典》等辞书亦未见收录,甚是费解。
《汉语大词典》:“原,原本;起初。”[20]927又“本,母金,本钱。”[21]703再结合上述文书,此处的“原本”可释为“成本、本金”。清水江文书中,不仅用“原本”,有的时候还会用“元本”,与“原本”同音,“元”字也有“开始、起端”之意[22]207,这和“原”字不谋而合,故清水江文书时常将“原本”与“元本”混写。
1)《谢乔限等抵当银契》:“凭有中人借主备得元本,上门续约,不得异言,立抵存照是寔。”(《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12-195-004-008,道光九年八月二十七日)[3]195
2)《谢凤包长出典土字》:“其银限至三年内,上门出约,魁得元本,不得有误,若有误者,立有典字为据。”(《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12-203-004-016,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3]203
另外,除了“原本”与“元本”外,还有其他的表达。
《王三桥借谷字》:“宣统初年己亥岁王三桥借净本谷二百四十八斤。”(《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12-235-004-037,宣统元年□□月□□日)[3]224
这里的“净本”同“原本”一样,指纯粹的本金,不加任何利润之类。
六、周牒
《谢老宏周牒字》:“恐后无凭,当日凭中三面立有周牒为据。”(《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13-244-005-007,民国□□年二月十六日)[3]234
按,“周牒”一词甚是费解。《汉语大词典》《辞源(第三版)》《近代汉语大词典》等辞书均未收录。
“周”在《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遍及,全;满;量词。匝,圈[23]1000。《说文·片部》:“牒,札也。”[24]318《说文·竹部》:“简,牒也。”[24]190《说文·木部》:“札,牒也。”[24]265可见“牒”的含义同“简”“札”二字相近,都是竹木的不同形态,被当作书写载体材料来使用。《汉语大词典》:“牒,证件,凭证。《新唐书·百官志一》:‘天下关二十六,有上、中、下之差,度者,本司给过所;出塞踰月者,给行牒。’牒,古代可供书写的简札。《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右师不敢对,受牒而退。’”[4]1048据此,“周牒”是偏正式合成词,该词意思落在“牒”上,这里的“牒”已经由原来的载体名称演变为文书。故此处的“周牒”是指买主与卖主之间交易记录的凭证,上揭用例即指。文书中常常会有“立有□□为据”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可参:
1)《谢保二卖地基字》:“立此卖字为据。”(《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09-37-001-037,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初十日)[3]38
2)《刘必求等卖田契》:“恐口无凭,立有卖契一纸,永远存照为据。”(《贵州清水江文书》JH-PQXZ-211-132-003-002,民国元年五月初九日)[3]137
由此“周牒”意同“卖字”“卖契”,即字约、契约,是指官方颁发的一种契约,有文书义。为避免产生矛盾纠纷,契约文书特别强调产业的交易必须立有凭证,由此便产生出“周牒”“卖字”等一类词。
查阅各种辞书和相关文献资料,并未发现“周牒”用例,在诗词中寻到了该词,但意思却并非此意。
《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遣戍征周牒,恢边重汉功。”[25]804
这里的“周牒”是指书板,文书的一种。
综上所述,贵州清水江文书中存在许多俗语词,这些词语具有与众不同的地域方言特征。继续加深对此契约文书词汇的考察,这将为语言研究提供丰富的案例,同时也能为汉语方言研究提供新的材料。
注 释
① 此件文书整理把时间写为“道光十一年二月初六四日”,有误。据文书内容,当为“道光十一年二月初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