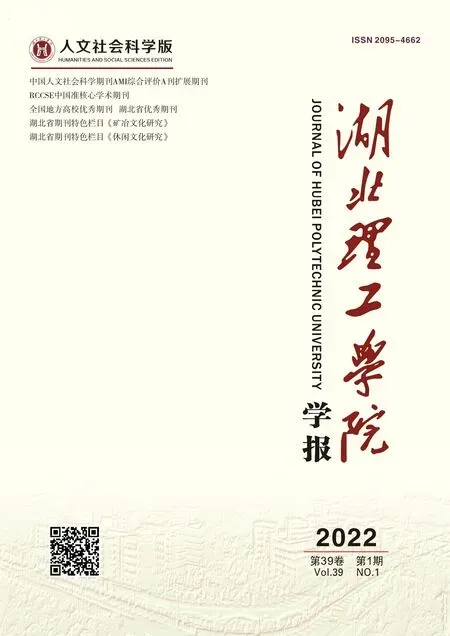论米家路《深呼吸》中的自然意象书写*
高 健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一直以来,美国华人学者米家路,多以诗歌评论者身份亮相于国内文坛①。直到2019年3月,新诗集《深呼吸:米家路中英对照诗选1981—2018》(以下简称《深呼吸》)的出版[1]②,才让人们惊喜地发现,原来这位涉猎广泛、关注新诗的评论家,亦是一位潜心诗坛、钟情于诗的创作者。难怪慧眼如炬的乐黛云,曾以“火花式的”[2]“抒情和诗化”[3]等特点评价其诗论。诗集甫一出版,立即引起海内外诗坛文友们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评价。旅美作家哈金指出:“《深呼吸》是一本别致的诗集,其中的诗十分纯粹。它们表现了诗人独具的品格:敏感、沉静、超脱却又执著。”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亦评价此集:“是一个修行了三十七年‘深呼吸’的诗人,加上纯净的灵魂洗礼,而终于产生的一种穿越时空的精心成果。”诗人及评论家杨小滨则进一步指出:“米家路诗歌中的纯粹抒情在现今的诗里已经相当罕见了……令人赞叹。”[1]不过,相较于海外学者的主动关注与积极评价,由于诗人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即长期定居海外,且其诗集出版时日尚短,目前国内有关诗集《深呼吸》的评论与研究还不多见。但无论是从海外汉语诗歌研究的角度,还是从诗歌书写特质的角度,米家路的《深呼吸》都不应被轻易忽略。
米家路,原名米佳燕,重庆人。1981年,就读于四川外语学院(2013年更名为“四川外国语大学”)期间,开始新诗创作及研究,其后笔耕不辍,1996年赴美留学,2002年开始任教于美国新泽西学院。现出版有诗学专著《望道与旅程:中西诗学的幻象与跨越》《望道与旅程:中西诗学的迷幻与幽灵》《身体诗学:现代性,自我模塑与中国现代诗歌1919—1949》;主编旅美华人诗集《四海为诗:旅美华人离散诗精选》,该集被乐黛云高度评价为:“近年来第一部流散海外的华人诗歌的总集”[4];2019年3月,个人诗集《深呼吸》出版。据诗人自述,《深呼吸》是其潜心新诗创作37年来的首次结集,其中的“大多数作品均首次从幽暗的箱底翻跃出来见光面世,仿佛深深呼一口气,感叹,‘活着真好!见光真好!’”[1]6。在诗集中,诗人依循倒叙闪回的时间次序,将诗歌依次分为三个篇章:“天涯离骚1996—2018”“望气歌乐山1985—1995”“青春流光1981—1984”。可以说,《深呼吸》是诗人多年来潜心于诗、执著于诗的有力明证,记录了诗人从青涩走向成熟、从故土走向漂泊的生命历程,展现了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与诗学信仰。
而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作为米家路持续关注与密集书写的主要意象群,值得关注。据笔者统计,《深呼吸》共收录诗作115首,而以自然风物为题的诗作就达57首,约占诗集总量的50%。而且,无论是在“青春流光”还是在“望气歌乐山”亦或“天涯离骚”中,自然意象,始终是诗人书写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自然意象,既是诗人一以贯之的主要审美对象,也是诗人诗灵迸发的重要载体,承载着诗人不同生命阶段的诗情与诗思。而在诗人独特人生体验,以及日益圆熟的诗学系统的烛照下,自然意象在米家路的诗歌中呈现出丰富、独特、多维的审美质感。下面,本文将从书写路径、书写缘由以及书写策略等三个方面对米家路诗歌中的自然意象展开探讨。
一、从“浪漫”到“智性”:自然意象的书写路径
九叶诗人郑敏曾表示:“诗人的创造灵感与对生命的敏感与经验都凝聚于意象中。”[5]意象,作为诗歌审美的核心要素,既是诗人主观情感的具体载体,也是我们窥探诗人内心世界、把握诗人创作心境、了解诗人美学趣味及艺术理想的重要切入口[6]。《深呼吸》作为一部横跨诗人37年人生旅程的里程碑作品,在诗集中,诗人以其诗意的笔触为我们点化、建构了一个较为丰富的意象世界。但总体而言,自然意象,始终在诗人的创作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我只是以歌当歌,表达我对自然、文化和人最基本的思想和感悟。”[1]419不过,伴随着诗人诗思的发展演变与日益成熟,自然,在诗人的笔下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依循诗人的人生际遇与诗思变化,呈现出从“浪漫”到“象征”再到“智性”的书写轨迹。参照《深呼吸》中的时间篇章,下面依次梳理自然在诗人各阶段诗作中所呈现的不同特质。
顺着时间之流溯源而上,诗集的第三部分:“青春流光1981—1984”,收录了诗人踏上诗歌创作“醉舟”起首阶段的主要作品,这一阶段可以说是诗人诗意的觉醒期。据诗人追忆,当时促使其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受“无可抗拒的青春期激情”的怂恿;一是受两位“诗歌王子”柏桦、张枣的感染与影响[2]。从这段表述不难看出,诗人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原因即带有几分浪漫主义的色彩。而纵览这一时期的诗歌作品,不难发现,诗歌中充盈着的也正是青春时期不可复制的阳光与朝气、浪漫与激情。“春天”“黎明”“阳光”“星光”“海洋”等洋溢着青春气息与浪漫色彩的自然意象,在诗人此时的创作中密集出现。试看两首诗人的早期作品,其一:“你是春天的信使,/你轻轻的呢喃,/婉转的歌喉,/点破河水的清波,/唤来旖旎的春光。”(《燕语》节选)其二:“当暗夜悄然离去,/黎明轻盈地降临,/在小径旁的草尖上,/你正聆听草间的耳语,/而未听见黎明的足音。∥你是那么甜蜜,柔顺,/那么亮丽,晶莹,/你是黑暗的见证,/你是时间的音韵。”(《晨露》节选)在这两首诗歌中,诗人都以第二人称对话的亲切口吻,将自己的内心感受投射进自然意象中,如以燕子的归来传达春回大地的喜悦,以草尖的晨露呼唤黎明的到来,在对自然美好与生机的描摹中,蕴藏着诗人对生活、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可见,在早期作品中,诗人对自然意象的书写,主要借鉴了浪漫主义诗歌常用的“自然的情感化”的方式,借助自然意象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诗歌中洋溢着积极乐观的浪漫激情。虽然此时诗人的诗歌技巧稍显稚嫩,但情感真挚、青春逼人。
“望气歌乐山1985—1995”,主要收录了诗人“北上南下”十年求学时期的诗歌作品。1985年,米家路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赴北京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师从乐黛云;1992年南下香港求学,并于1996年获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从诗作来看,相较于前一时期,此时,诗人的诗思开始由外向内转,在对历史的文化寻根,以及对内在自我的不断思索与检视中,逐渐摆脱了青春期的幻想与躁动,情感更为内敛、节制。与此同时,诗人诗学视野也逐渐开阔,此一阶段,诗人注意吸收和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诗艺技巧,隐喻和象征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较为普遍。这一时期,可视为诗人创作的转型期。与此相应,自然意象,在诗人笔下也呈现出新的质感。以这一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诗作《鸟在黄昏》为例,全诗共四个诗节,在第一、二节中诗人这样写道:“鸟归回之际/黄昏漫过灯塔幽暗的边缘/如梦的渴望回答着我/我摸索着/试图找回一种不复存在的印迹/或者归入印迹的启示中去∥子夜的晕月使我回想起/正午突然悸动的钟摆/马车从远方驶来,车轮/切开河岸与冰的距离,游鱼/闪示出我出生时食指的预言”。在诗中,诗人虽仍然以“鸟”“月”“马车”“河岸”“游鱼”等自然意象为书写对象,但在具体书写中,诗人开始摆脱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转而吸收象征主义常用的通感与隐喻,将自然、世界看作自我的影子,试图在梦幻般的状态下,体会万物之间种种互通的神秘感应,客观的自然与主观的幻想互相嵌入浑融,形成物我难分的诗歌意境,使得这一时期的自然意象书写,呈现出鲜明的象征主义特点。
“天涯离骚1996—2018”部分,主要收录了诗人自1996年负笈海外至2018年的诗作。从个人际遇而言,1996年诗人赴美留学,并于2002年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博士学位;同年就职于美国新泽西学院,目前为该校英文及世界语言文化系副教授,中文及亚洲研究学部主任。这一时期,诗人离家去国,以诗的形式记录下自己海外漂泊离散的复杂心路[1]6,为海外汉语离散文学贡献出一批高质量诗作。这一时期,诗人诗学视野进一步开阔,知识系统日益完备,诗歌的创作技巧也日趋成熟、稳健,诗作中的自然意象也从“田野”回归到“日常”,对生命存在与价值的哲理性思索成为诗人此一时期创作的主要内容。这一阶段,可视为诗人创作的成熟期。在这一时期中,虽然诗人身处都市文明发达的异域国度,但诗人最为敏感,着力书写的仍然是自然界的季节更替和一草一木,尤为突出的是对“雪”这一自然意象的观照。
“雪”,作为米家路钟情的自然意象之一,自创作伊始就大量出现在诗人的诗歌中。在1981年刚刚开始新诗创作时,诗人即歌咏道:“我爱雪花,/我爱被雪花点缀的世界,/虽然我在南方长大,/但这爱已从小就在心中萌芽。∥……我爱每一朵飘柔的雪花,/山边冬梅散发出的雪香,/漂浮在江河上面的雪冰,/收割后稻田里的雪霜。∥我爱雪花,/人间万物经她的洗礼,/变得更加圣洁无瑕,/她宁愿自己消失,/也要换来春天的鸟语花香。”(《我爱雪花》节选)不难看出,在早期创作中,诗人主要以纯真的笔致,抒发自己对于自然之雪的喜爱,并将自己对纯洁、美好的向往寄托于“雪”的意象中,洋溢着青春独有的单纯与浪漫。自诗人离家去国后,“雪”更成为其书写的重要意象之一,如《雪中迷蝶》《暴风雪袭来之前观鸟》《2010年第一场雪》《2012年冬天第一场暴雪纪事》等,都是以“雪”为书写对象传达诗情的诗作。而在这其中,创作于2018年初的《望雪》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春分时节
大雪却悄然而至
落满了后院
困搁在室内
望着窗外的雪花
瞥见一只孤鸟窜起
突然想起雪意的滋味
比如
背靠火炉
透过明亮的玻璃
观看外面的飞雪
与
伫立在飞雪中
受扑面雪花的拍打
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我猜想
透过玻璃观雪
玻璃更冷
心更暖和
望雪其实是望月
就是对空白的遥望
伫立飞雪中观雪
心更冷
雪更暖和
望雪其实是望水
就是对逝者的凝视
透过玻璃望雪
月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幻影
伫立雪中嚼雪
雪花漫过舌头便成了血脉
这首诗,语言素朴,叙述简洁,却充满耐人寻味的细节。在诗中,诗人不再以情感抒发为首要目的,转而返身日常经验,借助对“雪”的观望与凝视,开启对自我、对生命、对生存的智性思索。在诗中,诗人以自我对话和比较的方式,探讨与揭示出“雪”作为中华民族原型意象,与“月”“水”等意象间微妙的情感关联。在诗人眼中:“望雪其实是望月/就是对空白的遥望”;“望雪其实是望水/就是对逝者的凝视”。以诗人之思,洞悉了覆盖于自然意象之上隐秘的民族心理。在此基础上,诗人又进一步以“透过玻璃观雪”与“伫立飞雪中观雪”两种不同的望雪环境,展开对生命存在方式的智性思索。在不断对比后,诗人感悟到:“透过玻璃望雪/月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幻影/伫立雪中嚼雪/雪花漫过舌头便成了血脉。”点明诗人向往自然、倾心自然的人生哲学。可见,此时的“雪”已经不再是自然界中单纯的雪花和雪景,而是诗人感性与智性相契合的承载物,呈现出鲜明的智性诗特点。可以说,这一时期诗人对自然意象的处理方式,实践了诗人早年提出的创作宗旨,即:“诗是一种情感智化的纯粹的复合体,它并不向人们昭示诗人个人隐私的意图和契机,它是一种蠕动的氛围,一团布满了窗眼的空气,能畅入畅出。”[1]418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然意象和日常经验的加持下,米家路诗歌中的智性思索涤除了智性诗歌普遍带有的晦涩之味,呈现出明朗亲切的诗歌质感。
二、“返乡”母题的烛照:自然意象的书写缘由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在米家路长达37年的诗意旅途中,自然,始终是他关注与书写的主要意象之一。不过,就诗人自身所处的实际环境而言,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的踏水乡与歌乐山,依然保留着诗人与自然心心相印的呼吸空间的话,那80年代后期,诗人为了求学先后前往北京、香港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直至1996年移居海外,可以说,存在于诗人周围,纯粹的自然空间,其实正伴随着社会的加速发展和诗人的屡次迁徙,而不断遭受挤压与侵蚀。有鉴于此,我们不禁想问,为何在都市文明、工业文明的层层包围下,米家路却始终钟情于自然意象的反复书写呢?对自然意象的持续关注,仅仅只是由于诗人自身的诗学趣味和美学倾向吗?对此,阅读诗人的相关诗论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就诗人身份而言,米家路不仅是一位执著于诗的创作者,亦是一位横跨中西、学养深厚的诗学研究者。作为学者,米家路的研究视野较为广泛,既涉及诗学也兼论散文、小说、电影、哲学等领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多面手。不过正如学者刘再复在《米家路诗学序》中所言:“诗论是它(指米家路的诗学论著——笔者注)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兴奋点和归宿点。”[7]由此不难看出,诗学在米家路的学术研究中的核心地位。而作为一位视野开阔的诗学研究者,米家路对现代诗歌中的自然元素尤为关注,如《城市,乡村与西方田园诗:对一种文类现象语境的“考古学”描述》《奇幻之旅:毕肖普旅行地理学中的海洋景观》《河流抒情,史诗焦虑与八十年代水缘诗学》等都是以自然为线索而展开的诗学研究。而纵览米家路的诗论,其中最“‘明心见性’即明诗心,见诗性”的,即他在对中西诗学的梳理与回顾中,洞察与提炼出的“还乡”母题[7]。对此刘再复曾表示:“米家路的整部诗学论著,可视为‘放逐’与‘还乡’的主题变奏。”[7]
在对中西诗学的纵向梳理与横向比较,以及对中外现代诗人经典作品的细读中,米家路以一位诗人的敏锐与学者的理性,察觉到现代社会、工业文明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异化。“诗人栖居的家园被现代化的潮流吞没了,诗人的本己存在被潮流卷走了,世界被异化,被物化,被僵化与被机器化,诗人无家可归,真人无可逃遁。”[7]因此,在米家路的诗歌中,相对于自然的和谐、纯净与美好,现代都市往往被颓废、失落、病态以及无家可归的负面情绪所包围。“帝国的秋日/易开罐废弃/人民依然焦渴/高耸入云的黑烟/席卷GDP沉灰的天空∥在通往地球的咽喉处/人民呼吸的鼻息淹没”(《异乡人的秋日之十三》节选)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帝国,被人类盲目追逐物质与利益的废弃物持续污染与包围着,毫无生机。而生活在其中的人,在背弃、侵害自然的同时,也亲手将自己推入危险的境地,咽喉被扼,随时有窒息的可能。而在另一首书写异域体验的诗歌中,诗人写道:“午夜,一个中国人行色匆匆/在湿漉的时代广场上穿行/霓虹灯闪烁如乱窜的怪兽/搅乱街头急促的呼吸/艳女郎的红唇喷血如熔浆/吞噬着行人饥饿的胃/地面上冒出鸦片的气味/刺激人群疲惫的神经。”(《夜行纽约》节选)“怪兽”“熔浆”“吞噬”“鸦片”等隶属黑暗并带有恐怖色彩的意象,渲染出现代都市魅惑邪恶的“恶之花”属性,生活在其中的人也必然是异化的、扭曲的。
由此可见,在诗人眼中,充斥着物质文明的现代都市,已经无法为生命的存在与延续提供有益的场所与环境,“唯一可以‘自救’的道路便是‘还乡’(着重号为笔者所加)”[7]。在此,“还乡,意味着人性的复归,也意味着诗性的复归”[7]。而具体到何谓“还乡”,米家路在其诗论中有明确的解释:“现代诗人所‘还’的‘乡’绝不仅仅意指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乡村的回返。本文中的‘乡’的意思还包括自然本身(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自然之物,本样本原世界等)和精神本体世界(即终极性,真善美的‘家园’)。后者是前者得以神圣化移情的根据;前者是后者得以显现的媒介。也就是说,诗人是在对都市化进行否决之后所发出的对乡村、始原世界和精神家园的‘还乡’行为。”[3]据此可见,对自然的持续书写,是米家路渴望复归人性,并对人类业已异化的精神世界进行净化的重要途径。这里我们可以以诗人所写的《2012年冬天第一场暴雪纪事》一诗为例。
在诗中,诗人以纪实手法,记述了一夜暴雪之后,女儿第二天的日常生活和之后的计划。在诗歌的一开始,诗人首先为我们描述了大雪之后,自然精灵重现大地的情景:“先瞥见一只小松鼠吊在树干鸟笼上,/猛吃玉米粒儿,一定是饿极了,/松鼠瞧见了我,急忙跳下树枝,/跑到另一棵大树下继续吃,/爪上捧着食物,两只眼睛直盯着我。”而此时的女儿,则拿出刚买的滑雪板“说‘滑雪去!’/她兴奋地把身体俯在雪板上,/来回滑动,嘴里不断念叨,‘太棒了!’/雪板在积雪的街道上很快滑走,/女儿说,‘铲雪车来了就不好玩了’”。在这里,诗人以直接引语的方式记录下女儿充满童心的话语:“滑雪去”“太棒了”和“铲雪车来了就不好玩了”。刻画出孩童对自然乐园的惊奇与喜爱,以及对工业机器破坏自然乐园的反感。之后诗人又以纪实的方式,详细记录下女儿去公园以及与小伙伴们一起去校园滑雪的故事。而在诗的结尾,诗人写道,据天气预报预测,今夜仍有大雪,这时“小女儿惊奇地问道,‘那明天做什么?’/我一边脱靴子,一边擦眼镜,/然后对着镜子哈了一口热气,/看着冻红了双颊的女儿,回答说,/‘明天我们又滑雪去,怎么样?’”全诗到此戛然而止。
表面看来,全诗只是对暴雪初霁后,女儿一天滑雪生活的简单记录,展现出儿童的天真与可爱。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在诗歌中,天真可爱的女儿似乎暗示着人类天性中与自然相亲相近的原始情感;“滑雪”则代表了人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与和谐互动;“铲雪车”无疑则是现代文明对自然的破坏;而诗歌结尾听说今夜依然有大雪,面对女儿的疑问,诗人表示:“明天我们又滑雪去,怎么样?”这看似是诗人对女儿童心的呵护,其实亦暗藏着诗人一以贯之的诗学理想。正如上文提到的《望雪》一样,相对于隔着透明玻璃与自然保持距离与隔膜,诗人更倾向“伫立雪中嚼雪”,让自然直接汇入血脉,进而达到精神与人性的复归与净化。可见,诗人对自然的反复书写,不仅出自于对自然的单纯喜爱与依恋,也蕴含着是诗人所提炼与推崇的“返乡”母题。这或许才是诗人之所以执着于自然书写的主要原因。也正因如此,自然,在诗人笔下不再是单纯的抒情对象,也蕴藏着诗人的生存哲学、诗学理想与心灵寄托。这也是为何米家路诗歌中的自然总是纯净自在、清澈透亮的原因之一。
三、“新古典主义”:自然意象的书写策略
在诗集《深呼吸》的北美发布会上,米家路以“新古典主义”[8]总结自己的诗歌特色。注重中国传统诗歌艺术与现代诗艺的融合,既是米家路诗歌的创作特点,也是他书写自然意象的策略之一。作为一名海外汉语诗歌创作者,米家路既与汉语以及中国诗歌传统保持着天然的血脉联系,自觉要以“犀利的汉语之光照亮异乡人的旅途”[4],也主动吸收域外诗歌中的现代诗艺。他说,古代诗歌中的意象、词汇和思想离当代生活太遥远。而所谓“新古典主义”,就是用现代的语言、意识和技巧把中国古典文化、诗歌的意象与意境进行现代化商务表达。用现代化方式让诗歌得以推广和介入现代生活[8]。在自然意象书写时,米家路也注意以“新古典主义”展开观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互涉辉映下,自然意象在米家路的诗歌中呈现出丰富多维的质感。
“新古典主义”的书写策略,首先体现在米家路诗歌中的很多自然意象,都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情结与审美意趣。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相较于西方诗歌注重表现人与自然的对峙,或者只将自然视为人的精神理性的体现;中国传统诗歌强调“天人合一”,倾向于将自然作为歌咏的对象,“而且大多表现出人与自然的物我相得,欣然融洽的意趣”[9]。表现在诗歌中,最显著的特点即在于,传统诗歌中的季节意象与季节感特别突出。早在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中即有:“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陆机《文赋》中亦提到:“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对此,日本汉学家松浦友久也表示:“在中国古典诗里,季节与季节感作为题材与意象,几乎构成了不可或缺的要素。”[10]
不难发现,在米家路诗歌中,很多自然意象也都带有鲜明的季节和季节感。如诗歌《南泉春游》《春之校园》《野餐之趣》《春夏之交》《秋歌》系列、《望雪》《春日响雷》《立夏偶感》《秋日的草垛》《异乡人的秋日》《雪中迷蝶》《暴风雪袭来之前观鸟》《2010年第一场雪》《2012年第一场暴雪纪事》等等,从诗题中即可感受到强烈的季节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诗人阅历与心境的不断积累与变化,季节意象与季节感,在其诗歌中也流露出明晰的变化痕迹。如在“青春流光1981—1984”部分,诗人正处于精力充沛的青春期,在创作中,春天以及与春天有关的,充满希望的季节性意象较为常见:“寻着春天的弦音,/踏着嫩叶的银铃,/拉着袖口的旋风,/来到温泉池边。∥我微笑,向/花蕊里甜蜜的春雨,/摇醒的蝴蝶花瓣,/抽芽的绿树与湛蓝的天。”(《南泉春游》节选);而在“望气歌乐山1985—1995”和“天涯离骚1996—2018”中,随着诗人生活与心态的转变与成熟,虽然仍有一部分诗歌涉及春天,但相对而言,秋冬以及与秋冬相关意象的书写更为密集。如诗人在北大与香港中大期间创作的四首《秋歌》,就是以丰富的自然意象对“秋实”“秋风”“秋雨”和“晚秋”的书写。移居海外后,冬季以及与冬季相关的自然意象,在诗人的诗中更加频繁,如前文所提到的《望雪》《2012年第一场暴雪纪事》等即是如此。除此之外,在具体创作中,米家路诗歌中的很多自然意象也与传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在一些诗歌中,诗人依然沿用了自然意象的传统含义,如以桃花、李花的凋谢,暗示春天的逝去,“向春看,/桃花谢了,/随着春;/李花也谢了,/留下满枝的嫩挂”(《春夏之交》节选)。而在一些诗歌中,诗人更直接沿用传统诗歌中的自然意象,如在诗歌《世纪末:风·雅·颂》中,诗人就以《诗经》中常用的自然意象:河流、鲜花、鱼、酒、粮食、火、秋天、雨等来结构诗情。
以现代诗艺熔铸传统意象与意境,也是米家路自然意象书写的方法之一。作为一位长期浸淫于西方诗学的研究者与创作者,米家路对西方诗学、现代诗艺相当熟悉。他深知古典诗歌中的意象与现代生活相距甚远,因此,在使用传统自然意象的同时,也十分注意以现代意识与技巧为其注入现代诗思,以保证诗歌能与当下接轨,准确传达诗人的本真感受。在具体创作中,米家路“主要采用现代意识、技巧和西方现代主义的片段化、潜意识和无意识的表达,让古典文化接轨现代”[8]。以诗歌《雪中迷蝶》为例:“我为何来此?/背井离乡,朝/更死亡的方向逼近/别了吧,暖春啊,暖春∥何以如此残暴、凶狠?/持续向下的伏击,将/我的羽翼散乱,扑腾/狂醉的气流激起浪漫∥谁的梦将我唤醒?/戴面具的影子悬空,赤裸/挥动旌旗,拍击浑圆的日鼓/那鼓声令我战栗,耳叶纷坠∥多么想跳一曲更刺骨的花舞哦/百合花瓣瓣赴死的卷扬,旋滑/令这撕裂的爱情更凄美/我柔软的翼啊,会斑斓在下个春日?”诗歌中的“蝶”依然带有传统诗歌中“庄生梦蝶”的影子,“谁的梦将我唤醒?”但在具体书写中,诗人以第一人称(传统诗歌很少使用第一人称)所发出的疑问开篇,从主体角度将“蝴蝶”在刺骨的风雪中摇摇欲坠、濒临死亡的切身感受展现得淋漓尽致。而通过戏剧性场景的搭建,以及象征、隐喻等现代诗艺的使用,诗人以“雪中迷蝶”的所感所想,暗示人在迷途、在逆境、在异乡,在巨大生存压力下的生存体验,赋予自然意象以强烈的主观感受。
“新古典主义”的书写策略还体现于,在自然意象的书写过程中,诗人不单单局限于对自然意象的客观描摹,还积极融入自己的情感与思索,在亦真亦幻的诗境中,蕴藏自己的哲理感悟和主体感受。以诗歌《裂》为例,在诗歌开始,诗人有这样一段引子交代了本诗的来历:“二月某日清晨驱车路上,/偶然瞥见一棵大树从中劈开,/其扭曲的断枝弧形般耸立/在积雪的大地上,裂变的/曲折美令人诧异。”全诗录如下:
裂
裂
裂
裂 裂
裂
裂
裂
从垂直的向度,以势不可挡的
渴望,撕裂皮和肉
毫不畏惧坠落,向下,向下
朝崇高反向剥离
——裂必是一种低度的诞生
挣脱躯干的瞬间
缘于地心的暴力,扭曲
释放刻骨铭心的痛,耸立的
纠缠塑造生动的大地
——裂必然呈示大道的生成
谁曾瞥见这剧变的时辰?
它或许发生在天地混沌的暗夜
或许发生在天地开启的黎明
以弧弦的姿势,持续弯曲
直至意志力在零点折断
裂的碎声从何处溅出
是从躯体内的筋络处
还是从骚动的根茎处?
涅槃的叶片嗖嗖拍击
断枝间悬空的积雪
裂必是一个纯然的动词
它不及物的开放溶解尘土,撩拨
腐烂的气息,令折翅的
羽毛自由下坠,真空无限的轻
水银般弥漫,擦亮一束束光芒
在《裂》中,诗人以自然界中发生裂变的树为书写意象,叩问与追索了“裂”的哲学意义与存在价值。在具体书写过程中,诗人首先借鉴了西方现代诗学常用的视觉诗形式,以汉字“裂”在空间上的有意安排,直观呈现出被劈开的大树的形态,给人以强烈的树之裂变的视觉冲击和震撼。不过,诗人并没有停留在视觉诗的建构与诗意的暗示上,而是继续以通感、幻想、隐喻和象征等现代诗歌技巧,并结合道家与存在主义的哲学理念,赋予“裂”以反崇高、追求独立的精神品格。在诗人看来,反抗宇宙之力的裂变,源于一种内在的渴望,是对崇高的解构、对过去的挣脱、对“大道”的追求。在对“裂”的时间和根源的诗学追问中,诗人进一步肯定了“裂”的必然性与主体性。在最后一节中,诗人更从形而上的角度,以语言学词汇与想象场景的并置与拼贴,宣示“裂”中暗藏的生机与力量,赋予自然意象以现代诗思。而在诗情表达中,诗人融主体于客体,以“树之裂”暗示诗人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思索。长期的跨文化生存体验,背负母国文化的异乡人生活,在诗人眼中是否也是一种“裂”呢?而这种文化之裂、身份之裂、精神之裂,是否一方面让诗人感受到撕裂的痛苦,一方面也开阔了他的视野,给予诗人拨开迷雾、追求真理的力量呢?可以说,在自然意象的书写中,诗人放入了自身的个体感受和对生命的哲理思索,达到了心灵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对应与契合。
在《深呼吸》的编辑说明与致谢中,米家路感慨道:“笔者真没想到对诗歌深吸的那一口原气居然存活了三十七年的星际旅程,犹如潜隐江湖的苦行僧,在岩层底下默默修行,无关世事纷争,既刻骨铭心体悟真道,又随遇而安漫步生命历程,所以这部诗集与其说是呈现诗歌某些高超精湛的神秘技艺,还不如说是作者奉献给广大读者那口恒而持久的、锲而不舍的修行魅力与心灵真气。”[1]感悟生命、专注内心,可说是米家路诗歌创作的重要源泉。而在这一过程中,对自然意象的执著书写,也成为米家路诗歌的重要特点之一。在米家路的诗歌中,自然意象既呈现出从“浪漫”到“智性”的书写路径;也与他提炼推崇的“返乡”诗学高度契合;而在中西美学互涉交融的“新古典主义”的观照下,自然,也呈现出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的诗学魅力,值得我们阅读与欣赏。
注 释
① 多年来,米家路一直致力于现代诗学研究。著名学者刘再复曾表示:“他(米家路)的诗歌视野深厚宽广,论述扎扎实实、抓住了现代诗人的大苦闷和他们展示的诗意梦想,从而道破了中西现代主义诗歌的主题变奏,的确是一部非凡价值的诗学著作,让我们读后,不能不赞叹,不能不赞美。”(参见米家路:《望道与旅程:中西诗学的幻象与跨越》,秀威资讯科技2017年版,第5页。)2018年9月,米家路获得由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江汉学术》编辑部主办的第三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敬文东、姜涛为其颁奖,授奖词为:“米家路致力于创作主体精神面貌与心理镜像/反镜像的挖掘,通过重构外部经验与内部体验、异乡与原乡、西方与东方等因素的阐释结构体、持续校准着诗学研究各要素的空间坐标。同时,他在研究中植入了时间性的自觉,经由记忆修辞、潜意识碎片等坐标点,绘制出对现当代诗学的社会—文化想象图景,使之进入到某种充盈着历史气息的‘创造’状态,形塑出了研究者的‘自我’。”(参见米家路、杨小滨、盛艳:《第三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颁奖录音实录》,《江汉学术》2019年第2期。)
② 本文所引诗歌如无特殊说明均出自该诗集,故不再一一标明。需要说明的是,《深呼吸》为中英文对照诗选,原文为米家路创作的汉语诗,后经译者翻译为英文,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米家路的汉语原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