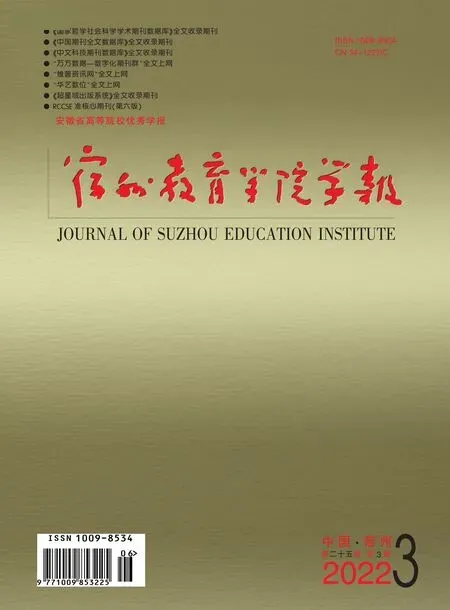文化差异与反思
——论《无声告白》华裔群体身份重建
陈韩韦虹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无声告白》是华裔新晋女作家伍绮诗所书写的长篇处女作,2014年出版不久便被美国诸多媒体评为最佳图书。小说的主人公詹姆斯·李是一位美籍华人,拥有纯正的华裔血统,但却因肤色和族裔问题无法融入白人群体。为了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获得主流文化的认可,詹姆斯决定与白人女性玛丽琳组成中美跨族裔家庭,以期在美国文化语境中站稳脚跟。而大女儿莉迪亚的突然死亡,却逐层揭穿少数华裔群体“成功”面具下的身份焦虑与自卑心理。《无声告白》中所涉及的族裔身份认同与归属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仅是美国特定文化语境在文本层面上的重述与再现,更是当今文化研究与批评领域中一个不能逃避的现实问题。
斯图亚特·霍尔是当代文化研究的鼻祖,作为一位移民到英国的非洲“黑人”后裔,霍尔不仅对文化“两栖人”的边缘处境与身份困惑深有体会,而且对文化的多重模式、全球族裔文化认同现状有着独到的见解。在《文化研究读本》一书中,霍尔就曾明确对文化研究的重点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让文化研究囊括种族的关键问题、种族的政治、对种族主义的抵抗、文化政治的关键问题,是一场深刻的理论斗争[1]。这种在理论上向种族、文化政治的关键问题宣战的斗争观念,是研究文化身份问题与文化认同问题所必然面对的意识形态难题。霍尔坚信,要想摆脱霸权主义下沉重的“殖民经验”,唯一的途径便是重视文化裂变的差异性,在文化裂变中寻求身份认同[2]。只有通过承认文化的差异性,才能在历史、文化、政治等语境中理解霍尔的文化认同理念。在后殖民语境中,霍尔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等传统文化认同问题转变为“我会成为谁”这一动态过程,强调了非中心化主体的话语权力对建构文化身份的重要性[3]。霍尔的文化认同理论,不仅能窥析詹姆斯等华裔群体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与文化失语困境、协助探寻少数华裔摆脱边缘人形象的内外驱动力,而且对华裔边缘人进行身份反思与重构、族裔间关系的改善以及中美文化交流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义。
一、《无声告白》中华裔群体的“他者”身份危机
《无声告白》以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末的美国社会为历史语境,揭露了西方“白人至上”意识形态对华裔边缘主体的文化压迫。在白人优越主义文化观念的支配下,白人对华裔的凝视与观察似乎已成传统。华裔群体典型的黄皮黑发外貌特征,在白色人种中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以致被划分为异类群体。文化身份的特殊性使詹姆斯及其混血子女不幸沦为白人眼中的 “他者”,游离于中美文化缝隙中,无法界定自身文化属性,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与情感焦虑。
(一)白人凝视下的文化“他者”形象
文化研究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族裔身份认同问题,往往带有明显的文化霸权主义倾向以及种族主义倾向。在《无声告白》中,虽然詹姆斯及其中美混血子女内斯和莉迪亚已经被白人主流文化所同化,但他们却始终因为肤色和血统问题而被排除在外,遭受着无尽的种族迫害与心理霸凌。白人目光中的厌恶与疏离,是他们成为“他者”对象、产生身份认同危机的影响因素之一。
异样的视觉凝视通常能够激发被凝视者的心理羞耻感,从而使后者产生低人一等的心理状态。“凝视”是一种“与眼睛和视觉有关的权力形式”[4]。在白人社会文化语境中,这种“凝视”包含了过多的权力话语,主要表现为文化、种族层面上的排他主义。詹姆斯的父亲是第一代华裔移民,凭借“纸儿子”契约身份来到美国谋生。在当时语境下,虽然美国国会因惧怕“大熔炉”杂质过黄而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但却允许在美华人子女入境,因此,詹姆斯得以在美国落地生根。然而,作为第二代华裔群体的代言人,不管詹姆斯如何向美国主流文化靠拢,都始终被排斥于人群之外。
“使羞耻者屈从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他人的审视与贬低”[5]。凝视者作为凝视的主体,通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为他者定性。白人眼中的詹姆斯被一味刻板化了,在他们看来,华裔群体就是一群“头戴尖顶帽”“留着大辫子”[6]113的苦力工,具有与生俱来的奴性。詹姆斯自小在劳埃德学院求学,是该校的第一个并且是唯一的东方学生。与众不同的华裔身份与特殊的家庭情况,使得詹姆斯饱受同学的嘲笑与戏谑,沦为集体注视下供人娱乐的笑柄。长久以来,詹姆斯一直试图融入人群,甚至以妻子玛丽琳的白人身份为依托组建跨族裔家庭,以期望摆脱华裔身份特性,从而得到白人群体的认同,但情况却始终没有好转。同样的,作为中美跨族裔混血,血统的杂糅性使内斯和莉迪亚重演着父亲的痛苦经历,亦不可避免地成为白人眼中的“他者”。大儿子内斯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家庭的与众不同,因为“他的父母从不出门交际,也不在家请客,没办过晚餐派对,没桥牌牌友”[6]59。詹姆斯一家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与周遭的一切显得格格不入,几乎可以被划分为社会中被疏离化的那一类群体。虽然内斯具有一半的白人血统,但他却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父亲那极为典型的亚洲人样貌。在年少时的一次游泳经历中,由于肤色与外貌原因,白人孩子不愿靠近他,甚至大喊“中国佬找不到中国啦”[6]88,这种赤裸裸的言语攻击比白人的目光凝视来得更为可怕,就好比被人揭下最后一块遮羞布,还要忍受始作俑者的嘲笑与羞辱,令人极度难堪。而大女儿莉迪亚则更多地继承了白人母亲玛丽琳的影子,尤其是那双湛蓝的眼睛。正是因为这双特属于白人的眼睛,詹姆斯与玛丽琳将偏爱全部给了莉迪亚,一度忽略内斯和小女儿汉娜的存在,以致兄妹之间矛盾冲突不断。然而,纵使莉迪亚在外貌上与白人更为相似,但由于她的筋骨里流淌着一半亚裔的鲜血,因此,亦不能规避白人凝视所带来的伤害。
作为华裔代表,詹姆斯及其子女一直期望被美国文化所接纳,但却因族裔身份问题而未能如愿。白人凝视对少数华裔的劣性定义,使他们敏锐地觉察到自己文化身份的不同。面对这种毫不掩饰的观察与质问目光,他们始终无法融入美国社会,在中美文化夹层中苟延残喘,无法定位自身文化身份,沦为自己和白人眼中的文化“他者”。
(二)身份认同危机及情感焦虑
在白人主流文化与华裔边缘文化的交锋碰撞中,华裔文化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作为华人后裔,詹姆斯虽然出生在美国,并早已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人,但是由于他的华裔外貌特征极为显著,却终究不被白人主流文化所承认。文化身份的游离与缺失让詹姆斯身陷囹圄,产生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无法从焦虑的情绪中脱离出来。
身份认同危机与情感焦虑是华裔群体在美国强势主流文化压迫下所面临的主要心理困境。在这种因边缘化身份导致的尴尬处境中,为了获取文化生存策略,美籍华人群体主要有三种价值取向,其中之一便是极力迎合美国文化,全力隐藏和否定中国文化身份[7]。詹姆斯自小便生活在美国,虽然最终在大学里任教,但他还是那个沉默寡言、没有几个朋友、惧怕社交的异类。透视詹姆斯的一生,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融入人群,他曾做过许多尝试。例如:在年少时,因害怕说话有口音,他拒绝和父母说中文;和玛丽琳热恋期间,詹姆斯也曾说谎隐瞒自己的过去;在意识到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时,他以玛丽琳的白人身份为枢纽,组建了跨族裔家庭,妄想通过婚姻媒介融入白人主流文化。詹姆斯对白人主流文化无条件地接受与认同,映衬出他对华裔文化的厌恶与排斥,表明他深受片面文化价值观的支配与残害。
除了向白人社会积极靠拢外,詹姆斯还严格恪守“模范少数族裔”行为准则,在社会不公中保持不争不抢的保守态度。然而,这种刻板形象却为白人主流社会种族主义的合法性提供了“公正”的充分依据[8]。当詹姆斯完成了哈佛的博士课程,并“坚信自己会被哈佛录用”[6]50时,他却被系里无情地拒绝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白人同学威廉·麦克弗森。显然,白人骨子里的种族等级观念已变相成为一种“玻璃天花板”,阻碍了詹姆斯的职业晋升,并将其排斥到文化边缘地带。
从本质上来说,身份认同危机是詹姆斯最大的焦虑来源。无论他如何努力尝试融入白人群体,迎来的却始终是无法合群的挫败感。白人对华裔的种族主义歧视与心理霸凌,致使以詹姆斯为代表的华裔群体产生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逐渐走向自我封闭。詹姆斯身份认同危机的爆发,衍生了一系列难以言喻的文化自卑感与羞耻感。当白人接待员对詹姆斯担任美国历史教授的身份感到惊讶时,他用饱含“自我辩护的锋芒之气”的语调来刻意强调他“是美国人”[6]9。詹姆斯的辩护姿态不仅展现了他对美国身份属性求而不得的迫切心理,而且恰好影射出其内心的情感焦虑与身份自卑。在一系列自欺欺人式的伪装之下,詹姆斯不仅沉浸于自己所虚构的白人文化身份假象中,而且还自私地将自身期待强加于最像白人妻子的莉迪亚身上,企图凭借女儿的“成功”来攻破自己无法突破的文化围墙,以此缓解内心焦虑感和自卑感。然而,詹姆斯这种过度的投射性“期待”,却使莉迪亚走向了谎言与悲剧。
虽然詹姆斯被美国文化所同化,并极力擦除自身华裔身份特征,但还是无法融入美国主流群体。白人的淡漠与疏离,触发了詹姆斯的身份认同危机,引起了一场持续发酵的情感焦虑。华裔在美国文化中摸爬滚打的辛酸与苦涩,难以得到白人的共情。在“成功”的假面具之下,实际隐藏着他们支离破碎的心。
二、《无声告白》中华裔群体的身份重建
虽然美国少数华裔积极尝试适应社会文化环境,但白人的刻意疏远已经让他们丧失心理优势。在内心沉重的自卑感与羞耻感的双重作用下,他们往往否定自我,低估自己的能力与水平,一步步沦陷为美国文化中的失语者。在意识到身份二重性的情况之下,美国少数族裔通过后来文学中的“双重声音”来界定自身身份[9]。莉迪亚深夜来到湖边,乘船前往湖中央,划向的不是死亡与殒没,而是精神上的涅槃重生,是对自我的超越与重新建构,反映出华裔新生代子女对文化话语权意识的提升与加强。女儿的自杀行为,同时也让詹姆斯接受自我与文化反思的洗礼。在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詹姆斯与自己达成和解,重建了文化身份属性。
(一)文化失语者的自我建构与人格独立
身份属性的缺失一度使詹姆斯一家退居到文化失语的边缘地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虽然法律被迫承认跨族裔婚姻的合法性,但这些家庭仍饱受外界质疑。詹姆斯的华裔身份,早已让这个独特的家庭千疮百孔。作为中美混血儿,女儿莉迪亚亦无法摆脱文化“夹心人”身份。
在文化失语境况中,建构自我与实现人格自由是华裔失语者构筑自身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在小说的前半部分,虽然莉迪亚被设置成了心理“消音”模式,但却早早暗示她已经沦为文化失语者中的一员。莉迪亚的失语在很大程度上与“模范少数族裔”神话有关。白人的“模范少数族裔”话语对族裔个体的压力不仅是消极的,更是极具破坏性的[10]。“模范少数族裔”这个标签,听上去似乎合理且美好。但在它的背后,却暗含着白人对华裔群体的错误认知,并且只会助长白人社会对华裔的隐性歧视。白人将华裔群体全部归结为“成功”的一类,不承认个体之间的差距性,这种一概而论的刻板印象使华裔群体不得不面对不平等现象。莉迪亚丧失文化话语权,正是由于白人对“模范少数族裔”神话所标榜的完美性。显然,莉迪亚并不属于成功的那一类群体。母亲揠苗助长式的教育方式,压得莉迪亚喘不过气来。在这种高压学习计划中,她渐渐跟不上节奏,成绩也相应下滑。但是莉迪亚不敢说出真相,她宁愿用谎言与伪装来欺骗母亲。她始终坚信,只有自己变得“优秀”,并“一心”向着母亲的职业梦想前进,才能断绝母亲再次产生离家出走的想法。
为了保证家庭的完整性,莉迪亚努力迎合父母的期待,用谎言构造了一个完美的乖乖女形象。自玛丽琳回归家庭之后,莉迪亚的真实自我便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戴着乖巧人格面具的虚假形象。一直以来,莉迪亚都默默承接父母的愿望,即使在毫无能力的情况下,也要执意编织谎言,甚至“连眉毛都不抬一下”[6]17。因为她知道,只有顺从父母的心意,这个家庭才能得以延续下去。然而不幸的是,当谎言越垒越高,基石已稳,已无法推翻重新来过时,莉迪亚已然泥足深陷,逐渐迷失了自我。但是,白人男孩杰克的谈话却让莉迪亚得到了启发,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活在恐惧之中,对这个脆弱的家庭再次分崩离析的恐惧。于是,在那个清冷的深夜,莉迪亚的独立人格与自我主体意识逐渐觉醒,获得了精神上的救赎。她不愿再为了他人而活,她要为自己而活,“从现在开始,她要做她想做的事情”[6]272。
莉迪亚的结局,不仅是消解白人偏见与家庭矛盾的试金石,而且象征着华裔失语者从 “沉默”到“发声”的意识转变。身为少数华裔的后代,莉迪亚以己为例,打破了“模范少数族裔”完美神话。在这种几近毁灭性的重压之下,她只能倚靠谎言来换取父母的爱与陪伴。莉迪亚的沉默与失语,不仅是她本人对父母的真情告白,更是华裔群体陷入文化失语现状的一个缩影。因此,为了建构文化叙事的话语权,华裔群体必须摘除“乖巧温顺”的人格面具,摆脱沉默的失语者形象,建构自我意识,实现人格独立。
(二)文化反思下的自我妥协与身份重建
在多元文化冲突的背景之下,少数华裔应及时突破自身文化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从自身出发,在立足于文化困境的同时,反思自身的文化处境,与自己、他人达成和解。这种文化认知模式,不仅有利于华裔群体重建自身文化身份,而且还能增进族裔间的交流与理解。
华裔群体的文化反思,弥补了身份认同观念上的狭隘与不足。乔纳森·卡勒曾指出:“文学作品为身份的塑造提供了各种隐含的模式。……在另一些叙述中,角色是根据命运的变化而变化的,或者身份是根据在生活的磨炼中所反映出的个人品格而决定的”[11]。人的个人品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华裔个体可以从客观事实出发,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调整自身心态,在文化夹层中不断反思,从而重建自身文化身份。在家庭危机爆发之前,詹姆斯一味追求白人主流文化,摒弃自身华裔身份,将自己的文化压力施加于莉迪亚身上,以此缓解自己内心的自卑感。不论他如何努力,也无法求得归属感并真正融入白人社会,文化认同与归属问题始终困扰着他。詹姆斯身份定位的失败,打破了华裔想要融入美国社会的幻想,暴露出华裔群体的心理创伤与文化烙印。
在莉迪亚的死亡谜底被揭开后,詹姆斯才彻底摆脱内心一贯以来的逃避主义思想,逐渐正视心理创伤,意识到自我反思与自我决定的重要性。“关乎差异或特殊性的政治首先是关乎同一性和普遍身份的事业之一部分,一个特殊性受到侵害的群体仍然应该享有与其他群体同等的自我决定的权利”[12]。要想消除这种文化上的阻碍,必然不能绕过它、甚至逃避它,而是要迎难而上,贯穿其始终,才能真正结束它。于是,当意识到一切委曲求全都无益时,经过自身文化反思,詹姆斯在中美文化夹层中找到了一种平衡的文化认同方式,即抛弃一味追求白人文化的片面观念,在承认中美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之上,将隐性的源文化与显性的现文化融合在一起。
于是,当詹姆斯再次见到“叉烧包”时,他能够自然而然地用中文大声表达出来,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舌头“仍然能够卷曲成它熟悉的形状”[6]201。“叉烧包”不仅使詹姆斯感受到了“甜咸交织的温暖”[6]202,而且还勾起了他对自己民族的回望,意味着他打开了那扇被迫尘封已久的记忆大门,并从容不迫地追忆自己消失的往事。詹姆斯从深刻的民族记忆中所获取到的足够的温暖与安全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渐趋治愈了其内心因双重文化交融而产生的痛楚和苦涩。对詹姆斯而言,民族文化将他从身份认同危机中解救出来,并且赋予了他沉重且坚实的情感支撑。因此,在对自我进行妥协的条件下,詹姆斯接纳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冲突的双重文化境况中找到了平衡的支点,并以此重建了文化身份,从而改善了被白人孤立的局面。在莉迪亚的葬礼上,白人邻居的态度也有了很大转变,他们“围住了李家人,抱紧他们的胳膊,说着安慰的话”[6]61。这表明,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詹姆斯一家赢得了白人邻居的认同。而詹姆斯与妻子玛丽琳之间也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在许多年的“沉默”之后,夫妻之间坦诚相见,二人的情感矛盾也以双方互为妥协的方式得到了修补。实际上,由詹姆斯与玛丽琳所组建的中美跨族裔家庭危机的解除,也是作者伍绮诗帮助少数华裔群体重建文化认同的一次尝试。
由此看来,要想回答“我们会成为谁”这个关乎于文化定位的关键问题,华裔群体必须要努力寻求一种能够保持平衡的文化认同方式,并以此摆脱“他者”形象。在小说结尾,詹姆斯寻求的不是单一的文化认同,而是通过摒弃“非此即彼”的文化二元对立思想,致力于探寻多元文化之间的平衡。詹姆斯对中美文化冲突的反思,不仅能够帮助他直面不堪的记忆与内心的伤痕,而且还有利于华裔主体积极采取对外沟通策略,从而重建自身文化身份,增进中美文化之间的理解与交流。
结 语
伍绮诗以自身“被观察者”视角出发,绘制出少数华裔追寻美国身份属性的艰辛历程,揭露他们在美国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艰难生存状态和文化失语困境。在少数华裔的“成功”表象之下,实则隐藏着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及情感焦虑。虽然詹姆斯及其子女成长于占主导地位的美国文化之中,并且有着全然西化的生活方式,但却因自身存在身份的特殊性而游离在这种文化之外。面对白人集体的视觉凝视,他们只能将自己封闭起来,用“沉默”的方式来逃避一切伤害。然而,当“沉默”一再起反作用时,华裔群体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文化反思,并决定不再“沉默”。从自身出发,与自己达成和解,是少数华裔摒弃文化二元对立、建构文化话语权的先决条件。因此,在中美文化交流依然冲突不断的背景之下,作为双重文化夹层中的“两栖人”,华裔群体更应摆脱他人的“凝视”与“期待”,实现精神上的成长与人格上的独立,力求追寻中美文化之间的平衡,最终在重塑自身文化身份的同时,积极发挥自身文化交流媒介的作用,求同存异,从而促进中美文化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