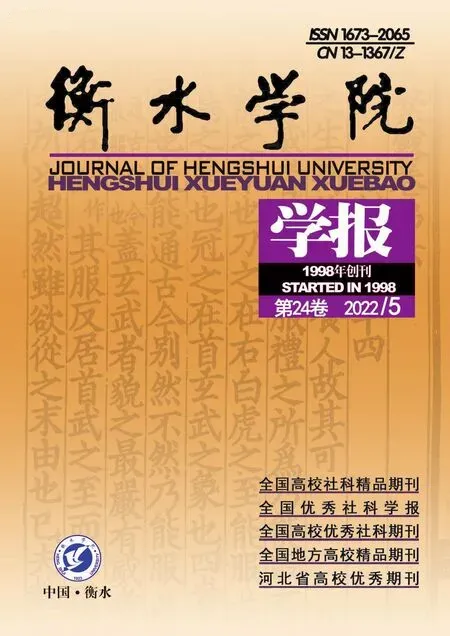董仲舒与司马迁对“白鱼赤乌”与“天命”传承的阐发
邓红
(北九州市立大学文学部,日本福冈北九州 802-0841)
一般认为,司马迁和董仲舒有师承关系。《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云云,这里的董生即是董仲舒。后面大段记述司马迁对《春秋》的答语,可看作是来自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教诲。《史记·儒林传》云:“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对董仲舒的春秋学评价甚高,甚至高过当时的丞相,“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誉美之情溢于言表。
在思想方面,司马迁的一些理论也可以在董仲舒那里找到依据。《史记》中可以找到许多和《春秋繁露》相同的思想片段,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就来自于《春秋繁露·盟会要第十》[1]。但是迄今为止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似乎还很薄弱,本文仅想以白鱼和赤乌体现出来的天命论为例,探讨董仲舒、司马迁关联的一些侧面,以求教于方家。
一、白鱼和赤乌的故事
《史记·周本纪》有这样一段关于白鱼和赤乌的记事:
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舟中,武王俯取以祭。(马融曰:鱼者,介鳞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众与周之象也)既渡,有火自上覆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乘船时,一条白色的鱼儿蹦上船头;一道火光翩然飞下屋顶,结果发现是一只红色的大乌鸦在那里唱歌。这两个自然现象本来应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不值得稀罕,所以周武王当初是准备把白鱼烤来吃了,《尚书大传》卷五《周传七》有:“中流,有白鱼入于舟中,跪取出涘以燎。群公咸曰:‘休哉!有火流于王屋,化为赤乌,三足。’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可见是因为群臣们的阻挡和神话式的解释,所以才由“燎”改为“祭”,而又正值诸侯汇集,白鱼入舟又被人们进一步神话,解释为“纣可伐矣”之象征;然周武对此次发兵能否一举成功没有把握,于是说:“女未知天命,未可也。”意思是说你们未必知道天命,伐殷似乎还没有到时候,便率师归还。等到周武王灭掉商纣夺得天下后,白鱼赤乌则被追认为是周革殷命之“天命”的象征,而在天人感应论盛行的汉代又为人津津乐道。
司马迁为八百年后的汉代人,当然不可能亲眼见到白鱼赤乌。他在《周本纪》写下这一段有关白鱼和赤乌的“记事”时,是以什么著作为蓝本的呢?在司马迁的《史记》中,白鱼赤乌一类的神话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查找先秦史籍,我们发现如此有关周革殷命之“天命”传承的重要“记事”,居然不见于讲究文武周公孔孟一脉承传的儒家经典之中,只能从其他一些古籍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墨子·非攻下》云:“赤乌街圭,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墨子间诂》解释云:
赤乌衔珪,毕云:“‘鸟’,《太平御览》引作‘雀’。‘珪’,《初学记》引作‘书’。”诒让案:《太平御览·时序部》,引《尚书·中候》云:“周文王为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入丰,止于昌户。王乃拜稽首受取,曰:姬昌苍帝子,亡殷者纣也。”《宋书·符瑞》志同。《史记·周本纪》集解、正义引《尚书·帝命验》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衔丹书入于酆,止于昌户,其书云‘敬胜怠者吉’云云。”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丹书文同,与此异。以上诸书,并作“衔书”,与《初学记》同。《吕氏春秋·应同》篇云:“文王之时,赤乌衔丹书,集之周社。”亦与此书“降岐社”事同,疑皆一事,而传闻缘饰不免诡异耳。降周之岐社,今本纪年“帝辛三十二年,有赤乌集于周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毕云:“《太平御览》云‘命曰:周文王伐殷’,《事类赋》云‘命伐殷也’。”
《墨子·非命下》也有:“太誓之言也,于去发。”《墨子间诂》解释道:
《诗·思文》篇,正义引《大誓》曰:“惟四月,太子发上祭于毕,下至于孟津之上。”又云:“太子发升舟,中流白鱼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曰:“得白鱼之瑞,即变称王,应天命定号也。”
以上《墨子间诂》在解释白鱼赤乌的由来时,提到了《中候》《帝命验》和《大誓》这三篇《尚书》的文章,似乎司马迁的记事来源于《尚书》。《周本纪》的《索隐》也说:“此已下至火复王屋为乌,皆见《周书》及今文《泰誓》。”
但是,《中候》《帝命验》两篇并非《尚书》中的文章,而是两本纬书,不足为凭。唯一具有真实性的,就是那个《大誓》了。
二、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历史观和天下观
《大誓》属于古文《尚书》中的一篇,出土于汉武帝时期。尽管有些文献上的可疑之处,讲的“天命”却一脉相承,司马迁使用它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司马迁就学过董仲舒,对他老师的那一套天人感应、天命传承的理论心领神会,于是《史记》的宗旨才会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探求天道和人事的关系,其中天命传承、天人感应应该说是最重要的内容。《天官书》云:“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通古今之变”,一个“通”字则告诉我们,古今天下的历史是连贯通衢、没有中断过的。其中一定有着某种必然联系,这就是“通”。
司马迁利用编写历史的机会,建立以天命传承、天人感应“究天人之际”为核心,以“通古今之变”为内容的普天下式的历史观。总的来说,这样的历史观有两个大的框架或亮点。
一个是“人”的大一统世界。根据司马迁和《史记》的叙述,早从三皇五帝起,中国就是一个囊括当时整个天下的“大”世界。譬如《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说,黄帝的足迹“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几乎和汉帝国的疆土重合。
其次,天下一开始就是“一统”的,夏、商、周都是全中国的统治者。不仅如此,三皇五帝也基本上被描写成整个天下的管理者。譬如“帝颛顼高阳者,……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址,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史记·五帝本纪》),而不管实际上这个一统的形式是多么的神话。而且夏只停留在传说时代,殷商以后才有实际上的支配,殷商在当时也似乎只是一个超级大国,实际上的统治并没有普遍天下。到了周代,“一统”达到理想的全盛时期,似乎天下的诸侯都是周王分封的,于是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其实周朝的管辖范围不出王城,其和各邦国也只是有血缘上和文化上的象征关系,周王绝没有后来的大一统帝国皇帝那样的权威、实力和管辖力,我们不妨将之称作“象征王”或“文化王”。
这种说法与其说是历史事实,还不如说是后世的司马迁以及汉代的人们勾画的“古代应该是那样”的理想蓝图,或可称为汉帝国的逻辑。任继愈先生曾说:“秦汉统一是中国社会历史上的一大变革。这个变革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封建王朝二千多年的格局——即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被中华民族所接受并认为这是正常的状态。”[2]如果将这个逻辑往前推,则得出这样的看法:“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整体性的,统一是常态,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分裂是变量。(秦)汉帝国的统一只是回到历史的常态,而不是新造。”[3]
应该说,对如此“大一统”帝国蓝图的描绘,是从战国时代就开始了的,最后由司马迁用许多历史事实、半神半人的“记事”——譬如本文提到的“白鱼赤乌”之类,乃至神话——司马迁根本不在乎神话和历史之间的界限,譬如《高祖本纪》中关于刘邦的神话在他看来就完全是真的,或者写得像真的,这也许就是人们往往把《史记》当作文学作品的理由吧——拼凑出来的。
于此问题就出现了:既然早从三皇五帝起,普天下就必须是一个“大一统”的世界,那么一定要有一个遍布天下、“一统”世界的手段和联系纽带、命令的传递方式乃至保证一统得以施行的系统。换言之,政治上的“大一统”,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行政手段和系统来实行,必须要有思想上的高度一致性来保障。但是在各方面都非常原始落后的远古时代,不但相互往来交通非常困难,甚至连语言文字都还不相通,要做到这些又谈何容易!
三、《尚书》中的“天命”承传
幸好在儒家的《尚书》中,早就为司马迁等撰绘“大一统”蓝图和历史的人们准备好了一套“天”之“命”即“天命”的承传系统。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关于“天”和“天命”的观念,都来自《尚书》的《甘誓》《汤誓》《牧誓》,也即是一脉相承的“天命”论。
《甘誓》是禹之子启和有扈氏在甘之野进行战争时作的誓词。启对部下们说,有扈氏犯有违反“天”之罪,故自己讨伐有扈氏是具有大义名分的,他说: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说是有扈氏犯有“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罪恶,违反了“天”的意志,所以天要惩罚有扈氏,这就是“天罚”。所谓“天罚”,首先是天切断赋予有扈氏的“天命”,再命令启去讨伐有扈氏。
《汤誓》是殷之汤王在讨伐夏桀时作的誓词。汤王为了取夏而代之,宣告夏桀违反了天意,自己夺取政权有正统性,说: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
这样的“天命”继承形式和《甘誓》基本同样。但夏桀犯下的违反天意的具体罪状不同:
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周人奉天对殷施行革命,这是殷人祖先干的同样的事的再演。《牧誓》里的“天命”继承形式,和前述的二个誓词,特别是和《汤誓》大同小异:
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泰誓》则有:
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上帝弗顺,祝降时丧。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
《尚书》见到的一脉相承的“天命”论,意味着得到“天命”也就等于有了正统的政治支配权,普天下的人都得俯首帖耳。换言之,“天命”就是那个遍布天下、“一统”世界的手段和联系纽带、命令的传递方式乃至保证“一统”得以施行的系统,是思想意识形态的保障手段。“究天人之际”说穿了就是对这个“天命”系统的理论探索;“通古今之变”就是用“天命”论去编织历史,描绘“大一统”的蓝图。
总之,“天命”是通过神秘的宗教形式灌输进了当时人们头脑中的思想观念。没有这样的宗教式信仰,要将拥有数千年历史、广袤的疆土、分散于中土大地的点文明揉在一起,装进一个大皮囊式的“大一统”帝国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四、董仲舒对“天命论”的理论贡献
董仲舒虽然是《春秋》学者,但对这个《尚书》中一脉相承的“天命论”是颇有心得的,这不仅是因为《尚书》是儒学的核心经典,“天命论”也是继秦而立的汉王朝企图巩固大一统帝国统治的理论根据。董仲舒生活在比司马迁稍早的时期,又是当时的学术大家,《尚书大传》《大誓》之类都是见过的,所以他对白鱼赤乌的神话时有言及。
《尚书传》言:“周将兴之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恐恃之。(《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赤乌。”此盖受命之符也。(《汉书·董仲舒传》)
这里的“《尚书传》言”“《书》曰”,都是引用的《大誓》之文。董仲舒引用这些文章,不仅是想说明白鱼赤乌为“受命之符”,而且要进一步建立以阴阳五行为表述方式的天人感应论,所以他在《贤良对策一》中紧接着上一句话说:
及至后世,淫泆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矣,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汉书·董仲舒传》)
认为统治者即使领得“天命”,也必须施行德政。政治正确,则天会施放出阴阳调和的好元气,向天下显示一些瑞符。反之,王的政治出现恶政,天则显现阴阳紊乱之贼气,谴告王的恶政。对于这样的理论,《春秋繁露·王道》有着详细的论证,譬如:“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①关于董仲舒的“天命论”的和“天人感应论”,拙著《董仲舒思想的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有详细阐述,本文以之为基础。可见在董仲舒那里,白鱼赤乌显然是和景星、黄龙之类相同的符瑞。
也就是说,董仲舒对“天命论”的贡献在于,他没有停留在一般性的故事传递和内容诠释,而是运用他独创的“天人合一”论对“天命论”进行了发展性改造,并通过贤良对策的机会,直接提供给了大一统帝国秩序的奠基人汉武帝。
而汉武帝在《贤良对策》的策问开门见山便问: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汉书·董仲舒传》)后来又问:
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汉书·董仲舒传》)可见汉武帝的“策问”就是以《尚书》的天命论为前提和基础,直截了当地询问“天命”落实到汉朝的具体情况如何的:我们汉朝受命的符兆体现在哪里?灾异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继承发扬先圣王们的长处?三代亡国之君桀纣们的错误和教训在哪里?天和人的关系如何处理?以什么来保持王朝的长治久安?
董仲舒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基本都是根据他的“天人合一”论的基本原则而提出的。
首先,董仲舒说:“天者群物之祖。”规定天为至高无上神祇。以此为前提,设计了灾害、怪异、伤败等三阶段的灾异论,通过对“天”的主宰性以及和人有关联,来证明“天人相关”。关于天意、天道、天命等,则说“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故天瑞应诚而至”,得到天命,才算得到人类社会的正统统治权。这里的“天瑞”虽然没有明说,应该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白鱼、赤乌、景星、黄龙之类吧。
其次,董仲舒谈论了儒家思想和“天命”的关系,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把“天道”“天佑”“鬼神之灵”和儒家政治上的德治主义、伦理道德之五常之道结合起来了。
在此之上,说人类社会的君主,要根据“圣人法天立道”之原则,天的“任德不任刑”之“天意”和“仁义”本性,行德治,修饬五常。反之,则不能维持“五常”之地上的社会秩序,也不能得到天的庇护,鬼神之灵佑。
总而言之,如对策所说“圣人法天立法道”“天人之征,古今之道,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往来相应”“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此故,王者上谨承天意,以顺命”“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将“天人合一”论基本原则融入传统的“天命论”中,将主宰之“天”和君主、“天命”和君主之德、“天道”和儒教理念互相联系起来,以把关于“天命”的诸问题、灾异、人事的根本等当时的政治课题,放在了他所创立的“天人合一”系统中,对之进行了神秘而又颇具智慧的诠释和陈述。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对“天人合一”的“天命论”也有详细的阐述。如《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通篇都是讲“天命论”:
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犹子安敢擅以所重受于天者予他人也,天有不予尧舜渐夺之故,明为子道,则尧舜之不私传天下而擅移位也,无所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诗云:“殷士肤敏,祼将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无常予,无常夺也。故封泰山之上,禅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尧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夺也,今唯以汤武之伐桀纣为不义,则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说,将以七十二王为皆不义也。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宁能至汤武而然耶!
王者有德受命于天而王天下、王无道而被讨伐、天命靡常、以德安民、有道伐无道等天命论原则都在其中。而《楚庄王》篇的“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讲新王改制以明受命于天,和对策里的“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一致,都是对“天命论”的发展。
五、司马迁对“天命”承传的历史性描述
和董仲舒不同的是,司马迁是个历史学家。历史(history)不是繁杂的文献堆积或单调的史事阐述,也不是枯燥的理论著述或神话般的宗教说法,而应该是各方面的结合。历史应该既有理论性,即所谓历史观、天下观,也应该有着故事性(story)的一面,才能“成一家之说”。换言之,以“天命”承传来作为“大一统”历史观的核心、以之来贯穿历史,有神话也有历史,有理论也有情节,天人相通,才叫通过“究天人之际”来“通古今之变”。
那么,司马迁是如何将“天命”承传系统编入历史中的呢?
先来看关于夏启的“天命”神话。我们知道,在传说的尧舜时代,王位是通过禅让来传承的,到了禹去世时,真正继承禹的王位的是禹之子启,为中国史上不用禅让而是世袭的方式继承王位之始,王位的继承法由此为父子或兄弟相传,开启了“家天下”之先河。那么,启凭什么得到帝位呢?司马迁在《夏本纪》开头,便为我们叙述了一个启的父亲禹治水的故事。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于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视尔事矣。”
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岛,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诸如此类,禹还治理天下了得,于是“九州岛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于是王位除夏禹家以外无人敢染指,尽管象征性地传给了皋陶,后来又传给益,益却不好意思接受而躲了起来,最后终于传给了启。当然不服气的也有,有扈氏就是一个,于是: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既然启奠定了天下用世袭的方式继承的基础,也就意味着“天命”必须在夏姒这个王族中代代相传。但到了夏代末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夏本纪》)。夏朝即露败象,说明“天命”要转移了。这个转移在司马迁的“history”中,当然应该有着某种看得见的迹象。
于是司马迁在《殷本纪》一开场,便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有关玄鸟的神话“story”: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着于百姓,百姓以平。
对此《诗经·商颂·玄鸟》也有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也有人说玄鸟可能是商王族的图腾。从图腾到《诗经》编成诗歌来歌颂,司马迁再编成神话故事,以为殷汤讨伐夏桀的“天命”讨伐和取而代之的“天命”承传做铺垫。
到了殷商末年,殷纣王暴虐无道、丧尽民心,于是周之武王率领天下诸侯一举灭商,建立了周王朝。武王之所以能夺得天下,固然和之先的文王、公季等周王一族的苦心经营分不开,而更和周族的开山祖先后稷一登上舞台就不同凡响、与众不同有关。于是司马迁又给我们讲了一段神话“story”: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
总而言之是同样手法,周之所以能取夏而代之,在后稷出生时就有天命转移的迹象,只不过当时还不显著罢了。最后是周武王替天行天道,伐暴虐无比的殷纣时,出现了白鱼赤乌。这个赤乌特别重要,因为前面已经提到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赤乌既然降落,说明它象征的“天命”降生出地上的王国了。
六、结语
哲学家在历史领域的任务,在于揭示历史事实深层里显现出来的某种共同现象,并把这种共同现象描绘成一种规律性的原则。各个时代的哲学家由于历史条件和思想发展阶段所制约,描绘出来的规律原则往往只是他们所处环境的时代反映,但却是他们那个历史阶段中颇为尖端(leading)十分前沿(frontier)的历史哲学。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天命论”即是如此,因而为汉武帝所采纳,使之成为维系汉代以来“大一统”皇权专制帝国的意识形态(ideologie),成就了以后两千年儒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主流地位。
而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他的使命是按照汉帝国的天下观和历史逻辑写作一部“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白鱼赤乌是显示殷商的“天命”将要转移到周王朝的一个象征,是用于“究天人之际”的一个故事“story”,是描绘“大一统”蓝图中的一个环节。他在写作历史时对“天命”的描述,如果没有历史人物、制度、地理、风俗等故事性的点缀和有声有色的描绘,历史便会显得枯燥无味,甚至失去信赖感。反之,没有“天命论”的支撑和架构,司马迁那种大一统的天下观、历史观也很难维持下去,汉帝国一统天下也就没有理论根据和思想保障。
所以,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所谓“究天人之际”,其实就是以儒家一脉相承的“天命论”来作为按汉帝国的逻辑来编撰历史时的理论大纲。而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如此娴熟准确地运用“天命论”,显然受到其师董仲舒的影响。董仲舒对白鱼赤鸟的发挥,从“天人合一”角度对“天命论”的理论阐述,以及董仲舒的公羊学,为司马迁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