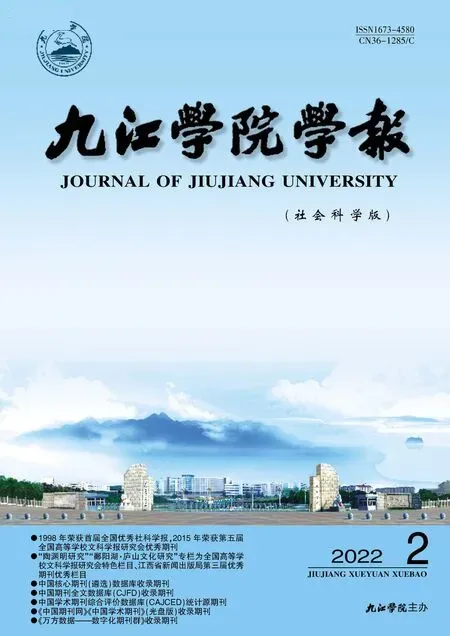关于刘勰的“屈宋逸步,莫之能追”*
——《文心雕龙》屈宋并称“折衷”解义
雍寒清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常有作家并称的情况。“两个或多个作家并称,是从魏晋开始的,而其滥觞则始于汉末政治斗争中志同道合者的相互标榜和月旦人物时的简称。……早期的并称,包括竹林七友、贾谧二十四友之类在内,其意义主要是政治层面上的,而随后出现的一些并称,其意义就渐渐地指向了文学层面。……总之,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方式,它是从世族人物品藻中流转而来的。”[1]《文心雕龙》的文学批评也深受这一独特的文学批评方式的影响,《序志》篇中刘勰阐述了自己的论文方法与原则:“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胜数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2]刘勰采取“折衷”的思维模式,在品评中将大量风格相似或文学成就相近的作家并称,以不同文体的“势”“理”——即其内在的客观规律为标准,通过擘肌分理的过程进行比较品评。《文心雕龙·辨骚》中,刘勰以“势”“理”为依据,第一次将屈原与宋玉并称,言“屈宋逸步,莫之能追”[3],将不受后世重视、褒贬不一的宋玉与屈原并称,开屈宋并称的先河。
前至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载宋玉等“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4]。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言宋玉等赋作“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5]。不仅汉代评论者对宋玉评价不高,及至近代郭沫若更是在1942年创作的历史剧《屈原》中,将宋玉塑造成了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历代学者对宋玉评价都是贬多于褒,难能可贵的是刘勰创作《文心雕龙》时摈弃了掺杂世俗道德的评价尺度,从文学视角“擘肌分理,唯务折衷”[6]对宋玉及其辞赋给予了客观评价,将其与屈原并列。故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者对宋玉文学创作进行深入研究时,多引《文心雕龙》屈宋并称的提法。但学界研究时往往只是简单征引刘勰所下屈宋并称的评语,对刘勰为什么提出屈宋并称这一合称的研究较少。本文拟从刘勰的“折衷”视角出发,观照屈宋并称问题,探寻刘勰屈宋并称的文学根据及其对后世的文学影响。
一、《文心雕龙》对屈宋创作的“折衷”评价
据汤炳正先生收于《屈骚探幽》中的《〈楚辞〉成书之探索》一文考证:“从汉代直到唐代,原本《楚辞章句》的篇次,跟《楚辞释文》是相同的;而唐到宋初则新旧两本并行;宋以来则新本通行古本完全失传。因此,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楚辞章句》篇次,也应该跟《楚辞释文》的篇次相同。”[7]据此我们认为刘勰创作《文心雕龙》时依据的《楚辞》本所收篇章包括:《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九思》,共17篇。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里将原书分为五部分,其中涉及屈宋、《楚辞》批评的篇目有“文之枢纽”全书总论中的《宗经》《辨骚》2篇;“论文序笔”文体论中的《明诗》《诠赋》《颂赞》《祝盟》《杂文》《谐隐》6篇;“剖情析采”创作论中的《定势》《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8篇;探讨文学评论的《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5篇,以及全书序言的《序志》,共22篇。
《辨骚》是从《楚辞》中研究文学变化的专篇,刘勰将其与《原道》《徵圣》《宗经》和《正纬》并列为全书的“文之枢纽”,可见刘勰对《楚辞》的重视与推崇。在《辨骚》中,刘勰首先对汉代文学家对屈原和《离骚》的评价进行了综述,认为前人“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8]其次,刘勰以“势”“理”为依据,归纳了《楚辞》的“四同”“四异”作为其评价的前提。再次,刘勰以屈、宋作品的艺术风格归类列举了《楚辞》中屈原与宋玉众多篇目,并指出其独到之处。最后,刘勰提出“屈宋逸步,莫之能追”[9],指出《楚辞》对后世作家的影响。
除《辨骚》外,涉及屈宋与《楚辞》整体批评的篇章有《声律》:“《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10]指出《楚辞》中带有楚方言音韵的地方特色。《章句》:“六言七言,杂出《诗》《骚》。”[11]指出《楚辞》句式多样,有六言与七言的不同句式。“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馀声”[12],指出《楚辞》句中多用语气词“兮”的特色。《事类》:“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13]指出屈宋作品中多次使用前代圣君贤臣相合与忠臣被弃以死明志的典故,但都有创新,没有直接引述原文。《时序》:“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14]再次将屈宋并称,认为屈原作品可同日月争光,宋玉的《风赋》和《高唐赋》《神女赋》等赋作都富有文采。《才略》:“屈宋以《楚辞》发采。”[15]也将屈宋并列相称,指出其文采斐然,都以楚辞创作出彩。《知音》:“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16]刘勰引屈原《九章·怀沙》中自陈自己不为世人所理解的原文,阐明知音赏识的重要性。《序志》“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17],直言《文心雕龙》的写作在根本上探索道,在师法上效仿圣人,在体制上探源经书,在文采上酌取纬书,从《楚辞》中研究文学的变化,探求从《诗经》到《楚辞》内容与形式的变化。刘勰将“辨骚”置于全书的框架纲领一级,在此主要对屈宋的辞赋创作进行讨论,可见刘勰认为楚辞在先唐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小觑的。
刘勰对《楚辞》进行总体评价时,4次直接将屈宋并列相提。在刘勰看来,文学成就与创作风格上堪与屈原比肩的只有宋玉一人。下面对屈原和宋玉的个体批评进行梳理。
(一)《文心雕龙》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
文体论中,《明诗》言“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18],认为《离骚》是屈原被君王疏远后的怀怨讽刺之作。《诠赋》“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19],认为屈原的《离骚》扩大了对声音形貌的描绘,使赋这一文体在楚辞中萌芽时受其影响扩大了描写范围。《颂赞》:“及三闾《桔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矣。”[20]《橘颂》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咏物诗,被南宋诗人刘辰翁称为“咏物之祖”。刘勰认为《橘颂》文辞典雅精工,屈原“体物寄情”,既颂橘又颂人,寄寓了自己的情意。
创作论中,《定势》云“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21],从侧面反映出《离骚》辞藻的华丽卓越。《比兴》“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逢兼‘比’‘兴’”[22],既指出屈原因君王听信小人谗言遭到流放,又点明《离骚》创作中对《诗经》的继承关系,《离骚》的讽喻深受《诗经》的“比”“兴”影响。《练字》“《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23],指出《离骚》中存在偶用重复字的现象。虽然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以此为犯忌,但刘勰还是肯定了《离骚》的写法,认为如果创作需要,则宁可重复。
文学评论部分,《时序》:“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馀影,于是乎在。”[24]辞赋自西汉武帝时逐渐兴盛,至东汉成帝、哀帝两朝,辞赋家的创作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但其创作还是深受屈原影响,继承了《楚辞》辞藻华丽、物类丰富的传统。《物色》:“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25]《离骚》宏大精妙的诗学结构与参差错落的杂言诗体组合,形成了大量物象组合的弘博丽雅的美学风貌,对物类触类旁通的描绘也有了更高的要求。“《骚》述秋兰,‘绿叶’‘紫茎’;凡摛表五色,贵在时见,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26],指出《九歌·少司命》中“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27]两句植物鲜明的色彩描绘其可贵之处在于及时看到和恰当描绘,若多次出现则会流于平庸。“且《诗》《骚》所标,并据要害,故后进锐笔,怯于争锋。……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28]刘勰以为屈原作品中的写景要义在于抓住了景物的要害,使后人不敢与之相较。至于屈原能够深刻领会前人《国风》《九歌》,则是依靠个人对客观自然江山的领悟与感知。《程器》:“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幹之沉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29]对屈原忠直贞正的品行予以肯定。
(二)《文心雕龙》对宋玉及其作品的批评
文体论中,《诠赋》:“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30]刘勰认为荀况与宋玉都是最早的赋家,他认为宋玉的《风赋》《钓赋》是最早成形的赋体文学作品。“宋发夸谈,实始淫丽。……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31]宋玉赋总体呈现铺陈辞藻,宏大华丽的艺术风格,其中尤以比说大话的《大言赋》和描绘高唐神女美貌的《神女赋》最为典型。《祝盟》:“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丽也。”[32]《招魂》是宋玉为招楚顷襄王生魂所作的招魂词,全诗极尽铺陈和夸饰,耀艳深华,恢诡谲怪,刘勰认为极富文采。《杂文》:“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文。”[33]《登徒子好色赋》中登徒子向襄王进谗:“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34]《讽赋》中唐勒也曾向襄王进谗:“玉为人身体容冶,口多微词,出爱主人之女。入事大王,愿王疏之。”[35]面对近臣多次进言,《对楚王问》中襄王质问宋玉:“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36]面对小人进谗,襄王见责,宋玉在多篇对问体赋作中加以申辩,发出“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37]的喟叹。《谐隐》:“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38]刘勰肯定了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创作目的是讽谏襄王不要沉溺于美色,值得研习。
创作论中,《丽辞》:“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39]刘勰援引《神女赋》中赞美高唐神女美貌超过毛嫱、西施作为对偶中最为困难的事对举例。《比兴》:“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40]刘勰用《高唐赋》中以吹竽比喻树枝发出的悲切之音作为声音比喻的范例。《夸饰》:“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41]在《大言赋》中,记录了襄王与宋玉、唐勒和景差比说大话,景差言:“‘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锯牙云,晞甚大,吐舌万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并吞四夷,饮枯河海。跋越九州,无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长。据地坋天,迫不得仰。’”[42]景差的夸大描绘形象性强,宋玉的则有包举宇内,并吞八荒之心,是夸张的典例。
文学评论部分,《知音》:“然而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杨》,宋玉所以伤《白雪》也。”[43]宋玉《对楚王问》中面对襄王责难,以音乐中《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为喻,表明自己品行高洁、志向远大、行为超群,因而不为世俗所理解不足为怪。刘勰借此对世俗抛弃深奥内容而取浅薄之文的现象予以否定。
经过梳理我们发现,刘勰《文心雕龙》引例屈宋及其辞赋频率相当高。对屈宋楚辞体的华丽辞藻与铺陈描摹刘勰是持肯定态度的。具体到各人,刘勰不仅对屈原作品给予肯定,对他高大俊洁的人格品性也予以赞扬。宋玉由于历代史料记载较少,刘勰主要是对其作品文学成就及其创作意图予以分析,指出其过人之处。总的来看,刘勰品评屈宋文章无不体现其贯穿全书的“折衷”原则。刘勰以“势”“理”为依据,通过‘擘肌分理’的过程,把握文章自身的合理规定性[44]。
二、《文心雕龙》屈宋并称的“势”“理”依据
刘勰《文心雕龙》品评作家作品时主要考量作家文本的文学价值,对于作家本身的个体品性关注较少。故而在前代学者多批评宋玉品性低微、作品铺张淫丽时,刘勰以赋文体的“势”“理”为依据,站在纯文学角度经过客观审慎分析,认为宋玉的文学成就可与屈原相媲美。下面主要从屈宋作品形式与思想内容两方面探求刘勰认为屈宋足以并称的文学依据。
(一)屈宋文学创作形式开拓成就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45]《辨骚》开篇,刘勰就指出自《诗经》出现后的百年,诗歌领域创作都为散文创作的光辉遮蔽,直到屈原《离骚》的出现,诗歌才重新焕发生机。屈原开创了一种具有鲜明楚国地方特色的新诗体——楚辞,他也由此被后世誉为“辞祖”“辞圣”。
目前学界虽对传世的屈原作品具体篇目仍然存在争议,但对其作品的文学成就都给予了较高评价。这里我们认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共26篇作品(其中《九歌》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11篇作品,《九章》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9篇作品)都是屈原的作品。
楚辞吸收借鉴《诗经》,但又与《诗经》风格迥异,成为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诗经》句式整齐,楚辞则句式灵活,且多用“兮”字。《诗经》重自然写实,主要以北方景致为主。楚辞重主观抒情,多描绘南方楚地景象,“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46]故而鲁迅赞其“逸响伟辞,卓绝一世”[47]。后世历代文人提起屈原从不吝惜辞藻,可见屈原及其创作对中国文学影响之深远。
宋玉由于传世资料较少,迄今对其生平缺乏完整详实的资料考证。现在我们多认为宋玉是楚籍宋人,是景仰屈原道德文章的后学。在《诠赋》中,刘勰将宋玉与荀况同时列出,认为他们都是早期赋家。但现在根据对宋玉赋体文学创作的年代、成就及影响,我们认为宋玉才是开创赋体文学当之无愧的“赋祖”“赋圣”[48]。
20世纪初,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宋玉著作几乎都被认定为伪作。20世纪末,随着新的出土文献材料出现,学者们开始对宋玉著述确立新的认识。根据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考察,我们认为宋玉现存有《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微咏赋》《御赋》《对楚王问》共14篇作品,其中《九辩》《招魂》为楚辞体诗歌,其余12篇均为散体赋。
与屈原相比,宋玉传世作品不多,但其赋作却大都具有开创性特色。《钓赋》《风赋》是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笛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咏物赋。《风赋》既是咏物赋,又是寓言赋,其君臣问答的结构形式和韵散兼行的句式特点奠定了汉代散体大赋的体制。《高唐赋》《神女赋》在中国赋史上代表了赋体文学的成熟。
因此我们可以说屈原开创楚辞,宋玉开创楚赋,都对后世文体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二人在文学文体的开创方面是足以相提并论的。
(二)屈宋文学创作思想内容特色
关于屈宋创作在思想内容上的相似性,刘勰在《辨骚》篇中业已指出:“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49]下面对屈宋作品进行具体分析以佐证刘勰的论断。
第一,叙情怨,郁伊而易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50](《离骚》)“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51](《九章·抽思》)“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蹇蹇之烦冤兮,陷滞而不发。”[52](《九章·思美人》)屈原多以男女恋爱婚姻关系象征政治上的君臣关系,自比弃妇,以求女象征求君。形象生动抒发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愤与哀伤。“怆恍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岁忽忽而遒尽兮,恐余寿之弗将。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蹇充倔而无端兮,泊莽莽而无垠。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见乎阳春。”[53](《九辩》)宋玉一生沉居下僚,仅为襄王文学侍从,在被襄王疏离后,其境况比屈原更为窘迫。宋玉直陈一介寒士丢官去职后衣食无周的生活窘况,却仍不忍背弃君王,对君王亲佞远贤不辨忠奸满怀悲愤,满腔孤愤力透纸背。
屈原、宋玉都有因忠直而被小人进谗后为君王疏远的经历,且两人都是政治理想难以实现,转而作文。《襄阳耆旧传》载:“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54]面对楚国昏暗的政治环境,屈原、宋玉都寄希望于君王激浊扬清,但怀王、襄王父子两代处在旧贵族的包围中不思进取,反而归罪于忠正耿直的臣子,故而两人在抒发无罪被弃的怨愤之情时显得更加真挚感人。
第二,述离居,怆怏而难怀。“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55](《离骚》)“悲莫悲兮生别离。”[56](《九歌·少司命》)“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57](《九章·哀郢》)屈原在诗中多次设想自己四处远游,但终不忍离开故国。现实中却被两代君王流放,远离故乡郢都。离别亲友故乡之痛成为屈原内心难以弥合的伤痛。“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58](《九辩》)“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菉蘋齐叶兮白芷生。”[59](《招魂》)“徊肠伤气,颠倒失据。闇然而暝,忽不知处。情独私怀,谁者可语。”[60](《神女赋》)无论是讲述自己远离故乡漂泊却一事无成,或是回忆曾经与君王未曾分离时的情景,或是为襄王描绘神女离去时沮丧悲伤的心情,宋玉都能恰到好处地抒发离别的哀伤。
楚国地处南方,宗亲意识浓郁,巫鬼之风盛行,屈原与宋玉在楚文化的浸染中对故土有着深厚的依恋。但两人被弃流亡的经历注定会引发无限的离情别绪。诗人笔下的离别更比普通人多几分缠绵与惆怅,故而刘勰以为屈宋之叙述离别,更使人感到悲哀。
第三,论山水,循声而得貌。“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61](《九歌·少司命》)“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62](《九章·涉江》)“山林险隘,虎豹蜿只。鰅鳙短狐,王虺骞只。”[63](《大招》)屈原作品主要以抒情为主,间或杂有对山川草木、虫鱼鸟兽的描绘。屈原摹景喜用叠字,从视觉或听觉角度描绘自然物象状态。“遇天雨之新霁兮,观百谷之俱集。濞汹汹其无声兮,溃淡淡而并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长风至而波起兮,若丽山之孤亩。势薄岸而相击兮,隘交引而却会。崪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砾磥磥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磕磕。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沫潼潼而高厉。”[64](《高唐赋》)宋玉与屈原一样多用叠词,《高唐赋》是宋玉山水描绘的经典名篇,主要铺叙巫山巫峡的自然景观。宋玉选取多重视角自下而上展现不同时节的巫山盛景。屈宋作品中的自然风貌主要是南方楚地风光,屈原作品中的山水描绘主要作为抒情点缀穿插出现,而到宋玉赋中,自然山水则成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宋玉对其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描绘。刘勰认为从屈原到宋玉,描绘山水的笔法更加成熟,按照声情便可窥知全貌。
第四,言节侯,披文而见时。“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65](《离骚》)“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66](《九章·涉江》)“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67](《九章·怀沙》)屈原诗歌中以四季更替指代时光流转,无论哪一个季节,在心情低沉的屈原笔下都成为引发其哀伤的愁绪。季节交替带来的不是自然生命的循环往复,而是屈原对自己年岁日衰的喟叹。“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68](《招魂》)“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69](《九辩》)伤春悲秋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永恒的话题,正是肇始于宋玉。伤春悲秋之感古已有之,但前代作品都只是以春日暖阳和悲凉秋景起兴言情,并未将伤春悲秋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宋玉不仅明确提出了“伤春悲秋”的主题,还围绕这两大主题展开了生动细腻的描绘,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感伤主义传统。屈原和宋玉都具有观察自然的审美视野,普通的自然四季经过艺术加工便浸染了他们的主体精神,客观时节也由此成为寄寓情感、起兴感怀的艺术意象。经过对屈宋作品的细致分析可以发现,刘勰认为屈宋足以并称的原因主要是从作品本身出发,在作品形式上,屈原开创楚辞,宋玉开创楚赋,都有文体的创新;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上,在抒发怨情、叙述离别、描绘山水和叙述季节等方面,屈原和宋玉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刘勰作出屈宋并称的定论完全符合他在《序志》篇中所说论文的根本方法:“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于异,不屑今古,擘肌分理,唯务折衷。”[70]可见刘勰所下屈宋并称的定论是相当客观的。
三、《文心雕龙》屈宋并称的文学影响
刘勰是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体系严密,“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因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屈宋并称,无疑对扭转前代风尚,重新确认宋玉的文学史定位产生深远影响。
(一)揭示了宋玉的文学创作成就
屈原是楚辞和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创者,也是中华民族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作品内涵丰富,文辞瑰丽,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故而历代对屈原辞作都给予了较高评价,这里不再赘述。
刘勰在屈宋并称中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宋玉的文学创作成就。《文心雕龙》中明确涉及的宋玉辞赋有:《九辩》《招魂》《风赋》《钓赋》《对楚王问》《登徒子好色赋》《神女赋》《高唐赋》和《大言赋》,刘勰对这些宋玉著述归属权给予了充分肯定,为其正名。首先,在文体上,宋玉师承楚辞开创了楚赋这一新的文学体裁,是赋体文学的开山祖师,奠定了“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确立了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其次,对《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描写女性形象的艺术手法予以肯定,宋玉即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全方位描写女性形象的作家。再次,《高唐赋》全方位、多角度描绘了巫山自然风貌,是中国辞赋史上第一篇独立的山水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完整的山水文学作品,宋玉即是中国山水文学之祖。最后,《招魂》《九辩》开创了中国文学伤春悲秋的文学母题,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感伤主义传统。
(二)确立了宋玉与屈原并立的文学史地位
“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而宋玉则是楚赋的代表作家;屈原所创作的楚辞重抒情,而宋玉所创作的楚赋重体物;屈原喜犯颜直谏,宋玉好微辞讽谏;屈原崇高伟大,宋玉自然亲切。从屈原到宋玉,实现了由楚辞向楚赋的转移、由缘情向体物的嬗变、由直谏向曲谏的发展、由崇高向世俗的回落。”[71]长期以来,因宋玉赋微辞讽谏的特质,与之并列的屈原则是犯颜直谏,故而后世学者解读时多以宋玉品行低下、作品夸饰媚俗,认为其不应与屈原并称。刘勰独具慧眼以文学的评价标准将宋玉与屈原并称,确立了宋玉与屈原并立的文学史地位。
宋玉辞赋是文学自觉的产物,是宋玉作为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发地追求文学审美特质的结果。“从屈原到宋玉等人、从辞到赋,是由泛文学到纯文学的演变过程, 只是到了宋玉那里,文学才真正以独立的形态出现,才出现纯粹的文本。”[72]可以说,宋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职业作家。
刘勰创作《文心雕龙》正是基于纯粹的文学批评,刘勰看到了宋玉辞赋的成就,认为宋玉是足以与屈原齐名,在文学史上理应享有崇高的地位。客观地说,刘勰提出屈宋并称,一方面确实对宋玉文学地位的提高有积极影响,但另一方面,在崇尚人格道德的传统社会,人微言轻的宋玉为独立不迁、品行高洁的屈原所遮蔽,造成屈宋并称,却普遍认为宋不如屈的现象。
(三)界定了辞与赋两种文体的分野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是赋学研究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赋体研究论文。刘勰在著述中往往辞赋并称,但还是将辞与赋作为两种不同的文体加以区分,并对赋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梳理。在内容与形式上,赋都深受《诗经》和楚辞的影响。
在起源上,刘勰认为《诗经》“六义”的“赋”是文体之赋的源头之一,赋的形成发于楚辞。以主客问答的对话开篇,极力描写声音形貌以显示文采,就是赋与诗分体的开始。在结构上,赋用序言开头,以总论结尾。序言作为发端位于赋的开篇,引出作赋缘由;结论在文末总结全篇。在分类上,有京都、宫殿、苑囿、打猎和抒写情志等类型。在发展中,刘勰梳理了历代赋家,认为赋兴于楚,盛于汉,而衍于魏晋。
“辞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纯文学阶段的开始和文人群体的生成,辞赋作家的创作又经历了从屈原到宋玉的转变。如果说屈原的作品还没有完全和现实政治脱钩,还处于半自觉状态,那么,宋玉等赋家已经把文学创作当成人生娱乐的重要方式,在作品中表现出明显的唯美倾向。”[73]一般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起于魏晋,但这一提法似乎过于笼统,针对不同文体,其文学自发与文学自觉的时间也有所不同。对于辞与赋两种文体而言,早在先秦就已进入自觉阶段。刘勰将赋与辞进行区分,在文体学研究领域是至关重要的。
综上,刘勰以“折衷”的思维方法,在《文心雕龙》中首次提出屈宋并称,并多次援引屈宋及其辞赋。以“势”“理”为依据,刘勰从作品形式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综合考量,认为屈宋均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足以并称。屈宋并称不仅重新揭示了宋玉的文学创作成就、确立了宋玉与屈原并立的文学史地位,还界定了辞、赋两种文体的分野。如陆侃如所说:“谁是中国文学之祖?我毫不迟疑的说:屈原与宋玉。他们不但给予楚民族文学以永久的生命,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学的稳固的基础。”“古代若无屈宋,则文学史决没有那样灿烂;而楚民族若无屈宋,则楚文学也决占不到重要的位置。所以,凡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尤其是研究古代文学的人——都不可不从屈宋下手。”[74]可见屈原和宋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刘勰屈宋并称不仅在楚辞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后世作家品评也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