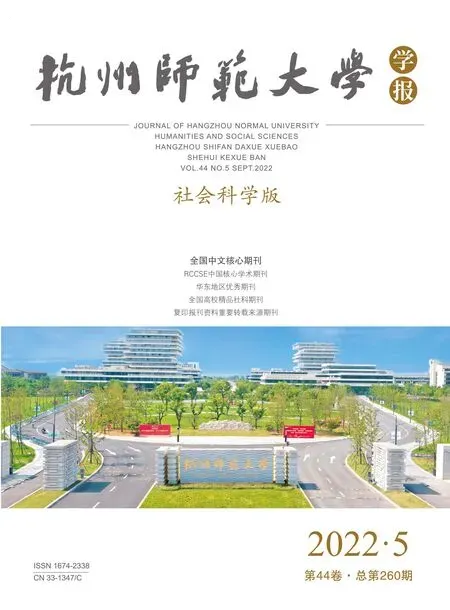“把人当人”:鲁迅晚年的人道主义与奴性批判
高力克
(浙江大学 国际文化学系,浙江 杭州 310058)
鲁迅晚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党外的共产主义文学家。但“共产主义者的鲁迅”[1](P.702)并没有摈弃其早年“立人”的启蒙主义,亦没有改变其批判国民性和旧社会弊害的批判知识分子立场。作为一名左翼文化战士,鲁迅坚持在思想文艺战线从事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战斗的文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鲁迅在文化战线上致力于新民主主义启蒙。对于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启蒙思想,学术界多关注其早年留学时期到五四时期的思想。其实,启蒙是鲁迅毕生一以贯之的思想主题。晚年鲁迅对国民精神中的奴隶性的批判,是其“立人”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想的深化,亦是其文化批判最为深刻的思想遗产。
一、“立人”与改造国民性
鲁迅“立人”的启蒙思想形成于20世纪初留学日本期间。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反思晚清改革运动:从洋务派到维新派“竞言武事”,“计其次者,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2](P.180)追求西方的军事工商宪政,皆舍本逐末。“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2](P.193)在鲁迅看来,“立人”之道,在尊重个性和申张精神。而中国自古“尚物质而疾天才”,今日又受害于西方现代文明之“物质”与“众数”的偏弊,人的个性被剥夺殆尽。中国的改革,必须着眼于“人”的觉醒,“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2](P.181)鲁迅期待,“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2](P.192)。“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3]“立人”,即由个人的觉醒到民族的觉醒,中国由此转变为“人”的国家。
鲁迅慧眼独具地认识到,欧美之先进,“根柢在人”,故中国的革新“首在立人”,即树立自由独立之现代人格。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鲁迅率先高举“人”之大旗,揭示了“人的解放”的启蒙主题。他的“立人”以“致人性之全”的人格健全的“新人”为目标,其方法是以文艺转移性情,而“改造国民性”。鲁迅在其《呐喊·自序》中阐述了自己弃医从文的启蒙宗旨:“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P.5)
国民性问题,是鲁迅启蒙思想的中心主题。早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受梁启超新民思想、日本“国民性”思潮和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中国人之气质》的影响,开始探索国民性问题。他在东京弘文学院期间,常与好友许寿裳讨论理想的人性与国民性的缺陷问题。答案是:我们民族最缺乏诚与爱,而两次奴于异族是其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无诚爱可言。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4](P.203)鲁迅深刻地认识到,改造国民性的根本目标,就是克服国人的奴隶性。欲实现人的解放,必须改造国民性,根除国人的奴隶性。
鲁迅的“立人”思想和对奴性的批判,深受尼采唯意志论哲学的影响。尼采主张“浪漫英雄主义”的个人主义。在他看来,人有贵贱高低之分,一方是充盈、丰满、伟大的完人,另一方是无数不完整、不健全的庸人。[5](P.116)生命即权力意志。人类由于权力意志的强弱,而天然存在少数“命令者”与多数“服从者”,二者分别代表了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基督教是否定生命的、最有害的奴隶道德。尼采所谓“主人”与“奴隶”的性格类型,亦即“高贵者”与“奴性者”,抑或“贵族品质”与“奴隶品质”。现代社会的主奴关系是精神化的:“主人”代表自由的精神,“奴隶”则代表受束缚的精神。超凡脱俗的自由精神,总是不懈地为高贵事物而奋斗,最大化地实现人的创造性潜能。[6](PP.109-121)现代民主社会沿袭了基督教的奴隶道德。现代性的问题在于“奴隶”(受束缚的精神)取得了“主人”(自由精神)的权力。这是群体对个体的完胜。而那些通过为人类创造新价值和新可能性而进行领导的“命令者”却越来越稀缺。顺从的群体本能被完好地继承了,并且以牺牲命令的艺术为代价。[6](P.121)鲁迅启蒙主义的“主人—奴隶”范式,即源于尼采哲学。他的“改造国民性”亦集中于奴性批判,将奴隶性归为国民性最严重的精神病症。
对奴隶性的批判始于严复。他认为,中西文明的根本差异是自由,中国自古匮缺自由传统,“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7](《论世变之亟》,P.4)。自秦以降,政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隶待人民。皇帝既以奴隶待人民,而人民亦以奴隶自处。奴隶之于主人,只是形劫势禁、无可奈何而已,并非心悦诚服地爱国家与皇帝。[7](《原强修订稿》,P.35)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倡言自由,批判奴性:“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8](P.55),“人之奴隶我不足畏也,而莫痛于自奴隶于人;自奴隶于人犹不足畏也,而莫惨于我奴隶于我。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吾亦曰:‘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斯为末矣。’”[8](P.64)鲁迅的奴性批判,继承和发展了严、梁的思想。
鲁迅崇尚19世纪欧洲“新神思宗”和“摩罗诗人”的自由精神。在《摩罗诗力说》中,他赞扬英国摩罗诗人拜伦“重独立而爱自由,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2](P.212)。鲁迅对愚昧的国民,即取拜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衷悲疾视态度。“哀其不幸”的衷悲出于人道主义,“怒其不争”的疾视则出于个人主义。鲁迅“立人”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继承了拜伦“自尊而怜人之为奴,制人而援人之独立”[2](P.215)的自由精神。
在鲁迅批判“吃人的礼教”的小说名篇《狂人日记》中,主人公是一个被礼教戕害的精神病人。尼采视地球为一个疯人院,并通过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倡言从“虫豸”到“人”再到“超人”的进化论。而鲁迅通过“狂人”阐述的从“虫”到“野蛮人”再到“真的人”的进化论,则以“真的人”作为超越“吃人”的“野蛮人”的理想人格。鲁迅所谓礼教“吃人”,比喻封建礼教吞噬人性的精神奴化。
在其最杰出的小说《阿Q正传》中,鲁迅发人深省地刻画了一个现代国人的灵魂。在他的笔下,阿Q的愚昧、卑怯、懦弱、贪婪、狡黠、浑浑噩噩、逆来顺受、欺软怕硬、精神胜利法、麻木不仁等性格特征,跃然纸上,淋漓尽致地显示了一个奴隶与游民混杂的病态灵魂。
鲁迅“立人”的启蒙主义呼唤“人”的解放,并以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为思想武器,对皇权专制导致的国民精神中的奴隶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灯下漫笔》中,鲁迅沉痛地指出:中国历史是一部奴隶的历史。“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2](P.311)中国历史只有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2](P.312)“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2](P.313)在鲁迅看来,奴隶性已演化为普遍的国民心理:“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辱,但也可以凌辱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2](P.314)“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2](P.316)鲁迅号召青年奋起反抗这吃人的旧社会:“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2](P.316)
鲁迅“立人”的启蒙主义独树一帜,但其尼采式启蒙思想,亦具有“排众数”与“觉众数”的内在矛盾。其“排众数”而“重个人”的尼采式个人主义与其“群之大觉”的启蒙目标相矛盾,此亦为鲁迅的启蒙主义与尼采的浪漫英雄主义的分歧所在。鲁迅追求“人国”的国族主义情怀与尼采崇尚“超人”的贵族个人主义自由理想,大异其趣。五四以后,正是“超人”和“天才”的幻灭,才使鲁迅疏离了尼采的浪漫英雄主义而转向马克思主义。
二、晚年鲁迅的启蒙主义
五四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新文化运动由分化而退潮。鲁迅经历了孤独者的“彷徨”和对尼采式个人主义的疏离。1927年春,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目睹“四·一二事变”中国民党清党运动的白色恐怖与青年党人的卑劣残忍,他向来迷信青年的进化论思想随之“轰毁”。同年秋,鲁迅离粤而定居上海后,受到创造社、太阳社左翼文人的围剿,开始阅读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从此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鲁迅改宗马克思主义后,告别了自己所属且憎恶的“中产的智识阶级”,转而寄希望于新兴的无产阶级。在《二心集》序言(1932)(1)本文在鲁迅晚年(1930年代)作品后面标注创作的时间,以便清晰地梳理鲁迅晚年思想的演变过程。中,他指出:“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9](P.151)
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对未来冀望于无产阶级,但自己并没有从事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彼时,文坛有《创造》之无产阶级、《语丝》之小资产阶级、《新月》之资产阶级的归类。被归为“小资产阶级”或“中产的智识阶级”的“语丝派主将”鲁迅认为,目前中国尚未产生无产阶级作家,由于无产阶级的教育欠缺和汉字的难学,无产阶级尚难以创作自己的文学作品。无产阶级文学的作者都是小资产阶级左翼作家。而作为一个左翼的启蒙文学家,鲁迅所坚持的“战斗的文学”,批判重于建设。他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者,而非无产阶级文学的创造者。晚年鲁迅仍坚持其启蒙立场,其杂文写作重在对旧社会、旧文化之弊害的批判。
在《答国际文学社问》(1934)中,鲁迅写道:“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能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但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漩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10](P.14)作为一个启蒙者,鲁迅的杂文写作更注重与旧社会之黑暗的战斗。他对于苏联文学的兴趣,亦是战斗重于建设。“我觉得现在的讲建设的,还是先前的讲战斗的——如《铁甲列车》,《毁灭》,《铁流》等——于我有兴趣,并且有益。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大半因为想绍介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10](PP.14-15)在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活中国的姿态》所作序(1935)中,鲁迅坦言著者“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10](P.210)。暴露旧社会的弊病,正是启蒙者鲁迅之“战斗的文学”的宗旨。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中,鲁迅重申其小说创作的启蒙主义宗旨:“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9](P.393)鲁迅一如既往地坚持其启蒙主义,从留学时期、五四时期到1930年代,矢志不渝。他晚年反对梁实秋等人“为艺术的艺术”的资产阶级小说观,仍坚持其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
鲁迅晚年的杂文,仍以批判性为主。除了与资产阶级文人的文坛笔战,其社会批判仍延续了国民性批判的主题,尤为对国民心理中根深蒂固的奴隶性的批判。而其国民性批判的思想武器仍未脱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鲁迅夫子自道:他的思想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起伏消长。好友刘半农赠给他的对联“托尼思想,魏晋文章”,即指鲁迅思想中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与尼采的个人主义。鲁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其启蒙思想和批判精神中仍保留了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精神。在《我的态度气量与年纪》(1928)中,鲁迅指出:“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等。”[9](P.90)启蒙时代卓尔不群的批判者鲁迅,却并不讳言黑暗和厌恶人道主义。
在鲁迅的启蒙思想中,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人”的话语与尼采式个人主义的“主—奴”话语,一以贯之,晚年亦无改变,尽管他已不再冀望于“超人”。晚年鲁迅思想中的“人”不是“超人”,而是具有自由独立的健全人格的现代“人”。在其“人—奴”对立模式的批判话语中,“立人”即祛除奴性,树立主体人格。如果说康德的启蒙,旨在脱离人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那么鲁迅的启蒙,则旨在脱离专制社会的“奴隶”状态而获得“人的解放”。
三、晚年鲁迅的奴性批判
鲁迅的奴隶性批判,基于对中国皇权专制社会之国民精神疾患的深刻反思。文明,是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进化。而奴隶性则是野蛮社会之反文明的病态人格。奴隶性是“人”之大敌,它否定人的价值,抹杀人的尊严,泯灭人的个性。奴隶性戕害人格,使人堕落为非人的动物。鲁迅指出,“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10](P.405)。而奴隶的本质,就是“把人不当人”。奴隶性是帝制传统遗留的最深固最严重的精神疾患,它是对人道和文明的野蛮践踏,其反人道和反文明的野蛮性,是中国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严重精神障碍。
在中国人的精神奴化史上,也许再没有比舍生取义的“侠”的堕落更为严重且具反讽意味了。在《流氓的变迁》(1929)中,鲁迅慧眼独具地揭示了“侠”的奴化的历史。他指出,墨子之徒为侠。惟侠老实,故墨者的末流,以死为终极目的。后来,真老实的侠逐渐死完,只留下取巧的侠,如汉代与王公权贵相馈赠的大侠。“‘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9](P.123)清代以来,有“侠气”的人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和为天子效力,而沦为官员的保镖,替他捕盗。“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9](P.124)为盗要被官兵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打,侠客要安全,于是成了流氓。在鲁迅笔下,“侠”从古时不满现状的墨子之徒沦为流氓的历史,即“侠”之精神奴化的历史。古侠具有“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11](《游侠列传》,P.518)的精神。这种春秋时期舍生取义的“侠”的英雄精神,在帝国时代逐渐被奴化而沦落,“侠”终于堕落为奴性十足的“流氓”。
在鲁迅看来,奴隶性是一种主奴同构的病态的主奴根性,专制社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虽处于对立的阶级,却共同具有一种专制文化之亦主亦奴、欺弱媚强的权威人格。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中指出:“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得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9](P.239)耐人寻味的是,倡言无产阶级文学的鲁迅对工人之主奴根性的剖析亦毫不留情。
在《谚语》(1933.6)中,鲁迅深刻地揭示了主奴根性之欺下媚上、骄慢卑怯的双面人格:“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9](P.414)
鲁迅进而追根溯源,从儿童教育的弊病,批判了中国家庭戕害儿童之自由健全人格的奴化教育。他在《上海的儿童》(1933.8)中指出:外国儿童轩昂活泼地玩耍,中国儿童则精神萎靡,被别人压得像影子一样。“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9](P.433)“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9](P.434)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1934.8)中,鲁迅批评了中国社会崇静抑动的倾向对儿童人格成长的危害:“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10](P.63)
在《新秋杂识》(1933.8)中,鲁迅以蚂蚁之喻,提出了“人的战士”拯救儿童而反对奴化儿童的任务:“蚂蚁中有一种武士蚁,自己不造窠,不求食,一生的事业,是专在攻击别种蚂蚁,掠取幼虫,使成奴隶,给它服役的。但奇怪的是它决不掠取成虫,因为已经难施教化。它所掠取的一定只限于幼虫和蛹,使在盗窟里长大,毫不记得先前,永远是愚忠的奴隶”[12](P.214),“跟着武士蚁去搬运败者的幼虫,也还不失为一种为奴的胜利。但是,人究竟是‘万物之灵’,这样那里能就够。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制造打仗机器的蚁冢,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这才是人的战士的任务。”[12](P.215)
在《偶成》(1933.9)中,鲁迅批判了奴隶文化之崇尚暴力和反人道的野蛮性:“奴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9](P.449)“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用奴隶或半奴隶的幸福者,向来只怕‘奴隶造反’,真是无怪的。要防‘奴隶造反’,就更加用‘酷刑’,而‘酷刑’却因此更到了末路。”[9](P.449)奴性是专制社会暴力文化的产物,残酷产生残酷,兽道产生兽道。奴隶的残忍,是“把人不当人”的主人残忍压迫造成的。
在《漫与》(1933.9)中,鲁迅对“奴才”卑贱畏葸的畸形病态人格,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批判:“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不同。”[9](P.453)这是鲁迅对“奴才”入木三分的经典批判。奴才比奴隶更卑鄙下贱,其自轻自贱,自安于奴,以奴为美。奴隶为“身奴”,奴才则为“心奴”。奴才是奴性的极致,其心灵的奴化,无可救药。
在鲁迅看来,中国社会盛行的枭雄崇拜,表现了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他在《拿破仑与隋那》(1934.11)中指出:“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们却总敬服他的英雄。甚而至于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隶,我们却还恭维成吉思;从现在的字眼睛看来,黄人已经是劣种了,我们却还夸耀希特拉。”[10](P.111)“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10](P.111)
对于1930年代德、意、英、美的强政府潮流,鲁迅持警觉的批判态度。他认为这种庞大权力的兴起与中国秦始皇的专制传统一样,都会导致国民精神的动物化。他在《同意和解释》(1933.9)中强调:“据说现在的世界潮流,正是庞大权力的政府的出现,这是十九世纪人士所梦想不到的。意大利和德意志不用说了;就是英国的国民政府,‘它的实权也完全属于保守党一党’。‘美国新总统所取得的措置经济复兴的权力,比战争和戒严时期还要大得多。’大家做动物,使上司不必征求什么同意,这正是世界的潮流。懿欤盛哉,这样的好榜样,那能不学?”[12](P.228)“中国自己的秦始皇帝焚书坑儒,中国自己的韩退之等说:‘民不出米粟麻丝以事其上则诛。’这原是国货,何苦违背着民族主义,引用外国的学说和事实——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呢?”[12](P.228)
鲁迅从历史传统、政治文化、儿童教育等多方面批判了奴性的病态人格。其奴性批判的深刻性,在于其揭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的主奴同构的主奴根性,这种欺下媚上的卑怯的主奴根性,是皇权专制社会的畸形病态人格。鲁迅晚年对国民精神中之主奴根性的批判,深刻犀利,入木三分,是其“立人”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想的深化。
结 语
对奴隶性的批判,是鲁迅文化批判之最为深刻独到而震撼人心的启蒙思想遗产。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并没有改变其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使命。对于鲁迅来说,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和礼教禁锢所造成的国民精神之根深蒂固的奴性,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最大精神障碍。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需要一场破除奴性和“立人”的人道主义精神革命,启蒙在中国仍是未完成的历史课题。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分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兴起,鲁迅成了在启蒙战线上坚持战斗的孤独斗士。昔日北大新文化盟友陈独秀、李大钊由启蒙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文学界一代新崛起的青年左翼文人发起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运动。而晚年鲁迅从尼采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并没有改变其“启蒙者”改造国民精神的批判使命。鲁迅终其一生是一个坚持不懈地批判奴性而追求“人”的解放的启蒙者,这正是他的伟大和深刻之处。
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从一个启蒙文学家转变为一个左翼文学家和党外共产主义者。作为一名文坛的战士,鲁迅的思想和行为不同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共产党人。20世纪30年代初,他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其主要的杂文写作仍坚持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晚年鲁迅仍承袭了其启蒙思想家和批判型知识分子的思想关切,针砭旧社会的弊害和疗救国民精神的疾患,同黑暗势力作“轫的战斗”。
晚年鲁迅仍坚持其启蒙主义之“人”的理想,其“立人”的思想一脉相承,“人—奴”二元对立范式仍是其国民性批判的基本思想武器。他的国民性批判聚焦于奴隶性,他持之以恒地批判奴性,呼唤个性解放和自由独立的现代人格。这种现代人格是人的主体性的精神表征。奴性是皇权社会臣民人格的精神特征。“立人”和人的现代化,即祛除奴性,实现从奴隶到人的人格转型。
关于奴隶的本质,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有深刻的揭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13](P.8)奴隶,是古代野蛮的奴隶制度的产物。“凡是生于奴隶制度之下的人,都是生来做奴隶的;奴隶们在枷锁之下丧失了一切,甚至丧失了摆脱枷锁的愿望;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奴役状态,有如优里赛斯的同伴们爱他们自己的畜牲状态一样。……强力造出了最初的奴隶,他们的怯懦则使他们永远当奴隶。”[13](P.11)在《爱弥尔》中,卢梭进一步强调奴隶之于人类精神之深远的消极影响:“我们所有的智慧,都脱不了奴隶的偏见。我们所有的习惯都在奴役我们,束缚我们,压制我们。文明人从生到死都脱不了奴隶的羁绊。”[13](P.8)卢梭深刻地指出,奴隶制度造成了奴隶和爱奴役状态的奴才意识。而人类所有智慧都摆脱不了奴隶的偏见,文明人也摆脱不了奴隶的羁绊。
康德阐发了启蒙运动对“人”自身的认识:人作为目的存在物,其本身是目的,人性本身就是一种尊严。“人格中的人性”与动物性和自然的人性相区别,其作为目的本身先天地具有一种尊严,而尊严之于人具有无条件的、无与伦比的、绝对的内在价值。在当代世界的社会政治价值中,人的尊严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开宗明义,宣告“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并进而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的尊严已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标志。而奴隶性是对人的尊严的亵渎和否定,它从根本上是反人性和反文明的。
鲁迅对奴隶性的批判具有穿越时代的深刻性。在当代中国,奴隶性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胜利而消亡。作家巴金晚年曾沉痛地反思:“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但是我也万想不到小说中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经过那十年的磨炼,我才懂得‘奴隶’这个字眼的意义。在悔恨难堪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来跟我当时的处境对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14](《十年一梦》,P.474)
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巨变,但封建主义的痼疾仍在,陶铸公民的精神文明大业,仍任重而道远。鲁迅的“立人”思想和奴性批判,在今天仍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中国的文明进步,“根柢在人”,归根结底是人性的升华。“人”之立,是中国大国崛起的真正表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国民精神是一个民族之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改造国民性难,用文艺改变人的性情更难。鲁迅的奴隶性批判旨在揭示封建社会遗存的国民精神的病症,其对于中国之人的现代化和精神进步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国民性问题涉及制度与人性,救治国民精神的疾患,诊断不能代替药方。其实,鲁迅晚年谈及其小说创作的宗旨:他所写的那些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9](P.393)。他已不提用文艺改变国民的精神。诚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5](P.9)要祛除奴性,树立自由平等的人格,需要社会的现代化和人文教育的普及。要改变阿Q的病态人格,首先要改变未庄的社会环境。诚然,改造社会已经超乎一个革命文学家的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