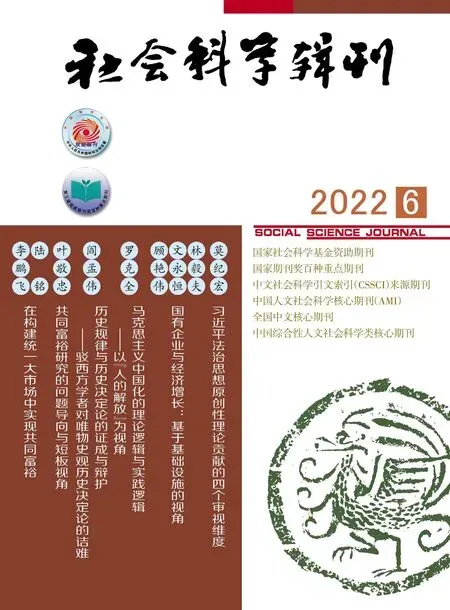四库馆臣对别本的认识、处理及利用
——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的考察
王雪玲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是修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同时也是一部集大成式的目录学著作,著录及存目图书多达万余。四库馆臣对著录及存目的每部图书分别撰写了提要,借提要交代作者之爵里及生平,撮举大凡,条列得失,间及卷帙之分合、文字之增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裨益当代,泽惠后人。张之洞认为《总目》是良师,阅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1〕;周中孚评价说:“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矣。”〔2〕虽然如此,《总目》亦难免有瑕疵,尤其是作为官修书目,《总目》奉敕编纂、悉承圣裁的钦定性质,直接导致了其重视图书来源而轻视版本的问题。正如馆臣所言“每书名之下,钦遵谕旨,各注某家藏本,以不没所自。其坊刻之书,不可专题一家者,则注曰通行本”。《总目·凡例》虽然就版本问题对纂修官提出过要求,即“诸书刊写之本不一,谨择其善本录之;增删之本亦不一,谨择其足本录之”〔3〕,但在《总目》著录及存目的文献提要中,仅对部分图书的版本问题有所交代,多数情况下语焉不详,偶尔直接忽略。正因为如此,前贤时哲对《总目》颇有微词,余嘉锡称:“《总目》之例,仅记某书由某官采进,而不著明板刻。馆臣随取一本以为即是此书,而不知文有异同,篇有完阙,以致提要所言,与著录之本不相应。”〔4〕程千帆、徐有富亦谓《总目》“只记载某书所从来,而不记载其究属何本”〔5〕。有鉴于斯,《总目》问世以来,关注、探讨和研究《总目》版本者不乏其人,清代学人邵懿辰、孙诒让、莫友芝等先后在《四库简明目录》上标注版本;叶德辉曾令诸子侄为其分撰《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其侄叶启勋所著部分先后在1933—1936年的《图书馆学季刊》上连载,惜未最后完成;杨新勋《四库提要版本著录申论——以经部提要为中心》亦梳理了今人的相关研究成果〔6〕,但迄今为止,《总目》屡屡言及的别本问题似未引起学者注意。修纂《四库全书》时,汇聚四库馆的图书不乏异本,馆臣概称之为别本,本文拟就其中的别本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厘清《总目》所言别本的概念及馆臣对别本的处理及利用,以期推进《四库全书》以及《总目》有关版本问题的研究。
一、馆臣所谓“别本”
目录学意义上的“别本”是相较于正本而言的一个概念,通常指异本,即同一部文献的不同版本,曹之谓“别本即正本之外的同书异本”〔7〕。别本之名出现较早,《隋书·经籍志》著录《江夏王义恭集》11卷,“又有《江夏王集别本》十五卷”〔8〕,但关于别本的概念及具体含义则鲜见论及。《总目》所及别本数量较多且含义丰富,与目录学意义上的别本也颇多不同,初步可分为同书之别本、别集或丛书之别本以及某部文献部分内容的摘出别刻本。
1.同书之别本
文献屡经雕版,往往衍生出多个刻本,正本之外均可称为别本。《总目》著录或存目的别本不在少数,大多同书同名。对同书同名之别本,《总目》通常在正本名称前加上“别本”二字以示区别。如《别本十六国春秋》《别本干禄字书》《别本晏子春秋》《别本朱子年谱》《别本革朝遗忠录》《别本汉旧仪》《别本农政全书》《别本考古图》《别本潜邱札记》《别本实宾录》《别本茶经》《别本韩文考异》《别本袁海叟诗集》《别本浚谷集》《别本攻媿文集》《别本缘督集》等。也偶有将“别本”二字置于书名之后者,如《晋书别本》《洹词别本》等。①《总目》所见同书之别本除在正本名称前后加“别本”外,有些与正本还有一些细微区别,如《别本浚谷集》之正本为《赵浚谷集》,《别本袁海叟诗集》之正本曰《海叟集》,且《总目》失载,提要见文渊阁本《海叟集》卷首。
《总目》所见同书之别本与正本的关系比较复杂,除版刻先后、行款不一等方面的差异外,往往还存在卷帙多寡、内容增删、编排次序甚至题名不一等诸多不同,有时不啻天壤之别。卷帙多寡者如《十六国春秋》,正本100卷,别本仅16卷。编排次序不同者如明人崔铣所撰《洹词》12卷,系赵王府味经堂刊本,“皆编年排次,不分体裁,杂著笔记亦参错于其间”〔9〕。而《洹词别本》17卷并《附录》4卷则系嘉靖三十五年(1556)池州知府周镐命贵池教谕范某重编刊刻,“始区别体裁,以类汇次”〔10〕,内容文字并无增损。内容增删方面较为复杂,各本情况不一。如子部谱录类著录宋吕大临《考古图》10卷、《续考古图》5卷、《释文》1卷,同时又存目《别本考古图》10卷,此别本乃元大德三年(1299)茶陵人陈翼子重刊本,删《续考古图》及《释文》,附诸家考证之文,馆臣称其已非吕氏之旧,“且亦自多谬误”〔11〕。题名不同者如集部别集类著录《原本韩文考异》和《别本韩文考异》各一部,原本题名“宋朱子撰”,别本题名“宋王伯大编”。又子部谱录类著录《茶经》3卷,“唐人陆羽撰”,又存目《别本茶经》3卷,“旧本题名玉茗堂主人阅”。两者卷数相同,但内容出入较大,别本系合陆羽《茶经》3卷为1卷,又附《水辨》《外集》各1卷,馆臣称此本“编次无法,疏舛颇多”,“冗杂颠倒,毫无体例”〔12〕,疑为庸劣坊贾托名之作。
2.别集或丛书之别本
古代文人之别集在结集刊刻前后,均不乏其中部分作品别刻单行的情况。结集前已别刻单行者,如子部类书类存目之《文安策略》乃明人刘定之揣摩程试所拟“场屋对策之作”,明人周荣所撰《呆斋公年谱》记《文安策略》成书于宣德九年(1434),刘定之时年26岁,尚未登第(刘定之及第在正统元年即1436年)。〔13〕馆臣谓正德八年(1513)刘定之刻《呆斋集》时,始将《文安策略》编入集中,“此其别行之本也”〔14〕。结集后别刻单行者如集部词曲类存目宋人程珌《洺水词》1卷,馆臣谓“珌有《洺水集》,已著录,诗余二十一阕已载集中,此毛晋摘出别行之本也”〔15〕。所谓“毛晋摘出别行之本”即《宋名家词》本,毛晋《跋洺水词》称其于崇祯六年(1633)购得《洺水集》26卷,虽“遗逸甚多而大略已概见”,于是“急梓其诗余二十有一调以存其人”〔16〕。多数情况下,馆臣并未交代别集与别刻单行本的先后问题,如史部史评类存目南宋陈亮《三国纪年》1卷,“大旨主于右蜀而贬魏吴,名为纪年,实史家论断之体,已载亮所著《龙川集》中,此其别行之本也”〔17〕;子部谱录类著录欧阳修《洛阳牡丹记》1卷,“已编入《文忠全集》,此其单行之本也”〔18〕;集部诗文评类著录南宋诗人杨万里《诚斋诗话》1卷,已收入杨万里《诚斋集》中,“此乃别行之本,今亦别著于录焉”〔19〕。
丛书尤其是综合性丛书,因兼括四部,容纳群籍,归类较为困难,故《总目》子部有类书而无丛书,馆臣将丛书存目于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且数量有限,总体评价不高,即使毛晋所编《津逮秘书》“较他家丛书去取颇有条理”,馆臣还是采取了“今仍分著于录,而存其总名于此,以不没其搜辑刊刻之功焉”〔20〕的办法。所谓“分著于录”,即存目丛书总名于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而著录或存目丛书子目于相应部类,无论子目篇幅长短,亦无论其在丛书中是单刻成册还是与其他子目合刻为一编,馆臣均视之为别本。如史部政书类存目王士禛《琉球入太学始末》1卷,全书不足千字,追叙明代琉球入国学事,馆臣称“其书已见士禛《带经堂集》中,此盖初出别行之本”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3《史部·政书类存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19页。案:王士禛《带经堂集》不见于《总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亦未收《带经堂集》,核清康熙四十九至五十年程哲七略书堂刻本《带经堂集》,《琉球入太学始末》作《纪琉球入太学始末》。,所谓“初出别行之本”实为《昭代丛书》本。②清初张潮辑刻的《昭代丛书》乙集所收《纪琉球入太学始末》即出自王士禛《带经堂集》。有些丛书虽未见总名存目,亦不乏有别本著录或存目者。如前文所及《别本十六国春秋》及颜之推所撰《还冤志》皆《汉魏丛书》本。又子部杂家类存目宋汪若海《麟书》1卷,“大旨主用兵之是,斥和议之非”,明人曾将其编入《若海集》,“此则别行之本,陈继儒刻入《秘笈》者也”〔21〕。但《汉魏丛书》及《宝颜堂秘笈》两部丛书均未见《总目》存目。
此外,有些类似于别集或丛书的文献亦有别刻单行本。如著录于史部职官类的《三事忠告》类似别集,系元人张养浩任县令、御史及参议中书省事时分别撰写的《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三书的合集,“三书非一时所著,本各自为编”〔22〕。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广西按察司佥事黄士宏始将三书合编刊刻,并题名《为政忠告》。宣德六年(1431)河南府知府李骥重刻,改名《三事忠告》,其中《牧民忠告》又存目于史部职官类,此别本乃“魏裔介摘出别行,非完书也”〔23〕。又如存目于集部词曲类词选之属的《宋名家词》形同丛书,故《总目》也采取了类似的处理办法,即“诸家词集虽各分著于录,仍附存其目,以不没晋搜辑校刊之功焉”〔24〕。《宋名家词》所收各家词集有的著录,有的存目。著录者如陈亮《龙川词》及《补遗》各1卷,存目者如洪瑹《空同词》1卷,仅收词十六阕。又存目姜夔词集两种,其一为《白石词集》1卷,系康熙甲午陈撰刻本,原附《诗集》之后,凡五十八阕,多有讹误窜乱;又存目《别本白石词》1卷,“此本为毛晋六十名家词中所刻,凡三十四阕,较康熙甲午陈撰刊本少二十四阕”〔25〕。
3.某部文献部分内容的摘出别刻本
馆臣还将某部文献中部分内容的摘出别刻本视为别本。如明嘉靖时人田汝成曾历官西南,“谙晓先朝遗事”,据见闻撰成《炎徼纪闻》14篇,“每篇各系以论,所载较史为详”,“与讲学迂儒贸贸而谈兵事者迥乎殊矣”〔26〕,此书著录于史部纪事本末类。史部杂史类又存目田汝成《龙凭纪略》1卷,“纪龙州土酋韦应、赵楷、李寰之乱,已见于《炎徼纪闻》中,此其摘出别行之本”③〔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3《史部·杂史类存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81页。案:《总目》有误,韦应其人既不见于《龙凭纪略》,亦不见于《炎徼纪闻》,赵楷为龙州土官属实,而李寰则为凭祥州土官。。又万历时人朱鸿所编《经书孝语》系摭拾《五经》《四书》中言孝之语为一编“而各为之发明”,末附《曾子孝实》,此书原附于朱鸿所刻《孝经》中,后又别刻单行,馆臣谓其“文既饾饤,论亦凡近,殊无可取”,因《孝经》已著录于经部,此书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姑置之儒家类焉”〔27〕。集部总集类存目明人崔铣所编《文苑春秋》4卷,“是集所录,起汉高帝《入关告谕》,迄明太祖《谕中原檄》,凡一百篇。各仿《毛诗小序》之体,篇首缀以数言,而别无诠释。大旨谓非关世教人心者不录,故名曰《春秋》”〔28〕。其中仿《毛诗小序》所为之叙录原各冠百篇之首,后来摘出别行,即史部目录类存目之《文苑春秋叙录》1卷本。
二、馆臣对别本的处理
修纂《四库全书》时,乾隆帝“特诏词臣,详为勘核”,对征集来的图书采取了“应刊、应抄、应存”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29〕,并系以提要,辑成总目。其中应刊、应抄者构成《总目》的著录书,应存者即存目书,只有提要。关于著录与存目,《总目·凡例》有明确规定,首先按质量将图书分为上、中、下三等,“其上者悉登编录,罔致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胪,见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兼匡厥谬。至于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虽咎誉之咸无,要流传之已久,准诸家著录之例,亦并存其目,以备考核”〔30〕。就别本而言,其与正本内容彼此重复是毫无疑问的,加之质量参差不齐,因此修纂《四库全书》时,馆臣严格遵奉乾隆圣谕,“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讹谬者,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31〕。此外,对于与正本并存的别本,根据不同情况,馆臣分别采取了正本别本均予著录、著录正本存目别本及正本别本均予存目三种处理办法。
1.正本别本均予著录
避免重复是图书编纂的基本原则,正本、别本难免彼此重复,但同时著录于《总目》者并不鲜见,原因则各有不同。
其一,因正本、别本差异较大,各有千秋,故同时著录以备参稽。如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102卷散佚于北宋,《总目》史部载记类著录《十六国春秋》和《别本十六国春秋》各一部,前者100卷,系明代万历年间嘉兴人屠乔孙、项琳所刊单行本,此本“盖抄撮《晋书·载记》,参以它书,附合成之,其实亦赝本也”;后者仅16卷,系《汉魏丛书》本,“寥寥数简,殆出后人依托”〔32〕。馆臣称别本在屠乔孙本之前,“而亦莫详其所自”,由于《十六国春秋》之正本、别本出入较大,且均非原本,但鉴于原本已佚,屠乔孙本“皆联缀古书,非由杜撰”〔33〕,故馆臣视其为正本而著录。又因屠乔孙本既非原本,《汉魏丛书》本亦“疑以传疑”,因此“姑并存之,以备参考焉”〔34〕。正本别本同时著录的还有朱子《原本韩文考异》和《别本韩文考异》。《韩文考异》重在考证韩愈文集各本之异同,“参校众本,弃短取长”,原于韩集之外别行,“至宋末王伯大,始取而散附句下。以其易于省览,故流布至今,不复知有朱子之原本”;《总目》著录之原本系李光地翻刻朱子门人张洽所校旧本,最为精善,李光地卒后,“其版旋佚”,故传本稀少,此原本“犹当日之初印,毫无刓阙,尤可贵也”〔35〕。别本则是宋人王伯大重编本,“离析《考异》之文,散入本集各句之下”,又采洪兴祖《年谱辨证》、樊汝霖《年谱注》以及孙汝听、韩醇、祝充等各家笺注为之音释,附于各篇之末,“盖伯大改朱子之旧第,坊贾又改伯大之旧第,已全失其初”;馆臣著录李光地所刻原本“以存旧式”,同时又著录王伯大所刻别本“以便参稽”〔36〕,无论正本、别本,均有不可替代之价值。
其二,为了强调别本在某方面的特别之处,在已著录正本的情况下,同时著录别本以凸显其价值。如南宋著名文人周必大生平著作由其子周纶依家刻《六一集》体例编为《文忠集》200卷,又称《平园集》,其中有《玉堂杂记》3卷、《二老堂诗话》2卷,又分别著录于史部职官类和集部诗文评类。馆臣谓《玉堂杂记》“皆记翰林故事,后编入必大文集中,此乃其别行之本也”,并特意交代了著录此别本的原因:
宋代掌制,最号重职,往往由此致位二府。必大受知孝宗,两入翰苑,自权直院至学士承旨,皆遍为之。凡銮坡制度沿革,及一时宣召奏对之事,随笔记录,集为此编。所纪如奉表德寿署名、赐安南国王嗣子诏书之类,皆能援引古义,合于典礼。其他琐闻遗事,亦多可资谈柄。洪遵《翰院群书》所录,皆唐代及汴都故帙,程俱《麟台故事》亦成于绍兴间,其隆兴以后翰林故实,惟稍见于《馆阁续录》及洪迈《容斋随笔》中。得必大此书,互相稽考,南渡后玉堂旧典亦庶几乎厘然具矣。〔37〕
《二老堂诗话》是周必大论诗之作,“凡四十六条,原载《平园集》中,此后人抄出别行者”,馆臣认为周必大学识渊博,又熟悉掌故,其论诗之语“多主于考证”〔38〕,在考证业已成为学术主流的乾嘉时期,《二老堂诗话》与《文忠集》同时著录也在情理之中。
2.著录正本存目别本
著录正本存目别本理应是《总目》的常态,《总目》存目书的数量几乎是著录书的两倍,其中别本占有一定比例。杜泽逊称“凡别本存目者,必于内容或体例与正本有一定差别,完全相同者例不两见”〔39〕,因此著录正本存目别本首先是为了避免重复。如史部编年类存目宋人尹洙所撰《五代春秋》两卷,此书纪事始于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迄后周世宗显德七年(960)正月,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馆臣认为此书已收入尹洙《河南集》中,“此盖其别行之本,以初原自为一书,故仍存其目焉”〔40〕。避免重复之外,著录正本存目别本尚有其他各种原因,有时是为了提醒后人比正本更为通行的别本实际上并非善本,有时则因为质量问题。前者如史部传记类著录《晏子春秋》8卷乃编修励守谦家藏本,存目之《别本晏子春秋》6卷乃乌程闵氏朱墨版,此别本对正本多有改窜,“然今代所行,大抵此本。恐久而迷其原第,因附存其目,以著其失焉”〔41〕。后者如吕大临《考古图》16卷已著录,又存目《别本考古图》10卷,“此本无《续图》及《释文》,乃元大德己亥茶陵陈翼子所重刊,附以诸家之考证,已非吕氏之旧,且亦自多谬误”〔42〕,故别存其目。
著录正本存目别本的情况以集部文献较为多见,馆臣在提要中对其原因偶有交代。如集部总集类著录南朝陈徐陵所编《玉台新咏》10卷,又存目清人冯舒校、冯武刊《冯氏校定玉台新咏》10卷。馆臣谓《玉台新咏》刻本虽多但久无善本,“明代刻本,妄有增益”,全失其真,《总目》著录的正本是赵宋王室后裔、明代著名刻书家赵宧光家藏旧刻本,“有嘉定乙亥永嘉陈玉父重刻跋,最为完善”〔43〕。存目之别本系以宋嘉定本为主,参校诸本而成,“今赵氏翻雕宋本流传尚广,此刻虽胜俗刻,终不能及原本,故仅附存其目焉”〔44〕。又集部别集类著录南宋楼钥《攻媿集》112卷,“与《宋史·艺文志》及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相同,犹为旧帙”〔45〕。又存目《别本攻媿文集》32卷,《诗集》10卷,别本“前后无序跋。又文集有目,而诗集无目。较原集少七十八卷,盖后人选录而成。然世所传写大抵此本,今亦附存其目焉”〔46〕。在无法区别正本别本的情况下,两者相较,善者著录,劣者存目。如清初阎若璩所撰《潜邱札记》是“考证经籍,随笔札记之文”〔47〕,传本有二,一为吴玉搢重订本,一为阎若璩孙阎学林重编本,因前者“尚有端绪”故著录入子部杂家类〔48〕,后者“盖学林尊其家学,不欲一字散失,故全录旧文,漫无体例”〔49〕,因不及吴玉搢本有条理而存目。
3.正本别本一并存目
虽然乾隆帝已经指出了著录与存目的处理原则,《总目·凡例》对存目标准亦有所交代,但具体到每一部存目文献,其原因则各不相同。黄永年认为《总目》存目书的标准比较复杂,大有逐一研究的余地,“像凡例那样想用三言两语来概括,总难免会有捉襟见肘之感”〔50〕。杜泽逊将存目原因归结为九条:限制规模、贵远贱近、扬汉抑宋、压制民族思想、维护封建伦理道德、避免重复、尊官书而抑私纂、原本残缺或漫漶过甚无法校写、著作水平庸劣或伪妄之书。〔51〕《总目》中正本别本同时存目者并不鲜见,两者鄙陋芜杂,质量欠佳,缺乏史料价值当是主要原因。如经部礼类存目《家礼仪节》和《别本家礼仪节》各1部,前者系明人邱濬“取世传朱子《家礼》而损益以当时之制”,系无名坊贾所刻,“已非原本之旧”〔52〕,又经坊贾窜乱,殊无伦次;后者题名杨慎编,实则无名坊贾据邱濬之本刊刻,“其图尤为猥琐”〔53〕。四书类存目明陈禹谟所撰《经言枝指》100卷,其中《名物考》20卷“摭拾旧文,亦罕能精核”〔54〕后经钱受益、牛斗星补订而成《别本四书名物考》24卷,“禹谟原本多疏舛,受益等所补乃更芜杂”〔55〕,故一并存目。又史部杂史类存目无名氏《北平录》和《别本北平录》各1卷,两者皆抄自实录,从《总目》提要看,《北平录》与《别本北平录》所记似非一事,经笔者比较,实际上是同一部文献的不同版本。①《总目》言《北平录》“载明洪武三年徐达、李文忠分道出塞,追王保保及袭破应昌府事。纪录颇为简略。惟达与文忠所上二表及太祖封爵诸臣诏谕,则全篇载之。疑后人从实录中抄出者也”。又言《别本北平录》“纪明洪武元年命徐达、常遇春等北征之事,而终以君臣鉴戒之语。其年月皆与史合。核检其文,亦从实录抄出也”。参见〔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2《史部·杂史类存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75页。检《金声玉振集》本《北平录》,叙事始自洪武元年,与《别本北平录》确为同书异本。正因为如此,在馆臣看来,明初实录保存完好,抄自实录的《北平录》,不论正本别本,均无著录价值,故一并存目。又如集部词曲类存目姜夔的《白石词集》和《别本白石词》各1卷,前者系康熙甲午陈撰刻本,附于诗集之后,“凡五十八阕,较毛晋汲古阁本多二十四阕。然其中多意为删窜,非其旧文”〔56〕;后者则为毛晋《宋名家词》本,仅三十四阕,比陈撰刻本少二十四阕,“盖第据《花庵词选》所录,仅增《湘月》一阕,《点绛唇》一阕而已”〔57〕。
三、利用别本校勘补缺
讹夺佚缺与典籍辗转传刻相生相伴,而校勘则是勘定古籍脱漏衍误、订讹补缺的必要手段,古人早就认识到了别本在文献校勘中的作用。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国家藏书,即广罗异本,相互补充。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556),诏令校定群书,樊逊等11人“同被尚书召共刊定”,“时秘府书籍纰缪者多”,樊逊建议效仿刘向借助众本校书之故事,向富藏图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秘书监尉瑾移尚书都坐,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58〕。南宋刘跂《金石录序》曰:“昔文籍既繁,竹素纸札,转相誊写,弥久不能无误。近世用墨版摹印,便于流布,而一有所失,更无别本是正。”〔59〕由此可见别本在古文献校勘中的作用与价值。
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常因无别本可资校补而深感惋惜。如南宋刘黻所撰诗文多有散佚,其弟应奎裒集诗文残稿为《蒙川遗稿》4卷,“惟传抄既久,文多讹脱,更无别本可校,为足惜耳”〔60〕。对无别本可资校补的缺佚文献,馆臣采取暂付阙如以存其真的处理办法。如南宋李心传所撰《旧闻证误》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姊妹篇,主要记载北宋史事,两者不相重复。“或及于南宋之事,则《要录》之所未及,此补其遗也”,此书体例同《通鉴考异》,先列旧文,次为驳正,条分缕析,决疑定舛,“于史学深为有裨,非淹通一代掌故者不能为也”,原书15卷,明代已无传本,馆臣辑自《永乐大典》,亦仅存十之三四。元代周南瑞所编《天下同文集》“所载颇有苏天爵《文类》所未收,而足资当日典故者”,此书系麻沙元版,原本50卷,佚卷17、18、31、34、35、41共6卷,“盖麻沙旧式,分卷破碎,传抄易于佚脱。今既无别本校补,亦姑仍原本录之,以存其真焉”〔61〕。姑仍其缺或姑仍其旧实属无奈之举,因而当有别本可资校补时,馆臣尽量利用别本校勘补缺,所用别本主要有《永乐大典》本、丛书本和其他别本或刻本。
1.《永乐大典》本
《永乐大典》在修纂《四库全书》中的作用不言而喻,馆臣不仅从中辑出了《旧五代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元和姓纂》等多部重要著作,辑佚之外,还充分利用《永乐大典》进行校勘补缺。如元人程端学撰有《春秋三传辨疑》20卷,清初汇刻《通志堂经解》,因其残缺不全未予收录,《总目》经部春秋类著录者为浙江吴玉墀家藏抄本,其中卷1“蠹蚀最甚,有每行惟存数字者”,卷2以下则完整无缺,经馆臣用《永乐大典》进行校补,“遂复为全帙”〔62〕。又史部地理类著录元陆友仁《吴中旧事》1卷,此书记载作者家乡吴郡之轶闻旧迹,可补地志之缺,“其体例则小说家流也”,因“刊本颇讹脱”,馆臣以《永乐大典》所载“互校补正,备元人说部之一种。虽篇帙无多,要与委巷之谈异也”〔63〕。又子部儒家类著录《袁氏世范》3卷,作者宋人袁采有多部著作皆失传,此书因陈继儒刻入《宝颜堂秘笈》而得以保存,惟丛书本“字句讹脱特甚”,“今以《永乐大典》所载宋本互相校勘,补遗正误,仍从《文献通考》所载,勒为三卷云”〔64〕。集部别集类著录宋人姚勉所著《雪坡文集》50卷,系其从子姚龙起所编,《宋史·艺文志》失载,“外间传本颇稀,讹阙特甚。今以《永乐大典》所载,各为校补。其《永乐大典》不载者,则仍其旧”〔65〕。
借《缘督集》和《别本缘督集》的提要,似可窥见馆臣利用《永乐大典》进行校补的细节。曾丰著作早在宋代已版行于世,后来渐次散佚,元代尚存40卷。明代万历十一年(1583)詹事讲刻印曾自明所辑12卷本《缘督集》“去取乖谬”,曾丰精华之作反因此本复次散佚,“殊堪惋惜”,因《永乐大典》编自明初,“尚见丰之原集,其所收录,较刊本多至数倍”,馆臣据以增补,“乃裒然几还旧观”,“佚而复存,亦云幸矣”〔66〕。《别本缘督集》即詹事讲所刻12卷本,“据事讲《自序》,其先本曾氏裔也,所选仅诗三卷、文九卷,挂漏颇多。今已采其中《永乐大典》所未载者,编入新本,故附存其目,不更缮录焉”〔67〕。也许正是由于《永乐大典》在修纂《四库全书》中的特殊地位,馆臣校补时,虽如同别本加以利用,但并不视其为别本。以上所及馆臣利用《永乐大典》校补的文献,除《雪坡文集》和《别本缘督集》外,均注明《永乐大典》本。
2.丛书本
修纂《四库全书》时,征集到的丛书以明人汇辑刊刻者居多,明人所刻丛书往往不取完本,多系摘录节抄,导致馆臣对丛书的整体评价不高,但在无别本可资校补的情况下,亦用丛书本进行校补。如史部载记类著录宋郑文宝所撰《江表志》3卷,卷首缺郑文宝撰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的序言,馆臣据《学海类编》本“补录成完帙焉”〔68〕。宋曾慥所撰《高斋漫录》属笔记杂著,所记“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迹,以至文评、诗话,诙谐、嘲笑之属,随所见闻,咸登记录。中如给舍之当服赪带,不历转运使之不得为知制诰,皆可补史志所未备。其征引丛杂,不无琐屑,要其可取者多,固远胜于游谈无根者也”,《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做2卷,世鲜流传,清初曹溶采自他书收入《学海类编》者仅五页,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1卷,“视溶所收多逾什之三四,其或溶本有之,而《永乐大典》失载者,亦参校补入”〔69〕。再如集部诗文评类著录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两卷系从《永乐大典》辑出之本,“考《说郛》及《学海类编》载此书,均止寥寥三四页。此本为《永乐大典》所载,犹属完帙。然有二条,此本遗去,而见于《学海类编》者。今谨据以增入,庶为全璧”〔70〕。
3.其他别本或相关刻本
编纂《四库全书》时,馆臣亦能充分发掘利用其他别本或相关刻本的校勘价值。如《总目》经部小学类著录唐颜元孙《干禄字书》系两淮马裕家藏宋椠翻刻本,“然证以蜀本,率多谬误”,馆臣著录时曾用蜀本互校,“补缺文八十五字,改讹体十六字,删衍文二字,始稍还颜氏之旧”〔71〕。然不知何故,馆臣用以校补的蜀本未见著录或存目,存目者系明末清初人魏裔介所刊《别本干禄字书》两卷本。又史部正史类著录的《金史》为内府刊本,其中卷33、卷76有缺文,盖明代监版脱误所致,馆臣用内府所藏元版校补,“仍为完帙”〔72〕,惜此元版未见著录或存目。馆臣用以校补且见于著录的别本有南宋汪藻的《浮溪文粹》。《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汪藻《浮溪集》60卷,岁久散佚,世无传本者几数百年,嘉靖时人胡尧臣曾刊行无名氏所辑《浮溪文粹》15卷,仅录诗文85篇,“而其原集终不复可见”。馆臣修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浮溪集》36卷,又用《浮溪文粹》参校补正,“庶操觚之士尚得以考见其大略焉”〔73〕。
四、结语
作为一部官修书目,《总目》奉敕编纂,悉禀圣裁,在重视图书来源的同时,忽略了图书版本的重要性,加之编纂《四库全书》时,对图书内容又多有改窜,致使有关《四库全书》版本问题的研究困难重重。作为版本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别本,《总目》着墨较多,为了解和研究《四库全书》的版本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综合相关记载可见,《总目》关于别本的认识、处理及利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妥当的,尤其是在别本的处理方面,并非简单地一概存目,而是根据内容及版本优劣,分别采取了正本别本均予著录、著录正本存目别本和正本别本一并存目三种处理办法。说明《总目·凡例》所言“一一辨厥妍媸,严为去取”〔74〕并非虚言,也体现了馆臣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以及珍视文献、甄别取舍的审慎态度。当然也毋庸讳言,《总目》涉及文献庞杂,馆臣对别本的认识较为模糊,有时将题名不同且内容出入较大的同名文献简单地视为正本与别本,如前文所及《十六国春秋》与《别本十六国春秋》、《原本韩文考异》与《别本韩文考异》。此外尚有存目两种同名文献而未区别正本、别本者①《总目》史部地理类存目《海道经》两种各1卷,似为同一种文献的不同版本。前者为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后者乃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参见〔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75《史部·地理类存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50页。,又有提要所及文献名称与实际不符者②《总目》集部别集类存目明人吴文华《济美堂集》8卷,馆臣称“文华有《粤西疏稿》,已著录。是集凡诗文四卷,颇沿台阁旧体。前四卷即《粤西奏议》及《留都奏议》,其初别本各行,后又编入集中也”。参见〔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78《集部·别集类存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01页。,尽管如此,瑕不掩瑜,馆臣对别本的认识仍不乏可取之处,且有深入探讨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