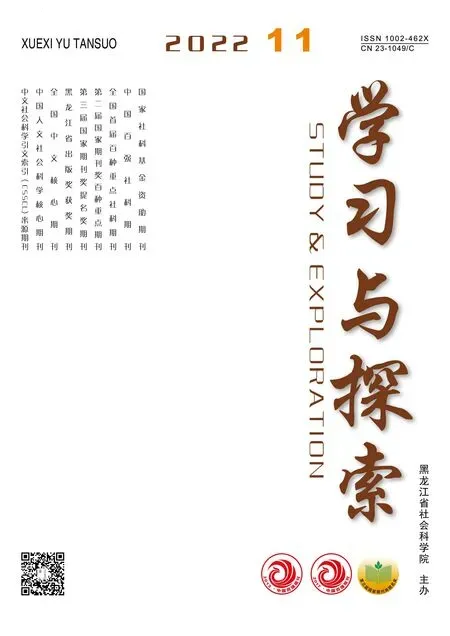李大钊文艺思想的基本要义与哲学根基
王 春 辉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哈尔滨 150080)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作为革命先驱者与启蒙思想家,其文艺思想无疑是重要的理论资源。李大钊文艺思想以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为旨归,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致力于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探索十月革命的道路,呼吁民族自觉和民族解放。李大钊始终紧跟社会政治、现实问题、中国革命的步伐,“李大钊的思想发展过程,是和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相符合的,他的思想中的某些特点,正是这一历史过程某些特点的具体而深刻的反映”[1]11。目前学界对于李大钊的民主思想、政治思想研究得较为深入,而对于李大钊的文艺思想研究相对零散,仍具有较大的阐释空间。
李大钊文艺思想包含三部分,一是哲学思想,二是史学思想,三是文论思想。在《史学与哲学》的开篇,李大钊谈及史学及文学与哲学的密切关系,强调三者之间的知识贯通性,“史学和哲学、文学的来源是相同的,都导源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三者“同源而分流,可以共同帮助我们为人生的修养”[2]64。因此,本文试图从哲学、史学、文论三个方面系统地梳理李大钊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在这一稳定的理论场域内,阐述李大钊哲学观、唯物史观、文论观的基本要义。
一、李大钊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
李大钊在《史学与哲学》一文中谈道:“哲学仿佛是各种科学的宗邦,各种科学是逐渐由哲学分出来的独立国。哲学的领域,虽然一天一天的狭小,而宗邦的权威仍在哲学。”[2]67由此可见,李大钊十分重视哲学所起到的引领与指导作用,这也奠定了李大钊哲学思想的核心地位。李大钊的哲学思想不是象牙塔式的抽象义理,而是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与实际问题出发,以整体的、达观的思路,分析问题的本质,给出科学合理的解释。李大钊的哲学学说不为建立宏观的理论体系,而是意图启发仍然以封建传统观念看待事物的民众,让人们能够自觉地以客观理性科学的态度去生活,以新的思想意识指导人们的生活方式。
1.唯物的自然观与时间观
李大钊认为自然是客观的、发展着的,是能够为人所认识的。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李大钊虽是讨论在人类的历史文化中,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往往来自于对某种学说的绝对信仰,但是仍能从论述中看出李大钊所秉持的自然观,即他将自然视为真理,视为一种评判的标准。“吾人生于今日之知识世界,唯一自然之真理外,举不足劳吾人之信念,故吾人之伦理观,即基源于此唯一自然之真理也。”自然是事物发展的法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尊崇自然即是尊崇理性,李大钊认为人的伦理观、道德观皆应摒除旧的思想束缚,应该真正地认识自然规律,以理性客观的精神建立伦理道德秩序。“吾人以为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1]79唯物的自然观明确物质的诞生与存在是在自然规律之中由社会群体所创造的,由此物质存在的本质、事物间的关系不再受到错误的落后观念之蒙蔽,新的自然观、世界观得以建立,因此李大钊认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企于自然进化之程,少加以人为之力,冀其迅速蜕演,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1]80,可见唯物自然观之重要。
时间观在李大钊的哲学思想中居于根基性地位,如何认识时间是李大钊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对时间意识的确认,一是为了坚持唯物主义哲学的客观性,因为对于物质的正确认识,对于物质与意识两者的辩证关系,对于唯物辩证法中联系观点、发展观点、矛盾观点的理解,都离不开客观的时间观念;二是通过树立唯物的时间观,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人生观与世界观。
李大钊从古语古字中考察人们记录时间的方式及其历史内涵,如《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中提出:“原人的‘秩序’‘恒久’的观念,大概得自太阳的出没和地球在太阳系中与其余诸星相保持的关系。云气的变幻,日月的运转,颇能与人以谐和、华丽、秩序、恒久的观念。”[1]341再如,李大钊从《说文》《尔雅》等书中找出季、年、禾、期、历等字的原义皆与禾田、年岁等含义有关,提出“中国以农立国,而周朝复以农开基;故以谷熟为年”[1]314。这表明,人们对表示时间的汉字的创造与书写,正体现了对于时间所形成的自然心理和原始认知,形成了保留在人们集体无意识中的时间观念。
李大钊为纪念晨报五周年著文《时》,主要讨论的也是关于时间的观念问题。首先,李大钊将历史与事物的发展置于时间滚滚不停的洪流之中,认为历史的兴衰和人生的成败皆是“时”的幻身游戏。在介绍唯物论时间观之前,李大钊分别从玄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方面阐述了时间在这些语境之中被阐释的辩证玄思,在科学语境中对时间的认识偏于计算与统计,在研究意识、心理的语境中对时间的认识又限于相对和不定。李大钊意图树立的是关于时间的哲学认识,以此说明历史的客观流动性,肯定历史的发展轨迹为“过去—现在—未来”,李大钊说道:“凡诸过去,悉纳于今,有今为基,无限未来乃胎于此。”“过去未来,皆赖乎今,以为延引。”“今是生活,今是动力,今是行为,今是创作。”[1]486在《今》一文中,李大钊对时间范畴“现在”的哲学意义也做出了精准的界定:“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这就是今最可宝贵的道理。”[1]94
李大钊以联系的观点看待时间,在连续的线性时间发展中,“现在”最富辩证性也最富创造性,对于此刻的人生,李大钊不仅号召大家竭力争取,亦要牢牢把握,方法论即为,“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要拿出努力,谋未来的发展,善用今,努力为将来创造。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1]96“过去与将来,都是在那无始无终、永远流转的大自然在人生命上比较出来的程序,其实中间都有一个连续不断的生命力。我们不能划清过去与将来,截然为二。这中间不断的关系就是我们人生的现在。”“我们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应该把我们生命中过去与将来间的关系、时间全用在人生方面的活动。”[1]165
通过《时》《今》《现在与将来》等文章的思考,李大钊归纳出时间的两个特性:异于空间的单一线性发展,即“时是有进无退的”;无论是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只可发生一次,即“时是一往不返的”,并相对应总结出几种人生观:面对时间的流动性,人们要杜绝徘徊踌躇,应迈往努进,“苟一刹那不有行为,不为动作,此一刹那的今即归于乌有,此一刹那的生即等于丧失”[1]486;面对时间的一往不返,应珍惜当下,彼此互助团结友爱。
李大钊通过对时间的论证,既形成了完整、整体的历史线条和时间运动的流淌轨迹,也确定了“当下”无可替代的作用——当下作为时间发展中的关键一环,为人类积极把握实践创造了现实条件,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突出当下的历史地位的同时,意在赋予人类平等的历史地位,鼓舞人们抛开落后消极的历史观,努力奋进,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李大钊呐喊道:“你不能旁观,你不可回顾,因为你便是引线前进的主动。”“吾人是开辟道路的,是乘在这时的列车的机关车上,作他的主动力,向前迈进他的行程,增辟他的径路的,不是笼着手,背着身,立在旁观的地位,自处于时的动转以外的。”[1]488可见,李大钊十分警惕对看待历史的论调,对宣扬悲观的、停滞的、主张逆退循环的历史观抱以痛斥的态度,坚持人的认识为螺旋式上升、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规律。
2.新与旧的矛盾观
新与旧是李大钊牢牢扭住的一对相反相成的辩证概念,在许多批评时事的短文和政治性、学理性论文中,李大钊都习惯用新与旧的社会案例来表明观点、批评时事。例如,李大钊认为对于阻碍社会发展的旧事物应不留余力地加以铲除,提出“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1]117。而对于新事物,“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的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1]119。
在《新的!旧的!》一文中,李大钊将新与旧对立的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学观察,从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现象论述进化的法则,他提出宇宙的进化、历史的更迭是凭借新与旧的运动来实现的,“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1]97。李大钊认为,在历史发展的前进运动中,以新事物的诞生取代落后的旧事物,除旧纳新、推陈出新是世界的进化法则,旧事物根深蒂固,新事物尚为萌芽,新与旧便呈现为矛盾对立的社会形态,阻挠事物的更新发展。正如李大钊所言:“矛盾的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凑到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1]97李大钊以这种矛盾对立的方法看待社会生活中的诸种问题:如宪法、政治、法制习俗、社会生活等等。同样,李大钊也提出了解决新事物力量薄弱的方法论:“鼓励青年释放创造力,打破矛盾生活,脱去二重负担。”[1]100
在学理上,李大钊剖析了新旧两种不同的历史观,道出旧历史观非科学落后的原因所在,以新的历史观将社会的进步与人的主动创造联系起来。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谈道:“旧历史的方法与新历史的方法绝对相反:一则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社会本身以外,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一则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动力与指导力;一则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观,一则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这全因为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与变迁全为天意所存,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力所造,这种人类本身具有的动力可以在人类的需要中和那赖以满足需要的方法中认识出来。”[1]339新与旧的对立是李大钊认识社会矛盾分析社会问题的主要手段,两者作为一对互为依存、互为对立的矛盾概念贯穿着李大钊哲学的始终,对新事物与旧事物本质的辨别形成了李大钊唯物辩证法的扬弃观点。
3.辩证否定观的扬弃思想
李大钊善于运用联系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比如他提出“一人之未来,与人间全体之未来相照应,一事之朕兆,与世界全局之朕兆有关联”[1]101。再如《庶民的胜利》中“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1]111。联系的观点意味着历史不是个别的单一的特例,而是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
李大钊还运用联系的观点看道德观建立的问题,《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开宗明义提出:道德是什么?道德的内容是永久不变的还是常常变化的?道德有没有新旧?道德与物质的关系是什么?李大钊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来解决这几些问题。指出道德是有动物的基础之社会的本能,道德因时因地而变动,道德有新旧的问题发生,新道德的发生就是社会的本能的变化,物质开新,道德必跟着开新。今日需要的道德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1]273。可见,李大钊视新道德的建立为一个联系的发展的辩证过程。
辩证法的否定观点提供了扬弃的方法论,李大钊在多篇文章中都运用了辩证的思维方式,如提出天运人生周行不息,盈虚消长,相反相成,再如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提出:“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吾以为宇宙大化之流行,盛衰起伏,循环无已,生者不能无死,毁者必有所成,健壮之前有衰颓,老大之后有青春,新生命之诞生,固常在累累坟墓之中也”[1]58。李大钊视事物的发展为循环更新的链条,从衰颓之中能见新生,在废墟之中能见新事物的崛起,在衰老之中能见青春,在否定之中亦见事物的更新。
李大钊提出的青春之中国,体现的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扬弃精神,以及事物自身所蕴含的更新与变革力量。“盖尝闻之,生命者,死与再生之连续也。今后人类之问题,民族之问题,非苟生残存之问题,乃复活更生、回春再造之问题也。”[1]71在扬弃的过程中,事物否定自己,衰败的必将被新生的所取代。正如“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1]70,而脱胎于旧事物中的新生命只是事物发展间的一环,新事物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为需要裂变更新的旧事物,历史便在无限更新无限循环的辩证否定之中得以发展。
五四时期的思想先驱皆重视青年对新中华崛起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大钊视青年为青春中华的建设者,青年亦要以辩证否定的扬弃精神磨练自己锤炼意志。在《今》一文中,李大钊认为青年唯一的责任,就是“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实则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如何能杀得?所谓杀者,不过使今日的我不仍旧沉滞于昨天的我”。勉励青年不沉溺于历史的负累,秉持创新与扬弃之精神。
二、李大钊文艺思想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海格尔的辩证法的影响,就是历史观是从哲学思想来的证明”[2]68。李大钊的现代史学研究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上的,通过认识当下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认识历史的本质,与旧历史观作对比,认清社会历史的根本问题。自1920年起,李大钊开始在北京大学开设“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革命、历史哲学等问题做了学理性和系统性的深入研究,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将《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结合起来,既蕴含经济观点,也容纳革命的实践经验。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谈道:“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篇文章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论,比较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学(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介绍“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以及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资本集中说”,得出“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1]194。
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李大钊强调社会的进步也基于人类的感情,与社会进步基于生产程序的变动一说并不发生冲突。因为“除了需要的意识和满足需要的愉快,再没有感情,而生产程序之所以立,那是为满足构成人类感情的需要。感情的意识与满足感情需要的方法施用,只是在同联环中的不同步数罢了”[1]339。由此可见,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不是机械的死板的学说,而是结合了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的灵肉一体、物心两面的科学理论。
在李大钊所倡导的历史观之前,存在两种历史观形态:一是宗于神道天命,二是依托于神德者,这两种都形成于道德教化之下没有科学的历史法则的认识。
李大钊将西方自康德已降的历史法则总结为四大类: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与进步的历史观,个人的历史观与社会的历史观,精神的历史观与物质的历史观,神教的历史观与人生的历史观[2]3。第一种是价值本位,后三种则以历史发展的动因为准绳。李大钊推演和总结各个历史观,得出了“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可以称为新史观”[2]4的结论。新史观主张以新史料、新智识重作历史,树立新的史学标准,以抗辩旧的史观。故《史观》中认为:“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2]1李大钊认为历史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亦是人类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人们赖以生存的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纵观即为历史,横观则为社会哲学。历史不是陈编,而是“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是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2]1。历史的重要性在于:一切史的知识、史学研究、史的记录,都要统摄在历史观之下。
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李大钊指出:“从前把历史认作只是过去的政治,把政治的内容亦只解作宪法的和外交的关系。这种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人类的历史乃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2]25李大钊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应独立在政治学或其他学科之外,在分科及界定历史学的概念时,李大钊作以明确清晰的划分,各个文化科学皆含有自身的组织学与历史学,各种文化内容应独立且形成自身的学科规范,而非受其他学科的隶属和支配。“不得以一种组织学概组织学的全般,也不得以一种历史学概历史学的全般。”[2]22普遍的历史学与各个学科的历史学之间的关系不是历史学的全部,离开了各个特殊的历史学,也无法形成抽象的、整体的历史学,两者之间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应该说,李大钊对学科的内部组织与学科间独立性的认知,是科学的也是前卫的。
李大钊在《史学与哲学》中强调史学可以分为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两个部分,记述历史的目的在于收集历史事实加以描写,而历史理论则是科学地考察零碎事实间的因果关系[2]66。在《史学要论》中李大钊更加细致地划分出记述的历史可以分为个人史(即传记)、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六大部分。历史理论可以分为个人经历论(即比较传记学)、氏族经历论、社团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人类经历论六大部分。
唯物史观以客观物质的眼光探寻人类历史、思想、社会生活变迁的根本原因,认为经济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强调人要在变化的、发展中的辩证法思维中看待事物更迭、认识事物的本质。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一文中,李大钊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将带有历史意义的社会比喻为建筑,认为社会是由基础(Basis)与上层(Uberbau)共同构成。“基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氏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氏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氏历史观的大体。”[1]293这种客观理性地看待社会进程与历史发展的学说,令历史学研究带有科学精神,从此历史学从为英雄作传转向了科学研究。
唯物史观的史学价值、人生观意义重大,“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1]340。我们应该“应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1]340。“斯时人才看出他所生存的境遇,是基于能时时变动而且时时变动的原因”,这些变动都是“新知识施于实用的结果,就是由象他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所创造的新发明新发见的结果,这种观念给了很多的希望与勇气在他的身上”。“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这种唯物史观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就是将人从被动的被压迫被否定的历史地位、社会处境转变为了自觉的、主动的生存处境,“这个观念可以把他造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人,他才昂起首在生活中得了满足而能于社会有用”[1]338。
李大钊在《研究历史的任务》一文中重点研究了历史的抽象意义,他通过反观历史本身的本体性质,区别了历史材料与历史本体,提出古籍史书的记录并不是历史的代名词,而只是作为研究历史的材料,明确了“历史是整个的、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决不是历史”[1]479。而历史的这种生命性不是任意发展的,而是以经济作基础,随着新的经济关系的发生,人类生活也随之“跟从新建筑”[1]480。
李大钊还吸取希腊历史学家希罗陀德的观点,提出历史学家的两大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这种科学认识不仅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在今天对文学史整理工作、文学研究、历史学研究也具有深刻的启发性。正如李大钊所言:“于整理上,要找出真确的事实;于理解上要找出真理。”也就是说在进入历史时,要充分的发挥后人的主动性,不怕改作重做,而是要坚定今人客观的立场,秉持新的历史观念,揭开历史的迷雾、遮蔽与谬误之处,“推翻古人的前案,把那些旧材料旧纪录,统通召集在新的知识面前,作一个判决书”[1]483。李大钊坚信历史不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以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是发展着的,因此,李大钊才指出:“真理的见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较的。”[1]483
三、李大钊文艺思想中的文论观
李大钊文艺思想的流露往往是伴随着他的哲学思辨而展开的。因此,他的文论观既不是铺述式的,也不是暧昧含混的隐喻式的,而是凝练思想浓缩精华,在严密的逻辑与论点的输出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方法,直抵事物本质,“以期获得一种哲学的明慧,去照彻人生经过的道路”[1]505,以科学客观的精神追寻真理,以求为后人做出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基础。李大钊的这种治学态度受到其人生观的影响:如果“你一旁观,你一回顾,便误了你在那一刹那在此不准退只准进、不准停只准行的大自然大实在中的进程,便遗在后面作了时代的落伍者”[1]487。李大钊认为人应该跟上历史的脚步,以自己发展、变换的认知与智慧,开拓时代的疆土,尽好自己作为历史发展中的一环的职责与义务。
在以往对李大钊文艺思想的研究中,《文豪》《什么是新文学》是必会提及的作品。《什么是新文学》无疑是李大钊文艺思想的核心,篇幅虽短,却道出了新文学的本质内涵。李大钊认为新文学的本质在于为社会写实、以博爱心为基础、为文学而创作,单从文学语言或内容题材上进行的创新算不得具有新事物意义的文学。文学应该饱含真爱真美,尤其要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1]277为指导,以此培育新文学新运动的根基。《文豪》所谈的是文学家的社会使命与责任担当,也就是通过文学的感化力量净化人心,将世间凄苦以艺术渲染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文学中倾注文学家的世界观、同情心、悲悯与忏悔精神,读之使人的心灵受到洗涤与净化,直感“作者已先我而淋漓痛切出之”[3]70, “造光明世界于人生厄运之中”[3]68。李大钊的《文豪》将文学的功用分析得鞭辟入里,文学模仿现实并加以渲染,在敏锐地观察社会现象之后,发挥文学的感化功用,“以全副血泪,倾注墨池,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昭示人心来复之机,方能救人救世”[3]71。
如果说《文豪》《什么是新文学》是从理论层面论及文学的本质,那么《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与《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二文则体现了李大钊对于理论的实践,是他将所吸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在文史学科研究的典型例子。李大钊将唯物史观抽象的理论细化进中国的文史哲研究之中,不仅是学理上的紧密结合与生动应用,同时也体现出李大钊鲜明的文艺思想和治学态度。
《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是李大钊在北大授课时的讲义,文章以词源的形式考究了从原始社会起,人们对于时间的计算和表现方式,原始社会的经济组织形态的变迁以及货币流通方式等问题。李大钊意在透过原始社会的文字书契之演变,以象形解意的方式,客观地认识原始社会的经济、社会伦理秩序等问题。“从文字语言上考察古代社会生活的遗迹”,继而“考察当代社会生活的背景实在当代社会的经济情状”[1]355。借用中国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诗经》《说文》等经典著说、古文字、西学的历史事例与学理界说等知识,梳理原始社会的基本形态及其演变过程,以文化风貌观察民族的存在方式。在文章中,李大钊抛开了神秘主义的宗教阐释方法,阐述传统积习、宗教学说、图腾起源等遮蔽在历史深处的文化问题,将研究视角锁定在原始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客观的文字字形作为打开关窍的钥匙,在说明文字的象形意义之时,道出建立在此经济基础之上的原人的社会意识。可以说,《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是李大钊对唯物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一场具体的文化实践。
在文章中,李大钊首先明确的是象形文字的客观性和物质性。李大钊不仅列举了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同时也指出苏格兰、墨西哥、埃及等古迹上也存有象形文字,以说明“上古时文字都象形”[1]342。诸如伏羲画卦始得记号文字、神农时代的结绳记事、埃及以椰树树叶表年数等实例,证明象形文字是上古时代人们生活的真实记录,是人们生活的产物。可见,文字书契以象形的方式将生活形态凝练进文字表现之中,承载着事物存在的意义,是原始文化与经济构成的一种客观反映。正是文字的这一属性,带动了李大钊全篇的唯物分析。
李大钊指出,“人类最初的家庭是森林,后来遇见了一个冰期,变更了气候,人类遂转徙河岸海滨去”。生存环境的变更带来了不同的生存方式,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样貌,迁徙的过程即人类原始文明的演进过程。李大钊考究了农耕文明、石器时代、“钻燧改火”三种由物质生存方式而决定的纪年方式,以及受物质存在影响的、带有鲜明印记的观念意识,比如以农立国的中国以谷熟为年,季、期等字皆与稼穑、禾熟、年岁等寓意有关,因为重“黄色”,称始祖为黄帝。再如“古代有钻燧改火为历岁一周的记号习惯”,将精于用火者奉为君主等。从中可见,李大钊对象形文字、远古文明的认识带有唯物史观的鲜明烙印,强调物质存在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
其次,李大钊从经济形态上来论述原人社会的唯物反映,古代以贝为货币,贝部文字多为经济用语,亦有用石或骨仿造贝形用为货币。李大钊同样通过《尚书》《诗经》等古籍的文字记载,推断各个时期的货币流通方式。所强调的依旧是物质生活对意识观念的决定作用,并将这种影响留存于文字形式上。
最后,李大钊还考究了图腾的历史由来,以及“感生说”背后的生理原因,更是以女子的婚娶为例,从“妇、娶、婚、嫁”等字中得出“男子在经济上占了优越地位以后”女性地位所发生的变化。李大钊意在破除人们对于传统所抱有的思维定势,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此文的意义在于以科学、客观的学理方法分析历史,以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治学,并运用大量人类学、考古学知识与实例论证文化的演变进程,形成客观的科学的文化观、历史观。李大钊的这一文论观点在他的人文研究中是一种根本思路,在《研究历史的任务》一文中,李大钊特别强调:今天的史学研究“必把这些神话一概删除。特别注重考察他们当时社会的背景与他们的哲学思想有若何关系等问题”[1]484。李大钊通过吸收理解唯物史观,将其应用到人文学科的研究当中,注重的便是物质与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重视产生文化的社会背景与经济基础。在20世纪初的时代背景中,这种文论观念是超前的也是科学的客观的,具有理性精神的。
《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史学研究上的应用,体现了李大钊看待历史、人生、时间三者之间关系的态度。《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同《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样,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找寻并列出实例,总结理法,破除偏信与误读,揭示文化研究、文学研究、史学研究中的真理性认识,启发新智,是真理性认识与实践的结合,体现了李大钊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在此文中,李大钊反对将文学创作中的想象、美化、虚构等“空笔”的手法运用到历史书写中去,这样会导致对历史真实的实在性认识不清,“本求迈远腾高,结局反困蹶于空虚的境界,而不能于实地进行一步”[1]505。李大钊主张对待历史的态度应是严肃认真的,将历史作成哲学的样子,以老成的科学的精神不断进行训练,给人以觉醒和启发。
李大钊认为对待历史、对待时间的态度在认识论意义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现代史学给予人们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态度方能塑造脚踏实地的人生观[1]506。面对历史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进路,人们应形成进步的世界观,了解历史的进程源源不断向前发展,历史由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历史规律,人们自然就会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创造生活,发现自己、认识自我,这正是李大钊所揭示的唯物史观对人生态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结 语
在李大钊的文艺思想中,哲学、史学与文学这三种思想似三条河流,最后汇入“人生修养”的总体层面。也就是说,李大钊的文艺思想是为了塑造现代人的理想人格,实现趋于至善的人生修养。其中,文学可以启发民族的社会的情感,哲学可以令人达观对事物形成整体的本质认识,而历史既能激发人的民族情怀,同时也能提高洞察世事的能力。也就是李大钊所说的:“史学教我们踏实审慎,文学教我们发扬蹈厉。”[2]71
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中勉励自己:“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1]61李大钊呼吁以博爱的互助精神打破旧事物旧文化的束缚,打破人与人之间孤独的生存状态。正如《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中所言:“纵的组织的基础在力,横的组织的基础在爱。我们的至高理想在使人间一切关系都脱去力的关系,而纯为爱的关系,使人间一切生活全不是争的生活,而纯是爱的生活。”[1]304这不仅是李大钊治学的理想目标,亦是他用生命来践行的崇高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