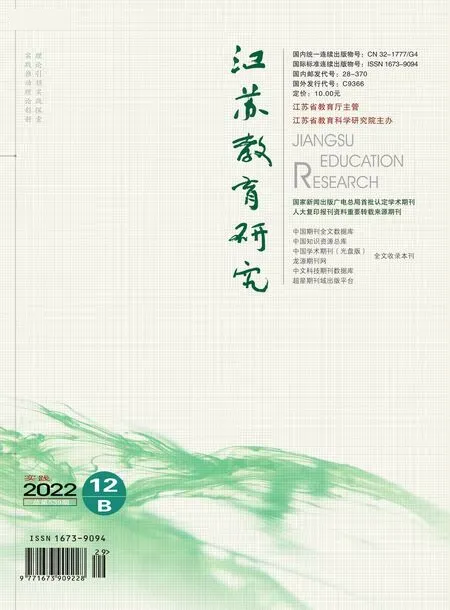问乎之妙:儿童问学课堂的意蕴
杨九俊
问,是儿童接触陌生事物后的第一反应,也是他们探究未知世界的基本方法。“学问千千万,起点在一问。”儿童是天生的好问者,教师要善待儿童的“问”,对此《礼记·学记》说:“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问”是许多老师在教学中给予高度关注的,但像潘文彬老师团队的儿童问学课堂做得这么风生水起的,实在不多见。潘文彬的“问学”之妙在哪里呢?
一、儿童问学课堂是素养型的
儿童问学课堂指向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这体现在问中有“人”,闪烁着主体性的光芒。“问学”,“学”从“问”起步,是学生的主体作用决定了课堂的起点和走向,而教师的积极引导,学生的沉浸投入,则是这种课堂重要的表现。儿童问学课堂回归儿童立场,解放儿童,呵护天性,让儿童在课堂上像儿童的样子,能够自由自在地想,无拘无束地问,快快乐乐地学。戴维·迈尔斯认为:“在一个惬意的环境中被动地生活所感受到的快乐,远远比不上那种有激情地投入到有价值的活动中,以及为目标而奋斗所能体验到的满足感。”[1]更何况,在学习的情境中,被动式学习是难有惬意的。
儿童问学课堂能充分发挥学习者的主动性,把“问”的权利还给儿童,让儿童在学习的过程中萌“问”、想“问”、敢“问”、会“问”、乐“问”、善“问”,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产生学习探究的欲望。“问”中有“思”,“问”是围绕核心知识的学习进行的,这就使“问”具有打开思维之门的作用。“思”源于“疑”,杜威描述的“思维五步”的第二步是“使感觉到的(由直觉经验得到的)疑难或困惑理智化,成为有待解决的难题和必须寻找答案的问题”。于是,思维的爬坡就成为学科实践的主轴,这是我们在儿童问学课堂中常常看到的风景。
问中有“法”,问不止于“学会”,还在于“会学”。儿童问学课堂的“三问”——问源、问流、问法,不仅强调问的“法”,而且“问源”“问流”也可以看作“问法”。皮亚杰认为,不要关注儿童走得有多快,而要关注儿童走得有多远。儿童问学课堂培养的学习能力是“带得走”的。显然,问中有“人”,问中有“思”,问中有“法”,形成了潘文彬老师的团队培育核心素养的“自己的句子”。
因此,儿童“问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提问,而是一种思维活动,是一种质疑问难,是一种探索实践,是一种求知过程;是儿童在问题的驱动下,自主学习、主动探究,围绕核心知识的运用,大胆地“问”、主动地“学”,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在自主、合作、探究的过程中学会学习、快乐成长。
二、儿童问学课堂是项目化的
潘文彬老师的团队自觉地将儿童问学课堂置于项目化学习的领域。他们发现儿童问学课堂与项目化学习有诸多相同之处,比如:两者都既是一种教学模式,也是一种学习模式;两者都能纳入儿童的视角,都符合“儿童本位”的教学思想;两者都离不开真实的问题情境;两者都指向共享共建共情的对话或平台的建构;两者都指向儿童的全面发展;等等。
于是,他们以项目化学习为基本载体,开展儿童问学课堂的创造性实践。项目化学习这几年很热,也有多种阐释,我还是比较赞成一种“朴素”的理解,即扣住内容、活动、情境、结果四大要素来开展学习活动。内容,现实生活中包括知识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它应该有知识系统性的线索;活动,学生使用一定的工具和研究方法开展探究行动,具有挑战性和建构性;情境,为学生提供更丰富、更真实的学习经历,有助于促进学生合作,有利于学生掌握并使用工具;结果,指在学习进程中或学习结束时学会的知识、技能,包括“学会学习”,也包括共情和价值认同[2]。儿童问学课堂正是由这四个要素支撑的,他们特别赋予“活动”重要位置,并概括出其游戏性、探索性、合作性、开放性等特点。
儿童问学课堂以儿童最关心的问题为教学起点。儿童带着问题进课堂,教师通过“问学单”将儿童课前普遍关心的问题作为教学的核心问题,围绕核心问题来设计教学活动,在教学活动中引入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关键概念或核心知识,并把核心问题转化为驱动性问题,通过真实的学习情境,吸引并推动学生自主学习,在真实的学习实践活动中不断地走向知识的核心。从某种程度上说,驱动性问题有效连接了核心知识与学习活动,儿童在主动的学习过程中,不断产生新问题,同时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呈现自己的学习成果,在系列学习活动中提升素养。因此,儿童问学课堂的项目化实施还要有成果意识,这种成果意识决定了项目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做”,项目化的“活动”,就是“做中学”。在儿童问学课堂中,“做”因“问”而生,因“学”而成,“做”主要是探究性的思维活动,“做”就是在真实情境中的问题解决与创新。参照“学以成人”的说法,这就是一种“做”以成人。
三、儿童问学课堂是结构性的
项目化已经涉及结构,这里专门讨论结构,是因为儿童问学课堂中的“问”不同于一般的“问”,而是将“问”置于结构之中。体现结构性甚至结构美,成为儿童问学课堂的重要表征。最高阶的学习,不是获得多么丰富的知识,而是在知识的传递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儿童问学课堂以向四面八方打开的“问”串起学生的“学”,又在“学”的过程中持续地催生新的“问”。儿童问学课堂不以知识学习的完成为重点,而是更加追求在持续的“问”中将思维向各个方向打开,向多个学习共同体打开,在问中更好地“学”。《培格曼最新国际教师百科全书》谈到课堂结构时引用了这样的观点:“结构因素的共同点是他们给学校教学过程中的那个部分定下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度。”这就告诉我们观察课堂结构有两个维度,时间的和空间的。时间维度一直是得到较多的关注的。赫尔巴特将教学过程分成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四个阶段,此后,关于教学过程的讨论,大抵以这个表述为底本。项目化学习的四个要素有“过程”的脉动,又强调要素的相互融合和动态生成。潘文彬老师的团队在实操时将“问”贯注于“五学”(自主探学、分享互学、优化练学、总结理学、多元评学)之中,也是从时间维度建构了“问学”的结构。难能可贵的是向学课堂从空间维度看“问学”,带给我们更多的欣喜。
第一,问学形成交叉型网格式的信息传输系统。传统教学是老师与学生单向的信息传递,有所进步的也只是双向的多向的信息传递;而儿童问学,可以“问”自己,“问”伙伴,“问”师长,“问”教材,“问”网络……养成随时随地请教别人的习惯,让儿童认识到,不管是谁,只要能给你启发,给你帮助,都可以成为你的老师,都应该向他请教,这就构成了立体的多维的信息交流系统,课堂就成了信息畅通的学习场。
第二,“问学”以小组合作为重要的组织策略。教学组合的小型化、多层次,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儿童问学课堂以学生自己的生活为基础,打通人与人交流合作的通道,打通课堂与生活的联系,让学习也成为学生的日常生活。在这种学习过程中,学生学会了有效配合,他们会交流,会积极主动地发言,清楚明白地表达观点,倾听别人的观点;会互帮互学,互相促进;会评价,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敢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和伙伴的变化与进步。独立学习与小组学习相辅相成,在集体性教学体制下个性化学习得到更多关照,而社会情感能力也得到更好的培养。
第三,问学之问在学生,也在老师,还在家长。恰如学校出版的《学习就这样发生了——一百个问学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有学生,也有老师和家长,当学生写下属于自己的问学故事时,他们记录的不只是问学体验,还有对问学过程的元认知;当老师们怀揣热爱,整理澎湃的问学思潮时,他们写下的不只是问学反思,更有问学智慧;当家长们主动配合,共护坚固的问学阵地时,儿童问学的时间和空间都在进一步生长,儿童的生命也在生长。这些散落在字里行间的十年问学记忆,虽然朴素,但让我们看到儿童问学课堂的开放性、生成性,特别是家长兴趣盎然的“卷入”,大大拓展了课堂的空间。
多年来,我力主“课堂向四面八方打开”,潘文彬无疑是知音,开放的课堂才是生气勃勃的,这种结构的张力,让我们感受到创造的力量。当然,恰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谬的事情。”[3]从时空整合的角度看儿童问学课堂的结构,让学生站在中央,多元主体对课堂的共建共享,在动态生成中创造积极可能性,等等,许多的意蕴是值得我们回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