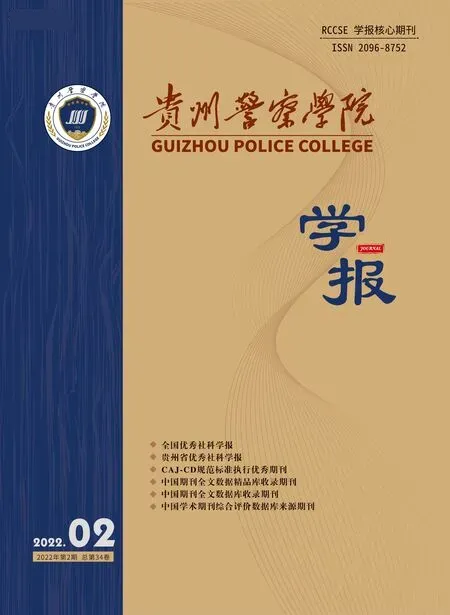机动车侵权特殊规则的适用现状与理论回归
赵银仁(河海大学,江苏 南京 211100)
一、问题之所在
200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施行,结合2006 年施行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在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领域,我国初步构建了损害赔偿与受害者救济的特殊立法体系。其后,该体系为《侵权责任法》《民法典》所继受。《道交法》第76 条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规定了特殊的归责原则,即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适用绝对的无过错责任,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部分,在机动车之间适用过错责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适用特殊的无过错责任(以下简称“特殊规则”)。由于特殊规则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举证责任等做出了特殊规定,而且事故发生后通常由交强险先行赔付,因此,能否适用特殊规则成为受害者获赔的关键。
现行立法和司法以是否构成交通事故作为特殊规则适用的标准,《道交法》第119 条规定在损害后果系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时,认定构成交通事故,即对交通事故采用了较为宽泛的机动车在道路上的二重判断标准,这种宽泛的认定带来了法律适用上的困境和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过重的赔付责任。
此外,如果从《道交法》立法原理之危险责任理论以及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对于机动车损害赔偿特殊规则的适用标准应该有所限制。从危险责任的角度来看,现有的交通事故标准缺乏危险责任的危险性要件,并且在判断交通事故时,实务中又进一步扩大了道路标准以及非道路情况下参照适用的范围。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德日两国的立法对我国《道交法》的立法具有深远影响,并且两国的机动车损害赔偿与受害者救济体系同我国一样,都采用了无过错责任结合交强险赔付的模式。但是,德日两国在立法中,除了交通事故要件外,还增加了危险性要件,要求损害须因机动车运行而引起。因此,从危险责任理论和比较法的角度来说,有必要对我国现行机动车侵权特殊规则的适用标准做进一步的梳理。
二、特殊规则适用的现状
《道交法》第76 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可以适用特殊规则。《道交法》第119条对交通事故做出了宽泛的规定,即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该条对交通事故采用“机动车+道路”的二重认定标准。基于该标准,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的事故基本上都属于交通事故的范畴。
(一)机动车的认定标准
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是否属于机动车这一要件通常不是争议的焦点。对于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因为欠缺机动车的参与,不适用机动车特殊规则,作为一般侵权案件处理。例如,在一起自行车与电动自行车相撞事故中,法院认为本案为两个非机动车发生的碰撞,因此不适用特殊规则而适用一般侵权的规定。①参见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2009)睢民初字第28 号民事判决。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如果对机动车要件产生了争议,除了依《道交法》第119 条进行判断外,通常委托鉴定机构基于相应的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现行有效的是GB7258-2017,此前的2012、2004、1997 年的版本已经被替代和废止)来认定。在实务中,争议焦点是电动自行车、燃油助力车等车辆是否是机动车,是否应适用机动车侵权特殊规则。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在我国被大量制造和使用,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不需要行为人获得驾驶证,导致事故频发,而大部分电动自行车使用人并未购买强制责任保险,事故发生后相对人很难获得有效的保险赔偿。根据我国原来的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目前在道路上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大多数不符合国家标准,属于超标非机动车,应纳入机动车范畴。2018 年我国出台电动自行车新的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较之旧标准,新标准提高了机动车认定的门槛,提高了车身重量和车速的标准,但是仍然有大量超标电动车被销售和使用,而且电动自行车不需要驾驶证、不强制购买责任保险的现状没有任何改变,对事故的减少、受害者的救济并未起到任何积极作用。
在审判实务中,对涉及非机动车案件的处理有两种模式。一是如前述自行车与电动自行车相撞事故案中,电动自行车的性质(是否为机动车)未成为案件争议焦点,法院将电动自行车作为非机动车处理。二是将电动自行车的性质交给鉴定部门进行判断。例如,在一起燃油助力车交通事故案中,上诉人诉称自己的燃油助力车系从正规销售渠道购买并领取合格证明,取得相关牌照,日常也是按照非机动车标准使用,因此,一审通过鉴定认定该车为两轮摩托车(机动车)的判断错误。二审法院认为,本案车辆属于机动车已经经过专业机构鉴定,当事人根据车辆购买时的性质和自己认知来判断车辆的属性没有合理性。①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455 号民事判决。但是,在电动自行车被判定为机动车时,如何适用法律并不完全一致。大部分案件中法院支持应该适用特殊规则,但是也有法院坚持适用一般侵权责任的规定。例如,在一起电动自行车与自行车相撞事故中,虽然被告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经鉴定为机动车,但是,法院认为案件应该适用一般侵权责任而不适用特殊侵权归责。②参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0)杨民一(民)初字第2746 号民事判决。本案二审法院虽然认可案涉超标电动自行车应该适用机动车的相关管理规定,但是维持了一审判决对案件适用一般侵权责任的做法。二审法院认为,有关案涉电动自行车超过国家标准的责任,购买人可向相关责任人追责。③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57 号民事判决。对同属于机动车范畴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法院在审理时却出现了明显与现行法规定相背离的法律适用模式。
笔者认为,超标非机动车问题不仅仅是审判实务的问题,也是非机动车行政管理、交通管理的问题。该问题需要相关团体和国家机关协作,从生产、销售、使用三个环节严格规范管理。实务中,对超标车辆不适用机动车相关规定的做法不仅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也会破坏现有的机动车损害赔偿法的体系。对于超标车辆,要严格适用机动车的相关规定,需购买强制责任保险并适用损害赔偿特殊规则。同时,可以试点推进电动自行车、燃油助力车等非机动车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避免事故发生后受害者无法获得救济。
(二)道路的认定标准
交通事故的认定要求事故须发生在道路上,《道交法》第119 条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道交法》第77 条和《交强险条例》第44 条规定,车辆在道路以外地方发生事故时,参照相关规定处理。根据以上规定,在道路上发生的事故适用《道交法》,而在道路以外发生的事故,则参照《道交法》和《交强险条例》处理。虽然规定了参照相关规定处理,但在道路以外发生的事故是否应该和机动车事故一样处理、是否应该适用强制责任保险的赔偿,这一点仍有争议。
在处理非道路上发生的事故时,对法律适用和交强险赔付问题各方争议颇大。保险公司通常主张,案涉事故为非道路上发生的事故,不适用强制责任险。但是,从救济受害者等角度出发,这种抗辩很少被法院采纳。例如,在一起三轮摩托车在工厂内部道路上与货车相撞案件中,交警基于事故发生的地点,做出了案涉事故为非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保险公司据此主张本案不构成交通事故,不应适用机动车侵权特殊规则,且不应由交强险赔付。然而,法院认为《道交法》第77 条和《交强险条例》第44 条对此类案件做出了参照适用的规定,因此,本案虽然系非道路上发生的事故,但仍可参照适用机动车侵权特殊侵权规则,并由交强险予以赔付。④参见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2)同民初字第530 号民事判决。
笔者认为,《道交法》不仅是关于交通事故的民事损害赔偿法,更是关于交通行为管理的行政管理法。从民事损害赔偿来看,机动车侵权特殊规则和交强险的赔付应该限定在道路范围内。因为,通常情况下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其危险性会高于在非道路上行驶时的危险。特别是在汽车修理厂、学校、工厂内部等地区,往往对车速和行驶路线有严格的限制,从危险责任角度来看其危险性较低,没有适用特殊规则的前提和必要。从立法角度来看,如果不加区分,则现行立法就没有区分道路与非道路的必要。从行政管理角度来说,虽然对于非道路上发生的事故不作为交通事故来处理,但是对于违章行为仍然可以参照适用相关规定来管理。
(三)机动车停驶时损害案件的认定现状
对于机动车停驶时发生损害的案件,司法实务中多数严格适用前述交通事故标准认定属于交通事故。而对于交通事故的认定,人民法院基本上认可交警的事故认定。部分情况下,即使交警没有做出交通事故的认定,或者做出不属于交通事故的认定,但是人民法院仍然倾向于宽泛适用“机动车+道路”的二重标准。例如,在一起停驶货车轮胎爆炸案中,货车虽处于停驶状态,但是轮胎突然爆炸,炸伤了路过的原告。本案案发时由于没有报警,因此,没有做出交通事故的认定。但是,人民法院认为机动车疏于养护和检查且事故发生在道路上,认可案涉事故属于交通事故并适用特殊规则。①参见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2013)浦民初字第1879 号民事判决。实务中,对于未发生在道路上(例如在修理厂、停车场等)的案件,出现了扩张认定属于交通事故,进而适用特殊规则的情形。例如,在一起汽车修理店内轮胎爆炸案中,货车轮胎在修理店内维修时爆炸致人死亡。人民法院认为,交通事故不仅包括在道路上的事故,也包括为了实现交通之目的而从起点到终点的完整过程。车辆维修系运输过程的一部分,在维修时发生的事故也属于交通事故,应该适用特殊规则。②参见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4)鄂青山民一初字第00303 号民事判决。这种认定不是对非道路上的事故参照道路事故处理,而是扩张道路的认定范围,进而极大扩张了特殊规则和交强险的适用范围。
近年来也出现了对交通事故的范围进行限缩的案例。例如,在另一起机动车在修理厂维修时轮胎爆炸案中,人民法院提出了不同的审判观点。该案中,货车轮胎因为损坏被卸下维修,在维修时爆炸致人死亡,对于该案是否属于交通事故产生了激烈争论。最终,人民法院再审认定,本案车轮与汽车分离时间已久不能被视为机动车。此外,法院认为不能无限扩大对道路的认定,否定了修理厂作为道路的认定。因此人民法院虽采用“机动车+道路”的标准,但是对相关标准作出了限缩解释和认定,最终否认了特殊规则的适用。③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民再提字第00140 号民事判决。现行立法和实务中采用“机动车+道路”的二重标准来认定交通事故,进而判断机动车侵权特殊规则和交强险的适用范围。实务中对机动车和道路的判断争议不多,但在司法适用时仍然存在着几个问题:一是超标非机动车在鉴定为机动车后仍然适用一般侵权责任;二是超标非机动车的损害无责任保险兜底,即使适用特殊规则,判决结果也难以兑现和执行;三是道路与非道路上发生的事故都宽泛适用特殊规则。笔者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实务中对相关法律的解释、理解和适用标准的不统一,对机动车损害赔偿特殊规则的产生和原理没有清晰的认识。
三、机动车侵权特殊规则适用的理论回归
(一)特殊规则适用的法理依据
从《道交法》的立法理由来看,立法者认为即使驾驶员尽到了最大的注意义务,也不能完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因此,对这种具有高度危险性的高速工具应该适用无过错责任。[1]因此,《道交法》第76 条承继了《民法通则》第123 条关于无过错责任的规定。此外,在特殊规则适用时结合交强险的适用,可以转嫁责任、分摊风险、救济受害者,符合风险社会责任理论。[2]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德日两国对机动车损害赔偿的立法采用相同的观点。德国在1909年的《道路交通法》中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其原理在于,机动车在运行时所具有的高度危险性,即使尽到最大注意义务也难以避免,换言之损害并非因过错而系因为危险而引起。[3]日本的《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在立法时也认为,机动车具有体型大,使用频繁、速度快等危险性,①参见1955 年6 月2 日日本参议院运输委员会会议录12 号,第1 页。客观来说机动车事故无法完全避免,因此基于危险性应适用无过错责任。②参见1955 年6 月13 日日本参议院运输委员会公听会会议录1 号,第1-2 页。以上理由与我国的立法理由一致,可见我国《道交法》第76 条确立机动车侵权特殊规则的立法时充分借鉴了德日两国的立法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德日两国对机动车损害赔偿案件适用危险责任,但是其适用范围严格限定在因具体危险而引起的损害,对于其他损害仍然坚持适用一般侵权责任规则。两国在立法上都规定,适用特殊侵权规则的前提在于事故须发生在机动车运行时,或限定在因机动车运行而引起的损害,对于非因此而引起的事故不适用机动车损害赔偿特殊规则。我国虽然采用了类似德日两国的特殊规则,但是,立法上并未以运行要件来限缩危险责任的适用范围,仅依靠交通事故要件显然难以彰显事故所具有的危险性。实务中,对于机动车非运行(典型的如停驶)时发生的货物坠落、轮胎爆炸、被非机动车撞击、车载货物爆炸等事故,如果根据“机动车+道路”的二重标准来认定的话,可以认定为交通事故。但是,这些情况下发生的事故要么不具有危险性,要么系轮胎爆炸、货物爆炸等非因为机动车本身所具有的高速度的危险引起。
(二)立法与司法的理论回归
综上,从《道交法》的立法理由、危险责任的基本理论以及比较法角度来看,我国对机动车特殊侵权规则的适用总体来说较宽泛,缺乏危险性要件,使得立法和司法实务与危险责任理论背离。尤其对大量停驶时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审判中或是机械地适用交通事故标准,或是将道路要件扩张到所有的事故发生领域。从事故形态来看,此类事故往往不具有危险性(例如,因机动车违停而阻挡视线发生的事故被认定为交通事故的案件在实务中屡见不鲜),或者其危险性并非机动车所具有的通常意义上的危险(即高速度的危险),而是因为停驶时货物坠落、轮胎爆炸、车内物品爆炸等危险引起。笔者认为,对于不具有危险性或虽具有危险性但并非机动车所具有的典型危险的案件,不应适用机动车侵权特殊规则,而应分别适用一般侵权规则和具体危险类型所对应的特殊侵权规则(如易燃易爆类危险责任规则)。否则不仅容易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和对侵权责任法体系的破坏,而且也增加了被告和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有失公允。
从实务看,对于不具有危险性的停驶状态下发生的事故的定性和特殊规则是否应该适用产生了较多争议。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立法中缺乏机动车典型的高速危险性要件。因为立法中对特殊规则的适用并不需要对机动车速度要件限制,因此在最极端的速度为零(停驶)状态下,是否应该继续适用特殊规则产生了争议。虽然在实务中出现了通过对机动车和道路要件的限缩解释来限制特殊规则适用的情形,但这种限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全面地解决立法中危险性缺失的问题。更令人遗憾的是,现行立法以及新近颁布施行的《民法典》未能从体系上全面解决机动车侵权特殊规则适用范围过宽、危险性要件缺失的问题,仍然采用转致性立法技术,即适用《道交法》的相关规定。
笔者认为,德日两国早于我国很多年颁布施行机动车损害赔偿领域的特别法,经过多年实践检验较好地解决了受害者救济和特殊规则合理适用问题,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如前所述,两国在立法中除了规定机动车造成损害以外,还将事故的发生状态和发生原因限定在机动车运行时,进而将不具有危险性的机动车停驶状态下的事故、非因机动车运行而引起的事故(如车内物品爆炸事故、机动车触碰高压电线引起的事故等)排除在机动车侵权特殊规则的适用范围外。这种限定不仅符合危险责任的理论要求,而且符合特殊规则的立法原理,可以有效避免在机动车损害赔偿领域出现的特殊规则适用范围过宽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在《道交法》第76 条中,将特殊规则的适用严格限定为机动车因运行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从而限制特殊规则的适用范围,实现特殊规则适用的理论回归。
四、结语
我国《道交法》第76 条施行近20 年以来,有效解决了多年来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领域立法缺失、受害者救济困难、责任保险缺乏强制性的困境。特别是改变了既往《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不合理的过错责任原则,实现了对非机动车和行人的特殊侵权救济规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道交法》对机动车损害赔偿特殊侵权规则的适用范围做出了宽泛的界定,审判实务中出现了进一步扩大对非道路上发生事故参照适用道路上事故,或者直接对道路做扩大解释的情形。以上立法和司法的现状致使目前我国实务中几乎与机动车有关的所有事故的损害赔偿都被纳入到机动车侵权特殊规则的适用领域。这样的立法和司法现状不仅有违危险责任理论,破坏了侵权责任法的既有体系,也使保险公司和机动车方承担了过重的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应进一步重视法律内在的逻辑和法体系的稳定性,为此一方面应该展开对《民法典》的解释和完善;另一方面也要对既有的特别法进行梳理,使之更好地融入《民法典》的体系中。对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和《道交法》进行梳理和完善,不仅可以解决现有立法和司法中的焦点问题,也可以有效应对无人驾驶等科技进步带来的新型法律问题,使得立法、司法、法律解释更加科学、合理、稳定和合乎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