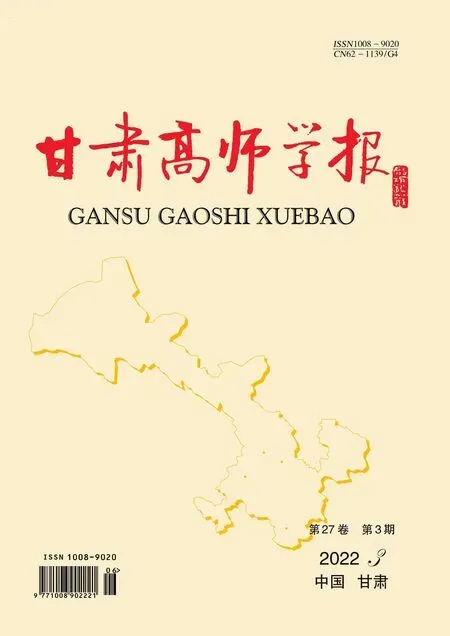基于敦煌出土文献的西北方音研究述评
尹 雯
(1.兰州工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 730050;2.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3.南方科技大学 人文科学中心,广东深圳 518000)
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因发现大批唐代前后的文献而举世闻名。这批文献既有失传已久的古代字书、《切韵》系韵书、音义类写本残卷等,也有古书传抄本、敦煌俗文学作品、佛经、医书、算经、日历以及各类社会经济文书、军事文书写卷,还有藏文、粟特文、突厥文等其他文字对音材料。因多为手写本,抄撰者和翻译者在传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方言痕迹。它真实记录了唐五代时期语言文化的方方面面,是许多传世文献所不能比拟的。张涌泉先生表示:“敦煌语言文学研究与敦煌文献整理,是敦煌学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几个领域。”[1]从罗常培先生用敦煌文献来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开始,学者们认识到敦煌文献的语言学价值。王新华在其博士论文《唐五代敦煌语音研究》[2]中用图表形式对照了周大璞、张金泉、周祖谟、罗常培四位先生整理的韵部,但没有对基于敦煌出土文献的西北方音研究进行细致述评。
根据《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1909—1984)》[3]《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续编》[4]《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5]和网上学术资源刊布显示,涉及敦煌文献的汉语方言研究论著有40 余篇(部),多数为语音研究。本文进一步梳理与敦煌出土文献相关的西北汉语方言语音研究成果,以期能深入挖掘其语言学价值。
一、基于敦煌对音材料的方音研究
敦煌文献中有不少吐蕃人学汉语用的经卷,译者方言能代表唐五代时期流行于西北的一部分方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继钢和泰的《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1923)、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1931)之后,罗常培先生利用汉梵对音来拟测汉字古音,著《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6],开启了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区域方音史的学术新风尚。罗先生将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大乘中宗见解》残卷、藏文译音《阿弥陀经》残卷、藏文译音《金刚经》残卷、《开蒙要训》及《唐蕃会盟碑》拓本对音材料与《切韵》音系对比,系统拟测了敦煌对音材料所代表的方言音系。罗先生还将山西的兴县、文水,陕西的西安、三水(今旬邑县),甘肃的兰州、平凉六地方言与拟测的唐五代西北方音进行对比。
沿着罗常培先生开启的研究之路,一代代学者前赴后继。日本语言学家高田时雄在其《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1988)[7]中以汉语音韵史研究方法为纵轴,以基于敦煌文献的实证为横轴展开,进一步补充和修订罗常培先生《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汉藏对音材料,并尝试复原九、十世纪中古时期的敦煌及河西方言面貌。
储泰松先生在《梵汉对音概说》(1995)[8]中分析了敦煌对音文献梵文中的辅音,认为译主既结合方音来译经,也兼顾了流行于当地的通语,这些梵汉对音材料反映的是北方方言。在《唐代音义所见方音考》(2004)[9]一文中关注了敦煌出土文献里的玄应《众经音义》、窥基《妙法莲花经音义》、云公《涅槃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等唐代佛典、史书音义中的方音现象。这两篇文章涉及文献较多,都基于对译者方音的研究,让我们了解了唐代方言分区的主要轮廓、语音差别、北方方言特点以及南北方音的差异,认为中唐以后南北方音的差别加大,而北方内部的方音差异缩小。
我国境内所出土的粟特语文献年代最早的是斯坦因在敦煌得到的一些信件。聂鸿音的文章《粟特语对音资料和唐代汉语西北方言》(2006)[10]将粟特语对音材料结合同时代的波斯语—汉语对音进行音韵学分析,认为这些资料可以用作研究汉语西北方言史和晋语史的参考。他的另一篇文章《汉语西北方言泥来混读的早期资料》(2011)提到:“在敦煌藏经洞所出的汉字注音本《开蒙要训》里也可以见到泥来混读的现象,溺注音为历、罐注音为农。这里泥来混读不限于洪音,不过看不出是读n-还是l-。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P.3861 号佛经写卷中的咒语把梵文音节nam音译为拦或梨难,这似乎表明当地方言是把泥来二母混读成了n-。”[11]
此外,博士论文有史淑琴的《敦煌汉藏对音材料音系研究》(2008)[12],通过整理分析21 种敦煌出土的汉藏材料,对其所反映的语音系统及藏语的特点作了细致的研究。
总体来看,学者们已经意识到敦煌对音材料里有大量方言痕迹,方言范围不外乎西北方言。在研究过程中都结合了汉语语音史相关研究成果,尝试在文献中探索西北方言里n、l 不分等情况。这些研究中使用的方言例证不多,且大都不是一手田园调查材料,如日本学者论对音材料里的河西方言,恐有偏差。
二、基于敦煌韵书、字书以及经部文献的西北方音研究
敦煌本《文选音》包括P.2833 号与S.8521 号两个写卷。周祖谟先生撰文《论<文选音>残卷之作者及其方音》(1966)[13],讨论了西北方音问题;张金泉先生关注到了“重字反切”[14];韩丹、许建平等学者沿此路深入讨论“切上字重”“切下字重”[15],认为《文选音》具有重要的音韵文献价值。
龙晦先生通过细致校对罗常培先生所未见之材料: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卜天寿《论语》,进一步分析144 对互注字,发现只有15 对字有音变,认为八世纪西北语音与内地基本一致,晚期的变化比较大。[16]
《字宝》是唐五代时期民间流传的一种字书,全书总计3738 个字,按四声收入434 条常用词语,并注以反切或汉字直音。刘燕文的《从敦煌写本<字宝>的字音看晚唐五代西北方音》(1989)[17]一文对《字宝》中的反切和直音进行分析研究,探求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特点。张金泉在《敦煌遗书<字宝>与唐口语词》(1997)[18]一文中进一步将《字宝》注音及其被注字与《广韵》音对比,找到了一些罗常培先生所归纳的止遇二摄互注等唐西北方音。
许建平先生在《唐写本<礼记音>考》(1991)[19]里指出,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元韵转入寒类,与寒、桓、删、山、先、仙六韵通押,入收声消变,[y][u]分化。
黄易青先生《<守温韵学残卷>反映的晚唐等韵学及西北方音》(2007)亦从出土韵书入手,认为“此卷还反映晚唐西北方音,其中有确凿材料反映晚唐轻唇已在轻唇十韵中分化完毕,正齿音二三等相混,正齿音浊塞擦音床与浊擦音禅相混,洪转为细与浊塞擦转为浊擦有关;觉、药合流,职德与陌麦昔锡相近”[20]。
徐朝东、唐浩在《敦煌韵书P.2014、2015 异常反切考察》(2015)[21]一文中利用敦煌韵书P.2014、P.2015 的不同与其他韵书的异常反切,推求唐五代时期西北方音,发现全浊声母清化、知二与庄组相混、同等韵合并,佳韵部分喉牙音字归入歌麻韵,元归入仙先韵、影喻疑三母相混、仙先合并、入声尾消失、浊上已变去等,并积极求证于同时期其他语言材料。
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采用分析互注字、观察反切、与《广韵》对比等方法,总结其中的语音变化规律。学者们还积极求证于同时期其他语言材料,将其放入汉语史中作进一步研究。
三、基于敦煌诗歌、俗文学中的方音研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邵荣芬先生以《敦煌变文集》《敦煌曲子词集》等材料中的别字异文为观察对象,作《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1963)[22]一文,为唐五代西北方音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后一些学者寻此路关注敦煌俗文学中的各种语言现象。张金泉在《敦煌曲子词用韵考》(1981)[23]中认为,敦煌曲子词纯朴自然的语言,保存着古代西北口语。他对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所收录曲子词的韵脚进行了归纳整理,得出18 个韵部。孙其芳的文章《敦煌词中的方音示例》(1982)[24]认为,敦煌词表现了一些西北方音,特别是甘肃方音,主要体现在一些同音致误的字词中,抄录者在抄录时,随声致误,如《天仙子》中“如”作“无”、《献忠心》中“仙”作“香”等,文中结合甘肃方言作了简要分析。汪泛舟在其文章《敦煌曲子词方音习语及其他》(1987)[25]中认为,敦煌曲子词与唐五代边地一些方言词不无关系,这从许多词篇的押韵中可以看出,如《望江南》《定风波》等,他还提到敦煌词出现了四声通叶的词以及双叠词、慢词。陶贞安的学位论文《敦煌歌辞用韵研究》(2004)[26],以任半塘先生的《敦煌歌词总编》为基础材料,进一步分析唐五代北方语音。霍文艳的学位论文《敦煌曲子词用韵研究》(2008)[27]通过研究法藏、英藏、俄藏以及部分甘肃藏敦煌文献中917 首敦煌曲子词用韵状况,进一步揭示元入寒先、“浊上变去”、“入派三声”等北方通语的语音演变情况,关注-m、-n、-η 三韵尾相混等唐五代西北方音特征。徐朝东在《敦煌韵文中阴入相混现象之考察》(2011)[28]里罗列了敦煌曲子词中4 例、变文中2 例阴入混押的材料,认为入声字同阴声字合押在敦煌曲子词与变文中并不多见,而敦煌诗歌中则无一例此现象。曲子词和变文中的阴入混押,体现了唐五代时期西北尤其是河西地区的方言里入声韵尾已开始消变。
学者们以项楚先生校注的《王梵志诗校注》、张锡厚先生的《王梵志诗校辑》和徐俊纂辑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为语料,分析敦煌诗的押韵情况,开展语言学研究。都兴宙的文章《王梵志诗用韵考》(1986)[29],通过对王梵志诗全部押韵字的归纳排比,得出25 个韵部,认为王梵志诗韵部所反映的初唐时期北方语音既与《广韵》音系有所区别,与晚唐五代变文、曲子词所反映出的北方实际语音又有不同。苗昱在《王梵志诗、寒山诗(附拾得诗)用韵比较研究》(2004)[30]中认为,王梵志诗中出现了效摄和流摄、效摄和蟹摄、果摄和蟹摄、止摄和假摄通押等情况,-m 尾向-n 的靠拢已经露出端倪;江部与东钟部近,与阳唐部远。丁治民、赵金文的文章《敦煌诗中的别字异文研究——论五代西北方音的精见二系合流》(2009)[31],补充映证了罗常培先生所说的精、见二系自五代起开始合流。
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韵,方法多为对韵脚的系联、整理、分析,也有学者关注声与调。黎新第在系列论文中讨论了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入声韵尾、个别声母以及异等韵母相混的情况,如《入收声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应已趋向消失——敦煌写本愿文与诗集残卷之别字异文所见》(2012)[32]。其《对几组声母在五代西北方音中表现的再探讨》(2015)[33]一文,分析了精、庄、知、章、见五组声母在五代西北方音中的分合与拟音,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新的支持与补充修正。
徐朝东的文章《敦煌世俗文书中唇音问题之考察》(2018)[34],认为轻重唇音在隋唐五代的音义材料里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切韵》系列韵书里轻重唇声母切上字仍有相混;另一种是实际口语中,轻唇音和重唇音分化已经完成,明微分化的速度稍慢,全浊奉母开始清化,非敷奉合流已成为河西方音重要的语音特征。
四、基于敦煌变文、愿文的方音研究
变文是唐五代民间流行的一种说唱文学,其形式多种多样,有“讲经”“论议”“转变”“说话”等。敦煌变文更接近当时口语,是中古汉语研究中的代表性语料。其中的别字异文和韵文资料极为丰富,具有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价值。周祖谟先生的文章《敦煌变文与唐代语音》[35]罗列了52 种讲唱韵语,辨析其韵类,归纳出二十三个韵摄,并借用《四声等子》十六摄的名目按阴阳入三声的次第,将各摄摘要举例排出,认为中唐以后北方的音韵系统已经不同于《切韵》,变文的押韵部类代表北方实际语音,现在北方普通话的韵母系统就是在这二十三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周大璞先生的《<敦煌变文>用韵考》(1979)[36]系列论文也对二十三个韵部作了分析,并与《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的二十三摄五十五韵和《汉语发展史》的晚唐韵部二十七韵作比较,分析了“邻韵通押”的情况,最后谈了入声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逐渐消失,浊上已经开始变去。都兴宙先生的文章《敦煌变文韵部研究》(1985)[37]得二十四部,并与《广韵》进行对比,认为虽然有入声字混用现象,但不能说明入声字混而为一甚至消失。变文所代表的韵部,不仅仅是西北或某一地区的方言韵部。杨同军先生的学位论文《敦煌变文的语音系统》(2003)[38]从声母、韵部、声调三个方面归纳了敦煌变文的语音系统,探讨其特点和性质,认为敦煌变文的语音系统与《切韵》音系已大有不同,如轻重唇音分化、全浊声母消失、韵部系统大大简化、入声韵尾弱化、浊上变去已经形成等。
敦煌愿文是敦煌文献、石窟题记和绢书、幡缯中的请愿文章,它数量大,内容广,材料丰富,记录了唐五代时期西北地区的语言面貌。李海玲的学位论文《敦煌愿文别字异文材料所反映的语音问题》(2013)[39]以《敦煌愿文集》为底本,以同音替代为选取标准,对愿文中的别字异文材料进行分析,并与同时期其他敦煌文献、现代西北方言比较,发现了一些语音现象,如轻唇音分化、非敷奉合流、知章组合流、精组见系相混、云以代用、浊音清化、止摄不分、-n 与-m 尾开始相混、鼻音韵尾有消变迹象、全浊上归去、入声开始消失等。
以上学者均将敦煌变文、愿文看成统一整体去研究其中的语音特点。但是,这一部分的材料多为口耳相授所得,讲经人很可能来自中原等佛教传播较为广泛的地区,如当时的长安、洛阳等地,抄经人的籍贯也各异。如此看来变文、愿文里的方音会因讲经人、抄经人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尝试区别对待这些材料。
五、结合敦煌文献的现代敦煌汉语方言语音研究
许多学者在研读敦煌文献的过程中,将其与现代方音联系起来。储泰松在其著作《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2005)[40]中将敦煌文献与现代关中方言对应。这些研究绝大多数是借用现代方言学者的研究成果。语言学家李蓝先生则用实地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敦煌方言语音资料,结合敦煌文献进一步对罗常培先生的唐五代西北方音研究成果展开对比研究。他在《敦煌方言与唐五代西北方音》(2014)[41]一文中认为罗先生的研究虽然运用了现代方言,大致建立了现代方言与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对比关系,但是他手中的甘肃汉语方言的调查材料非常有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用到敦煌文献嫡传地——现代敦煌方言的调查材料。因此,李蓝先生继续沿用罗先生的研究方法,将亲赴敦煌调查所得的现代敦煌方音乃至甘肃全省的方言,与敦煌文献、《切韵》音系联系在一起,细致构建对比关系。他认为,虽然现代敦煌方言并非唐五代时期敦煌方言的嫡传后裔,但其来源不外乎清中叶甘肃56 州县移民带来的甘肃方言,总体来看仍与甘肃及其他西北方音一致,属同一方言区域,所以仍可用比照研究《切韵》音系的方法,把敦煌方言和甘肃省境内的其他汉语方言视为一个整体,将其看作是敦煌文献的基础方言,以此为基础来研究现代甘肃方言与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对应关系。
六、结论
基于敦煌出土文献的西北方音研究,将中古汉语语音研究、西北汉语方音历史演变研究、现代西北方言语音研究有机统一在一起,总体呈现以下特点:
1.敦煌出土文献蕴藏着丰富的西北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
作为唐代陆上丝绸之路重镇的敦煌,在当时国际交流频繁、民族融合深入。敦煌出土文献里的对音材料集合着藏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等多民族语言文字,这些语言和汉语间的译音也随之兴起。从本文介绍的这些研究成果来看,译者多为北方人,且兼顾了当时的通用语,所以北方方言是其语言翻译基础。敦煌诗歌、曲子词、变文等中大量的别字异文为西北方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所以,敦煌出土文献体现了西北方音已成为学界共识。这些基于敦煌出土文献的西北方音研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切韵》、观察唐五代“官话”以及梳理中古汉语语音发展史,亦可用于研究藏语等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史。
2.敦煌出土文献与现代西北方言,尤其是甘肃汉语方言之间能互证互通
周祖谟先生认为研究现代北方话与普通话发展史应从敦煌出土文献时期的语音状况研究起。罗常培、李蓝、储泰松、王新华等学者都尝试将敦煌出土文献与现代西北方言,尤其是甘肃方言联系起来进行对比研究,李蓝先生认为疑母读同见母这一条是甘肃汉语方言确为敦煌文献、唐五代西北方音基础方言的铁证。还有一些学者在敦煌出土文献中寻找西北汉语方言词汇的踪迹。虽然五代后敦煌等西北地区丧失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出入口功能,从而导致历史文献的断层和居住人口断层,但这并不影响现代西北方言可以为敦煌文献的整理提供互证校勘研究。李正宇文章《敦煌方音止遇二摄混同及其校勘学意义》(1986)[42]运用敦煌方音止遇混同的规律校勘敦煌遗书,举50 例求本字,体现敦煌方音的校勘学价值。王耀东、敏春芳的《敦煌文献的方言学价值》(2011)[43]一文举例说明可以利用敦煌文献拟测唐五代西北方言,研究现代西北地区的方言,反过来看还能解决同期传世文献中有关方言的一些难题。
3.敦煌出土文献有效助推汉语语音史研究,尤其是西北方音历史演变研究
基于敦煌出土文献的汉语语音史研究、西北方音研究,总体上还是沿着罗常培先生开辟的研究之路在走。研究方法大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观察敦煌出土文献里的押韵、译文、别字异文等,寻找有关语音的文献例证,并进一步深入到语音史层面展开对比研究;另一种是用现代西北方言、已有的语音史研究成果去印证解释敦煌出土文献里出现的语音现象,对文献进行校勘学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唐代语音有二十三韵部,已经开始了从四声八等到四呼的简化过程;已有轻唇音,出现浊音清化现象,逐渐区分送气与不送气音,全古浊声母仄声送气,泥来相混,疑母读同见母;阴入混押,入声韵尾开始脱落,-n,-m 尾开始相混;梗摄与齐韵、宕摄与果摄有合并现象,鱼止通转、止蟹二摄韵母合流等等。敦煌出土文献印证了声调方面浊上归去的重要规律,这一时期入声在西北方言里逐渐消失并开始分派四声。
基于敦煌出土文献的西北方音研究仍有许多值得继续研究的地方,如敦煌文献中的别字异文非常多,尚未整理穷尽;罗常培先生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中诸多观点需要更多的敦煌文献材料例证与现代汉语方言例证;在汉语语音史研究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探索,如西北方音鼻韵尾的演变情况、韵母混押的规律、精见二系合流情况、泥来混读、来母字为什么会译为d-等等。还可以进行基于敦煌对音材料的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西北方音研究亦可用于对敦煌出土文献的校勘,上文所述的“互证”研究当有可为。张涌泉先生认为,今后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以及敦煌文献的整理,应从“资料更全、研究更精、图版更清晰”三个方面继续努力,那么基于敦煌出土文献的西北方音研究随着资料的丰富与方言调查的深入,将会有更多、更新的成果,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