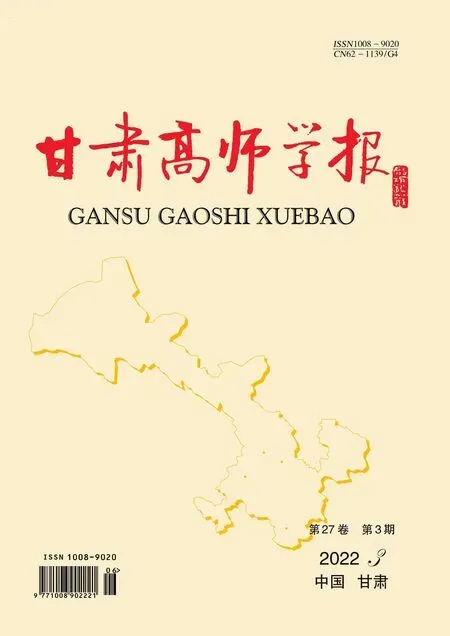女性主义视域下成濑巳喜男电影的空间叙事
寇文静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甘肃兰州 730070)
在日本电影界,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成濑巳喜男、黑泽明被誉为四大电影巨匠。与其他三位导演相比,成濑巳喜男的知名度并没有那么高,但他却是杨德昌、侯孝贤、王家卫、关锦鹏等人都非常推崇的日本导演。他的影片作为一种女性电影,往往通过空间的建构和叙事的发展,令女性身处不同的空间之中,由于女性天生对空间敏锐的感知能力,加之生活阅历、情感需求等的不同,空间便不仅仅是她们的活动场域,更是能够被她们所感知,从而产生不同情绪和心情,甚至影响她们行为方式的场域。
列斐伏尔曾指出空间所具有的生产性,它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和某些关系的再生产”[1]。福柯则认为空间是权利运作的基础。爱德华·W.苏贾也认为,“父权力量的空间化,或者说父权的特定地理学,不仅见于建筑物的设计(家舍、办公室、工厂、学校、公共纪念碑、摩天大楼),而且见于都市主义自身的结构,见于城市的日常生活。市郊化和都市延伸成为妇女边缘化,或者诚如本人开始所言,妇女‘落井’ 的物质象征。她们被蓄意孤立起来,离开工作地点和公共生活,蜷缩在小家庭和现代生活方式之中,推波助澜使之俯首帖耳于男性的养家人和他的军团”[2]。也就是说,不论身处私人空间还是公共空间,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在空间中往往受到更多的压抑、排斥甚至于囚禁。在这种情况之下,女性该如何自处,是妥协还是反抗,她们的内心又经历着怎样的斗争,这些都是我们在成濑巳喜男的电影作品中所能够看到的。
一、隐秘的私人空间
(一)压抑的厨房与父权的客厅
对每个人来说,“家”这个词语都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仅是指家庭的居住空间,更重要的是指人们居住在家里所得到的一种心灵以及精神上的归宿感。家庭作为一个私人空间,一般而言,我们认为它是令人感到安全的、放松的、愉悦的。然而,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之后,大多数男性外出工作,进入了更多的公共空间,女性则留在家中,与外部世界隔绝了起来。在这种情形之下,男性通过劳动不但能够得到经济上的报酬,更是在家中拥有了较高的话语权。留在家中的女性每天则需要面对大量的家务,以及照顾婴幼儿的工作,这些往往被认为是女性的“本分”,是她们作为女性理应承担的。即使是一些外出工作的女性,在同等条件下,也容易出现薪资水平不如男性的情况,并且当她们结束工作回家之后,往往仍要承担大部分的家务。此时,家庭空间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便有了不同的意义,男性更多的是将它作为工作之后的休息场所,而女性还要面对除此之外的孤独、压抑以及失落感。成濑巳喜男的电影中有着大量有关家庭空间的叙事,这些叙事的意义“挑战了被家庭空间象征性地和图形式地施加的封闭。他的女性人物的现代主体性在空间中被表达出来,作为一种想要超越家庭角色这个容器的欲望被表达出来”[3]。
《饭》是成濑巳喜男拍摄的第一部由林芙美子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映于1951 年10 月。这一年6月,作家林芙美子的小说《饭》还没有写完,就因心脏疾病骤然离世。成濑和首次合作的编剧井手俊郎、田中澄江在电影版《饭》中为原著补上了结局,弥补了读者的遗憾。该片讲述了结婚五年没有孩子的家庭主妇三千代和丈夫初之辅,因为丈夫侄女里子的来访,打破了他们枯燥平淡的生活。初之辅与里子的打情骂俏让三千代决心回东京的娘家,她想逃离这一切,然而最终,当初之辅来东京找她,三千代还是决定跟他一起回到大阪的家中。
影片中,三千代的家是一栋传统的日式建筑,厨房则是导演为观众呈现出的第一个家庭空间。当三千代从屋外进来,径直走入厨房的时候,我们看到相比其他家庭空间的宽敞明亮,厨房显得又小又昏暗,不到两平米的空间里摆满了各种锅碗瓢盆。初之辅悠闲地坐在饭桌前边吸烟边看报,三千代则在厨房和客厅之间往返多次,一一把饭菜摆好。此时,三千代的声音以画外音的方式出现:“厨房与饭桌之间,就是静静消耗女人生命,让女人老去的地方吗?”很显然,面对日复一日的家庭主妇生活,三千代感到了失落和不满。
当三千代好不容易离开家去参加同学聚会,回来却发现里子不但没有做晚饭,还与丈夫暧昧不清,她满心委屈,坐在厨房门边说道:“你知道我每天过得是什么样的日子吗?你有没有替我想过?这就是婚姻吗?就像个女佣人一样,从早到晚,过着洗衣烧饭的日子,生活在狭小的空间里。”然而,此时的初之辅兀自躺在客厅,对于妻子的抱怨没有丝毫关心,任妻子说什么他都不理不睬。在这里,导演对影片中的空间建构不但显示了三千代与丈夫疏离的关系,更寓意了在这个小家中,丈夫初之辅是权力的象征,而三千代则一直被这种不可言说的权力所压抑着。
成濑以不同的空间视角对这段剧情进行了处理。首先是一个远景镜头,画面中初之辅几乎占据了整个前景画面(图1),并以一个很舒适的姿势侧躺在客厅的榻榻米上,在画面的右前方,三千代作为后景背对着他坐在厨房的门边上。通过景深的制造,观众会看到他们之间的距离较远,而从这种人物的空间位置又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之间的权利关系。初之辅肆意占据着客厅的空间,对他来说,这里既是身体和心灵休息的地方,也是他的权力空间。因此,虽然三千代在诉说她的不满和委屈,但是她并没有进入到客厅。第二幅画面是以三千代为前景的中景镜头(图2),此时,摄影机的拍摄角度显示了她正处在厨房这个空间,初之辅位于画面右侧并且焦点模糊,他的眼神并没有望向三千代的方向,说明丈夫距离妻子的私人空间相距甚远,并且他并没有任何想要交流或打破两个空间的表现。通过这两个镜头可以发现,夫妻二人根本不在同一个空间,这不仅仅是物理上的空间,更是心灵上的空间。可想而知,他们的夫妻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问题。

图1

图2
《情迷意乱》是成濑1964 年的电影,讲述丈夫和公公都已去世的礼子,多年来一直兢兢业业为夫家经营店铺,如今生意受到镇上新开的超级市场的影响,亡夫的两个妹妹久子和孝子希望在家庭店铺的基础上新建超级市场,并由弟弟幸司做经理。然而幸司很早以前就悄悄爱上了他的嫂子,他认为当年店铺被战火摧毁时,是礼子重建它并一直在经营,理应由礼子做经理。当礼子几乎同时知道了幸司对她的爱意以及家里打算建超级市场的决定后,虽然也被幸司所迷恋,但她认为自己应该离开,从而不再妨碍和影响这个家以及幸司。
在本片中,礼子告诉全家人自己决定的一幕发生在客厅。我们能看到礼子的婆婆坐在方桌的上方,久子和孝子坐在方桌左右两边,此时礼子并没有坐在方桌下方,而是坐在距离桌子有一段距离的右侧边(图3)。这个空间显示着丧失了父亲和大儿子的家庭,虽然没有了实质性的父权存在,但是却由婆婆、久子和孝子掌握着家庭的话语权,即便作为儿媳的礼子一直维持着家庭的经济运转,在此时她却甚至没有坐到桌边的权利。当然,这也从一定层面上说明,不论是婆婆还是幸司的两个姐姐,并没有把礼子当做家人一样对待。而当摄影机从另一个角度看去,这个家庭唯一的男人幸司是站在客厅以外的(图4)。这可以看作是幸司从心底根本不打算进入家庭的权利空间,尽管他的姐姐们还有母亲仍然遵循着旧有的家庭体制中男性作为继承者的传统,但很显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此外,画面中幸司是站在礼子身后的,从人物的心理空间来看,这就好像是幸司成为了礼子的后盾,在默默支持和保护着她。

图3

图4
(二)安放心灵的租住房
对成濑电影中的女性来说,租住房是一个特别的空间,它们虽然是临时的居住场所,却可以逃避原有的生活环境,或者成为本无安身之地的女性的避难所。加斯东·巴拉什认为,“对于狭窄、简陋且局促的独处空间的回忆,就是我们关于给人安慰的空间的经验。这种空间不需要扩大,但它特别需要被占有”[4]。租住房正是这样的所在,它是真正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是可以令她们独立的空间,也是可以让她们面对自我,庇护心灵、安放心灵的空间。
《浮云》和《放浪记》两部影片,一部是根据林芙美子最后一部完整的小说改编而成,一部是基于林芙美子自传所写成的戏剧改编。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不论是《浮云》中的雪子还是《放浪记》中的芙美子,本质上都是流浪的人,她们没有家,因此租住房对处于社会边缘的她们来说,就是一个给人以安慰的空间。
《浮云》上映于1955 年,此片曾获当年电影旬报年度十佳影片第一名,也是之后日本为庆祝电影诞生百年而选出的百部电影中排名第三的作品。该片女主角雪子曾跟表兄伊庭一起生活,却遭到伊庭的强暴。后来她在战争中作为日本农林省工作人员去了越南,在那里和同事富冈有了恋情。富冈并不是一个有责任和担当的男人,他有妻子,回到日本也没有离婚。日本战败后才回到东京的雪子,唯一可以依赖的人就是富冈,然而常常失业、性格优柔寡断又喜欢喝酒和勾引女人的富冈,却并没有以同等的爱回馈雪子。直到妻子生病去世,情人阿节被丈夫杀死(兴许是因其丈夫对富冈的妒忌),此时他必须去屋久岛工作,雪子坚持要陪他一起去,富冈才有所触动,但是雪子最终死在了屋久岛上,她得到了富冈的爱,却献出了生命,而富冈的情感今后注定只能四处漂流。
影片中,雪子在东京租住的是一个简陋的储藏间,阴暗并且潮湿,下雨的时候甚至会漏雨。屋子里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光线都很暗,似乎暗示着雪子不光彩的身份。在这个小小的租住房里,几次富冈与她的见面,雪子穿的都是一件白色的针织衫,作为黑白片,白色在昏暗的画面空间中特别引人注目,这更加凸显出她对纯洁而忠贞爱情的向往。富冈提出在这里过夜,被雪子拒绝,因为这里是她得到温暖的地方,也是整部电影中她唯一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她不想破坏这个空间在她心中的圣洁。雪子的家庭情况导致了她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住所,漂泊的生活同样带给她情感上的流离失所,这种自我空间的缺失,使得她一再地逃离,只为找到一个可以让她停留的地方。因此,对于富冈执着的情感,一方面是她对于过去越南那个梦一般空间的留恋,一方面也是希望富冈能给她带来一个稳定的空间,比如一个家。
《放浪记》的故事内容是基于林芙美子一直居无定所的生活经历所改编的。影片中的芙美子总是不停地更换住所,这其中包括她和诗人伊达春彦同居的房间以及和丈夫福地贡租住的房屋,由于它们不是芙美子本人租的,因此不在这里的讨论范围。那些芙美子自己租住的房屋空间都不大,甚至有些是多人合租的,但是在这些狭窄逼仄的空间中,总会有芙美子的书桌,好一点的话还会有一个小小的书架。当她在这些空间写作的时候,不管是白天或者黑夜,哪怕只有一只蜡烛为她照亮,哪怕一起租住的人都呼呼大睡,她的内心都是安然自得的,就像跟她一起租住的酒吧女招待所说:“拼命写东西时的脸,真的很美丽。”对芙美子来说,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有一个可以看书写作的地方,就是能够让她得到心灵的安慰,享有安全感的空间。
《闪电》是成濑第二部改编自林芙美子小说的作品,上映于1952 年,讲述生活在东京下町的观光车讲解员清子的故事。清子的家庭由母亲、两个姐姐、一个哥哥组成,清子是其中最小的孩子。母亲结过四次婚,分别生下了他们兄妹四人。这样一个没有父亲的混乱家庭,哥哥姐姐们个个令人失望,然而他们还想让清子和人品极差的面包店老板纲吉结婚。种种原因,导致清子无法忍受家里的每一个人,遂离家出走,自己在郊外租房生活。导演在影片中营造出来的清子的家和租住房是两种感觉完全不同的空间。清子的家位于庶民区老街的后巷,家门口的街道狭窄而拥挤,家里的两层住房虽然还算宽敞,但是并不够整洁,片中使用了不那么明亮的布光,暗示家庭内部的混乱和阴暗。反观清子租住的房子,这是一栋位于郊区小巷的住宅,门前的道路满是绿色的植物,给人一种温暖、宁静、生机勃勃的感觉。清子的房间在二楼,它是明亮而整洁的,窗外视野开阔、景色宜人,坐在窗边心情都会自然而然地变好。在这样的环境中,清子得以暂时忘记家里的烦心事,远离那种阴暗的氛围。
二、暧昧的室内公共空间
(一)边缘女性工作的酒吧
咖啡馆、酒吧等城市化的空间,在成濑巳喜男的电影中随处可见,这一切都显示出日本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然而,这些公共空间对于生活在其中的女性来说,似乎并不那么友好,它们往往到处充斥着男权思想的影子。多琳·马西在她的《空间、地方与城市》一书中曾说:“现代主义初期对公共城市的狂热描述中,城市是男人的城市。林荫大道、咖啡馆,还有酒吧和妓院,这些都为男人而开,去那里的女人也是供男人消费的。”[5]可见,女性处在现代化的城市之中,曾一度是多么的尴尬和无奈,她们无法享受和男性一样的权利,只因为她们是他者,是第二性。
在成濑的电影中,有一类女性是他非常关注的,她们生活在社会边缘,有的从事艺伎行业,有的是酒吧、咖啡馆的女招待或者旅馆的老板娘,还有的专门为男性提供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这些行业被统称为“水商卖”。由于工作性质的暧昧性,这些女性不可避免的会遭到男性或多或少的骚扰,然而在成濑的镜头下,她们往往有着令人同情的境遇,不可言说的心酸,以及令人敬佩的品格,并且她们中的大部分最终并未屈从于男性。
在影片《女人步上楼梯时》中,女主角矢代圭子在银座工作的酒吧,是导演着力要营造的一个空间。相对于一般的城市公共空间来说,它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因此虽然是黑白片,我们仍然能明显地感觉到它昏暗和暧昧的氛围,即使是在白天,酒吧内仍然拉着窗帘,阳光始终无法透进来,仿佛在透露着酒吧这一空间与酒吧外是两个世界,一个黑暗,一个光明。另外,导演还对进入酒吧的楼梯做了特写,狭窄而冗长的台阶以仰拍镜头被放置在景框中央(图5),台阶左右两边是厚重而宽阔的墙壁,给人一种强烈的压抑感和窒息感。在电影画面中,景框的上部往往象征了权力、权威和精神信仰[6]。而对圭子来说,必须走到这些楼梯的最上方才能进入酒吧。很显然,酒吧代表了一种男性的权利。酒吧的客人基本都是男性,只要他们付钱,这些女招待甚至圭子这样的妈妈桑,都需要为他们服务。圭子内心并不喜欢这个地方,但是丈夫去世,年迈的母亲和独自带着患病儿子生活的哥哥都需要她来照顾,种种无奈,迫使她必须努力工作。可以说,圭子代表着一类边缘女性,她们需要工作来挣钱养活自己和家人,然而在当时的日本,对她们来说并没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因此只能通过这种与男性有关的职业,才能够尽可能快的改变自己的困境。

图5
(二)令情感升温的火车
火车是现代化的产物,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移动性,从而使得它与一般的空间相比,拥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在成濑的作品中,火车是常常会出现的一个空间。乘坐火车的时候,由于时间相对较长,封闭的空间又限制了人物的活动范围和活动内容,这时候如果有人同行,往往会增加彼此之间的距离和感情。
影片《情迷意乱》中有一段男女主人公在火车上的剧情,导演用不断变换的疾驰的火车外部空间和男女主人公逐渐接近的火车内部空间交叉剪辑,不断推动着叙事的发展,从而使得观众一点一点看到面对幸司炽热的感情,礼子心中的纠结和挣扎。
在这一组剪辑里,两人之间空间距离的接近,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他们心理距离的接近。另外,火车呼啸而去的同时,也意味着礼子和幸司逃离了他们原本充满着压抑感的生活空间。由于女性天生对空间非常敏感,因此随着外部空间的不断移动,曾经的生活空间距离礼子越来越远,使得她内心的空间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我们看到,幸司最初找到礼子所在的车厢,说要送她回家时,整个车厢坐满了人,此时的幸司只能远远站着(图6),并时不时抬头冲礼子笑笑。礼子内心是不想让幸司跟着她的,因为她已经决定要离开曾经的家,当然也包括离开幸司。然而随着火车的行进(图7),幸司有了座位,这时他虽然距离礼子的座位还有好几排,但当他回过头来看礼子时(图8),礼子开始对他有了微微的笑意,这表明她已经接受了幸司送她回家的事实,也表明她不再如之前在家时那么紧张,而是开始试着接受自己的情感,因此对于幸司的接近也不再那么抗拒了。火车继续前进(图9),幸司坐到礼子的后侧方(图10),他向礼子要了桔子吃,之后坐到礼子后方(图11),开始问礼子要她手里的杂志看,并时不时跟她换一本,此时的礼子已经很配合幸司的举动了。这个场景从画面空间来看,他们的空间距离也已经从火车座位的两侧转到了一侧,暗示着礼子的心渐渐敞开了。在礼子内心深处,虽然深知不能爱上丈夫的弟弟,但是的确对幸司有所爱恋,因此随着火车继续行进(图12),车上的乘客不断变换,幸司很自然地就坐到了礼子的对面(图13)。而随着火车上的乘客越来越少,礼子和幸司得以享有了一个相对单独的空间(图14)。从这个时候开始,没有了别人的打扰,他们终于可以敞开心扉地交谈,不用再顾忌别人的眼光。然而,当礼子看着坐在对面昏昏欲睡的幸司,知道终点即将达到,而她也将和幸司告别,便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情,难过地掉泪了。幸司发现后,着急地坐到礼子旁边(图15),问她为什么哭。幸司的这一举动完全打破了两人之间外部的空间距离和心理的空间距离,从而导致礼子完全打开了自己的欲望,决定和幸司一起提前下车。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0

图11

图12

图13

图14

图15
三、自由的室外公共空间
(一)连接自由与束缚的街道
在城市空间中,街道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它的作用更多的是显现在连接其他两个空间上。
在影片《饭》中,一开场我们就看到了关于街道的空间叙事。这是大阪市的郊区,虽然在地图上显示是市区,可是它看起来却更像是乡下。弯弯曲曲的街道两旁都是些人家,女主角三千代就住在这样的街道旁一栋日式的住宅里。作为家庭主妇,她每天最多的活动空间除了家里就是到门外的街道和邻居寒暄几句。在这样的日子里,街道的存在是让她能够摆脱束缚和压抑的家庭空间的所在。因此,我们看到在成濑的镜头下,尽管三千代家附近的街道看起来并不繁华,却有着一种宁静、诗意的美感。然而,不管是家还是街道,与真正的城市空间都是有距离的。相比三千代,他的丈夫初之辅则每天身处都市空间,对他来说,家庭空间、工作空间,甚至工作之后偶尔在城市的娱乐场所放松一下,都是稀松平常的体验,他的世界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反观三千代,她走出家门的机会并不多,除了影片后半部分回到东京的娘家,就只有一次借着同学聚会的机会,来到离家较远的大阪闹市区闲逛的经历。
同样,在1964 年上映的影片《山之音》中,街道这个空间是连接女主角菊子位于镰仓的家以及丈夫、公公位于东京的工作单位的通道。影片讲述的是儿媳菊子和公公信吾之间惺惺相惜的情感。菊子和丈夫修一是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修一对菊子的冷淡和对婚姻的不忠,让公公信吾非常不满。然而修一越是如此对待菊子和自己的婚姻,菊子和信吾的心就走得越近。整部影片中,菊子只有两次去了东京,一次是去流产,另一次是告诉信吾自己决定与丈夫分手。这两次经历从外部空间来看,是菊子离开了家庭这样的私人空间,来到了作为公共空间的东京,从心理空间来看,流产意味着菊子摆脱了即将出生的孩子对她人生角色的束缚,与丈夫分手则意味着摆脱了家庭伦理对她的束缚。而街道空间作为菊子和信吾每次单独置身的空间,代表着一种轻松和愉悦。在这里,菊子和信吾的每一次对话,都有着许多可能性,虽然他们不能将心中的情感明确地表达出来,但是他们那种不可言说的情感却在这个空间一点点地升温了。
(二)无所拘束的公园、林间、河边
在《浮云》一片中,大量室外空间的建构,是基于雪子和富冈一起行走的场景。从雪子刚回国时他们一起走过的东京的废墟地带,到影片中闪回的越南的林间,从幽静的公园,到温泉小镇上上下下的楼梯,从黄昏中城郊的马路,到旅馆外河边的小路,空间的不断转换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叙事一点一点进行着,雪子和富冈的命运也在时空的变换中越来越紧地纠缠在一起。
波德莱尔曾指出过城市漫游者的形象,并认为除了漫游者,“这些局外人或观察者还包括了诗人、拾荒者、女同性恋、老人和寡妇(一般假定这群人可以躲过令人讨厌的异性恋审视),以及娼妓和流莺,她们在发展中的大都市里全都仰赖机智过活”[7]。战争的失败,迫使雪子和富冈成为了社会的边缘人群,雪子无家可归,并且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福冈难以融入社会,无力承担应有的责任。面对雪子,福冈既无法割断彼此的联系,又不能许她一个长久而安定的关系。因此,他们只能不断地在城市的各种室外空间漫游,而在这些空间中,唯有公园、林间、河边这样的室外空间,是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它们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可以不考虑性别、阶级等因素,容纳一切想进入这些空间的人。对于雪子和福冈来说,战争期间在越南的美好经历,让他们无法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的日本,而这些象征自由的室外公共空间,令他们压抑的内心和无法被承认的关系得到了缓解和放松,因此他们漫无目的地游走,肆无忌惮地交谈,从而借以逃避他们无法融入的城市和无法确定的关系。
类似的室外公共空间,在成濑的电影叙事中并不难发现。《乱云》中的十和田湖,《山之音》中的新宿花园,皆是男女主人公在面对不被认可的关系时,所能够选择并置身其中的空间形式。《乱云》中的由美子和三岛,背负着由美子丈夫离世的阴影。三岛最终选择离开由美子的世界,临行前,他们的关系在十和田湖这样的空间中得到了缓和和升温,这也是影片中他们第一次在室外公共空间的独处。可以说,十和田湖美丽的景色和没有束缚的空间特性,令由美子和三岛的内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放松,使他们能够更加正视双方的关系,而三岛在此过程中发烧病倒,又令他们加剧了对彼此感情的认知。《山之音》中菊子和公公信吾之间微妙的情感,在电影里一直隐含于各种细节之中。菊子是传统的女性,不论对丈夫还是公婆,她都是乖巧顺从的,甚至丈夫修一要求她流产,菊子也没有质疑和反抗,因此即便她明白自己和信吾之间产生了难以言说的情感,也绝不会做出有悖于自己身份的事情来。直到影片结尾,菊子约信吾来到新宿花园,并告诉信吾她决定和修一分手,才开始将自己从儿媳的身份中解放出来。空旷的新宿花园,没有了菊子和公婆共同生活的家宅的束缚感,令她开始对未来有了憧憬。或者说,离开被伦理道德深深包裹的家宅,身处充满自由意味的新宿花园,才让菊子想要重视自己的情感需求。
相对于成濑影片中大量室内空间的建构和表现,室外空间的数量显得相对较少,然而正是这些室外空间的出现,衬托出电影中的女性在室内空间所感受到的压抑、束缚等心理状态。总之,成濑在他的作品中通过空间叙事,让观众更加深入地感知了人物的情绪以及人物与空间的关系,空间随之“进入了意义和情感的领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