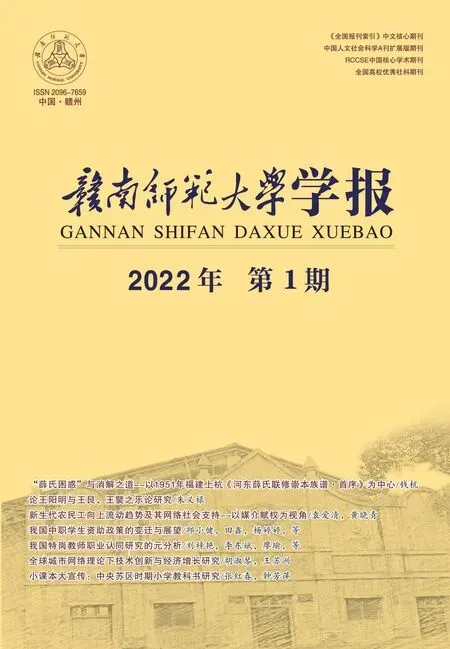迷惘与留恋:社会转型时期作家的乡土意识*
李旭琴,罗 甜,2
(1.赣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2.大连外国语大学 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乡土文学在中国经历了萌生、发展、断裂又复归的过程,而对“乡土文学”的理解,学界亦各有说法。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Ⅱ》中,严家炎对“乡土文学”条目的解释为:“乡土文学,通常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一部分小说创作。”[1]刘绍棠从自身的创作实践出发,认为乡土文学“主要是写农民,写农村……它的特殊性,主要是着重于风土人情的描写。写一个地方的特色,地方的人情,人情的美好。”[2]冯骥才认为“乡土小说是要有意地写出这乡土的特征、滋味和魅力来。表层是风物习俗,深处是人们的集体性格。”[3]因而,就表现对象而言,乡土文学多以农村社会为基本描写对象,在乡村独特的风俗人文中展现人物性格和命运,具有浓郁的乡土风情。即“殊不知乡土小说的三大要义(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才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条件。”[4]17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乡土文学有了新的特质。“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乡土小说的创作不再是指那种18世纪前描写恬静乡村生活的‘田园牧歌’式的小说作品,它是指在工业革命冲击下,在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中所表现出的人类生存的共同人性意识,这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4]7从某一方面来说“乡土文学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耕文明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而产生的”。[5]如何将传统的乡土文学与都市文明相融合,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作家们大多呈现出一种迷惘与留恋的态度。本文拟以阿城《棋王》、路遥《人生》、陈忠实《白鹿原》、汪曾祺《受戒》四部作品为例,探讨作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中所呈现出的“迷惘与留恋”的乡土意识。
一、乡土的书写对象及其特征
(一)《棋王》思考中的迷惘与留恋
《棋王》中,阿城通过叙事者“我”在“文革”时期和“棋呆子”王一生相遇相识的故事,以“我”一直都在思考王一生的行为举止为叙述,在社会转型时期以平淡的口吻回望“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以对话般的“隐喻”方式来思考乡土社会在时代变迁中的流变。
“我”和王一生都是离家千里下放到农村的知青,在火车上因棋相遇,这虽看似平常,却隐晦表现了“文革”时期的社会生存状况:“我”是一名知识青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下放农村,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但此去之地按月有二十几元工资,便很向往要去。到农村以后,物质、精神生活的双重匮乏与落差对人精神的折磨,引发了作者的思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否能真正净化人性,在艰苦的社会环境中,人的本性难免会遵从内心原始的生存欲望,人性便难以捉摸,深不可测。
在全区象棋大赛中,王一生因平时表现不好,分场不允许他出去参赛,因而没能报上名。同为下放知青的“脚卵”为此欲给地区文教书记“走后门送礼”,让王一生取得参赛资格,极其渴望下棋的王一生却拒绝了。阿城用极其平淡的口吻描写这一思想行为,仿佛一切本应如此,但似乎又并非如此。显而易见,“我”和“脚卵”与王一生的思想对比折射的是作家对乡土社会的思考,对参赛是否应走后门的犹疑不决实质上是作家对乡土社会美好人性和精神特质的思考。
阿城以审视历史的方式描写了“文革”时期知识青年的生存欲望和人性变化,思考生存环境的恶劣与知识青年的命运,借此展现乡土社会的复杂性,也使乡土文学具有更深刻的思想性。
(二)《人生》爱与恨中的迷惘与留恋
《人生》中,路遥通过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与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知识青年黄亚萍之间的“三角恋爱”,展现社会变革时期乡村社会的生存状况与精神面貌。路遥以“才子佳人”式的爱情纠葛,书写新时期人们面对物质追求人性的复杂与多变,在“爱与恨”的缠绵中再现路遥对转型时期乡土社会的迷惘与留恋。
高加林是一个渴望改变自身生活与命运的农村知识青年,但在支书高明楼的暗箱操作下,其子三星取代了他民办教师的工作。他只能被迫接受现实,留在农村,接受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接受刘巧珍对他的爱。巧珍是个“理想国”般的人物:善良、能干、通情达理,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灵”,可谓集天下所有美德于一身。高加林在落魄时,巧珍的陪伴,既是对高加林事业失落的安慰,也是路遥对农村土地里美好人性的留恋。然而人生总是起起伏伏,高加林遇上城里姑娘黄亚萍,面对精神相通的灵魂和奢求已久的城市,高加林在人生道路上迷茫和动摇了,变成了他自己曾经唾弃的那种人。高加林的动摇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不确定,在漫长的人生道路面前,谁也说不清楚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是否都能选择对得起良心的那条路。最终高加林“竹篮打水一场空”,人生走进了死胡同,既失去了留在城市的工作,也失去了“金子般”的巧珍。
路遥通过浅层的爱情纠葛来思索乡土人生的前路,高加林在人生选择上的摇摆,折射出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时期千千万万农村知识青年的摇摆。在面对“诱惑”时如何遵从本心,在“爱情和面包”上如何抉择,充分显现了变革时期乡土社会的复杂性。
(三)《白鹿原》折磨中的迷惘与留恋
陈忠实在《白鹿原》扉页中,借用了巴尔扎克“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6]的表述,以白鹿原为舞台,集中展现了清朝末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进程,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中乡土社会在历史变迁下风雨飘摇的历史命运。“白鹿原”是传统乡村社会的典范,朱先生、白嘉轩等人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教化乡民、指导民众生活,使白鹿原成为传统宗法社会的理想圣地。然而“白鹿原”上错综复杂的社会习俗和生活方式,在新思想与旧观念交融的革命时期就显得落后于时代。白嘉轩最初“娶了七个女人,前六个都死了”,在旧时代为传宗接代不断娶妻生子的社会风气,在白嘉轩这儿虽说顺理成章,但也是思想和观念上的折磨:他一方面担心无后对不起列祖列宗,另一方面又担心再娶会继续害人性命。然而作为传统封建礼教的忠实拥护者,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却将女性物化为“糊窗纸”,作为传宗接代的“纸”坏了就应该尽快糊一张好的。母子两人截然不同的态度,恰是宗法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人的折磨。
除此之外,“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去抗争的叛逆者”[7]田小娥的命运也是如此。年轻貌美的田小娥嫁给70多岁的郭举人作填房,她不仅不得宠, 还成为对方滋阴补阳的加工工具。她遇到黑娃,不惧世俗眼光和黑娃走到一起,用这种背叛行为来表达对郭举人的愤恨。她只想和黑娃安安生生过日子,但白嘉轩不让她进祠堂,公公鹿三撵她出门,村民对她指指戳戳,说她是烂货、婊子,最终死于黑娃父亲鹿三之手。鹿三老实巴交,本本分分,却为了“白鹿原的青年们”,“替天行道”杀死田小娥这个“异端”。
在古老的白鹿原社会里,以儒家文化为指导的乡村社会自然而有序地运转着,是友好和谐的精神家园。随着革命的到来,白鹿原封闭的社会被打开,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乡贤社会在历史的洪流中终究走到了对立面,在文化交汇的折磨中书写对传统乡村习俗、传统乡村观念和传统乡村文化的迷惘与留恋。田小娥的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新旧思想在折磨中的碰撞与撕裂。作家在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描写和乡村治理时隐晦表达了他的艳羡与留恋之情,然而在乡村“吃人”社会里,又展现了作家对新旧思想不能两全的迷惘与困惑。
(四)《受戒》自然牧歌里的迷惘与留恋
汪曾祺的《受戒》以自然牧歌般的笔法书写了主人公明海出家前后的所见所闻所感。庵赵庄是个善出和尚的地方,寺庙佛门本应充满清规戒律,但是和尚们抹牌、吃肉、娶妻、收租、放账,过着与常人无异的世俗生活。明海去当和尚,也是为了有一口饭吃。社会道德似乎并不压抑人性,汪曾祺在“受戒”中打破“戒律”,在自然牧歌里讴歌单纯、自然的乡土社会和人性的纯美。小说如同一幅风俗画,再现了江南水乡恬静、淡雅、宽宥的乡村生活。在这片江南水乡中,淳朴自然的气息是在山野中生长起来的,这种不自知的美完全是现实社会中清规戒律压制人性的对立面。
汪曾祺的笔下,人性似乎本应如此:纯美的环境塑造朴素的民众,但在变革时期的社会现实中,人性渐被金钱物化,使人不由得思考原始乡土社会是否能真正释放人性?庵赵庄的一切都是惬意的,所写的故事仿佛就是一个梦,如同“梦中桃花源”一般。然而梦是虚幻的,梦里蕴含着的是对逐渐物化的现实世界的回避。作者用“浪漫派”的笔调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人性的“理想国”,在似真似假的梦境里昭示作者对美好人性和文化的迷惘与留恋。
二、迷惘:该往何处去
(一)不知前路的文化迷惘:内在性的无处安放
摧毁一个民族的文明从来都不是轰隆隆的枪炮,而是隐藏在人们骨子里的劣根性,从而带来的“文化的消解”。随着商品经济在我国的发展,传统的乡土文化在城市文明面前显得无力而又沉重,在历史前进的路上不免逐渐被抛弃。上述文本中所叙述的文化结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对传统渐渐失去活性的无力和对现代文明先天性的距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乡村文化逐渐被消解在历史的洪流中,无法融入物质文明的狂欢,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成为无根的浮萍。
《棋王》是对传统儒家文化该往何处去的迷惘。叙事者“我”是一个迫于社会现实离开老家,前往农村插队的游子,是带有上帝视角的旁观者。故乡是隐藏在游子内心的思念,既有对故土的留恋,也有对亲人的思念。而棋王王一生则是带有传统和现代烙印的“文化游子”。象棋在中国有着千年的历史,琴棋书画自古以来就是高雅的象征,王一生对棋的“痴”,更是道家文化和儒家精神相结合的深层次体现。王一生对棋的痴迷其实是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周围人却无法理解这种精神坚守,因而使之在复杂的社会里尤显格格不入。传统文化该往何处去的迷惘、“棋呆子”下棋的落寞,背后折射的是传统文化的坚守与现代文明的冲突。
《人生》中的高加林则是在追求更为富裕的物质文明中,在渴望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方式时,在爱情上抛弃了农村姑娘巧珍,追求城市女孩黄亚萍。这实质上是出于对城市生活方式,甚至是都市文明的恐慌,意味着戴着所谓“资本”帽子的生活方式会侵蚀社会人性。面对城市文明生活时的摇摆不定,陈旧落后的农村社会与高速发展的城市生活,这种种从根本上来说其实就是对故土的迷茫和对城市文明的不确定。
《白鹿原》中白鹿两个家族的变迁,再现了传统儒家思想和封建礼教的被破坏。宗法制社会崩溃,新的思想被视为“异端”被摧毁,人们在新的社会认同和社会秩序未建立时呈现出茫然无措,乡村社会赖以生存的文化认同在变革时期体现出落寞之感。千百年来,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仁义礼智信”在变革时期失去了原有的色彩,而儒家文化背后的封建礼教则被无限放大,在维持社会秩序和凝聚社会共识上失去了活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折射的是如何以一种新的文化信念来代替传统的思想观念、维护社会安定、引领文学文化发展的茫然与无措。
《受戒》则是通过纯美的自然乡野,从“真”的世界里把“恶”过滤掉,留下“善”,营造出“文以载道”的唯美之“美”。在汪曾祺的文学世界中,这种自然牧歌式的文化其实暗含着避世思想,是对当下乡土文化塑造人性、反映社会现实的迷惘。在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在交汇碰撞中不断发展,被城市化破坏了原始自然环境的乡村,如何在发展中重塑乡村文化,塑造健全美好的人性,成为汪曾祺田园牧歌作品中的迷惘。
总的来说,作家们对社会文化发展前景的迷惘其实就是在经历社会变革以后,对乡村文明该往何处去的不确定性,是对乡土社会如何在社会转型的征途中持续发展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确定在社会大发展大变革时期,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变,会不会在精神层面腐蚀人性?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否会向西方现代主义所表现的空虚、颓废、无助发展?在文明的冲突与碰撞下,“文化”该往何处去的迷惘深深植根于作家的思想里,反映在作家作品中。
(二)未知的恐惧:城市文明的陌生化
在乡村文明面前,城市文明具有不可理喻性:所有的怪诞都是在“变化”的侵蚀下发生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世界里,小农经济式的自然环境大变,延续了千年的人情关系社会土崩瓦解,人性变味,乡土文学生存的土壤渐渐消失。而“乡土文学从诞生之初就是扎根于农村现实社会的写实文学,并且随着中国农村的变革与发展汲取现代性意识。”[8]
因此,此时乡土文学作家们在描写乡土社会时所呈现的心理结构是多元复杂的。一方面,乡土社会所面临的是在中国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文化结构根深蒂固,刻在人们灵魂深处,无法在短时间内通过物质上的“城市化”抹去;另一方面,在20世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社会背景下,有知识者脱离城市较为优越的物质环境,来到物质生活相对落后的乡村社会,这种心理结构对作家的经历难免会产生种种影响,作家在创作中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一影响表现出来。因而,作家们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呈现出对乡土社会与城市文明的复杂情感,一方面拔高乡土社会田园牧歌般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又抨击落后、闭塞的社会环境,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化心理使得乡土文学笼罩上一团散不去的迷烟。
如前所述,《棋王》中,为让王一生有参赛资格,脚卵去求助地区文教书记。十几年前去过脚卵家的书记,依旧惦记着脚卵家的古玩字画。在脚卵未提到自己手里有一副明朝的乌木棋又想求助于他时,书记不说话且再三暗示脚卵家的字画古董,并承诺脚卵的调动大约不成问题,可到地区文教部门给他找个位置。当脚卵表示还可将乌木棋送与他时,王一生的参赛也成了“举贤不避私”的大义之举了。这些可正可反的行为举止,恰恰暗示了城市文明对人性的丑化。《人生》则以高加林人生的不幸结局,折射高加林一直执着的城里生活其实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城市带给你的未必是美好的幸福天堂,更可能是痛苦的深渊。《白鹿原》和《受戒》虽未直接描写城市生活,但其中蕴含着非一般意义的“城市文明”,即对陌生文化的排斥:《白鹿原》是对新思想的否定和排斥,《受戒》则以乡土社会的纯净人性和自然的美好来否定城市文化。
在这4部作品中,作家们尽情地表达那个特殊年代里知识分子对“回城”和“留乡”的迷惘。“回城”和“留乡”未必体现在实质行动上,而是作家通过营造一定的社会氛围,在不同的环境中暗含对陌生城市文明的恐惧。
三、留恋:割舍不开的乡土
(一)生于斯长于斯的留恋
人类对土地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眷恋之情,在这个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土地里,演绎着生死存亡与爱恨纠葛,甚至赋予对“母亲”式的情感。作家在对“土地——母亲”这一意象进行生动描绘和书写人类社会爱恨情仇时,总会凭借经验来寻找一个“记忆空间”,从而承担着作家们的“理想国”。在这个记忆空间里,所发生的故事美化了“既陌生又熟悉”的精神家园,传递了情感与思想,彰显了独特的精神风貌,从而达到与读者共鸣并反映一定时期社会的经济文化。在大变革与大发展时期,作家们将乡土社会作为“记忆空间”,他们书写的乡土社会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原有的风土人情社会,以一种“留恋”的超体验方式成为其精神寄托。
《棋王》中“我”和下乡知青们对“民以食为天”这一“吃”文化的不懈追求,和王一生对传统棋道精神的坚持、《人生》中德顺爷对高加林的鼓励,以及巧珍的朴实品质和美好人性、《白鹿原》中白嘉轩对家业的坚守和对传统儒家精神的传承、《受戒》里乡土社会中美好人性的勾勒,均显示出在农村社会背景中,作家们对延续几千年乡土文化中美好人性的留恋。
(二)城市召唤下的乡土情结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意识,“是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产物,具有现代意味的怀疑精神和反思精神,它不仅仅表现出对土地的依恋和对故乡的深情,更是作为与现代文明相对立的一种精神资源存在。”[9]人们从所谓的落后向先进出发,从宁静的山野走向喧闹的城市,从农耕文明跨越到城市社会。在物质文明的层面,作家们或许对城市文明投入赞美的笔墨,然而在精神层面的追求上,则倾向于书写古老农业文明所孕育的精神内涵。
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乡村在物质层面经历了城市化发展以后,精神面貌也随之改变,传统农村文明所蕴含的文化精髓逐渐被现代工业所孕育的城市文明同化。现代工业社会所孕育出的城市文明带来的距离、冷漠、疏离,与传统农村“人情社会”格格不入。已经陌生化了的乡土社会变成人们回不去的“他乡”,在精神上成为游离于农村与城市的“孤魂野鬼”。失去情感载体和理想国的作家们则开始在城市文明里怀念乡土社会,审视城市文明,重新探索经历了城市化的乡村文明,如何在新的时期和新的社会发展中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四、结语
时光翻页,所有人都会被历史的车轮碾过,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回望乡土文学的创作历程和创作实践,中国农村社会孕育了极具特色的乡土文学,呈现出复杂的双重性质。一方面,作家以赞美、留恋的方式描绘了纯美的乡村环境与朴实、善良的乡土人情社会;另一方面,作家也以怀疑、迷惘的姿态书写了愚昧狭隘、落后闭塞的乡土社会。这“是传统性的消解和现代性生成的过程,而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以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10]社会在时代的推进下不断发展和变迁,乡土小说家们在新的时期不断变幻创作视角和创作方法,21世纪以来,乡村社会的巨变使得乡土文学的发展也呈现出不一样的“迷惘”与“留恋”。拆迁征地、打工进城等新话题在乡土叙事中的延伸,作家们在城市长大加大了与乡村的隔膜,缺失了最真实的乡土体验,乡村风景在城市化建设中逐渐同质化甚至消失等一系列问题,仍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审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