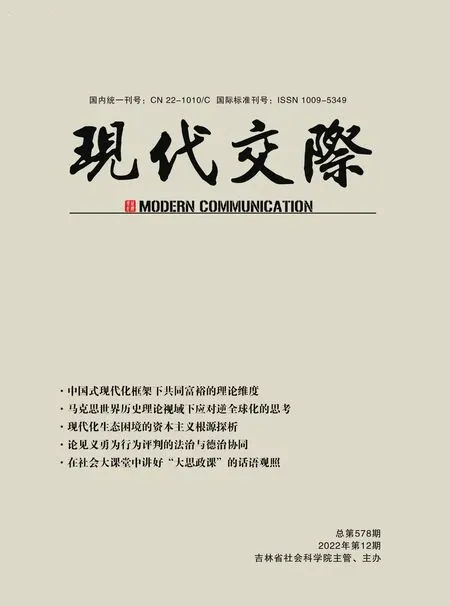“小大之辩”的另一种解释向度
——无小无大
□王满学 毕明良
(西藏民族大学 陕西 咸阳 712000)
庄子在《逍遥游》中借助于蜩与学鸠对鲲鹏的嘲笑,引入“小大之辩”。历代对于“小大之辩”有三种解释向度:以郭象为代表的小大同扬;以罗勉道为代表的扬大抑小;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小大同抑。借用庄子在《齐物论》中的话来说:“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逍遥游》中的“小大之辩”真的是庄子针对于“小”与“大”孰优孰劣所做的讨论吗?结合《齐物论》来看,庄子《逍遥游》中的“小大之辩”并非孰优孰劣的讨论,但这并非意味着“小大之辩”没有意义。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庄子正是将他的思想隐藏在这段似是而非的“小大之辩”中。历代学者往往将“小大之辩”作为庄子对“小”与“大”孰优孰劣的评论来认识庄子的思想。然而,通过《齐物论》中庄子的言论我们可以发现,庄子并不是要对“小”与“大”孰优孰劣做出自己的评论,而是为了打破“小”与“大”的界定,是要在天人之间开辟出一条由“人”而通达“天”的道路。这种对“小”与“大”的界定就是主观“成心”的表现。当我们打破这种对“小”与“大”孰优孰劣所做的界定,以超越“成心”的视角——“道”的视角,以“以明”的方法去重新思考“小大之辩”,我们会发现庄子“小大之辩”的文本中处处暗示“小”与“大”的消解,即“无小无大”。
一、“成心”——小大皆由己
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郭象言:“今日适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是非由“成心”所生,“成心”即“与接为构,日以心斗”而“莫知其所以萌”的主观认知之心。这种主观认知之心,先于判断产生,是先入为主的遮蔽。主体对其他事物的认知判读,必然受到“成心”的遮蔽,从而导致事物的本真存在并未被主体所真正认知。主体所认知的只是“成心”遮蔽在主体本身之上的“影子”。“成心”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成心”的存在意味着主体对事物的认知始终都存在着主体自身的主观因素以及主体的位置因素的影响。这就意味着“成心”是主体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主观认知。另一方面,事物对主体也始终无法达到完全客观的显现。换句话说,事物的显现存在着事物本身主观因素的影响。①“成心”是一切“是非”的来源。“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事物对主体的显现无法控制,因此主体只能从本身入手:当主体自以为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去观看事物时,这种自以为就已经包含了主体的因素。这种主体自以为的“客观视角”虽然仍无法摆脱“成心”的困扰,但这正是摆脱“成心”的一条路径。也就是说,只有主体完成“自觉心”的觉醒,主动去将自我的存在境域扩大开放给事物,事物才可以完整地显现给主体。主体自我位置视角的开放,意味着事物对主体的开放,只有在达成一个互相完全开放的视角之下,即主体完成主观的客观化过程后,才可以达成“成心”的消解。庄子把这种方法称为“以明”。
毫无疑问,历代学者均将“蜩与学鸠”和“斥鴳”作为“小”者。可以说,二者的“小”完全是自我主体的“成心”所导致。《逍遥游》中这样描述: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蜩与学鸠”以己之“决起而飞”对比鲲鹏的“怒而飞”,嘲笑“鲲鹏”九万里之风而无用;以己之“成心”观物,得到的必定是“自贵而相贱”的结果。在这里,“蜩与学鸠”不识得“鲲鹏”之“积”,即不知“鲲鹏”为何要以九万里之风才可扶摇而去往南冥的原因。在它看来,随处而飞,无所目的,撞到树上就停下,飞不动就落在地上。“蜩与学鸠”并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主动努力的方向,而只是顺遂己之“成心”。由此“成心”,二虫对“鲲鹏”发出自己的嘲笑。这正是其之所以为“小”的原因。在庄子看来,为“小”者,并非生来的“小”,而是自我成就的“小”。小大皆由己而不由人。当“蜩与学鸠”以己之“成心”观于“鲲鹏”,不识“鲲鹏”之“自觉”之“积”,以“鲲鹏”为“小”时,恰恰证明了此时的“蜩与学鸠”才是属于“小”者。庄子在后文以“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之二虫又何知!”驳斥二虫的“嘲笑”。但这种驳斥并非落实在二虫本身,而是落实在二虫的“知”。庄子以二虫之不“知”来驳斥二虫,因为二虫是自以其所知而知,即以其“成心”为其所知。以其“成心”观于他物,所得到的“知”,必定不是事物本真存在的显现。郭象在注解此处时说:“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地,而荣愿有余矣。姑小大虽殊,逍遥一也。”[1]10郭象以小鸟大鹏各尽其性为逍遥,但是庄子在此处重点并非大鹏与小鸟的逍遥比对,而是在以小鸟的嘲笑对比于大鹏,从而得出小鸟是自以其所知而为大的实际为小者。庄子在《齐物论》中说:“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二虫以其“决起”为是,以“怒而飞”为非,这是由己之“成心”所产生的错误认知。以二虫之“笑”与鲲鹏之“默”做出鲜明对比,前者以己之“成心”自以为是,后者以己之“默”不自以为是。“是非”则通过“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否认他者的合理性,并通过“画地而趋”的方式不断巩固自己的封界。[2]二虫由其“成心”而将自我与鲲鹏局限在“成心”所设置的生存境域之中,这就导致二虫自以为“大”,实际上却为“小”者而不自知。因此,庄子的意图并不是在寻找证明“小”与“大”孰优孰劣,而是在强调小大皆由己心所成。
同样的,庄子对“斥鴳”的描述如下: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斥鴳”与“蜩与学鸠”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仍然是以“成心”观于他物而导致的自我为“小”。但在“自觉心”的线索之上,“斥鴳”终究比二虫进步了一点。钟泰说:“上蜩与学鸠曰‘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拟自弃者之言。‘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拟自暴者之言。自弃与自暴虽不同,要其为小知则一也。”[3]12“斥鴳”与“蜩与学鸠”相同的地方在于,仍然对“鲲鹏”发出了嘲笑。前者以“决起”嘲笑“鲲鹏”之九万里,后者以“飞之至也”嘲笑“鲲鹏”之不知至。二者都是以己之“成心”观于“鲲鹏”,得到的都是对“鲲鹏”的嘲笑。由此也使二者都各自以为“大”而实为“小”。不同点在于,“二虫”以“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发问,“斥鴳”以“而彼且奚适也”发问。前者强调为什么要积九万里之风来飞往南冥,后者强调为什么要飞往南冥。前者不识“积”之作用,后者满足于己之“成心”,自以为得,又以事事物物“翱翔蓬篙之间”为事事物物之自得。前者由不知九万里之风之用而不识得“自觉心”,后者以“此亦飞之至也”而知“自觉心”。“斥鴳”的问题在于,它识得“自觉心”的作用,识得“积”之作用,却因己之“成心”而满足于当下。以“飞之至也”为终,满足于此,并以此“飞之至也”观于事事物物,以为事事物物皆如此。“斥鴳”也就是后文所说:“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斥鴳”的“飞之至也”是虚假的,是主体“成心”满足的虚假状态。“其自视也亦若此矣”,主体一旦受到“成心”的蒙蔽,便会按照“成心”的引导以“成心”观己,以己观物,最终得到自我的虚假肯定,并以此否定他人从而落入为“小”者。“斥鴳”以己之“成心”为己画牢,虽然比之二虫略有进步,但仍然是无法拜托“成心”的控制而终为“小”者。郭象以“物各有性,性各有极”[1]13解庄子“小大之辩”之意,实则不知“斥鴳”自以为尽其性而实则仍为“成心”所困。
相比较而言,“鲲鹏”似乎一直是“大”者。在根本上,鲲鹏亦未能彻底摆脱“成心”之困扰而达到“逍遥”,但“鲲鹏”仍有通达的可能。不同于“蜩与学鸠”的“决起”,“鲲鹏”以“怒”表达出生命主体的自我通达的可能。《逍遥游》“怒而飞”之“怒”与《齐物论》“万窍怒呺”之“怒”、《外物》“春雨日时,草木怒生”之“怒”同。“怒”同“努”,古时无“努”字。陆树芝与宣颖皆以“奋”解“怒”。“怒”中自有生生之意存。“怒”是一种主动的奋发勃起,是一种不可遏制的上升的冲动,是“自觉心”的显现发用。老子言“万物并作”,“怒”即一种对自我认知的主动性,是一种自我迸发向上的自觉的“作”。“鲲鹏”之“大”,在于其主体之“自觉”;它意识到“自觉心”在由下而上、由人而天的过程中的重要位置。钱澄之说:“鹏之一飞九万里,全在一‘怒’。凡草木之甲坼,虫鸟之孵化,必怒而始出。怒,其悬解时也。二小虫闻鹏之图南而笑之。笑者必不能怒;不能怒,故终不能飞。”[4]“怒”意味着主体由“自觉心”有了破除“成心”的意图;正是这一“怒”,使得“鲲鹏”同“蜩与学鸠”与“斥鴳”产生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不是形体上的“大”,而是“鲲鹏”所处位置上的开放境域之“大”。由此,“鲲鹏”在不断将自我的存在境域扩大给事物,踏上了由人而天的上达之路。
“鲲鹏”的大,不是被给予的形体之“大”。“鲲鹏”的大是自我成就的“大”。“蜩与学鸠”接受了“成心”所给予的“影子”,将“影子”作为事物的本真样貌而认知;“斥鴳”虽前进了一步,但它在“自觉心”破除“成心”的道路上迈出一步后停滞不前,重新被“成心”所蒙蔽。“鲲鹏”进一步将以“自觉心”来破除“成心”,它已经触及最根本的境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在这里,“鲲鹏”意识到天下事物,无有不同;“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所谓的不同,只是由各自视角不同;由天而视下,无异于由下而视天;二虫、“斥鴳”亦无异于“鲲鹏”;野马,尘埃,万物之相互成就而已矣。这也是“鲲鹏”只是触及最根本的境域而未能达到的原因所在。“鲲鹏”面对二虫与“斥鴳”的嘲笑,虽以沉默应之,然未能以己之“自化”而使其二者“化”②,这就意味着它仍未能完全破除“成心”之见。“鲲鹏”没有神人的“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的能力,但“鲲鹏”仍有进一步“自化”的可能性。③
“鲲鹏”的“大”与“蜩与学鸠”“斥鴳”的“小”是不同的。“鲲鹏”不自以其形体之“大”为“大”而实为“大”;“蜩与学鸠”“斥鴳”以其自以为“大”而实为“小”。小大皆由己,而非由外物。前者以克“成心”乃称其大,后者以从“成心”乃称其小。“小”与“大”之间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相反,由地视天同于由天视地;由“小”及“大”亦不是妄言。可以由“小”及“大”,也为由“大”及“小”做出反证。“如此,小物也可能因获得大知而实现逍遥;大物也可能因只有小知,故不得逍遥。”[5]15去除“成心”的过程,也就是“自觉心”觉醒的过程。张载有言:“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见闻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6]“大其心”,即去除“成心”、觉醒“自觉心”的过程。只有去除“成心”,达到“吾丧我”的“天籁”之境域,才能够走向“小大之辩”的终点——“无小无大”。
二、“以明”——无小无大
庄子在“小大之辩”的讨论中首先明确“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以“小知”为“小年”,以“大知”为“大年”。随后,庄子以“朝菌”“蟪蛄”“冥灵”“大椿”“彭祖”“众人”做出一系列的对比,以他们的生存寿命,即以“岁”为根据划分出“小年”与“大年”,进一步印证“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观点。庄子的论证逻辑似乎是这样的:以“岁”划定“大年”与“小年”;以“朝菌”“蟪蛄”“冥灵”与“大椿”之间的比较,证明“小年不及大年”;以“小年不及大年”证“小知不及大知”;而“小年不及大年”的原因是“知之不及”,“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既然“晦朔”“春秋”都不知,而又何以知“冥灵”与“大椿”?小年与知少相关联,大年与知多相关联,即所谓“以小年之不及大年,则小知不及大知又可知矣”。小年以其知少为小,大年以其知多为大。在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小年”因知少而为小,“大年”因知多而为大,那么在知小与知大的比较过程中,知少者为小与知多者为大的依据在哪里?换句话来说:如何以知之多少划定知之大小,知多者一定为大?知少者一定为小?这个依据在《齐物论》中所言明,即“成心”。以“成心”而观,则知少者为小,知多者为大。“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个事物具有‘大’的客观物性,并不必然使其获得肯定性的‘大’之价值评价。”[5]10“小大之辩”并不是对“小”与“大”做出孰优孰劣的评论,庄子是以“小大之辩”来通达“无小无大”的万物齐一的至高境域。“正是时间量级造成存在者彼此之间的存在视域或世界视域的巨大差异,而自由主体的成长也就是走向更高的时间量级,走向更大化的世界视域。”[7]但是在将自由主体的成长纳为走向更高的时间量级时,主体就不可能充分地对其他事物展开自身;一个在时间量级上无限性的“比”便已经包含其中了,而这种无限性的“比”又是一种有限的无限性,这就注定了在依照这种“比”而得到的结果,必然不会是主体与事物的互相开放。
在庄子所做出的“小大之辩”系列比较中,似乎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大”与“小”。“大”与“小”正是在“比”的过程中才可以得出。在“朝菌”“蟪蛄”“冥灵”“大椿”的比较系列中,前者永远是在与后者比较过程中而为“小”,后者永远是在与前者的比较过程中而为“大”。换言之,没有绝对的“大”与“小”,只有相对的“大”与“小”;“大”与“小”之间的比较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依据,即“成心”。只有在以“成心”来观各物时,才可以得到“大”与“小”的结果。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永远不可能存在作为绝对的“大”与“小”。庄子进一步说:“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庄子强调,与“彭祖”比寿的行为是可悲的。那么同样的,与“朝菌”比寿是可行的吗?答案很显然,依旧是可悲的。因为只要还存在着“成心”,只要还存在于“朝菌”“晦朔”“冥灵”“大椿”所构成的这个序列,只要还存在着“比”,就意味着“成心”的存在,就意味着无法通达于“天”,仍旧是可悲的。钟泰言:“悲其知有小年而不知大年也。”[3]11然而只要有“比”在,只要有着“小”与“大”,那么就必定是可悲的;悲不在于知“大”或知“小”,而在于仍有“小大之辩”。郭象注解时说:“夫悲生于累,累绝则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1]15-16有悲则有累,有累则有“比”,有“比”则有“辩”,有“辩”则有“成心”;唯有去其“成心”,以道观之,方可知物是物,事是事,万事万物无不同,“大”与“小”俱无。王夫之在《庄子解》中说:“辨也者,有不辨也。有所辨则有所择,有所择则有所取,有所舍。取舍之情,随知以立辨,辨复升辨,其去逍遥也甚矣。有辨则有己,大亦己也,小亦己也。功于所辨而立,名于所辨而成;六气辨而不能御,天地辨而非其正;鹏与斥鷃相笑而不知为神人之所笑,唯辨其所辨者而已矣。”[8]78故庄子“小大之辩”的真实意图是以有“小”有“大”为反例,做出“无小无大”的要求。
上文已述,“成心”意味着主体自我存在境域的固化④,“大”与“小”存在于主体自我固化的生存境域之中。要克服“成心”的困扰,就要将主体自我的生存境域不断扩大,摆脱固化的束缚,将自我充分显现给事物;只有这样事物本身才会向主体充分显现;只有二者互相向对方展开最大的生存境域,才能够达到至高的万物齐一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庄子所追求的至高的“逍遥”境界。然而,这种由人而天⑤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作为有限性存在的人向无限性存在的天的靠拢。虽然庄子在《天地》中强调“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即由人而天的转化,但庄子也在《山木》中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大宗师》亦言:“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庄子认同由人而天的转化可行性,但这种上升之路并不是以人来取代天,而是要求有限的人借以天的无限性审视自身及他物,从而得到事物本身的样子。这也正是庄子在《齐物论》中所说的“以明”与“因是”。
庄子在《齐物论》中说:“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由此看来,“以明”是庄子用来去除“是非”之见的方法。下文言:“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以“成心”而观,则我所是者,为彼所非;所以说“是非”皆以无穷无尽,若要去除“是非”则需要用到“以明”的方法。何为“以明”,庄子举例说,用“马”之名言来说明“马”之“非马”,不如用“非马”来说明“马”之“非马”。换言之,要去除“成心”之蔽、“是非”之见,则需要将事物还给事物本身,对事物的判断认知应当落实在事物本身。以事物本质之“是”肯定事物之“是”,这也是庄子所谓“因是”之意。钟泰说:“实则言‘以明’即兼‘因是’,言‘因是’不离‘以明’,两支仍一体也。”[3]39钟泰先生理解得可谓到位,“以明”与“因是”实际上是同一的。“以明”强调以事物本身去认识事物本身;“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不需要主体在对事物之“用”上再添加什么,“去执”是也;“因是”强调以事物本身之“是”来肯定事物本身,“善用”而已。二者实际上为一件事情,故后文中说:“是以圣人合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谓两行。”“‘两行’者,因是、以明,如车两轮、如人两足,失一而不能行者也。”[3]43
把视线重新回到“小大之辩”,在“鲲鹏”的第三次出场时,庄子引入了很关键的一个视角,即“汤之问棘”。闻一多在“汤之问棘也是已”后补上一段:“汤问棘曰:‘上下四方有极乎?’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9]陈鼓应等学者皆从其说。一方面,庄子借用圣人视角暗示了“比”的尽头亦是无穷无尽的,“大”亦无穷、“小”亦无穷。这种由“比”而产生的无穷无尽的无限性视角,实际上正是人的有限性的体现。另一方面,只有超越这种以人之“成心”观“小大之辩”所产生的有限的无限性视角,才可以真正以“天”的无限性视角来达到对事物的最本质的认识,从而消除“成心”,破除“小大之辩”。《秋水》中亦有对有限的无限性视角的描述:
河伯曰:“然则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是故大知观于远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穷;证向今故,故遥而不闷,掇而不,知时无止;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明乎坦涂,故生而不说,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故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
这段话中,借用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从对“大天地而小毫末”的批判进一步引入对“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这种有限的无限性视角的批判,最终“小与大皆囿于量之有涯,而困于时之有止;其不可执大以为大,犹之乎不可执小以为小也。执大以为大而小其小,乃不知所执之大而固亦小……故能破小以知大者,必破大之见而后小之见亡”[8]214。庄子以对“小大之辩”的批判走向了“小大之辩”的解构。只有在将“扬大抑小”的“成心”之见去除之后,真正的无限性视角才可以得到展现,事物的本质也将呈现在面前。王夫之强调:“但言小知之‘何知’,小年之‘可悲’,而不许九万里之飞,五百岁八千岁之春秋为无涯之大。”[8]77因此,必须破除这种有限的无限性视角,也就是必须完成“小大之辩”的消解,即“无大无小”。
这种绝对无限性的视角,在《齐物论》叫作“以明”,在《秋水》叫作“以道观之”。《齐物论》有言:“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秋水》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
“以道观之”就是将事物还之于事物本身。主体在观测事物之时,便开始主动向事物展开自身;自我的生存境域不断地开放给事物,事物在接受生存境域的同时也向主体更多地开放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主体不断主动地去开放自我的生存境域,直至达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一切主观消融,完成主体主观的客观化过程,才是真正的达到“以道观之”的境界。这种境界也被庄子称为“逍遥”。
真正的“以道观之”的主体,是完成主体客观化的主体;彻底摆脱了“成心”的困扰,从而可以不“以物观物”,达到“物物而不物于物”;将自我完全的开放给事物,事物也将其本身开放给主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并不是一种理想,它象征着主体的彻底解放;在这种状态之下,“小”与“大”具无,“彼”与“我”具遣,真正的“以游无穷”了。
三、结语
历代学者都对于“小大之辩”阐发自我的见解,但并没有深思庄子“小大之辩”的二重含义。无论是郭象的“小大同扬”,抑或罗勉道的“扬大抑小”,都没有更加深层次地挖掘“小大之辩”的真正含义。⑥可以说“小大之辩”在表面上的义理是偏向于“扬大抑小”的,但在深层次上,在“扬大抑小”或者“小大同扬”的背后,是庄子意图消除“小大之辩”的“无大无小”。因为无论是“扬大抑小”还是“小大同扬”,这种表面义理的背后或者说基础,仍然是“成心”的驱使;只有在此层次之上,进一步深思庄子欲以“小大之辩”想表达什么,才可以得到“小大之辩”的真正价值在于“小”与“大”的消融。庄子在《逍遥游》《齐物论》《秋水》等篇章中都引入了有限的无限性,以此来表达真正的无限性的目的。
可以说,从“小大之辩”走向“无小无大”的过程,就是主体的客观化路程。⑦从“鲲”化“鹏”,“鹏”积九万里之风,庄子在《逍遥游》中极度强调“自觉心”的重要性。尽管庄子也强调自我“成心”的危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消除“成心”的过程,必定有着“自觉心”的参与。当一个人的“自觉心”并没有展露出来时,他的样子也就如“蜩与学鸠”无异。对于《逍遥游》而言,“大”是“化”的条件,“化”是“游”的前提。在主体消除“成心”的过程中,主体“自觉心”的觉醒与发用决定了“成心”的消除结果。只有当“自觉心”达到完全的发用之时,“成心”才可以得到完全的消除。这种最高的境界就是“逍遥”。在这种境界时,“自觉心”完成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转变,真正地将“以道观之”落实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念一意,皆和于天而不为天。这便是主体完成了客观化路程。
【注 释】
①情感态度与经验等构成这种固化的主观认知因素,但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主观因素的来源又是客观的。
②“鲲鹏”作为“逍遥”主体的象征,在追求“逍遥”的过程中一定包含成己的“自化”与成物的“化他”;如果只包含“自化”,那么“鲲鹏”与“视天下为一人”的“列子”也没有区别了。
③“鲲鹏”作为庄子《逍遥游》的重要意象,如若没有进一步“化”的可能,那么庄子的思想也便没有了实现的可能。
④这种“固化”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由人主观的表现出来的“固化”。
⑦在罗祥相先生看来这就是“以‘大知’实现自我消解”,在陈教授看来这就是针对在“大其心”之后的“等齐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