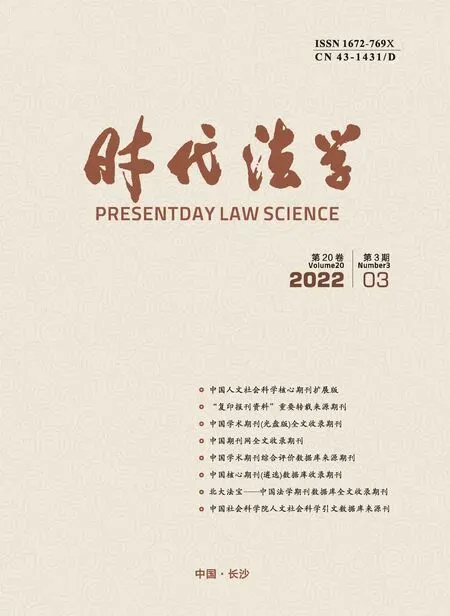论表见代理制度中“有理由相信”要件的证明*
余亮亮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4)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法发[2009]40号)第1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72条规定的“有理由相信”,是指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主观上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
值得注意的是,法发[2009]40号对于“无过失”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遭到来自程序法、实体法学界的双重质疑。程序法学者质疑道,消极事实无法被举证,不得成为证明责任的客体,法发[2009]40号使相对人不得不证明“无过失”这一消极事实,违反了消极事实的举证规则(1)姜世明.举证责任与证明度[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8.;同时,由于待证事实的难易性可以作为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辅助标准,就相对人“有过失”而论,由被代理人予以证明更为容易;因此,关于无过失的相反事实的证明责任应倒置于被代理人承担。更有实体法学者批判道,“法发[2009]40号的解释几乎使相对人主张表见代理难获支持,因为他很难成功举证自己无过失。”(2)崔建远.关于制定《民法总则》的建议[J].财经法学,2015,(4):15.这样分配证明责任将严重限制表见代理制度的适用,使其保护交易安全的规范目的落空(3)杨代雄.表见代理的特别构成要件[J].法学,2013(2):69.。有鉴于此,关于表见代理制度中的“有理由相信”要件证明责任分配这个论题,可分为以下两个分问题:第一,现有法律要件规范说指示下,相对人举证自身“善意且无过失”,是否会造成证明困难?如果造成,化解相对人证明困境的最优方案是什么?第二,本人可归责性、存在代理权表象、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的关系为何?厘清三者关系后,如何将证明责任减轻技术运用于《民法典》第172条所示的纠纷中?判断相对人证明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将之具体化?本文即围绕这两个分问题予以展开。
二、既存解决相对人证明困境方法之检讨
在进行有意义的探讨前,有必要对关键词进行厘清:法发[2009]40号中的“善意且无过失”并非是一个无意义的重复(4)例如有学者认为:“‘善意且无过失’,这是一个无意义的重复。因为如果将善意理解为非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而不知,则‘无过失’必然包含着相对人为善意。”陈甦.民法总则评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1231.。因为“无过失”并非当然包含“善意”这一要素,相对人“无过失”的判断标准为客观上是否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5)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无过失”表现为合理的注意义务,具体标准为相对人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有无要求行为人出示任何与本人有关的身份证明或授权文件、有无审查授权文件中约定的代理权限、有无对身份证明或授权文件存在的疑点征询本人。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536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734号民事判决书。,而“善意”的判断标准为“具体相对人”的主观样态(6)王浩.“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之重构[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4):182.。因此,“善意”且“无过失”两要件缺一不可,二者交集部分构成表见代理的主观要件,其准确含义为“相对人无过失地不知行为人无代理权”。但是,仅就“无过失”这一评价要件,不乏实体法学者认为,相对人被评价为“无过失”的积极事实的外延具有广泛性,若要求对其完全举证,将减损表见代理制度之功能(7)杨代雄.表见代理的特别构成要件[J].法学,2013,(2):66.。为减轻相对人的举证难度,避免因成立表见代理的门槛过高而危及交易安全,程序法学界分别以证明责任的倒置、优势证据规则为理论根据予以回应。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阐述并分析其可行性。
(一)证明责任倒置能否解决“证明难”的问题?
法谚有云:“为主张之人有证明之义务,为否定之人无之”(affirmanti non neganti incumbit probatio)。这一规则旨在排除否定事实方负担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在证据法上,由这一规则派生出的另一项规则是“主张积极事实之一方有证明义务,主张消极事实之另一方无之。”(8)骆永家.民事举证责任论[M].中国台北:台湾省商务印书馆,1995.72.该规则又称作消极事实规则。施以相对人对“无过失”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是否违反消极事实规则、造成举证困难从而危及交易安全?
具体而言,坚持消极事实规则,并主张通过证明责任的倒置使被代理人对相对人“有过失”承担证明责任的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以相对人证明其“无过失”的义务不利于交易安全,具体表现为与信赖保护原则的背离。表见代理制度主要以“实体法的趣旨”以及“基于实体法的价值判断”是证明责任分配的标准;合同法乃至民法整体的趣旨是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因此由被代理人对相对人“恶意或有过失”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提升表见代理成立的可能。若相对人举证证明自己无过失,则可能产生总有一些疑点无法举证加以排除的不公平结果,表见代理旨在保障交易安全的功能将难以实现,不利于贯彻外观主义原则(9)胡东海.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质性原则[J].中国法学,2016,(4):299.。
其二,“无过失”在性质上属于消极事实,外延具有不周延性。如果赋予相对人对该要件事实以举证义务,极易产生证明危机,导致个案不正义(10)陈贤贵.论消极事实的举证证明责任——以《民诉法解释》第91条为中心[J].当代法学,2017,(5):34.。既然如此,消极事实为“无”而非“有”,在客观上无法积极证明,故而主张事实“无”之当事人无需举证;若对方当事人提出“有”之抗辩,应视为证明责任的倒置(11)杨剑,窦玉梅.论消极要件事实的证明——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础[J].法律适用,2007,(7):55.。
可以发现,上述支持倒置证明责任于被代理人的论述,都是基于“消极事实在客观上无法积极证明”“信赖保护”“外观主义”等前提,采用的多是目的论解释的分析方法,对相对人承担“无过失”要件的证明责任进行实体法政策之价值判断上的否定评价,即通过法律要件分类说推导出的相对人需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的结论违背外观主义原则,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
实际上,上述理由所根据的“肯定者负举证义务,否定者无之”规则,是一个早已被纠正的错误。“因为证明困难并非不可能举证,这些因素绝不会改变我们的证明责任规则(Beweislastsatz)。”(12)[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第五版)[M].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395-396.何况,尽管无过失是一种法律评价(13)“消极事实亦包括事实之否定及状态,例如当事人恶意、无过失均可作为消极事实,为证明责任的对象。”Vgl. Baumgärtel,Beweislastpraxis im Privatrecht, 1996,Rn.333m.w.N.,但善意相对人,仍负有对成立该评价的根据事实的证明责任(14)至于权利人需提出何种间接事实方能证明其主观上为“善意且无过失”,后文将予以详述。。目前我国证据法学理亦认为:“消极事实,可用间接证据或情况证据证明之,非绝对不能举证证明者。”(15)姚瑞光.民事诉讼法论[M].中国台北:大中国图书公司,2000.378.
消极事实规则既然已被现代证据法所扬弃,那么在分析证明责任倒置有无正当性时,其依据首先应当是实体法规范的文义和结构。只不过,若单个条文表达与立法者意图相悖,则证明责任的分配应以立法者的价值判断为准。基于各国立法政策的不同,《德国民法典》对“善意且无过失”要件实行证明责任倒置的立法例于我国不具有充足的借鉴意义。在德国,其民法典第173条“于…不适用之”( finden keine Anwendung)的但书结构表明,“相对人明知或应知代理权消灭”为阻碍表见代理成立的权利妨碍事实,被代理人应当就此承担证明责任;鉴于证明责任本质上是一种危险或不利益,该条所蕴含的价值判断为意思自治利益应当让位于交易安全利益;因此,这与《民法典》第172条所蕴含的相对人对“善意且无过失”要件承担证明责任的结论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相对人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还是本人证明相对人“恶意或有过失”,证明责任的配置都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判断;何况与采纳 “双重要件说”(16)尹田.我国新合同法中的表见代表制度评析[J].现代法学,2000,(5):116.的德国法不同,仅从立法论观之,我国《民法典》第172条并未确定本人过错为表见代理的独立要件,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表见代理成立的“门槛”。从这个意义上说,由相对人自证其“无过失”不失为避免表见代理规则滥用的一种手段。故此,《民法典》第172条施以相对人对“无过失”要件证明责任的路径,在保护本人意思自治、避免外观主义泛化和滥用问题上具有明显优势。恰如崔建远教授所言:“外观主义所运用的领域有限,只得适用于当事人对该外观有理由地产生信赖,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场合;在民事代理关系中,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应属‘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依意思自治及不得擅自干涉他人自由及事务的原则,任何人都不得自作主张以他人名义从事代理行为并将法律后果交由他人承受。”(17)崔建远.论外观主义的运用边界[J].清华法学,2019,(5):6.在此意义上,施以相对人证明责任是防范其利用不当的诉讼策略(abusive litigation tactics),以损害对方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己利益的程序机制(18)滥用诉讼策略是指一方当事人以损害对方当事人合法利益为动机,最大限度实现自身经济利益。See Michael A. Crain , William S. Hopwood , Carl Pacini & George R. Young eds., Essentials of Forensic Accounting , 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 Inc.,2015, p.107-120.。只有相对人证明其信赖有理由,表见代理才能成立(19)如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引言部分第三自然段末尾指出:“从现行法律规则看,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
有学者支持证明责任倒置的一大理由在于:“如果相对人举证在实施法律行为时代理权之存在或其范围不存在疑点,难度很大,因为可能构成疑点的因素是无数的,他需要逐个举证加以排除,这样的举证行为是无穷尽的,任何人都不得加以排除。”(20)杨代雄.表见代理的特别构成要件[J].法学,2013,(2):70.诚然,相对人被评价为“无过失”的间接事实之外延具有不可穷尽性,若要求对其完全举证,未免过于苛刻。但是,这不能成为采取证明责任倒置技术的论据,证明责任的减轻并不最终导致证明责任的倒置。为了避免新的利益失衡,倒置技术的运用应具有“谦抑性”;当出现证明困境,出于价值取向的考虑,法官首先应当遵循实体法的规范文义(paradigm context),然后适用证明责任减轻制度来尽可能地认定事实;只有在穷尽所有证明责任减轻的技术,但仍然无法实现具体正义时,才能例外地倒置证明责任(21)除非在特定类型的案件中,直接改变证明责任分配的制度规范是不符合真理的,也超出了当事人的合理预期。Dare,Tim & Kingsbury Justine,Put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in Its Place: When Are differential Allocation Legitimate,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 Vol46 , p.503-518(2008).。
综上,构成“无过失”这一消极评价的事实应当由主张表见代理成立的相对人负担证明责任。与此同时,为适当减轻相对人的举证负担,裁判者可采取证明责任减轻之技术,而非证明责任的倒置。
(二)优势证据规则能否解决“证明难”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2月25号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新证据规定》)删除了《原证据规定》第73条第1款确立的优势证据规则;其删除该条文的意旨为统一民事诉讼的证据采信标准,避免法院仅仅适用《原证据规定》第73条第1款,只对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进行简单比较,忽略优势证据须达到高度盖然性这一最低限度。
尽管如此,优势证据规则在我国民商事审判实践中的适用情形不乏,而且,法院多认为,采取优势证据规则衡量当事人举证是否满足,是根据案情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减轻当事人对消极事实举证难度的方法之一。譬如针对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中 “不为公众所知悉”要件事实(2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337号民事判决书。、表见代理纠纷案中“善意无过失”要件事实(23)参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6民终3309号民事判决书。、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损害额”要件事实(24)参见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金商终字第1817号民事判决书。,法院均可利用优势证据规则,以减轻权利主张者对此的证明负担。但本文认为,在我国证明标准体系下,优势证据规则与证明责任减轻制度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证明责任减轻制度有其独立的适用范围与制度优势,所谓的优势证据规则不足以解决证明难问题。
第一,证明标准不同。我国的优势证据规则与证明责任减轻制度所采取的证明标准不同。《原证据规定》第73条第1款是基于“高度可能性”来判断待证事实的,这种证明标准对待证事实的确定性要求是 “极有可能”“十之八九”;而证明责任减轻所针对的证明标准,恰恰是沿着从“高度盖然性到较高的盖然性,再到证明责任的转移”这样一条脉络逐渐弱化(25)张卫平.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243.。在代理合同纠纷中,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时,往往会出现对自身主观上“无过失”的举证困难;《原证据规定》第73条第1款仅针对相对人的举证相较被代理人在证据的数量、形式、内容上具有优势,且相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较为完整证据链的情形;而那些可能预见、属于代理权存在或其范围的疑点,如果无法由相对人举证加以排除,则不能适用《原证据规定》第73条第1款;证明责任减轻制度正是用以解决这一问题。
具体而言,我国优势证据规则有别于普通法上的优势证据规则,两者所循证明标准与功能存在根本差异,原因在于:普通法上的优势证据又称为证据之优越(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意义在于实现诉讼便捷;有鉴于此,举证责任区分为“证据提出责任”与“说服责任”;前者旨在使法官相信有一个“真正的事实争点”,并将此争点交由陪审团认定,后者以优势盖然性为证明尺度,旨在使陪审团相信主张事实为真的可能性大于不真实的可能性(more likely than not),即事实发生的概率应高于百分之五十(26)Murphy, John W. Jr. Evidence—Burden of Persuasion,Kentucky Law Journal, Vol. 42,p. 258-266(1953).。只有在例外情况下,优势盖然性标准才不被适用。譬如,在惩罚性赔偿领域,为避免误判及于无辜的人,陪审团认定原告主张的事实为真,或采取高度可能性标准(27)据统计,若以数值来代表美国民事诉讼中的高度可能性标准的证明度,可粗略地以70%至80%加以表示。McCauliff, C. M. A. Burdens of proof: Degrees of belief, quanta of evidence, or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Vanderbilt Law Review, Vol.35, p.1293-1335(1982).(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或采取超越合理怀疑标准(28)在普通法中,超越合理怀疑证明标准适用于惩罚性赔偿领域的频率远远低于高度可能性标准,原因在于法院采取前者来约束权利主张方属于“知其不可而为之”,不能为原告所接受(least likely receive)。William Douglas Woody & Edie Greene. Jurors’ Use of Standards of Proof in Decisions about Punitive Damages,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Vol.30,p.859 (2012).。总体上,出于标准确定性和诉讼便捷的考虑,美国法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持一种较为宽松(lenient)的立场(29)Dominique Demougin & Claude Fluet ,Rules of proof, courts, and incentives,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39,p.21(2008).。恰如有比较法学者所指出的,普通法的诉讼目的在于纠纷解决,裁判者应当采取“一个较为公平且较有效率地捕捉个案真实的证明度”(30)See Ewald,William ,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 (I): What Was It Like to Try a Ra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Vol.143,p.1889(1995).;而大陆法系的诉讼目的在于权利保护,因此司法裁判的正当性通常取决于法官对待证事实形成“内心确信”(31)吴泽勇.“正义标尺”还是“乌托邦”?——比较视野中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J].法学家,2014,(3):149.;但基于例外情况下降低证明度的考虑,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亦确认了在表见证明等场合,优势盖然性可作为衡量证明尺度的依据(32)[德]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11.。
通过比较得知,普通法以优势盖然性作为原则性证明尺度,这就解释了普通法为何不需要另行设立证明责任减轻机制的原因所在。然而,与之不同,《原证据规定》第73条第1款并不具有此种证明责任减轻之功能,该条中的“证明力较大的证据”必须建立在达到高度盖然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简单的比较。由此,在涉及表见代理的民事纠纷中,即使相对人对表见代理的主客观要件予以间接证明,证明义务依然不得转移。这样一来,相对人亦无法从证明困境中摆脱出来。因此,《原证据规定》第73条第1款本身并不能解决证明难的问题。
第二,认定“待证事实得到证明”的方法不同。就优势证据规则而言,“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事实能否认定,应用相对人提供的证据与被代理人对反对事实提供的证据进行证明力上的比较。然而,对于证明责任的减轻,信赖有理由的判断标准为——相对人能否在初步举证阶段,利用间接证明途径,来证明合理信赖这一评价根据事实的存在;如果客观上不存在有权代理的表象,则被代理人根本无必要举证;显然,两项制度的证明方法不同。
第三,法律后果存在差异。实务通行做法认为,适用优势证据规则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衡量后,如果双方证据支持的事实均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法院应当依据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作出裁判,由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此过程中,主要事实是否存在的举证责任仅由一方当事人负担。然而,对于证明责任的减轻,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分配于原告、被告之间。理由在于,若原告依较高盖然性对主要事实完成初步举证,则被告对反对事实即负有证明义务(33)譬如在“深圳市前海龙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厦门友连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上诉案”中,证明责任减轻技术采纳与否决定了原告是否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民终14131号民事判决书。;在我国台湾地区,诸如此类通过由“原告负初步举证责任”转变为“被告负举证责任”之举证架构,来解决原告的证明困难、促使案件“争点事实”特定化,最终实现法院审理效率的案例并不少见(34)如我国台湾地区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指出的,“衡之举证责任分配之公平性及合理性,再审被告举证困难,应转而由否认其事之再审原告就其受益有何法律上原因之积极事实负举证责任,始为适当。”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89年台再字第63号民事判决书。类似案例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1年台上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而这些案件显然都不能适用优势证据规则。如此,在我国证明标准体系下,优势证据规则无法解决表见代理纠纷中相对人“证明难”的问题;该规则无法替代证明责任减轻的制度功效。
(三)小结:以证明责任减轻的运用为路径
针对“无过失”之消极评价事实,只能解释为主张表见代理成立的相对人负担证明责任。由此引致的“证明难”问题,证明责任减轻制度为其解决路径。比较不同制度间的功能可知,在《民法典》172条所示的案件中,证明责任减轻制度的运用在实现权利保护与纠纷解决之联动方面具备明显优势:一则赋予相对人凭借“定型化的事态经过”来间接证明主要事实存在的途径,相比证明责任的倒置,有利于兼顾本人的意思自治利益,避免外观主义的泛化与滥用;二则巧妙地采用了“若相对人对合理信赖完成初步举证,则本人须举证相对人恶意或有过失”之分阶段分配举证责任的技术;与我国法语境下的优势证据规则相比,在凝聚法庭辩论争点、缩小审理范围上具有明显优势。
三、本人可归责性系无过失要件的事实推定因素
证明责任减轻的技术主要包括不负有证明责任一方的事案释明义务、证明妨碍、表见证明(prima-facie-Beweis);前二者仅适用于“信息偏在型”案件中,法理基础为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的诉讼协力义务;后者的适用范围不局限于“信息偏在型”案件,它减轻举证负担的功能是通过变更证明主题——从主要事实转变为推定其存在的“定型化事态经过”来实现的(35)[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245.。在《民法典》第172条所示的情形中,证明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的诉讼资料并非完全或者主要处于本人处控制,事案释明义务与证明妨碍技术均缺乏适用基础;而表见证明技术旨在利用对非构成要件事实(Tatbestandsfremde Tatsache)的间接证明来减轻相对人的举证负担;其作用一则为对举证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帮助;二则旨在避免因实体法上的价值判断结论过于刚性与绝对造成新的利益失衡。故此,表见证明技术为相对人举证其“有理由相信”的适格手段(36)存在学理观点认为,表见证明(prima-facie-Beweis)性质上不同于间接证明,理由是表见证明是法官以经验法则为基础,凭借典型事项的经过对主要事实存在作出的推定,相比间接证明,表见证明可被动摇(durch besondere Umstände erschüttert),不具有终局性与强制性。但笔者以为,表见证明同样是以举证人对间接事实的证明为载体,只不过该间接事实具有某种特定性;而且,表见证明的推论基础并非全然源自经验法则,本质上源于实体法上构成要件中蕴含的前提条件,由此推出的结论之盖然性并不“逊于”普通的间接证明。故此,表见证明本质上属于间接证明的一种,对方只得通过附理由的否认或间接反证加以推翻。Vgl. Musielak/Foerste, Zivilprozessordnung § 286,Rn.25 ; Zöller/Greger, Zivilprozessordnung, 30. Aufl.2014,§286,Rn.33.。既然如此,相对人需要对何种“定型化事态经过”完成间接证明,才能有条件地推定其主观方面为善意且无过失。
(一)本人可归责性不是独立构成要件
构成要件上,表见代理制度必须对此周延设计,否则极易发生被滥用,形成随意侵害本人意思自治利益的错误趋向。循此逻辑,有学者以为,《民法典》第171条第2款第3句规定了狭义无权代理中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结合第172条,可知即便无权代理中相对人为善意且无过失,也不见得成立表见代理,由此解释出表见代理实则以本人可归责性为构成要件的结论(37)孙鹏.表见代理构成要件新论——以被代理人的过错问题为中心[J].云南大学大学学报,2004,(1):81.。支持者认为,相对商事交易中的表见代理而言,民法中表见代理的成立应当有所谦抑,此举不仅以潜在的方式建立起旨在避免侵害本人意思自治利益的闸门,还填补了立法漏洞(38)徐涤宇.代理制度如何贯彻私法自治——《民法总则》代理制度评述[J].中外法学,2017,(3):699-700.张弛.表见代理体系构造探究[J].政治与法律,2018,(12):134.。而在笔者看来,此种体系解释结论谬矣,原因在于:若结合上述两项条文能够得出该结论,则必须建立在承认以下两个命题的基础上:第一,《民法典》第171条第2款第3句中相对人的“善意”等于第172条中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第二,在构成表见代理时,相对人不得主张成立狭义的无权代理。质言之,相对人的请求权只能针对本人,并无其选择自由之说。显然,目前上述命题均未获得立法层面的肯定;在学理中,不论是否赋予善意相对人以选择权(39)肯定说赞同赋予第三人以选择权,理由在于最大程度地保护无过错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黄立.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11-412.否定说认为表见代理本质为无权代理,令本人承受有权代理之后果已是对相对人的特殊保护,实无理由赋予其选择权。徐涤宇.代理制度如何贯彻私法自治——《民法总则》代理制度评述[J].中外法学,2017,(3):700.还是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的程度在表见代理中是否要求更高(40)关于表见代理中“善意且无过失”的程度是否高于狭义无权代理之争论的梳理,夏昊晗.无权代理中相对人善意的判断标准[J].法学,2018,(6):140.,都尚未盖棺定论。因此,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民法典》并未将本人可归责性作为表见代理的独立构成要件。
另外,本文认为,本人可归责性与代理权外观和本人具有关联性是不同的。例如,在无权代理人与本人为夫妻关系时,从日常经验法则的角度,一方处置对方大额资产,对方不可能不知情。此时,也很难说本人对有权代理外观的产生具有过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把可归责于本人的代理权外观作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那么将无法构成表见代理。反之,如果把本人可归责性作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当中的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的推定因素,那么在前一种情况下,相对人只要举证行为人与被代理人之间存在一种亲属身份关系,这种身份关系客观上免除了他向本人进行核实的义务,表见代理成立。由此可知,事实推定因素和构成要件是不同的,前者不是必须要由当事人举证,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对某种替代性事实的举证来达到相应目的。
(二)本人可归责性是事实推定因素
表见代理制度是以外观授权为根据,通过对私法自治原则的适度限制来彰显信赖之保护,这是比较法上的普遍共识。在表见代理构成上,传统的“单一要件说”之所以被诟病,在于其绝对地、单纯地强调相对人信赖之保护,而置本人意愿全然于不顾。为解决有权代理的假象与真实授权的错位,德国法与法国法分别以“权利表见责任”与“表见法理”为制度基础,以不同的程度来强调“可归责性”要件在表见代理构成中的作用。在德国法中,“权利表见责任”的主体,是指“以可归责于他自己的方式引发了这一权利表象之人,或者是具有消除这一表象的能力而未去消除这一表象的人”(41)[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M].王晓晔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886.;此种将本人可归责性摆至独立要件地位的模式亦被日本法所继受,并根据事实上发生有权代理效果的难易的程度,将可能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形分为超越代理权的表见代理、代理权消灭后的表见代理、授权表见型的表见代理;在授权表见型中,即便本人未曾授予行为人以代理权,但由于其故意或放任无权代理行为的发生,故仅得在相对人恶意的情况下,才不构成表见代理(42)[日]加藤雅信.日本民法典修正案:第一编总则[M].朱晔,张挺译.中国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16.574.。因此,德、日两国实际十分强调可归责性因素的地位,并已经将其定性为表见代理的独立构成要件(43)[德]卡纳里斯.德国商法[M].杨继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47-151.。相较之下,法国法则基于保护交易安全的目的,建立了独立于民事责任的表见理论(44)所谓表见理论,是指“只要相对人对代理人的授权权限形成了合理信赖,即便被代理人不具备可归责性,仍需承担有权代理之责”。[法]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法国财产法(上册)[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123.。然不容忽视,在法国法司法实践中,可归责性仍为判断相对人具备合理信赖与否的因素之一。譬如,马赛商事法庭认为,如果“签收汇票和雇员职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存在关联性,那么即使雇员事实上没有相关代理权,也可以成立表见代理。”判决中存在“关联性或者因果关系”的措辞表明,法国法将“可归责性”概念弱化为了“关联性”概念,只要本人和有权代理的外观之间具有关联,该“关联”便可以构成相对人合理信赖的客观环境要素,成立表见代理(45)罗瑶.法国表见代理构成要件研究——兼评我国《合同法》第49条[J].比较法研究,2011,(4):69.。由以上分析可知,在大陆法系,“权利表见责任”与“表见法理”之区分,其根本差异在于本人归责性能否独立于相对人的合理信赖,成为表见代理的独立构成要件。
有学者近来指出,即便用风险归责思想为本人担责寻求依据并无不当,但由于有关意思表示成立、效力的判断规则本就是对表示风险进行分配的规则,并且相对明确客观,故此,与其说将本人可归责性作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毋宁说本人作出的有效代理权通知才是表见代理成立的必要条件(46)王浩.“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之重构[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4):179-182.。但笔者认为,所谓将代理权通知作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之应有之意,无非是指客观上存在可归责于本人的代理权表象。何况,在行为人使用遗失的公章、业务介绍信、授权委托书从事民事活动、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的场合,如果一概地承认归责性因素可被代理权通知所替代,那么将无法解释此时为何能够例外地成立表见代理。如此一来,《民法典》第172条“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恰恰为可归责性留下解释的空间。就解释方法的选择,狭义的法律解释应当优于漏洞填补。这一解释结果如下:
第一,代理权外观可归责于本人系判定相对人无过失的事实推定因素,并非特殊构成要件。在民法教义上,《民法典》第172条所规定的“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实际包含以下两种规范意义:其一,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言之有据、符合常理;其二,相对人为善意且无过失;两种规范意义的关系在于,前者系后者的事实推定条件。即鉴于前一种规范意义可以涵盖本人的可归责性,因此只要代理权外观能够追溯至本人的行为或表示,相对人就可被认定善意且无过失,除非明知或可得而知行为人无代理权(47)冉克平.表见代理本人归责性要件的反思与重构[J].法律科学,2016,(1):78.。以容忍代理为例,所谓容忍代理,是指本人知道他人为其代理人,而不为反对表示的情形。尽管我国民法典未明定容忍代理制度,但实际上,对于相对人而言,除非有相反证据的存在,本人放任代理权表象的发生,当可证明其“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故此《民法典》第172条可经由解释将容忍代理纳入表见代理的范畴,其解释路径为将本人归责性作为推定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的因素,以此实现动态安全与静态安全之间的弹性制衡。
第二,可归责性属于内涵和外延相对不确定的概念,学界对其含义素有争论。既有的解释路径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细化归责类型为过错、诱因、风险,进而确定如何考虑本人因素。另一类解释路径是通过比较权衡本人可归责性与相对人信赖的合理性,对可归责性具备与否加以综合判断(48)叶金强.表见代理构成中的本人归责性要件——方法论角度的再思考[J].法律科学,2010,(5):39.。从上述路径中可以提取出可归责性的共识性特征——代理权外观与本人之间具备关联性。既有的司法实践也为这种理解提供了经验支持(4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016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5314号民事裁定书。。
四、无过失要件证明责任减轻的进路设计
作为证明责任减轻的技术手段之一,表见证明技术的要义为,以待证事实系评价根据为前提,如果特定间接事实能够表明主要事实的存在,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就无需对主要事实进行完全证明,法院可直接认定主要事实的存在。其正当性在于,从A间接事实到B主要事实的推定,并非依赖一般经验法则,而属于基于实体法的内涵及目的而进行的事实推定(50)[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463.。我国既有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表明,以间接证明为载体的表见证明技术已广泛运用于旨在缓解当事人证明负担的民事案件中,譬如在以金钱为标的的案件里,违约方举证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将之与违约金数额相比较,得出该数额超出了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所得金额30%的结论,就算完成了违约金数额过高的举证责任(51)崔建远.民法总则:具体与抽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20.;据此,表见证明技术如何及于表见代理之成立值得被进一步具体化。
(一)相对人无过失的举证进路
在《民法典》第172条所示的情形中,相对人欲使代理效果归属于本人,需证明的事实主张如下:其一,存在代理权外观;其二,与行为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其三,自身无过失地不知行为人无代理权。前文已述,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代理权表象可归责于本人系“其三”项的事实推定因素。在对“其一”“其二”项举证成功时,相对人还应当证明该外观能够追溯至本人的行为或表示。譬如,当相对人举证存在如下情形之一者,可有条件地推定其无过失:一则本人向相对人以授权表示、通知或公告形式做出了代理权通知;二则本人知晓无权代理行为而不为反对表示;三则在代理权外观存在令人怀疑的事实,或按照惯例第三人负有核实义务,例如当授权委托书存在明显错误、实施的代理行为使本人将蒙受重大不利益时,相对人已向本人履行调查核实义务。需注意,这里的相对人必须属于认识能力较高的人,譬如具备营利性、营业性、公开性和专业性等特征的商主体或专家(52)方新军.无权代理的类型区分和法律责任——《民法总则》第171条评释[J].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2):54-55.。即便与《民法典》第171条有关无权代理相对人的主观要件相比,表见代理对相对人主观要件的要求明显偏严,即采纳一般理性人的标准,但出于交易成本的考虑,相对人并不负有普遍意义上的调查核实义务;如果一概课以其调查核实义务,那么在一些以金融机构理财“飞单”纠纷为典型的实例中,作为普通储户的相对人就不得不因未向本人核实“工作人员”身份的真实性,无法就成立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的主张获得支持,仅可在行为人满足职务犯罪条件时,向本人主张过错赔偿责任(53)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民终1410号民事判决书。。如此一来,普通储户实际成为金融机构组织风险的“埋单”者,而且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将代理界定为一种“形式化”交易资格的理念不符(54)如在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316号民事判决书中,最高院提审认为,即便在本人的营业状况、股东结构、工商登记已发生重大变更的情况下,相对人未就此向本人调查核实,但由于行为人在订立本案抵押合同时提供了被代理人股东大会决议原件,该原件与此前签订类似抵押合同的完全一致,故相对人完全有利有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表见代理成立。。故此,相对人对自身“无过失”事实主张的举证,通常不以已就代理权有无进行调查核实为证明对象,除非本人举证其认知能力高于一般理性人。
彼时,本人欲阻却表见代理的法律效果,则必须举证相对人为恶意或有过失。这样一来,表见证明技术一则赋予相对人对“无过失”这一评价事实予以间接证明的途径,避免了“强相对人举证之所难”的局面;二则通过分阶段分配举证责任的技术,迫使本人在抗辩抑或否认时因忌惮举证不能遭致的败诉后果,积极主张并证明“有过失”的疑点,以促成法院总结争点,纠纷解决更具实效性。
(二) 本人对相对人有过失举证的性质及标准
在证明标准上,有观点以为,本人对相对人“有过失”之事实主张的举证仅仅旨在推翻前述间接证明的前提,使其再度陷入真伪不明,是以即便表见证明技术能够发生证明责任的“转换”,但由于证明责任存在着客观证明责任与主观证明责任的划分,前者独立于每一个诉讼并从拟适用的实定法中推知,后者仍属于自由心证的射程范围且与分配败诉风险的结果无涉,故此本人举证相对人有过失,性质上属于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应当适用反证的证明标准,即将原先事实推定的结果拉回至真伪不明即可(55)包冰锋.间接反证的理论观照与适用机理[J].政法论坛,2020,(4):126.。但笔者以为,这种表述不甚准确,未能点出间接反证与附理由否认的不同。在待证事实系评价事实的场合,基于证据的非穷尽性,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无法利用直接证据证明主要事实的真实性,仅得利用间接证据推认主要事实的存在;反之,对方当事人为避免因间接本证的成功而自己惨遭败诉,有必要提出附理由的否认或抗辩;不同于附理由否认直接针对请求原因事实本身,抗辩正是依托于间接反证之过程,其包含对对方请求原因事实的肯定,所反驳的仅仅是请求原因事实的法律效果(56)占善刚.民事诉讼中的抗辩论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38.;而且,“如果间接反证所指向的其他事实能够构成推论的基础,那么,这些事实必须是积极的、肯定的,仅就该点而言,提出反证的人必须对此承担纯粹的确认责任。”(57)“只要能够证明所称事实的初步证据或间接证据(Indizienbeweis)是确凿的,主要事实存在的推定才具备正当性。”Vgl.BGH NJW 2010,363(364).故此,以间接反证为载体的抗辩性质上属于本证,其证明度须满足高度盖然性的要求。如此一来,本人对相对人有过失的举证证明度就不可一概参照反证的证明标准,而应当根据本人对请求原因事实的攻击路径来分别界定:一方面,如果本人的反驳与举证系直接针对间接本证中请求原因事实本身,那么,该攻击手段的性质为否认,应当参照不负有证明责任一方事案解明义务的证明标准,以恢复至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为最低限度(58)袁琳.证明责任视角下的抗辩与否认界别[J].现代法学,2016,(11):192-193.。另一方面,如果本人的反驳内容不排斥客观上存在有权代理的表象,而是以“另辟蹊径”的模式排斥有权代理的法律效果,那么,该攻击手段的性质为抗辩,应当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譬如,在委托代理合同被撤销场合,本人举证已及时地向相对人发出撤销代理权的表示、通知或公告等间接证据,以此证明相对人的“不知情”有过失(59)“若待证事实系可归责性要件事实,被代理人欲反驳此前间接证明的结论,可通过提出存在其他非典型事项经过的方式来证明无可归责性之事实。”Vgl. Arens/Lüke, Zivilprozessrecht, 6.Aufl.,1994,Rn.281.。
五、余论
《民法典》第61条第3款规定:“法人章程或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关于对此条的理解,存在来自判决、司法解释、专家、学者的声音认为,判断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表,应当遵照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来予以解释,其理由无外乎是基于我国现行法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有关表见代理构成、法律效果、举证责任的解释,自然可运用于表见代表范畴之中。循此逻辑,结合前文结论,推论出第61条第3款所蕴含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如下:第一,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相对人为证成“该合同对法人发生效力”之事实主张的真实性,必须举证证明客观上存在可归责于本人的代理权表象;第二,本人为反驳该合同对其发生效力,要么直接举证相对人恶意这一权利妨碍事实;要么通过附理由的否认来直接排斥原告的诉由本身;要么通过间接反证,举证其他能够证明相对人“有过失”的事实存在。
显然,依据罗森贝克规范说,以上举证责任分配结论与《民法典》第504条存在难以调和的体系矛盾。之所以产生这一矛盾,在于该理解没有从编纂、理解《民法典》必须摆正民法与商法之间关系的角度,区分民事代理与商事代表制度在规范意旨及功能、构成、法律效果以至举证责任方面的不同。具体而言,民事代理以保护本人意思自治为导向,强调任何人都不得自作主张地以他人名义从事代理行为并将其法律效果交由他人承受;所谓外观主义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其例外与补充;这一“不得已”的情况恰好凝聚为《民法典》第172条中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要件;故此,民事无权代理正是以狭义的无权代理为原则,以表见代理为例外;与之相异,商事代表制度以外观主义为导向,受保护交易安全目标的驱使,法定代表人在法人业务范围内从事的民事法律行为直接对法人发生效力;持法人“拟制说”者甚至认为,即便法定代表人实施越权行为,但由于法定代表人在履行职务时与法人人格合而为一,故在商事代表中不存在代表权的“表见”,更不会发生无权代表(60)崔建远.论外观主义的运用边界[J].清华法学,2019,(5):15.。且不论法人与法定代表人是否具备同一人格,在法定代表人实施越权行为,并与相对人订立合同的场合,如果遵照表见代理的构成及举证责任分配,那么,即便可相对人用证明责任减轻的途径来“释压”,仍不排除其对可归责于本人的代理权表象担负客观意义上证明责任之一事实,而且,相对于本人嗣后对其“有过失”进行举证而言,相对人实际负担着就自身“无过失”率先进行间接本证的义务。如此,于被代表人不免过于优惠,亦难以契合商事外观主义的价值取向。
为此,不妨根据《民法典》第504条的表达措辞,凭借其中规则与例外的关系,来说明何谓成立表见代表的权利创设事实与权利妨碍事实:一方面,作为表见代表成立的权利创设事实,相对人一则须举证证明其与法定代表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二则须举证证明法定代表人越权外,双方达成的合意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其他有效要件;另一方面,作为妨碍有权代表效果发生的权利妨碍事实,被代表人要么举证相对人明知越权事实,要么举证相对人未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即因过失而不知法定代表人越权。是以与民法上的表见代理相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