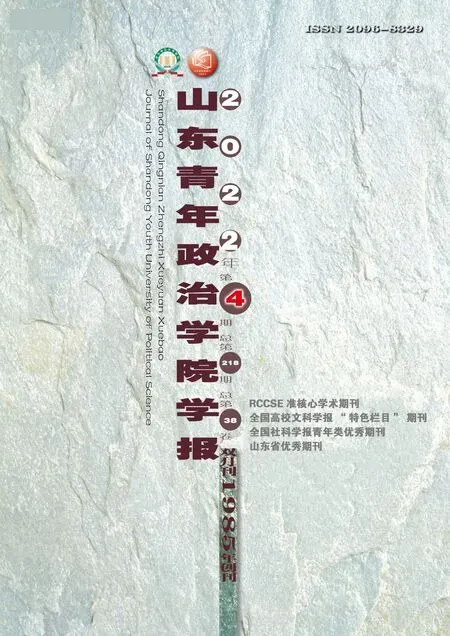因声致诚:董仲舒“深察名号”新论
张晓周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济南 250100)
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因建构了包含信仰、政治哲学、伦理等在内的经学体系,其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被汉廷采纳等贡献,而被史书尊为“群儒首”“儒者宗”。董仲舒实为春秋公羊学家,作为通经致用的经学家,他借助经学的诠释与体系建立了儒学的系统。董仲舒在建构其理论时,使用了“深察名号”的“正名”方法,深入考察、探究名号的内涵与意义。他说“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1]董仲舒是从治理天下的角度来论述“深察名号”的:他认为治理天下的第一步就要审视、辨析事物的大纲,而辨析事物的大纲就在于“深察名号”。因为名号,是事物、大道理的总纲。董仲舒给出了“天子”“士”“民”“祭”“王”“君”“性”等名号的系统说法。需要追问的是,董仲舒为何提出“深察名号”?该方法在其经学、儒学体系中发挥了何种作用?这不仅是董仲舒的问题意识,亦是本文的问题所在。
一、因声求义:“深察名号”信仰与理性的双重维度
“深察名号”常被视作董仲舒对孔子“正名”思想的发展,并且被他运用在政治哲学、人性论等领域。侯外庐[2]、冯友兰[3]等人虽持有唯心唯物二分的意识形态视角,但已经从逻辑、概念、分类的角度对董仲舒的“正名”思想进行研究。徐复观从训诂的角度认为该正名内容“有的可以成立……更多的是牵强附会”[4],不过他强调董仲舒的正名思想是纳入到其天的哲学系统里去的。李泽厚尽管没有具体研究“深察名号”,但其运用“理性与非理性”[5]的视角重新评价与褒奖董仲舒思想。该视角同样适用于对“深察名号”的考察:“非理性”部分指向董仲舒的神秘主义,反映了董仲舒的信仰维度,而“理性”主要指“实用理性”。张祥龙主张“深察名号”是董仲舒的语言哲学,前者借用印度教的《奥义书》诵“名号”以通达“梵”“大我”的方法来佐证“深察名号”的哲学意涵,并引用莱布尼茨对汉字的理解,得出结论“董仲舒意义上的‘名号’,其真正‘大端’——其本原——就在阴阳五行的卦象名号和思想名号里头”[6]。这种考察与结论同样极富启发性。
董仲舒在“深察名号”中大量运用声训方法。声训作为训诂学的根本要义,到了清代段玉裁、王念孙等乾嘉学派训诂专家又被重新地理解与说明。训诂方法分为声训、形训与义训。根据王力的研究,从许慎时代到段玉裁、王念孙的时代,“重形不重音的观点,控制着一千七百年的中国文字学”[7]。即从汉到清的一千七百年间,声训并没有被重视。这种局面直到乾嘉学派时期才得到扭转。段玉裁言:“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8]对于经学的研究,最重要的莫过于求得其义理,而要获得义理最关键迫切的就是要掌握住文字的发音。王念孙又云:“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9]文字不仅有发音,还有字形。王念孙直接认为训诂的根本宗旨起源于声音,并主张通过古音来求得文字的含义:以声音为线索,引而伸之,触类旁通,不限制于或者要超越文字的字形。正如王引之所说:“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10]声音便是指有声语言,而文字则指字形。乾嘉学派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区分了语言与文字,并认为“文字不是直接代表概念的,而是通过有声语言来代表概念;有声语言是文字的物质基础”[11]。乾嘉学派主张必须通过“有声语言”来唤起文字之义。“有声语言”是文字的根本,而文字乃是“有声语言”的标记符号,发声相同或相近的字之义可以相通,这就是“因声求义”的要旨。“深察名号”当中便有许多这样“活生生”的例子,如“士者,事也”“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12]等。从“因声求义”的角度来看,“事”与“士”音同,故义可相通;“王”与“皇、方、匡、黄、往”的发音相近或相同,后面五个字就可用于训释“王”。皇有大、盛大,古代“三皇”应当就已经蕴含着“王”的意思。“方”指王道的“正直而方”,可以升华为大中至正的境界。“匡”有“正”之意,依照董仲舒的观点,王正而天下正,以王之正而正诸侯大夫、天下之治。黄作为一种颜色,得到古代经典的大力推崇,如《周易》就明确主张由“黄中通理”而上升到至美的境地。在中国传统中,黄色是皇家贵族专用之色,皇帝的龙袍就是黄色。“往”指“王”能够往来四方,而王道的实行亦能够吸引四方民众前往。董仲舒对“王”的五种解读,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立体地理解“王”了。
通过“因声求义”的训释方法,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考察“深察名号”之深意,即“名号”的根本到底是什么。董仲舒强调探求事物之根本,如在《奉本》篇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13],视天地阴阳为礼之本。这种重视事物根本的思路贯彻于董仲舒的整个思想体系当中,“深察名号”也不例外。“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14]“謞”与“效”的发音相同,指大声呼喊、吼叫。古时候的圣人,大声呼喊而效法天地就叫作“号”,鸣叫而给万物命名叫作“名”。名号的发声虽然不同,但它们的根本都指向天意,所以圣人通过鸣号而通达、领会天意。名号——有声语言——天意,构成了溯源求本的链条,而有声语言成为接通名号与天意的桥梁。有声语言是名号的根本,而天意又是有声语言的根本。通过“謞”“鸣”出名号的声音,就可以通达名号之义,该义再升华一步就是天意。董仲舒把名号之义溯源于天意透显出了其对“天”的信仰。在董仲舒的体系中,“天”是“人心信仰的源出”[15]。信仰是一种情感、信念,信仰与理性不同,它属于人类的非理性部分。信仰往往难以明晰地表达与论证。理性对应着知识,而信仰与知识是不同的地盘。正如康德所言:“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16]康德明确了如何处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悬置、限制理性与知识,以避免它们对信仰的干扰。不能用理性检验乃至批判信仰,也不能用信仰检验乃至批判理性。两者互补而共同组成人类的构成要素。信仰在董仲舒体系中表现为天意、感应、祭祀等范畴或活动。
“深察名号”中除了有信仰维度的意涵,还有对“名号”理性诠释的部分。先来看对“士”的训释:“士者,事也”。在《尚书·康诰》中“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此指周公谋划营建东都洛邑之时,侯、甸、男、采、卫邦国的诸侯、百官和臣民等都来朝见周公,服事于周王室,这里的“士”即为“服事”,译注者明确地认为“士,与事通用”。[17]由此可见,“士者,事也”训释具有经典依据。
再来看对“王”的训释,它同样能够找到古代文本的支撑。在《诗经·周颂·桓》“于昭于天,皇以间之”,其意为:周武王的功德大业辉煌光耀于天,他代替殷纣成为新王。此处的“皇”指周武王,便释作“君王”或“王”之意。质言之,“王”与“皇”可以互训。《诗经·豳风·破斧》:“周公东征,四国是皇”,此处“皇,通‘匡’,即匡正,治理”。[18]因此,“皇”与“匡”可以互训;又因为“皇”与“王”可以相通,所以“王”与“匡”亦可相通。《诗经·小雅·楚茨》:“先祖是皇,神保是飨”,“皇”被释为“往”。[19]如上一般,“王”亦可训为“往”。而对于“王者,黄也”,张世亮等人认为,黄色在五行之中为土之颜色,土居中央方位,象征君王地位;根据五行生克关系,汉克秦,秦属水,则汉为土德:由此可知,黄为贵色。[20]此种观点符合董仲舒阴阳五行理论,当为正论。苏舆认为这与《周易·文言》“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有关[21],而比照董仲舒对“黄”的诠释“德不能匡运周遍,则美不能黄”[22]来看,苏舆所论言之有理。而对于“王者,方也”,董仲舒解为“道不能正直而方”[23],本文推测此亦是从《周易·文言》“‘直’其正也,‘方’其义也”而来。通过以上的考察,董仲舒对于“士”“王”的诠释都有其经学来源、经典依据。
董仲舒对“士”“王”等名号的诠释,已不再是信仰的部分了,而是一种理性化的表现。“名号”反映了事物的真实情况,“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所以真物也。名之为言真也。故凡百讥有黮黮者,各反其真,则黮黮者还昭昭耳。”[24]“真”指事物的真实样貌或意义。“名号”即产生于并用来言说事物之“真”。如果不“真”的话,那就不能用“名号”来命名。所以凡是幽暗模糊的事物,只要还原到它的“真”,那么幽暗模糊的也会变得清晰明白起来。“名号”反映事物之“真”就是其理性的部分,它经得起分析与论辩,尽管这种理性往往被称作实用理性。
实用理性还表现在对于“字”的训诂与“正名”的关系处理上。郑玄在对《论语·子路篇》的注释中云:“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为之字。”[25]按郑玄说法,“正名”也就是“正字”。江沅接续郑玄的思路主张:“孔子曰‘必也正名’,盖必形、声、义三者正,而后可言可行也。亦必本义明,而后形、声、义三者可正也。”[26]“正名”就是正“字”的“形、声、义”,而且必须明确字的本义,而后才能正字的“形、声、义”。董仲舒在“深察名号”中,主要从“声”的方面对“名号”之本义进行追溯与正定,与郑玄、江沅的思路非常相似。因此,董仲舒通过“因声求义”的方法,从“正字”转而达成“正名”,是经得起理性论辩的。
二、至诚之道:理顺天人关系,确立礼乐秩序
董仲舒“深察名号”的方法旨在理顺天人关系,确立礼乐秩序,其论述皆不离开“天人之际”框架以及礼乐制度的设计。如他对“天子”“士”“民”“祭”“猎禽兽”等名号的考察,无不是想在天人关系与礼乐秩序中给予它们以恰当的意涵与规定。即便是对“性”的探讨,也是这样:“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27]他对“性”“心”“身”的正名亦是放在了天人关系之中,并最终落实为礼乐教化对人性的改善。他在《深察名号》中对天人关系直接表述为:“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28]在董仲舒看来,各种事物的名号是圣人按照天意而取的。表面上看,在事与天之间是由名号而贯通的,但是名号经由圣人而取,因此,事与天之间本质上是由圣人来沟通、接通、贯通的。由事到名、由名到圣人、由圣人到天,依次贯通,从而形成圣人所取名号来自天意,而天意又是通过圣人而彰显,使得天与人合二为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这在董仲舒的经学天人之学中得到了大量论证与发展。通过新旧“天人合一”的发展脉络来呈现董仲舒所处的历史语境,可以更加明晰他的运思理路。
新旧“天人合一”的提法出自余英时的《论天人之际》一书。余英时认为“轴心突破”时期的诸子学派思想家、哲学家通过建构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新“天”,取代了传统礼乐传统中巫文化主导的旧“天”;前者被称作以“内向超越”为特色的“新天人合一”模式,而后者则名为“旧天人合一”模式。余英时强调,“轴心突破”之后,新旧“天人合一”的两种模式处于并存、交互状态,如汉武帝的“巫蛊事件”。①余英时的观察对于审视董仲舒的“深察名号”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董仲舒去世十多年后,发生了“巫蛊事件”,那么董仲舒处在新旧“天人合一”并存的时代,其思想方法与思维模式具有新旧的双重烙印与维度。
在礼乐传统中,“旧天人合一”是通过巫觋和巫术完成的。巫觋是唯一能够沟通天与神的特殊群体,他们成为帝王最信赖的助手,而帝王实际上便是“巫觋之首”[29]或者就是巫觋本身。巫觋成为“天人”之间的通道,天与人之间的“合一”也就集中在了巫觋身上。巫觋通过一整套祭祀仪式沟通天人,“旧天人合一”也就体现在该仪式上。这就是董仲舒为何在讨论“享鬼神者号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蒸”[30]之后,提出了上面提到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结论。祭祀是礼乐传统中的核心要素,既然“旧天人合一”是通过祭祀完成的,那么这些祭祀“名号”的本义就指向祭祀本身,而祭祀则进一步体现、导向“天人合一”的关系,这是其一。其二,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祭祀活动有大量详细的描述,比如“求雨”“止雨”等仪式。显然,他对于这些祭祀仪式都是了然于胸的。仪式包含巫师的歌舞,这种歌常以“号”的形式被巫觋表现出来。根据陈梦家的考证,“巫之所事乃舞号以降神求雨……名其求雨以祭祀行为曰雩”[31]。巫觋在名为“雩”的求雨仪式中,是通过歌舞、鸣号来达到降神求雨的目的的。巫师之“号”或许是董仲舒“謞而效天地谓之号”的重要来源,只不过董仲舒之“号”的发出者已不是巫觋,而是圣人。即使“深察名号”的“号”外在形式类似于或者根本就是巫觋之“号”,但其发动者已然是圣人了。圣人与巫觋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巫觋在“旧天人合一”传统中具有核心地位,而圣人通过哲学体悟或修行方法在“新天人合一”中取代了、至少极大地削弱了巫觋的地位。由此可见,必须从这“天人合一”新旧模式两个角度来考察董仲舒的“深察名号”,才能得其要旨。
余英时强调“轴心突破”之所以形成了“新天人合一”的历史范式,在于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诸子百家通过哲学思辨或个人修养的方法达成了“内在超越”,这与巫师的外向祈求迥异。比如“孟子强调‘万物皆备于我’,是为了实现‘诚’‘恕’‘仁’,即儒家的中心价值。”②而董仲舒有着同样的转向与关注,比如《祭义篇》中强调“君子之祭也,躬亲之,致其中心之诚”[32]。通过祭祀来激发君子心中之“诚”,甚至可以说以“诚”来解释祭祀礼乐传统,这已经蕴含“内在超越”的转向了。董仲舒对“诚”“仁”“义”等儒家价值的追求,不仅表现在祭祀的层面,而且还有精神修养、思辨论证的向度。在《天道施篇》中,董仲舒云“是故至诚遗物而不与变,躬宽无争而不与俗推,众强弗能入。蜩蜕浊秽之中,含得命施之理,与万物迁徙而不自失者,圣人之心也。”[33]他把“至诚”视为圣人内在修行的心灵境界,以此来拒绝外在浊秽、世俗事物的侵袭与干扰。
祥瑞作为董仲舒“天人感应”的重要环节,其运作也需要“诚”。在其第一次给汉武帝的对策中,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的核心是“诚”:“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34]三代受命,天降祥瑞,而君王之“诚”是天瑞出现的核心要素。天人之间的沟通,已然不是借助巫觋,而是通过人心之“诚”。“诚”的效用不仅如此,其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性亦是不可或缺。当汉武帝在第二次策问时,询问为何他付出了诸如亲自耕种,劝勉孝悌等一系列努力,但治理成效甚微,未让老百姓获得益处。董仲舒在对策中直言其中缘由:“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35]董仲舒批评汉武帝的诚心不足,导致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武帝亦无政治之功绩,因此建议汉武帝要“设诚”于心中,再去治国理政,如此才能向三王看齐。董仲舒把“诚”作为一种精神修养的追求目标,不仅圣人有“至诚”之心,君王也要“设诚”于心。
如果说孟子对“诚”的追求,还未把“诚”在天人关系、天人感应中的重要地位凸显出来,那么《文子》中的论述则可以帮助我们来考察该问题:“圣人象之……一言而大动天下,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故精诚内形,气动于天,景星见,黄龙下,凤凰至”[36]。《文子》的这段引文尤其重要,因为从这句话的角度来审视董仲舒的“名号”与“天人感应”思想的话,会完全排出掉巫觋、巫术的因素。这段论述足见其以“精诚”来沟通“天人”,形成了其“新天人合一”模式。董仲舒主张“天瑞应诚而至”,而他对“诚”的功能与重要性的认识和文子如出一辙。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董仲舒在《王道篇》的论述:“《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37]此处的“景星见,黄龙下”与《文子》的引文完全一致,足见董仲舒与《文子》思想的借鉴关系。董仲舒主张只有“王正”了,才能出现“景星见,黄龙下”这般的吉祥局面。王如何“正”呢?就是要君王“设诚”于心。这就是董仲舒“深察名号”的任务之一,就是对“王”的正名。而且《文子》关于语言、声音的观点——“一言而大动天下,是以天心动化者也”,亦与董仲舒“名号异声而同本,鸣号而达天意者也”相互发明。那么是否就能得出结论——董仲舒的“诚”与“灾祥”的思想就是来源于《文子》,这值得进一步研究,毕竟孔子、孟子、《中庸》等都对“诚”有大量论述。但至少可以看出,在董仲舒之前的时代,儒道两家均非常重视“诚”。
“深察名号”也反映了礼乐传统中“声音”对董仲舒的深刻影响。比如在礼乐文明发达的商朝非常重视声音,有“殷人尚声”的说法:“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礼记·郊特牲》)《史记·乐书》对“音”与天地之间的关系表达得更为明晰:“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38]前者只是表达了声音与天地之间的模糊关系,而后者则把声音当作天与人相接通的媒介。此两处虽还不像董仲舒所言“鸣号而达天意”,但声音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在礼乐传统中有其重要的地位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如果非要追溯其思想根源,则要寻到《周易》:如《中孚》九二爻“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中孚·彖》“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文言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孚”乃信之意,信又为诚,故在《周易》中已经大量出现“天人感应”“同声相应”的思想,其内在逻辑也蕴含着“诚”的要素。这或许就是董仲舒“同而通理,动而相益”[39]的思想来源。
三、感通与立象尽意:“深察名号”的运思方式
据王力的研究,声训在汉代之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如《周易·说卦传》:“乾,健也。坤,顺也。坎,陷也。离,丽也。兑,说也。”[40]乾、坤、坎、离与兑为卦名或卦象,它们象征的物象依次为天、地、水、火与泽。即天有健之义,地有顺之义,水有陷之义,火有丽之义,泽有说之义。《周易》与其他文本的一个重大不同就是通过“立象尽意”,即立卦象、物象来阐述圣人之意。《周易·系辞传》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普通的书籍并不能穷尽所欲表达之言,而言又不能穷尽所要表达之意,因为该种文本只有文字、字形。《周易》与此不同,圣人是通过卦象、物象来穷尽其意的,与卦爻象对应并蕴含着物象的卦爻辞亦能够穷尽所要论述之言。卦爻象与纯粹的文字不同,它打破了文字表意的局限,能够符示、象征多种意涵。如,乾卦既能符示健,又能象征马、首、天、圜、君、父、玉、金、寒、冰等物象。(《说卦传》)这是《周易》之象的强大表意功能,也彰显了《周易》的思维方式。
王树人为了给中国传统思维“正名”并与西方“概念思维”相区别而提出“象思维”。他认为,“象思维”奠基于《周易》,主要集中表现在“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观物取象’的思维与西方概念思维根本不同之点在于,‘象’不是不动的实体,不是用定义可以规定的概念,相反,‘象’是‘非实体’的、‘非概念’的,也就是具有非对象性和非现成性的特点,因此‘象’是借助概念用理性和逻辑所无法把握的。”[41]“象思维”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象的流动与转化”,这种“流动与转化”表现在不同象之间的“异相拟,类相合,似相通”。比如《周易·乾·大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健”与“君子自强”,既是“相异之象”,又是“相类之象”,也是“相似之象”。[42]《周易》把这种“观物取象”的方式与“名”联系起来:“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系辞下传》)卦爻象之名虽然微小,但所引申喻指的物象却广大,而这其实就是“象的流动与转化”。这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维模式,这也正是董仲舒思维特色。董仲舒在《天道施篇》云:“万物载名而生,圣人因其象而命之。”[43]万物生来就承载着名号,圣人通过观其象,而命其名。他在《阴阳义篇》又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44]从“取象”分类的角度来看,天与人是合一的。董仲舒认同圣人“观物取象”的方法,由此而为万物进行命名。对于“天”与“人”,又从“象的转化与流动”的角度,推断两者合一的关系。由此可知,董仲舒运用了《周易》象、类、名的“象思维”方法。
在王树人看来,声象为感知之象的种类之一。董仲舒在诠释“王”之内涵时,“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就是依据“声象”的“流动与转化”,在感知、闻见的领域呈现“王”的意涵。“声象”继续“流动与转化”,继而外在的感知之象被消解,而转化为整体的意象或气象。[45]董仲舒所谓的“名号异声而同本,鸣号而达天意者也”,此一过程便经历了这一转化与升华:圣人由“名号”之“声象”升华到蕴含“天意”的气象或意象,如此就完成了“立声象以尽意”的“象思维”过程③。
“深察名号”与《周易》“象思维”关系紧密的一个有力的佐证是上文引述张祥龙的说法:“董仲舒意义上的‘名号’,其真正‘大端’——其本原——就在阴阳五行的卦象名号和思想名号里头。”张祥龙是根据莱布尼茨对汉字的认识,从而得出的这个结论,与此处借助“象思维”的思路,可谓“殊途同归”。
“象思维”是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感通精神的呈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系辞传》)无思无为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避免人的思虑、行为对领会、体悟世界的影响。蔡祥元根据现象学的视角,认为《周易》的感通是圣人克服了人的主观任意性,而把握道之象;感通是“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认知方式”。[46]圣人通过感通,能够从道的视角来观照万事万象,并在感通的基础上进行诠释。如果前者处在非理性的、信仰的阶段,而后者则是理性的阐释。这同样适用于董仲舒的“深察名号”。董仲舒所论述的天人关系,天人感应以及把名号之义追溯到“天意”,都是其对天的信仰的表现。他从声训、立声象以尽意的角度去探究名号的“语源学”之“真”,则显示出理性探求的向度。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董仲舒的“深察名号”具有坚实的声训依据,体现了董仲舒的信仰与理性双重维度。他的目的在于理顺天人关系,确立礼乐秩序,为新帝国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指导。董仲舒具有中国哲学感通精神气质,其发展运用了《周易》“象思维”、立象尽意的阐释方法。至于说“深察名号”到底有何学术意义,我想它应当提醒我们重新认识汉字、汉语及其训释方法,有声语言比文字、字形更为根本与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汉字、汉语与西方所谓的“语音中心主义”字母文字、语言的对话与比较,或许能够开启更丰富的讨论空间。④
注释:
①②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62,148+187.本文从该角度探讨“深察名号”问题,受到薛学财《名号的神圣性及其在天人之间的中介作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第三十五>笺释》一文的启发,但本文与其论述的落脚点差异颇大。
③此一过程被《庄子》更明确地表达出来了:“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从这个上升通道考察的话,起初为“名号”之“声象”,声象首先被耳朵听到,而再转化为心之意象,最终升华为气象。
④关于该比较议题,已超出本文的范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顾明栋.汉字的性质新论[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04):33-41;尚杰.一种新文字的可能性——关于汉字哲学的一个文学维度[J].世界哲学,2018(01):104-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