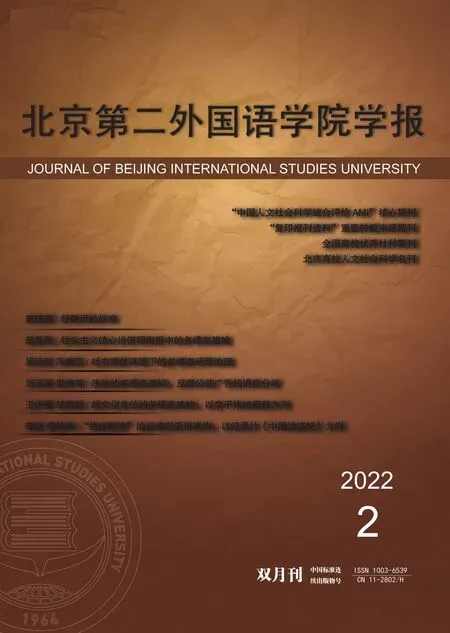好翻译的标准
姜望琪
一、严复的“信、达、雅”
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不能不提严复的“信、达、雅”。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提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赫胥黎,2007:141)他接着指出:“《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规,亦即为译事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赫胥黎,2007:141)严复还提到,求“达”也是求“信”,即“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郝胥黎,2007:141)。
综上所述,严复倾向于认为译文要“信”、要忠实于原文,这是不言而喻的。为此,他并未讨论为什么要“信”,而仅讨论了为什么要“达”、为什么要“雅”。但是,“达”和“雅”并不是翻译的最终目的,而是手段,“信”才是目的;“达”和“雅”最终都是为了“信”,“信”离不开“达”和“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者是一个整体,目的都是将原著的意思更好地转达给读者。但三者并不在同一层次上。“信”“达”是第一层次,是基础层次:不信不是译,不达也不是译,译必须“信”和“达”。“雅”则属于第二层次,是较高的层次。“信”“达”的译文是合格的译文、好的译文;“雅”则是为了使其“更好”。
那么,严复自己的译文是“信、达、雅”的吗?严格地说,特别是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严复的译文是有删节的。其《天演论》译自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Evolution and Ethics,该书最初的书稿为1893 年5月作者在牛津大学的演讲稿(以下简称“演讲”),1894 年再版时,在前面增加了“Prolegomena”(导论)部分。而严复却将“导论”译作《天演论》(上)(1898 年版),“演讲”内容译作《天演论》(下)。其实,通过“天演论”这个题目也可以看出该书不是全译——题目仅是“evolution”的汉译,而“ethics”(伦理学)却被丢掉了。这是因为严复跟赫胥黎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是要通过达尔文进化论探讨与此相反的人类社会生存原则——虽然物竞天择,但不适者也应该得以生存,也就是说,让不适者也能生存才是真正合乎人类伦理的社会;而严复则是要用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来唤起国人的忧患意识,推动社会变革,为此,他删除了赫胥黎“导论”第一节第五段中关于“进化”的一个注释①该注释的英文原文为:That every theory of evolution must be consistent not merely with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but with indefinite persistence in the same condition and with retrogressive modification, is a point which I have insisted upon repeatedly from the year 1862 till now. See Collected Essays, vol. ii. pp. 461-489; vol. iii. p. 33; vol. viii. p. 304. In the address on “Geological Contemporaneity and Persistent Types” (1862), the paleontological proofs of this proposition were, I believe, first set forth.(Huxley,1983:62-63)和第七段关于“进化”的正文内容②这段正文的英文原文是:The word “evolution,” now generally applied to the cosmic process,has had a singular history, and is used in various sense. Taken in its popular signification it means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that is, gradual change from a condition of relative uniformity to one of relative complexity; but its connotation has been widened to include the phenomena of retrogressive metamorphosis, that is, of progress from a condition of relative complexity to one of relative uniformity.(Huxley,1983:64)。他还在“导言二·广义”后增加了1 040 字(而英文原文仅为812 个单词)的“按语”,介绍了他赞同的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进化”的定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天演论》颠覆了赫胥黎的原意,并不符合“信”的要求。《天演论》的“按语”共有17 704 字,约占全书总字数33 814 的一半以上。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不是翻译,而是创作。
其次,对于英文原文的内容,严复也并未全译。赫胥黎为了吸引听众,也为了把自己在伦理方面的探索比作杰克的上天探险,用“Jack and the Beanstalk”这个故事作为“演讲”的开场白,并贯穿始终。其第一段开头是:“There is a delightful child’s story, known by the title of ‘Jack and the Bean-stalk’ with which my contemporaries who are present will be familiar”(Huxley,1983:104);第二段开头是:“My present enterprise has a certain analogy to that of the daring adventure. I beg you to accompany me in an attempt to reach a world of a bean”(Huxley,1983:105)。这些内容严复在翻译时都未译出。他的《天演论》(下)是这样开始的:“道每下而愈况,虽在至微,尽其性而万物之性尽,穷其理而万物之理穷,……”①此处的白话文翻译是:事物的规律每往下深入研究就越有比较,哪怕是最细微的事物,想要了解其性质,则万物的性质皆可了解(赫胥黎,2007)。(赫胥黎,2007:161)。然后又道:“今夫筴两缄以为郛,一房而数子,瞀然不盈匊之物也。然使艺者不违其性,雨足以润之,日足以暄之,则无几何,其力之内蕴者敷施,其质之外附者翕受;始而萌芽,……”②此处的白话文翻译是:现在用两根绳索扎成花房的外围,一个花房里放几颗种子,种子是眼看不清手捧不住的微小之物。然而让花匠不违其性质,用足够的雨水滋润它,让充足的阳光温暖它,则用不了几日,种子内蕴的活力就会施展,其表面的质地就会吸收,开始发芽(赫胥黎,2007)。(赫胥黎,2007:161)。
再次,在对全文段落进行翻译时,严复也有很大的改动。例如,“导论”第一段是:“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 ”(Huxley,1983:59)。而严复的译文是:“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来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赫胥黎,2007:142)。严复的译文将原文中的人称都改了。对于译文改动这一问题,严复自己也非常清楚,因此,他在《天演论》“译例言”第一段中明确提到:“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鸠摩罗)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赫胥黎,2007:141)
从“达旨”这个意义上来看,严复是成功的。若将“信、达、雅”看作一个整体,从这样广义的角度出发,“达”“雅”是为了“信”,严复的翻译也可以说是“信、达、雅”的。特别是从翻译效果看,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的译作问世后,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鲁迅曾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听说有《天演论》这么一本书以后,他立刻就去买了,读了开头就感叹,“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他评价严复的译作“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地)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赫胥黎,2007:136)。不过,总的来说,至少就《天演论》而言,笔者认为,严复的翻译“信不足,达很好,雅有余”。出现这种情况跟严复所处的时代有关系,跟他的翻译目的有关系,还跟翻译的本质有关系。
所谓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将另一种语言已经表达出来的意义再表达一遍。由于语言形式发生改变,很难确保原来的意义完全不变。即使是同一种语言的同义词,实际也仅是近义词,完全相同的词也是没有的;不同语言的翻译对应词更是如此。因此,译文的“信”只是相对的,“不信”是绝对的。国外翻译界的传统说法是“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者即反叛者)。钱锺书曾根据《说文解字》中的“囮,译也”,提出汉语的“译”“诱”“媒”“讹”“化”是一脉相通、彼此呼应的(钱锺书,1981:696)。他认为,“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钱锺书,1981:697);“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①2019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博士生阮诗芸曾指出,钱先生的考证不够严谨。其实“译”与“绎”“峄”等同源,与“驿”通用,基本特征是“传”“连续”,本义是“传言”。古汉语中“睪”“皋”“皐”等是混用的,“䜂,相欺也”,又《玉篇》中训与“䜂”同义连用的“䜋”同样为“译”,而此“译”在唐钞本中与“䜂”字形难分,故《说文》中“囮,譯也”的“譯”也应与“䜂”相通(阮诗芸,2019:138)。不过,她并没有提及翻译是不是总有失真的问题。(钱锺书,1981:698)。
总之,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智力活动,不仅涉及原作、译作的语言和思想,还要考虑时代背景、译者的动机等。上文的讨论已涉及“信、达、雅”的多种含义和理解;下文将围绕“准确性”“可读性”“直译”“意译”“神似”“形似”等概念进一步说明翻译的复杂性,希望读者切勿简单地望文生义。
二、译作不能违背原作的主要思想
译作不能违背原作的主要思想,即严复强调的“信”,或者说“准确性”。笔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这是第一重要的,否则就不是“译”,而是“写”。不过,如上文提及的,“译”从本质上说都会对原文的意义有所改变,完全的“信”并不存在,“信”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此,我们从反面来提出这个标准,要求译作不能违背原作的主要思想。
傅雷认为:“破除了情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翻译书都要打入冷宫。”(傅敏,2006:26)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欠妥。说译作都有错,意味着“信”只是相对的;但“打入冷宫”应该是“根本不能用”“完全错误”的意思。如果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翻译书都是完全错误的,似乎言过其实。不过,有的错误确实是不可原谅的。
2020 年1 月3 日,唐山(2020)在《北京青年报》刊发了《名著误译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一文,指出名著误译是很严重的问题。文章还转引了诗人伊沙的发现——冰心翻译的泰戈尔的诗中存在较多的错误:“平均一首便有一处误译,也就是说,每两三百字便错一次。”①此书封面用的是泰戈尔《飞鸟集》(Stray Birds)的封面,并带有“郑振铎、冰心译”的字样,容易让人误解成冰心译过《飞鸟集》。实际上,冰心译的是《吉檀迦利》(Gitánjali),出版社把郑振铎译的《飞鸟集》跟冰心的《吉檀迦利》放在一起,出了合集。此外,唐山(2020)还提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董风云社长的一段经历,他在前往法国留学前读过福柯的《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的中译本,发现“虽然每句都能看懂,却无法串连成一页,直到今天,我也没看懂这本书”。在网络上,该书被网友列为“被翻译‘毁掉’的经典好书”第四名,与《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译)、《论自由》(许宝骙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龙婧译)、《精神生活》(姜志辉译)、《罗马帝国衰亡史》(黄雨石等译)、《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和《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等同列。
下面,本文将重点讨论语言学界的一个严重误译,即将言语行为理论中的“illocutionary act”译为“言外行为”。这个术语是1955 年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家奥斯汀(John Austin,1911—1960)在哈佛大学的“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讲座中提出的。
此前的哲学研究只关注有真假值的句子,即“命题”,奥斯汀明确反对这一做法。他主张,没有真假值的句子同样具有哲学意义。如“I name this ship the Queen Elizabeth”,看起来是一种自我描写,如同化学老师在做实验时说的“I pour this liquid into the tube”。但实际上,这两句话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句是自我描写,说明说话人当时在干什么;而第一句却不是描写性的(constative),而是施为性的(performative),句子本身就是在实施行为。这是言语行为理论的第一步,即区分描写性句子和施为性句子。“I apologize…”“I promise…”等也是施为性句子,在使用这些句子时,言就是行,说话本身就是做事。
然后,奥斯汀试图从语法上区分描写性句子和施为性句子,并找出它们的形式特征,如施为性句子的主语是第一人称单数,用施为动词,而且是现在时、主动语态等。但是,他很快发现这些特征并不是必要的:施为性句子的主语可以是其他人称,可以是复数,还可以是被动语态,如“We promise to clean the room afterwards”“You are hereby authorized to pay for the purchase”“Passengers are warned to cross the track by the bridge only”;甚至可以不用施为动词,可以说“I’ll come”,不一定非要说“I promise I’ll come”;可以说“Turn right”,不一定非要说“I order you to turn right”。最典型的可能是“Thank you”,从形式上看,它没有主语,像祈使句;尽管人们会开玩笑地说“你不能光用嘴谢我”,但说了这两个词后,说话人确实就已经向听话人表达了谢意,完成了致谢行为。于是,奥斯汀重新探讨了在什么意义上言就是行,说话就是做事。最终他提出,我们说的每句话都可以用来做事,因为说话时,我们同时实施了3 种行为,即“locutionary act”“illocutionary act”“perlocutionary act”。那么,这3 种行为是什么意思呢?
奥斯汀提到:“Locutionary act includes the utterance of certain noises, the utterance of certain words in a certain construction, and the utterance of them with…a certain sense and with a certain reference”(Austin,1962/1975:94)。而且,他指出应当主要关心下面这种行为,即“To perform a locutionary act is in general, we may say, also andes ipsoto perform anillocutionaryact, as I propose to call it. Thus in performing a locutionary act we shall also be performing such an act as: asking or answering a question,giving some information or an assurance or a warning, announcing a verdict or an intention…”①这段话可以译作:我们可以说,实施一个“locutionary act”,一般也是、而且本身就是实施一个(我所谓的)“illocutionary act”,例如,在实施一个“locutionary act”时,我们也在实施下列行为:提出或回答一个问题,提供一种信息、保证或警告,宣告一个裁定或意图等。(Austin,1962/1975:98)。奥斯汀还特别指明,“locutionary act”是“an act of saying something”,“illocutionary act”是“an act[performed]②此处方括号中的内容为笔者所加,下同。in saying something”。
这些论述提示我们,“illocutionary act”中的“il-”不同于“illogical”中的“il-”,不是否定的意思,而是“in”“within”的意思。奥斯汀在引进第三种行为时,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他说:“There is yet a further sense (C) in which to perform a locutionary act, and therein an illocutionary act, may also be to perform an act of another kind”(Austin,1962/1975:101)。因此,如果按字面意义直译,“illocutionary act”中的“illocutionary”也应该是“言内”,而不是“言外”。
从奥斯汀的整个理论来看,把“illocutionary act”译成“言外行为”也是错译。传统观念把言论和行为、说话和做事对立起来,而奥斯汀对此提出了挑战,认为言论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行为,说话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做事。其中,他主要强调的不是“locutionary act”这种通常意义上的嘴舌动作之类的行为,而是被包含在这种行为中的表达某种说话人意图的第二种行为,即“illocutionary act”。如果将这种行为理解为流离于言说之外的行为,那么奥斯汀所谓的“言就是行”“说话就是做事”便成了毫无意义的命题。
奥斯汀的学生、言语行为理论的完善者塞尔(John Searle,1932— )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与奥斯汀不太一致,他将奥斯汀的“locutionary act”进一步细分为“utterance act”和“propositional act”。但是,他关于这些行为之间关系的论述却同样适用。塞尔提到,“I am not saying, of course, that there are separate things that speakers do, as it happens, simultaneously, as one might smoke, read and scratch one’s head simultaneously, but rather that in performing an illocutionary act one characteristically performs propositional acts and utterance acts. Nor should it be thought from this that utterance acts and propositional acts stand to illocutionary acts in the way buying a ticket and getting on a train stand to taking a railroad trip. They are not means to ends; rather, utterances acts stand to propositional and illocutionary acts in the way in which, e.g., making an ‘X’ on a ballot paper stands to voting”(Searle,1969:24)。最后一句话中的比喻很形象地说明了“locutionary act”和“illocutionary act”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角度来看,这两种行为是同一种行为(在选票上打叉,其实就是“投票”):从行为本身来看,是在选票上打叉(locutionary act);从行为目的来看,是投票(illocutionary act)。
程雨民(2004:149)将“illocutionary act”译作“语现行动”,认为“语现”是“语言中所体现”的意思;其中“il-”是“内”的意思,由于奥斯汀本人的注释是“an act performed in saying something”,故不能译作“言外”。相似地,徐烈炯(1995:89)将“illocutionary act”译作“言谓行动”。他指出,这种行动不在言语之外,词缀“il-”恰恰是“内”的意思,不能译作“言外”。
目前,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这本书国内有两个译本,均出版于2012 年,且书名都译作《如何以言行事》。这两个译本都未用“言外行为”来翻译“illocutionary act”,其中杨玉成、赵京超译作“话语施事行为”(约翰·兰肖·奥斯汀,2012a),张洪芹译作“施事行为”(约翰·兰肖·奥斯汀,2012b)①姜望琪(2003)把“illocutionary act”译作“行事行为”,同时把“performative”译作“施为句”。。但是,将“illocutionary act”译作“言外行为”的也不少。其中,梅德明主编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百科全书》中的翻译较为特别。该书一方面提到,言语行为理论体现了“言”即②原文此处用的是“则”,笔者怀疑是“即”之误。“行”这样的语言观,其核心思想是“言即行”,另一方面却把“illocutionary act”译作“言外行为”(梅德明,2017:551),似乎自相矛盾——“言”既然是“行”,两者是一回事,怎么又会一个在另一个之外呢?
三、译文要有可读性
所谓可读性,就外译汉而言,指的是译文要符合汉语的习惯,要像中文的写作一样,不能有“翻译腔”。笔者在1993 年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笔者发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③笔者曾在1989 年、1991 年两度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笔译员。的翻译不仅要求内容正确,而且也要求在形式上接近原文。例如,教科文组织第26 届大会的一个决议案标题“Implementation of 25 C/Resolution 19 concerning UNESCO’s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th regard to young people: Report by the Director-General”被译作“实施关于教科文组织的促进有关青年的国际合作的贡献的决议25 C/19:总干事的报告”。这种翻译要求对于国际文件有其必要性,便于不同文本之间的对照。但是,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这个决议案标题如果译作“关于教科文组织在促进青年问题国际合作中作用的决议25 C/19 的实施情况:总干事的报告”,会更加符合汉语的习惯,其可读性更强(姜望琪,1993)。
增强译文的可读性着重体现在结构词的翻译上。教科文组织决议案的翻译问题,表面上看是语序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结构词的翻译问题,即“of”等词语的译法问题。如果每个“of”短语(或后置定语)都译作“X的”,那么汉语句子就会“的的不休”。相对而言,实义词直译虽然有时也很别扭,如将“International Year for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s”直译为“国际世界土著人年”,但这一方面可能是无奈之举,没有更好的选择,另一方面其仅涉及个别案例,影响不大。但结构词则不同,它们是语法的重要内容,影响整个语言的组织机制。例如,“Replacement of a member in terms of office”在教科文组织中的现有译法是“替换一名现任委员”。当英语用“some members”时,汉语通常翻译为“数名”。但这种译法并不符合汉语习惯,因为英语中的“a”“some”之类的词统称为“限定词”(determiner),使用这类词是根据英语语法的要求,而不是语义表达的需要,不用它们并不影响句子的意义。汉语则没有这种语法限制,“替换现任委员”是完全合法、通顺的表达。将“一名”“数名”翻译出来,反而让人觉得数量在这里很重要。这如同翻译“I’m a student”这个句子时,译作“我是学生”才是地道的汉语,而“我是一个学生”则是初学者的翻译。同样,将“He put his hands into his pockets”译成“他把他的手放到他的口袋里”是一个笑话,除非其中的“他”不指同一个人。
对于定语从句等长修饰语,笔者建议,要把长句子拆分成短句子。
例(1)
Anyone who uses a sentence of the formX is meeting a woman this eveningwould normally implicate that the person to be met was someone other than X’s wife,mother, sister, or perhaps even close Platonic friend.
(Grice,1989:37)
在翻译这个句子时,可以将定语从句提到前面来,先说“任何人说‘X 今晚将跟一个女人见面’”,然后用“他”重复主语,接着说“他通常都会暗示这个要见的人不是X 的妻子、母亲、姐妹、甚至不是其红颜知己”。
例(2)
My aim in this essay is to throw light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 a notion of meaning which I want to regard as basic, namely the notion which is involved in saying of someone that by (when) doing such and such he meant that so and so (in what I have called a non-natural sense of the word “meant”), and (b) the notion of meaning involved in saying (i) that a given sentence means “so-and-so” (ii) that a given word or phrase means “so-and-so”.
(Grice,1989:117)
这句话中的“between”后面有两个很长的宾语,如果不调整顺序,很难译好。笔者建议译为:“本文的目的是阐明(a)和(b)两种意义概念之间的关系:(a)我想称之为基本意义概念,即,当我们说某人通过做如此这般的事情(在做如此这般事情的时候)表示了这样那样的意思时(在我称之为‘meant’这个词的非自然意义上)用到的概念;(b)我们说(i)一个特定句子表示这样那样的意思和(ii)一个特定词或短语表示这样那样的意思时用到的概念”。
例(3)
…that anyone who cares about the goals that are central to conversation/communication (such as giving and receiving information, influencing and being influenced by others) must be expected to have an interest, given suitable circumstances, in participation in talk exchanges that will be profitable only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y are conducted in general accordance with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and the maxims.
(Grice,1989:30)
这个句子更为复杂,在翻译时如果只是调整顺序,将定语从句提前,译作“一个人关心会话/交际的中心目标(就像提供和接受信息、影响别人和被别人影响),他就预期必然会有兴趣在合适的情况下参与这种谈话,它只有在假定一般是按照合作原则及其准则而展开的时候才能获益”,句子的可读性似乎仍然差一点。如果把前一个句子译作条件从句,后一个句子明确改成主动语态,可能会好一些,即翻译为:“如果一个人关心会话/交际的中心目标(就像提供和接受信息、影响别人和被别人影响),我们预期他必然会有兴趣在合适的情况下参与这种谈话,它只有在假定一般是按照合作原则及其准则而展开的时候才能获益。”
需要强调的是,跟准确性相比,可读性是次要的。有人之所以将“illocutionary act”译作“言外行为”,可能就是因为汉语有“言外之意”这样的说法,“言外行为”的可读性比较高。但是,为了可读性而采用一个与原意相去甚远的误译,在笔者看来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四、神似与形似兼顾
翻译的神似与形似兼顾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术语要有透明性;在可读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形似。
术语透明性是指读者能从译名中轻松地辨认出源词,并能轻松地回译。这在国际会议场合几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例如,“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虽然很多英汉词典把它译作“防止核扩散条约”,但通常应译为“核不扩散条约”;“framework agreement”通常译作“框架协议”,现在人们对这一译文已经没有任何异议,但当初对于这一译法却是有过激烈争论的;计算机的“operating system”,根据其意义曾译作“管理程序”,但现在通常译作“操作系统”;社会工作者的“field work”按照内容来看,应译作“实地调查”,但现在通常译作“田野工作”;“natural selection”曾被严复译作“天然淘汰”,现在通常翻译为“自然选择”。从表面上来看,这些透明的术语似乎“直译”比较省事,这也是笔者强调术语透明性的一个原因。一个术语要想得到读者的支持,受到喜爱,被广泛流传,必须要好用、省力,如同被广泛接受的工具一样。
不过,笔者之所以强调术语透明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强调术语透明似乎是不顾内容、只顾形式,但实际上形式的相似有时也是内容相同的必要条件,是为了更好的“信”。例如,1946 年8 月6 日,毛主席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提到:“美国反动派是纸老虎。”翻译人员将这句话译完后,毛主席问怎么没听见翻译“纸老虎”,翻译人员表示将其译为了“scarecrow”。接着,毛主席又问斯特朗“scarecrow”的意思,她说这个词指的是农民插在地里吓唬乌鸦的稻草人。毛主席立刻就说,这样翻译不好,这不是他的意思。“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一只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因此,他坚持要把“纸老虎”译成“paper tiger”。①参见网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096797。
如上文所述,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将另外一种语言已经表达出来的意义再表达一遍。语言是形式,是意义的载体;语言变了,形式就变了,载体也就变了,意义就不可能不变。如果直译术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一部分形式,意义就会少改变一点,即“信”的程度就可能会增加。傅雷先生素来强调“神似”,但这丝毫不能说明他认为“形似”是完全不必要的。他明确提到,他的意思不是“原文的句法绝对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傅敏,2006:23)。他强调的是与“神似”相比,“形似”是次要的;如果两者不可兼得,那么就要放弃后者。他曾以法文版《哈姆雷特》中将“Not a mouse stirring”(一只耗子都没动)译成“Pas un chat”(一只猫都没有)为例,说明神似比形似重要(傅敏,2006:3)。但他同时又为自己曾把“蓝衣服”译作“绿衣服”而叹息,说“这种文字上的色盲,真使译者为之大惊失‘色’”(傅敏,2006:4)。这也说明,傅雷先生在形似跟神似不矛盾的时候,也会两者兼顾。他曾经解释道:“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又须能朗朗上口,求音节和谐;至节奏与‘tempo’,当然以原作为依归。”(傅敏,2006:56)这是翻译的神似与形似兼顾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神似、形似兼顾,在可读的前提下追求形似。
为什么要追求形似?因为形式很重要。任何内容、任何意义都要有载体,这个载体就是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式是内容/意义的基础,或者说,形似是神似的基础。此外,形式不仅仅是形式,它本身跟意义紧密相连,或者说,形式也有意义。朱光潜认为,思想与语言有一致性,一定的语言表达一定的思想。如果某个念头没有恰当的词语表达,那说明该念头本身还没有成形。“寻思必同时是寻言,寻言也必同时是寻思”“水到自然渠成,意到自然笔随”“韩愈定贾岛的‘僧推月下门’为‘僧敲月下门’并不仅是语言的进步,同时也是意境的进步”(朱光潜,1981:104-106)。
杜甫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不仅是在追求形式的新颖,也是在追求内容和意义的新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的进步就是形式的进步、表达方式的进步。莎士比亚之所以伟大,并非全部是因为他的剧作内容好——一些剧作内容在莎士比亚以前就存在,像威尼斯商人这样的故事已经流传多年,莎士比亚真正的过人之处是他的文字、他的表达。
赵萝蕤提到,直译法是她从事文学翻译的唯一方法,但又说,“我用直译法是根据内容和形式统一这个原则”;虽然内容最终决定形式,但“形式[并]不是一张外壳,可以从内容剥落而无伤于内容”(赵萝蕤,1989:607)。她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时学习了“中西诗比较”“文艺理论”“法国文学”等课程,对美国老师温德详细讲解的艾略特的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有着极大的兴趣,并试着翻译了第一节。1936 年,戴望舒闻讯后约她翻译全诗,于是她用一个月时间翻译完了这首艰深晦涩的现代派“怪诗”,一举成名。1980 年,赵萝蕤在《外国文艺》上发表了一个新的译本,将“1936 年不彻底的直译法”改为“1979 年比较彻底的直译法”(赵萝蕤,1989:609)。例如,《荒原》第一行的“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原译作“四月天最是残忍”,现改成了“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她解释说:“新译力图更加接近原作的内容和形式(其中包括分行及节奏)。这就是我所说的直译法。”(赵萝蕤,1989:610)换言之,赵萝蕤的“直译”并不是真的只译字面意义,否则,“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当年就可以译作“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她正是考虑到了“达”,考虑到了读者的接受力,才采用了“四月天最是残忍”这种当时颇为流行的句式。这说明,她并不是只注意“形似”,她也注重“神似”。
朱光潜(1984:454)明确说过,“直译和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应存在”“一个意思只有一个精确的说法,换一个说法,意味就不完全相同。所以想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必须尽量保存原文的语句组织。因此,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
五、似与不似之间
最后,笔者将对好翻译的标准进行归纳总结。我们强调,译作要“似”原作,至少在主要思想上不能背离原作。也就是说,尽管“译文总有失真”,“不信/似”是绝对的,“信/似”是相对的,但译文仍然要“信”,内容要跟原作一致,或称“要神似”。要注意译文的可读性,避免违反汉语习惯的逐字直译,特别是结构词。同时,形、义要紧密相连,在保证可读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形似”能更好地做到“信”。换言之,要神似、形似兼顾。
翻译是“戴着镣铐跳舞”,这是非常形象的比喻。译作既受到原作的限制,又受到目的语的限制,译者没有太多的自由。说得更极端一点,翻译更像是“走钢丝”,要左右逢源,直译、意译并用。过与不及,都是失败;稍有偏差,就粉身碎骨。但是,正因为如此,好的译作才尤其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