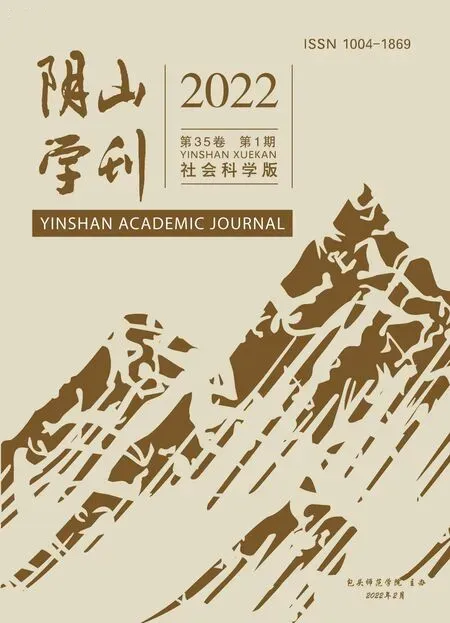论元末文人“崇陶”与“学陶” *
武 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元人多隐士,已是学界共持之论。查洪德先生将元代隐士分为三代,其中第三代是元明易代之际文人。由于社会矛盾凸显,战争频仍,士人的出处观念受此冲击,隐逸之风在此期更盛。其突出的代表是以顾瑛等人为代表的玉山文人,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门文人群体,以黄公望、倪瓒、王冕、王蒙、吴镇为代表的画家群体和以高启、杨基等人为代表的吴中诗人群体[1]。作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也成了元末文人共同尊奉的精神偶像。贡奎诗云:“我爱陶渊明,梦幻视今古。”(《元日书怀二首其二》)[2]他们不仅一递一声地传唱着“我爱陶渊明”,从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和崇高人格中培养起文人自我的独立价值以及寻找其心灵与出处、行迹的精神支撑,也在学习陶诗的过程中汲取着丰富的诗学养料。邓雅《与故人论诗》云:“郑卫非所好,鲍谢难同时。古人如可作,渊明真我师。”[3]689陶诗成为元末文人诗学取法的重要来源之一,而这种诗学取法也因他们对陶渊明的不同解读有不同的角度。而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以单一的角度来叙述陶渊明精神史在元代的接受,从而忽视了元末文人在陶渊明处获得的心灵与行迹的伸缩空间以及对陶诗的不同认知。(1)现有研究如罗春兰、周理凤、袁萍《斯人真有道,名与日月悬:陶渊明在元代的接受探析》(《南昌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李剑锋《元代屈、陶并称及是陶非屈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唐朝晖《隐逸与尽忠:元遗诗人接受史中的陶渊明》(《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王茜《元代文人“尊陶”现象探析》(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刘宗镐《论陶渊明儒者人格的生成及效用:南宋理学家对陶渊明儒者人格的认同及影响》(《科学·经济·社会》,2016年第2期)等。
一、“儒士形象”解读与“性情之正”的取法
有元一代,陶渊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儒士形象被人解读,胡助《大拙先生小传》载陈信之为人云:“恒以孝悌忠信语人。独好儒学,能文章,喜为诗,且善书,有晋人风致……醉后喜诵陶渊明《归去来辞》、苏子瞻《赤壁赋》,慨然慕其人。”[4]659在胡助看来,陈信有晋人风致,而作为晋人风致的代表,陶渊明即是一位坚持孝悌忠信的正统儒者。其实从宋代始,对陶渊明及其归隐的解读就有了道德伦理化的转向,杜甫所谓“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的评价转而为宋人“陶潜直达道,何止避俗翁”的理解。经过周敦颐、邵雍、朱熹等人的塑造,陶渊明成为正统儒家道德伦理的化身。陶诗中的“桃源”“菊花”等意象成为节操高尚的隐逸之士的象征,其“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书刘宋年号而书甲子”等典故也将他的归隐与遗民情结联系起来,成为后世遗民坚持节气操守的楷模。而陶渊明本以淑世之志,在天下无道、不谐于时的情形下被迫归隐,也为元末文人在面临出处、行迹问题时提供了生命伸缩选择的重要凭据,正如元末文人陈基所说:“靖节百世之士也,世不得而用之;节孝独行之士也,世莫得而遗焉;达卿用世之士也,顾所用何如耳。古今人不必同,不必不同,要其归卒无不同也,君子亦同其心而已矣。”(《六柳庄记》)[5]261无论全节而隐,保存道义,还是无道则隐,隐以求志,待时而用,在元末文人看来都是“君子同其心”的表现,可纳入儒家政治伦理化的范畴。
陶渊明高尚的节操,首先成为元末文人亟须的精神养料。据今人统计,元末遗民诗人有300多首咏陶、和陶、题陶画诗,咏陶、和陶诗人占遗民诗人总数的四分之三[6]。元遗民对陶渊明的解读,一方面是肯定及赞赏陶渊明不仕二姓的节操,郭钰《甲子》诗云:“渊明赋归去,正合书义熙。衣冠晋江左,寄奴我何知。”[7]又陈高《题陶渊明归去来图》云:“陶公令彭泽,明哲照几微。晋室日陵替,周鼎将迁移……闻风夙所慕,投绂方自兹。览图成叹息,永言以为师。”[8]在他们意识中,陶渊明是一位摒弃荣华利禄的高士,其不与刘宋政权合作的志节深为他们所景仰与追慕,陶渊明之坚贞似为他们的前代知音。
然而,陶渊明诗中摆脱尘俗的欣喜,在抽取其志节一面来解读的元末文人那里却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沉重,戴良《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序》说:“余客海上,追和渊明《归去来词》。盖渊明以既归为高,余以未归为达,虽事有不一,要其志未尝不同也。”“我之所历,如水行舟。始欹倾于滩瀬,终倚泊乎林丘。视末路之狂澜,睹薄俗之横流。”[9]271显然,这是一个追求志节而愁苦不堪的形象。因此,在元遗民看来,陶诗中的意象,往往并非仅限于其闲适生活的写照,而成了表现节操的陶写之具,“田园荒芜亦已久,彭泽何须求五斗。徘徊三径抚孤松,怅望闲云数归鸟。”(邓雅《题陶用大渊明归去来辞图用大名洪泗州虹县人镇襄阳授武节将军》)[3]693-694在这里,田园、孤松、归鸟已成为忠义的化身。而菊花也由良辰美景,赏心悦目的清新美好进而引申为高蹈清绝的象征。舒頔《云台观燕集序》中说:“昔人称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是谓‘四美’。余谓景之美者莫如秋,花之美者莫如菊……渊明爱菊,亦爱其气之清者……嗟夫!花非异于昔也,时有迁变,而人品独殊耳。”[10]572-573另一方面,元末文人正是从对陶渊明的解读中坚定了其不仕二姓的忠义之节。戴良《和陶渊明杂诗十一首》其五云:“我无猛烈心,出处每犹豫。或同燕雀棲,或逐枭鸾翥……从今便束装,移入醉乡住。醉乡固云乐,犹是生灭处。何当乘物化,无喜亦无惧。”又《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十九“结交数丈夫,有仕有不仕。静躁固异姿,出处尽忘己。此志不获同,而我独多耻。先师有遗训,处仁在择里。怀此颇有年,兹行始堪纪。”[9]272,276无疑,在“出处每犹豫”“静躁固异姿”之时,是陶渊明给予了他坚守名节的动力,在漂泊不定,穷困潦倒的岁月中,他将自己的余生托付于前贤,纵浪于大化之中,坚定而诚笃。
其次,元末文人对陶渊明的解读也侧重于其虽有淑世之志,但不谐于时的一面,因此隐以全身求志也是元末文人从陶渊明那里得到的启发。黄枢《乐志善所蔵陶渊明画像》云:“五柳弄碧色,众菊含秋芳。兴怀栗里翁,寸衷为激昂……慕彼晋征士,画像蔵巾箱。今日白衣来,得酒盈清觞。邀我坐东篱,索我题诗章。因将靖节心,与君细论量。饮酣得纵笔,勿谓吾为狂。”[11]卷一《论语·述而》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元后期文人看来,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是陶渊明归隐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陶渊明并非执意流连于田园山水,而是时势逼迫使然,在政治昏暗之时,诗人不愿与无道之世苟合,于是远离政治功利,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黄枢《寄傲轩记》载朱伯仁对陶渊明归隐的解读云:“予稔知伯仁之为人,孝于其亲,友于其弟,与人恭而有礼,察其身心之间,无所丝毫骄倨,而乃有取于此,何耶(按:指其‘寄傲轩’室名)?伯仁曰:‘吾见夫世降俗下,彼汲汲于名与利者,胁肩谄笑,摇尾乞怜,处汙秽而不羞,甘汨没而忘返。孰若吾之傲睨于嚣尘之表,亦乐夫天命如陶令者乎?’”[11]卷四在朱伯仁意识中,陶渊明是一位在世降俗下的社会环境中淡泊名利、傲睨嚣尘之士。然而遁隐出世并非放弃社会责任,他们认为陶渊明在“出”与“入”之间,有经世意识,只是不屑卷入政治漩涡。蒋寅先生敏锐看到:“虽然陶公归田园后诗文中不再挂怀世事,但在后人看来,他的退隐就仿佛是一种等待腾跃的蜷缩,只要世道更替,时来运转,他随时都可以复出。”“隐逸和仕宦根本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今天的隐士可能就是明日的达官,而此时的簪缨或许就是日后的布衣。仕和隐的界限常很模糊,仕的理想不是仕,隐的理想也不是隐,仕中有隐,隐中有仕。”[12]诚然,在元末文人书写陶渊明的诗作中,这种观点亦俯首即得,董寿民《次孟子玉同监见和车字韵》云:“清流那肯入污渠,未忍渊明早结庐……莫为饥寒变操守,他年何患食无鱼。”[13]又释良琦《松下渊明图》:“谢安却为苍生起,陶令何辞印绶回。若使生逢圣明世,青松老尽不归来。”[14]对于他们,“隐”不过是暂时的卧薪尝胆,“他年何患食无鱼”“青松老尽不归来”才是最终的目标。李存《送朱可方序》也表达了无道则隐、有道则出的观点:“朱君可方退然有慕于晋陶处士渊明之风,俾朋友之能文辞者咸述之,而仆切疑焉。盖尝闻诸长老,前五十年,东南士君子之有志于四方者,局局然,惴惴然,不得过大江一步。今幸遇明时,际天极地,无不交车辙马迹焉。而天子又忧乎林岩之间,有不屑于自进而非常调所得者,复为成周宾兴之礼以来之。夫如是,则士之进者,或可以少愧,而上之求者,亦不为不尽其道矣。”[15]李存认为天下有道则不必独善其身,行义达道之后,再隐求自乐,也未为晚矣。基于此种理解,元末文人在对待出处、行迹问题上有了较大的自由,暂时的抱屈隐居,是为了待时而出,隐逸可以是身隐、形隐而心不隐,可以是伺机观望的生活态度,也可以是践行道义的前期准备。
然而,无论隐以全节、隐以求志,还是隐以待机而出,在多数人眼中,陶渊明是个地道的儒士,“乌帽斜欹白发侵,老来空忆旧登临。一枝黄菊西风泪,数亩苍苔故国心。”(《九日客怀》)[16]他们对陶诗的品评取法,也多在其诗歌表现出的儒家正统诗学观念中给予阐释。
元末文人评陶诗往往将其与历代忠义之士并称。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认为陶公《述酒》与屈原《离骚》《远游》等篇有共同之处:“愚尝读《离骚》,见屈子闵宗周之阽危,悲身命之将陨,而其赋《远游》之篇……陶公此诗,愤其主弑国亡,而末言游仙修炼之适,且以天容永固、彭殇非伦赞其君,极其尊爱之至,以见乱臣贼子,乍起倏灭于天地之间者,何足道哉。陶公胸次冲淡和平,而忠愤激烈,时发其间,得无交战之累乎?”[17]在他看来,二人作品都是忠愤激烈的表现,从中可以读出忠君爱国,读出乱臣贼子,而陶渊明委运天命、安贫乐道也和屈原的忧乐之识相与沟通。陈旅《菊逸斋序》又将陶渊明与诸葛亮相联系,认为二人虽出处不同,但心可以相感:“昔周子谓:‘晋陶渊明独爱菊’,又曰:‘菊,花之隐逸者也,渊明为晋处士,若是花之不与群艳竞吐,而退然独秀于风霜摇落之时,则渊明可谓菊隐者矣。……然吾闻渊明中岁更字元亮者,慕诸葛孔明也。孔明与渊明出处不同,吾不知渊明所以慕孔明者何故?……盖尝思之,士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不于其迹,而于其心;物非人而能与人同者,不同乎人而同乎天。惟其心之可以相感,则渊明何必不为孔明。”[18]67-68所谓“心之相感”,强调的便是陶渊明的淑世之志和行义达道的抱负。因此,菊逸的真趣,依旧是其忠君爱国的儒家理想,同恕《渊明归来图》可谓把陶公的这一形象刻画殆尽:“呜呼靖节翁,后世忠武侯。出处虽事殊,抱负同天游。”[19]
由看重陶渊明的正士之节,元后期文人强调陶诗得吟咏性情之正的特点。倪瓒《谢仲野诗序》云:
《诗》亡而为《骚》,至汉为五言,吟咏得性情之正者,其惟渊明乎?韦、柳冲淡萧散,皆得陶之旨趣,下此则王摩诘矣,何则?富丽穷苦之词易工,幽深闲远之语难造。[20]306-307
元代文人似乎都对“穷而后工”的理论持保留意见,他们认为风雅正声虽然久亡,但感发怨慕之情,比兴美刺之义却无时无处不在,只要诗歌出自真情,所发之情又有所约束,不矫情伪饰,都可以得古诗“性情之正”的诗旨。入则行道,出则安贫乐道,从而幽深闲远之语也并非难造。周砥亦云:“夫诗,发乎性情,止乎礼义,非矫情而饰伪也。嗟夫王者迹熄而《诗》亡,然后《春秋》作矣。寥寥数千载下,晋有陶处士焉,盖靖节于优游恬淡之中有道存焉,所谓得其性情之正者矣。”[21]136他们以为陶诗之所以自成天籁,在于陶诗“源于风雅,取则于六义,情感于中,义见乎辞,诵之者可以兴起”,从而不事模拟,杜绝了“无病呻吟”的弊习,达到“悠然深远,有舒平和畅之气”的理想境界。(倪瓒《秋水轩诗序》)[20]306
然而元末文人一方面强调陶诗得“性情之正”,看重“居乱世而有怡愉之色”的陶诗精神,主张学习陶诗“优游恬淡”“舒平和畅之气”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对“忠义激烈”的诗风给予肯定,主张回忌“矜持”,认为“冲淡和平”与“忠义激烈”同得古诗遗意,倪瓒在《拙逸斋诗稿序》中说:
三百五篇之《诗》,删治出乎圣人之手,后人虽不闻金石丝竹咏歌之音,焕乎六义四始之有成说,后人得以因辞以求志。至其风雅之变,发乎情,亦未尝不止乎礼义也。《诗》亡既久,变而为《骚》,为五言,为七言杂体,去古益以远矣。其于六义之旨,固在也。屈子之于《骚》,观其过于忠君爱国之诚,其辞缱绻恻怛,有不能自已者,岂偶然哉?五言若陶靖节、韦苏州之冲淡和平得性情之正,杜少陵之因事兴怀、忠义激烈,是皆得三百五篇之遗意者也。[20]305
其实陶诗“冲淡和平”的一面是宋人挖掘而强调的主要内容,而在元人看来,陶诗也有如杜诗“忠义激烈”的表现,这也是元人将屈、陶并称的重要原因。只不过这一面在元末战乱中文人们看得更为真切,倪瓒讲述周正道的经历说:“生当明时,侨寓吴下,求友从师,不惮千里,其学本之以忠信孝友,而滋之以诗书六艺,其为文若诗,如丝麻粟谷之急于世用,不为镂冰刻楮之徒费一巧也。兵兴三十余年,生民之涂炭,士君子之流离困苦,有不可胜言者。”[20]306战乱之际,生民涂炭,流离困苦,“忠义激烈”自然是真情的抒发。因此,他们认为学陶要回避“矜持”,而所谓“矜持”,并不是否定陶诗的价值,而是强调摒弃流连光景、岁锻月炼,沿袭剽盗之言和缛丽夸大之语。以浅易明白的语言寄寓深远之意,从而兴发感怀,使闻之者足戒,达到古诗之遗意。
当然,在元末文人那里,陶诗得乎性情之正关键在于陶公所树立的高尚节操,贡师泰《跋陶渊明图》云:“自司马氏之东也,一时勋名气节之伟,风流韵度之雅,盖不可偻数也。然人物独称陶渊明,文章独称《归去来词》。往往好事者,既咏歌以致其敬慕……三公九卿,岂重于一令?千言万语,岂多于一词也耶?”[22]因此他们学习陶诗,首先主张从陶公的人品出发,经过对其情性、人品的学习以合其诗之气与味,进而认识陶诗的内理,即神气,以培养属于自我的诗歌风格。杨维桢《张北山和陶集序》云:
东坡和渊明诗,非故假诗于渊明也,其解有合于渊明者,故和其诗,不知诗之为渊明为东坡也。涪翁曰:“渊明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固不同,气味乃相似。”盖知东坡之诗可比渊明矣。[23]241
他认为苏轼与陶渊明虽然出处不同,但苏轼的出世之想及其情性、人品与陶渊明有所暗合,因而苏轼和陶诗与陶诗“气味相似”,是和陶诗的典范。其《赵氏诗录序》云:“评诗之品,无异人品也。人有面目骨体,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风雅而降为骚,而降为《十九首》,《十九首》而降为陶、杜,为二李,其情性不野,神气不群,故其骨骼不庳,面目不鄙。”[23]239杨维桢将诗品与人品一体而论,认为诗如其人,人如其诗,陶诗的成就就是他人格的再现,是承自《风》《骚》《十九首》一脉,陈绎曾《文筌》云陶渊明:“心存忠义,身处闲逸,情真,景真,意真,事真,几于《十九首》矣。但气差缓耳,至其工夫精密,而天然无斧凿痕迹,又有岀于《十九首》之表者,盛唐诸家风韵皆出此。”[24]由此可见,陶诗虽承自《风》《骚》《十九首》但陶诗有自我的个性与风格,因此元末文人不仅强调对陶公人品的学习,也重视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人品的培养,展示其个人的诗品,所谓“屈诗情骚,陶诗情靖,李诗情逸,杜诗情厚”“诗之状,未有不依情而出也”,而此“情”根基于“发于言辞,止于礼义”的“情性之正”。(杨维桢《剡韶诗序》)[23]242故而通过学习陶诗,也就获得了与陶公相似的人品以及自为一家的诗品。
二、“逸士形象”解读与“平淡自然”的取法
元末文人对陶渊明的解读也侧重关注陶公归隐后自适自乐的生活,以及在隐逸生活中追求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而此种价值与儒士兼济之志恰恰相反,是人格的自由及精神的酣畅。元末文人多以陶渊明的超脱襟怀否定“入世”的价值向度,传统文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追求在他们那里一一受到揶揄,伯夷、屈原、伍子胥、李斯、班固……一切以道德事功垂世的历史人物都被他们拉出来示众,警示世人放弃“上下求索”的艰辛痛苦和事功的虚无价值。“伯夷耻粟饿,屈原避谗死。独有柴桑翁,一不失张弛。所以百世下,风流激颓靡。遐观八极表,衰荣何足数。”(马祖常《读陶潜诗》)[25]张养浩《双调·沉醉东风》云:“班定远飘零玉关,楚灵均憔悴江干。李斯有黄犬悲,陆机有华亭叹。张柬之老来遭难,把个苏子瞻长流了四五番:因此上功名意懒。”[26]471将历史豪杰逐个评点后,他们意识到,千古是非、功名利禄最后总归虚无一场,倒不如放浪形骸,学陶公归去,赏菊东篱,日饮流霞,尽情享受快意人生。
然而,对“兼济”之士的调侃与否定,并非是他们的本意,他们也曾努力地“兼济”过,只不过在仕途壅滞、战乱频仍的时代,原初的志向早已被消磨殆尽,“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干休了丞相。这几个百般,要安,不安,怎如俺五柳庄逍遥散诞。”(张养浩《双调·沽美酒兼太平令》)[26]456在“补天无术”“经世无策”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转而追求“出世”的隐逸生活,追求无拘无束的理想人生。
元末文人在经历了战乱的摧残后,清醒地认识到,所谓“道显于世”“治国平天下”都是膺厚禄者的事情,与他们无干,传统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在他们心目中已不重要。秦约在《可诗斋夜集联句序》中说:“今四邻多垒,膺厚禄者,则当奋身报效,吾辈无与于世,得从文酒之乐,岂非幸哉!”[21]141-142又熊梦祥《春晖楼中秋燕集序》云:“弛张系乎理,不系乎时;升降在乎人,不在乎位。其所谓得失安危,又何足滞碍于衷耶?……呜呼!于是时能以诗酒为乐,傲睨物表者几人?能不以汲汲皇皇于世故者又几人?”[21]332-333时势的发展自有其本身的理数,时运升降也不由其位而定,他们能做到的只剩下诗酒之乐,得失安危在此时已然缥缈,与其将费心费力的经世安民,将一种虚无的责任感强加在自己身上自我折磨,倒不如在山水诗酒中尽情地享受,放下崇高,急流勇退,自我解脱,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而此时,陶渊明又被元末文人借来,以一种绝俗超世、自适自乐的形象填充他们对自由极度渴望的精神空缺。
首先,元末文人对陶渊明的解读侧重在对一种自适自乐之平居生活的向往。王沂《题龙氏乐善堂》诗云:“余爱渊明诗,匪善奚以敦。谁云甘泉谷,中有至乐存……筑堂种嘉木,丛阴庇其根。恶禽不敢栖,好鸟时飞翻。清琴横我床,浊酒盈我尊。愿言怀静者,时复扣衡门。”[27]他从陶诗中找到至乐生活的细节,堂前嘉木成荫,好鸟归来,浊酒盈杯,静者扣门,一幅闲居自适、乐天知命的美好场景。许氏兄弟(许有壬、许有孚)在隐居圭塘别墅时亦往往从陶公处得到闲居生活的快意,在神山避暑,晚行田间的畅游中每以陶诗为韵制诗,许有孚《水口听琴》一诗,在潺潺的流水中享受渊明琴外之趣,慰藉着他往昔置身官场的劳顿之心。在玉山草堂觞咏畅乐中,陶公闲适身影也随处可见,“自笑渊明居栗里,也随慧远入庐山。何当共下吴江钓,坐向船头话八还。”(顾瑛《玉山顾瑛次韵龙门释良琦元璞》)[21]301-302此际的陶公,似乎也成了顾氏草堂的座上雅客。在他们眼中,陶渊明的真率、随性就是他们所向往的理想生活:“渊明好饮酒,重觞即忘天……谁知醉中吟,其乐不可言。”(邓雅《饮酒》)[3]689“渊明非嗜酒,寓意酒杯中。大化观天地,闲情对菊松。”(邓雅《题渊明画像》)[3]702陈基《桃源小隐记》记载了时人慕陶渊明“桃花源”而在界溪一地筑“桃源小隐”事及其人闲适自乐的生活:“(主人)尝读晋人所记桃花源而慕之,且曰:‘安得若人者,与之游乎?’于是环其庐皆种桃,而扁曰‘桃源小隐’。客有过而为之赋者,曰:‘仲春之月桃始敷,风日晴美。其蒸如霞,既秾且郁,天发其葩灼灼丽姝烂云锦。以为居此,岂避秦之子,而彼美人者,得以挹其芳而玩其华耶?’生乃止客,取酒剧饮,日且暮,俱藉草卧花下。须臾月白,风露在草树间,夜气袭人……生乃歌陶渊明诗以和之,然其人卒不可得而见。”[5]351美好的生活环境,平居生活的闲适惬意,接杯觞、弄笔墨的朋友之会、欢宴咏歌,俨然一幅世外桃源的景象。
其次,元末文人对陶渊明自适自乐之平居生活的向往,意在摆脱世俗的约束和负担,获得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满足,以此超脱于轮回之外,实现自由人生的价值。舒頔认为陶渊明俯仰无惭,获得心灵的超越,在于其对利禄纷争的摒弃,其《次王和夫见寄韵》诗云:“俯仰无惭一不惊,寒香晚节颇关心……老景肯输诗笔健,旷怀宁让酒杯清。纷纷利禄争先步,谁似渊明去就轻。”[10]652张之翰则认为渊明的超然在于富贵贫贱之外“萧然乐其乐”,其《题渊明图》云:“人云《归来辞》,在晋第一文。我谓靖节公,在晋第一人……言语益精拔,怀抱任旷真。进不急富贵,退不忧贱贫。萧然乐其乐,无怀葛天民。”[28]然而,无论如何元末文人都在对陶公的解读中将其超脱的襟怀努力付诸实践,“宾朋日过从,饮酒和陶篇。悠然得所乐,庶以全其天。”(邓雅《题鞠孟端悠然亭》)[3]675“浊醪泛佳菊,细和渊明篇。”(邓雅《寄艾录事潜虚》)[3]684在仿效陶公的生活,细读陶公的诗篇中,他们优游于浩渺云山,得到了“全其天”的无尽快乐。胡助《隐趣园记》载其儿胡璋逍遥于隐趣园事:“吾儿雅不欲仕,独慕古人之遗风余烈于山林间,故得园池之胜,与隐者之趣,固未必同也。诚能得夫隐居之趣,是与造物者游,逍遥乎尘埃之外,彷徨乎山水之滨,功名富贵何曾足以动其心哉。呜呼!古之君子真得隐居之趣者,亦不多也。晋有陶渊明,唐有李愿而已。”[4]684隐趣的意义在于不依附任何外物,与造物者同游,以此抗衡功名富贵,涤化心灵,回归文人独立、自由的生活方式。
对陶渊明自适自乐之平居生活的向往和对他绝俗超世的人格与精神的激赏,也影响了元末文人对陶诗的取法。“手携渊明诗,倦坐据绳床。悠然宇宙间,是非两忘羊。”(周权《春暮》)[29]他们在陶诗中品味到对自然、宇宙的适意,水光山色间的无穷之意,自然遇之,自然感动,他们将心中所感,胸中之趣以平淡之笔陶写下来,记录自己的心灵和情绪,不苟藻饰,也不求媚俗,悠然自乐,是非两忘。
元末文人对陶诗自然平淡的取法直接受到宋人评陶诗的影响,认为陶诗之平淡是繁华落尽,学问工致后的成熟境界。然而,元末文人出于他们对陶诗平淡风格的再次沉潜琢磨,在宋人的诗学观念之上又有所补益与发展。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言:“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30]严羽评陶、谢诗的区别,着眼于谢灵运诗富丽精工,出自人工雕刻,陶诗质性自然,止写胸中意。而在杨维桢看来,陶、谢诗之所以有“摹形”与“写意”的区别,在于二人对自然景物欣赏与观察的方式不同,其《张北山和陶集序》云:
吾尝评陶、谢爱山之乐同也,而有不同者,何也?康乐伐山开道入,数百人自始宁至临海,敝敝焉不得一日以休,得一于山者粗矣。五柳先生断辕不出,一朝于篱落间见之,而悠然若莫逆也,其得于山者神矣。故五柳之咏南山可学也,而于南山之得之神不可学也,不可学则其得于山者,亦康乐之役于山者而已耳。[23]241
杨维桢认为谢灵运对自然景物的欣赏与观察重在于“游”,是一种“伐山开道”的集体游览,所到之处并不深入体会自然真意,只得山水之“形”。谓之为“粗”,享受的是游览过程的趣味。陶渊明则在静处深入体察自然之“神”,享受的则是景物本身所带来的趣味。故而陶公“得于山”,康乐“役于山”。从陶、谢二人对自然景物观察方式的异同处着眼,元人更为深入地阐明了二人诗风的区别,也因此,杨维桢为学陶者指出了一条可资借鉴的途径:学陶不必步韵倚声,迹于其诗,在于学习陶公的胸中之意,以求意的方式体察自然外物,再以自己的志趣发言为诗。
宋人对唐宋人学陶诗有细致评说,这些观点也为元末文人所接受,但元人又在细微处给予具体阐述,陈秀明《东坡诗话录》引黄庭坚语:
白乐天,柳子厚,俱效陶渊明,作诗而推子厚诗为近。然以予观之,子厚语近而气不近;乐天气近而语不近。子厚气凄怆,乐天语散缓,各得其一,要于渊明诗,未能尽似也。东坡亦尝和陶诗百余篇,自谓不甚愧渊明,然坡诗语亦微伤巧,不若陶诗体合自然也。要知陶渊明诗,须观江文通杂体诗中拟渊明作者方是逼真。[31]
黄庭坚认为白居易、柳宗元、苏轼学陶是从“气”和“语”两方面出发,所谓“语”即陶诗自然而发的平淡诗语,“气”则是由平淡诗语体现出的壮逸之气,即陶诗的风格特征,认为柳诗“语近”但风格稍落“凄怆”,白诗、苏诗有壮逸之气但语言似有散缓工巧。元人论此则更为周详,进而扩展至“情”“趣”,“意”“韵”,“貌”“味”等范畴。元人认为陶渊明淡泊渊永、远出流俗的风格得益于其真实情感的抒发,而陶、韦、柳并称,其实只是论其形似而未及情感的真实与否,张养浩在《和陶诗序》中谈道:
夫诗本以陶写情性,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既拘于韵,则其冲闲自适之意绝无所及,恶在其为陶写也哉!余尝观自古和陶者凡数十家,惟东坡才盛气豪,若无所牵合,其他则规规模仿,政使似之,要皆不欢而强歌,无疾而呻吟之比,君子不贵也。[32]
他以为拘于陶诗的韵律语言,则闲适冲淡之意不能较好表现,学习陶诗根本在于学陶诗以性情为诗,诗歌陶写性情则在很大程度上便可以除去规规模仿的弊病,而从情性理趣中流出的诗歌也能达到造语精圆、自然无斧凿痕迹的效果,充分表达诗歌的情感。进一步,元人又以“意”和“韵”来讨论陶诗,郝经《和陶诗序》云:
赓载以来,倡和尚矣。然而魏晋迄唐,和意而不和韵;自宋迄今,和韵而不和意,皆一时朋俦相与酬答,未有追和古人者也。独东坡先生迁谪岭海,尽和渊明诗,既和其意,复和其韵,追和之作,自此始。[33]
郝经所讲之“意”,不单是陶诗文本所表现的风格特征,也内化了创作主体的襟怀与思致,认为陶公“天资高迈,思致清逸”,“任真委命,与物无竞”的生命追求,使其诗歌能够跌宕于性情之表,超然属韵。而这种“意”与“韵”的完美结合,需要一种特殊的人生经历,这也就是郝经赞赏东坡和陶诗的重要原因。再进一步,元人认为陶诗的平淡风格与“貌”及“味”有密切的关系,陈旅《静观斋吟稿序》云:
三百篇而下,汉、魏诸诗弗可及已。晋、宋间,则陶渊明为最高,后世之务为平淡者多本诸此,然而甚难也。盖平则貌凡,淡则味薄,为平淡而貌不凡、味不薄,此以为甚难也。唐大名家如杜少陵诸人,不得专以是体论之。若韦苏州辈,其亦平而不凡、淡而不薄者乎![18]58
陈旅将平淡的对立面视为“貌凡”和“味薄”,后世学陶者效其平淡诗风,多流入平淡的负面价值。那么如何弃除“味薄”?元人认为需要深入体会诗歌的“景外之景”和“味外之味”,陈基《悠然亭记》云:“斯亭也,近俯太湖之苍茫,远览夫椒之嵯峨,飞鸟往还,与山气相回薄,悠然之顷,宛有真趣。此靖节所谓‘欲辩已忘言’者也。盖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自然无名,太虚无迹,言之不足,以尽其意,默之则足,以全其天。”[5]346又邓雅《读陶渊明二首》云:“吟诗不须苦,吟苦失诗意。吾笑郊岛徒,彫锼损肝肺。凯风因时来,微雨从东至。凭几诵陶诗,诗中有深味。”“我性爱陶诗,难窥数仞墙。闲来辄诵之,愈觉滋味长。太羮无盐梅,土鼓谐宫商。谁能起公死,执鞭向柴桑。”[3]678他们一致强调,学习陶诗在于涵泳陶诗中的深意、深味。这种深意、深味即陶诗中平淡而不薄的隽永内涵。而如何避免“貌凡”,在陈旅看来,超越凡俗之“貌”虽然是“天趣道韵之妙”,并非学力所能致,然而却不得不有深厚的学力。他认为摆脱凡俗,一方面需要沉潜于“理性之蕴”,“养于中者有素”。另一方面也要有超尘脱俗的生活环境,“隐居清淡之乡,日与云烟水石相上下”,从而摈除外物诱惑,悠然忘怀世间尘俗。“中有所养”“外无所诱”形诸吟咏,则自然达到平而不凡的境界[18]58。
要之,在元末,文人们无论将陶渊明解读为一位正统儒士,取法陶诗“性情之正”的内涵,还是把陶渊明解读为一位“逸士”,取法陶诗“平淡自然”的风格,他们都从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和人格中寻找到了心灵与出处、行迹的精神支撑,元末释大圭《归来》诗云:“归来溪上一茅堂,读罢陶诗倚石床。万事悠悠长啸里,闭门风雨麦秋凉。”[34]在陶诗的吟咏中,他们的心灵有了归处,精神得以安顿。当然,也在学习陶诗的过程中充分汲取了陶诗的养料,进而培育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诗学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