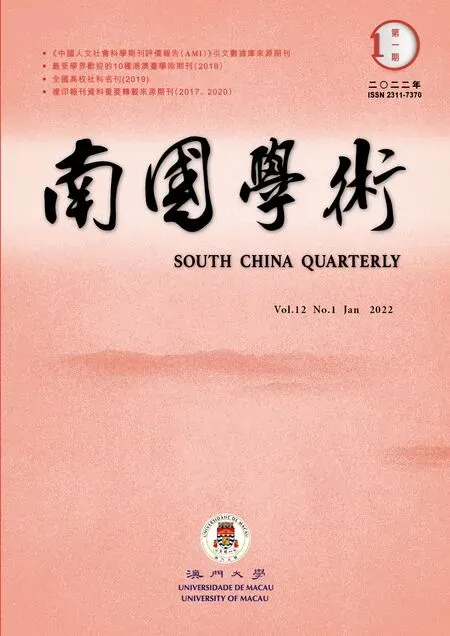賦體用“比”的批評意涵
許 結
[關鍵詞]賦學批評 六義入賦 比法 比體 物象與精神
在賦學批評中,其作爲《詩經》“六義”之一的探源說法甚多,而當賦成爲文章一“體”之後,其對《詩經》中他義的運用,又具有了創作論的特徵,其中賦體用“比”就是一個重要方面。對此,劉勰《文心雕龍.比興》首論“比”與“賦”的關係,區分賦中之“比”的諸端功用,提出“賦”中多用”比”;不過,出於《詩》學批評的立場,他認爲“興之爲義,雖精於比”,即揚“興”而抑“比”,客觀上說明了《詩》多“興”而“賦”多“比”的創作現象。繼後,相關言說不斷,最突出的是元代祝堯《古賦辯體》以《詩經》之法衡“賦”,其中用“比”說“賦”篇最多,而結合同時代的陳繹曾《文筌》有關漢賦“體物”的討論,其中列有“象體”“比體”諸端,則喻示的是以“比”入“賦”由“法”到“體”的變遷。因此,對於古人認爲賦的寫作“比”多而“興”少,宜於從賦體創作本身進行考量,方能彰顯其價值與意義。
一 劉勰的賦“比”說解
賦體用“比”是從《詩經》的“六義”而來,即《周禮.春官》“(大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毛詩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但是,在辭賦蔚然大國的漢代,並沒有“六義”入賦的說法。漢人的賦論主要談功用,說賦是“古詩之流”,講賦乃“不歌而誦”,牽涉到“六義”,也僅是賦似“風”擬說“諷諫”,或“賦”“頌”連稱,歸於“雅”正。真正將“六義”附會“賦體”始於晉人,最典型的是皇甫謐爲左思《三都賦》作序說的“古人稱不歌而頌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故孔子採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①〔南朝梁〕蕭統 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唐〕李善 註,第641頁。,將漢人說《詩》思想引入賦域。到劉勰《文心雕龍·詮賦》開篇即謂“詩有六義,其二曰賦”,顯然是承續“六義入賦”由“用”變“體”的思路,並使之概念化。而漢人解《詩經》的“比興”,如二鄭所言“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故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鄭玄)、“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鄭衆)②〔漢〕鄭玄 註、〔唐〕賈公彥 疏:《周禮註疏》,收入《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第796頁。;南朝人用之於詩歌創作,如鍾嶸《詩品》“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③〔南朝梁〕鍾嶸:《詩品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陳延傑 註,第2頁。,用之於辭賦創作,則是劉勰《文心雕龍》的《比興篇》。
根據現有文獻,劉勰是首先將“比興”用於“賦”法的。品讀《文心雕龍.比興》,其於賦法之論,以用“比”爲重鎮,可析爲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合論比興,是淵承於《詩經》而呈現於“楚騷”,其云:
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制《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誇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云構,紛紜雜沓,信舊章矣。對此,楊明照《文心雕龍校註》引“楚襄信讒”到“興義銷亡”以對應《漢書·藝文志》中“楚臣屈原……沒其諷諭之義”一段文字,認爲“足與舍人此文相發”。考劉氏所言“依《詩》制《騷》,諷兼比興”,是繼承王逸《楚辭章句序》“《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的話語④〔宋〕洪興祖:《楚辭補註》(北京:中華書局,1983),白化文等 點校,第2、3頁。。其中,由《詩經》而“騷”再到漢人賦頌“比體云構”,論點集中於第二個層面,即賦體用“比”的凸顯:
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鵩賦》云“禍之與福,何異乣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繭曳緒”,此以容比物者也。①〔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范文瀾 註,第602頁。
這段文字先明“比”義,即取類以喻於“聲”“貌”“心”“事”等,繼而摘錄具體賦句分別說明“比聲”“比貌”“以物比理”“以聲比心”“以響比辯”“以容比物”諸端,基本上都是比喻之法(包括明喻、隱喻、借喻)②周振甫:《文心雕龍註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399、400頁。。如《高唐賦》以風吹纖條比喻樂器之“竽”聲;《洞簫賦》以“優柔溫潤”的簫聲喻慈父畜子之愛憐;《長笛賦》以“繁縟絡繹”的笛聲喻戰國策士范雎、蔡澤的游說之辭鋒等。由此又引出劉勰言說的第三層面,得出賦體“比”多而“興”少的結論:
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鵠求鶩,則無所取焉。③〔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註》,第602頁。
這裏有三個視點:其一,在價值判斷上,劉勰是重“興”而輕“比”,貶抑賦家用“比”是“習小而棄大”;其二,賦體創作取法比興,以“比”爲主即“若斯之類,辭賦所先”;其三,賦體用“比”亦有優劣,優則“切至爲貴”,劣則“刻鵠求鶩”。綰合這幾點,前賢有所評析。如黃侃《文心雕龍札記》論劉氏《比興篇》云:“題云比興,實側註論比,蓋以興義罕用,故難得而繁稱。”又論其“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語云:“切至之說,第一不宜沿襲,第二不許矇矓。紀評謂太切轉成滯相,按此用措語不工,非體物太切也。”所引紀昀所評,即“亦有太切轉成滯相者。言不一端,要各有當,文無定體,要歸於是”④“紀評”引見周振甫:《文心雕龍註釋》,第396頁。。此就上述第二、三個視點而論的。又如,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有關此篇的“釋義”云:
賦家之文,多用比體,亦出自然。考興之爲義,雖精於比,而其爲用,則狹於比。……比則依情託義,可以曲折相附……而賦體本以敷佈爲用,敷佈云者,蓋有經營結構之功,與無心而發者異趣,是故唐詩宋詞,託興尚多,而漢魏辭賦,興義轉亡,體實限之也。舍人此篇辭意,雖惜興義之銷亡,而薄比體之代用,然於比、興二體盛衰之故,已能窺其本原。
這又是就上述第一、二視點陳論,其中落實於賦體對“比則依情託義,可以曲折相附”的闡釋,頗有深意。如論“賦體本以敷佈爲用”“有經營結構之功,與無心而發者異趣”,且聯繫到唐詩宋詞創作,以爲詩詞“興”多,而辭賦“比”盛,關鍵在“體實限之”⑤清人沈祥龍《論詞隨筆》比較詩與詞,認爲“詩有賦比興,詞則比興多於賦。或借景以引其情,興也。或借物以寓其意,比也。蓋心中幽約怨悱不能直言,必低徊要眇以出之,而後可感動人”。引自唐圭璋 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5册,第4048頁。,其涉及“漢魏辭賦,興義轉亡”與“唐詩宋詞,託興尚多”的詩賦史觀。
然則爲何賦體多“比”?以“體實限之”解釋,固然有其正確性,但對“六義”入“賦”的途徑以及劉勰列述賦“比”的意義,尚有未發之蘊。如果從詩賦批評的早期歷史來探尋這一問題,可以臚述如下綫索:一是由漢人兼述“風(諷喻)”“雅(雅正)”以言“賦”的致用觀,到晉人“六義”之一體的“賦”體觀,是從文學批評的觀點將“賦”獨立於《詩經》;二是由漢人如鄭玄論《詩經》之比興的功用到劉勰論“賦”中“比興”特別是“比”的功用,形成由“《詩》用”到“賦用”的演繹;三是《詩經》“六義”之“賦”體義的獨立到對其“比興”的借用,是由賦之“體(文體)”到賦之“法(技法)”的變遷,劉勰賦體用“比”論的呈現,其理論意義重在這一點。由此可見,劉勰《比興篇》的賦體用“比”,是以二鄭(玄、衆)評《詩經》之法爲媒介,完成了他的賦論觀由“賦用”到“賦體”再到“賦法”的演進過程。
回到劉勰《比興篇》中論賦法之“比”,觀其摘錄宋玉《高唐賦》、枚乘《菟園賦》、賈誼《鵩鳥賦》、王褒《洞簫賦》、馬融《長笛賦》、張衡《南都賦》中的賦句爲例,以說明“比聲”“比貌”“比理”“比心”“比辯”“比物”諸法,可見其賦法之“比”,是基於賦體句法論的。①許結:“賦體句法論”,《社會科學戰綫》1(2018):165—174。而劉勰賦句“比法”批評觀的建立,又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淵承。即東漢王逸在他的《楚辭章句序》中倡“依經立義”,即引《離騷》句子爲例,所謂“‘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維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等,這些顯然爲劉勰所取法。但相較而言,前者重在經義,後者重在“比”法,又非同一範疇。二是批評背景。劉勰《比興篇》以賦句論“比”法並非孤立現象,如他的《通變篇》論賦之“誇張聲貌”,即羅列司馬相如《上林賦》“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揚雄《校獵賦》“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張衡《西京賦》“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等賦句爲例證。又如,其《麗辭篇》論“麗辭之體,凡有四對”則以相如《上林賦》“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句爲“言對”例,宋玉《神女賦》“毛嬙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句爲“事對”例,王粲《登樓賦》“鍾儀幽而楚奏,莊舃顯而越吟”句爲“反對”例,張載《七哀》“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句爲“正對”例。②許結:“賦體駢句‘事對’說解”,《文學遺産》1(2017):16—26。如果探究這種引賦句論法則的原因,誠如劉勰《麗辭篇》所敍述的“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這又與《比興篇》以賦句論“比”法及所謂“若斯之類,辭賦所先”吻合。所以,在劉勰的論述中,賦體用“比”之法,是屬賦句論範疇的。
當然,以賦句論“比”法,同樣彰顯賦體“影寫雲物,莫不纖綜比義”的特徵,所以,“賦”的“比”多而“興”少乃“體實限之”的解釋,宜有深層的批評意涵,這也爲後世賦學批評由“比法”到“比體”導夫先路。
二 從比法到比體
從辭賦創作史來看,自劉勰引諸家賦句用“比”,漢晉以降乃至唐宋賦作,尋查其用例不勝枚舉,這決定於賦體擅長於詞章表現而多採取比喻的方法。可是,考述賦學的批評文獻,似乎繼劉勰後如唐宋時代罕有專論賦“比”之法的。南宋時,鄭起潛爲士子科考律賦作佔畢工具的《聲律關鍵》,在“五訣”之“認題”中有“比方”一法,舉賦例則如“玉比德”“太祖比迹湯武”類③王冠 編:《賦話廣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第1册,第31頁。,是就賦題而言,涉及比義,卻非比法,然於比體卻有所啓示。其後以六義之“比”說賦者,最突出的是元人祝堯的《古賦辯體》,其特點是改變前人以比法衡賦句,而以賦篇說比體。明確提出“比體”一詞的,是與祝堯同時的陳繹曾,他在《古文矜式》中提出辭賦有六種“體物”之法,分別是“實體”“虛體”“比體”“象體”“量體”“連體”,所謂“比體”乃“借物相興”;而在其《文筌·漢賦制》中又加上“影體”,其論“比體”是“設比似以體物,如賦‘雲’言‘羽旗’,‘雪’言‘璧玉’是也”④〔元〕陳繹曾:《文筌》,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713册,第477頁。按:陳氏在《楚賦制》中又有“比物”一目,釋義云:“以物比事辭通而意露,與況物絕不同。”。很顯然,陳繹曾所說的“比體”,仍是一種技法,但是他將其作爲“體物”的一種方法,結合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的說法⑤清人魏謙升《賦品》專設《瀏亮》一品,以“朗如行玉,清若流泉。疑義霧解,藻思芊綿。聰明冰雪,呈露坤乾。微辭奧旨,無弗棄捐”形象地說明陸機“體物一語,士衡薪傳”的賦論價值。引自王冠 編:《賦話廣聚》,第3册,第360頁。,其中也就內含了賦體的意義。可以說,陳繹曾所說的“七體”,是對賦“體物”的細化,而綰合七者又共呈“體物”賦的本質。
由此反觀劉勰《比興篇》論賦用“比”,也是基於對賦體的基本認識,這可以結合他在《詮賦篇》的論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論賦之本);“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論賦之用);“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賦別於詩);“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論賦之源);“麗詞雅義,符采相勝……此立賦之大體”(論賦之體)。其中“用”與“體”,即“體物”與“麗詞”,正對應用“比”的“取類不常”與“辭賦所先”的“體用”思想。唐宋時期以律賦爲闈場程文,漸失楚漢賦體,於是到宋元時代又興辭賦辨體之論,故而對賦的“物盡其態”描繪特色與“賦像班形”的審美取向予以標舉,“體物”論又由闈場律賦反歸於楚漢古賦。宋人方逢辰《林上舍體物賦料序》云:
賦難於體物,而體物者莫難於工,尤莫難於化無而爲有。一日之長驅千奇萬態於筆下,其模繪造化也,大而包乎天地。其形狀禽魚草木也,細而不遺乎纖介,非工焉能!若觸而長,演而伸,杼軸發於隻字之微,比興出乎一題之表,惟工而化者能之。前輩賦《鑄鼎象物》曰“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歌傾;鉉既上居,足想王臣之威重。”因“足”“鉉”二象,而發出經綸天下之器業。賦《金在鎔》曰:“如令分別妍媸,願爲藻鑒;若使削平僭叛,請就干將。”因“藻鑒”“干將”四字,架出擎空樓閣,“願爲”“請就”,又隱然有金方在冶之義。①〔宋〕方逢辰:《蛟峰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187册,第536頁。
天地萬物,模繪造化,乃“體物”的另一種言說,然其闡發“物態”之“肖”與“擬象”之“妙”,視闈場律體如徐奭《鑄鼎象物賦》之“足”“鉉”二“象”,范仲淹《金在鎔賦》之“藻鑒”“干將”四“字”爲“體物”之“工”的典範,也是一種賦學體用觀的呈現。與之不同,祝堯反思唐宋闈場律賦與宋代文賦之失“體”,而倡導“祖騷宗漢”的賦學觀,所謂“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爲古……心乎古賦者,誠當祖騷而宗漢”②王冠 編:《賦話廣聚》,第2册,第747、750、286頁。。如何“祖騷宗漢”?如何將漢大賦體物譬如《子虛賦》那樣“取風雲山川之形態”“取鳥獸草木之名物”的“誇”“贍”之詞引歸於體義,祝堯最突出的批評觀就是導入“六義”以論賦。如論司馬相如《子虛》謂“賦之體而兼取他義,當諷刺則諷刺而取之風,當援引則援引而取諸比,當假託則假託而取諸興,當正言則正言而取諸雅,當歌詠則歌詠而取諸頌”③王冠 編:《賦話廣聚》,第2册,第747、750、286頁。。其中論“比”,已非摘句之法,而是通冠全篇,最常見的是“比而賦也”。例如,評禰衡的《鸚鵡賦》:
比而賦也。其中兼風家常便飯之義。虛以物爲比,而寓其羈栖流落、無聊不平之情。讀之可爲哀欷。凡詠物題當此等賦爲法,其爲辭也,須就物理上推出人情來,直教從肺腑中流出,方有高古氣味。
又如,評張華的《鷦鷯賦》:
比而賦也。凡詠物之賦,須兼比興之義,則所賦之情不專在物,特借物以見我之情爾。蓋物雖有情,而我則有情;物不能辭,而我則能辭。要必以我之情推物之情,以我之辭代物之辭,因之以起興,假之以成比。④王冠 編:《賦話廣聚》,第2册,第747、750、286頁。
所謂“比而賦”,賦是鋪陳,爲其體義,“比”爲方法,烘託賦義,以成其篇章之“體”。合觀上引祝堯評述的兩篇賦作,要在“就物理上推出人情”與“以我之情推物之情”,其與劉勰摘句說“比”之法雖不盡同,然其比喻的本義仍是相近的,衹是祝氏以全篇明賦體爲要則。綜觀祝堯《古賦辯體》用“比”,與劉勰《比興篇》列舉六篇賦的句子述“比”不同,反而是“楚騷”多而“漢賦”少。以該書卷一、卷二“楚辭體”爲例,《九歌》冠以“賦而比”語,落實到具體篇章,如《東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東君》《山鬼》皆“賦而比”,《湘君》《湘夫人》是“兼興而比”,《少司命》則“兼六義。然全篇比賦之義固已在風興雅頌之中矣”;《九章》中則《涉江》《抽思》《懷沙》皆“賦而比”,《思美人》《悲回風》乃“比而賦”;至於《卜居》爲“賦,中用比義”、《九辯》“興而賦”,而“似叔世危邦之象則比也”,其間無不用“比”。由於以通篇作品冠以“比”體,所以異於劉勰論賦摘句說“比”,其於卷三、卷四“兩漢體”中僅舉賈誼《吊屈》“比也”,禰衡《鸚鵡賦》“比而賦也”,餘則皆“賦”。至於“三國六朝體”與“唐體”,亦僅有張華《鷦鷯賦》、鮑照《野鵝賦》、駱賓王《螢火賦》、李白《大鵬賦》四篇署以“比而賦”。而其“外錄”所收續騷之作卻多用“比”,如賈誼《惜誓》、韓愈《訟風伯》、息夫躬《絕命辭》諸篇爲“比而賦”,嚴忌《哀時命》“出入比賦”,邢居實《秋風三叠》“賦中有比”,陶潛《歸去來辭》“賦中兼比”等,其義附着於“楚辭體”,故多用“比”。
對照劉勰與祝堯論賦用“比”,其差異又不僅在摘句(重“法”)與整章(重“體”),所不同者更在對“楚辭”態度截然不同。劉氏以“騷”近《詩經》,故“興”多而“比”少;漢賦騁詞喻意,故“比”多而“興”少;祝氏取義則“楚辭體”用“比”多,而“兩漢體”則用“比”少。究其緣由,在於宋元以後賦體批評觀的變化。落實到“六義”入“賦”包括用“比”之意,主要表現出兩大徵象:
一是《詩經》對“賦”引領作用的強化。考《詩經》之“六義”衡賦,自《周禮》“六詩”、《毛詩序》“六義”、鄭玄等人的《詩經》說,到皇甫謐、劉勰等引入賦體論而完成,然或論“體”(賦爲六義一體),或論“法”(如用“比”),未衷一是,到了唐宋孔穎達、朱熹論《詩經》提出“六義”三經三緯的“體用”思想,始發生一大折變。孔穎達在《毛詩正義》疏文中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①〔漢〕毛亨:《毛詩正義》,收入《十三經註疏》,〔漢〕鄭玄 箋、〔唐〕孔穎達 疏,第271頁。分別“異體”與“異辭”以爲體形與體用。繼後《朱子語類》卷八十記載朱熹答弟子問云:“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卻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又提出了“三經三緯”說,其中說風雅頌中都有賦比興,以明“三緯”用於“三經”的詩篇之“用”,已蘊含了體義。朱熹說法的批評實踐,就是他《詩集傳》以“比興”論詩篇。在《詩集傳序》中,朱熹明其編撰《詩經》旨云“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落實到具體詩篇的用“比”或“興”,正是基於章句而明其體式。如《邶風·柏舟》朱註“比也”,觀該詩首章“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遨以遊”,朱氏疏解云:
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爲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泛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爲無酒可以遨遊而解之也。②〔宋〕朱熹《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1958),第15頁。
論此詩用“比”,既是解題與章句分析,也是全篇體式的評說。正是這種方法被祝堯完全移植到《古賦辯體》,構建了以“比”論“體”的格式。例如,評賈誼《吊屈原賦》“比也”,即“《吊屈原賦》全用比義”,而“於比義中發詠歌嗟嘆之情,反覆抑揚,殊覺有味”;③王冠 編:《賦話廣聚》,第2册,第145頁。正是兼括題義、章句與體式的比喻,將賦者與被賦者涵泳爲一,而不落迹象。
二是“楚辭”於賦“體”的強力介入。漢人視戰國楚邦屈原等人的作品是“賢人失志之賦”,故《漢志》列目“屈原賦”,辭賦是不分的。但就創作而言,漢代散體大賦與騷體賦還是有着明顯的不同。故漢晉以來,從劉向、王逸編輯《楚辭》之文、阮孝緒《七錄》別立其目,到了南朝劉勰分述《辨騷》《詮賦》、蕭統《文選》於“賦”外別“騷”爲一體,即《文選序》云“楚人屈原,含忠履潔……騷人之文,自茲而作”,楚騷從文體性質得以獨立。到了宋代大量註騷之作,其中如洪興祖的《楚辭補註》、朱熹的《楚辭集註》以其全帙傳世而固化了騷體批評的意義。就其批評方法而言,朱熹《楚辭集註》同於《詩集傳》,由“六義”說《詩經》轉向解“騷”,其差別在“《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落實到具體篇章,或評析章句,或通述全篇,如《離騷》前部分的描述文字,即重在句法,除了“賦也”,其“比而賦”一處,“賦而比”十一處,“比也”十三處。如評“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所謂“比也。成言,謂成其要約之言也。悔,改也。遁,移也。近曰離,遠曰別。言我非難與君離別也,但傷君志數變易,無常操也”。至於論“篇”,如《九歌》之《東皇太一》“全篇之比也”,《云中君》則“比之比”。如評《東皇太一》篇云:
此篇言其竭誠盡禮以事神,而願神之欣說(悅)安寧,以寄人臣盡忠竭力,愛君無已之意,所謂全篇之比也。①〔宋〕朱熹:《楚辭集註》(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蔣立甫 校點,第33頁。
朱熹的說法與劉勰不同,劉氏認爲《離騷》近於《詩經》,故興多,而朱氏以爲《離騷》變於《詩經》,故比多;其論句法用“比”,同於劉氏之說,然觀其通論篇法,則表現了由章句到體式的變化。由於《騷》辭“比”多,直接影響到祝堯《古賦辯體》卷一、卷二《楚辭體》的用“比”之論。觀其評述《東皇太一》:
全篇賦而比也。言己至誠盡禮以事神,願神之欣悅安寧,以寄人臣竭力盡忠,愛君無已之情。又古者巫以降神,神降而下託於巫,則見其貌美服好,身雖巫而心則神也。②王冠 編:《賦話廣聚》,第2册,第48—49、337—338頁。
其主要內容幾乎抄錄《楚辭集註》語,而略有發揮,所不同者一謂“全篇之比”、一謂“賦而比”,這實與祝堯再次將《楚辭》納入賦域相關。由此再看祝堯評鮑照的《野鵝賦》:
比而賦也。此賦雖亦尚辭,而其凄惋動人處實以其情使之然爾。遐想當時明遠賦此,豈能無慨於其中哉。以六朝之時而有賦若此,則知辭有古今而情無古今。③王冠 編:《賦話廣聚》,第2册,第48—49、337—338頁。
通過這段評述鮑照具體賦作的話,其中內含了祝堯賦論的多重思考:回歸《詩》《騷》傳統,論賦重在情、理、辭三者合一,而尤其重“情”於中的根本作用;論賦作以“騷”情爲榜樣,所以用“比”並不着重於“句法”,而更寄意於通篇的“喻體”,即擬情的關懷;而更重要的則是再次將曾經“別騷一體”的《楚辭》納入賦域,以標舉其“祖騷宗漢”的理論思想。④“祖騷宗漢”的賦學觀並非《古賦辯體》獨有,是元人針對六朝駢儷、唐宋律俳及文賦創作的反思而産生的集體意識。如袁桷《清容居士集·策問》對“古賦當祖何賦”問云:“屈原爲騷,漢儒爲賦。”劉因《敍學》云:“三百篇之流,降而爲辭賦,離騷楚詞,其至者也。”正基於此,纔出現賦“比”旨歸於“騷”的審美趣味,是楚騷強力介入賦域,脫化出由“比法”(論句)到“比體”(謀篇)的新思考。
三 賦“比”多“興”少的反思
從劉勰到祝堯,在其論賦用“比”的歷史批評空間,實際經歷了兩個轉向:一是由論《詩》取法(包括“比”)到論賦摘句言法之“比”的轉變;二是由論賦句法之“比”向論賦體義之“比”的轉變。而無論是摘句還是明體,如劉勰《比興篇》所評說的,抑或祝堯《古賦辯體》所臚舉的,其論賦都是“比”多而“興”少。探究這種“比體雲構”的現象,也不能僅限於賦作陳辭的語言特徵,或者是一種修辭手法,還應關注其體義的品格建構。這又可從探源、呈象、精神三個層面加以說明。
就探源而論,賦體用“比”決定於《詩經》之“六義”入“賦”,這成爲歷代賦學批評的常態,並不限於某一體。例如,以《詩經》之“風雅頌”衡賦,路德《詩賦準繩序》云:
凡作詩賦,寫景抒情者,風之意也;揆時審勢者,雅之遺也;歌功論德者,頌之體也。就一篇論之,其中端而虛者,得於風者也;和而莊者,得於雅者也;雍容揄揚而近實者,得於頌者也。業詩賦者,必先學爲風人,然後本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⑤〔清〕路德:“關中書院課士詩賦序”,《檉樺館文集》(運城:解梁刻本,清光緒七年,1881)。
此合論詩賦,兼取三“體”。或僅論一體,如趙鏞《六義賦居一賦》云:
然而義爲辭轡,辭爲意輪。義析之有六,辭萬變而皆循。風雅頌爲經,體殊別而不相雜;賦比興爲緯,用參錯而還相因。侔色揣稱,兼資乎比興;指事徵理,必在於敷陳。以宣士德於遐陬,則顓蒙共喻;以抒下情於黼座,則幽情畢。⑥〔清〕趙鏞:“六義賦居一賦”,《賦海大觀》(上海:鴻寶齋印本,清光緒二十年,1894),卷10。
以一體之“賦”兼取“六義”,取資前人經緯體用之說,所謂“兼資乎比興”,也屬泛論。清代康熙帝《御製歷代賦彙序》認爲“賦者,六義之一也。風、雅、頌、興、賦、比六者,而賦居興比之中,蓋其鋪陳事理,抒寫物情,興、比不能並焉,故賦之於詩功尤爲獨多”①許結 主編:《歷代賦彙(校訂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第1册,第1頁。,是從三“用”即於“比、興”間獨成“賦”體以論其價值。於是,又或由賦體兼及“比興”之用,如劉熙載《賦概》云:
賦兼比興,則以言內之實事,寫言外之重旨。故古之君子上下交際,不必有言也,以賦相示而已。不然,賦物必此物,其爲用也幾何!
他主張:“春有草樹,山有烟霞,皆造化自然,非設色之可擬。故賦之爲道,重象尤宜重興。興不稱象,雖紛披繁密而生意索然,能無爲識者厭乎?”②〔清〕劉熙載:《藝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97、98頁。所以,論其要略,賦體用“比”是與《詩經》之“六義”的體用觀相關,尤其是作爲“三用”的賦比興,賦自成一“體”而兼及“比興”之“用”,至於其用法或摘句、或謀篇,以“用”歸“體”,旨趣皆一。而從上引劉熙載的話語,其所言“尤宜重興”是承續劉勰重“興”而輕“比”思想的,但其關注的“賦物”與“稱象”問題,又聯繫到“興象”與“比物”的創作實際,前者重於詩,後者偏於賦,則是賦體用“比”多的歷史呈現,且關涉到賦創作自身的語言特徵。
賦體“比物”的呈現,決定於賦的“體物”方式,而其體物的作用,又在於呈象以取義。這也就需要賦家用大量描繪性的語言再現世界,形成劉勰《詮賦》中言賦“蔚似雕畫”的特徵。所以,在陳繹曾《文筌》中所分解漢賦的七種“體物”形態,最接近於賦體語言描寫本質的是“象體”與“比體”。與“設比似以體物”的“比體”相比,“象體”儘管又分“扇象”“碎象”“排象”諸法,然究其根本是“以物之象貌,形容其精微而難狀者”,所以採用諸如“縹”“爛煥”“浩然”“皇矣”“赫兮”“峨峨”“崔嵬”等象詞(包括大量的叠字與連綿詞),以彰明賦中之“物象”。如果說“象體”是直觀物象的描寫,則“比體”是借物寓象的方法,以折射物象的喻意。從這樣的思路來看,確實是楚騷“比體”相對多些;而漢大賦因面對外在事象的呈現,尤其是劉熙載《賦概》所言“賦起於情事雜沓,詩不能馭”的特徵,故多以“象體”顯物。而到東漢以降,賦體向以小篇詠物、抒情的變化,包括向楚騷的回歸,“比體”顯然有所增加。例如,寫“美人”,司馬相如《上林賦》的描寫是“靚妝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嬽嬽,嫵媚孅弱,曳獨繭之褕紲,眇閻易以恤削,便姗嫳屑,與俗殊服。芬芳漚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綿藐”,多用如“綽約”“嬽嬽”“嫵媚”“粲爛”“連娟”等詞法,以象貌形容其精微難狀。而曹植的《洛神賦》的書寫方法是“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仿佛兮若輕雲之蔽月,飄搖兮若流風之回雪。遠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穠纖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若約素”,連用喻詞即“驚鴻”“游龍”“秋菊”“春松”“輕雲”“流風”“朝霞”“芙蕖”“約素”,無一語直觀美人,卻達到借物寓象的效果。③有關辭賦的“象體”,詳見許結:“漢賦‘象體’論”,《文學評論》1(2020):167—175。由此,最易表現賦體因物呈象方式的“象”“比”二體的比較。可見,無論是劉勰出於“六義”之“比”的言說,還是陳繹曾出於“體物”方式的義例,落實到具體的賦作描寫,均屬借物寓象的功用與方法。因此,所謂賦體用“比”多,也是基於其語言表現的最本質特徵。
賦體用“比”多的原因,還不限於詞章的描寫或篇章的定義,似宜考慮賦家基於章句而超越章句的主體精神的建構。在“六義”進入賦體評述其創作法則以前,賦作之“比”的呈現在“比喻”之法,而更爲明顯的是“比德”之用。取其廣義,也是從《詩》教而來。如清人程廷祚認爲,“漢人說《詩》,不過美刺兩端”④〔清〕程廷祚:《青溪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宋效永 校點,第38頁。;而漢人說賦,亦如班固《兩都賦序》所言“或以抒下情而通諷喻,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①〔南朝梁〕蕭統:《文選》,第21頁。,也是或“美”或“刺”。這又與古代王朝的政教思想相關,例如,《周禮·地官》中記述的王朝教育官的“師氏”“保氏”之職,所謂“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保氏則“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其中的“媺”就是美,含有“頌上德”之義,而“諫王惡”可衍爲“抒下情”之諷。如果對照比興,所謂喻德主“興”,諫惡主“比”,即鄭玄《周禮註》所言的“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的功用。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比”“興”與師保的教育思想有着淵承聯繫。衹是在具體的發展過程中,作爲賦的寫作,漸漸強化了如“比方於物”與興“託事於物”(鄭衆)的方法,“比”的“諫惡”功能淡褪,而得以兼取“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王逸《離騷經序》)的美刺觀。也正因爲“比”的功用往往涵蓋了賦的美刺兩端,也使其在賦中的能量越來越大,甚或成爲其主體精神的營構方式。這不僅在賦作中如劉勰所言“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的全面展示,而在具體作品中,其關鍵詞語也是以“比”的方式表現。例如,《世說新語·文學》記錄一則有關袁宏寫《東征賦》的故事: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勛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煉,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勛,爲史所讚。”
陶公,指陶侃;胡奴,侃子陶範,後者因袁宏賦中沒有表彰先公勛績,竟白刃相向,致使作者“窘蹙無計”,情急中以賦中數語應對。這則故事劉孝標註引《續晉陽秋》另載其人:“宏爲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爲《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啓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聞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衆爲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爲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爲允也。’溫泫然而止。”故事中的人物變了,但袁宏以其賦中說道陶侃或桓彝勛業,或謂之“精金百煉”,或謂之“風鑒散朗”,“稱”人之美,皆用“比”法。同樣的道理,祝堯在《古賦辯體》中界定《楚辭.思美人》是“比而賦也”,並申述理由云:
其謂寄言於雲,而雲不將;致辭於鳥,而鳥難值。今薜荔爲理,而憚緣木;因芙蓉爲媒,而憚濡足。原之思何時釋邪!《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當是時也,有能思原之思者乎!②王冠 編:《賦話廣聚》,第2册,第83、84頁。
以其所思之“美人”比喻屈子“獨醒”“獨清”之人生,美其操守而警示世道之混濁,既爲全篇之體義,又是其創作精神之所寄。
“比”法用於賦章主體人格(或文章品格)的展現,且基於賦作擅長比喻的語言特徵,而旨歸於《詩經》“六義”之一的神聖性,或許正是賦體用“比”的藝術呈像及其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