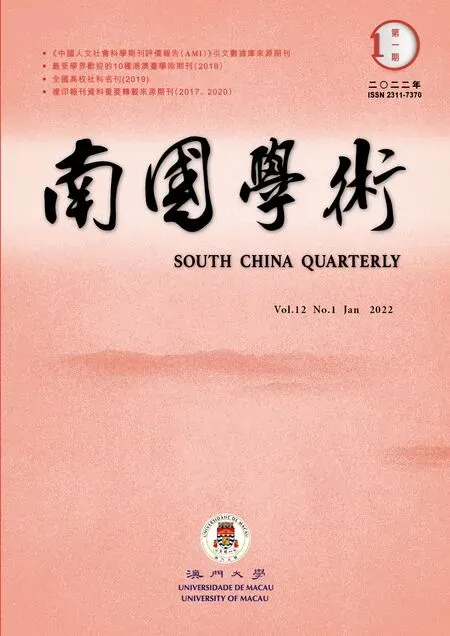走出馬基雅維利政治思想的現代性迷思
——解決西方兩派紛爭的新進路
吳業國
[關鍵詞]馬基雅維利 邪惡 共和主義 權力政治 現代性價值
引 言
1532年,意大利學者馬基雅維利(N. Machiavelli,1469—1527)的《君主論》在其死後五年得以出版。在書中,他試圖深入探討權術問題,提出了“邪惡”(evil)主張,大意是:君主必須懂得善用野獸之道,當遵守信義反而對自己不利時,英明的統治者絕不能、也不應遵守信義;施恩應細水長流,而傷害則應乾脆利落。①施特勞斯指出,馬基雅維利並不是第一個表達類似觀點的人,這種觀點由來已久。柏拉圖也曾借用其筆下人物卡里克勒斯、特拉西馬庫斯闡發這些邪惡的政治信條;修昔底德則是藉古代雅典的戰爭使節來宣揚同樣的主張。施特勞斯特別指出,衹有馬基雅維利,敢於在他名下,無所忌憚地闡發這種信條〔Leo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Seatt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10〕。之後,他又在《論李維》書中進一步將“邪惡”闡釋爲“德性”“機運”“自由”等,認爲英勇且富有領導力的君主應具有傲慢勇敢、殘酷有力、願意作惡這些美德。②Jack Donnell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75-177.上述主張和闡釋,使後來的讀者頗感震驚。
由於“邪惡”問題是構建馬基雅維利形象的重要進路,因此,在20世紀以来的西方政治學界,主要有兩種理解並形成兩個學派:一派是施特勞斯(L. Strauss,1899—1973)等人所堅持的傳統觀點,把馬基雅維利看作專制與暴政的邪惡導師,對權力政治無限推崇,由此衍生了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從《君主論》的命運看,出版不久即遭譴責,1559年更是被列入教皇保羅四世的禁書目錄;在17—18世紀歐洲的荷蘭,馬基雅維利長期被用作一切政治惡行和去道德政治行爲的象徵。③[德]吉塞拉·波克、[英]昆廷.斯金納、[意]莫里齊奧·維羅里 編:《馬基雅維里與共和主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閻克文、都健 譯,第340—343頁。馬基雅維利被惡魔化後,其學說和思想日漸庸俗化,人們將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手段的邪惡上,甚少有人考慮其思想背後深層次的原因。
另一派是以波考克(John. G. A. Pocock)爲代表的劍橋學派,致力於探討馬基雅維利學說中的愛國主義或共和價值。這源於在馬基雅維利那裏,德行與惡行奇怪地結合在一起,所以,他们力圖從歷史政治環境與其思想的理想指向上爲他辯護。其實,在17世紀,哈林頓(J.Harrington,1611—1677)就在《大洋國》一書中闡發了馬基雅維利是要恢復古人的經綸之道④[英]詹姆士·哈林頓:《大洋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何新 譯,第6頁。;斯賓諾莎(B. d. Spinoza,1632—1677)也認爲,馬基雅維利是出於某種善良的用心說明,暴君是無法剷除的,獲得自由的民衆衹需要“慎於將自己的身家性命完全委託給一個人”。⑤[荷]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溫錫增 譯,第44頁。之後,盧梭(J-J. Rousseau,1712—1778)在《社會契約論》裏多次援引並對其給予同情的理解:“《君主論》乃是共和黨人的教科書。”⑥[法]盧梭:《社會契約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何兆武 譯,第91頁。盧梭在註釋中對他的觀點進行補充:馬基雅維利是個正直的人,也是善良的公民;但由於依附美第奇家族,所以不得不在舉國壓迫之下把自己對自由的熱愛僞裝起來。黑格爾(G. W. F. Hegel,1770—1831)更認爲,要理解《君主論》,必須考慮馬基雅維利以前和所處時代的意大利的歷史,“它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天才所作的最偉大最高貴的精神創造”。⑦關於黑格爾對馬基雅維利思想的評論,還可見《哲學史講演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賀麟、王太慶 譯,第3卷,第375頁。這些辯護者們在《君主論》末章以及《論李維》中發現了作者對意大利統一的激情呼告,看到了他擁有共和理想的愛國者形象。這使得後來者有堅定的信心去探尋馬基雅維利留下的現代政治思想遺產,致力於探尋共和主義“德性”“自由”概念的思想源泉。
20世紀至今,馬基雅維利的形象愈加分裂,學術爭議聚焦在馬基雅維利與現代政治的關係上。學者們不斷從方法論的角度追問,馬基雅維利的“邪惡”言論是如何開啓價值中立的政治科學的?或者說,它是如何對人類政治活動作出價值判斷的?進而探究,他的政治思想究竟是權力政治學說還是公民共和主義⑧蕭高彥:“從君主治術到政治創建:《李維羅馬史疏義》導讀”,《李維羅馬史疏義》(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3),第522頁。?以期走出馬基雅維利“邪惡”思想的現代性迷思。
一 方法論上的爭議:政治科學?
在《君主論》中,馬基雅維利結合個人的政治實踐,通過回顧古代羅馬共和主義的發展,展開了對基督教歐洲神學政治困境的反思,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政治思想。他強調對現實政治的討論,而不是想象中的共和國或君主國。①The Prince, Chap.18, in Machiavelli: 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volume.1, 61. 他認爲,理想的共和國與君主國未曾在現實生活里出現過。本文關於《君主論》《論李維》的英文引文,均出自該文集,並參考潘漢典、馮克利的中譯文,個別地方有改動。他深知,審慎與技藝在奪取政治權力或者治理國家時的重要性,因此,儘管他本人未曾使用過“政治科學”一詞,仍被後人認爲是政治科學之父。例如,卡西爾(E. Cassirer,1874—1945)就將馬基雅維利與伽利略(G. Galilei,1564—1642)相提並論,以強調其現代性意涵,認爲伽利略的動力學奠定了現代自然科學的基礎,“馬基雅維利也爲政治科學開闢了一條新路”②[德]恩斯特·卡西爾:《國家的神話》(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范進 譯,第162頁。,將西方擺脫古典而引向現代。
不過,視馬基雅維利爲現代開端人物的施特勞斯,對於馬基雅維利是不是政治科學家卻意見含糊。一方面,他在《論僭政》裏認爲,“一切特定的現代政治科學依賴於馬基雅維利鋪設的基礎”③Leo Strauss, On Tyrann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24.;另一方面,又在《關於馬基雅維利的思考》一書中認爲,馬基雅維利的著述“充斥着‘價值判斷’,他對於社會所作的研究屬於規範性的”④Leo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11.。即便如此,施特勞斯仍然意識到,“馬基雅維利在本質上是一位愛國者”⑤Leo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11.。這意味着,他承認馬基雅維利對現代政治科學的影響,但並不把他當做科學家看待。
在施特勞斯眼中,馬基雅維利在兩個方面發展了傳統的政治哲學。首先,提出了通達政治事務的現實主義路徑,這不同於傳統政治哲學的理想主義;其次,馬基雅維利認爲“命運”是一個女性,可以通過力量加以控制。理想的傳統政治哲學基於對自然的特殊理解,認爲一切自然存在者都指向一個終極目的,一個它們所渴望成就的完善狀態,因而古典政治哲學所追尋的是對德性之踐履最具指導性的最好政治或政制,但這種最佳政治秩序的建立卻必須依賴於難以把握的命運或機運。藉助於馬基雅維利,施特勞斯注意到了古典政治哲學將道德前置而現代政治哲學將道德後置的差異性。不僅如此,機運是可以被駕馭的,政治社會甚至是最值得嚮往的政治社會的建立並不依賴於機運。⑥[美]施特勞斯:“現代性的三次浪潮”,《蘇格拉底問題與現代性——施特勞斯講演與論文集(卷二)》(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彭磊 等譯,第34—37頁。
施特勞斯的這一主張,得到了其弟子曼斯菲爾德(Harvey C. Mansfield)等人的追隨。曼斯菲爾德從“傳統”來看馬基雅維利政治理論的現代意義,認爲現代性一旦確定也就成爲傳統,若要保持現代性就需要更加現代,而這是危險的。因此,他主張,爲了理解現代,“必須審視他的開端”。⑦Mansfield, “Machiavelli’s Political Scie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5(1981):294, 293.他回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那裏,認爲衹有馬基雅維利一人明確主張追求“創新”(novelty),並將馬基雅維利的現實主義與現代政治科學緊密聯繫起來。
需要注意的是,曼斯菲爾德不是從“事實—價值”兩分的角度去闡述馬基雅維利的政治科學的,因爲馬基雅維利不做價值判斷。他認爲,馬基雅維利作爲政治科學之父,教給人們的是對人類利益的追求,通過對生存的承諾,把“政治科學與追求人類利益的進步關聯起來”。⑧Mansfield, “Machiavelli’s Political Scie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5(1981):294, 293.曼斯菲爾德延續了施特勞斯學派的一貫作風,探討了作爲帝王師的馬基雅維利,其政治科學的意圖是要將政治科學家與哲學王的傳統區分開來,彰顯出馬基雅維利政治科學的意義。
同樣,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強調政治的阿倫特(H. Arendt,1906—1975)並沒有像其他研究者那般重視馬基雅維利的政治科學,包括他的現實主義。她認爲,馬基雅維利在政治思想史上的獨特位置與他通常受到讚揚的現實主義沒有太多關聯,他並非政治科學之父,柏拉圖纔是。①Hannah Arendt, “What is authority”,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Penguin Books,1977), 137.
伯林(I. Berlin,1909—1997)比阿倫特走得更遠,他否認馬基雅維利作品裏有政治科學的因素。認爲馬基雅維利的學說肯定不是建立在17世紀的科學基礎上的,因爲他生活的時代要早於伽利略、培根(F. Bacon,1561—1626)一百年,他的方法如同前科學的經驗醫學,是一個由經驗之談、觀察、歷史知識和一般的機敏組成的大雜燴:“他滿腦子都是各種箴言、有用的警句、實踐心得、漫無邊際的思考,尤其是歷史類比,儘管他聲稱要去發現一般規律,即永遠有效的普遍法則。”②[英]伯林:“馬基雅維利的獨創性”,《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馮克利 譯,第50頁。
持反對意見的還有將馬基雅維利解讀爲公民共和主義的維羅里(Maurizio Viroli)。他認爲,不論人們如何界定“科學”這個概念,主張馬基雅維利是近代政治科學的創建者是錯誤的,因爲他並不打算建立一門政治科學,而是“力圖找回和提煉可供用作修辭實踐的政治理論的一些概念”。③Maurizio Viroli, Founders of Modern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 2-3.與伯林一樣,維羅里指出,如若科學意指可證明的,或者是代表伽利略的研究方法,那麽,在馬基雅維利那裏是找不到類似方式的,他使用大量歷史事例嘗試提出作爲總的原則框架。因此,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學說並不是近代意義上的“科學”。④Maurizio Viroli, Founders of Modern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 2-3.
二 權力政治與共和主義之爭
1969年以後,關於馬基雅維利的研究出現了一個新的轉向,即專門以核心理念爲研究主題。學者和評論家並不衹是關注那些難以捉摸的“基本問題”,而是“轉向了馬基雅維利哲學裏的‘基本概念’”⑤John H. Geerken, “Machiavelli Studies since 1969”,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7 (1976):360.。其核心是圍繞權力政治與共和主義之間的論爭,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從基本主題上的解釋,探究馬基雅維利的政治主張究竟是權力政治還是公民共和主義;二是對其核心概念的解讀,最爲重要的是“德性”“機運”“自由”。而且,很多研究者的進路是將核心概念的解釋整合到對基本問題的探討上,進而解讀馬基雅維利對政治的現代理解。
(一)政治的自主性與權力政治
1.人類“必需”與政治的自主性。沿着科學解讀馬基雅維利政治思想的思路,就會碰到政治與道德的問題。這是不少研究者探究馬基雅維利原創性的出發點。他們從技藝的角度去解釋馬基雅維利的政治思想,並將他的政治學觀念轉移到技藝領域,爲政治尋找一個衹屬於政治的地盤,在那裏與道德無關。“他把政治從其他許多方面的考慮中孤立地抽出來”⑥[美]喬治·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鄧正來 譯,第394頁。,政治本身就是目的。政治與道德的區分,也是對馬基雅維利所具有的獨創性最普遍的一種說法。但恰恰是這個問題,使得馬基雅維利本已複雜的思想更像是一個謎了。科克倫(E. W. Cochrane,1928—1985)在1961年就認爲,馬基雅維利可能是一個永遠難以解決的難題,這個難題在過去三十年裏一直吸引着意大利學者們,“對之做出了詳盡的闡述”。⑦Eric W. Cochrane, “Machiavelli:1940-1960”,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3(Jun, 1961): 113-136.科克倫認識到,“必需”(necessity)與“自主”(autonomy)是馬基雅維利政治思想的核心,使得政治在善惡的道德之下,“有着難以抵抗的規則”。⑧Benedetto Croce, Politics and Moral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45), 59.科克倫的後繼者認爲,馬基雅維利並沒有否認基督教道德的正確性,但這種道德並不適用於政治事件,因爲任何政策如若依賴於道德則會以災難告終。因而,對當時政治實踐所做的實事求是的客觀描述,正是馬基雅維利內心苦惱的標誌。⑨Eric W.Cochrane, Machiavelli: 1940-1960. 這些說法是科克倫等人對馬基雅維利政治思想的理解概括。對於馬基雅維利而言,道德是一回事,政治是另外一回事。“馬基雅維利對大衆的道德與宗教對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影響並非漠不關心。”①[美]列奧·施特勞斯、約瑟夫·克羅波西:《政治哲學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李天然 等 譯,第395頁。
關於馬基雅維利的政治自主性,沃林(S. S. Wolin,1922—2015)給予了更加強勢的支持。他認爲,馬基雅維利之所以被譽爲第一位真正的現代政治思想家,不衹是與中世紀思想模式的決裂,還包括了對傳統準則如自然法的擯棄,以及對幾乎專門集中於權力問題的實用主義分析方法的探索,從而賦予馬基雅維利政治思想的現代性,“其試圖從政治理論中排除任何不表現出絕對政治性的成分”②Sheldon S. Wolin, Politics and Vision: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4), 199.。
此類將馬基雅維利的政治思想視爲一種政治自主性的觀點,依賴於對其政治“必需”所作的探究。而這些探究,則是基於馬基雅維利本人在《君主論》《論李維》中對人性所作的一般性的判斷:“他們是忘恩負義、容易變心的,是僞裝者、冒牌貨,是逃避危難、追逐利益的。”③Nicollò di Bernado,Machiavelli: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volume.1, 62, 63, 111-112,57-58, 66, 519.“對自己父親的死的忘記比遺產的喪失還要快。”④Nicollò di Bernado,Machiavelli: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volume.1, 62, 63, 111-112,57-58, 66, 519.因而,一個國家在立法的過程中,必須秉持“所有人都是邪惡的,衹要有機會,他們總是會發洩他們頭腦中的仇恨”⑤Nicollò di Bernado,Machiavelli: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volume.1, 62, 63, 111-112,57-58, 66, 519.。而且,人從不行善,除非必需驅使他們如此,“當他們有太多的選擇自由並能如其所欲而行,那麽,混亂和無序便會到處蔓延”。⑥Machiavelli, 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 volume.1, 112.
2.權力政治與國家理由。在前述人類的“必需”之下,能夠看到權力政治若隱若現的影子。“君主但凡可能,就要行善;若有必要,就要爲惡”這樣的概括,符合馬基雅維利對政治自主性的主張,也是對馬基雅維利的權力解讀的開端。他們聚焦於馬基雅維利在政治領域裏對權術的強調,認爲政治手段、軍事措施幾乎是馬基雅維利唯一關心的課題,而且這些手段和措施與宗教、道德幾乎完全分割開來,政治活動的目的是“爲了保存和擴大政治權力本身”。⑫[美]喬治·薩拜因:《政治學說史》,第397、394、396、394頁。因此,將政治與道德區分開來,通過藉助以權力爲目標,結合人性導致的必需,這些學者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衹對政治權力這單一的目標感興趣,而對其他一切則漠然置之”⑬[美]喬治·薩拜因:《政治學說史》,第397、394、396、394頁。。
在這種情況下,對馬基雅維利權力政治做辯護的通常是基於國家理由。首先,“治國之道、興邦之術、增強國勢之策和導致國家衰亡之虞”⑭[美]喬治·薩拜因:《政治學說史》,第397、394、396、394頁。,成爲馬基雅維利文本的核心內容。在《君主論》《論李維》中,這樣的主張比比皆是:君主爲了保持國家,常常不得不作出“背信棄義,不講仁慈,悖乎人道,違反神道”⑮Nicollò di Bernado,Machiavelli: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volume.1, 62, 63, 111-112,57-58, 66, 519.的行爲,不必考慮行爲正當與否,撇開殘暴與仁慈、榮耀與恥辱之間的糾葛,拋棄所有的顧慮,“一心思考能夠拯救祖國生命、維護祖國自由的策略”。⑯Nicollò di Bernado,Machiavelli: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volume.1, 62, 63, 111-112,57-58, 66, 519.
“保衛祖國應當不計榮辱,不擇手段”,後來被馬基雅維利的好朋友圭恰迪尼(F. Guicciardini,1483—1540)概括並經由邁內克(F. Meinecke,1863—1954)闡發爲“國家理由”。邁內克認爲,馬基雅維利的一生同國家的最高目的緊密結合,其政治思維方式是思考國家理由的“一個不斷的過程”。①[德]弗里德里希·邁內克:《馬基雅維里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時殷弘譯,第87、51—53、89—90、63頁。所謂國家理由,是“告訴政治家必須做什麽來維持國家的健康和力量”,政治家一旦確信自己對形勢的理解準確無誤,就應依照它來行動,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國家理由呈現出深刻和嚴重的國家必需。國家及其民衆的福祉被當作終極價值和目的,而權勢理所當然地成爲一種“必不可少的、無保留地必須獲取”的手段。②[德]弗里德里希·邁內克:《馬基雅維里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時殷弘譯,第87、51—53、89—90、63頁。在馬基雅維利那裏,他看到個人無法逃避他與生俱來的對權勢的慾望,因此,他希望靈魂與肉體結合起來創造英雄主義,造就一種新的自然主義倫理,這種倫理“將無所偏袒和義無反顧地遵從自然的指示”,而馬基雅維利的德性正是“創立和維持欣欣向榮的國家,特別是共和國所需的力量”。③[德]弗里德里希·邁內克:《馬基雅維里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時殷弘譯,第87、51—53、89—90、63頁。邁內克以共和國所需替馬基雅維利的“爲惡之途”進行辯護。根據邁內克的觀點,當統治者變成了自身權勢的僕人的時候,權勢“開始制約他個人,不讓他隨心所欲。這個時刻一至,‘國家理由’就誕生了”。④[德]弗里德里希·邁內克:《馬基雅維里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時殷弘譯,第87、51—53、89—90、63頁。因而,國家理由在道德上呈現出曖昧性,客觀的國家利益對掌權者構成了限制。由此,一個服膺於獨立權威的君主形象就出現了。這與前揭曼斯菲爾德藉助執行官發現馬基雅維利近代執行理念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
(二)道德二元論
然而,與上述詮釋體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不管是伯林還是劍橋學派,他們都反對科克倫的主張,拒絕認爲馬基雅維利區分政治與道德。在伯林看來,政治自主性是對馬基雅維利的誤解。而政治自主性對權力政治的強調,同樣困擾着另外一批嘗試追溯至亞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 ,前384—前322)古典共和傳統的“劍橋學派”的學者。
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裏認爲,把馬基雅維利與其同時代人之間的分歧,說成是政治的道德觀點與政治和道德分開的觀點之間的分歧,是不恰當的,“最主要的差別倒是在於兩種不同的道德之間——對於最終應該做些什麽這個問題所存在的兩種對立的和不可調和的看法”。⑤[英]昆廷·斯金納:《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奚瑞森 等譯,上卷,第213—214頁。馬基雅維利衹是拒絕了道德論證的結構,認爲想要維持君主的地位與國家,就必須時刻準備在需要的時候違背各項道德和政治德行。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他持有爲了維持國家可以去做任何事情的觀點,相反,他堅信君主德性的重要性。⑥[英]昆廷·斯金納:《國家與自由:斯金納訪華講演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第36—37頁。
專門就科克倫的這個區別提出反對意見的是伯林,他是從否認馬基雅維利的政治科學觀開始的。認爲馬基雅維利的成就不在於把政治學從倫理學中解放出來,那是科克倫和許多評論家強加的。馬基雅維利所成就的事情要深刻得多,這就是對兩種不可調和的道德的區分。一方是異教徒世界的勇氣、活力、百折不回、公共成就、秩序、紀律等道德,以及對保證其實現所需知識和權力的維護,這也是一個道德或倫理的世界,它們體現着最高的人類目標;另一方是基督教的慈愛、憐憫、愛上帝、寬恕敵人等道德,這比任何社會、政治或其他現世的目標,以及任何經濟的、軍事的或美學的考慮都更爲高貴。⑦[英]伯林:“馬基雅維利的獨創性”,《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第54—55、64—65頁。伯林所作的兩種道德之間的區別,是一種亞里士多德式的理解。他先是區分了兩個世界,一個是個人道德的,一個是公共組織的。這兩個世界都是人類最高的。然後認爲,政治行爲是人性中固有的行爲,人類群體沒有選擇的機會,共同生活決定了其成員的道德義務。“對於這樣理解的倫理學,一個人除非瞭解其城邦的目標和性格,否則便無從知曉,更不可能哪怕是從思想上去擺脫它了。這是馬基雅維利不假思索便接受的前基督教道德觀。”⑧[英]伯林:“馬基雅維利的獨創性”,《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第54—55、64—65頁。伯林基於古希臘城邦倫理,賦予政治以倫理目的,認爲政治生活與人類最高目標密切相關,然後根據馬基雅維利讚成伯里克利(Περικλ ,前495—前429)那樣一個會有人爲所追求的(公共)目標犧牲生命的世界,從而認爲馬基雅維利的價值也是道德價值。進而闡發其政治思想內含着公共道德的要求,因爲“人的本性指向了一種公共道德。”①[英]伯林:“馬基雅維利的獨創性”,《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第73頁。
伯林通過追溯馬基雅維利與亞里士多德傳統的關係作出解讀,意在區分馬基雅維利的政治思想裏存在兩種道德,從而將之作爲多元主義的開端。但是,他的這種闡釋,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公民共和主義的進路,成爲從馬基雅維利政治思想中尋找公民美德的主要來源。
三 劍橋學派與施特勞斯學派的論爭
關於馬基雅維利是否“邪惡”,劍橋學派與施特勞斯學派之間存在激烈的衝突。這裏以兩個學派的主要觀點爲主綫,呈現兩派關於馬基雅維利的學術論爭。
2.2.1建成区扩展数量和强度德州市主要建成区从1997年的85.39 km2增加到2017年的151.56 km2,净增长面积达66.17 km2,增加了1.77倍,平均年增长3.30 km2(见表2).
(一)共和主義及其批評
1.共和主義解讀的開端與承續。劍橋學派重視研究的歷史語境,在研究方法上獨樹一幟,與施特勞斯學派的文本解讀形成了鮮明對照。②[英]昆廷·斯金納:《國家與自由:斯金納訪華講演錄》,第200頁。劍橋學派對馬基雅維利解讀的路徑是,將其與15世紀以來意大利人文主義政治思潮關聯起來,並向前追溯至亞里士多德、西塞羅(M. T. Cicero,前106—前43)所塑造的公民共和主義傳統。這主要以巴隆(H. Baron,1900—1988)、斯金納、波考克、維羅里爲代表。
18世紀以前的西方,與16—17世紀的學者對馬基雅維利的態度一致,普遍將馬基雅維利視爲專制與暴政的倡導者,認爲馬基雅維利破壞了亞里士多德式政治理念,“他把人類的高貴藝術轉化爲暴君統治的藝術”。③Maurizio Viroli,“Machiavelli and the republican idea of politics”, 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viersity Press, 1990), 143.但是,哈林頓寫於1656年的《大洋國》逆時代主流,將馬基雅維利視爲共和主義者,這爲劍橋學派重新詮釋馬基雅維利的共和主義思想提供了靈感;尤其是哈林頓對“審慎”作出“古典”與“現代”的區別,並在此基礎上對馬基雅維利定位:上帝向人類所揭示並得到希臘人和羅馬人追隨的“古典審慎”,是依據古典明智構建起的“法治政府”,是“公民社會基於公共權利與利益獲致構建與持存”,相反,作爲一個人或少數人統治一個城市或一個民族的藝術的“現代審慎”,是依據他或他們的私人利益建構的“現代政府”,制定法律保護着一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它是“人治而非法治政府”。④維羅里在這里闡釋了哈林頓的區分(Maurizio Viroli,“Machiavelli and the republican idea of politcs”, Machiavelli and Republism,144)。作此區分後,哈林頓認爲“馬基雅維利是唯一力圖回歸前者的政治學家”。⑤J. Harrington, 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61.
此後一個多世紀裏,將馬基雅維利作爲共和主義的解讀進路消失了,直到巴隆1966年勾勒出古典共和主義思想在文藝復興時期重興的圖景後,纔開始重新出現。⑥Hans Baron,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巴隆及其後的吉爾伯特(F.Gilbert,1905—1991)⑦Felix Gilbert, History: Choice and Commitment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viersity Press, 1977).都將《君主論》當做一本獨立的作品來解讀,力圖從中挖掘馬基雅維利思想的共和主義要素。他們發現了共和國公民的道德品質與專制君主的臣民素質間的深刻不同,而馬基雅維利不再是一位不偏不倚、道德中立的觀察者,或一個自我陶醉、一心衹考慮自己內心的個人問題、“苦惱地”將公共生活看做道德原則葬身之地的人。⑧Hans Baron,“Machiavelli: The Rebulican Citizen and the Author of ‘the Prince’”,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76(1961):217-253.
2.古典共和主義的復興。在巴隆的影響下,斯金納、波考克、維羅里等人對馬基雅維利的共和主義進行了深入解讀,形成了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學術思潮中古典共和主義的復興。但他們對馬基雅維利的關注,多是對“自由”“德行”等關鍵觀念的詮釋。
斯金納試圖發展出有別於自由主義傳統對自由的理解,來處理消極自由與積極參與、個人權利與公民美德之間的悖論。①斯 金納寫了一系列文章來探討自由的概念,“The Paradox of Political Liberty”;“The Republican Ideal of Political liberty”,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viersity Press, 1990);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斯金納認爲,馬基雅維利是一個“古典共和主義的人文主義傳統的最傑出的代言人”②[英]昆廷.斯金納:《馬基雅維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王銳生 等譯,第12頁。。他在《論李維》一書中發現,共和主義思想家們所訴諸的並不是積極自由的概念,而是一種沒有訴諸個人權利、依賴於自治共同體的消極自由:“馬基雅維利的學說是一種消極自由學說,他在發展這一學說時根本沒有涉及個人權利的概念。”③Quentin Skinner, “The Idea of Negative Liberty: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Philosophy in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18, 207-208.但是,這種自由觀念同時包含着公民參與的必要性。它依賴於特定的共同體形式,“衹有採取自治的共和制共同體形式,個人自由纔能得到充分保障”,這是一切古典共和主義公民學說的核心與中樞。④Quentin Skinner, “The Idea of Negative Liberty: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Philosophy in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18, 207-208.斯金納總結馬基雅維利的共和主義精髓有二:第一,如果不堅持自由的生活方式,任何城邦都不可能實現偉大;第二,如果不維護共和政制,任何城邦都不可能堅持自由的生活方式。⑤[德]吉塞拉·波克、[英]昆廷·斯金納、[意]莫里齊奧·維羅里 編:《馬基雅維里與共和主義》,第197—198、218頁。
波考克的《馬基雅維利時刻》則試圖爲美國共和主義繪製思想譜系。他將一系列共和主義,從亞里士多德開始,經由佛羅倫薩的布魯尼(L. Bruni,1370—1444)、馬基雅維利,到最後把英國、美國都納入這一思想傳統中來。《馬基雅維利時刻》與斯金納1978年出版的兩卷本《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一起,被認爲是“劍橋學派”歷史寫作方法的代表作。按照波考克的說法,該書撰寫的歷史既是歷史性的也是共時性的。
《馬基雅維利時刻》一書所探討的是羅馬意義上的“德性”,力圖復興的是個人採取政治和軍事行動的能力;並且堅信,佛羅倫薩人首先提出“積極公民”的觀念。它源於亞里士多德所表達的“政治的動物”的理想,在馬基雅維利這裏等同於公民參軍打仗。⑥[新西蘭]波考克:“從佛羅倫斯到費城——一部共和國與其替代方案之間的辯證史”,《共和主義:古典與現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6頁。顯然,這一點波考克與巴隆是一致的。與此同時,他還堅信馬基雅維利思想中“衹有武裝的公民纔是真正的自由人”⑦[新西蘭]波考克:“從佛羅倫斯到費城——一部共和國與其替代方案之間的辯證史”,《共和主義:古典與現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6頁。,從“武裝的”“積極的”公民的盛衰角度,揭示羅馬、佛羅倫薩、英格蘭、歐洲以及一般的公民社會的歷史是如何被重寫的。至此,他超越了巴隆。
波考克對自己所理解的德性與斯金納做了區分。他認爲,斯金納所發現的13世紀那種西塞羅式的理想是關注人類社會的全部利益,更多的是正義,但馬基雅維利並沒有討論過正義問題。波考克則是從伯林的視野主張“權利”與“德性”不可通約,試圖在天生具有的權利與自身發現並在與同類共同行動中表現出來的德性之間劃出界限。⑧J. G. A. Pocock, “Virtues, Rights and Manners: A model for Historians of Political Thought” , Politocal Theory 3(1981):353-368.因此,他認爲馬基雅維利式公民應該關注“某一有着超強德性的公民能否通過確立一種平等規則”,最終實現自我約束;而不是斯金納筆下西塞羅式“法與正義之下公民共同體”。⑨[新西蘭]波考克:“從佛羅倫斯到費城——一部共和國與其替代方案之間的辯證史”,《共和主義:古典與現代》,第13頁。在他看來,馬基雅維利的思想裏存在一種類似於亞里士多德的德性與命運的對立關係,當共和國遭遇臨時限制時,仍力圖在非理性事件中保持倫理與政治的穩定。波考克正是藉此將馬基雅維利視爲中繼,勾勒出共和主義的綿長傳統。⑩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511-513.
延續共和主義的觀點,維羅里認爲,馬基雅維利追隨着先人關於共和主義的觀點,堅信政治的主要目的是塑造和培育公民的情感,以一種不太讓人熟悉的方式用“政治的”(politico)一詞表示共同體的實際生活,實際是對古代的完全讚同。⑪[德]吉塞拉·波克、[英]昆廷·斯金納、[意]莫里齊奧·維羅里 編:《馬基雅維里與共和主義》,第197—198、218頁。面對他人否定馬基雅維利共和主義政治觀的觀點,維羅里提出:“馬基雅維利沒有否定共和主義政治觀,也沒有否定政治人。毋寧說他是重新加工了城邦哲學的語彙,使之在新的政治背景下發揮作用。”①[德]吉塞拉·波克、[英]昆廷·斯金納、[意]莫里齊奧·維羅里 編:《馬基雅維里與共和主義》,第239—240頁。
3.對共和主義解讀的批評。與此同時,劍橋學派對馬基雅維利所作的共和主義解讀,也受到了來自兩方面的批評。一是施特勞斯的學生,主要是曼斯菲爾德。他反對波考克、斯金納等人誤解馬基雅維利的共和主義,指出馬基雅維利與傳統道德哲學的“德性”概念已經沒有關聯:在亞里士多德那裏,道德德性是被作爲政治的目的;而在馬基雅維利那裏,則是一種政治化的德性。馬基雅維利從來就沒有提過什麽共和德性,哪怕他確認共和國要優於君主國。②Harvey C. Mansfield, Machiavelli’s Virtu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23.二是麥考米克(John P. McCormick)。他認爲,“劍橋學派”一方面沒有注意到共和主義傳統中的寡頭制傾向,另一方面沒能注意到馬基雅維利政治思想中堅定的反精英主義。馬基雅維利是一位尚未得到承認的折中派,介於最小民主理論、精英民主理論家與更具理想主義色彩的參與民主理論家之間。這種折中,使馬基雅維利更接近於平等民主論者,而不是通常所認爲的精英論者、共和論者或實質民主論者。馬基雅維利既承認精英極有可能在最包容的民衆政體中獲得大部分職位,但也強調普通民衆可以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希望以一種更加嚴厲的手段來控制精英。因而,馬基雅維利的政治理論從根本上說是民主主義,而非共和主義。③John. P. McCormick, “Machiavelli against Republicanism:On the Cambridge School’s ‘Guicciardinian Moments’”, Political Theory 31(2003):615-643.關於麥考米克對馬基雅維利民主理論的進一步闡釋,可參見John. P. McCormick, “Machiavellian Democracy: Controlling Elites with Ferocious Populis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June 2001):297-313.
(二)施特勞斯學派對傳統觀點的重申:邪惡的導師
施特勞斯雖然將馬基雅維利視爲現代政治哲學的奠基者,然而他在意圖與方法上明顯不同於科克倫等人的政治自主性主張。在《關於馬基雅維利的思考》一書中,施特勞斯反對將馬基雅維利詮釋成政治科學家或愛國者,重申馬基雅維利在傳授邪惡。他認爲,馬基雅維利其實屬於一個類型獨特的愛國者,他的愛國主義是在祖國的位置與靈魂的位置之間作出均衡,因此,“將馬基雅維利這個思想家描述成一位愛國者是混淆視聽”;縱然被迫接受馬基雅維利學說是愛國主義,那也是一種對自身的愛,在品位上低於對自我與道德上的善所應懷有的愛。施特勞斯反復強調的是,馬基雅維利是在傳授邪惡。這樣纔能對馬基雅維利“作出恰如其分的應有認識:他的思想的勇敢無畏,他的目光的深邃廣闊,以及他的語言的優美雅致”。④Leo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10-13, 27-28.
爲此,施特勞斯首先將注意力回歸到《君主論》上,這也是他與共和主義者的重要區別。因爲,《君主論》是一本獻給君主的書,渴望賞識器重,而不少研究者包括斯賓諾莎、盧梭卻認爲,《君主論》衹是針對君主的一部諷刺作品。在施特勞斯那個時代,研究者普遍認爲,馬基雅維利學說的充分表述存在於《論李維》中,“以致人們閱讀《君主論》,必須總以《論李維》作爲參照的指南,而絕對不可以衹讀《君主論》”;而且,這是共和主義者經由巴隆復興以來一直採取的研究進路。但施特勞斯認爲,有理由假定,君主在馬基雅維利進言之前就懂得某些嚴酷的真理,馬基雅維利向一個君主進言的時候,“更爲直抒胸臆、無可諱言”,因此,《君主論》“比《論李維》更爲直言不諱”。⑤Leo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10-13, 27-28.他通過馬基雅維利文本中的矛盾探究馬基雅維利的意圖,最後回歸到對馬基雅維利最簡單的看法上,即他是在傳授邪惡。
(三)衝突與統一:關於馬基雅維利形象的論爭
有意思的是,儘管兩個學派都意識到馬基雅維利政治作品中存在的衝突,但都力圖描繪馬基雅維利統一的形象。例如,劍橋學派的斯金納認爲,《君主論》與《論李維》的政治教訓如出一轍,兩書可統一爲一個基本論點:“任何人‘無論採取何種異乎尋常的行動,衹要對於組成一個王國或締造一個共和國有幫助’,都不能加以譴責,否則就是不近情理。”⑥[英]昆廷·斯金納:《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上卷,第284—285頁。斯金納在《論李維》最後一卷結尾處發現了馬基雅維利將國家的生存與自由置於首位,而一切其他的考慮則束之高閣。自盧梭以來,共和主義者傾向於將《君主論》視作一部諷刺性作品,強調根據《論李維》來閱讀《君主論》,以降低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不區分暴政專制與君主政制、也不區分君主私人野心與仁民愛物的公益德行所帶來的道德壓力。施特勞斯學派同樣致力於提供一個統一的馬基雅維利。曼斯菲爾德直言,《論李維》有着更多的共和主義因素,而《君主論》更多的是君主制甚或專制政體的因素。①Harvey C. Mansfield and `Niccolo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Livy (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22.
然而,劍橋學派斯金納和曼斯菲爾德的兩種解釋,並不足以提供一個完整的馬基雅維利形象。前者凸顯愛國主義,將馬基雅維利的“德性”詮釋成“共和德性”,力圖建立起一個正大光明的馬基雅維利形象。這雖然緩和了馬基雅維利的邪惡主張給人帶來的道德張力,但反對者認爲這是對馬基雅維利的誤讀,因爲馬基雅維利從未提過什麽共和德性。②曼斯菲爾德對共和主義的解讀進路強烈反對,認爲馬基雅維利並非如常人所言是共和德性的信徒,哪怕他的確認爲共和國要優於君主國〔Harvey C. Mansfield, Machiavelli’s Virtue(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23〕。對共和主義的批判還可見John P. McCormick,“Machiavelli against Republicanism: On the Cambridge School’s‘Guicciardinian Moments’”,Political Theory 5(Oct.,2003):615-643.至於曼斯菲爾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解釋進路,彰顯出各自內部的張力,但這種進路忽視了二者之間的共性。
與劍橋學派相反,施特勞斯強調《君主論》更直言不諱地道出了馬基雅維利的真義,因此他否認對國家的熱愛是馬基雅維利最珍愛的資源,反對以共和福祉來爲違反道德的政策或行動辯護。並且,以此反對對馬基雅維利作出愛國主義的解釋,因爲這種解釋未能讓人們看清真正的邪惡。若以愛國主義爲理由,則會將“惡”修飾爲“善”,從而將本是善與惡的衝突轉化成善與善的衝突。
實際上,不管是在善的多元價值之間的抉擇,還是對永恆善惡界限的僭越,雙方都傾向於將注意力集中在價值判斷上。伯林或共和主義者力圖在馬基雅維利的世界裏尋找到善,而施特勞斯則要在馬基雅維利的邪惡裏重新發現永恆存在的“抉擇”(alternatives),認爲在愛國的分量與靈魂的分量之間的均衡構成馬基雅維利“邪惡”思想的核心。
圍繞着馬基雅維利的邪惡展開的張力,雙方的分歧最終集中體現在如何看待其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波考克反對將馬基雅維利視爲現代“第一位”政治思想家,認爲其所倡導的價值是極端意義上的“古代”價值,這正是理解早期近代君主制“共和”思想之吊詭面相的關鍵。③[新西蘭]波考克:“從佛羅倫斯到費城——一部共和國與其替代方案之間的辯證史”,《共和主義:古典與現代》,第15頁。在這個基礎上,伯林認爲馬基雅維利的世界裏存在着兩種互不相容的生活方式:異教徒的道德與基督教的道德,據此認爲馬基雅維利是第一位二元論的思想家。但伯林並沒有將馬基雅維利視爲現代政治的開創人物,在他看來,並不存在什麽現代性的特徵。④[伊朗]拉明·賈漢貝格魯:《伯林談話錄》(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楊禎欽 譯,第57頁。施特勞斯學派則堅信,馬基雅維利是現代政治乃至現代性的開端人物。施特勞斯非常重視馬基雅維利在《論李維》開篇中的宣示:發現了新的體制和秩序;這種發現如予傳播,將很危險;儘管如此,他仍然要將馬基雅維利的發現傳播出去。⑤Leo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36.正是馬基雅維利宣稱要建構一種新秩序,使得他重新審視將霍布斯(T.Hobbes,1588—1679)視爲現代政治第一人的主張。⑥[美]列奧·施特勞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導論》(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申彤 譯,第3頁。到了晚期,施特勞斯更是視馬基雅維利爲現代性三次浪潮的肇始者,將現代性看作是對前現代政治哲學的徹底變更。在這個標準下,施特勞斯堅信,霍布斯雖是第一個與不充分、不健全的政治哲學傳統的決裂者,但衹是接續了馬基雅維利首創的現代政治思想。
結 語
20世紀以來,圍繞着馬基雅維利的“邪惡”問題,西方學術界立足於現代政治建構,存在着兩種截然對立的研究進路。施特勞斯學派基於傳統的觀點,試圖將馬基雅維利與現代政治的興起聯繫起來;而以波考克爲代表的劍橋學派將之視爲中繼,認爲承續了亞里士多德的共和主義傳統。對馬基雅維利的“邪惡”問題指涉的“德性”“機運”“自由”等概念,兩種對立的研究進路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詮釋,並呈現出權力政治與共和主義之爭。兩派的長期爭論,凸顯了一個分裂的馬基雅維利形象。進入當代,備受訾議的馬基雅維利的形象更具對立性:“馬基雅維利是現代政治科學、形而上政治學與國家理性之父;馬基雅維利是異教道德與現代喜劇、馬基雅維利主義以及反馬基雅維利主義之父……他是共和自由的愛國者導師,同樣也是專制君主制、恐怖主義以及絕對主義的導師。”①John H.Geerken, “Machiavelli Studies Since 1969”,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7(1976),351.在浩繁文獻之下,馬基雅維利儼然成爲謎一般的人物。由於研究者力圖構建起一個統一的馬基雅維利形象,卻又無法對其達成一致,因此,“自馬基雅維利之後,每一代研究者都宣稱已經發現一個不同於其前輩所理解的‘新’的馬基雅維利”②Eric W. Cochrane, “Machiavelli:1940-1960”,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3(Jun., 1961),113.。
既然馬基雅維利被普遍認爲是政治思想史的革命式人物,他的著作打開了先前被神學和道德所佔據的政治場所,從中世紀政治反思的宗教和道德傾向中解放出來,試圖就原始權力的運作達成現實的論述;③Claude Lefort, Machiavelli in the making (Evanston: No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12),77.那麽,面對劍橋學派與施特勞斯學派紛爭所造成的馬基雅維利難題,當今學術界就需要科學認知馬基雅維利作爲現代政治的開端,以及他的政治哲學與西方現代性政治思想興起之間的關係,從而呈現馬基雅維利政治思想的現代性價值。
首先,關於馬基雅維利的現代轉向的討論,以往常常集中在其政治歷史著述中,接下來可以憑依黑格爾“考慮他所處時代的意大利歷史”的倡議,呈現其完整形象。馬基雅維利是一位對時代有着高度自覺性的政治家和作家,因此,對其《君主論》《論李維》《佛羅倫薩史》《曼陀羅》等文本的理解,應當置於其賴以形成的那個歷史語境中分析,進而爲重新審視馬基雅維利與現代性政治思想興起之間的關係提供全新視角。
其次,重新理解現代政治的意涵。由於馬基雅維利的學說極富爭議,涉及在政治行動中是否應該遵守的原則,因而是否將馬基雅維利視爲現代政治的開端人物,影響着人們對現代政治的理解。例如,在馬基雅維利《君主論》“邪惡”問題的語境中,或認爲他是現代政治的開創者,或認爲他承續了亞里士多德的共和傳統,並使之延續到美國共和主義者那裏。這就需要結合馬基雅維利本人作爲政治家的個人經歷、意大利民族四分五裂的狀態與馬基雅維利對一個統一的意大利的渴望,以及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與商業社會形成等歷史語境,對其進行文本分析與外部解釋,清理兩種不同觀點之間的邏輯進路與內在缺陷,歸納其思想意涵在現代性政治思想形態生成過程中佔有的地位,在此基礎上,對現代政治做出新的理解。
最後,審視現代性政治形態的生發要素。評判馬基雅維利的現代轉向問題,應在歷史與理論兩個維度上同時觀察和分析現代性政治思想的興起。與傳統傾向於對馬基雅維利所涉及的古今問題一刀切的解讀不同,今後的研究似應展現出馬基雅維利在現代轉向上的複雜性及其現代感的微妙性,從而對馬基雅維利與現代政治的關係做出新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