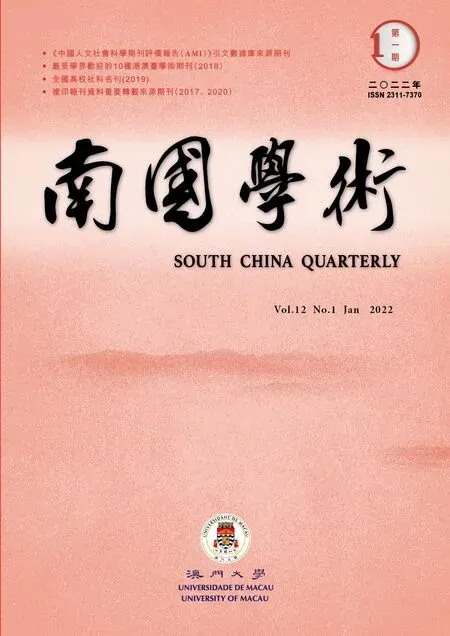古代中國“酒哲學”文脈鉤沉
趙建軍
[關鍵詞]中國“酒哲學” 儒道釋特徵 民族化
古代中國的“酒哲學”意識,源於早期公共性社會意識解體爲個體化的精神創造,即從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思想開始的。而秦漢之後發展起來的以儒、道、釋爲代表的“酒哲學”思想,又成爲中國哲學的重要內容。在古代中國,由於“酒哲學”立足於民間文化意識和哲學觀念,不僅推動了儒、道、釋“酒哲學”的發展,而且始終保持自身與生活實踐的緊密結合,對民族意識的形態與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基礎意義。
一 倫理本體:儒家的“酒哲學”觀念內核
中國哲學的原始胚胎是早期公共性社會意識。巫師作爲群體情緒和意念的代表,通過“觀象立意”方式創生了“河圖”“洛書”和“先天八卦”宇宙論直覺思維。夏商周時期,原始公共性社會意識向禮樂同構方向發展,依託於“後天八卦”的人文意識覺醒,建立了《周易》卦象系統,初步奠立了中國哲學的思維模型,而後就在這種公共化哲學思維的胚胎中,孕育了個體化的哲學思想創造。
這種個體化的哲學創造,在爲特定時代統治者代言意義上,顯示其鮮明的意識形態性質。在思想家個體專注於獨創性表達時,即使他可能還不屬於一定統治階層的核心成員,也能夠以仿佛遊離於階層之外的開放視野,表徵超越現實的思想需求,給特定統治階層帶來永恆利益的思考和觀念設計。故此,個體思想家的哲學創造,具有被統治者和其他階層普遍認可的可能性。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創始人孔子、孟子在躍升到意識形態性質的哲學思考的同時,高度關注了酒與飲食問題,提出了與其思想體系相一致的“酒哲學”觀念。儘管這些觀念在整個體系中佔比不高,但“酒”這種特殊的物質天然地黏合了與精神生活相關的廣闊領域,因而,儒家的思考就不單單是基於爲某一階級、階層謀劃的一種敍談,而是切實從酒飲的實際生活出發,關注酒與生命、文化的本質關係,從而使儒家關於酒的哲學思考深刻體現了思想家的深邃,現實地提升和推進了時代文化與哲學的理論發展。
儒家的“酒哲學”所關心的核心問題是酒與“仁”“禮”的關係。孔子、孟子從維護“禮”的政治秩序出發,主張對“仁”的道德精神完善。基於這樣的前提,充分肯定酒的怡悅情志的功能價值。儒家學派的後繼者,遵循先儒的“酒哲學”觀念,使酒成爲古代中國文化合理、辯證認知的對象,充實了以倫理、道德制約酒飲的精神內核。
——孔子“酒哲學”的禮、樂統一觀。孔子從酒的價值意義角度來理解其本質:(1)酒以“禮”“仁”爲本。《論語·爲政》:“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對這段對話,後世註家的主要分歧是,服勞之事、酒食供養算不算“孝”。三國時期的何晏所撰《論語集解》 認爲,“服侍”“酒食”本身不在“孝”的意義範圍,但也不與“孝”義相乖,人子盡可將“服勞”“酒食”與“色難”諸般事侍弄好,使酒食合於禮,歸於仁,則孝道亦體盡。清人劉寶楠《論語正義》對此提出異議,認爲沒有孝心、仁心,沒有內在的深愛,要做到表情上的“和氣”“愉氣”“婉容”,談何容易!其實,孔子以“色難”舉諸酒食之譬喻,當是歸結在禮、仁爲本的“孝道”之上;不論是“順承父母色”,抑或人子“和顏悅色”,都是內在仁心、孝心的一種發散,都是遵循禮序的體現。當然,“服勞”“酒食”本屬事物性存在,與內在的仁、禮含蘊不同,但酒食以禮、仁爲本,本質是社會性、文化性、倫理性的,孔子對此看得很清楚。(2)酒當符合禮的法度。在孔子之前,大禹、周公都有“酒禍國”“酒亂性”的認識,主張禁酒。孔子則從倫理價值角度,辯證認識到酒的社會角色與價值,强調酒應在禮制規範下發揮其積極的價值、意義。《論語·雍也》:“觚不觚,觚哉!觚哉!”《說文》:“觚,鄉飲酒之爵也。”段玉裁註:“鄉亦當作禮,鄉飲酒禮有爵觶,無觚也。”在孔子看來,鄉飲用觚,就是一種對酒的禮制、規範的逾越,因而對此提出批評。(3)酒內在通樂,酒飲的佳境是禮、樂的統一。《論語·鄉黨》記述了孔子對飲酒、食肉的觀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主張飲食應主副食搭配,肉可以多吃,但“食氣”即肉食的熱量不能勝過主食;而酒飲,以不醉爲度。在這裏,孔子把酒從一般飲食對象中分離出來,賦予了特殊的意義、價值內涵。因爲,酒飲的情形獨特,因人而異,它內在地與“樂”相通,可以體仁達樂,所以,能飲則飲,不硬性節制,以免束縛性情,仁心無由表達,情志無由宣泄。據史料所載,孔子本人善飲,《孔叢子·儒服》說:“堯舜千鍾,孔子百觚。”但北魏高允《酒訓》卻指出:“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爲妄也。”其實,孔子能否飲酒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酒哲學觀飽含深刻的文化識見,深刻揭示了酒的社會、文化本質,對後儒士子影響甚大。
——孟子“酒哲學”的“仁義外化”觀。孟子繼承並推進了孔子的“酒哲學”思想,把酒放在社會、文化語境中討論,揭示酒飲行爲的社會、文化價值內涵。這主要體現在:(1)仁義在心,不假外求。《孟子·盡心下》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他認爲,所謂內心的仁義,是遵循聖賢禮法的志意。擁有仁義,就能守持恭儉的初衷,氣勢上傲睨富貴、珍物和美酒,有守則不患無,得仁則不懼有,志意舒展,巍巍然“己之氣象”,呈現出“孔子則無此矣”①〔宋〕朱熹:《孟子集註》(日本:京都寺印製,寬正七年,1795)。的民本主體價值態度。(2)酒飯可養生,須以品德修養爲先、爲重。在《孟子·離婁下》中,以酒事爲話語,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大意是:齐国某男,每從外面回來就摆出酒足飯飽姿態,炫耀聚飲者皆頭面人物。其妻妾外出盯梢,發現此男竟是到荒郊祭奠亡人處吃剩飯殘酒。其妻妾爲之羞愧不已,相擁而泣,不想該男子歸來後仍在妻妾面前得意洋洋。孟子通過這一故事,強調品德修養的重要:飲酒吃飯雖是人的日常需要,但若品格不正,把酒飲作爲誇飾或傲慢的資本,衹會爲人不恥。《孟子·告子上》還引《詩經·大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認爲:“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綉也。”意思是說,仁義飽滿,就不羡慕別人的美味佳餚;口碑好、名譽好,就不會艷羨別人穿的錦繡衣服。孟子將孔子純粹的主體心性及仁德概念,擴大爲可外化的仁義概念,並依於性、命各存其理的認識,强化了對酒的社會價值的詮釋,進一步拓展了儒家的社會倫理思想。
——儒家後繼者的“酒哲學”思想拓展。儒家後繼者以歷代卿大夫和在野士人爲主體。他們發揚孔孟所強調的酒的社會、文化本質與功能,推動儒家思想進一步向現實化、生活化方向發展;同時,還對上古和前儒家時期的公共哲學意識給予了應用性改造。譬如,西漢董仲舒對陰陽五行觀念進行了體系化理性處理,東漢班固的讖緯思想強化了陰陽五行的感性體驗,此後,儒家話語權衰落,但已奠定的“酒哲學”理論卻推動了陰陽五行的工藝、技術應用。在唐宋時期,儒家回歸道統,不僅驅動酒哲學進一步現實化、世俗化,而且徹底地使之詩化了。如果說,在唐以前,不論漢代的司馬相如、揚雄所寫的酒賦多麽富麗奔放,世人仍不免有“勸百而諷一”之譏;魏晉的阮籍、嵇康雖然鄙視名教禮義、敢於逆悖世俗,也不過佯醉掩飾乖張,或在倫理規範的制約下難以盡心表達。那麼,唐宋詩人、詞人則不然,他們皆善飲酒作詩,性情表達不受拘限。至元明清,酒成爲藝術家、詩人表現生命情志的最好憑藉和伴侶。在儒道釋融合背景下,儒家後繼者或具儒家傾向的士人的詩化“酒哲學”認知與道家、釋家相比,所做出的貢獻就更爲突出,並且佔主導地位。這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性情表現成爲中國酒文化最本質的觀念。詩化“酒哲學”在唐宋之後成爲酒文化的主脈,不僅深刻影響了“酒哲學”的文化呈現,而且影響了酒文化的總體發展邏輯。所謂詩化哲學,是指以生命情志表現爲目的的思維、思想系統。唐詩、宋詞、元明戲曲、明清小說,都是詩化哲學的外化形態,都深刻表達了中國的哲學理念。中國文化重在以生命情志爲本體,重在“由內而外”的呈現,“重在表現理趣、情致、神韻等。詩文之好者,其價值正在使人必須隨時停下,加以玩味吟詠,因而隨處可使藏焉、修焉、息焉、遊焉,而精神得一安頓歸宿之所”①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第78頁。;而酒催化了詩化哲學的觀念、情感、趣味,許多文人雅士通過此媒介使情感更加飽滿、更趨幽婉,使情志一泄爲快;而對那些情志淡泊高遠者,則以酒託志,逍遙無礙。
二是儒家“酒哲學”的核心理念更趨精密和系統。宋代的理學、心學,經過對道家、佛家思想的過濾和攝取後,在處理“理”與“慾”的關係上更爲周緻圓融。在宋代理學語境下,“酒哲學”重視“氣”的合理性,主張酒飲爲養,與道德心、氣養相一致。“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②〔宋〕程頤:“周易程氏傳”,《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724、847、844頁。,“坎”卦卦辭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牅,終無咎。”程頤釋之曰:“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至也。”③〔宋〕程頤:“周易程氏傳”,《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724、847、844頁。意思是,坎,水也。坎爲復卦,險中有險,“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爲有孚之象”④〔宋〕程頤:“周易程氏傳”,《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724、847、844頁。。所謂“中實”,即本質性、決定性的品質。程頤認爲,繁複的禮儀和華麗的修飾,都不能通達“其心”,不如用一樽酒、兩簋食,再奏上美樂,可以直揭本心。所謂“納約自牅”⑤程頤特以臣“進結於君之道”爲喻說明酒通心達志的本質。然坎卦重在習險,涉險出坎,強調酒爲“質實”爲其本意,“進結於君”係舉至險之例。,是指通過酒食的交流,達到誠信相知,互約通明。心學大儒王陽明雖然與理學的視樽酒簋食爲“質實”的主張有所不同,認爲理即心,心即禮,但也強調飲酒即心的“發見於外”,是情志的直接呈現,“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⑥〔明〕王陽明:《王陽明全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第225頁。,主張心性本體的至誠、自明要與“七情之樂”相通相存,具體而飽滿,方充溢知的智慧與行的憂樂。宋儒使中國“酒哲學”思想變得深湛和系統,尤其是“酒哲學”理念向“知行合一”“功夫”的邁進,增益了傳統“酒哲學”的實踐價值內涵。
三是個性覺醒促發儒家詩化“酒哲學”的心聲。儒家心學的“致良知”“心性”本體,蘊藉了“自明”的個體化情志和主動性認識,在明代中葉掀起新的人文思潮,與資本主義因素奠基的民主思想萌芽形成回應。也就在這個時期,酒文化、酒哲學展現出前所未有的革新面貌:(1)明代中期的儒者將隱士情懷和風度摒棄,以積極姿態融入社會。從對酒的熱烈追求到風花雪月的奢華生活體驗,反映了世俗心正成爲士人新生活狀態的情志修飾,他們內心渴望着將高蹈的志向在休閑而充實的生活中表現出來;(2)先前儒家“酒哲學”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觀念遭到衝擊。“酒哲學”依託於酒實體的生命活性,自然地、毫不費力地轉換到以當下心聲和體驗爲所重的階段,個體自由觀念促使意識形態體系對酒飲的情志表現、通脫瀟灑給予了相當程度的容納。“社會化、文化化的酒生命活性,凸顯的不僅是人因飲酒而魅力四射的形象、性格,而且也包括酒本身所迸射的、能被人捕捉到的酒哲學、酒倫理、酒藝術理蘊和韻味。”⑦趙建軍:“生命活性:中國酒文化的邏輯本質”,《東方論壇》4(2021):125。李贄的“童心說”,公安派的“性靈”觀念,竟陵派的“趣味”認知,都打下濃濃的時代烙印。儘管這些滲透了酒生活情調和個體自由思想的哲學觀念在當時還不特別普遍,但它凸顯了古典現代性的思想萌芽,使中國古代哲學融入了新時代的思想構成。
四是“中和”觀念使古代“酒哲學”的認知達到巔峰。清代儒家哲學趨向溫柔敦厚的知識化集成,“中和”觀念統合各種認識,將這些不同的認識轉化爲博大精深而又富有活力的社會、文化理論。其中,詩化哲學不再作爲文人標新立異的獨創,而是與儒家原有公共觀念融合一體,成爲社會各階層美化生活的正常形態。中和觀念在表面上以調和、中庸意識爲主導,採取折中路綫調解對立,不免壓抑了個體的酒飲感覺和自由渴求,讓社會進入一種平靜狀態,實質上是在協合“酒哲學”的不同趨向,使之形成統一的、和緩的生活氛圍,讓人們在酒飲的享用中,以消費方式促進社會的良性發展。在清代,無論是國宴、鄉宴、族宴,還是其他名目的酒宴,所烘托的情感、意識表達,都讓整個社會融化於理論化統合的巔峰狀態。然而,隨着晚清西方力量侵入中國,對傳統文化和“酒哲學”觀念構成挑戰,於是,古代“酒哲學”在它已然達到鼎盛之際,呈現出衰落態勢。但是,中和觀念本身並非保守的觀念,它在逐漸轉化積澱爲社會化、知識化、美學化的知識、觀念和理論系統的同時,也在嘗試汲取新的社會文化和理論滋養。它的主導性、引領性並沒有因爲遭遇了西方思想的阻遏而消亡,相反,它深深浸透在中國人的血液裏,通過民族化的生活、儀式化的風俗,沉潛爲更深在的“酒哲學”內蘊。
總之,儒家“酒哲學”的貢獻,是以深厚的古代思想積澱,奠定了中國酒文化、“酒哲學”的倫理內核。在整個古代,儒家“酒哲學”系統,與時代文化保持了既相適應又在變動中隨機調節、拓展的節奏。也正因爲如此,儒家“酒哲學”構成傳統“酒哲學”(包括非儒家“酒哲學”)最有深度的思想語境。當古代走向近現代之後,儒家“酒哲學”的某些觀念及其政治化應用,譬如酒榷制度,繁縟的酒禮、酒儀,逐漸消失了旗幟性引領作用,但因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社會基礎依然存在,它依然作爲社會化的知識、理論形式,由社會官方意識、官方話語和文人先鋒話語等向百姓輸送着理念認知與趣味觀念,依然以其獨特的力量抵抗着西方酒文化、酒哲學對民族意識的侵襲。可以說,衹要中國人持存傳統的價值認知與生活方式,儒家“酒哲學”就會始終存在。
二 生命意趣:道家“酒哲學”的思想根蘊
在中國古代,道家“酒哲學”的話語權力雖然一直處於次要性、輔助性地位,但其社會、文化影響力卻非比尋常。因爲,道家所具的重自然、重趣味的思想品格,爲處於逆境期的人們帶來極大的情思撫慰;尤其是士人,以道家“酒哲學”意識爲內心所期冀而孜孜以求的精神風範、氣韻,成爲他們人生追求的一種至境。在江湖上,那些遁迹山林的隱士,載酒泛舟,橫簫長鳴,佇立起比儒士更顯輕盈的瀟灑形象。這種藝術化的自我陶醉頗令世人讚歎,並因此對道家思想的感覺也格外傾心,不像視儒士那般很難擺脫迂腐刻板的印象。歷史風塵的蕩動,似乎也確證了這樣的狀況,往往技藝超絕、道行高深之人多出於道家。但是,若以此作爲道家思想的真實表達,則不免差池甚多,尤其具體到“酒哲學”文化的歷史本質,並不是這樣的高蹈、飄逸就能充分表達和證明的。
與儒家哲學一樣,道家哲學也源於巫性意識,經過原始公共文化的篩選和過濾,原始道家從巫、易文化中脫胎出來。儒家本乎“天道”,道家也本乎“天道”而生,“天一生水”。但它與儒家“天一生水”有別。儒家用此來摹狀天成之意,以原性歸於天意,則原性屬“命”不可違逆,人履天道就當順乎天意,自上而行下,懷仁而不暴殄萬物,以仁善情志,雲行雨施,顯陽剛性狀;道家則不然,秉乎天地交合,亦分得先天陽性之氣,但其動亦柔亦剛,柔中含剛,重自然素樸原生,貴本守簡,追求奇妙生趣的化成至境之功。
商湯統一天下後,酒釀乘天地人協合於國家政體、農業初興的大勢,形成了人工化私釀與官方營釀的生產語境,前儒家與前道家的酒道意識在公共性觀念形態中萌生出來。到了商周交替之際,本於陰陽交合而重生殖崇拜意涵的道家原生意識,愈加變爲從屬性的陰柔品質。而源於史官記事的儒家原生意識,纏結於人情風俗和祭祀儀禮,得以霑溉人倫禮序演變爲剛性文化,隨着人道逐漸替代天道,前儒之道也漸漸演化爲性命之理,至春秋、戰國更累疊爲儒家倫理哲學。因此,若以道體而論,前儒並無酒的本道,不過是依從於人的生命存在,依從於國家政體、政治禮序的仁德雨露滋潤情志,形成外在於酒的“天道(陰陽五行)”“人道(人倫綱常)”,並以此內在本質顯現人文化成的理蘊。而對於前道家來說,則表現爲另一番情懷:自視血統高貴的殷商貴族在降周後,一方面靜觀世態變化,體味天下異趣,但心志並不甘於柔弱屈尊的處境,乃用心智發奇特詭譎之思,探尋智慧謀略,力求守拙返樸,以柔化剛;另一方面,由於心智冷靜,不縈縈繫念於一得之利,反倒能精緻於陰陽和合之術,從中悟得“道”“趣”“意”“韻”的超勝,得自然事理奧妙。如此,酒蘊意涵在道家哲學的生成中,反倒有更爲深入的延展,成爲中國文化重要的創造淵源。
道家首創者老子的哲學觀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道的本蘊。一切存在物的生成、長大,都有自身內在的“自然”本蘊,衹要不迷失本蘊,就是依道而行,就能夠有天、有地、有人,有世間萬物。酒作爲人的創造體,自然有其作爲物的本蘊,道在“本蘊”。切中酒的本蘊,就切中酒道。這樣的酒道是無限生長的,從酒而及人、地、天之間的運動,具化於酒的生命顯現。
道的本蘊是法自然,自然的本蘊依商周哲學語境,以陰陽和合爲妙旨,於是,正向、反向皆歸根於自然“生生”。《老子》說“道者反之動”,其意有二:一是說人從自然感悟到道;二是說所悟之幾微,“返”爲其本蘊。這樣,道的所悟,便一方面在一種逆向否定中趨稀薄化,終至於靜;另一方面,道的本在隨反向的衍射而生長,於是,天、地、人無不有道。由於天、地、人趨近,則“道”“理”愈顯現,如次天道、人道、地道;而具化及微,則有事道、物道,次如兵道、商道、棋道、藝道,酒道爲其一種。在人道、地道、天道的延遞和交互轉化間,因其有水之原質原氣,有釀造之人工作爲,有酒蘊之氣息蒸騰,從而集衆道之蘊於自身,成爲一種聚合不同道旨、本蘊的獨特的道。
由於儒道哲學都基於巫、易等公共性語境生成,故在儒道分化之先,已有天道、地道、人道,卦象的演繹和陰陽五行的化合,讓人們感悟甚深。而道家在另闢與儒家不同的哲學進路中,淡化了人倫本蘊,以悠遊不迫的所遇所即,追求擺脫世間一切人爲造作束縛的妙韻。如此,雖然儒家也有人道之“天一生水”,以水中之“丨”形容人的性情的濡潤而生,載物陷物,含仁剖光,追求天下的通感俱化。但道家靈動地跳脫於與自然的微妙關係當中,若即若離,幽渺純粹,簡生道及萬物之本蘊,反而獲得更大的、包含了物理生長的獨特趣味和效應。故到戰國時期,經莊子的鼓噪,道家愈發使道蘊具化到人和萬物,強調無待無恃的自成,其理蘊的曉暢空靈,令人產生無盡的遐想和嚮往。而且,因爲道蘊貴在簡素,故雖然莊子發展了老子的學說,卻在根本意旨上沒有做太多的改竄。這一點體現到酒道上,同樣如此。《說文解字》言:“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從水,從酉。……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美,遂疏儀狄,杜康作秫酒。”①〔漢〕許慎:《說文解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班基慶、王劍、王華寶 校點,第436頁。“酒”字右邊的“酉”,在甲骨文、金文中像敞口圓肚的容器,中間一橫示意液體。《康熙字典》釋曰:“‘酉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爾雅·釋天》‘太歲在酉曰作噩。’《史記·律書》‘八月也。律中南呂,其於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②〔清〕張玉書、陳廷敬 等:《康熙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0),第1280頁。這裏依自然的演進實象解釋,吻合道家關於天地造物、人化器皿、具象而成萬物的意蘊。
因此,道家“酒哲學”的認知,一方面,天然與自然、世間具悖論關係:當其有賴於天地人之道,成就自身時,轉化生成自身獨特的理蘊,其象、氣、味、韻的具化,以微妙別在獨異於自然,獨異於人世間的心、事、象,形態似水,其性如火,飲之醉狂如癡如癲。酒釀已成,經“開門”出口,裝甌、裝瓶、裝罈入於千家萬戶,以酒的別致本蘊,煥發出黏性、散性——黏人心、散情性,令人趨之樂之,躁動發狂,陶醉其中不能自已。固道家酒蘊既內含守持,又顯化於外動。動靜相照,差異顯明。另一方面,酒道的具化是歷史中的生成,它不是抽象本蘊的具化,累疊的積蘊促成自身的優化機制,使得無論本蘊的綿延,還是本蘊物化的顯於釀造和享用,都體現出隨機性和應變性,順逆反和,獨化整合,遊悠於至大至渺,智能張力十分強大。正是在這一方面,道家“酒哲學”無論在宮室還是茅屋,都顯示其無比的韌性,成爲可與儒家“酒哲學”爭勝比肩的重要思想理論。
隋唐開始,中國社會又進入繁盛時期,在對人心的感性召喚方面,儒家“酒哲學”因其方正、僵硬而日益顯得局促,道家“酒哲學”卻逐漸顯現出強大的潛能,不僅在人人榼酒以赴自然勝景方面如此,而且在人際酬對、自我省思、爲情愛猜燈解謎、嬉戲歡愉方面都滲透無間,讓人們充分感受到逍遙達觀的快樂和清揚飄逸的美感。值此之時,其他文化觀念、思想可以表志寄賀、酒偕禮孝,然而若論高壇對酌,奏琴賞月,共賞清幽美好,則非道家酒蘊意趣而不能勝之。故唐宋文士,對酒多敞開情志,儒道俱修,不管是爲官任職,還是外放優遊,俱能以酒護心,守住心靈的快樂和智慧家園,如唐之陸羽、白居易,宋之蘇軾、歐陽修,元之王實甫、王驥德,明之陳繼儒、張岱、譚元春,清之錢謙益、袁枚等,哪怕思想上有濃郁的儒家傾向,行事作派仍表現出道家“酒哲學”的格調與風範。道家“酒哲學”對隋唐以後中國士人的影響,可謂至巨殊深,已經成爲中國士人安身立命的重要精神支柱。正因爲如此,道家“酒哲學”無論在朝在野、酒肆路坊,都產生了綿綿不絕的美韻和現實效力。
三 因緣幻化:佛家“酒哲學”的理論境界
佛教哲學以“緣起論”“成佛論”爲內核,般若、涅槃思想爲主體內容。戒酒觀念屬於因修道而制定的僧團戒律,體現了宗教的生活態度,但戒酒本身並不真正反映佛教哲學的內在構成。根據佛家的基本原理,修道指向精神智慧的修煉,以擺脫煩惱纏縛,過一種無拘無礙、自由自在的智性生活。從精神修煉角度看,自然事物和人工造物都屬於幻化所成,是意識、思維的變現。這種認識無疑極其主觀,然而它基於主體精神的自主性和空性,假定了外部存在由意識認定爲假相不真,也就不無強調修道實踐偏至的理蘊。爲此,佛教哲學以達成生命覺悟之目標安立身心,提出了深邃、嚴密的哲學體系,將成佛視爲最高境界,以一切生滅無常,客觀世界並無必然性,惟人心可超然生死和萬物,獲得精神解脫爲最高幸福。
酒作爲人工釀造物,在人的生命中必然會遇到。佛家雖然對酒沒有明確的解析,但從修道角度提出了明確的飲食要求,認爲酒激發人的性情,擾亂智慧,力主戒酒,將飲酒列爲“五戒”(不殺、不盜、不淫、不欺、不飲酒)之一。《惟日雜難經》說:“所以不飲酒者何?醉便惡口兩舌,妄作非法。設人善能,尚自亂意,以是故不飲酒。”從培養信徒理性克制力、精進力來講,佛教的戒律是有益的;但若從對酒的認知來看,佛教不及儒家辯證而全面(既能看到危害,也能看到酒促進人倫和諧的作用),也不及道家從道化角度對酒蘊予以人格化的深化。然而,佛教那些關於飲食的明確規定,包括戒酒的主張,主要是從僧團生活和修道實踐着眼提出的,若是從佛教哲學的構成及其思想機制着眼,則有另一番化成之理;而且,也恰恰因人們能夠從佛家思想的認識體悟到這方面的理蘊,所以促使佛家“酒哲學”也成爲中國古代“酒哲學”的重要理論構成之一。
促成這一狀況實現的,主要是中國佛教,或者說是中國化的佛教。所謂“中國化”,即被中國人所接受認可的思想構成和實踐方式。從東漢末年至東晉,佛教在中國先被作爲黃老方術,融入民間公共意識中。當此之時,僧人遊化各地,酒與茶成爲僧俗交往的媒介,遂引發人們從佛教角度對酒的新認知。到了隋代,中國本土僧人的數目大增,他們在清苦的生活中,不自覺地延續經年養成的生活習慣,在相互品茗對飲間,悄然將飲酒作爲一種雅致之舉而風行。這種私下或半公開的飲酒生活,爲中國化佛教的“酒哲學”觀念的形成奠定了生活基礎;再加上,隋代佛教理論在中國僧人手上有了根本的突進,於是,酒思融入哲思,佛門屢出禪話,維摩詰的居士佛、菩薩觀念對僧人、士人都產生很大的誘惑,遂使“酒哲學”觀念在時人詩文中經常得到表達。到了唐代,僧人與士人的吟酒酬對成爲競相仿效的雅舉,酒詩名篇迭出,已無須在意僧人是不是在飲酒。如果說,這是佛教傳播過程中帶來“酒哲學”的一種自然推進,那麽,唐代國家意識形態政策的改變,則從公共化層面推進了中國化佛教“酒哲學”認知的發展。唐初至盛唐,李淵、李世民對儒、佛、道採取均衡對待的政策,對各家均無明確貶抑,極大地激發了各家爲爭奪話語權而對自身思想系統的建設。對佛教來說,一方面,建立中國化佛教各宗思想體系的意識趨於自覺,隋代已有中國化佛教宗派天台宗,唐代又有唯識宗、華嚴宗、禪宗等基本上或完全中國化的佛教宗派系統,致使中國佛教哲學蔚然成就大觀;另一方面,佛教畢竟是“外來戶”,它們在努力與世俗社會交流、讓整個中國社會都接受佛教思想方面下了莫大功夫,這又使得佛教“酒哲學”與世俗社會逐漸形成默契,達到深度有機交融。在各類經文中,在中國僧人所寫的論、序、弁言、詩文中,“酒哲學”思想常常通過借喻和論道的方式暗示出來,人們不管是直覺接受其思想的影響力,還是間接地接受思想暗示,都能夠通過中國化佛教思想的撰述,僧人與士人的交往酬對,以及佛教風靡下的時代話語中,得到其理論主旨。
一是酒性亦般若空。天台宗是隋代最具中國化特色的佛教學派,創始人智顗大師說:“自恐此身內舊食皆是無明煩惱潤益生死,今之所食皆是般若,想於舊食從毛孔次第而出,食既出已心路即開,食今新食,照諸暗滅成於般若。故《淨名》云:‘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是爲明證,以此食故成般若食,能養法身。法身得立即得解脫。’”①〔隋〕智顗:《摩訶止觀》,收入《大正藏》(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96),第46冊,第687頁。在智顗大師看來,世間人的飲食,“皆是無明煩惱潤益生死”,所謂飽有脹噎,餓有困乏,饑腸轆轆難忍,甘肥沃腸昏昏,縱然生死因飲食潤益得所快活,也不過一時之樂。唯以般若觀食,則所食成就般若智慧,故般若食即性空食。依此,酒性即般若空性。如此之飲食既濟養身體,令血脈舒張,通泄無礙,毛孔髮鬚皆增益智慧,智慧給養充分了,煩惱沒有了,心境覺悟,便“法身”成就,生命得以常在。循此思路,對於酒,佛教亦提出積極正面的主張,認爲酒潤益生死體現因緣和合功效,增益智慧爲增上緣,是因緣福德,有無量智慧光照耀。《大寶積經》云:“好酒香味具者是酒之醍醐,接取已盡下有糟滓。”②〔北凉〕釋道龔 譯:《大寶積經》,收入《大正藏》,第11冊,第641頁。意思是說,好酒吐出芬芳的香味,如同乳漿(乳品分五級:乳、酥、生酥、熟酥、醍醐)裏的醍醐。《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醍醐之味,乳、酪、酥中微妙第一。”醍醐是最高級,常被用來形容智慧頓悟;稱酒爲醍醐,即是肯定乳酒能醍醐灌頂,令智門大開,頓悟成佛。同時,因酒之醍醐的質地精純,已將糟滓去除,用之饒益生命智慧,愈顯酒之本性。智顗大師以新食益般若空性,空空爲慧,而酒性空空,亦無自性,則佛教“酒哲學”的本蘊,俱在生命智慧的覺悟超升。
二是飲酒幻覺別創生命奇境。隋代天台宗對直覺的重視,對飲酒頗具開啓思悟的意味。生命直覺的綻放,可謂一念三千世界。唐代唯識宗(又稱瑜伽宗或法相宗)對心理活動的開掘,更促動中國人的智慧心理趨向精緻和細膩,對飲酒的心理頗多引導和啓迪。華嚴宗對生命理想通達圓融境界的闡發,愈是激發了中國人的飲酒情懷和“酒哲學”智慧的飛翔。但也有人認爲,唯識宗心理分析太注重理性,中國人不大能夠接受它所倡導的印度佛教原旨。這其實是一種誤解,中國人的心理活動本來就細膩、豐富,正是中國智慧潤澤了瑜伽識性,纔產生了法相唯識宗的中國化心理識性。因此,在注重“生”的價值意義上,直覺、識性和想象、幻覺都起着作用,在飲酒中尤爲明顯。直覺如蓮花晶瑩剔透,識性如利刃,直視人的本性;又如蛟龍探海,徑入深邃幽密的洞穴。中國“酒哲學”在充分汲取佛教理蘊的營養後,獲得了愈發隱秘幽微的生命肌理,得以讓生命情志更自由地放飛。這或許正是中國古聖對酒爲幻物最好的詮釋。“《楞伽》云:‘味著三昧樂,安住無漏界。無有究竟趣,亦復不退還。得諸三昧身,乃至劫不覺。’譬如昏醉人酒消然後覺,彼覺法亦然。”③〔唐〕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收入《大正藏》,第11冊,第496頁。酒醉如“三昧之樂”,“酒消然後覺”,其幻在不自覺而覺,以法譬諸酒智,通透無比。
三是酒化禪意生命。“禪”原意爲禪定,即靜思維。中國儒、道哲學中的“自然”“仁心”“虛靜之心”“心齋”“坐忘”都蘊有排除雜擾、發端於素樸心念的意涵。佛教的禪意,講究通過修煉程序獲“定”。漢末的小乘禪,注重呼吸法;南北朝的達摩,以面壁法、心念法獲取禪意;隋唐以後,隨着中國佛教義理的完善,逐漸成熟了另創的中國佛教派別——禪宗。在禪宗中,酒成爲融化僵硬理性、解構俗世疲憊的靈丹妙劑,追求直截了當、含蓄雋永、象韻蔥郁、意蘊悠長的藝術化人生,即所謂酒化的人生——酒酣之至灑脫淋漓,酒道玄妙深奧莫測,酒話縹緲風雲詭譎,酒醉無憾生死兩拋,酒智奪魂利鋒快刃……中唐以後,禪宗祖庭遍佈全國,僧人自主抉擇生命方式,詩化哲學回歸林山河海,催放出無數令人拍案叫絕的公案傳奇,僧人、文士飲酒吃茶味禪,似乎成爲拼修智慧的必備功課。種種禪行,如煙花火蕊,璀璨無形,加之皆善飲詩作文,酒禪詩賦美不勝收,中國佛教禪宗倡舉的“酒哲學”觀念可謂深深駐扎於朝野士人之心。以唐代爲例,許渾《長慶寺遇阮秀才》“晚收紅葉題詩遍,秋待黃花釀酒濃”①〔清〕曹寅、彭定求 等:《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0),第6115頁,第5694頁、第2086頁、第7010頁。,姚合《和秘書崔少監春日遊青龍寺僧院》“高人酒味多和樂,自古風光衹屬詩”②〔清〕曹寅、彭定求 等:《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0),第6115頁,第5694頁、第2086頁、第7010頁。,岑參在崇濟寺所作《攜琴酒尋閻防崇濟寺所居僧院》“相訪但尋鐘,門寒古殿松。彈琴醒暮酒,卷幔引諸峰”③〔清〕曹寅、彭定求 等:《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0),第6115頁,第5694頁、第2086頁、第7010頁。,趙鴻《杜甫同谷茅茨》“工部棲遲後,鄰家大半無。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盂”④〔清〕曹寅、彭定求 等:《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0),第6115頁,第5694頁、第2086頁、第7010頁。等等,不勝枚舉。
酒禪是中國人特別傾心、獨具神化之功的一種道行;禪酒超越了一般物質與精神的功用,成爲通達中國人潛意識的飲品。在酒化的禪意裏,中國人本然地登臨哲學高境,情志的發願、溝通,充滿性靈之趣,鼓蕩着活潑潑的情懷。這種情趣和境界與佛教般若食之初衷可謂不謀而合,也與中國“酒哲學”的情志抒攄傳統耦合融一。它所傾瀉的獨特而非凡的力量,是古代中國“酒哲學”的一大亮點。
四 變革與整合:古代“酒哲學”的民族化趨勢
古代中國“酒哲學”的民族化問題,既反映中華民族集體意識的成熟,也反映個體意識的淬煉養成。在民族化進程中,“酒哲學”聚焦了權力、潛意識、自我期許、審美烏托邦想象,伴隨着酒生產技術的提高和規模擴張,形成頗爲壯闊的流動態勢。在某種意義上說,古代“酒哲學”理論和觀念已成爲中國邁向近現代文明的一種內在驅力。因爲,思想與精神的變革,衹有在滋味咀嚼時纔被賦予“身體美學”的喚醒,它因發之於身而愈爲真切和深刻;同時,“酒哲學”也帶來精神的躍動與張力,不僅具現於個人,而且具現於整個民族,從而現實地影響着整個民族的歷史與文化變革和走向,使之從細化完善到整合統一,最終構成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寶貴積澱。當然,在趨向近現代進程中,“酒哲學”作爲總體哲學的一個側面,無法逆料外部世界的變化,更無法以自身系統的轉換力、適應性來調節、應對來自物質生產力方面的思想、文化衝擊,但酒畢竟是生活的融劑,它滲化於人的機體,時時催發人的生命血氣朝着某一個方向升騰。也就是說,它是一種能夠促發精神爆發力的物質。爲此,在近現代,酒的醞釀寄寓着人們深沉的智慧期待,酒力的發酵凝聚着對歷史矛盾和障礙的化解與突破的元素,“酒哲學”的目標,始終指向對社會沉寂的打破。古代“酒哲學”正是以這種姿態和潛能,持有醞釀新質的慣性,而駛向未來更爲恢宏的空間。
其一,“酒哲學”的民族化。“酒哲學”的思想意識、理論觀念、價值內蘊的民族化問題,是關係到中國各民族主體生存、存在意識的重要問題。自中華民族以意識形態規約古老的公共意識和個體意識,形成主導的意識形態以來,民族意識一直受到儒學意識形態的嚴重制約,因此,“酒哲學”的發展總體上比較節制,但這種節制也是留有餘地的。譬如,在漢代,西部巴蜀、東部吳越、中部湘楚、北部匈奴、東北鮮卑和西北關中,這些文化圏與黃河下游、淮河流域地帶的儒家意識形態控制相比較爲薄弱,酒風就十分熾盛。也就是說,酒風熾熱地帶往往不是中原地區,而是中原以外的周邊諸文化圈。這是中國“酒哲學”史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雖然在“酒哲學”深度意涵的開掘上,各周邊文化圈不及中原,不及中原的君主、貴族、卿大夫、一般士人和普通百姓對酒文化、酒哲學悟解得那麽深入,這給儒道文化在中原通過“道化子民”“以酒載道”,創造出有歷史、有文脈的酒化效果提供了可能;但是,“酒哲學”的深致和效力,也通過具有差異性的多樣化、廣泛性得到體現。正是在後一方面,酒文化的“世俗化”概念與“民族化”概念構不成對等,即它們不屬於同位的、可置換的概念,“民族化”更依賴於地理、飲食、風俗儀式與民族語言、生活習慣等的養成。“酒哲學”的民族化是一種歷史記憶和民族標記,它超越當下的物質、精神創新,是文化傳統沉澱於民族繁衍和傳承的顯性特徵,也是一個民族呈現於現實每一瞬間的生存圖志。民族意識、民族精神與意識形態的締結,不單純是與權力、話語的締結,更是民族共同心理、意志的一種自在表達,因此,“酒哲學”的民族化,哪怕是在意識形態中心之外,它也擁有民族自身的“話語個性中心”。
從南北朝開始,中國“酒哲學”的民族化就開始了它的中原與周邊文化圈的對流。南朝時期,南方偏安,北方五胡十六國競逐,在將狂野風俗帶進內地的同時,也將嗜飲少節制的酒風帶入。中華民族的成長,“酒哲學”的成長,不是說很純淨地衹接受詩情畫意的東西,也接受文明程度落後,但激情、力量和胸懷毫不遜色的邊遠民族的酒俗酒風,自然也注重保持漢族自身的情志潛能。之後,逾隋、唐,歷宋元明清,周邊文化圈與中原的交流互通成爲常態,逐漸地,很多少數民族人口數量激增,對文化的選擇也順應漢族主體文化,使“酒哲學”觀念傾向於民族意識的整體融合,喻示着中華民族具備統一、和諧的強大場勢和同化場能。這時,已經消除了漢族的絕對、唯一的優勢,使中華民族成爲多民族融合的偉大民族。元代的忽思慧《飲膳正要》便表達了與漢族同樣的心聲:“夫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勞作,故而能壽。”①〔元〕忽思慧:《飲膳正要》(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8),第3、24頁。這與《黃帝內經》的口吻、觀念幾無差異。對於酒,忽思慧也以儒家“酒哲學”觀念爲主導,強調有益於身心、規避過量受酒的毒性所傷:“酒味苦、甘、辛、大熱、有毒性;主行藥勢,殺百邪,去惡氣,通血脈,厚腸胃,潤肌膚、憂愁。少飲尤佳,多飲傷神、損壽、易人本性;其毒甚也——醉飲過度,喪生之源。”②〔元〕忽思慧:《飲膳正要》(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8),第3、24頁。由此可以看出,以極其善飲的蒙古族尚且奉儒家“酒哲學”思想爲正宗,其他民族更不例外了。作爲文化有機整體的一個側面,酒文化與“酒哲學”的民族化歷程,顯示了中國人對於酒擁有共同的、深厚的集體認知與生活基礎,因而使之就能夠充分汲取所有民族的文化思想資源,充分發揮不同民族的個體情志力量,自信地使“酒哲學”思想、理論的場域推向更廣闊的世界。
其二,“酒哲學”觀念的民族化變革。中國的酒文化有自己的發展特點,尤其是“酒哲學”觀念的變革,空間因素對變革的影響、作用很大,其整體趨勢無外乎兩端:一是中心向非中心捩轉,一是非中心向中心傳統認歸。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化變革幾乎形成一種規律,每次大的民族遷移、交融,都帶來後來更大的民族化回歸。反映到“酒哲學”的變革,也是有規律地在酒爲德而飲、爲禮而飲、爲情而飲、爲興而飲之間轉換。東漢末年曹操詠酒:“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抒發出繫念生死憂患的慷慨悲壯情懷,反映中原“禮崩樂壞”下的個體“酒哲學”心理與認知。南北朝時,北方胡人“你方作罷我登場”,啖肉縱酒成風,“酒哲學”的本體觀念悄然發生轉換,德性、禮義的佔比遭受強烈衝擊。至唐代,李淵、李世民父子儒道釋並舉,尊重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飲酒習慣,酒樂結合,禮樂並舉,多層次酒宴形式得到推廣,情感交流依政治、民俗禮序釋放。“安史之亂”後,地方藩鎮勢力崛起,“酒哲學”民族化變革依託佛教在祛魅化和詩樂形式的遮罩下向世俗化遷轉,同時向傳統文化中心回歸。隋唐之後,“酒哲學”發生兩次大的民族化變革:第一次在宋代,使酒意識與道、禮、氣、樂統一。二程、朱熹發掘易學、陰陽五行的公共性思想資源,融合佛家意識於儒學理性,由“理”“氣”統一,到以“理”制“氣”;再有“心學”糾其偏頗,“理”“氣”皆歸於“良知”“功夫”,合於“心”即酒道,使人的生命本體最大限度地完成向融解矛盾的方向耦合,人人有自我,又良知通大道,酒氣率性揮灑,有所依有所止,呈現出嶄新的民族“酒哲學”意蘊氣象。第二次在清代,對唐宋以降偏重於樂化的傾向有所調整,尤其是對“酒哲學”本體的“理”“樂”“氣”“慾”統一,以及在樂化基礎上的理性化提升所導致的南宋至明代的感性過於放縱、娛樂化風氣過於濃郁的趨向,從中華民族整體的更高尺度予以衡量和校正,強調實學對酒文化、哲學的引領,提倡溫柔敦厚的酒俗良風,使中華民族向務實求真方向發展。這種改變看上去有些保守,但作爲“酒哲學”導向,是對各個民族的“酒哲學”思想和精神風貌的一次結構性調整。它注重真實,注重理據,肯定了生活和民俗的基礎,尊重了事實和傳統。它堅實了古代文化的核心觀念,使古代“酒哲學”真正基於現實性產生效力,獲得相應的本質化肯定。
其三,“酒哲學”的民族化整合。從“酒哲學”的理論構成來說,兩次變革與其他工具性的、實踐性的、政策性的、命令性的、觀念內化性的意識形態調整相比,起到了更加自如和遊刃有餘的效果,且更有實踐張力。概括而言,成效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酒興的民族動機整合。酒興的本質是調動生命潛能,使之能夠良性釋放。酒興是漢民族的心魂。多民族統一的中華民族,能與“酒興”和合,則功莫大焉。因酒興也激起對立,故酒興的民族動機整合非常重要。在歷史上,不管是匈奴南下,還是附屬國進貢,酒興合則情志合,情志合則道義合。所以,酒興整合對治理民族之亂起到了非常之效。
二是酒力對民族激情有促發之效。國家中的個人與個人、民族與民族,但凡酒力迸發,往往亦折射相互角力與相容相與的程度。當酒力迸射與生命情志統一,則高歌之處皆民族鬚眉與巾幗;若酒力萎靡,則曼妙淺斟,率多壓抑悲憤之事。酒力對民族精神的提振,不僅對單一民族重要,對多民族融合的中華民族尤其重要。歷史上,宋代重文輕武,鄙視粗鄙蠻野的酒力,結果積貧積弱;明代中後期的酒享用意識過於娛樂化,亦重文輕武,導致疆域面積大片萎縮。當然,“酒力”的提振、整合,也講究“科學”,故提倡適量飲酒,也是民族“酒哲學”的核心觀念,它與重視酒力對民族激情的促發並不矛盾,它有力保證了民族“酒哲學”意涵的健康發展。
三是酒韻的民族境界整合。“酒哲學”的民族化整合,有境界、韻味的內在追求。“酒哲學”的境界、韻味,反映文明價值達到的高度與水平。中華民族自古追求中正和諧的理想,追求既浪漫又高雅的境界和韻味,在趨向高水平的文明境界、韻味時,“酒哲學”的境界、韻味是各民族均樂於醺醺於斯,甚至醉於斯的美好嚮往。歷史上,隋唐以前,漢民族的“酒哲學”境界,主要以政治倫理的和諧爲最高尺度,酒化詩學偏重抒發胸臆,注重生命氣韻的迸射;這種酒哲學的境界、韻味有抒泄“塊壘”、直觸自然、感應自然的爽快,但格局未免狹促。隋唐時期,佛教智性與儒道意識融合,改變了酒化詩性的生命氣質,向注重主體意趣和世俗情趣轉化,酒哲學境界中和了“形上”與“形下”,十分有益於民族精神、心理的塑造。宋代繼承唐代酒哲學的氣質和韻味追求,情感表達更加充沛、飽滿和細膩;但“酒哲學”的境界、韻味,畢竟是一個深度問題,它能否與其他文化的、精神的,諸如政治、倫理、審美和藝術的境界、韻味相協合,還需要歷史的不斷磨礪,因此,宋代的詩化“酒哲學”與浸潤了理學和心學的“酒哲學”,雖然有偏向玄思或沉溺於情思的不同表現,但總體上霑溉詩學、理學、心學的酒哲學境界和韻味,開闊了人的心胸,釋放了過去累結的心結,凝定了心志的趨向,對民族認知和精神心理走向成熟是一大進步。元代酒哲學境界比較開闊、粗放,在文化總體方向上有所倒退,卻由漢民族主體持存了“酒哲學”境界、韻味的歷史收穫。明代又轉向輕靡,對“酒哲學”韻味別有增益,然其精神境界則有所倒退。清代復歸於凝重醇厚,對塑造中華民族的精神趨於內涵精緻、優雅細膩和博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助作用。整體上看,不同時代的“酒哲學”境界,遵循了“酒哲學”境界的自律節奏,其中有得有失,總體情況還是好的,假如沒有這種內在的境界、韻味追求,民族“酒哲學”的認知、精神水平會差很多。
四是酒思的民族化意蘊整合。思性氣質是“酒哲學”的人文底色,酒思的方向、輻射力度和融攝酒蘊其他構成的程度,標誌着“酒哲學”的思性深度與結構化程度。歷史上,歷代酒思皆有其特定的方向,都伴隨着民族化進程而變易、調整或捩轉。漢代酒思集中於漢民族主體文化,受儒道核心觀念制約,酒禮在官方話語中變得僵化、刻板,缺少生命力,但士人另闢了酒醉仙鄉的詩性話語,鋦補了漢代“酒哲學”意蘊的結構性不足。這個時期的酒哲學意識格局總體上是封閉的,並沒有向周邊各民族拓展。到魏晉南北朝,得益於審美覺醒和民族融合,“酒哲學”意蘊向生命與存在領域掘進。在隋唐,“酒哲學”的思性與儒道釋融合,得到系統化提升;同時,“酒哲學”的“詩性之思”也進一步向世俗情懷延拓。宋元時期,理學、心學澆鑄“酒哲學”,使之獲得“體”“用”皆具的邏輯深刻性與完整性,外化於生活美學,文化水平大幅提升,生命力也達到自由自在的呈現。但宋代的酒思整合尚不完備,詩化酒意表達了情感意願,卻對本能有所削弱,從而婉約詞成爲宋代酒詞酒韻的主調,豪放之詞相對見弱,酒韻意味反而不及婉約詞綿長、耐咀嚼回味。這是思性與詩性聚焦於酒興的感性激發上的一個矛盾,融解這個矛盾成爲民族文化軟實力必須要經歷的過程。因此,對宋人酒思,既欣賞其意醉、情醉,也感慨其志趣之醉、血氣之醉;醉者所思不同,生命表現不同,思性張力不同,呈現得胸懷、境界也不同。在元代,馬背上的民族一旦駐扎下來,對駐地居民的飲酒風氣影響甚大;也是基於這種狀況,元末明初士人引領的深度酒思,更凝重地轉向對民族命運和個體命運的思考,酒思更富有文化積澱的質蘊。明中葉至清中期,酒幻思想蓬勃,得以容納酒釀和酒飲的各種現實表現,對酒醉及醉後狂癲都能予以寬容理解,這就是酒思對胸懷解放的一種根本體現。
當然,“酒哲學”的整合不僅是綜合的,還要與其他力量相協合,因而企望酒思破局單調、僵硬的現實,不免有些誇大思想的力量,因爲輕靈幻化的酒思,雖然能夠促進智慧和酒質的提升,也能夠促動酒飲的民族生活氛圍,但承接民族命運的現代化根本轉換,還需要其他民族化因素與酒思的深度整合。酒思融入歷史的節奏已經是酒作爲重要物質、精神資源的體現,若能夠參與民族發展的跨越性節奏,酒思整合之益,則愈顯其潛能揮發之極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