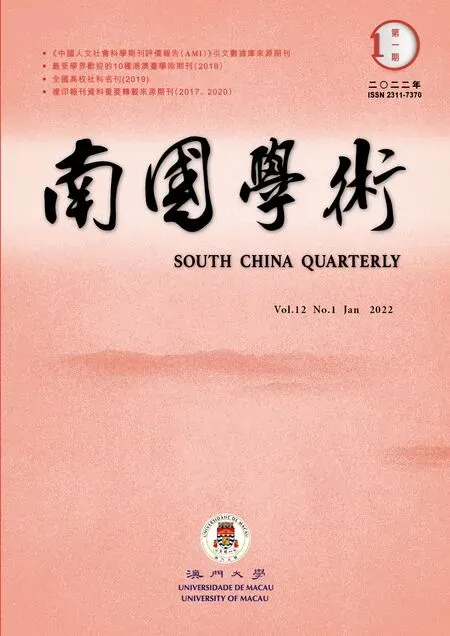西方三種自由理論對“國家”的形塑
李石
[關鍵詞]消極自由與國家 積極自由與國家 共和主義自由與國家
在西方政治理論中,“自由”概念一直處於核心位置。1958年,以賽亞·伯林(I. Berlin,1909—1997)在牛津大學的演講稿《兩種自由概念》中第一次區分了“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他認爲,所謂“消極自由”,即“非干涉”的自由,指的是人們的行動不受他人的干涉;所謂“積極自由”,強調行爲者能達到自身目的,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成爲自己想要成爲的人。自伯林對“消極自由”“積極自由”做出區分以來,西方學術界對“自由”概念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歇。在這些爭論中,又不斷涌現出對“自由”概念的不同闡述。從理論結構上說,不同的“自由”概念最終會導出不同的國家學說和政治主張,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理想,因此,本文試對“消極自由”“積極自由”“共和主義自由”這三種概念將分別導出什麽樣的國家形態進行分析。
一 消極自由與消極國家
在伯林的區分中,“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根本區別在於,是否對“自我”進行劃分,並進行高低優劣的評價。在消極自由理論中,“自由”的障礙來自他人的干涉(包括其他社會成員、國家或政府的干涉)。由於消極自由理論並不深入到行爲者“自身”去尋找自由的障礙,自由的實現在於他人干涉的消失,因此,以消極自由爲基礎的政治學說就必然主張儘量減小國家和社會對個人行動的干涉,不論這些行動是出自一個人的慾望還是理性。與之相反,積極自由理論總是深入到“自我”的結構當中去討論自由問題,常常認爲自由的障礙可能內在於行爲者自身,可能源於行爲者的非理性慾望、錯誤認知,或者行爲者的意志薄弱、怯懦等等。按照這種理解,自由的實現並不在於他者干涉的消除,而在於行爲者能排除自身的干擾,做更好的自己。積極自由理論甚至主張,藉助外在的權威鑒別出行爲者的真實慾望,扭轉行爲者錯誤的認知和價值判斷。
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之間的這一根本區別,決定了以消極自由爲基礎的政治學說反對國家或社會對行爲者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進行過多的干預,衹要個人行爲不妨礙他人的自由,就不應該對其進行限制。與之相反,以積極自由理論爲基礎的政治學說則要對個人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以及人生目標等進行考察,以鑒別出行爲者自身當中那個較好的“自我”,並藉助某種外在的政策手段鼓勵“較好自我”的實現,以達成積極意義上的個人自由。由此,消極自由理論與積極自由理論必然導向不同的國家學說。消極自由導向功能最小化的消極國家,而積極自由則導向對人們的價值觀念進行適當管控的國家,或者是爲人們實現自己的生活目標提供更多物質支持的福利國家。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對“消極”“積極”這組相反概念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德國哲學家威廉·馮·洪堡(A. v. Humboldt,1767—1835),他將國家分爲積極國家與消極國家。在《國家的作用》一書中,他立足於個人自由,對國家權力的應用作了嚴格而細緻的規定,主張將國家的功能限制到最小,主張一種消極國家,因而成爲西方最早對“最小國家理論”(minimal state)深入闡述的政治思想家之一。
按照洪堡的見解,國家的作用往往是雙重的:“它可能促進幸福,或者僅僅防止弊端;而在後一種情況下,它就是防止自然災害和人爲的禍患。”①[德]威廉·馮·洪堡:《論國家的作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林榮遠、馮興元 譯,第37頁。前一種作用是積極的,爲了實現這一目的,國家必須具備許多積極的功能;後一種作用是消極的,僅具備消極作用的國家是功能最小的國家。古代國家屬於前者,現代國家屬於後者。洪堡認爲,要想維護人們的“自由”,讓人們憑藉自身的內在動力健康地發展,國家必須是消極意義上的國家,不應具備過多的“積極”功能。洪堡在這裏所說的“自由”,其含義就是“消極自由”,就是要求國家儘量少地干涉人們的行動,給予人們“非干涉”的自由。相應地,國家的積極功能則對應於“積極自由”概念。因爲,對人們幸福的關心往往是以某種既定的生活方式爲標準的。在洪堡看來,這會從根本上抑制生存環境的多樣性,是對人們消極自由的最大侵害。因此,消極國家的權力應該嚴格地限定在“安全”界域,而不應對公民的積極福利做任何努力。
消極國家的核心功能就是爲人們提供安全。因爲,沒有安全,就沒有自由。在安全問題上可分爲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前者要求國家抵禦外來的侵略,後者則是要盡力制止人們之間的互相爭鬥。對於外部安全的維護,雖說是國家功能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洪堡認爲,那些爲了防範外部侵略而被組織起來的軍人們,由於個體自由完全被禁錮在機器式的生活當中,人生完全被犧牲了,因此,國家必須盡一切努力避免戰爭。
除了安全之外,“公共教育”也是通常人們所認爲的國家的核心功能之一。這種手段在古代國家中得到廣泛應用,並卓有成效。但是,在“消極自由”概念所主導的消極國家中,“公共教育”卻常常受到質疑。因爲,公共教育必然會限制教育的多樣性。在個人的發展中,個性化的私人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公共教育衹會將人們塑造成同樣的人,過類似的生活,是對人們自由的極大傷害。因此,在消極國家中,公共教育應完全處於國家作用範圍之外。
另外,消極國家還反對政府干涉人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宗教是涉及人們靈魂內心的事務。在這方面,任何強制都會起到相反的作用。衹有通過人們自由的思考和實踐,纔有可能培養起堅定的信仰,而人們的感受也將更深刻。因此,在自由的環境下,人們不僅不會背離信仰,反而會更加篤定,並由此而自覺自願地遵循各種社會習俗。在支持消極自由的學者看來,在宗教的問題上,國家權力的應用總是事與願違,使得人們背棄信仰,逃避法律。
上述即是一個消極國家的大致圖景,亦即古典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最小國家”:功能僅限於“保護”,最大限度地給予人們“非干涉”的自由。在經濟領域,它主張放任市場,反對政府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和干涉。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教育、醫療、養老、社會保障等事項,也都交由自由市場來安排。在這樣的國家中,私立教育、私立醫院以及各式各樣的商業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將會主導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時,它反對政府和國家干預人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主張對所有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保持中立。因此,在消極國家中,人們的興趣和志向將得到最大限度的寬容,除非與他人的自由發生矛盾。
消極國家是不是一種美好的理想國家,或者說烏托邦?對於這個問題,“最小國家”理論的當代闡釋者諾齊克(R. Nozick,1938—2002)認爲,“最小國家”雖然不是所有人心目中的理想國家,但衹有最小國家纔能包容人們有關理想國家的所有“想象”。由於價值觀念的不同,人們對何謂“理想國家”的想象是不同的。如果強迫所有社會成員生活在某些人想象的理想國家中,那樣就會侵犯人們的自由。因此,衹有對所有關於理想國家的想象都保持中立的最小國家,纔有可能真正地成全所有的“理想國家”。諾齊克論述到,最小國家是理想國家的“框架”(framework),或者是所有理想國家的“元國家”。①Robert Nozick, Anarchy,State, and Utopi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4), 317-320.也就是說,衹有從“最小國家”中,纔可能誕生出理想國家。
然而,消極國家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自由市場的運行邏輯,總是在不斷加大貧富差距——富者越富,窮者越窮。與此同時,由於窮人買不起各種保險以及優質的教育和醫療服務,生活質量將大大降低,並且面對更大的風險。更重要的是,由於教育的差距,窮人與富人之間的不平等還會一代代傳遞下去。社會各階層之間缺乏流動性,窮人的孩子依然是窮人,沒有上升空間。由此看來,消極國家有可能是一種不平等程度高、貧富差距大、窮人與富人之間的矛盾隨時激化的國家形態。另外,由於許多公共設施的建設無法在短期內帶來經濟回報,所以,在消極國家中,人們缺乏相應的動力去推動公共設施的建設。高速公路、鐵路、橋梁、電信網絡等設施的建設滯後,將成爲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巨大障礙。
消極國家的各種特徵根源於“消極自由”概念。消極自由理論主張最大限度地實現人們的自由,儘量減少“他者干涉”。也就是說,它希望國家管得越少越好——任何國家功能的增加,都會侵犯它的“非干涉”意義上的自由。這樣的自由學說,必然會導致其理想的國家形態是衹具有保護功能的“最小國家”。任何超出“保護”功能的國家——干預市場的國家、構建社會保障體系的國家、維護分配正義的國家、對價值觀念進行引導和管控的國家……都會與消極自由理論不一致。在西方學術史上,洛克(J. Locke,1632—1704)、洪堡、哈耶克(F. A. v. Hayek,1899—1992)、弗里德曼(M. Friedman,1912—2006)、諾齊克等思想家,是這類國家學說的主要代表。
二 積極國家的兩種形態
與簡單明瞭的“消極自由”概念及其對應的“最小國家”不同,“積極自由”概念較爲豐富,而其對應的國家形態也較爲複雜。與消極自由理論相比,積極自由理論有兩個顯著特徵:一是將行爲者的“自我”進行二分,並對不同的“自我”進行評價。例如,將自我劃分爲“較高自我”與“較低自我”,“理性自我”與“慾望自我”,“真實自我”與“虛假自我”,等等。二是將兩個自我中的那個較好自我外化成某種道德或政治權威,並且將對該權威的服從闡釋爲自由。在積極自由的意義上,一個國家爲了使公民實現自由,就應推行相應的價值觀,協助人們進行自我的劃分和評價;同時,國家還應爲公民提供更多的實質性機會,協助公民去做他們真正想做的事情。
洪堡認爲,國家的積極功能在於推進人們的幸福,這與積極自由的理論路徑是一致的。在積極自由理論中,“自由”就是行爲者能夠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實現自我、獲得幸福。爲了達到這一目標,一方面,行爲者必須持有正確的價值觀,這對應於行爲者較好的自我;另一方面,行爲者還需擁有一定的物質保障和相應的機會。上述兩方面,恰恰對應於一個積極國家在推進個人幸福時可能採取的兩種方式。
那麽,一個國家如何纔能推進人們的幸福呢?這基於人們對幸福的不同理解。
其一,積極自由理論認爲,如果一個人的價值觀念有問題的話,他絕不可能幸福。因而,幸福的實現要求人們持有既定的價值觀念。這種觀點在政治哲學中被稱爲“至善主義”(Perfectionism),其核心主張是:人們衹有在特定的價值體系或者生活方式中,纔能實現理想的自我。它“設定某些人是內在地低於其他人的,並認爲有些人的生活方式是內在地低於其他方式的”①[英]尼古拉斯·布寧、余紀元 編:《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735頁。該辭典將“perfectionism”譯爲“完美主義”,但中國學術界大多譯爲“至善主義”。。這爲國家限制某些價值觀念及其相應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理由。
依據至善主義,國家要推進人們的幸福,就必須對人們的價值觀念進行干預,可能會採取引導和禁止兩種手段:一是以主流社會認同的價值觀念引導其社會成員。除了公開出版物之外,這種引導有時也通過統一價值觀念的公立教育而實現。二是限制與主流價值觀念不同的價值觀念的傳播。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這些干預措施的程度可能會存在差異。在極端情況下,國家會對人們的價值觀進行嚴格管控,禁止思想和言論自由,並可能會導向專制主義。但值得注意的是,從現實世界看,政治理論家的推導和預言或許有些危言聳聽。因爲,國家對價值觀念的管控並非一定會導向專制主義——所有國家都對價值觀念進行管控——或引導,或限制,因此,都存在着主流價值觀念與非主流價值觀念的分野。所謂對價值觀念保持中立的純粹的“消極國家”,不過是理論家們不切實際的空想。
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 Rawls,1921—2002)試圖建構一種對所有價值觀念保持中立的純粹政治的學說。他在《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中,將包含價值觀念、對世界的根本性看法(例如,基督徒認爲上帝存在、上帝創造了萬物),以及理想生活的構想等道德哲學內容的學說稱爲“整全性”(comprehensive)學說。羅爾斯認爲,“合理的多元論”(reasonable pluralism)的事實意味着,不同的社會成員持有不同的整全性學說。例如,一個社會中可能會有佛教徒、基督徒、信奉儒家傳統的成員、信奉自由主義的成員,等等。在這樣的情形下,如果一種政治學說是“整全性的”,那麽就得不到所有人的認同。所以,他主張將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截然分離,構建一種純粹的、“非整全的”政治學說。通過這種學說,持不同價值觀念的人們經由“重叠共識”而達成一致,並在此基礎上建構穩定的政治秩序。所謂“重叠共識”,是指持有各種“合理的整全性學說”的公民所達成的共識。①②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4, 14-15.
然而,羅爾斯的理想是很難實現的。原因在於,這一“穩定的政治秩序”是不可能跳出價值觀念限制的。羅爾斯試圖找到獨立於各種宗教、形而上學、道德學說的“政治的正義概念”,但爲了確定這一概念的內容,又不得不訴諸民主社會的政治文化;而這種政治文化,卻不可能像羅爾斯所構想的那樣獨立於任何價值觀念。②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4, 14-15.例如,民主社會的政治文化將所有社會成員看作是“平等而自由”的,但如何通過政治制度的設計來維護這種都認同的“平等而自由”,就不可避免地將價值觀念的紛爭引入進來。至少在“自由”的實現是否需要對行爲者的價值觀念進行考量的問題上,持不同自由概念的人們就會爭論不休。因此,一種純粹政治的、獨立於任何價值觀念的政治學說衹能是空中樓閣,並不能如羅爾斯所企盼的那樣,帶來穩定的政治秩序。由此看來,國家的積極功能——對社會成員之價值觀念的干預,在現實的國家中是必不可少的。因爲,政治秩序的根基正是在於某些深入人心的價值觀念(例如,平等、自由、民主、公正、法治、忠誠、和諧等等),它們如果不能通過公共討論、交流、辯駁、修正……並最終得到大部分公民的認同,那麽,政治秩序就不會穩定,國家也就不復存在。
其二,在積極自由理論看來,人們的幸福不僅取決於人們的價值觀念,還依賴於基本的物質保障。這些保障包括人們“從搖籃到墳墓”的方方面面——生育、醫療、教育、養老、失業保險等等。衹有保障了人們的基本需求,人們纔可能從爲了生存而進行的枯燥勞動中解放出來,纔有可能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實現積極意義上的自由。由此,與“積極自由”概念相對應的國家的積極功能要求,在社會中建構足夠好的保障體系。在這一方面,“積極自由”概念導向了一種“福利國家”。相應的,“自由”概念的爭論也展現出新的形式:由“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之爭,轉變爲“形式自由”(formal freedom)與“實質自由”(substantial freedom)之爭。
在“自由”的概念史上,消極自由受到的最大的批評就是其“虛僞性”。在經濟不平等普遍存在的條件下,窮人事實上擁有的自由少得可憐。由此,一些學者將消極自由稱爲“形式自由”,而將與其相對的概念稱爲“實質自由”。“實質自由”的核心理念與“積極自由”一致:將自由理解爲行爲者能夠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並且認爲,衹有當國家和政府提供了足夠的社會保障,行爲者纔有機會從生存困境中擺脫出來,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實現自由。因此,也可以將“實質自由”看作是“積極自由”理論家族中的一個分支。
比利時當代哲學家帕里斯(Philippe v. Parijs)在《所有人的真正自由》一書中論述了“實質自由”概念,並將其稱爲“真正的自由”(real freedom)。他寫道,“實質自由”包括三個組成部分:安全,自我所有③“自我所有”(self-ownership),指行爲者對自身及其勞動成果的所有,其核心是私有權。,機會。與之相對,哈耶克、諾齊克等人所支持的“形式的自由”衹包含“安全,自我所有”兩個部分,對人們是否真正有“機會”去做那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是漠不關心的;而“真正的自由”則要求,保障人們擁有達成自己計劃的實質性的“機會”。在支持“形式自由”的學者看來,社會制度的設置對人們自由的保障衹需對人們打開“允許”之門,而無需保障人們擁有相應的“能力”。帕里斯則認爲,人們是否擁有相應的能力,實際上會影響甚至限制人們想要做什麽。對於市場經濟中的窮困者來說,其自身的能力和財富限制了他進行各種活動的自由。“一個理想的自由社會,必須表達爲所有社會成員的自由最大化的社會,而不僅僅是不干涉人們自由的社會。”①Phillipe van Parijs,Real Freedom for All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3.
基於“實質自由”的概念,爲了增進人們的幸福,國家應在允許人們嘗試各種合理生活計劃的同時,協助培養其實現生活目標的各種能力。由此,國家應建構免費或價格低廉的公共教育體系、醫療保障體系、失業保障體系、養老保障體系等等。在這些社會保障體系的支持之下,人們纔有可能擺脫爲了生存而進行的各種掙扎,獲得實現自己理想的實質性機會。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也是支持“實質自由”概念的理論家,在“實質自由”的基礎上,他發展出力圖保障人們“能力平等”的社會正義學說。②[印]阿瑪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任賾、于真 譯。
總體而言,由“積極自由”概念引申出的“積極國家”,其“積極”功能在於增進人們的幸福,幫助人們實現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而人們的幸福,通常又與人們所持的價值觀念以及可獲取的物質資源相關,所以,“積極國家”會通過兩種手段增進人們的幸福:一是對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念進行管控;二是以稅收等再分配政策籌集資金,建立涉及醫療、教育、住房、養老、失業等方方面面的社會保障體系。因此,從理論上說,積極國家可能呈現出兩種形態:一種是對價值觀念進行適當管控的國家,其極端形式是走向專制主義;另一種是全面保障人們基本生活需要的國家,各式各樣的福利國家都屬於這種類型。但是,在現實政治中,任何基於“積極自由”概念的“積極國家”都是上述兩種類型的綜合,區別在於:管控是多一點還是少一點,福利是多一點還是少一點。
在積極國家中,人們大多能享受到免費的公立教育,免費或價格低廉的醫療服務,有效的住房、失業、養老保障,等等。在這樣的國家中,窮人和富人的生活質量不會有天壤之別,貧窮的代際傳遞有可能被阻斷,各階層之間的流動性較強。當然,在積極國家中,人們不會擁有毫無限制的言論自由,但衹要國家對價值觀念的管控沒有達致極限,社會成員仍將保有獨立思考和建構自己人生理想的空間。
積極國家最容易受到的攻擊是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和“再分配”政策。這兩種攻擊都來自消極自由理論。爲了管控價值觀念,國家必須適當限制人們的言論自由;要爲人們提供更好的社會保障,國家必須實行“再分配”政策,將一些人的錢用於社會保障體系和公共設施的建設。然而,持“消極自由”概念的人認爲,這些措施會侵犯人們的“非干涉”的自由。
三 共和主義自由與國家
由伯林引發的西方學術界對“自由”概念的爭論持續至今,即使美國哲學家馬卡盧姆(G. C.MacCallum,1925—1987)徹底否定了兩種自由概念的區分③Gerald C. MacCallum, “Negative and Positive Freedom”,Philosophical Review 76 (1976): 312-334.,也未能將紛爭平息。在馬卡盧姆之後,對自由概念的討論又掀起了新的波瀾,這就是“共和主義自由”理論的復興。
“共和主義自由”的復興同時發生在兩個學科領域:(1)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劍橋學派的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波考克(John G. A. Pocock)等學者開始發掘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共和主義思想。他們通過對馬基雅維利(N. Machiavelli,1469—1527)、霍布斯(T. Hobbes,1588—1679)、哈林頓(J. Harrington,1611—1677)等思想家的重新闡釋,重述政治思想史中的共和主義傳統。在這一思想傳統中,“自由”是一個核心概念,從這一概念中可以推導出共和主義的政治理論和國家學說。(2)在政治哲學研究的領域,澳大利亞哲學家佩蒂特(Phillip Pettit)認爲伯林對兩種自由的區分並沒有窮盡所有的自由概念,他試圖在伯林的兩種概念之間構造出一種新的自由概念。而這種自由概念,與劍橋學派思想史家從思想史中發掘出的“共和主義自由”概念一拍即合。上述兩個學科領域的研究進展促成了“共和主義自由”概念的重新闡釋以及共和主義政治理論的復興,代表性著作有,斯金納的《自由主義之前的自由》《霍布斯與共和主義自由》,佩蒂特的《共和主義:一種關於自由與政府的理論》等。
在佩蒂特看來,伯林以“非干涉”(non-interference)與“自我控制”來區分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但“干涉”與“控制”並非同一含義,因此,在“非干涉”與“自我控制”之間還有一定的理論空間,還可以構建一種自由概念。他將這第三種自由概念稱爲“非支配”(non-dominance)的自由,即排除他人對行爲者的“支配”。那麽,“支配”與“干涉”有什麽不同呢?區別在於,與他人的“干涉”對應的是行爲者的“行動”;而與他人的“支配”對應的則是行爲者的“意志”。所以,佩蒂特強調的是:自由的實現在於排除他者對行爲者“意志”的支配,而不在於排除他者對行爲者“行動”的干涉。如此看來,“非支配”的自由特徵是:一方面,它與積極自由類似,關注的是行爲者能夠控制自己的慾望,成爲自己意志的主人,但它不對“自我”進行二分,區分出慾望、理性,或者“較高自我”“較低自我”,不將行爲者自身的因素算作對其意志的阻礙;另一方面,它又與消極自由類似,將不自由的根源歸結爲他人對行爲者意志的支配。
爲了更清晰地說明“非支配的自由”與“非干涉的自由”的區別,佩蒂特以“受寵的奴隸”作爲例子。一個“受寵的奴隸”可能擁有行動不受干涉的自由,但他的行動總是可能受到主人的專斷意志的干涉,這使得他時時處處提心吊膽,不得不時刻揣摩主人的想法,即使主人從未發過脾氣,也沒有限制過他的行動。佩蒂特認爲,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可能擁有“非干涉的自由”,但並不擁有“非支配的自由”。換句話說,即使人們行動的自由沒有受到實質性限制,但行動自由受到限制的可能性卻隨時存在。相反,如果是在一個統治權力受到限制的法治國家,人們對自己行動自由的界限非常清楚,並且認同每條法律背後的理由,那麽,人們即使行動上受到限制,但意志並不受支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適應法律並主導自己的生活。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擁有“非支配的自由”,但並非無限制地擁有“非干涉的自由”。
由此說來,“非支配的自由”的核心在於“意志”不受他人支配。然而,這一自由理想在人類社會中卻很難實現。因爲,人類社會中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集體決策,而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必須服從有可能與自己意志相違背的集體決策。那麽,人們如何在集體決策的過程中不受他人意志的支配,獲得“非支配的自由”呢?盧梭(J-J. Rousseau,1712—1778)的政治哲學提供了一個頗具智慧的解答:讓自己的意志融入到集體的意志中,使自己的意志變成集體意志。①在伯林的批評中,盧梭被當成了積極自由理論的代表,其“强迫自由的悖論”是伯林重點攻擊的對象。然而,盧梭最開始表述的自由概念更像是共和主義的自由概念,衹是在推導到最後一步時,纔跌入了積極自由的悖論之中。追溯盧梭自由理論的發展脉絡可以看到,共和主義的自由概念與積極自由概念僅一步之遙。在《山中書簡》一書中,盧梭對自由做了這樣的論述:“與其說自由是按自己的意願做事,不如說,自由是使自己的意志不屈服於他人的意志,也不使他人的意志屈服於自己的意志。”②Jean-Jacques Rousseau, “Letters from the Mountai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 (Hanover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1), Vo1.9, 260-261.簡言之,自由即是意志不受他人支配。這一含義,與佩蒂特所說的“非支配”的自由完全一致。盧梭認爲,在自然狀態下,人們之間是相互隔絕的,每個人都是獨行俠,每個人的意志都不受他人的支配,擁有自然的自由;然而,當人們進入社會,人們的意志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個普遍的意志。此時,人們要想自己的意志不受他人的支配,衹能是將自己的意志融入到這個普遍的意志之中。而要將自己的意志融入到普遍的意志之中,唯一可行的制度設計衹能是直接的民主參與。正是基於這一推理,盧梭推崇古代的直接民主,而反對代議制形式的間接民主。
除了直接的民主參與外,保護每個人的意志不受他人支配的另一個制度設計是法治——以法律統治國家。在盧梭的人民主權理論中,民主與法治是合二爲一的——民主即“人民的統治”(rule of people),法治即“法律的統治”(rule of law)。在盧梭的闡釋中,人民的意志就是公意,而“公意”就是法律。他通過“公意”這一概念,一方面將民主與法治合二爲一,另一方面將服從與自由也合二爲一。從後者來說,在人們進入社會狀態之後,人們服從“公意”就是在服從法律,服從法律就是在服從自己的意志。
佩蒂特重新闡述了“共和主義自由”概念。他雖然讚同盧梭對自由的最初理解——行爲者的意志不受他人支配,卻不讚同盧梭的自由理論中“公意”所要求的絕對服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個人意志與“公意”完全融合有困難,造成了盧梭自由理論的失敗。在制度層面,佩蒂特讚同盧梭的觀點,也主張廣泛參與的民主和以憲法爲基礎的法治。他認爲,法治是防止人們受到“支配”的最佳手段,而法治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法律是普遍而公開的,對所有人都適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立法者在內。第二,政府部門要依法行政,其自由裁量權要受到限制。對於民主,佩蒂特認爲,廣泛的參與式民主能夠保證政府的行爲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意願,最大限度地體現人民的意志。①Philip Pettit, Republicanism: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3-181.總之,“非支配”的共和主義自由爲人們描繪的圖景是:這是一個人們廣泛參與民主決策的國家,一個以代表所有人意志的憲法爲基礎的法治國家。
綜上所述,自伯林提出兩種自由概念的區分之後,西方學術界對“自由”概念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這些爭論中,消極自由、積極自由、共和主義自由這三種概念導向了不同的政治主張和國家形態。消極自由理論主張,應減少國家對個人行爲的干涉,國家對所有價值觀念保持中立,最終導向了消極國家,甚至是“最小的國家”。積極自由理論主張,國家應對個人的價值觀念適當管控,爲社會成員提供足夠好的教育、醫療、住房等各種社會保障,極端情況下有可能導致專制國家,通常情況下會導向某種形式的福利國家和對價值觀念進行適當管控的國家。共和主義的自由理論反對國家和政府對人們意志的控制,在制度層面主張通過參與式民主和以憲法爲基礎的法治而消除國家的專斷權力,這樣的政治理論將最終導向共和主義的國家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