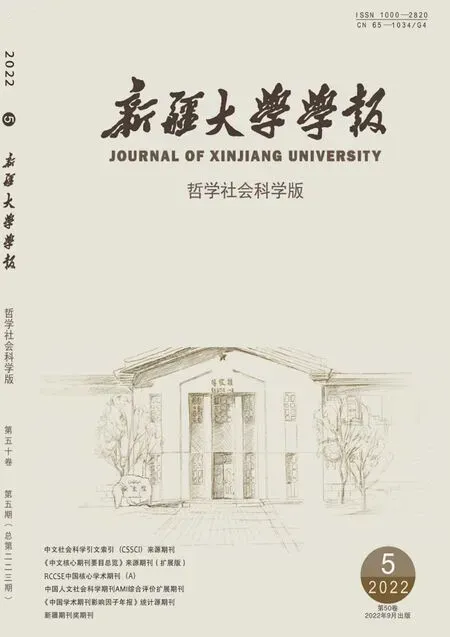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的陆机批评*
黎思文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陆机为 “太康之英” ,其诗辞赡体美,情繁旨缛。历代的批评家多认同陆诗胜在辞采,而弱于抒情。西晋至唐代是陆机评价的高峰,然而以之为上品的钟嵘,在激赏其含英咀华之时,仍不讳言 “气少于公幹”[1]162。宋代以后,陆诗品第骤降,人们对其 “体气” 的指摘明显多了起来,叶适等理学家评陆诗为 “格卑气弱”[2]。明清之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又拈出 “情辞” 二端,对陆机的批评别具一格。
陈祚明(1623—1674),字胤倩,钱塘人,博学善文,是明末清初的诗人和诗论家,有《采菽堂古诗选》和《稽留山人集》等著作传世。《稽留山人集》又名《敝帚集》,二十一卷,四库馆臣列为存目。《采菽堂古诗选》正集三十八卷,补遗四卷,这不仅是陈祚明精心编订的一部大型诗歌选本,也是其评点古诗和构建六朝诗史的集中体现。
《采菽堂古诗选》选诗众多,以年代为序,选录了先秦至隋朝的四千四百八十七首诗。其中选诗九十首以上的诗人就有六位,分别是庾信(232首)、陶渊明(160首)、鲍照(128首)、谢眺(118首)、沈约(96首)、陆机(95首)。其论庾信曰: “生平歌咏,要皆激楚之音,悲凉之调。情纠纷而繁会,意杂集以无端。”[3]1080论陶渊明: “公诗自成千古异观,如古器虽有衅文,不伤其古。无一首可删也。”[3]389论鲍照: “既怀雄浑之姿,复挟沉挚之性。”[3]563论谢眺: “去晋渐遥,启唐欲近。天才既隽,宏响斯臻。斐然之姿,宣诸逸韵。轻清和婉,佳句可赓。”[3]635论沈约: “以命意为先,以炼气为主。辞随意运,态以气流。故华而不浮,隽而不靡。”[3]721综观对选诗数量最多的几位诗人的总评,皆以褒扬称善为主,认为他们或以辞胜,或以气胜,或以情胜,或兼善众美。然而,针对入选九十多首诗的陆机,陈祚明的评点与前面五人迥异,不惟批评陆诗敷旨平浅,还具体指出其拟古、乐府、述志、赠答各类诗作之短。《采菽堂古诗选》对陆诗的选与评如此表里不符,与陈祚明的人生遭际、情辞并举的诗学审美以及明末清初对七子和竟陵的折衷与修正风潮不无关系。
一、尚辞失情
陈祚明所处的是朝代更替的时代,也是诗学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诗人学者,一方面看到明代复古与反复古两派的成就,另一方面又对其拘泥一途和矫枉过正深恶痛绝,所以力图补偏救弊,强调诗歌既要保持声调、辞句的雅正,又要抒发真挚的情感。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凡例》中开宗明义地说: “诗之大旨,惟情与辞。”[3]凡例1所谓情辞并举,即不偏重情或辞的任何一个方面。如果不能平衡诗歌情与辞的关系,则大约失在两端: “崇辞失情”[3]凡例4和 “崇情刊辞”[3]凡例3。
陈祚明用 “崇辞失情” 批评复古派, “己实无情而喋喋焉,繁称多词,支支蔓蔓,是夫何为者?故言诗不准诸情,取靡丽谓修辞,厥要弊,使人矜强记,采摭剿窃古人陈言,徒涂饰字句,怀来郁不吐,志不可见,失其本矣”[3]凡例1-2。七子高倡复古,但注重辞藻声律而忽视真情实感,陈祚明在《凡例》中说: “过矣于鳞之言曰:‘修辞宁失诸理。’”[3]凡例7他反对为扭转文风,以师古为口号,食古不化,不能陶镕显志、袭故弥新,而陷入因袭辞章的窠臼,力有余而巧不足,导致情疏律庸。他评李攀龙云: “于鳞拟古乐府,涂窜本词,尤其拙劣,不足观矣。”[3]759认为王世贞评谢灵运《登池上楼》 “池塘生春草” 为 “佳语非佳境” ,是不知情之故,又云: “元美作《卮言》时,方尚填缀,若钟嵘所讥者,故终不能赏此自然之奏也。”[3]528所谓 “方尚填缀” 指的是七子尚辞失情的陋习。这种以缀辞为高的诗文作法,在陆机身上亦有体现。
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人倒是重情,然又伤于平率,失之于雅,走向另一个极端: “崇情刊辞” 。《凡例》说: “夫有情而不善言之,则如不言。有情而言之卑陋俚下而无所择,取诮百世,则如默焉。”[3]凡例4句句直指竟陵之病。 “惩噎而辍食,思一矫革,大创之,因崇情刊辞,即庳陋俚下;无所择,不轨于雅正,疾文采如仇雠。”[3]凡例2情感千古皆有,若不受拘束随口而出,很容易偏离清真步入俚率一路,甚至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陈祚明要求诗歌既要情真,又要辞雅。 “以情为本,而注重修辞,而辞又以雅为准则,这就是陈祚明的最基本的诗歌美学观。”[4]
陈祚明主张情辞并举,不仅不排斥辞,而且承认辞的功用,他在《凡例》中说道: “夫辞,所以达情也,情藏不可见,言以宣之。”[3]凡例3辞有典雅、绮丽,有雄浑、平淡,有细密、疏野,有豪放、婉约,有千种万钟,各具特色。历代踵事增华,至少极尽所能发挥语言文字的魅力。而人有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惧,并无优劣代降之分。后人仅能通过传世之辞来感知古人之情,是所谓 “情见乎辞” 也。因此, “崇情刊辞” 与 “崇辞失情” 两弊相权, “尚辞失之情,犹不失为辞也。尚情失之辞,则情并失”[3]凡例4。陈祚明选录陆诗九十五首,对陆机 “咀嚼英华,厌饫膏泽”[1]162是认可的,他倍感遗憾的是难以在陆诗之中觅得缠绵抑或悲切之情。
首先,陈祚明肯定陆机的缀辞之才,认同《诗品》对陆诗辞赡体美的评价。《采菽堂古诗选》的总评,一般由诗人小传、《诗品》评语、自撰评语、诗风譬喻等几部分构成。如果对钟嵘《诗品》的品评有异议,陈祚明会在自撰评语中提出辨正,如论左思: “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简贵。创成一体,垂式千秋……钟嵘以为‘野于陆机’,悲哉!彼安知太冲之陶乎汉魏,化乎矩度哉?”[3]344
就陆诗批评而言,陈祚明屡用 “矜秀” “平畅” “雅练” “矜琢” 等审美概念。究其原因,士衡矜重,尚规矩,贵绮错,风格雅正。从这些概念出发,可以见出陆机在雕字琢句、结体谋篇方面下功夫,对诗歌的形式较为看重。《日出东南隅行》写艳,尽态极妍,端丽妖娆,《采菽堂古诗选》云: “撰句矜秀,是晋人正格。”[3]195但造情则失于浅,除拟古外,占陆诗较大比重的述志、赠答众作,被陈祚明认为是 “皆不及情”[3]293。
其次,陈祚明批评陆诗的 “性情不出”[3]294。陈祚明论诗,虽然情辞并举,但是以情为本。关于个中缘由,他有具体阐释: “古今人之善为诗者,体格不同而同于情,辞不同而同于雅。予之此选,会王李、钟谭两家之说,通其蔽而折衷焉。其所谓择辞而归雅者,大较以言情为本。”[3]凡例4其于稍嫌辞费而隐藏深情者,单文只字而有独到的情感抒发者,一概收纳。因此,在陈祚明的诗学理念中,陆机长于法,潘岳长于情, “安仁有诗,而士衡无诗” 。不同于一般的评价结构,陈祚明通过论潘、陆异同来凸显潘岳风格,对其主张的情辞关系进行了一次具体演绎: “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剌剌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安仁过情,士衡不及情;安仁任天真,士衡准古法。夫诗以道情,天真既优,而以古法绳之,曰未尽善,可也。盖古人之能用法者,中亦以天真为本也。情则不及,而曰吾能用古法。无实而袭其形,何益乎?故安仁有诗,而士衡无诗。钟嵘惟以声格论诗,曾未窥见诗旨。其所云陆深而芜,潘浅而净,互易评之,恰合不谬矣。不知所见何以颠倒至此?”[3]332-333也就是说,《诗品》关于潘、陆诗风和价值的判断是错位的。
陈祚明扬潘抑陆,一方面重构了钟嵘确立的 “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1]34诗人品第,另一方面树立了 “以情为本” 诗学典范,同时呼唤真情的流露。他评源出于陆机的颜延之说: “约束矜庄,掩其容态。暂复卸妆闲燕,亦能微露姣妍。”[3]504总的来说就是缀词太繁,用法太过,正如大家命妇,若能卸下矜庄,复归自然,便能看见娇妍本色。然而,饱尝家国破碎之悲的陈祚明,见到的并非振起精神抒发激楚之声的陆诗,而是 “性情不出” 的陆诗。他的陆诗分评多是一褒一贬,承认文辞之巧与秀,而责备不能感人至深:
有亮音而无雄气,有调节而无变响,士衡诗大抵如此。[3]294(《短歌行》)
撰句矜秀,是晋人正格。校陈思绕静气,比子桓少余姿。[3]295(《日出东南隅行》)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对陆机的观照,几乎完全集中在对拟古的批判之上,以致忽视了对陆诗中为数不少的乐府诗之深情的挖掘,如《苦寒行》《豫章行》《悲哉行》等,寓情于景,慷慨激昂。他推测陆机少情的原因, “岂余生之遭难,畏出口以招尤?”[3]294然而并没有就此深入剖析陆诗,相较而言,他对庾信低徊蕴藉的 “拉沓缠绵”[3]1105明显付出了更多耐心。
二、法胜其辞
居于情辞之间,还有神、气、才、法。陈祚明称之为 “取诸其怀而术宣之,致其工之路也”[3]凡例1,也就是将内在的情感外化,达到诗之精工的路径。神、气、才、法四者,陈祚明重点放在讨论 “法” 之上。尚辞往往与尚法牵拘在一起,他在《凡例》中专门用 “法胜其辞” 来批评陆机: “予不赞士衡、文通者,徒以法胜其辞,直浅之乎言情也。”[3]凡例8所谓 “法” 与 “辞” ,在《采菽堂古诗选》中有明确的界定: “诗之大旨,惟情与辞。曰命旨,曰神思,曰理,曰解,曰悟,皆情也;曰声,曰调,曰格律,曰句,曰字,曰典物,曰风华,皆辞也。曰神,曰气,曰才,曰法,此居情辞之间,取诸其怀而术宣之,致其工之路也。”[3]凡例1如复古派李梦阳谓自己得尺寸古人之法, “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二”[3]567。作文程式化,是以法生辞,而非为情造辞。过于固守法度,满足于鹦鹉学舌式地效仿古人,必然束缚情志之表达。如此言情难有深意,常近乎伪。
陆机 “法胜其辞” 突出表现在拟古之上。前人谓拟古昉于陆机,字摹句效,犹如临帖。陆机拟古诗曾名重一时,要之,在文学自觉和 “五言居文辞之要” 的时代,陆机用力在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上创新,将质直的古诗雅化,客观上提供了一个通过模仿增进诗道的典范。这种尝试和探索,在诗体成熟的时代,容易被认为是雕虫小技,华而不实,空洞无物。宋元以降,陆机的拟古饱受批评。刘履和王世贞就认为陆诗之病不在才多,而在于模拟。原因即在于,若既沿袭古诗之意又用其字句,则与剽窃无异。
《采菽堂古诗选》以陆士衡和江文通并举,也正由于此二人具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模拟:陆士衡拟古诗十四首,江文通作《杂体诗三十首》。陆诗之中,拟古所受的溢美之词最多,非议之声也最大。如钟嵘推重 “五言之警策者”[1]459,标举士衡《拟古》,将其视为与《十九首》比肩之作。而陈祚明则嫌其使用技巧太过,拟古诗之辞与古诗之意,将自我情感局限在古诗的结构之中,显得四平八稳,也就流于平浅。拟意和拟字,稍作转换,其实就是情辞关系。陈祚明转而借用到情辞并举、以情为本的诗歌观念当中。
拟古诗若能借古人之话说自己之话,寄寓本人的感遇和情志,自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那也是应当鼓励和推崇的: “求胜于古,始堪拟古。”[3]315陈祚明并不完全排斥拟诗,他本人也大量拟古,曾作《拟古诗十九首》和《后拟古诗十九首》,认为古诗正体是冲淡隽永,言有尽而意无穷。他主张拟古应当有感而发: “古今人不相远,独以其情耳。自士衡、文通之流效而为之,莫臻其妙。夫情有所止,而故作之,非其至也。”[5]464不难想见,所谓拟渊明似渊明、拟左思似左思的江淹,在《采菽堂古诗选》中的地位不会太高: “意乏圆融,调非玄亮。衡其体气,方沈直是小巫。”[3]752其《杂体三十首》仅得皮肤,未得筋骨。这种批评与对陆机的品评呼吸相通。
陆机拟古最大的问题在于循法。拟古之法有高下差异,能辨古诗之体,参悟其性情声调,是用 “法” 的高级阶段;仅随古人成构,因袭词章,只是用 “法” 的最初境界: “法有循之以为谨,有化之以为变,有忘之以为神,无无法者。士衡循法者乎?文通、玄晖其流也;子建化于法矣,休文其流也;《十九首》、古乐府,神于法者乎?嗣宗、元亮、康乐、子山,盖日孜孜焉。”[3]凡例6清人毛先舒也喟叹陆机用法的问题: “士衡之诗,才太高,意太浓,法太整。”[6]如此一来,拟诗的才气、刻意、整饬,排挤了原诗的自然高古。陆机在步骤前人的轨范中,有意无意忽视了表现或细腻幽微或壮怀激越之情。其拟古据钟嵘《诗品》原有十四首,萧统《文选》选录十二首,陈祚明删削四首,《采菽堂古诗选》仅选八首:
《涉江采芙蓉》篇,更无佳致。 “沉思钟万里” “钟” 字,近《兰若生朝阳》篇 “执心守时信” ,语生率。 “譬彼向阳翘” “翘” 字,凑韵。《西北有高楼》篇 “迢迢峻而安” “安” 字,无趣。 “但愿歌者欢” ,亦少味。夫歌者欲得听者之欢,何及愿歌者之欢?但久伫立,彼即欢乎?且通首亦平平。《庭中有奇树》篇, “欢友兰时往” “欢友” 字, “兰时” 字,并生。通首亦乏致,故不录,仅录八首。此八首,亦皆平调,本不足法,但差胜耳。《东城一何高》篇,亦稍嫌之。[3]315
陈祚明认为这些拟诗皆差强人意,倒是像《太山吟》之类作品无章法可循,劈头直陈山高云郁,仿佛亲见泰山,即事即咏, “正惟不作章法,顿挫反而有余情”[3]300。
陈祚明将陆机和江淹视为 “法胜其辞” 的代表,《采菽堂古诗选》甄录陆机所存十二首拟古诗中的八首,从选诗数量上看,远远多于明清其它古诗选本。不过这并不能说明陈祚明认可陆机的拟古之法,他总括道: “士衡诗束身奉古,亦步亦趋。在法必安,选言亦雅,思无越畔,语无溢幅。”[3]293陆机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其结果便是情旨庸浅,对奉行以情为本理念的陈祚明来说,是诗家之大忌。这也直接导致陆机在潘、陆优劣论中毫无疑问地处于下风:
陆士衡诗如都邑近郊良家村妇,约黄束素,并仿长安大家,妆饰既无新裁,举止亦多详稳。[3]294
潘安仁诗如孺子慕者,距踊曲跃,仰啼俯嘘,其音呜呜,力疲不休,声澌益振。所喜本擅车子之喉,故曼声宛转,都无粗响。[3]333
(《悼亡诗》)造情既至,转展愈曲愈悲。 “念此” 二句,一岁以内令哀也。 “尔祭” 四句,延及一岁以后。 “徘徊” 二句,临坟之切也。 “谁谓” 二句,延及旋车以后,一不知伉俪之笃,乃至于此。固是夫妇间千秋绝搆,士衡不能道此只语。结句用意更曲。[3]340
陆诗被形容为村妇效颦,功在模拟而未能超越;而潘诗如薛访车子喉转引声,潜气内转,哀音外激,感人至深。陈祚明对二者的类比譬喻,意在说明潘岳情深而陆机情浅。颇具戏剧性的是,正是陆机首倡 “诗缘情而绮靡”[7]。西晋以前, “诗言志” 一直是中国诗论的纲领。依照朱自清先生的看法,赋诗、献诗、教诗、作诗均可以言志,此志主要就怀抱而言,强调美刺作用,与政教关系密切。①参见朱自清《诗言志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7-51页。西晋以后,诗歌的 “言志” 和 “缘情” 在不同时代各有偏重,二者似乎相互角力,共同构建起中国诗学理论。面对汉魏诗歌的伟大成就,太康文人选择了 “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8]的策略。陆机等人通过大量使用俳偶、拟古等技巧,规摹前作或自铸伟辞,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人情志的表达力度。
三、 “同我” 与 “殊调” :陈祚明 “伤平浅” 之原因
陈祚明评陆机 “造情既浅,抒响不高”[3]293, “述志赠答,皆不及情”[3]293, “敷旨庸浅,性情不出”[3]294, “衷情本浅,乏于激昂”[3]294,完全将陆诗作为反面典型加以批驳,连谭献都为陆机打抱不平,深感 “《采菽堂古诗选》论陆士衡语稍苛”[9]。然而,陈祚明实则借此抒发个人愤懑,申张自己的诗学理念,力图破除明代复古派和竟陵派两家的陈见。
陈祚明有意提升南朝诗人地位,构建六朝诗史。初唐以后,诗人诟病六朝文学绮艳俚俗,缺乏汉魏风骨。明人一味主张近体学唐,殊不知齐梁诗稍趋律体,是唐调之源。陈祚明通过大量选录宋齐梁诗,确立六朝诗在诗歌由古到近变体中承上启下的地位。《采菽堂古诗选》选诗超过四十首的诗人有十七位,分别是曹植、嵇康、阮籍、陆机、陆云、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眺、萧纲、沈约、江淹、吴均、何逊、张正见、江总、庾信。梁陈以后诗人不仅占了半数,历来颇受选家轻视的宫体诗人萧纲、张正见等竟赫然在列。
首先,《采菽堂古诗选》突破了萧统《文选》的取材。《文选》选诗谨严,去取有旨,然而陈祚明认为其仍不乏遗璧,从诗学审美上看,萧统对 “志幽言远”[3]388的陶诗不够重视;从客观历史上看,萧统莫能选录沈约、任昉、阴铿、何逊、庾信等梁陈以后之诗。所以《采菽堂古诗选》特别致力于囊括陶诗,经过再三披览,终觉 “无一首可删也,乃尽载正选中”[3]389,即他所说的 “于时得一人焉”[3]凡例10;并尽心收录梁陈以后诸作,即 “于后得五人焉”[3]凡例10。
其次,陈祚明修正了钟嵘《诗品》的品第。《采菽堂古诗选》正文主要由总评、原诗、分评三部分构成,其中总评又一般采用诗人小传、《诗品》评语和陈祚明评点的模式,可见陈祚明对于《诗品》的重视。他在总评和分评中经常反驳钟嵘的意见,有学者称之为 “异质性批评”[10],如评潘岳: “钟嵘惟以声格论诗,曾未窥见诗旨。”[3]333评左思: “钟嵘以为‘野于陆机’,悲哉!彼安知太冲之陶乎汉魏,化乎矩度哉?”[3]344评任昉: “所造至此,钟嵘胡足以知之?而谓‘动辄用事,诗不得奇’,悲夫!”[3]783
不惟如此,他还推尊齐梁陈三代诗歌,推翻《诗品》确立的曹植—陆机—谢灵运为上品第一流诗人的定论,而以北周庾信为第一: “审其造情之本,究其琢句之长,岂特北朝一人,即亦六季鲜俪。”[3]1081并重构了以六朝诗人为优的品第序列,否认《诗品》的代降之说,认为谢灵运胜于曹植,曹植胜于陆机。在评谢灵运时,陈祚明说: “钩沉索隐,穷态极妍,陈思、景阳,都非所屑。至于潘陆,又何足云?”[3]519通过贬低陆机等人,将魏晋诗人置于南朝诗人之下,达到了为南朝诗正名的目的。
虽然《采菽堂古诗选》未定诗人品第,但是综览陈祚明的评论,陆机显然不是一流诗人,更不符合情辞并重、以情为本的诗学理念。陈祚明大量选录陆诗,却将陆机作为反面典型加以评说,主要是不满陆诗情感平浅,恨其亡国之悲不显、远情逸调不彰。这又与陈祚明的解诗方法有关。
1. “同我者乃能知我也”[3]429
此为陈祚明评点陶渊明《咏贫士》的话语,意思是唯有 “同” ,才能感同身受领会诗人之志和诗歌之旨。那么如何 “同” 呢?概而言之,不外乎同乎行事和同乎心事。关于这两点,陈祚明与陆机有诸多相似:
首先,同乎行事:国破家亡和北上飘零。吴凤凰三年秋,陆抗因病辞世。陆机与兄弟分领父兵, “墨絰即戎”[11]857,在荆州参与对晋作战。吴天纪四年二月,龙骧将军王濬顺流东下,所至辄克,机兄陆晏、陆景均战死。次月, “一片降幡出石头” 。据史传所载,历经兄弟罹难、东吴亡国的陆机, “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12],后被征辟入洛。一千三百年后,易代之剧换了几个主角, “家亡—国破—退居—羁旅” 的悲剧一幕再度上演。顺治三年五月,陈祚明长兄,时任南明鲁王大理寺少卿兼御史的陈元倩,因师旅尽溃,走至山阴化龙桥,偕妻妾赴水而死。此后,南明小朝廷覆亡。陈祚明 “携亲以归,弃诸生,与兄贞倩、弟康侯奉母居河渚”[13],作明遗民近十年。迫于生计,旅食北京,以馆师为业。陈祚明的人生轨迹几乎与陆机重合。
其次,同乎心事:黍离之悲和乡关之思。试观陆机《豫章行》,写兄弟离别,连山川都着凄苦之色彩。只因假题于乐府,其感慨世殊事异的悲伤令人浑然不觉。吴淇《六朝选诗定论》 “再三把玩,字字有亡国破家之感”[14]256。再看陈祚明《春感六首》: “辇道春云覆,宫壕细草生。稍看腾浴马,不见语流莺。水态河桥动,风光苑树萌。侠邪从步屧,莫起故园情。” (其二) “肯恋长安乐,还山讵可忘。相从僮渐长,忆艺菊应荒。玉涧流仍碧,宫垣树欲苍。春归不待客,芳草遍江乡。” (其三)[5]473山河虽在,已易他主。庭院荒芜,宫树苍苍。草木无知,人何以堪。曰归曰归,奈何淹留无期。心生对故国、故乡、故人的思念之情,尚可强作镇定,而 “摧刚为柔,刓方为圆”[5]序448对一个有志之士无疑是沉重的精神打击。类似的情形在《猛虎行》中亦有表露,险恶阴森的自然环境,象征险象环生、波诡云谲的政治生态。要保持自身的耿介高洁多么不易,所以陆机叹 “志士多苦心”[11]335。
再次,同中有异。易姓改号之后的个人选择,在任何时代都是敏感话题。陆机入洛后,受到太原王济、范阳卢志等人的排挤,与其亡国之余的身份大有关系。只是在魏晋士无特操、政失准的时代,文人士大夫受儒家忠君守节思想束缚较小,社会对改节的包容性较强。而明清鼎革对深服华夷观念的传统知识分子刺激极大,仕与不仕关乎民族气节问题,陈祚明本人对此相当介怀。从《采菽堂古诗选》评《与殷晋安别》可见出一二: “殷先作者晋臣,与公同时;后作者宋臣,与公殊调。篇中语极低徊,朋好仍敦,而异趣难一也。”[3]403身仕仇雠与终老布衣两种抉择,陆机迫于前者,陈祚明选了后者。相比陶潜,陆机没有满足陈祚明对于出处的要求。
当然,个人命运往往被政治社会形势裹挟,可是主观不作为和客观难作为毕竟两回事,个体在黑暗无助中的呐喊和挣扎正是最打动人心的部分。例如庾信尽管被扣留北朝,可诗中的 “激楚之音” 和 “悲凉之调” 使之成为陈祚明心中的寄托和《采菽堂古诗选》之冠。那么,与陆机人生境遇相似,与吴淇评诗方法相同,陈祚明为何又得出与《六朝选诗定论》截然相反的评价?
2. “言情必淋漓曲尽”[3]1116
相比庾信,陆诗没有满足陈祚明对于言情的期待。诗歌的情感表达应当婉曲还是直致,确切而言不能一概而论。在《采菽堂古诗选》的评语中,我们可以看到陈祚明心中的千古至文《古诗十九首》得 “言情” 之精谛在于能够 “含蓄不尽” :
言情能尽者,非尽言之之为尽也,尽言之则一览无遗。为含蓄不尽,故反言之,乃使足思。盖人情本曲,思心至不能自已之处,徘徊度量,常作万万不然之想。今若决绝,一言则已矣,不必再思矣!故彼弃予矣,必曰 “亮不弃” 也。见无期矣,必曰 “终相见” 也。有此不自决绝之念,所以有思,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为径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写之。故言不尽,而情则无不尽。[3]81
人们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壮志难酬、年寿有时、情侣别离、朋友阔绝等等,都能生出普遍深刻并引发强烈共鸣的情感。诗人在表情达意之时,务必低徊反复,方能余味无穷。姜夔就说: “诗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15]事实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是多数诗人的审美追求,同时也是陈祚明对于陆机的要求。他在分评《悲哉行》时批评陆机语多累赘,起句轻俊,与建安诗歌 “不求纤密之巧” 不同,步入齐梁一路: “言情于景物之中,情乃流动不滞也。但如此已足,翻嫌‘目感’二句,重述径露。诗以含蓄有余,令人徘徊为妙,写尽乃最忌。”[3]301一层紧接一层,不留想象和阐释的空间,这本是晋世群才的通病。那么,《采菽堂古诗选》又何以提出诗贵曲尽呢?
“言情必淋漓曲尽” 是陈祚明对抒发黍离之悲与乡关之思的特殊要求。他和庾信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十分钦佩其 “激楚之音” 和 “悲凉之调” ,在评庾信《仰和何仆射还宅怀故》时提出此原则,同时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践行类似主张。《赠曾庭闻南征歌》写朝代更迭,充满了对新朝的嘲讽与怨恨: “风尘一起事全非,自分终身老布衣。落魄曾为人所羡,远游只为食恒饥。君更兵间逃百死,章贡孤城血如水。生灵百万一朝屠,事急潜身窜狱底。”[5]618
陆诗于哀乐两处尽失激昂。陈祚明本人之诗不题清朝年号,而书甲子,显示出陈氏不仕异族的遗民心态,大有效法陶潜的意思。《稽留山人集》中的诗词虽经校雠削改,刊除了明显违碍之语,但其《皇姑行》《瘦马行》等在克制中仍壮怀激切,正如庾信歌诗 “时隐时彰” 表露怨怼悲愤之情。庾信、陶潜之所以成为《采菽堂古诗选》中入选诗作最多的二人,除了贯彻陈祚明推尊六朝的诗学理念外,还寄寓了他志洁行廉的人生理想。反观陆机,吴亡受征辟入洛,人格或为陈祚明所不齿,其诗不喜亦不悲的感情基调,也不是遗民所期待的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招致陈祚明的极大不满。
“夫破亡之余,辞家远宦,若以流离为感,则悲有千条;倘怀甄录之欣,亦幸逢一旦。哀乐两柄,易得淋漓。乃敷旨庸浅,性情不出,岂余生之遭难,畏出口以遭尤?故抑志就平,意满不叙,若脱纶之鬣,初放微波,圉圉未舒,有怀靳展乎?大较衷情本浅,乏于激昂者矣。”[3]293-294相比庾信的北朝羁迹,陆机的赴洛仕晋与陈祚明的旅食京师实属异世同调。谜底已被陈祚明揭开,他并非不能,更多是不愿在陆诗中窥探其缠绵悱恻之情。庾信《杨柳歌》委婉曲折地伤己奉使,并有故梁之思和身世之叹, “比绪不清,文旨杂出,稍令费解”[3]1085,虽然不如《拟咏怀二十七首》之悲凉孤愤,但陈祚明还是窥测出庾信为了避免猜嫌隐藏在 “烦冤郁纡”[3]1085之中的真情。陆机则没有这么幸运,陈氏评骘陆诗,多嫌其平率无致,如《于承明作与弟士龙》 “述情非不切,而未能低徊”[3]310。此诗言情慷慨悲切,陈祚明却用诗贵婉曲含蓄的原则来评点,令人一头雾水。总之,陆诗在陈氏的诗学理念之下一直左支右绌,未能尽善。
由于具有相似的人生际遇和复杂心态,陈祚明对理解陆机、陶潜、庾信等人诗中真意充满自信,其眼下的陆诗、陶诗和庾诗不免着选诗评诗者之主观色彩。身处易代之际的陈祚明不仕满清,生活凄苦,他的《醉后作》道尽了个中无奈与悲哀: “故里孤山下,凄清水石佳。如何辞隐逸,作客傍优俳。饮食羁长铗,乾坤一布鞋。谁人知恸哭,歧路向天街。”[16]只是 “以陈律陆” ,用自己的出处方式要求陆机,期待怨怼愤怒之情,这就有失偏颇了。
陈祚明藉评选为自己情辞并举、以情为本的诗论张目,折衷明代七子和竟陵两派,构建六朝诗史。其推崇庾信,抬高宫体诗人,过分贬抑陆机,却不免有失公允。围绕情、辞、法三者,陈祚明指出陆诗辞旨平浅、性情不出等弊病,将贬陆推向高潮,影响到有清一代其他诗论家的看法,如沈德潜《古诗源》称: “士衡以名将之后,破国亡家,称情而言,必多哀怨,乃词旨敷浅,但工涂泽,复何贵乎?”[17]明显可见出承袭《采菽堂古诗选》总评的痕迹。陈祚明曾将陆机情浅之因归结为 “余生之遭难,畏出口以招尤” ,不过他并未将这种因果关系抽绎出来。而在与陈祚明同时的吴淇看来,这种国破家亡之因,造就的不是陆机的衷情本浅,而是骚思更深: “屈子之忧谗畏讥在破家亡国之前,而士衡之忧谗畏讥在家破国亡之后,其骚思更深。”[14]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