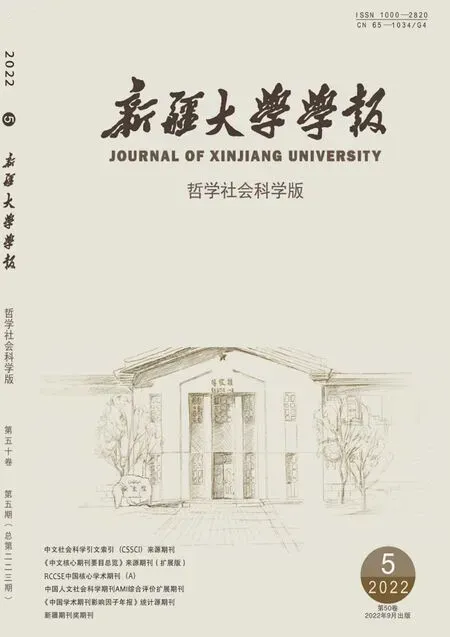易代之际的记忆建构及文学生成:以庾信《拟咏怀诗》为中心*
郭晨光
(北京师范大学 汉语文化学院,北京 100875)
太清二年(547)八月,侯景被武帝接纳仅一年后便发动叛乱,次年三月攻陷台城。陈寅恪曾言: “侯景之乱,不仅于南朝政治为巨变,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分之大事。”[1]太清六年(552)三月,侯景之乱平。十一月,萧绎即位江陵,改元承圣。梁朝政局早已分崩离析、内忧外患。诸王各自为政,萧纪割据于蜀而称帝,萧詧盘踞襄阳,称藩于西魏,萧勃固守岭南。北齐(东魏)和西魏趁乱占据了大量南方土地,早有侵逼江陵之意。巨大的国族灾难彻底改变了梁朝士人的命运, “衣冠士族,四出奔散”[2]。据正史记载,萧氏家族中战死、被侯景所杀、兄弟自相残杀、病饿死的就有三十六人。徐摛、庾肩吾、谢举、伏挺、王筠、羊侃等殒命于侯景之乱、江陵之变。阴铿、张正见、江总、张讥、周弘正、沈炯、徐陵、萧子云、陆琼等流寓他乡或滞留北方,有些后入仕陈朝。萧悫、袁奭、朱才、颜之推、颜之仪等相继进入北齐,庾信、王褒、王克、殷不害、宗懔等数十人被俘至长安。
面对异族入侵,对历史的追忆和反思最早是由南入北的文人分别在长安、邺下进行的。其中以庾信为代表,《哀江南赋》有 “赋史” 之称,从梁建国后五十年写起,叙侯景之乱和江陵之陷。《拟连珠》前二十首迄自梁武帝承平年间至陈霸先代梁,落笔比《哀江南赋》更远,都是按照井然有序的时间线索叙 “一国之所以兴衰,一人之所以变迁” 。《拟咏怀诗》呈现西魏攻陷江陵之事,所叙片段东鳞西爪、零散杂乱,缺乏井然有序的时间线索。其实,庾信《拟咏怀诗》在江陵、长安和小园三重时空中描绘整个动乱历史的全过程,交错着故国和他乡的复杂情感。作为这场灾难的经历者和见证人,通过反思和深省,其间涉及怎样表现离乱的书写策略?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对《拟咏怀诗》生成机制的理解。
一、江陵、长安和小园:《拟咏怀诗》书写的三重时空
入北文士的作品中,庾信笔下所追忆的历史图景最为丰富。不仅与其生平遭际密切相关,而且自出生之日起,就与萧梁王室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其父庾肩吾曾为梁散骑常侍、中书令。庾信《哀江南赋》自云: “王子洛滨之岁,兰成射策之年”[3]108,即十五岁时射策高第。萧纲入主东宫后,将父子等人立为东宫学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①庾信及家族的生平经历,参见鲁同群《庾信年谱汇考》,载范子晔编《中古作家年谱汇考辑要》(卷三),中国图书出版集团2014年版。。入北的若干年后,庾信以流亡者身份书写幸存者回忆录,常常回望这段往事,在不同的时空中,拼接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江陵之陷,是《拟咏怀诗》描写的第一重时空。承圣三年(554)十一月,西魏大军南伐,江陵城陷。江陵作为南北交战的主战场,也是庾信写作设置的坐标轴。五言诗篇幅短小,不适合大面积铺叙,无法同时容纳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庾信在谋篇布局上,使用联章体组诗围绕江陵城陷的主题,把战争中各种不相关的事件分别嵌在各短篇之中,如《拟咏怀诗》其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七、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七,类似于大时空下并置的一个个小空间。通过选择、剪辑而成跳跃式的片段,注重事与事之间的空间铺排。所叙事件 “隔年涉月” “事为之碎” ,组诗中的片段需彼此相参,才能最大程度了解整个历史进程。为了强化组诗内部的逻辑性,庾信使用 “互见法” 使之前后照应,《其八》 “长坂初垂翼,鸿沟遂倒戈”[3]234,《十二》 “梯冲已鹤列,冀马忽云屯”[3]237,均写萧绎、萧詧兄弟阋墙,导致西魏来伐。《其六》 “悲伤刘孺子,凄怆史皇孙”[3]232,影射简文帝、元帝被屠戮,与《二十三》 “徒劳铜雀妓,遥望西陵松”[3]246,《二十七》 “出门车轴折,吾王不复回”[3]249,皆伤元帝之死。通过各个事件相参而形成不同的主题,《其三》 “俎豆非所习,帷幄复无谋”[3]230,国家的动乱导致朱雀航事件,庾信望敌先奔;《十五》 “始知千载内,无复有申包”[3]240,把自己比作申包胥逃往江陵乞援,为自身开脱。既是对诗人遭际的深刻记叙,同时又将这种记叙置于国家动乱的历史中勾连、展开。
庾信并未亲身经历江陵陷落,承圣三年(554)夏四月丙寅,元帝派其出使西魏。当他到达长安尚未完成任务时,恰逢西魏十二月辛亥攻陷江陵,至此羁留北方。《拟咏怀诗》冷静陈述的战争过程及结果,可能源于梁朝故臣的讲述,即《哀江南赋》 “楚老相逢,泣将何及”[3]140,入北的梁朝故臣重晤叙旧,哀伤故国。又或许是庾信追忆侯景之乱引发的文学想象,是一种想象的真实。主要表现在:(一)交代江陵城陷前因后果、详述战争本末。《其八》 “白马向清波,乘冰始渡河。置兵须近水,移营喜灶多。长坂初垂翼,鸿沟遂倒戈。的颅于此去,虞兮奈若何”[3]234,元帝承制江陵,王僧辩讨平侯景,中兴有望,然萧詧勾结西魏,倒戈相向,乃至元帝被魏人所弑。《十二》 “周王逢郑忿,楚后值秦冤” “武安檐瓦振,昆阳猛兽奔。流星夕照镜,烽火夜烧原”[3]237,萧绎与萧詧结仇导致西魏来伐,魏师攻城之急、军容之盛。(二)注重战争场面的现场性描写,把江陵作为一系列正在发生时间的动态地理空间。《二十三》 “斗麟能食日,战水定惊龙”[3]246、《二十七》 “罗梁犹下礌,杨排久飞灰”[3]249, “下” “飞” “食” “定” 这些动词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风起云涌战争场面的交织、切换,如同连续不断动态画面的延伸,将情节推向高潮。特别注重 “持续性的画面” 的呈现,《十七》 “阵云平不动,秋蓬卷欲飞”[3]242,兵阵像凝固在水平线上的乌云,空气的静止导致了秋蓬的停滞与欲飞。 “闻道楼船战,今年不解围”[3]242,战争早已结束, “今年” 暗示当下依旧胜负难分。 “过去进行时” 的画面混淆打破了时空界限,使时代氛围自然过渡至当下。
这一时空中的江陵图景,还有满城风雨的飘摇。太清三年(549)三月,侯景攻破台城,城中士人相继逃往江陵。阴铿从建康逃往江陵,《南史》本传称 “及侯景之乱,(阴)铿尝为贼擒,或救之获免”[4]1556。舟行途中作《晚泊五洲》, “戍楼因嵁险,村路入江穷”[5],一个 “险” 字,不仅是矶崖之险,更是生命之险,景语中表现了这种 “担惊受怕” 和 “惊魂甫定” 。大宝元年(550),庾肩吾逃至建昌界藏匿,作《乱后经夏禹庙》《乱后行经吴邮亭诗》[6],后者云: “泣血悲东走,横戈念北奔。”[7]1990庾信于551年往江陵途中遇侯景之兵,《哀江南赋》云 “届于七泽,滨于十死”[3]140,在江夏(今武昌)藏身数月。有关被迫北上、入仕的经历,《其五》 “吴起尝辞魏,韩非遂入秦”[3]232,《其七》 “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3]233,《其十》 “李陵从此去,荆卿不复还”[3]236,《二十六》 “秋风苏武别,寒水送荆轲”[3]248,指代去国离家的共同遭际。被西魏羁押的士人除王褒、王克、刘瑴、宗懔、沈炯、颜之推,还有一国的君主——梁元帝。江陵城破后,元帝被萧詧所执,十二月辛未,被魏人所弑,临终前作《幽逼诗》四首,《其一》 “南风且绝唱,西陵最可悲”[7]2061。《拟咏怀诗》中记载了这段史实,《二十三》 “鼓鞞喧七萃,风尘乱九重”[3]246,天子出降,为萧詧所诘辱。 “徒劳铜雀妓,遥望西陵松”[3]246,庾信没有目睹元帝遇害,使用了 “互文性” 的典故遥寄哀思。
江陵发生的种种变化,是庾信不愿回望的过往,《伤心赋序》自云在丧乱中失去了二子一女,记忆深处的伤痕和梦魇不曾远离。用典故直陈时事,保持一定隔绝、距离,避免对其有巨大心理伤害的情景重现。
长安是《咏怀诗》书写的第二重时空,庾信随使臣北上,至此羁留北方。诗人并不试图回到历史现场的另一重表现即反复强调立足长安,《二十二》 “不言登陇首,惟得望长安”[3]235。还有使用地名、典故代替长安、北国,《其二》 “渭川” 、《其五》之 “华阴” “关外” 、《其六》之 “灞陵园” 、《二十二》之 “平乐” 、《二十四》之 “东陵侯(瓜)” 等。北国的自然环境与南方相比有天壤之别,加上心境颓唐,庾信笔下的 “长安” 不再是贵游子弟唱和的浪漫 “时空坐标” ,而是荒寒、惨淡、真实的存在。《其十》 “遥看塞北云,悬想关山雪”[3]236,《十七》 “日晚荒城上,苍茫余落晖”[3]242,《二十六》 “萧条亭障远,凄惨风尘多”[3]248,描写的时节大多为秋冬,长天寥落、塞北雪深、亭障相属,风尘蔽日,一派萧条景象。《昭君辞应诏》 “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胡风入骨冷,夜月照心明”[3]388,清陈祚明评为: “写的荒寒,固非咏古”[8],其实就是庾信在北上途中的真实体会。王褒在被押解近长安时作《赠周处士》, “崤曲三危阻,关重九折难” “云生陇坻黑,桑疏蓟北寒”[7]2336,不仅是写崤山、函谷关曲折险绝,更是作者去国离乡不安情绪的写照。入长安后为昔日被俘同僚刘瑴送葬撰《送刘中书葬》, “塞近边云黑,尘昏野日黄”[7]2339,入北南人眼中的长安,永远是低沉、阴霾,充满着压抑的 “谶景”①宇文所安指出所谓 “谶景” 指: “正如异兆对于主政者接触社会的情势一样,世界的谶景是被诗人感受到当下的真实景象。这些谶景不是预兆,它们是当下这个结构的潜在标示。” 参见宇文所安《世界之谶:中国抒情诗中的意义》(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Omen of the World),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85年,第44页。。
小园作为《拟咏怀诗》的第三重时空,其实是嵌套在第二重时空之中。长安是庾信的居住地,它并不是避风港,而是痛苦、堕落的开始。就现存诗赋看,他在长安周边,营建与城市府第相对的别业。《十六》 “野老披荷叶,家童扫栗跗。竹林千户封,甘橘万头奴”[3]241,《十八》 “琴声遍屋里,书卷满床头” “露泣连珠下,萤飘碎火流”[3]242,《二十五》 “由来千种意,并是桃花源。榖皮两书帙,壸卢一酒樽”[3]247。庾信继承了传统的隐逸观念,将小园塑造成 “避秦” 的桃花源。小园(家)是一个地理空间存在,也是安身立命之所。家与国密不可分,抒情人对家的情感自然延伸至国。理想中的家国只存于全盛的南梁,而非陈霸先建立的陈朝。失去以家为基点的地理空间,意味着身份的丧失②宇文逌《〈庾信集〉序》称庾信在北被达官贵族呼为 “南人羁士” ,就是对其身份的歧视。参见庾信撰《庾子山集注》,倪璠注,许逸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5页。。庾信有意将隔绝、封闭的隐居环境建构一个安顿身心、消解耻辱的 “心理空间” ,着力将自己打造成一个 “隐士” ,刻画小园内的琴棋书画、园林山水以及清冷的隐居色调, “有意在景物描写上造成隐居环境的封闭之感”[9]。然而理想中的 “桃花源” 仍然不能抵挡外界的摧残,《二十》 “其面虽可热,其心常自寒”[3]243,《二十四》 “无闷无不闷,有待何可待。昏昏如坐雾,漫漫疑行海”[3]246。《十六》 “君见愚公谷,真言此谷愚”[3]241,清闻人倓言 “伤其屈体魏周,愿为归隐而不得,徒于山斋筑室,真为愚也”[10],小园为其提供了缓解 “从宦不宦,归田不归”[3]55尴尬处境的隐居方式。
诗人通过 “双线并列” 的结构将历史(江陵)和当下(长安、小园)进行编排配置,使两者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共同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状结构。庾信记录发生在江陵的大事时,有意增加了一条辅线,汇聚小园生活的点滴、所思。真实的生活琐屑、无序堆积,是诗人遇有见闻、随手记录的产物。这些描绘日常琐事的诗句,拥有了记录生活痕迹的叙事意义。两条线索时而平行,时而相交,时而形成对峙。比如在江陵事变中对家国的回忆和眷恋,也出现在长安或小园之中,把宏大的历史叙事拉向一个平凡、现实的空间里,也隐藏着诗歌风格从严肃、悲愤到现实、平和的转换。庾信发明的 “双线并列” 的结构,有了更加深刻的意义——既可以全方位展示社会的风貌图景,同时又把身不由己陷入其中的个人苦难、生存状态作为表现的中心。
二、悲痛、眷恋与无奈:《拟咏怀诗》书写的情感脉络
江陵、长安和小园,三重时空对应着三种身份和心境。不同的时空图景的衔接和照应,拼接出一幅离乱之中的芸芸众生相。易代之际遗民的情感状态,其实就是一种 “时空知觉”[11]。三种情感在时空中错综交织,令庾信笔下的《拟咏怀诗》拥有了丰富复杂的情感脉络。
(一)亡国悲痛,是庾信书写《拟咏怀诗》的第一条情感脉络。建康和江陵作为庾信的故乡,当这些熟悉的故国风景因战乱而发生巨大改变,这种悲痛之情最为强烈,《其九》 “怀秋独悲此,平生何谓平”[3]235,《二十三》 “鼎湖去无返,苍梧悲不从”[3]246。元帝之死将这种情绪推向高潮,《二十七》 “出门车轴折,吾王不复回”[3]249,十二月辛未,元帝为魏人所弑。萧詧使以布帕缠尸,束以百茅,葬于津阳门外,一国之君竟遭此厄。作为组诗的最后一句,诗人殇元帝之死,似乎还有更多的感情可以表达,却戛然而止,定格在诗人的惊悸与悲恸的镜头下。
对于南朝人来说,梁朝国祚灭亡,失去的不仅是王室朝代。萧梁(502—557)是南朝享国最久的朝代,武帝早年励精图治,崇儒重教,江南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整个南朝时期的顶峰。北齐高欢曾说: “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12]347《哀江南赋》也称 “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遂成邹鲁”[3]140,把江南比作孔孟的故乡邹、鲁。文教昌盛之地在数十年不识干戈的情况下迅速分崩瓦解,无论是罪魁祸首侯景还是拓跋氏政权,都代表着野蛮与落后,正是他们摧毁了代表正朔的华夏文明。颜之推《观我生赋》斥侯景为 “傅翼之飞兽” “贪心之野狼” “绝域之犬羊” ,《梁书》《陈书》等史书称其为 “獯丑” 。庾肩吾《乱后行经吴御亭》中 “獯戎鲠伊洛,杂种乱轩辕。辇道同关塞,王城似太原”[7]1990,侯景就像古代的 “獯戎” (匈奴),闯进建康王城(洛阳边的伊、洛二水),建康而今成为《诗·小雅·六月》中的 “太原” 。昔日的衣冠之邦成为野蛮之地,令人不忍回望。
(二)故国眷恋,是庾信书写《拟咏怀诗》的又一条情感脉络。入北羁客用诗笔书写故国胜朝,惯用 “伯夷舒齐” “钟仪” “申包胥” “苏武” “刘琨” 等身陷异国而保持名节的历史人物。此外,还特别喜欢使用有关 “南” 的方位、典故,通过地理空间与故国发生链接,让语言修辞表达内心对故国至深的眷恋。《二十二》 “南国美人去,东家枣树完”[3]245、《重别周尚书》 “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3]370。其中 “南冠” “南风” “南云” 的使用频率较高,如庾信《率而成咏》 “南冠今别楚,荆玉遂游秦”[3]339,用 “钟仪南冠” 之典昭证自我气节。为故国忠烈吴明彻撰《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铭》,也说 “天道在北,南风不竞”[3]969。诗歌中较早写作 “思南” 之音是《行行重行行》, “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7]329。文人大量使用有关意象的当属同样国破家亡、被迫北上的陆机。据《升庵诗话》 “南云” 条载: “诗人多用‘南云’字,不知所出,或以江总‘心逐南云去,身随北雁来’为始,非也。陆机《思亲赋》云:‘指南云以寄钦,望归风而效诚。’陆机《九愍》云:‘眷南云以兴悲,蒙东雨而涕零。’盖又先于江总矣。”[13]江总于乱离之际流寓岭南数年,陈灭后北上,遭际的变化致其诗文常有 “南归” 之愿。
(三)无奈入仕,是庾信书写《拟咏怀诗》的第三条情感脉络。当南归的愿望已无法实现,出仕还是隐居?成为摆在入北士人面前的共同问题。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的士人,为了强化自我气节和身份,不断在诗文中使用 “伯夷舒齐” “钟仪” “苏武” “申包胥” “刘琨” 等典故符号。然而面对严酷的政治环境,又不得不成为 “李陵” “王粲” “阮籍” “陆机” 等失节之士。个体身份的丧失是庾信和其他南人共同的处境,时常陷入自怨自恋、孤苦无依的精神状态,庾信《伤王司徒褒》 “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3]308,颜之推《古意诗》其二 “昔为时所重,今为时所轻”[7]2283,为此不惜给两个儿子起名 “思鲁” “敏楚” ,以示 “不忘本也”[12]626。如何通过写作寻回自我身份?通过开创新典——枯树(木),将其作为共同的 “名字” 。《二十一》 “独怜生意尽,空惊槐树哀”[3]244、《北园射堂新藤》 “空心不死树,无叶未枯藤”[3]277、《别庾七入蜀》 “山长半股折,树老半心枯”[3]324,内心痛苦、虽生如死的枯树即是庾信无奈入仕新朝的精神写照。由梁入周的刘臻《河边枯树诗》 “奇树临芳渚,半死若龙门”[7]2656,由齐入周的孙万寿作有《庭前枯树诗》,表达移根北方后半死不活的状态和漂泊之感。唐人将其升级为一种特殊象征物,如卢照邻《行路难》 “君不见长安城北渭桥边,枯木横槎卧古田”[14]、杜甫也曾作《枯柟》《枯嵕》, “睹木兴叹” 遂成为相沿以生、代代相传的文人写作传统①吴开《优古堂诗话》 “睹木兴叹” 条,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4页。。
三、见证、追忆与反思:《拟咏怀诗》的 “心史” 性质
易代士人身处鼎革之变,出于自我昭正气节或防止后人遗忘等考虑,士人 “存史” 意识比较自觉。据《隋书·经籍志》载,反思侯景之乱和梁亡历史的史著有何之元《梁典》、萧韶《梁太清纪》、萧世怡《淮海乱离志》、刘仲威《梁承圣中兴略》、谢吴《梁皇帝实录》等。这些亡逸的著作是其遗民情节的体现。反映在诗学上,诗人 “以诗存史” 的创作观念比较突出,《拟咏怀诗》的独特之处不仅通过个人创作记录家国事变,更在于时代历史触发了诗人心灵的悸动,展现诗人心路历程的转轨,凸显了咏怀诗的 “心史” 性质。
见证,是《拟咏怀诗》书写的第一重维度。生逢易代之际,庾信亲眼目睹并体尝了巨大的民族灾难给个人、家族带来的创伤,诗文中多次出现 “信” “我” “尔” “余” “自” “兰成” 等第一人称,以近乎实录的态度和直笔手法记述了改朝换代等重大时事。作为一名见证者,立足当下眺望逝去的历史,以更高的视角、悲悯的情怀,找寻在 “历史现场” 看不到的东西。
(一)战争给梁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带来的灭顶之灾。《十一》 “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3]236,用二妃哭舜、杞梁妻哭倒杞城喻君臣被戮、百姓被俘北上。 “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3]236,据《晋书·天文志》,长虹照耀营垒,是流血之象。《十二》 “古狱饶冤气,空亭多枉魂”[3]237,血流遍地、冤魂众多。西魏于十二月攻陷江陵后,进行了屠杀、掳掠, “阖城长幼,被虏入关”[15]860,据今人考证,这个数字当在十余万之间①杜志强《颜之推〈观我生赋〉的史料价值阐释》,《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4期,第12页。。发生在江陵的诸多大事,庾信并未亲身经历,叙写离乱的文学经验,可能源于刚结束的侯景之乱。《其七》 “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3]233,《昭君辞应诏》 “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3]388,记录梁朝女子被侯景所辱之时事。《颜氏家训·养生篇》载 “侯景之乱,王公将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无全者” ,刘盼遂以颜证颜说: “之推《观我生赋》‘独自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弦’,自注:‘公主子女,见辱见雠’皆为此事。”[16]439据《资治通鉴》《通典》《太平御览》等正史、类书记载,侯景纳简文帝溧阳公主、羊侃女为妃,占据东宫后,将妓女数百人分给军士,被侯景及部下所虏、侮辱者不计其数。
(二)作为君主,梁元帝在战争中政策、用人等方面的失误。庾信在《哀江南赋》《拟连珠》中比较武帝、简文帝、元帝三位帝王的功过得失。《拟咏怀诗》不再顾念元帝平侯景之功,直陈其在江陵败亡中应负之责。《十三》 “绿林多散卒,清波有败军”[3]239,元帝用人失策,用任约、谢答仁等侯景旧党平乱。《其八》 “长坂初垂翼,鸿沟遂倒戈”[3]234,《十二》 “周王逢郑忿,楚后值秦冤”[3]237,元帝与萧詧结仇,詧倒戈导致西魏来伐。《十五》 “六国始咆哮,纵横未定交。欲竞连城玉,翻征缩酒茅”[3]240,暗指萧绎、萧詧、萧纪等宗室争斗不休,与西魏时而开战、时而通好。庾信作为文士的历史感与史官的理性认识常常一致,史官言: “不急莽、卓之诛,先行昆弟之戮。”[17]《通鉴札记》卷十 “元帝骨肉相残” 云: “江陵亡国之祸,而其戎首罪魁,则梁元帝是已”[18],将国祚灭亡的原因归于萧绎。
诗人不惑于当下具体的人、事,而是立足今日眺望历史的远景,对记忆的回溯比附历史,即倪璠《注释庾集题辞》所谓 “其指南梁,则以楚事为辞;言西魏,多以秦人为喻”[3]4,以战国时期的秦楚战争及秦末的楚汉之争,比附西魏(秦)伐江陵(楚)。《其二》 “既无六国印,翻思二顷田”[3]230,《十二》 “周王逢郑忿,楚后值秦冤”[3]237,引秦事以比魏、周。《二十六》 “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3]248,《二十七》 “鸡鸣楚地尽,鹤唳秦军来”[3]249,用四面楚歌暗示梁朝兵败的必然结局。以古证今、以人喻己是为了证明当下, “历史是一种讽喻,各种人物在机械的重复或重新上演着当下的情感或事件”[19],从古今同构的历史事件找寻背后的普遍意义。
追忆,是《拟咏怀诗》书写的第二重维度。这一书写方式依然以长安、小园的具体地点为依托。追忆,是对往事的回溯、唤醒。《哀江南赋序》称: “追为此赋,聊以记言”[3]95,即通过追忆,对以往的人事再度体认。在《拟咏怀诗》中,当事人常常会将记忆中的过去携带到当下的情节中,过去参与对当下的感知。庾信心心念念的往事,主要是前半生在南梁的辉煌家族史和南方的贵族文化,《其六》 “畴昔国士遇,生平知己恩”[3]232,父子出入禁闼,深得武帝、简文帝的宠信。通过对比,凸显往昔与今日的落差,《其五》 “惟忠且惟孝,为子复为臣。一朝人事尽,身名不足亲”[3]232,庾氏家族深受圣恩,入北之后却只剩下人事既尽、身存名灭。将 “昔” “今” “如” “似” 等词汇勾连, “眼前事” 与 “往事” 相叠加,形成今昔渗透的效果。《其九》 “昔尝游令尹,今时事客卿”[3]235,《伤王司徒褒》 “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3]306,感慨境遇变化导致的人生错位,以及强烈的失落感。诗人感慨之余,希望通过追忆,唤起人们对南梁昔日的荣耀记忆。抑或通过今昔景致的重合,表现人生的困顿感,《十八》 “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3]242,往昔与今日,通过具体的节令联系在一起,表现双倍的苦痛。庾信有意打乱情节的连续性,将这些今昔对比的语句从旁插入,创新了这种重叠性的时间结构,使记忆更加清晰、深刻,反映出诗人对家国巨变、人生沧桑的深刻体认。
《拟咏怀诗》书写的第三重维度,是反思。诗人在唤起以往记忆的同时,也唤醒了自我批判意识。在具体写法上,通过模拟阮籍表达对国家覆亡,个人应负之责的深刻思考。
庾信之所以选择阮籍,主要在于情感的共鸣①这是庾信后期作品在选择模拟对象上的共同点,除了阮籍,还有拟陆机《演连珠》作《拟连珠》、拟向秀《思旧赋》作《思旧铭》。。《其一》开篇 “步兵未饮酒,中散未弹琴。索索无真气,昏昏有俗心”[3]229,与蔑弃世俗的名士形象大相径庭,庾信将其建构为一个清醒的、为魏晋易代担忧的士大夫,并且绝口不提他用以遁世的酒。有诗论者认为: “庾信论其未饮酒反无真气”[20], “无真气” 实则说明庾信笔下的阮籍之 “世俗气” ,《十六》 “对君俗人眼” 反用阮籍 “青白眼” 之典。《十八》 “寻思万户侯,中夜使人愁”[3]242,亦反用阮籍《咏怀诗》其一 “夜中不能寐,忧思独伤心”[21],将阮籍夜不能寐归因于其用世之心。易位之后的阮籍形象在《拟咏怀诗》中偏离了原文本中的意义,呈现出 “反用” 倾向。庾信使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模拟方法——反仿。 “模仿有正有负,亦步亦趋是模仿,反其道以行也是一种模仿”②参见列许登堡《隽语·散文·书信》,转引自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载《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2页。,从被模仿对象的反面而进行的仿作的特殊转换手法,是一种 “否定性” 的模仿③较早使用反仿可追溯到扬雄拟《离骚》而作《反离骚》。诗歌中反仿手法更为常见,范云《赠沈左卫》 “越鸟憎北树,胡马畏南风” 是《古诗十九首》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的反仿,钱锺书评为 “此诗家‘反仿’古例之尤佳者” 。参见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700页。。通过对阮籍形象的反仿,以看似冷静的笔触注入个人的深醒。
整个国家谈玄成风,不习武事。士大夫 “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16]384。据《南史·陶弘景传》载,弘景逆知梁祚覆灭,预制诗云: “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误朝阳殿,遂作单于宫。”[4]1897侯景之乱很大程度上由于士人竞谈玄理,缺乏事务能力。在朱雀航事件中,庾信望敌先奔,这段人生污点仅在《其三》轻描淡写来了句 “俎豆非所习,帷幄复无谋”[3]230,责任在于简文帝用人失当,为自身辩护。玄风影响下皆崇虚诞的风气与西晋年间何其相似?国家败亡后士人的反思都是从否定 “阮籍” 开始,刘琨《答卢谌诗》 “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7]851,干宝《晋纪总论》 “故观阮籍之行,而绝礼教崩驰之所由”[22]。每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既是社会动乱的受害者,又是国家败亡的推动者。作为梁朝全盛时期成长的贵族子弟,庾信早年与阮籍一样任诞不羁。在世运升降的关头,认识到学问空疏、世风堕落之于国家覆亡的罪责,通过 “反阮籍” 忏悔,否定自己的前半生:阮籍崇虚诞、不涉事务,庾信对待工作尽职尽责、恪尽职守。作司水下大夫,有督治渭桥之功,为弘农太守兢兢业业,任麟趾学士努力校书,当洛州刺史 “为政简静,吏人安之”[15]734,反仿在原本与摹本之间制造出的强烈对立,使诗歌具备了类似史著 “春秋笔法” 那样评判褒贬的功能。
庾信模拟阮籍的另一种方式是借他人之故事自叙生平。《其一》 “步兵未饮酒,中散未弹琴”[3]229,近于咏史诗中的人物小传,透露了旁观者的叙事视角。诗人化身为阮籍,代他人发声,而非仅以诗人自我为中心,抒一己之情。《其四》 “惟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3]231,用第一人称 “余” 介入阮籍 “穷途而哭” 之事,借阮籍口吻表达两人相同的处境和无奈——走投无路、极度苦闷又不得不与当权者合作。入北羁客时常诗文多次使用此典,《与周弘让书》 “阮籍穷途,杨朱歧路。征蓬长逝,流水不归”[23],面对昔日的故友,怀思的故国早已不存,归乡的愿望成了真正的 “穷途” 。《十六》 “对君俗人眼”[3]241,作为他乡之羁客,处处谨小慎微,哪里还敢展露 “青白眼” ?《十八》 “寻思万户侯,中夜使人愁”[3]242,阮籍的用世之心是庾信不能忘俗体现,也是其试图融入北方政局的心态变化。 “诗人进入角色叙述,有助于突出作品的摹仿性”[24]。移情成为他人,有着浓郁的自传色彩,这种拟作方法显然更加高明。通过叙事的灵活转换,让他人的经历凸显自身的不同侧面,其笔下的自我形象也日渐成熟:从任诞的贵族子弟发展为顺应时势、有责任担当的士大夫,以及调和从宦和归隐两种极端的人生态度。
四、情、景、事:《拟咏怀诗》的文学生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拟咏怀诗》的生成方式。三重不同的时空景象、多种复杂感情穿梭其间、当事人深邃的理性反思,三者紧密结合,通过多维度的书写来完成,方能生成独具魅力的诗作。庾信作为 “一予而三化” 的诗人,以其阅尽人世兴旺的眼光、饱蘸历史风云的笔墨,于诗歌中呈现出一幅幅各具特色且前后照应的记忆图景。《拟咏怀诗》通过不同时空下跳跃的历史事件、生活图景,重重叠叠地并列在读者面前,从而形成事与景并置、交融的境界。同时作为 “以诗纪史” 的抒情诗,庾信将叙事与抒情并列、合作,或让抒情建立在叙事的基础之上,与叙事深度融合,使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协调的文学样态。
庾信在《拟咏怀诗》中惯用转折顿挫的结构方式,每首诗中所叙之事往往点到辄止,并不打算就此铺开,进而转向抒情(含议论或咏怀),让诗中的叙事与抒情呈并列关系,具体表现在:(一)有些诗作中集中展现动乱的全过程,详述事件本末和发展,基本采用顺序的叙述模式,保持相对清晰的叙事线索,仅在结尾处一、两句抒怀、议论,呈现 “先叙后抒” 的倾向。《十一》 “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3]236,《十二》 “天道或可问,微兮不忍言”[3]237,《十九》 “天下有情人,居然性灵夭”[3]243等议论、感概,类似于史书中的赞论。从文学表达上又是倾诉式的, “诗人充当了历史家的角色,或者从另一角度说,是怀着诗人的多情善感在诉说的历史家”[25]。有时这种议论、感慨也出现在诗作前面、中间等其他位置,呈现 “在叙中抒” 的倾向,《十九》 “愦愦天公晓,精神殊乏少”[3]243,《二十四》 “千年水未清,一代人先改”[3]246。破碎、跳跃的论断与叙事主线结合的并不紧密,就像空间画面的并置。诗人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事件之中,直接插入强烈的情感评价和道德判断,这种史家之褒贬、诗人之美刺,正是庾信士大夫 “权力意识” 的支撑,也是诗人内心不平之气的抗争。
(二)一些诗作并不以历时性的叙事为主,所叙之事若隐若现或间或一、两句,事件的历时性进程很不充分。《十一》 “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3]236,《二十三》 “鼓鞞喧七萃,风尘乱九重” “徒劳铜雀妓,遥望西陵松”[3]246,其中的事更像一个场景的横断面,并不追求完整。以《二十一》为例,全诗如下:
倏忽市朝变,苍茫人事非。避谗应采葛,忘情遂食薇。怀愁正摇落,中心怆有违。独怜生意尽,空惊槐树衰。[3]244
第一句 “倏忽市朝变,苍茫人事非” ,开门见山点出到江陵之变导致的改朝换代,为一时之事。其叙事还未完全展开便快速过渡到 “避谗应采葛,忘情遂食薇” ,诉说在北已食周粟的现实。违心仕周的无奈、痛苦,如同婆娑的槐树一样半死不活、永远哀伤。所叙之事再度被 “抒情、议论” 等因素阻断,为情绪所裹挟。短短四十字的诗作构筑出时、事、情,通过 “一时一事” 使 “情” 有不竭不尽之感,展现出超越时间、空间的无限开阔境界。这类诗作中, “事” 的成分占比不多,关注点在于通过 “事” 来传 “情” ,情、景、事等诗歌组成部分才可 “合成一片,无不绮丽绝世”[26],达到完美的诗境。
庾信《拟咏怀诗》在国破家亡的历史条件下,在北国以一己之力树立并发展了 “诗史” 写作传统:将过去的事件、行为,通过追忆展现为富于传记意义的历史图景,并与当下自我的反思和深醒并置、协调,让历史记忆与文学创作深度结合。这是庾信的独特贡献,也为后代遗民诗人历史记忆的书写提供了宝贵经验,如汪元量在南宋灭亡后对古都临安的追忆和摹写,明清易代的王夫之沿着阮籍、庾信的道路撰写《咏怀诗》等。对于易代世变的士人来说,他们所经历的不仅是单纯的王朝更迭,而是文化的断裂。以诗存史之 “史” 与以诗补史之阙之 “史” 显然并非指作为专门学问之 “史” ,而应是一种记忆的责任。易代之际,诗歌承担的记录官修史书由于话语权力的丧失而无法记录的史实的责任,实践了 “史” 的真正意义,成为一个民族历经劫难而得以存活下来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