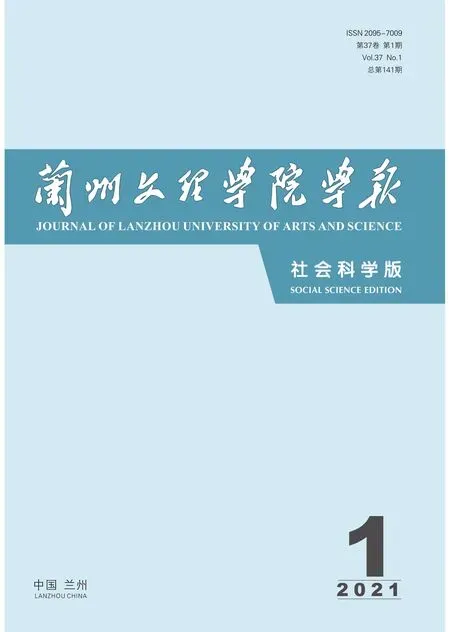裕固族民歌在非遗保护中的价值
——为何裕固族民歌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杜 亚 雄
(中国音乐学院,北京 100621)
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在中央政府门户网上发出通知,批准并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等十个不同的类别,共518项。在这份名录中,民间音乐共有72项,其中有关少数民族民歌的有蒙古族长调、蒙古族呼麦、裕固族民歌、傈僳族民歌、藏族拉伊、壮族民歌、侗族琵琶歌、侗族大歌、彝族海菜腔等十个项目。裕固族只有一万多人,为什么它的民歌能和蒙古、藏、壮等民族的民歌一块被录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本文希望回答的问题。
裕固族是甘肃特有的少数民族,居住在河西走廊中部和祁连山北麓,主要聚居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县黄泥堡裕固族自治乡。裕固族是由古代回鹘人一支的后裔融合其他民族后形成的。
“回鹘”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南北朝时在汉文史籍中称为“铁勒”“敕勒”“袁纥”,隋唐时称为“回纥”,宋代称“回鹘”,元明则称“撒里畏吾儿”。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回纥打败了突厥,在今蒙古高原建立汗国,史称“回纥汗国”。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回纥可汗要求将汉文的“回纥”改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1]。《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五》中说:“回纥,其先匈奴之裔也。 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新唐书·回纥传》中则说:“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裕固族的先民是匈奴一支的后裔。
唐开元五年(公元840年),回鹘汗国为黠嘎斯人所灭,回鹘人分三支迁徙。西迁到河西的一支,史称“河西回鹘”,西迁到今新疆吐鲁番和帕米尔高原的两支,分别称为“高昌回鹘”和“葱岭西回鹘”。“河西回鹘”是今天裕固族的先民,而“高昌回鹘”和“葱岭西回鹘”则是维吾尔族的先民[1]3。
从元代起,操突厥语的河西回鹘后裔“撒里畏吾儿”人由蒙古贵族统治,这些操突厥语的人与操蒙古语的王爷、头目、官员和军士长期相处,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并于明代初年从嘉峪关外迁至河西走廊中部和祁连山北麓,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后来成为裕固族。新中国成立前后,裕固族曾被称为“撒里维吾尔”,1953年改称“裕固族”[1]4。
裕固族有两种本民族语言,一种是西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另一种是东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西部裕固语是突厥语中最古老的语言,在突厥语族诸语言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世界著名突厥学家C.E.马洛夫说西部裕固语是古代回鹘文的“嫡语”,同时他又根据一些语音特点,把它归到比突厥文、回鹘文文献语言更古的“上古突厥语”[1]9。东部裕固语保留着较多古代蒙古语的成分,包括词汇和某些语音,特别是词首古音h保留的相当多,因而东部裕固语在蒙诸语言中,更接近13-14世纪的古代蒙古语,而与现代蒙古语有较显著的差异。
民歌是传统音乐中最重要的体裁形式。民歌一般都是口头创作,口耳相传,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经过集体加工而形成的。因为民歌不像创作歌曲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独立完成的作品,而是由某个民族或某个地区的人民世代传承的集体创作,也是无数人智慧的结晶,所以民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它特性,一个是它的变异性,另一个是它的保守性。
毛泽东说过:“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2]民歌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现象,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反映社会生活,当然也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改变。如陕北有一首古老的情歌《骑白马》,最早是一位热恋中的姑娘唱给意中人的,歌中唱到:“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我没有汉,咱二人好像一骨朵蒜,谁也离不开瓣(伴)。”在抗日战争期间,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和日本帝国主义做殊死的斗争,这首民歌的歌词变成了一位八路军战士对心爱姑娘的内心独白:“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去看姑娘,打日本我顾不上。”最后,这首民歌经过著名民歌手李有源填词,变成了唱遍神州大地的《东方红》,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热爱。这个例子非常生动地说明了民歌的变异性。
民歌在变异的同时,也具有保守性。从《骑白马》的几种不同版本到《东方红》,歌词有很大变化,但曲调却基本没有变,因此这个例子同时也说明了民歌的保守性。毛泽东曾论述过艺术的保守性,他1956年8月24日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3]从《骑白马》到《东方红》歌词改变而曲调基本不变的事实,说明音乐较之其它艺术形式更具有稳定性。笔者在1971年,在甘肃嘉峪关地区搜集到一首汉族民歌《茉莉花》,其歌词和曲调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出版的《缀白裘》书中所记录的《鲜花调》以及英国人巴罗在1804年出版的《中国旅行》中记录的《茉莉花》几乎一模一样,这说明民歌可以在数百年中,流传数千公里的过程中保持其原来的旋律。民间音乐在调式、音阶、旋法特点上的稳定性就更大。西安半坡村出土的距今6 700 年的陶埙就己具备了五声音阶的特性音程小三度,1978年在湖北隋县出土的2 400年前的曾候乙编钟和今天流传在当地的民歌有着基本相同的音阶构成便是明证。
歌曲是语言艺术(歌词)和声音艺术(曲调)结合的艺术形式。人们记录歌曲时,把曲调写一行,歌词另写成一行或数行,放在曲调的下方,歌曲是两种文学和音乐两种艺术结合的形式,而目前这种记录方式不能反映的歌曲的本质,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目前人类至今尚未能发明一种同时将歌词和曲调一起记录起来的方法。目前的这种记录方式给人们一个错觉,让大家感到作为语言艺术的歌词和作为音乐艺术的曲调是两码事。其实歌曲在唱出的时候,只有一个声道,而不会有两个声道。如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事实,我们就能明白,在歌曲特别是在以字行腔的民歌中,语言和音乐其实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民歌在千百年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和语言不能分割,民歌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与语言的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既然裕固族的两种民族语言分别保存了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的特征,按照民歌是语言艺术和音乐艺术结合的性质,分别用西部裕固语和东部裕固语演唱的裕固族民歌也应当分别保存上古民歌和中古民歌的特征。但这个看法在尚未用音乐学的研究证明之前,只能是一个假说,证明这个假说是民族音乐学界的任务。
民族音乐学在英文中称为“ethnomusicology”, 作为音乐学中的一个门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比较音乐学”逐步发展形成的,而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则是由英国音乐学家埃利斯在1885年所创建的。埃氏创建此学科最初的目的就是要借鉴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通过研究现存的音乐,从中抽理出历史上,特别是史前时期音乐发展的线索。
历史比较语言学是把有关各种语言放在一起加以共时比较或把同一种语言的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进行历时比较,从而实现所谓“时空转换”的学问,通过上述方法以找出不同的语言之间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对应关系和异同。利用这种研究方法,可以研究相关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找出它们在历史上的共同母语,还可找出语言发展、变化的轨迹。19世纪的语言学家们运用这种方法,研究了印欧语系诸语言,取得了很大成就。埃利斯借鉴这种方法,通过比较许多不同民族音乐所采用的音阶,对音乐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历史比较法亦成为各国音乐学家经常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
采用民族音乐学的历史比较方法研究裕固族民歌,证明上述有关裕固族民歌历史性的假说,必须从歌词和曲调两个方面进行。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对用西部裕固语演唱的民歌(以下简称“西部民歌”)的比较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而对用东部裕固语演唱的民歌(以下简称“东部民歌”)的研究尚处于开始阶段。下面我们先谈谈对西部民歌的研究,然后再讲对东部民歌的研究。
对西部民歌的研究,和其他民族的民歌一样必须分歌词和曲调两部分进行。由于记谱法的发明远远晚于文字的发明,历史文献中又有裕固族先民创作的两首民歌被记录下来,这为我们进行歌词方面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条件。这两首民歌是汉代的《匈奴歌》和南北朝时的《敕勒歌》。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次征讨匈奴,攻打焉支山和祁连山,皆获大胜,匈奴人失去了这两座山,乃作《匈奴歌》。词曰:“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这首歌以哀婉的语调,表达了匈奴人民对故土、对生活的眷恋和热爱,是匈奴民歌中硕果仅存的一首,堪称千古绝唱[4]。
公元646年,东魏进攻西魏,兵败撤退,军心涣散,高欢开宴会以安定军心,敕勒族大将斛律金在聚会时唱《敕勒歌》,群情为之一振。词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歌自然高古,气势宏大,亦为中国诗歌史上的民歌精品。
对这两首歌词进行研究,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不同与汉族诗歌的特点:一是两句为一节,和自《诗经》中的国风以来四句一节的汉族民歌完全不同;二是每行首字押韵(《匈奴歌》),这也和汉族诗歌尾字押韵不同。裕固族民歌中有不少押头韵,也以两句一节为主。这就说明裕固族民歌在歌词方面保存了古代先民民歌的特点。《匈奴歌》和《敕勒歌》都是用汉文保存下来的古代民歌,不是原文。原文的诗歌则更能说明问题。
高昌汗国时期(850-1284年)的诗歌,最大特点是押头韵,也有不少是两句为一节的。著名的维吾尔族学者马合木提·喀什葛尔于公元1 072年到1 077年,在深入民间,广泛采集民间传说、歌谣、故事和谚语的基础上,编写了一本《突厥语词典》。这部书中记录了不少当时讲突厥语各民族的民歌,它们分每节四行和每节二行两种,四行的比较多见,每句是7或8个音节,主要押尾韵①。尾韵除四行一韵,用AAAA、ABAB、AABA几种形式外,还用在古代突厥语民歌中最有特色的AAAB式。每节两行的民歌,每行多为9-12个音节。
西部民歌的格式和《突厥语词典》上记载的古代民歌几乎完全一样,也分每行两节和每行四节两种。每节四行的每句7-8个音节,用尾韵、中韵,也有用头韵的。尾韵格式为AAAA、ABAB、AABA和非常特殊的AAAB形式,著名的裕固族民歌《裕固族姑娘就是我》就采用AAAB式。每节两行的以每行11-12个音节最常见。西部民歌和古代民歌除了共同点之外,还有两点不同:第一,裕固族民歌中有时用头韵,而古代民歌中没有。第二,裕固族民歌多为两句一节,而古代民歌大多为四句一节。高昌汗国时期的回鹘诗歌押头韵,《匈奴歌》和《敕勒歌》为两句一行,可见裕固族民歌所保存的押头韵和两句一节这两个特点,是比《突厥语词典》上记载的古代民歌更为古老的格式。
历史比较语言学认为亲属语言是同一历史来源的语言,当一个社会在地域上分化成若干半独立的社会时,语言会随着分化成方言;当社会分化更进一步深化,使一个社会发展成几个不同的独立社会时,语言就会进一步深化分化成亲属语言。现在同属一语系的语言在遥远 的古代是同出一源的。
根据历史文献和语言学提供的材料,和裕固族血缘关系最近的民族是维吾尔族,其次是突厥语族诸民族,再次是阿尔泰语系其他语族诸民族。一般说来,血缘关系近的分离时间晚,血缘关系远的分离时间早。如维吾尔族和裕固族的先民都是回鹘,他们是在840年分离的,血缘关系近,裕固族和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诸民族血缘关系远,他们分离的时间恐怕要追溯到史前时期。
历史比较法可以采取由近及远的顺序,沿着历史的长河溯源而上。然而经过比较我们发现和裕固族血缘关系近的维吾尔族的民歌,在歌词结构方面和西部民歌相差比较远;而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民歌的民歌,如蒙古族和鄂温克族民歌,在歌词结构方面和西部民歌则比较接近。另外,在遥远的东欧有一个民族民歌歌词的结构和西部民歌十分相似,这就是匈牙利族。
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在《论匈牙利民间音乐》[5]一书《匈牙利民间音乐的原始阶段》一章中各地例举了54首匈牙利民歌,其中歌词为7或8个音节一行,每节有四行(7x4或8x4)的有24首,11x4的有6首,10x4的有5首,9x4的有2首,12x4的有1首。如果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四行为一节利民歌尾韵格式中也有AAAA、ABAB、AABA和AAAB式的。不难看出匈牙利民歌除不用头韵外,所有的特点几乎和裕固族西部民歌都是一样的。这是偶合吗?当然不是。为了使研究更深入,我们需要研究西部民歌的音乐特点。
民歌在音乐方面最重要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调式和曲式结构的特点,另一方面是节奏的特点。五声音阶羽调式是西部民歌最主要的调式,一首民歌后一半的旋律是前一半移低纯五度的重复,则是其主要的曲式结构形式之一,这种曲调结构形式在民族音乐学中称为“五度结构”。西部民歌很强调前短后长的节奏形态,这是由于西部裕固语重音后置,全都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的缘故。
维吾尔族民歌虽然有采用五度结构的,但采用五声音阶的很少,因此其旋律和西部民歌风格并不相近。我们在这两个兄弟民族的民歌之间,还没有找到相似的曲调。
采用五度结构和五声音阶羽调式这两个特点,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歌共同的特点。许多蒙古族、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的民歌都采用这种结构形式和羽调式,因此在这些民族的民歌中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和裕固族民歌相近的旋律。
匈牙利民歌歌词的结构和西部民歌很近似,在曲调方面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据柯达伊的研究五声音阶羽调式是匈牙利古代民歌最主要的调式,而五度结构也是其最主要结构形式,匈牙利民歌也常用前短后长的节奏型,此外这两个民族民歌的终止式在音调和节奏上也有不少共同特点。因为词曲的特点都一致,匈牙利有不少民歌的曲调和西部民歌极为相似,像是一首歌曲不同的变奏。
1988年,匈牙利科学院邀请了我国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裕固族歌唱家阿尔昂·银杏姬斯到布达佩斯进行学术访问,并开了一场裕固族民歌和匈牙利民歌的比较音乐会。匈牙利歌手演唱的每一首匈牙利民歌,银杏姬斯几乎都能唱出一首与其相近或相似的裕固族西部民歌。2018年3月,在上海举行裕固族民歌展演时,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民间音乐系教授雅诺士.安德拉斯(Janos Andras)和他的学生纳达斯梯·芬妮·艾斯特尔(Nanasday Fanni Eszter)应邀专程赴沪参加演出。他们演唱、演奏了和西部民歌相似和相近的匈牙利民歌,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2018年 5月15日,中国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中国与匈牙利民歌的亲缘关系研讨会”,会上由裕固族歌手妥英杰、钟玉梅以及来自匈牙利的纳达斯梯·芬妮·艾斯特尔歌唱家合作演唱了3组曲调相似的裕固族西部和匈牙利民歌。2019 年10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和赛盖德等地举办的庆祝中匈两国建交 70 周年的歌舞晚会上,裕固族歌手安梅更多次与匈牙利音乐家们合作,演唱了与匈牙利民歌相似的裕固族民歌。
匈牙利民歌为什么和西部民歌歌词、曲调都很相近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匈牙利民族源于亚洲,民间传说他们的祖先是匈奴人。匈牙利语言学家克勒西·乔玛·山道尔 (Korosi Csoma Sandor, 1784-1842年)曾于200年前认为匈牙利人和我国古代回鹘有亲缘关系 , 于是徒步走到亚洲来,希望到河西走廊裕固族居住的地区寻根,可惜因染病在印度大吉岭去世,没有到达他所向往的裕固族草原。匈牙利音乐家巴托克·贝拉 (Batok Bela, 1881-1945)1936年到土耳其采风,发现土耳其民歌的风格和匈牙利民歌风格非常接近,在90首歌中有 20 首和匈牙利古代民歌的曲调有密切联系,其中有4首和匈牙利民歌十分接近。他指出“匈牙利古老的音乐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民间音乐的相似之处,恰好说明古老的匈牙利音乐风格是古老的突厥音乐的一部分。”[6]121匈牙利的另一位音乐家柯达伊也说过,匈牙利民族“现在是那个几千年悠久而伟大的亚洲音乐文化最边缘的支流 ,这种音乐文化深深地植根在他们的心灵之中,在从中国经过中亚细亚直到居住在黑海的诸民族的心灵之中 ”[6]60。
众所周知,匈奴人在公元前121年失败退出河西走廊之后,在公元93年离开我国北方草原西迁,西部民歌和匈牙利民歌相似和相近的事实证明了西部民歌保存了匈奴民歌的特点,匈牙利民歌也保存了匈奴民歌的特点。本文前面提出的假说,便可以通过这个事实得到证明。
西部裕固语属于上古突厥语,用这种语言演唱的民歌也保持了 2 000多年前的形态,这是裕固族民歌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东部民歌在我国民歌中的特殊价值。
对东部民歌研究工作还不够深入,有关其歌词的结构以及与其他民族民歌歌词的比较研究,尚需要展开。从音乐方面来看,东部民歌和西部民歌一样,虽然都采用五声音阶调式体系,但它们所采取的调 式骨架不同。西部民歌多采用四度—五度骨架,这种骨架有三个支点 音,其中上、下两个支点音是支柱音,中支点音是半支柱音,上、中、下三个支点音之间的音程分别是四度、五度。东部民歌多采用五度—四度骨架,这种骨架有三个支点音,中支点音是支柱音,上下两个支点音是半支柱音,上、中、下三个支点音之间的程别是五度、四度。在东部民歌的旋律进行中,作为为支柱音的中支点音常被遮掩起来,最后“千呼万唤始出来”在终止时方才出现。这种揭示调性的方法很独特,给人以“曲中声尽意未尽”的感觉。
五度—四度调式骨架及这种独特的“绕唱”方式,在西部民歌中很罕见,在汉族民歌中也不多见,但在操蒙古语族语言的土族、保安族、东乡族民歌中却是常见的。这能够说明此种旋律类型是蒙古语族诸民族共有的,也说明东部裕固人和蒙古语族诸民族有渊源关系。
一定的音程在旋律显要的位置上出现,是形成旋律性格特征的 一个重要方面。蒙古族民歌中常出现八度下行跳进,这在东部民歌中也屡见不鲜。东部民歌中有不少曲调的节奏和乐汇都非常接近蒙古族 民歌,听起来很像蒙古族的旋律。
蒙古族民歌的体裁包括长调和短调两个类别。长调民歌曲调悠长,节奏自由,多采用散板,具有浓厚的草原气息。短调民歌曲调短小,节奏整齐,结构紧凑。我国蒙古族民族音乐学界乌兰杰在1985年出版的《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一书中指出:7世纪以前,蒙古人在额尔古纳河流域过着狩猎生活,与那个时代的生活相适应,蒙古民歌以短调为主。7世纪以后,蒙古人的先民跨出额尔古纳河流,向蒙古高原迁徙,开始从事畜牧业,随着生活的这一根本变化,反映游牧生活的音乐作品——长调大量产生。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蒙古南部从游牧封建下的领主所有制向一般地主所有制过渡,大批牧民转入农业生产,又产生了节奏鲜明、旋律流畅的短调。这样,蒙古族民歌经历了一个由短调转为长调,而后又从长调转为短调的发展过程。这一理论被我国民族音乐学界称为“蒙古乐风三变论”,它对研究蒙古族音乐史有极大的意义,同时也使我们对蒙古语诸民族民歌在古代的发展有了一个基本认识[7]。
从音乐形态上看,大部分东部民歌既不是长调,也不是短调。它们没有蒙古族长调的旋律那么高亢,节奏也没有长调那样自由,但也不像蒙古族的短调旋律那样流畅,节拍那样整齐,而是处于长调和短调中间的一个过渡形态。根据乌兰杰先生的“蒙古乐风三变论”,这种长不长,短不短的音乐形态,可能是保留了7至12世纪时蒙古民歌在从短调发展到长调时的一个历史形态,能为“蒙古乐风三变论”提供一个鲜活的旁证。
我1964年初到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去采风,开始研究裕固族民歌,比较深入地研究了裕固族民歌,2005年,也参加了裕固族民歌申遗的工作。裕固族民歌之所以能够被列入首批国家级文化遗产名录,是因为它分别保存了我国古代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民歌遗产中的因素,所以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希望我国音乐界能够充分地认识到裕固族民歌的价值,并认真地学习、继承裕固族民歌这份珍贵的遗产,并使它能永远传承,发扬光大。若能如此,裕固族甚幸,裕固族所在的甘肃甚幸!
【注释】
①这两个时代的民歌,可参看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