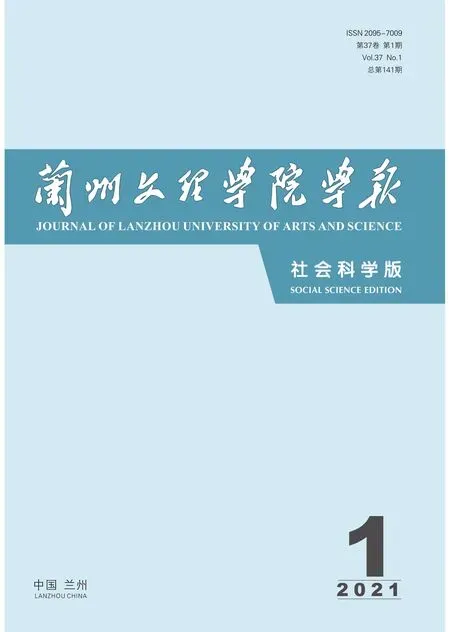音乐图像类文物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与使用
朱 迪
(兰州文理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中国音乐考古学自20世纪至今,已走过百年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在现代考古学的基础上形成。考古学形成于上世纪20年代,过去的史学研究多集中在文献研究方面,北宋出现了以欧阳修、洪适、赵明诚等学者为代表的“金石学”,即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主要是以古代的青铜器以及碑刻为研究对象,对商代以后的文化遗存进行研究,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自金石学开始,学者们逐渐关注到实物研究的重要性,但此时对于实物的研究多集中在钟鼎彝器方面。清代,乾嘉派学者钱大昕以考据著称,他利用碑刻史料与古代历史文献相互比勘印证,一方面重视“金石之学”研究,另一方面也不忽视历史文献的重要性。近代,王国维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二重证据法”,强调一方面重视文献研究,另一方面也要重视考古文物的研究,音乐考古学便在此背景之下形成。对于学科定义,王子初先生在《中国音乐考古学》中指出:“音乐考古学是以古人音乐活动的遗物和遗迹为研究对象,以此来了解古代人的音乐生活和音乐风貌,从而解释古代音乐艺术的发展和规律的一门学科”[1]。从时间范围上来讲,音乐考古学的时间跨度要从人类诞生开始直到清代末期,从空间来讲不局限于中国,而是要放眼于世界,具体来讲,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了器物和图像两方面。
实物与图像构成了音乐考古学的两大部分。过去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器物方面,尤其是出土乐器的研究,例如钟磬、吹管、丝弦,先秦时期各种打击乐器、乐器铭文等。考古学中图像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王子初老师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以下简称《大系》)中,《大系》对十几省的音乐文物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其中包括了器物与图像。图像相较于器物,所包含的内容更丰富、更多面、也更杂,研究成果涉及到音乐考古学、音乐史学两方面的内容,相对系统地对音乐图像类文物进行了分析与阐述。由于承载图像的载体有所不同,因此,王子初先生认为:严格来说其中有些图像不能够划为遗物,而是遗迹,例如洞窟壁画等[1]33。
一、音乐图像类文物的类别与内容
在音乐考古学当中,实物类的研究对象多以器乐为主,主要是遗址、墓葬、祭祀坑、窖藏或者专门的“乐器陪葬坑”中出土的乐器,而音乐图像类文物不同于实物类,图像类材料因为表现形式和承载器物的多样化,因此内容更加庞杂,具体来说,音乐图像类文物从传世和出土的图像遗存、遗物类型上可以分为:岩画、乐俑、画像石、墓葬壁画、雕砖石刻、器皿饰绘、洞窟壁画、绘画作品、书谱等。
(一)岩画
岩画是远古时期的先民以石器刻凿或者以矿物颜料绘画的方式创作并保留下来的一类音乐图像,也是音乐图像类文物中最古老的一类。目前所见最早的岩画在史前时期。岩画常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如我国的北部、西北以及东北地区,具体包括黑龙江大兴安岭岩画、内蒙阴山、贺兰山岩画、西藏八宿拉鲁卡岩画、新疆阿勒泰、库鲁克、呼图壁岩画、甘肃祁连山岩画、云南沧源崖画、广西宁明花山崖壁画等。岩画反映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到史前人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图腾崇拜、文字符号、狩猎农耕、祭祀宗教等。远古时期的音乐形式没有明显的音乐、舞蹈、器乐的划分,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形式,因此在古老的岩画中,与音乐相关的部分为原始乐舞,具体来说是宗教性乐舞,与祈雨、模拟动物、图腾崇拜、天神崇拜等内容相关。
(二)乐俑
乐俑是音乐图像类文物中,占比相当大的一部分,乐俑包括陶俑、木俑等。乐俑的出现是为了替代活人的殉葬方式。中国古代史前时期以人殉葬的现象相当普遍,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黄河中下游的大汶口遗址中就保存了目前考古发掘最早的以活人殉葬的情况,活人殉葬的现象中,不仅有成年男性与女性,还有婴儿和儿童。殷商时期,由于奴隶制社会制度的加深以及社会阶级的悬殊,活人殉葬的形式达到了顶峰,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一些贵族逐渐开始不再以活人殉葬,而是以俑人替代活人,在齐、楚、秦、韩等国较多。俑人在秦朝时达到了巅峰,最典型的以秦始皇兵马俑著称。汉代,以俑人殉葬的方式在丧葬习俗中普遍盛行。目前发掘的乐俑中汉代出土的俑人数量最多,唐代出土的乐俑最为精美。古人事死如生,墓葬中出土的俑人形态各异,造型丰富,且具有各地的地方特色。乐俑具体的包括说唱俑、乐舞俑、奏乐俑、杂技俑、俳忧俑等。
(三)画像石与墓葬壁画
画像石与墓葬壁画从汉代开始出现,一般来说画像石与墓葬壁画内容常出现于墓室墙壁或是棺椁上。汉代的画像墓葬始于汉武帝时期,由于汉代的社会生活、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因此丧葬习俗也随之改变。汉代统治阶层独尊儒术,在儒家孝道文化的影响下,汉代厚葬成风,墓葬风格多偏向恢宏华丽的风格,画像石和墓葬壁画逐渐开始盛行。东汉末年,当社会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时,这种葬俗观念也随之淡化,墓葬中的画像石和墓葬壁画也逐渐减少。
(四)砖雕石刻
砖雕石刻通常以古代建筑为载体,常常是古代民居、祠堂、寺庙等建筑的装饰,砖雕石刻表现的内容非常丰富,一方面是表现古人音乐文化生活的内容,另一方面还有表现历史神话故事的内容。
(五)器皿饰绘
通常,一些在古代生活器具上或者乐器面板上起装饰作用的图像被归为图像类材料中的器皿饰绘,古代的铜镜、玉牌、魂瓶、琵琶捍拨面等都有饰绘,这一类音乐图像展示古代音乐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包括民间音乐、文人音乐、音乐交流与传播等,侧面反映古代风俗文化、社会状况、政治制度等,器皿饰绘的表现内容与古代人民生活极为贴近。
(六)洞窟壁画
洞窟壁画与墓葬壁画,虽然都是壁画类型。但是其作用与表现内容大相径庭。墓葬壁画受汉代厚葬风气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孝文化,而洞窟壁画受宗教影响极大,多表现宗教音乐文化,以及宗教音乐供养人相关的内容。洞窟壁画最典型、规模大且造型精美的要以四大石窟壁画为首,山西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以及安西榆林窟、西千佛洞、新疆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壁画是壁画的集大成者,时间从北凉延续至清代。莫高窟壁画中有大量图像涉及古代乐器、乐舞以及大型歌舞伎乐演奏。
(七)绘画作品
绘画作品中展示的音乐类图像从唐代开始、明清居多,这期间保留了大量画作。内容表现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贵族享乐、少数民族乐舞等内容。
表现贵族享乐活动的有韩熙载夜宴图,描绘了五代南唐官员韩熙载在家中设宴,并以歌、舞、乐宴请宾客的场面,画作描绘了宴请的过程,其中包括琵琶伎乐演奏、观舞、清吹三部分。表现文人音乐的有:伯牙鼓琴图、竹林听阮图等。展现少数民族乐舞的有:苗族乐舞图;丧葬仪式音乐的有:大傩图;宫廷音乐方面的有清代的紫光阁赐宴图等。
二、音乐图像类文物的特殊性
音乐图像类文物与音乐实物类文物作为音乐考古学的两大类实证材料,单独来说都有各自不可忽视的重要性,然而单一的实证材料,总有一些自身的缺陷。这就如同在历史学研究中的文物与文献材料,都有各自的优势、劣势,在史学研究中往往形成互补关系,共同来论证。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我们无法还原音乐发生时的场景,因此需要借助图像的记录尽可能的靠近音乐活动的场景,以探索音乐本体以外的、更加宏观的、音乐文化方面的内容,而图像的记录既是一种实证材料,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创作,甚至很多时候会受到绘画风格、雕刻风格、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我们将音乐图像作为一种考古文物用于音乐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研究之前,首先需要辨别图像记录的准确性,判断图像作为考古文物的价值,最终才能作为音乐考古学中的图像类文物来进行研究。从音乐图像类文物本身来说,讨论这类材料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很有必要。
音乐图像类文物作为音乐考古学和音乐史学中最普遍且最广泛的一类论证材料,很多时候它能够反映出土乐器实物和文献材料无法展现和还原的历史音乐活动发生的场景。
(一)反映宏观的音乐生活场景
出土乐器展现音乐本体的内容较多,如律学、乐器学、声学等方面。洛庄汉墓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编钟,被称为“汉代第一编钟”,这套编钟的出土,证实了商周时期优越的“一钟双音”铸钟技术得以延续到汉代,虽然调音技术不同于商周时期,但“一钟双音”技术在汉代没有失传。这些音乐本体方面的内容,更多的是通过出土乐器实物来论证。
相较而言,音乐图像类文物更多的是展现更加宏观的音乐活动场景,具体包括了乐器的编配使用、乐器与文化习俗等,归根结底,背后所反映的是音乐文化。长沙金盆岭石棺墓出土的乐俑魂瓶,是一件宋代的随葬器物,魂瓶装饰繁复,魂瓶饰双层俑人,上层俑人持法器,下层俑人为乐俑,共六个俑人,其中一人持鼓槌,做敲击状,旁边有一架鼓,鼓的另一边乐俑手持拍板,紧接着旁边有一吹笛俑,吹笛俑旁边两个乐俑怀中有腰鼓,这种拍板、鼓、笛的乐器组合形式,是典型的宋代民间乐器合奏中的“鼓板”乐器合奏形式。这种乐器组合形式与文献中记载的宋代民间小器乐合奏形式一致,文献与图像相互印证,论证了这是宋代民间常见的乐器组合形式。
与文献相比,音乐图像类文物更为生动和具体。以乐器的编配形式为例,《旧唐书》中记载唐代宫廷音乐多部伎的演奏形式和乐器编配,对于清乐的编配载:“乐用钟一架、磬一架、琴一、三弦琴一、击琴一、瑟一、秦琵琶一、卧箜篌一、筑一、筝一、节鼓一、笙二、笛二、箫二、篪二、叶二、歌二。”[3]文献能够详细记载乐器的编配和规模,却不能直观体现出具体的用乐场合与乐器的摆放,而音乐图像一方面能够记录乐器的摆放,另一方面展现了音乐活动的场景。《紫光阁赐宴图》描绘了清乾隆年间在紫光阁举行盛大的礼乐仪式,宴请藩外使节的场景。图像内容宏大,画面中共展示了三组乐队,分别是中和韶乐、蒙古乐队、仪仗队前乐队。《紫光阁赐宴图》中具体展示了乐队规模、用乐场合、乐器编配等内容,是研究清代宫廷音乐有价值的图像资料。音乐图像类文物比文献记载更加具体、更加直观。
(二)展现材质易腐的乐器的形制
对于出土乐器实物来说,很多时候受材质的影响,保存较为困难,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出土乐器,由于年代久远,目前所见的出土乐器实物多为材质易保存的乐器,如青铜钟、铜铃、铜铎、铙、铜鼓这一类铜制乐器,石磬一类的石质乐器,以及陶埙、陶玲、陶钟这一类土制乐器。而像瑟、筝、阮、琴、箜篌一类的木质乐器,由于木材不易保存,现在保留的出土实物少之又少。以阮为例,根据文献,阮是汉代出现的乐器,而木质乐器易腐,并没有完整的阮乐器出土。目前所见的出土实物仅有武威弘化公主墓弹弦乐器残件,据该墓墓志铭记载,该墓为“大唐故武氏夫人”弘化公主墓。乐器残件仅剩一部分琴颈和琴头,琴头琴颈上有60余枚骨质梅花,琴头有四枚琴轸,琴轸圆锥状,表面刻有螺旋刻纹,遗憾的是,该乐器音箱没有保存下来。而相较于出土实物,图像类型广泛,因材质的缘故,更易保存,如图像中的砖画壁画、砖雕石刻等。南京西善桥荣启期墓室的竹林七贤画像砖中详细地描绘了阮的形制,砖画以线描为主,画像中阮咸怀抱乐器阮,乐器圆形音箱长颈直项、四弦四轸清晰可见,弹奏者手执棒状拨子,置于弦上,呈现出正在演奏的状态。
对于文献而言,记录乐器的形制没有出土实物和图像直观和生动,而出土实物是三者中,最直观和准确的,但是由于材质的限制,一些出土实物中没有保存的乐器,只能退而求其次,借助于图像来进行研究,图像填补了出土实物缺失的遗憾,对于乐器形制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表现乐舞形态与音乐文化
古人常用文字来详细记述音乐活动发生时的情景,音乐活动时所使用的乐器或许可以保留至今,但是乐舞的形态却很难用文字准确表达,相比较之下,音乐图像类文物更能够直观地展现乐舞的形态。
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丰富的乐舞造像,以最典型的112窟壁画《西方净土变》中的反弹琵琶造像来说,画面中的人物共有三层,上层与下层人物手持法器,中间一层是一组六人的小型乐队,反弹琵琶伎乐天在乐队正中间翩翩起舞,神态悠然雍容,手持梨形音箱琵琶,图像中展示了反弹琵琶伎乐人的乐舞形态、神态表情、表演服饰、使用的道具,以及乐舞人表演的场景以及与乐队的排列的形式。从表演的服饰与道具又可以体现出与西域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四)表现古代音乐作品与社会文化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如今我们无法听到古代音乐的旋律,即使保存下来的出土或传世乐器,也无法再现古代音乐作品,然而书谱中记录了古代音乐作品,可以通过乐谱一窥古代音乐活动风貌。
乐谱可以反映歌词的格律与旋律的音韵之间的关系、记谱法的发展、作品的风格、作者的创作背景、时代背景对作品的影响,从而进一步研究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生活、经济状况对音乐文化的影响,另外乐谱中的记录可以作为参照还原古代音乐作品,让古代音乐作品的概貌得以再现。
图像类遗存作为载体,所反映的音乐内容,说到底是对社会文化、政策制度、文化生活、经济状况、宗教文化的反映,无论什么音乐内容,最终背后所蕴含和映射的都是以上这些社会文化方面的内容,最终我们需要借助图像类遗存研究音乐活动、音乐现象以及音乐发展的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三、音乐图像类文物的局限性
音乐图像类文物有自身的优势和特殊性,同时也有着先天的一些局限性,例如受到古代美术不同时期绘画、雕塑、雕刻等艺术风格的影响;受社会文化背景或统治阶层因素的影响,内容上有一定程度的夸大或者回避;受制作者自身水平的限制,使得图像内容表达不够准确;另外,音乐图像类文物不同于实物,它是无法发声的,因此有一部分音乐图像类文物无法尽量贴近音乐史实。那么在研究音乐图像类文物的史学意义时,对于音乐图像类文物的价值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以辩证的观点客观判断音乐图像类文物的作用与价值,这对于音乐图像类文物如何用于史学研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一)受创作目的的影响
每个历史时期由于统治阶层的政治态度、政策、文化发展、社会文化生活以及经济水平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时代特征。这些因素决定了每个历史时期音乐图像类文物的创作初衷。如乐俑的出现是为了代替史前时期以活人殉葬的传统;汉代画像石和墓葬壁画的出现是受到当时儒家孝文化的影响,以这种华丽的厚葬风格体现孝道;初唐至盛唐时期莫高窟中常常能见到大型天宫伎乐图,其中乐舞乐器组合规模宏大,与唐代佛教盛行、宫廷音乐高度发展有极大的关系。这些创作初衷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音乐图像的内容及风格,甚至还会因为创作初衷,而对作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艺术加工。
以莫高窟220窟北壁初唐时期壁画中一件造型独特的阮为例,220窟中的阮为莲花阮(又名花边型阮),花边阮直项,琴颈不似普通阮那么长,音箱为莲花花瓣形,因此而得名莲花阮。莫高窟壁画中这样造型的阮非常罕见,莲花是佛教的象征,造型如此独特的乐器是真实存在还是受大乘佛教文化的影响而进行的艺术创作,还值得进一步考证,而从乐器学的角度来分析,莲花阮的造型虽精美,但在乐器制作中,其音箱并不能够使用大块头的整木来制作,因此音色会受到很大影响,并不适宜演奏,其观赏性和音乐文化价值要远远大于实际的演奏价值。
(二)艺术风格的影响
音乐图像类文物一方面是考古学文物,另一方面也同时是艺术创作作品,会受到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的影响,一部分音乐图像类文物的艺术性要高于史学价值。中国绘画作品有写意和写实之分,写实作品尽量贴近实物,因此也具有较高的史学参照价值,而写意作品,重情绪、风格而轻细节,因此很多时候在音乐史学研究中,不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南北朝时期壁画风格粗旷,注重写意而非写实,其中北周洞窟壁画299、301、428窟中的弹拨乐器,以粗线条的方式描绘了乐器大致的外形造型,其余的如琴弦、品柱、琴轸均没有表现。而经历了初唐时期绘画风格的变化,盛唐时期以及之后的绘画风格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如第45窟盛唐时期的壁画《观无量寿经变》、第112窟中唐时期的壁画《报恩经变》《药师经变》,风格越来越注重写实,即使是二十余人的大型的乐舞乐队,也展现得细致清晰,其中琵琶类乐器的直项或者曲项、音箱与琴轸、笙簧类乐器的笙簧数、演奏者的演奏姿态、持乐器的姿势、演奏法都有清晰的刻画。因此艺术风格也是对图像影响很大的因素之一。
(三)制作者水平的限制
音乐图像类文物作为创作作品,除了受上述影响外,还会受到制作者或者创作者自身水平的限制。很多创作者并不十分懂音乐,创作时不会重点关注到音乐的部分,所反映的音乐方面的内容不仅不准确,很多时候还会起到误导作用。
陈旸《乐书》被认为是宋代的音乐百科全书,其中最可贵的是后105卷乐图论绘制了乐器形制图,陈旸在宋代宫廷时任吏部尚书,虽通晓乐律,但对音乐和乐器制作并不十分熟悉,因此在《乐书》中对于箜篌、律管等一些乐器的绘制图不仅不准确,甚至还会误导读者。刘勇在《陈旸〈乐书〉乐器插图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面对作为读者,又作为专业的音乐学者,面对古代乐器插图(特别是一些陌生的乐器)时,应该有一种意识,即插图也像文字一样,有时未必完全可靠。”[3]绘制的图像与文献相同,都会受到记录者的极大影响,因此我们在研究图像材料时,需要经过客观判断,才能够确定图像中哪些内容可以对史学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音乐图像类遗存与社会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体现在它所反映的内容,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体现在它的创作方面,无论是创作初衷、创作风格都极大地受到大时代背景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创作背景的社会学、历史学调查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音乐图像类文物的价值判断与史学研究意义
(一)音乐图像类文物的定位
历史学研究中,首先出现的是文献学研究,北宋时兴起了以欧阳修、洪适、赵明诚等学者为代表的“金石学”,即考古学的前身。自金石学开始,古代学者们逐渐关注到实物研究的重要性,研究多集中在钟鼎彝器方面。清代,乾嘉派学者钱大昕以考据著称,他提出一方面要重视“金石之学”研究,另一方面也不忽视历史文献的重要性。近代,王国维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二重证据法”,后来学者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三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的概念有三种不同体现,一是黄现璠先生的观点,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加入“口述史”的研究;二是饶宗颐先生的观点,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将考古材料又划分为考古材料和文字材料两类;三是叶舒宪先生的观点,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加入文化人类学的材料。朱大渭先生提出:治史者“要真正掌握地上文献资料、地下文物考古资料、1000多年来前人的研究成果资料,一定要穷尽这三类资料,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择善而从,推雅取正从而掌握准确可靠的有关资料,以及前人的真知灼见”。
无论哪一位学者视角下的“三重证据法”,终究体现的是史料的多元化的观点,在历史学研究中物尽其用。陈寅恪先生治史注重以诗证史、以史说诗、官书和私著兼顾。章太炎先生在《中国通史略例》中说:“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4]。
1.图像材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
文献能够通过文字说明历史,出土实物中的乐器往往能够通过声音、形制等直观地反映音乐本体,而图像类往往要通过描述、分析,以及社会学、历史学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因此,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是容易被忽视的一类材料。而事实上,在音乐史学研究中,文献遗存、出土实物、图像遗存缺一不可,图像更多的是反映音乐与社会文化方面的内容,是相对更宏观、更抽象、也更复杂的,因此,往往能够对文献研究和出土乐器的研究成果起到弥补的作用。
在音乐史学研究中不可忽视图像类的重要性,图像类遗存应当与出土实物、文献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三者对古代音乐的发展规律的研究起到不同方面的积极作用。
2.图像材料与实物材料的关系
与实物类材料相比,出土乐器更多的反映音乐本体、包括乐器的形制、声学性能、律制、调音方法等具体的内容,而图像类材料多反映宏观的音乐文化方面内容。
对音乐史学现象和规律的研究不能只顾音乐本体,而忽视背后的音乐文化现象,也不能单纯考虑音乐文化现象而不顾音乐本体的内容,图像类资料与出土实物在音乐史研究中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把握好这两者,能够更全面、更客观地看到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问题。
3.图像材料与文献的关系
图像类材料往往没有文献记载详细和准确,而文献资料往往没有图像类资料生动和直观,因此在音乐史学研究中,文献与图像往往要相互借鉴,相互佐证来共同论述古代音乐发展的现象和规律。
4.辨别音乐图像类文物的有效性
在明确音乐图像类文物在史学研究中的定位后,还要明确辨别研究的音乐图像类文物是否具有史学研究价值。一方面要判断图像的来源,尽可能是第一手资料来源,另一方面,要对图像表达的内容、图像背后的历史、文化、社会因素综合研判图像贴近历史的真实程度。
当代历史学研究注重“多重证据法”。每一种实证材料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音乐图像类文物也不例外,这类材料有其特殊性也有局限性,因此这就决定了对音乐图像类文物进行研究时,一方面,不能够尽信图,英国学者彼得伯克认为:“大部分图像在被创作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将来会被历史学家所使用。图像制作者所关注的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有他们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5]因此,不能够孤立地看待音乐图像类文物,以免对事物研究过于片面,而出现断章取义、管中窥天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平等看待音乐图像类文物、出土实物和文献的关系,既不能在研究中把音乐图像类文物完全置于主导地位,简单的看图说话并不能够尽量真实说明音乐现象,也不能忽视音乐图像类文物的史学研究价值,音乐图像类文物与文献、出土实物相比,是新型的实证材料。图像能够弥补文献和实物在史学研究中的不足。另外,在研究音乐图像类文物时还应当仔细甄别,去粗取精,才能尽量贴近历史。
(二)音乐图像类文物在音乐史学研究的四个层次
音乐图像学借鉴了西方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即潘诺夫斯基提出的图像阐释方法的“三层次理论”[6],第一层次是“前图像学描述”,主要是图像本体的阐述;第二层次是“图像学分析”;第三层次是“图像学的文化阐释”,主要对图像背后蕴含的文化进行分析。音乐图像类文物的研究也离不开这几个层次,除此之外,音乐图像类文物用于历史学研究之前,应该综合研判图像是否具有史学研究价值。音乐图像类文物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引申为四个层次。
第一步,是要尽可能详细的描述图像的本体内容。做到尽量客观,清晰和准确。
第二,要对图像进行考古学、历史学和音乐学的研究与分析,这一部分要尽量做得扎实、充分,尽可能的从多方面入手来分析音乐图像画面蕴含的信息。
第三,要对图像内涵进行辨析。图像中所反映的内容是否贴近历史,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受到影响的程度有多大,图像的可信度有多高,图像中哪些方面所反映的音乐史学信息相对准确,这些都是在经过扎实充分的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分析之后判定的。
第四,是综合以上信息对音乐图像类文物画面中所包含的内容进行文化学解读。
在这些研究工作中,对音乐图像类材料的价值辨析是尤为重要的环节,图像的真实程度极大影响了研究结论,因此在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研究中,音乐图像类文物材料虽然种类多且内容丰富,但是使用时要慎之又慎,要多方辨析、研判,才能用于音乐史学研究。
小结
音乐图像类文物与出土乐器共同构成了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内容,随着出土乐器研究成果的蓬勃发展,音乐图像类文物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音乐图像类文物主要有:岩画、乐俑、画像石、墓葬壁画、砖雕石刻、器皿饰绘、洞窟壁画、绘画作品这几类。音乐图像类文物在史学研究中有特殊性也有局限性,特殊性体现在于音乐活动宏观场景的展现、材质不易保存的乐器形制的展现、乐舞形态的展现,这些直观的内容都对音乐活动与古代音乐发展规律和音乐文化的研究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局限性在于音乐图像类文物既是文物也是艺术作品,受诸多因素影响,并不能够完全客观反映史实。历史学研究提出“多重证据法”,音乐史学研究与音乐考古学研究也应当如此。以音乐图像类文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前提下,需要结合多重实证材料,与出土实物、文献的、口述史、音乐文化人类学材料多方印证,才能够更加客观、更加辩证的看待和研究音乐史学问题,促进音乐史学科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