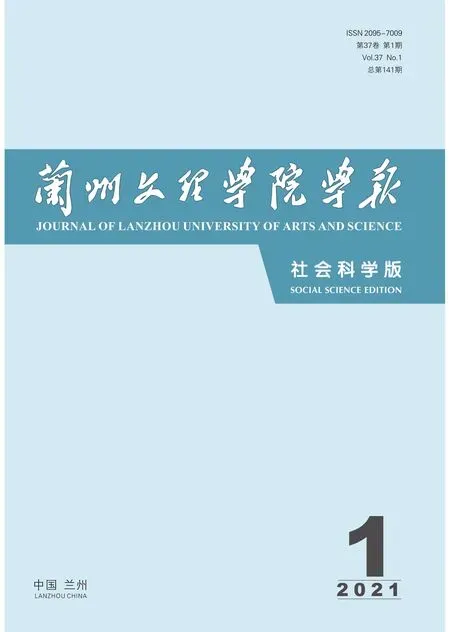李美皆的B面
——评《晚年丁玲形象研究》
张 伟
(包头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内蒙古 包头 014030)
阅读学术著作而流眼泪,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过,此前,我没有过。读《晚年丁玲形象研究》,我潸然泪下,为丁玲,为那一代受难的作家,为那一代屈辱的知识分子,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最晚近的一次大灾难。
李美皆的文学评论,以明快而锐利见长,她总是快人快语,单刀直入,我手写我口。她似乎不屑于引经据典,拉大旗作虎皮,用不着名流大咖来助阵。透过文字,我们读出一份自信,一种独立思考、坚定地做出属于自己的审美判断的学术气度。
而她的学术著作《晚年丁玲形象研究》,则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她旁征博引,占有资料宏富。如果拿重复率那一套工具理性的劳什子来衡量,恐怕是通不过的,但却是论证之必要。她让自己的每一个判断,每一个结论,都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历史就是一笔糊涂账,需要李美皆这样的学者来澄清。
著作采用页脚注,有好多个页面,注释占到半页,甚至多半页。引用的著作多达上百部。内文中的引文,以楷体录入,直观地显示出阅读量之大。除了引用著作、文章,还有信件、日记、年谱、交代材料等,丰赡而详实。
丁玲晚年的是是非非,那就是一团乱麻。
我特别佩服李美皆,愣是把那一团乱麻理清楚了。概括地说,丁玲晚年,其人是复杂的。一个棱角分明、个性鲜明的女作家(她笔下的莎菲,是带有“自叙传”色彩的,从中能看到丁玲的影子),20年的右派生涯,被改造,被扭曲,面目模糊,恐怕连她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儿了,“我是谁”,这一哲学命题,在丁玲这里有了形而下的新含义。说话写文章,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或者言不由衷里带出一些真言,信誓旦旦里真诚地说着假话,总之是一笔糊涂账。此其一。
丁玲一生,环境复杂,出没在她身边的人,有国民党的特务,共产党的叛徒等等。及至晚年,仍处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一个人跟人吵架时说的话,与他心平气和时说的话,能一样吗?有时恰恰相反。语境不同,发声不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丁玲哪些话是冲着周扬去的气话,哪些话是对青年作家的谆谆教诲,哪些话是为解决自己的历史问题而故意说给高层领导听的。此其二。
丁玲晚年,舆论纷纭,各方对丁玲的言说,也是复杂的。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那是一个迷雾重重、将明未明的时代,何者为正确,何者为错误,混沌一片,莫衷一是。那是一个大梦初醒、噤若寒蝉、心有余悸的时代,因言获罪,让多少有良知的人蒙冤罹难,“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们对即将开启的新人文环境还在试试探探。此其三。
李美皆的功力表现在,掰开了,揉碎了,举重若轻,驾轻就熟,让百家之言为我所用。蚕吐丝,丝纺线,线织布,无序变有序,规矩成方圆。这部书,像老和尚的百衲衣,针线细密,缝合得宜,不啻为一款做工精细、考究的精品。
作为女性学者,李美皆是怀着“理解之同情”走进丁玲的内心世界的。“想必这思想汇报里更多地包含着陈明智慧的结晶,以丁玲的心性,是写不好认罪书的;由陈明来写,似乎那屈辱就由陈明来承担了,对丁玲也是一个解脱。”[1]30在这段话中,我们读出了一种体恤,一种悲悯。
右派的帽子在丁玲头上戴了二十多年,受尽磨难,到老来,却又成了僵化保守的“左”的代表人物,被讥讽为文学界的“左王”。左乎右乎?李美皆指出,“丁玲晚年给许多人留下的‘左’的刻板印象,其实是一个需要慎重认识和对待的复杂问题”[1]15。为历史问题平反所累,与周扬宗派抗衡,“左”成了一种策略和手段,一种功利性的考量,复杂地胶着在一起。嗟乎,一部中国当代史,摆不脱左与右的纠缠。李美皆认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也就是其研究价值所在,才肯花大力气去厘清。她努力超越单一视角,进行多维透视,比如性别观念的观照,就有了新的发现。当年魏明伦发表《雌雄论》,对宋庆龄、毛泽东等历史人物的不同性别角色、不同性别观念进行臧否,振聋发聩。李美皆引入性别视角,对晚年周扬在丁玲历史问题上的观念局限进行剖析。上下左右,旁征博引,勾连引申,视野开阔,展开充分的论证,直击男权社会里女性贞洁观等封建意识。这一部分,完全可以独立成章,是不可多得的妙文。
设身处地地去揣摩、描述丁玲的心路历程,也构成了该著的一个重要特点。对她的前后不一致,自相抵牾处,都做了毫厘不爽的辨析。自己写的那张“条子”,始而认为不是自首,继而又自认为自首。北大荒的劳动改造,她时而说是浪费时光,没有成绩(1979年四次文代会上);时而又表示无怨无悔(厦门大学创作讨论会上)。何者为真,何者为假?真假莫辨,却逃不过李美皆的火眼金睛。书中多有心理透视,“心态”“情结”等词语频频出现。诸如“逐臣心态”“怨妇心态”“念旧心态”“苍凉心态”“老年心态”“惧祸心理”“受虐狂心理”“精神分裂”“精神溃败”“心理刑场”“心理痉挛”“心理氛围”“谵妄状态”“攻心术”“心理战”“神经战”“人格扭曲”“辩诬情结”“政治情结”“讨伐情结”“领袖情结”“马列情结”等。还有,如“长期受虐留下的后遗症”。“即便不再为了毛泽东而奋斗,丁玲对毛泽东的情感也是一仍其旧。这是典型的老年人的念旧心态。”“那是属于老年的苍凉心态。”[1]40被改造,被碾压,被扭曲,同时也自我改造,自我变形,受动与主动变奏交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与周扬对着干的逆反心理,成了晚年丁玲的一种心理驱力。“所谓‘左’,未必代表她本质的真实,只是顺手的工具和有效的手段而已。”[1]125
李美皆对丁玲的评价,中肯而切当:“根本上,丁玲还是个刺猬型的女人:刺在外面,外强中干;好斗,却并不善斗;斗争性强,但战斗力弱;桀骜而不刚烈,强健而不强悍。”[1]741956年时,丁玲还表现的很倔强,周扬过来跟她握手,遭到拒绝[1]32。农场改造,丁玲承认自己是个人主义野心家。“在被批斗改造的过程中,来自他人的羞辱固然难以承受,但过后回忆起来,最致命的,可能还是这种自辱。也许这就是她复出后不愿回首‘伤痕’的原因,实在太令人汗颜和无地自容了!”“作为体谅丁玲的读者,最为丁玲难过的也是这种‘自辱’。”李美皆进而分析到:“但是,这首先不是丁玲的羞耻,而是一个把人的尊严剥夺净尽的时代的羞耻。”[1]33“无论丁玲怎么发言,都不会可爱,她在被逼到一种注定不可爱的境地中去。”[1]126从丁玲参差互悖的言论和行为中,寻绎其心理轨迹,每一处,都是那么入情入理。李美皆揭示出“中国知识分子深刻的精神矛盾和真实的生存状态”。在充分论证基础上,得出“被外部塑造的‘两个丁玲’”的结论[1]180。
书中不仅有丁玲自身早年与晚年对比,如,李美皆以内在化的写作与外在化的写作、女性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来对比分析丁玲早年与晚年的作品。还反复与同时代其他人做比较,在宏阔的视野里,纵横捭阖。比如与李锐等人的比较[1]29。同时,李美皆也指出,不具有可比性,强做对比,则必大谬不然。“用以比较的对象已经决定了比较的结果。”[1]13拿丁玲与韦君宜、巴金比,要求背有重负的丁玲也去“忏悔”“思痛”,就不具有可比性[1]104。
李美皆坚定地为丁玲辩诬,她写到:对丁玲的悲惨处境,“除了悲悯,还能说什么?这已经够不堪的了,如果后人不仅没有悲悯,没有羞耻的同感,反而用丑化的眼光去打量她,用挖苦的腔调去评议她,那就是人性的更大的不堪了”。“这不是个人的耻辱和悲剧,而是时代的耻辱和悲剧,是每一个参与那段历史的人的耻辱和悲剧,超然于岸上笑着他人尊严尽失的人是可耻的。”[1]34
人物研究,为传主树碑立传,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用力太猛,做过度阐释。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一部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经典,只有林语堂这样的大文人才能走进苏东坡的心灵世界,跨越时空展开对话。记得王尚文先生曾说过,他本想毕其一生来研究苏轼,读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感到无法企及,更遑论超越了,于是转而去搞语文教学法了。就是这样的一部书,也有可指摘之处。苏东坡与王安石是政敌,两人相见时的风度却很好,胡兰成批评说:“林语堂文中帮苏东坡本人憎恨王安石,比当事人更甚。苏与王二人有互相敬重处,而林语堂把王安石写得那样无趣……”[2]当把传主苏东坡当作“正面人物”来塑造时,其政敌王安石也就成了“反派角色”,也就“无趣”了,可“憎恨”了,思维定势使然,必致过度阐释,林语堂也未能免俗[3]。
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李美皆是脱俗的,她走出了那个怪圈。她热爱丁玲,为丁玲鸣不平,为丁玲慷慨辩诬,但她毫不讳言丁玲的种种局限性。书中多处有对丁玲的性格分析,都能看出,李美皆是扎扎实实地做过功课的。比如她指出,“丁玲自以为聪明的‘机心’,以及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的过度阐释、过度反应,确实有种让人不舒服的感觉”[1]49。李美皆绝不为尊者讳,她指出丁玲的“臆想狂式的杜撰”,揭破其自相龃龉处。“丁玲一面把冯达写得那么阴暗,一直在毒害她,另一面又写冯达为了解除她的痛苦寂寞,宁愿别的男人接近她、安慰她。”同时不忘勘察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由上述种种悖谬以及丁玲叙述的凌乱局促,可以推知她是在怎样精神崩溃的情形下作出这一交代的。”[1]64李美皆毫不留情地指出:“她对‘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的执著,不仅仅是不合时宜了,简直固执、保守到了自讨没趣的程度。”[1]171指出“她的发言左支右绌、捉襟见肘、前后矛盾、漏洞百出”[1]175。丁玲伤害过萧也牧,却不向萧也牧道歉,就此,李美皆向丁玲进行无情的拷问。“对于生命,丁玲缺少某种觉悟。太多的斗争、太多的运动,使人性异化成了狼性,锻造出了没有悲悯的一代。”[1]252第五章第三节,用一整节的篇幅,集中探讨“丁玲晚年形象的自我成因”,对其争强好胜、意气用事、不甘寂寞等性情,对其老年的弱点,都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李美皆痛恨极左路线,但她同样以“理解之同情”去对待政治漩涡中的周扬,没有像林语堂替苏东坡恨王安石那样,去替丁玲恨周扬。可以说,李美皆最大限度地做到了客观、公正。针对丁、周的矛盾,李美皆认识到,“斗争思维、宗派意识是相互的,当一个人反复向‘宗派’开火时,恰恰说明自己已经陷入了宗派,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强势还是弱势”[1]220。
我们看到了李美皆的B面,当然,她依然保持着她的清明和理性。其实,有的时候,史料越多,干扰越多,越难做出判断。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如果没有洞察力,就会陷于纷杂又相互支绌的材料里不能自拔,李美皆却能从繁杂的史料中超拔出来,以理性还世界以清明。
文学评论家的敏锐,首先体现在语感上,字句在她眼里,就像侦察目标在侦察兵眼里,无可逃遁。她常常从文字的罅隙里发现那些隐而未彰的信息,从而做出令人信服的判断。且看周扬的批示,其文字背后的用心,逃不过李美皆的锐利目光。“丁身体如不好”,一个“如”字透视出周扬的不确信,他派人去看看,是表示关心,更是想了解丁玲是不是真的老实下来了[1]31。毛泽东的“编者按”,是丁玲定罪的关键词。李美皆敏锐地发现其“时代的修辞特征”,并援引其导师王尧的论断:“1950年代以后,通行的汉语特别是集中反映了文体特征的社论与大字报,其实是马克思的英文句式、毛文体、鲁迅杂文的综合。”[4]针对着徐庆全的结论,李美皆尖锐地指出:“在丁玲和田汉、阳翰笙的历史问题的对比中,双方的两个‘虽然……但是……’的重心要找准。”[1]73掂轻量重,是非分明。针对对丁玲晚年之“左”的种种指责,李美皆说:“这应该不是一个转折关系,而是一个因果关系。”[1]107还有,“尽量不”,而不是“坚决不”“绝对不”[1]241。诸如此类的地方,在在印证着李美皆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优良质素。
1960年,丁玲回北京参加第二次文代会,受到冷遇。沈从文追上去要跟丁玲说话,丁玲有意回避,不愿交谈。李美皆就此分析到:“丁玲还放不下共产党员的清高,觉得自己再怎么落难,也是党内的事,自己人之间的事,犯不着一个党外的不先进分子来实施精神救济。到了这般时候,丁玲的营垒意识依然那么强烈!宁对推下自己营垒的战车死不放手,也不能接受另一营垒伸来的礼貌之手,这是一个革命者在非革命者面前的原则性问题。或许这也是党性的体现?”[1]31~32这里,用疑问句,而不用判断句,表明是悉心揣测而非妄下断语,也意在表示不可思议,令人费解,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引人深思。
李美皆在该著中保持了她一贯的锐利,令人激赏。“即便马蹄践踏了鲜花,鲜花也要抱着马蹄狂吻,可怜可叹,又可歌可泣。”[1]35她剖析丁玲的分裂,言辞犀利,一针见血。她尖锐地指出,“丁玲在政治与艺术关系问题上的摇摆,其实也是其政治人格与艺术人格之间的摇摆,她试图玩一种平衡术”[1]174。不知何错,又必须改造,这“人类寓言式的悖谬处境”,是一种黑色幽默,必然带来心灵的扭曲。李美皆引入龚自珍笔下的“病梅”,形象而生动。“既要努力做出触及灵魂的样子,又要尽可能自我回护,真难为他们。”[1]30对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真正用心去体谅。
李美皆做的是丁玲的个案研究,而这项研究的意义,却绝非仅限于有关丁玲的是是非非,其研究价值具有普遍意义。李美皆丝毫不回避,“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在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很普遍的”[1]45。如她书中所言,“虽然本书是与‘晚年丁玲’形象相连、以丁玲为个案来提出‘丁玲现象’的,但能够最好地代表这一现象的,也许不是丁玲,而是艾青、臧克家、欧阳山、魏巍、曾克、曹明、舒群等人”[1]8。李美皆是把这一课题提升到历史文化学、精神现象学的高度来审视、来研究的。“晚年”,不是年龄概念,而有其形象内涵;不是自然生命现象,而是精神文化现象。“通过丁玲道路来认识历史”[1]12,是李美皆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诉求。作家人格与外部环境特别是政治气候的关系、个性自由与政治规约的关系,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文学的生态环境等,是她的关注点。反思过去,建构未来,揭橥规律,是其旨归。
在我身边,有许多这样的老知识分子,他们年事已高,都是耄耋老人了。在他们正当盛年的时候,可以以充沛的精力为社会作贡献、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时候,赶上了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身心备受摧残。当他们摘掉那顶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帽子的时候,已经青春不再,回望被蹉跎的岁月,徒叹奈何。按理说,这些人应该是最痛恨极左路线的人。然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表现得极左,真是匪夷所思。“精神奴役的创伤”,已不可治愈,悲夫!“惨痛的‘教训’使丁玲打定主意任何时候都以歌颂者而非揭露和批判者的面目出现,任何时候都不再被人抓住‘右’的把柄而始终唱‘左’调,因为丁玲终于看清楚了,‘左’在政治上永远是安全的。”[1]125这是特别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就我目前的认识,有两点。一是政治高压之下,“左”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强行植入,已经长在肉里了。就像夏洛克要割下一磅肉,无法不带出血来。即便在经过了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他们也走不出思想的牢笼。二是心有余悸,被整怕了,“政治正确”永远是他们的第一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而经验告诉他们,“左”在政治上最安全。言不由衷,双重人格,自相矛盾,这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一代知识分子的脸谱。这是发生在丁玲身上的,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问题,值得反思。丁玲把秦城监狱坐牢,说成是北京郊区的优越生活。这让我想起,有一位老先生,他一面积极争取曾宪梓教师奖,一面振振有词地说,怎么能到资本家那里去领奖呢?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他虚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的心灵已经被扭曲,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在他那里是混沌的,是不分明的。真真假假,已经搅乱了他的心神。
异化的结果,“有人要看她自我作践,她就作践给人看而已,真实的罪感已经没有了”[1]79。多么沉痛!德国人至今还在反思、清算纳粹的罪恶及流毒,我们对极左路线的历史总结同样远远没有结束,李美皆写到:“为了让历史不再重演,巴金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文革’的外延可以扩大为整个‘左’的历史,丁玲的这些文字,应该陈列在这个博物馆里。如果这个博物馆客观上不成立,就让后人把它陈列在心里,让无数的心灵跟丁玲一道受难。”[1]80
全书的结构框架,设计合理。作者对丁玲历史问题的四次审查,做了钩沉。“历史问题总是在她的现实政治触礁时出现,使她雪上加霜。现实问题是短期病症,历史问题却是终生顽疾,只要有了前者的诱因,后者必定会发作。”[1]7130年代的事情,80年代才有了最终的结论,半个世纪,伴随丁玲大半生,设身处地地为她想一想,一个作家,一辈子挣扎在政治漩涡里,实在太可悲了。该著第二章钩沉索隐,“周扬与丁玲的关系,合成了一部左翼文艺运动史。左翼文艺内部一直存在着矛盾与纠结,周、丁二人的关系是集中体现”[1]199。丁玲与周扬的个人恩怨,直接关系到丁玲历史问题的结论,李美皆对此做了专章探讨。作家是用作品说话的,所以,第四章聚焦丁玲的“话语实践”。晚年丁玲,创作乏善可陈,倒是有不少发言和讲话,第三章就其“观念问题”做了梳理。问题互有交叉,行文巧为闪避,各有侧重。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何况,丁玲一生都为历史问题所困。对历史的钩沉,增加了该著的厚重感。作者总是还原回到特定的语境中,回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带着现场感来进行解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没有自我空间的时代,人越虚伪和残暴。”[1]211李美皆真正做到了知人论世,而不是断章取义,抓住只言片语大做文章。她不是只取所需,为我所用,而是胪列各家观点,加以辨析,呈现出强烈的论辩色彩。“所谓察人论世,就是指在对问题作出评判时要充分体察个体的处境,如果前提是有限制条件的,结论却不顾条件限制,那么,再怎么义正词严的结论,都是没有信服力的不察之论。”[1]142她还通过对不同版本的考证和辨析,来说明问题。
前人做学问,写文章,讲究义理、考据、词章。李美皆爬罗剔抉,尊重历史,又有不凡的史识。李美皆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的真相是可以无限接近,但永远不能抵达的。”[1]93“作为学术研究,却必须对细节进行考究。把细节虚化或回避掉是可以的,但只要涉及到,就不能不加以辨析。即便最终结论是正确的,所用论据也必须符合真相。”[1]96
李美皆始终坚守着清明的理性,辩证的思考。“丁玲的晚年表现,是促成她的历史问题彻底解决的有力推手,同时,也是为她的晚年形象带来消极影响的主要因素。可以说,她积极地寻求历史问题解决的过程,也是她消极的晚年形象逐渐定格的过程。外在的得与内在的失以一种充满悖论的方式贯穿在丁玲晚年。”[1]99如何看待丁玲晚年的“左”,在这里彻底讲清楚了。她的左,“可以看出她的政治策略与智慧,但也可以见出她的无奈和意志的脆弱。”[1]101文坛褒贬与官方评价的错位,掣肘着丁玲的思想与表态。
李美皆是明达的,又是审慎的,绝不妄下结论。“反思是一种能力,有人精神上被打垮了,丧失了反思的能力。有人反思的能力尚在,但失去了反思的愿望,只想为自己贴一个安全的政治标签,以解决现实问题。丁玲属于哪一种?亦或二者兼具?”[1]119李美皆在思考,也引导着读者深入思考。
李美皆把晚年丁玲的研究比作枯水期,并强调其价值所在。是的,许多时候,教训比经验更有价值,我们从教训中获得的教益,常常在经验之上。“本书是关于丁玲晚年研究的第一个长篇文本,是第一次将丁玲晚年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进行研究,也是迄今对丁玲晚年的最完整的研究。”[1]269其学术价值是显在的,必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