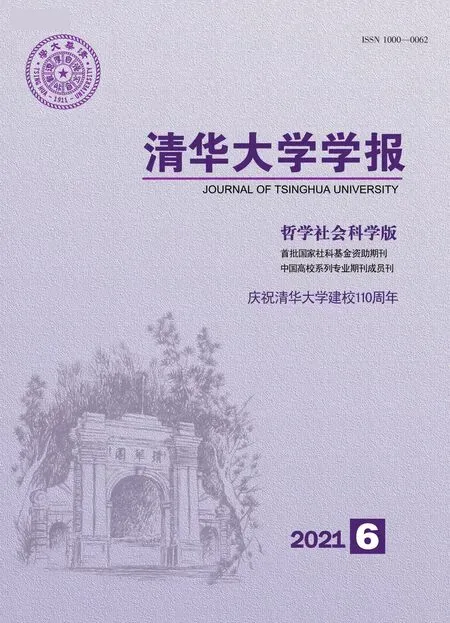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一个诠释学问题的探讨
李建盛
西汉今文经学家董仲舒表达的“《诗》无达诂”,现在被人们称为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诠释学命题。从现代诠释学角度看,这个“命题”无疑包含某些重要的诠释学维度。事实上,近年来许多关于这一命题的理解都把它与诠释学联系起来,把它与诠释学所认为的理解的开放性和解释的差异性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把它与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理论联系在一起,充分发掘这个命题在理解维度上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创造性诠释学空间。但是,对于“《诗》无达诂”为什么是一个具有诠释学意义的命题的论述却似乎并不是很清楚,也不够全面,在对“《诗》无达诂”与诠释学的比较性应用时也比较简单随意,忽视从“《诗》无达诂”的经学阐释到“诗无达诂”的诗学阐释的重要环节。本文探讨和论述的问题是,“《诗》无达诂”这个命题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诠释学维度,它在中国经学和中国诗学发展过程中如何从“《诗》无达诂”的应用性经学阐释转变为“诗无达诂”的审美性诗学阐释,它与哲学诠释学的理解有何重要的相似和根本的差异。
一、“《诗》无达诂”的诠释学维度
可以肯定地说,董仲舒提出的“《诗》无达诂”,起初并不是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阐释,它是在历史的阐释和运用中逐渐转变为“诗无达诂”的文学阐释,即从一种关于《诗》的实践应用性阐释转变成为关于《诗》本身的审美性诗学阐释,并转变为我们今天所谓的关于“诗”本身的诗学阐释。当然,这种转变无疑与起初对《诗经》的“非文学”的理解和解释有关,特别是与对《诗》作为“经”的解释性应用或应用性解释密切相关。在审美性的文学观念看来,“《诗》无达诂”当然不是今天的所谓“文学性”理解,但是,它之所以最终可以转变为关于诗或文学的诠释学命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于它是对作为“诗”的《诗经》的理解,而不是对非文学文本的理解,因而它能够在历史性的理解、解释和应用中转变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诗学命题。从现代诠释学,特别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来看,这种实践性应用的维度也同样是所有理解的一个维度,即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所谓的理解和解释总是包含着应用,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无达诂”这个命题首先体现的是诠释学的实践性应用维度,而不是《诗经》或“诗歌”阐释的文学性审美维度。
在董仲舒那里,“《诗》无达诂”是与“《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一同出现的,这表明理解的差异性并不只是对《诗》的理解所特有的现象,而是理解过程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它们共同体现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理解差异性问题,即这里的理解问题不只是一个解《诗》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包含理解《易》和《春秋》等经典文本的普遍性理解问题。“董仲舒提出‘《诗》无达诂’等重要表述,其本旨在于推阐《春秋》大义,‘通经致用’,似乎与诗学无关,而实际上却与文学、诗学的释义方法密切相联”。①毛宣国:《“〈诗〉无达诂”解》,《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如果从理解、解释和应用三位一体的哲学诠释学角度看,这种“通经致用”的理解,首先关注的不是一个关于《诗》文本本身的阐释问题,而是一个超出了单纯文本理解的诠释学应用问题。
许多论者都根据哲学诠释学强调的理解差异性和接受理论突出的接受主动性来讨论“《诗》无达诂”这一命题。当然,这个命题中包含这个维度。但仅仅突出这个维度不足以理解“《诗》无达诂”具有的诠释学意义。“《诗》无达诂”最初很难说是一个命题,而是董仲舒对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理解现象的概括,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篇》中写道:
董仲舒曰:难晋事者曰:“春秋之法,未逾年之君称子,盖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杀奚齐,避此正辞而称君之子,何也?”曰:“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②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4—95页。
董仲舒在谈到“《诗》无达诂”时所用的“所闻”,实际上是指董仲舒感觉和意识到了已经存在对《诗》《易》《春秋》等差异性理解的普遍现象,但是,他的目的实际上并不仅仅肯定这种现象,更重要的是要解决“《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这种纷乱的理解现象。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诠释学问题。尽管我们不能说这段话就是现代诠释学意义上的,但它无疑包含着丰富的诠释学维度。然而,在解读董仲舒的这段话时,论者们往往侧重于“达”和“诂”的理解,并把重心落在关于《诗》的理解问题上,而较少关注它所包含的诠释学维度。即便对“诂”的理解,人们也主要侧重于“释”和“解”的解释层面上,当然这是我们能够从中理解到的应有之义,不过,这种理解似乎过于简单便捷,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它包含的其他维度的诠释学含义。
我们首先来看与所谓诗学阐释更为密切的“《诗》无达诂”。无论“诗”还是“诂”都具有语言的维度,《诗》自不待言是语言性的作品,而“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诂,训故言也,从言古声。”段玉裁注曰:“故言者,旧言也。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2页。这里的“诂”有三层重要的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故言”“旧言”,也就是传统传递下来的语言性存在,即指文字记载下来的文本或文本表达的内容,即语言性文本的“本义”,亦即董仲舒所言的“诂”,“诂”在这里应为名词,即指传统的语言性存在及其意义。在《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训诂笔记上·训诂学定义及训诂名称》中,黄侃写道:“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①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81页。这里的“诂”被释义为“故”,即“本义”,这是“诂”所具有的最根本的含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古代传递下来的语言性存在及其所蕴含的原本意义。因此,“诂”首先是指一种语言性的存在物,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文本以及文本表达的东西。“诂”的第二层意思是解释,作“动词”,这是今天许多论者重点关注的含义。《尔雅·释诂》载邢昺疏云:“释,解也;诂,古也;古今异言,解之使人知也,释言则释诂之别。”②邢昺:《尔雅注疏》,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68页。这里不仅强调“诂”作为“故言”“旧言”的传统性语言存在,而且强调“解”与“释”互释,并突出“古今异言”的差异性,其意是古代的、传统的语言表达与今天的、现代的语言表达不一样,古代的、传统的语言文本难以为今天的、现代的人所直接理解,这就需要有人“解之”“释之”,从而使“故言”“旧言”能够为人们所理解,即用能够为今天的人所理解的语言来解释“故言”和“旧言”。用黄侃的话说,就是“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因此,“诂”包含“理解”和“解释”的意思。第三层意思是,“诂”可以视为理解和解释的一种结果,是在不同的空间或文化(“此地之语”)语境中,或者在不同时间里用不同的语言(“今时之语”)解释(“彼地”或“昔时”)语言的结果,即对“故言”“旧言”进行的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文化阐释。因此,“用语言解释语言”充分说明了文本的语言性和理解的语言性,也说明了无论“《诗》无达诂”中的《诗》还是“诂”,无论诂作为“故言”“旧言”还是作为解释活动或解释的结果,都是语言性的。没有语言,便没有作为理解对象的《诗》,也就没有作为理解和解释结果的“诂”。“语言与理解之间的本质关系首先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传统的本质是在语言的媒介中存在的,因此解释的首选对象是语言性的东西”。③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London:Continuum Publishing Group,2004,p.391。引文为本文作者译,下文同。正是这种用语言解释语言的活动,准确地说,正是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语言)文化语境中理解和解释语言性的历史文本(“故言”“旧言”)活动构成了文本与理解之间的诠释学关系。
其次,“《诗》无达诂”确实体现了一种理解的差异性和开放性。不同的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理解以及理解在不同语境中的运用,都必然会产生差异性。人们对某个文本的理解都带着他自己“今天”已有的“前理解”进入理解的事件中,都会根据他自己的前理解对所理解的文本做出他自己的解释,因此,黄侃所说的“用语言解释语言”便意味着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不同人必然会以不同的语言对“故言”做出不同的理解。用今天的语言解释古代流传下来的语言性文本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不仅包含着历史时间性的差异,也包含理解语境性的差异,即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所说的“时间距离”必然会导致理解上的差异性。唐孔颖达在对《毛诗·周南·关雎诂训传》正义时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④孔颖达:《毛诗正义》,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69页。而所谓“通”就是用“今言”释“古言”使人们能够有所理解。因此,“古今异言”便不仅仅是古代语言与今天的语言不同的问题,而且也是今天所做的理解与古代文本“故言”表达的东西有所不同的问题。陆宗达说:“‘诂’是解释‘异言’的。所谓‘异言’,就是同一事物因时代不同或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⑤陆宗达:《训诂简论》,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2—3页。显然,这里突出强调的是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在不同的时间或空间语境中必然存在差异性。“《诗》无达诂”表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诠释学情境中面对同样的《诗》,也会对它做出不同的理解,甚至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诗》做出不同方面的理解。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意味着人们可以从完整的四个方面对《诗》进行理解,也可以从其中的某个方面进行理解,甚至人们也可以不从这四个方面进行理解,而从另外的方面对它进行解释。因为,这不仅如明代竟陵派钟惺所说的“《诗》为活物”,而且作为时间性和历史性存在的理解者也是“活物”。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无达诂”无论作为语言性文本的《诗》,还是作为时间性和历史性存在的人对它的理解,都具有一种开放性,处在不同诠释学情境中的理解者对《诗》做出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从他的前理解出发所做的理解,而这种带着前理解所进行的对《诗》的理解必然具有其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限的理解,因而必须对他人的理解保持开放性。所谓“古今异言”,从诠释学的角度看,无论《诗》本身还是对《诗》的理解都具有“言不尽意”的开放性特征。因此,作为“解”和“释”的理解活动及其结果的“诂”,就很难对作为“故言”“旧言”做出如伽达默尔所说的“完全性把握”,①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p.391.而只能是一种差异性和开放性的理解,这就不可避免会出现董仲舒所说的“《诗》无达诂”现象。
再次,鉴于对《诗》等经典文本理解的这种开放性和差异性,董仲舒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过度诠释”,即“《诗》无达诂”这种“断章取义”的普遍现象,而不是像许多论者所认为的那样,董仲舒倡导“《诗》无达故”。董仲舒无疑充分肯定“《诗》无达诂”这种理解的差异性和开放性现象的普遍存在,但是,他的目的显然不是要放任这种现象,更重要的是把无论“《诗》无达诂”,还是“《易》无达占”和“《春秋》无达辞”这种现象作为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因此,他才紧接着说“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而这句话亦作“从变从义,一以奉天”。苏舆注:“本书(指《春秋繁露》)言奉天者,屡矣,《楚庄王》篇云‘奉天而法古’,《竹林》篇云‘上奉天施’,皆是。盖事若可贯,以义一其归;例所难拘,以变通其滞。两者兼从,而一以奉天为主。”②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94—95页。完整地看,“从变从义,一以奉天”并不像有学者所理解的那样,是对“《诗》无达诂”的一种补充,也并非完全是所谓的接受思想。有论者认为:“‘从变、从义、奉人’是对‘诗无达诂’的补充,说明接受思想的意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③张晶、刘璇:《中西文学接受思想的异曲同工——“诗无达诂”说与接受美学理论的比较》,《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2期。但是,董仲舒实际上要真正解决的是《诗》《易》和《春秋》等经典文本在人们理解和解释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过度差异性和开放性,即解决“赋诗断章,余取所求”这种“过度诠释”的问题。在董仲舒看来,针对“《诗》无达诂”等现象,既要重视“变”,不同的理解是存在的,这是理解事件中的事实性存在,否认这种“变”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变”,但在他看来“义”更为重要,因之“从义”,这里的“义”并非简单地指文本的“意义”,而应该指某种具有普遍性、超越性并最终具有某种约束性、规定性的东西。而“义”与“天”又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从变从义,一以奉天’虽以‘天’作为解释的终极准则,但其内涵却是社会层面的伦理,因为作为‘天’的现实化的‘义’,包含了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同时,由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现实化的‘义’也不变。这就意味着,‘义’所体现的伦理准则具有超越时代、超越民族的‘普适性’,它不会因为时间的延续、民族的流徙而发生变化”。④张金梅:《从变从义:儒家文化关键词的意义建构方式》,《中文论坛》2017年第2辑。因此,董仲舒尽管没有否认理解的开放性和差异性,但是他的根本目的是“从变”且“从义”,最终目的是统一思想,符合天道,即“一以奉天”。“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三致其意的是天的哲学和政治理论的建构,而‘诗无达诂’所滋长的歧义杂出——‘变’则尤其是需要用‘义’来限定的,由此董仲舒接下来即用‘一以奉人(天)’来归结……提出的‘诗’无达诂,解释者创造性地去解读他的文本则显然不是他所期望和预设的”。⑤张敏杰:《〈春秋繁露〉“诗无达诂”的历史语境及其理论内涵》,《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因此,董仲舒肯定“《诗》无达诂”的开放性、差异性和多样性,与“《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一样,最终的目的是使所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理解达到某种一致性,达到董仲舒所理解的“义”和“天”的某种确定性。故苏舆注曰:“盖事若可贯,以义一其归;例所难拘,以变通其滞。两者兼从,而一以奉天为主。”故而“从变从义”是为了在理解中达到某种一致性的“一”,而这种“一”的一致性的最终目的是“奉天”。应当说,这一点与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所强调的理解的开放性和解释的差异性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不仅仅是对董仲舒的误读,也是对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理论的误解。
最后,我们必须清楚,“《诗》无达诂”首先针对的不是《诗》作为文学文本的诗学阐释问题,而是针对“《诗》无达诂”这种理解的开放性和差异性的现象,而这种现象集中体现在“赋诗断章”和“断章取义”这个问题上,董仲舒同样要以“从变从义,一以奉天”的诠释原则来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知道,“赋诗断章”和“断章取义”是春秋时代和孔门用诗、引诗和言诗的一种普遍现象和文化传统,言诗的重点不在于“解诗”,而在于“用诗”,不在于作品的全部,而在于诗句的选择性运用;不在于所谓的审美鉴赏,而重在“语境性”的阐发。《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卢蒲癸“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诗》言志,而无需顾及《诗》之本义,如果这是针对个体的应用性理解而言的,那么,对于整体的“诗教”亦复如此,孔子所说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①朱熹集注:《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208页。这里也是重在“用诗”,而非“解诗”,重点在于《诗》所具有的政治和社会交往等实用功能。董仲舒肯定这一理解现象的普遍性,并承认任何理解的“诂”都无法达到作为“故言”的“诂”。但很显然,董仲舒的最终目的并非肯定“无达诂”“无达占”和“无达辞”这种理解的多义性和差异性现象,而是实现另一种“从变从义,一以奉天”的非文学性实践应用,即不是对作为文学文本的《诗》的理解,而是对《诗》作为文学本文的“经”的阐释。《诗经》在先秦称为《诗》,或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解《诗》即解《经》,而非现代意义上的解“诗”。段玉裁注曰:“故言者,旧言也。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孔颖达注曰“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所谓“通之使人知”就是通过理解和解释让人们明白和懂得其中之“义”,而所谓“释故言以教人”,是把对传统的语言性存在的理解和解释运用于对人的教化,因此,这不仅是理解和解释的过程,而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性应用过程。董仲舒解《经》的目的则是一种更高的运用,正如徐复观所说:“仲舒无达辞、无通辞之言,盖将救以书法言褒贬之穷。而更重要的则是他要突破文字的藩篱,以达到其借古喻今,由史以言天的目的。”②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4页。《诗》作为“经”的理解要求亦不例外,同样是以《诗》言天,为了“一以奉天”之用,这正是为何“《诗》无达诂”首先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诗学理解,而是“经”的解释和应用的原因所在。从哲学诠释学的角度讲,这种“应用”当然也是文学文本理解和解释的一部分。“我们不仅把理解和解释,而且把应用看作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我们认为应用与理解和解释一样是诠释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③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p.307.因为理解涉及把所理解的文本应用到理解者的当下情境的问题,因此,无论“《诗》无达诂”这种理解现象,还是董仲舒“从变从义,一以奉天”的诠释学解决都包含理解性应用或应用性理解的维度。
以上论述表明,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篇》中的这段话包含多维度的“诠释学”内涵,包含文本和理解的语言性、理解的开放性和差异性、理解的一致性和理解的实践应用性等诠释学维度,而不能仅仅从哲学诠释学的理解创造性和接受理论的阅读主动性来理解,更重要的是必须看到董仲舒说这段话的根本目的何在,才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诗》无达诂”等所具有的诠释学意义。
二、从“《诗》无达诂”的应用性理解到“诗无达诂”的诗学阐释
“《诗》无达诂”无疑具有多层面的诠释学含义,但它最初主要的是实践性的阐释应用,而并不关注《诗》的文学性本身。但是,它能够在阐释历史发展中转变为一种“诗无达诂”的理解,即从实践应用性的非文学理解转变为文学性的诗学阐释,无疑与《诗》本身是一种语言性的诗歌文本密切相关,同样与文学本身的发展和对文学自身的理解密切相关。当《诗》从“解经”转变为“解诗”之时,“《诗》无达诂”便必然会转向“诗无达诂”,而当诗作为文学本身的“文学的自觉时代”到来之时,中国古代文论家们从诗(文学)的角度阐释“《诗》无达诂”并使这个命题转变为“诗无达诂”便具有了可能性。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从春秋到董仲舒时代的“《诗》无达诂”的实践应用性阐释逐渐脱离“释故言以教人”的教化维度,钟惺所说的“《诗》为活物”实际上便变成了“诗为活物”,“《诗》无达诂”的实践应用性的阐释开放性和差异性,也就变成了“诗无达诂”的文学审美理解的开放性和差异性。
前面已经强调,我们不能单纯从接受理论来考察“《诗》无达诂”这个命题,而要从诠释学的角度来探讨,才能够较为完整地理解这个命题。早期的“《诗》无达诂”现象体现的实践应用性只是《诗》或“诗”理解和解释的其中一个维度,而不是其全部。论者们注意到了今文经学的衰落和古文经学的复兴导致了“《诗》无达诂”创造性接受和阐释的衰落,从理解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个角度看,这种理解并非没有道理。“自东汉以至北宋,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诗无达诂’的理论几成绝响”。①孙立:《“诗无达诂”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关系》,《学术研究》1993年第1期。其重要的原因在于东汉以来今文经学派的逐渐衰落,而古文经学派崛起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唐代经学诠释学“以一种诠释取代众说、以权威文本压制多元的作风不可能对文学接受没有影响,这一点我们从很少在文献中看到契近‘诗无达诂’多元理解取向的论说就能感觉到”。②李有光、董冰雪:《诗无定鹄——宋代诗学多元解释思想总论》,《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其中原因,正如清皮锡瑞《经学历史》所说:“唐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以此考试。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③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8页。显然,一种有确定性标准答案的《五经正义》的经学理解和科举考试制度所要求的解释,不可能是董仲舒曾经肯定的“《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也不再是“从变从义”,而只有“从义”而无“从变”,只有从“一”的一致性而无从“多”的差异性。尽管这里的“义”“一”可能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内涵,但是,它们追求某种确定性和一致性的解释却是显而易见的。由此,曾经风靡早期时代的“《诗》无达诂”倡导的“断章取义”“赋诗断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理解开放性和差异性“几成绝响”便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董仲舒“所闻”的“《诗》无达诂”,肯定的是他之前和他所在时代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不是他追求的《诗》之释诂的目的。他所谓的“从义”实际上所“从”者应为“从”《春秋》大义,或“从”六经大义,从“变”乃是次要的,或者说只是“权宜之举”。因此,后世论《诗》者倘若对《诗》的理解仍然贯彻董仲舒的“从变从义,一以奉天”的原则,“《诗》无达诂”这种开放性理解和差异性阐释行为,同样会在后来的发展中“几成绝响”,也难以真正成为诗学意义上的“《诗》无达诂”或“诗无达诂”,因为《诗》仍然是《经》,解《诗》仍然是解《经》,而不是解“诗”。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认识到,“文学的自觉”在从“解经”向“解诗”的转变过程中所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这个问题却被今天众多的“《诗》无达诂”论者严重忽视了。
随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到来,这种“从变从义,一以奉天”的经学理解并不符合《诗》作为一种“文学”的本性及其理解的开放性要求,把“活物”变成“死物”的经学阐释也必然会被抛弃。曹丕说“诗赋欲丽”,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刘勰说“情者文之经”等等,便充分体现一个时代对诗(文学)的崭新认识。鲁迅在评论曹丕的“诗赋欲丽”时写道:“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①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04页。郭绍虞说:“迨至魏、晋,始有专门论文之作,而且所论也有专重在纯文学者,盖已进至自觉的时期。”②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72页。在诗学阐释上,“文学的自觉时代”的人们与其穷经皓首发掘其微言大义,不如关注诗之为诗本身的问题。因此,一方面是今文经学的衰落,而另一方面是“文学的自觉”为魏晋至有宋一代对诗(文学)本身的关注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从而最终为“《诗》无达诂”的外在性阐释转向“诗无达诂”的内在性阐释创造了新的可能,诗(文学)的理解和解释不再需要今文经学,更不需要古文经学作为理论支撑。因此,只有文学本体的问题在历史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和理解,才有可能真正从文学角度理解《诗》并转变为对“诗”的解释,只有人们不再以“经”解“诗”,而是以诗(文学)解诗的时候,人们才能够从诗学而非“经学”的角度理解《诗》,故而单纯从今文经学或接受理论来论述“《诗》无达诂”这个命题,便难以真正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随着政局的动乱,儒学的衰微,玄学的勃兴,精神生产的专业化、集团化。文学主潮便发生了对先秦、两汉的反动。理论家们很少单独论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是把人的情感、思想、气质,总之整个精神世界强调出来,作为文学描写的对象。而对于文学艺术的内部的联系和审美规律的探求,也成了理论思维的主要内容。人们的文学观念的长足发展,不是表现在区分文笔,严为界说,更主要的是借助于道家、玄学、佛家哲学的思辨的方法和丰富的、义界精审的概念、范畴,在文学理论中,完整地提出了本体论,历史地继承了功用论,全面地概括出批评论,系统地创造了文体论,深刻地总结出创作论,具体地发展了变通论”。即便在政教中心论和审美中心论并存的唐宋时代,在诗歌理论中“审美中心论占了主流”,用“兴象”“意象”“意境”和“兴趣”等新的审美范畴,“对诗的本质、规律作出了更高、更抽象、更深刻的理论概括”。③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中国文学理论史》(一),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31—32页。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及其随之而来的对诗或文学自身问题的理解,在《诗》的经学解释向《诗》的诗学阐释这个转变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人们真正懂得了诗究竟为何物,否则解《诗》仍然是解《经》。
文学的诠释学活动并不是单一方面的解释活动,即不仅仅如许多论者在论及“《诗》无达诂”时所认为的只涉及理解的开放性和差异性,而且理应包含《诗》作为诗或作为文学本身的理解以及上面论述的实践应用性维度。“文学的自觉”带来了文学理解的自觉,只有理解了《诗》或“诗”为何是文学,对《诗》或文学作品的理解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的文学理解,“《诗》无达诂”的开放性和差异性才是真正成为“诗无达诂”,否则仍然会停留在经学解《诗》的实践性应用的功利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所说的这种相当于“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的自觉”以及关于文学本身的理论自觉,便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诗学或文学阐释过程。郑振铎在论述开元、天宝时代的诗歌特色时,用审美抒情的笔调写道:
开元、天宝时代,乃是所谓“唐诗”的黄金时代;虽只有短短四十三年(713—755),却展布了种种的诗坛的波澜壮阔的伟观,呈现了种种不同的独特的风格,这不单纯的变化百出的风格,便代表了开、元的这个诗的黄金的时代。在这里,有着飘逸若仙的诗篇,有着风致淡远的韵文,又有着健壮悲凉的作风。有着醉人的谵语,有着壮士的浩歌,有着隐逸者的闲咏,也有着寒士的苦吟。有着田园的闲逸,有着异国的情调,有着浓艳的闺情,也有着豪放的意绪。④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310页。
这一琳琅满目、风格多样、意趣丰赡的诗的海洋,让人们关注文学自身和阐释诗歌本身而不是以经解诗,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对诗本身的这种沉醉和关注同样是文学阐释极为重要的方面。有论者认为:“造成有唐一代文学多元解释思想匮乏的根本原因还在文学自身。”①李有光、董冰雪:《诗无定鹄——宋代诗学多元解释思想总论》。如果单纯从“《诗》无达诂”创造性接受角度看,这一判断没有什么问题。倘若从完整的文学诠释学活动来看,这种判断并不准确,因为它排除了文学解释理应具有的更重要的维度,即对诗或文学文本自身的理解。
在某种意义上,对诗或文学本身这个维度的理解类似于西方文学理论走过的重要历程,经历了作者中心论到文本中心论,然后才走向读者中心论。“人们可以把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全神贯注作者(浪漫主义和19世纪):完全关注文本(新批评);以及近年来明显关注读者的转向。奇怪的是,读者一直是这个三重奏中最弱势的,因为没有他或她,根本就没有文学文本。文学文本不只是存在于书架上:它们是只有在阅读实践中才能实现的意义过程。因为文学要发生,读者和作者一样重要”。②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Second edition,Malden,Oxford,Melbourne:Blackwell Publishing,1996,p.65.尽管我们不能把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学理解过程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做简单的对应性类比,但至少可以看到从关注文本转向关注读者的某种相似性,有了充分的文学自觉才能导致真正的文学接受和理解的自觉。由此,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诗品》对诗歌体式、诗歌风格、诗歌特征等等的文本特性的探讨,在中国诗学史上便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这是走向作为文学的诗的认识和真正的诗学阐释的必要环节,这些诗学专论对诗歌或文学本身问题的探讨,也并非与后来“诗无达诂”的诗学阐释了无关系。
前面已经论述过“《诗》无达诂”的语言性维度,如果从经学解释的角度看,就是用语言解释故言,从经学的角度解读《诗》,而随着“文学的自觉时代”到来,随着人们开始真正从文学角度理解诗这种语言性存在,“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哲学表达便转变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学理解。陆机说“恒患意不称物、言不逮意”,谢灵运说“但患言不尽意,万不写一耳”,刘勰说“文外重旨”,钟嵘说“文已尽而意有余”等等,这些关于诗本身的描述从诗的语言性存在上为理解的开放性和创造性开辟了广阔的诠释学空间。皎然言“文外之旨”,刘禹锡言“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司空图言“韵外之致”“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等等,这些诗学的理解从诗歌的本体存在上为理解的开放性和创造性开辟了诠释学宇宙。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在语言中,而且只有在语言中,我们才能遇到我们在世界中从未‘遇到’的东西,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些东西(而不仅仅是我们所意指的或我们对自己所知的东西)。”③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32页。诗歌或文学更是语言创造的世界,正是在这个由语言建构和开启的想象性世界中,人们才进入到另一个韵味无穷的意义时空,因此,语言不单是人类生存世界中的语言,而且也是人类表达世界及其意义的语言,而诗的语言在被称为诗的国度的中国文学中更具有典范的意义。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写道: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④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见李壮鹰主编:《中华古文论选注》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93—94页。
在这里,严羽固然是在论盛唐人对诗的审美追求和盛唐诗的艺术特征,固然也在以禅喻诗、以禅悟诗,但实际上更充分地体现了他对诗之为诗的根本特征的认识。从诗的题材或者诗人的才能到诗的意趣,从诗人的学识积累到诗之情理的语言表现,到诗的本质“吟咏情性”,到诗的根本特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再到诗的意象形态,直到诗歌语言开启的意义时空,构成了一种真正可以从“诗学”而不是“经学”来理解的诗意世界。这里的“意”不再是经学家们的“义”。从刘禹锡的“片言可以明百意”到司空图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再到严羽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等等,这种真正意义上的诗学理解,难道不是为后来以“诗”解《诗》或“诗无达诂”开辟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解的开放性、创造性和差异性诠释学空间吗?由此我们又何必汲汲于责备今文经学的衰落和魏晋至唐的关注诗歌本身而冷落了以经解《诗》的“《诗》无达诂”呢?“艺术的语言的独特标志便在于,单个艺术作品聚集成它自身,并表达从诠释学角度看属于所有事物的象征特征。与所有其他语言和非语言的传统相比,艺术作品对每一个特定的当下来说都是绝对的在场,并且它同时谨守诺言为每一个未来做准备”。①Hans-Georg Gadamer,The Gadamer Reader:A Bouquet of the Later Writings,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7,p.131.因此,文学和艺术的语言创造的意义世界向未来敞开,并对所有理解者来说都是一种绝对的在场。
“《诗》无达诂”在有宋一代再度出场和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一个诗学命题,固然与疑古思潮和禅学思想的出现和盛行有关,当然也与上面论述的充分自觉的诗学认识密切相关。如果说疑古思潮和禅学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仍是“《诗》无达诂”向“诗无达诂”转变的语境性理论动力,那么对诗歌本体的自觉意识则是这一转变的内在美学动力,正是二者的合力使“《诗》无达诂”成为了一种真正的诗学阐释。回到文本本身的诗歌解释已经出现,回到《诗》作为“诗”之经典文本的经学阐释在有宋一代也成为时尚。朱熹说:“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②朱熹:《朱子大全》,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809页。所谓“一切莫问,而唯文本本意是求”就是回到文本本身寻求文本的意义,而不是从外在强加给文本意义,即首先不是实践性的应用,而是对文本的解读,文本蕴含的意义就在文本之中,而非在文本之外。这种“唯文本本意是求”的诗学解释甚至不需要海德格尔的事实性诠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所说的“前理解”。这种看法与“文学的自觉时代”对“诗”的文学理解何其相似乃尔。由此,朱熹谈到时人对《诗》之解释时说:“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屈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之大害处。”③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77页。所谓“以《诗》说《诗》”,便是回到《诗》,这已经接近以“诗”解“诗”、以“诗”说《诗》。
一旦回到以“诗”解“《诗》”,以“经”解《诗》的诠释方法就会被抛弃,解释就回到了作为“诗本身”的《诗》,同时保留“《诗》无达诂”的诠释学意义,并使之变成了“诗无达诂”。杨时下面这段话便是充分的证明:
仲素问《诗》如何看?曰:《诗》极难卒说,大抵须要人体会,不在推寻文义。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者,情之所发也。今观是诗之言,则必先观是诗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则虽精穷文义,谓之不知诗可也。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孔子以为可与言《诗》。如此全要体会。何谓体会?且如《关雎》之诗,诗人以兴后妃之德盖如此也,须当想象雎鸠为何物,知雎鸠为挚而有别之禽;则又想象关关为何声,知关关之声为和而适;则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为幽闲远人之地。则知如是之禽,其鸣声如是,而又居幽闲远人之地,则后妃之德可以意晓矣。是之谓体会。惟体会得,故看诗有味,至于有味,则诗之用在我矣。④杨时:《龟山集》卷一二《语录三》,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31—232页。
杨时首先肯定《诗》作为语言性存在的“极难卒说”特征,理解的目的并不在于“推寻文义”,而在于“体会”,而这种所谓的“体会”又在于对文本即对《诗》本身的“阅读”。在这里,对《关雎》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近乎纯文本的“一切莫问”的想象性解读。其次,他突出强调《诗》本身的根本性质,即诗的语言在于表达情感,因此“观是诗之言,则必先观是诗之情如何”,而不再是“推寻文义”,准确地说不再推寻经学家们所谓的“大义”,“不知其情”便“不知其诗”。可以说,这里对所谓“诗”、所谓“情”的认识蕴含和体现了“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所有诗歌和诗学成果,而不单单是宋儒解经和禅学思想影响的结果。最后,杨时强调《诗》之“味”既是诗本身具有的“味”,也是对诗之“味”的理解,而这种“味”的表现,“味”的作用必须发生在“体会”中;所谓“诗之用在我”则集中突出作为接受者、理解者的“我”的诠释学能力。如果说杨时还在讲《诗》,那么罗大经则完全在说“诗”了。他对杜甫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的理解,便是地道的“诗无达诂”解释。在他看来,对诗的理解既可以是不同视角的理解,也可以是对文本不同内涵的把握,他把前者称为“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作甚么用”,意味着理解者总是从自身的“前理解”出发进行理解,并且理解总是一种“应用”。很显然,他这里所说的“诗”就是杜甫的作为文学的诗,而这里的“用”已完全不是早期“《诗》无达诂”“断章取义”的为我所用,而是一种真正的诗学阐释之用;他把后者称为“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则表明诗歌本身包含多方面的内涵,可以是诗中美景,可以是诗中理趣,也可以是诗中情感等等,而对诗的体会和理解如何,则最终“要胸次玲珑活络”。①罗大经:《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9页。在这里,诗歌本身的开放性和理解的开放性同时存在,开放性的文本与开放性的理解构成了真正的“诗无达诂”的诗学阐释,这种“《诗》极难卒说”的开放性和差异性理解便全然没有了以经解诗的味道。
这种诗学阐释一旦发生和实现便不再有返回的路,即便是论《诗》也必然是论“诗”了。明代钟惺《诗论》中的下面这段文字便是明证。他确实是在谈《诗》,但不是以“经”解《诗》,而是真正以“诗”解《诗》,这里的阐释已不再是任何经学派的理解,《诗》是“活物”的说法已成为真正的诗学阐释,并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诠释学内涵。
《诗》,活物也。游、夏以后,自汉至宋,无不说《诗》者。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以说《诗》。其皆可以说《诗》者,即在不必皆有当于《诗》之中。非说《诗》者之能如是,而《诗》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且读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诗》,列国盟会聘享之所赋《诗》,与韩氏之所传者,其事其文其义,不有与《诗》之本事本文本义绝不相蒙,而引之、赋之、传之者乎?既引之,既赋之,既传之,又觉与《诗》之事、之文、之义未尝不合也。其何故也?夫《诗》,取断章者也。断之于彼,而无损于此。此无所予,而彼取之。说《诗》者盈天下,达于后世,屡迁数变,而《诗》不知,而《诗》固已明矣,而《诗》固已行矣。今或是汉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汉,非汉与宋而是己说,则是其意以为《诗》之指归,尽于汉与宋与己说也。岂不隘且固哉?
……夫以予一人心目,而前后已不可强同矣。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何不能新之有?盖《诗》之为物能使人至此,而予亦不自知,乃欲使宋之不异于汉,汉之不异于游、夏,游、夏之说《诗》不异于作《诗》者,不几于刻舟而守株乎!故说《诗》者散为万,而《诗》之体自一,执其一而《诗》之用且万。噫!此《诗》之所以为经也。②钟惺著,李先耕、崔重庆标校:《隐秀轩集》卷二三《诗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91—393、392页。③ 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6页。
这段话的重要意义在于用以论《诗》的方式讨论《诗》的理解问题,实际上也是在用以论《诗》的方式论述“诗”的理解问题。钟惺从对《诗》的历代理解证明《诗》是“活物”,“所谓‘活物’,是将《诗经》看作一个灵活多变的开放性文本,一个具有派生能力和再生能力的文本,它超越了僵死的意义,在不断的理解与解释中获得新的生命”。③对于这种“活物”,每一代人都会做出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都具有其合理性,都是对《诗》的不同理解,这便证明了《诗》并没有限定哪一种理解是绝对合理的。正因为《诗》是“活物”,它才面向不同时代不同理解者保持开放,而每一个试图理解它的人也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它,所谓“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以说《诗》”,就同时强调了《诗》作为文学文本的开放性和接受者理解的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理解便是真正的“诗无达诂”。
在上面的引文中,我以为最具有诠释学意义的不是钟惺强调的理解的开放性和差异性,这固然是诠释学理解非常重要的方面,而是他认识到文学文本的同一性和文学理解的差异性相统一的诠释学问题。钟惺说:“故说《诗》者散为万,而《诗》之体自一,执其一而《诗》之用且万。”这句总结性的话具有特别重要的诠释学含义。他不但强调《诗》为“活物”,即作为诗歌(文学)作品的《诗》具有开放性,而且强调“说《诗》者散为万”的理解者的多样性,同时也强调“《诗》之体为一”的诗歌文本的同一性。换言之,在他看来,作为文学作品的《诗》始终作为“诗”而存在,作为“万”的不同理解者必然会对相同的文本《诗》做出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理解,但是,不管对《诗》有多么不同的理解,都是来自对同一文本《诗》的理解,否则便不是对《诗》的理解。由此,“执其一而《诗》之用且万”的文学阐释,不仅肯定理解的开放性和差异性,而且坚持《诗》作为文学作品的“同一性”。正如伽达默尔在谈到诗歌的理解时写道的:“诗歌文本以自身的权利规定它本身的所有重复和言语行为。任何言说都不可能完全满足诗的文本所规定的内容。一首诗的文本行使着一种规范性的功能,它既不是指回原初的表达,也不是指回言说者的意图,而似乎是源于它自身的东西,因此,在成功的喜悦中,一首诗甚至使作者感到惊讶和不知所措。”①Hans-Georg Gadamer,The Gadamer Reader:A Bouquet of the Later Writings,p.181.换言之,诗歌作品作为一个文本始终以其自律性存在站立在那儿,面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语境、拥有不同“前理解”的人言说,即严羽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而不同的理解者带着他的“前理解”进入诗歌(文学作品)敞开的世界中,并对同一个作品做出不同的理解,即王夫之所谓的“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而这二者的相互作用便构成了真正的“诗无达诂”的诠释学命题。钟惺这里所说的“执其一而《诗》之用且万”的“一”和“万”,与董仲舒的“一以奉天”和“《诗》无达诂”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因为在钟惺这里已经转变为真正的诗学阐释,“《诗》无达诂”的经学阐释真正成为了“诗无达诂”的诗学阐释。
三、“《诗》无达诂”或“诗无达诂”与诠释学理解之比较
前面的论述表明,从董仲舒肯定“《诗》无达诂”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经由中国古代文学自觉时代对诗(文学)的文体和审美认识,最后在诗学的理解语境中实现了从“《诗》无达诂”的实践应用性阐释向“诗无达诂”的审美性诗学阐释转变。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诠释学问题。从今天的理论语境来看,这一命题在诸多方面“暗合”现代西方诠释学和接受理论的某些理论洞见。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对西方现代诠释学和接受理论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我们回过头来反观中国传统的诗学或文学理论时,便发现在中西方理论之间有不少可以进行相互比较和相互阐释的层面。我们确实看到,在“《诗》无达诂”或“诗无达诂”这个命题的理解上,论者们大多借鉴或运用诠释学,特别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以及耀斯等的接受理论进行相互比较的阐释。而在这两者的相互阐释中,论者又更多地集中在理解的创造性、开放性和差异性方面,力图在两者之间寻找相似之处,而忽视了它们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差异。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诗》无达诂”这一命题与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有更密切的关联,鉴于篇幅有限,本文就这两者之间的相同和差异进行简要比较。
确实,两者之间存在暗合的诠释学维度,这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诗》无达诂”或“诗无达诂”和哲学诠释学都突出强调理解的语言性。无论在“《诗》无达诂”还是在后来演变的“诗无达诂”中的《诗》或“诗”,都是一种语言性的存在,无论“诂”作为“故言”“旧言”还是作为理解活动或解释的结果,无疑都是语言性的。没有作为语言性存在的《诗》或“诗”,便没有作为理解对象的诗歌文本,因而就不可能有作为阐释结果的“诂”。这便是黄侃所说的“用语言解释语言”,体现在“诗无达诂”这个命题上便是解释者用语言解释《诗》或“诗”的语言,这种语言性既属于被理解的对象,属于理解的过程,也属于理解者,因此,伽达默尔也把这种相互作用称为理解的语言事件。“意义的表达首先采取语言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以某种陌生的语言所说的内容传达给另一个人理解的艺术,诠释学以赫耳墨斯命名并非毫无理由,他是把神性信息传递给人类的解释者。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诠释学’这个词的起源,我们这里处理的就是一个语言事件,那么很清楚,是一个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因此涉及两种语言的关系”。①Hans-Georg Gadamer,The Gadamer Reader:A Bouquet of the Later Writings,p.127.伽达默尔同样强调了意义表达的语言性、理解过程和理解结果的语言性,而整个理解过程则是一个语言的事件。其次,两者都包含了诠释学理解的应用性,“《诗》无达诂”在先秦两汉时期的“断章取义”不是一种诗学的阐释,而是一种外在性的阐释应用,只有在“文学的自觉”以及文学之为文学的理论自觉后,才转变为一种诗学的阐释,如罗大经所说的“在人如何看,在人把作甚么用”这样的理解,便成了一种诗学的阐释应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认为,理解和解释本身就包含着应用,“所有的阅读都涉及到应用,所以一个人阅读一个文本时他本身就是他所领悟的意义的一部分。他属于他正在阅读的文本”。②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p.335.不同的人从自己的前理解出发对文本做出不同的理解,并应用于他自己的情境,“《诗》无达诂”应用于经学的理解,而“诗无达诂”则应用于诗学的理解。再次,两者都不关心作者的意图,而是集中于文本,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严重忽视。“《诗》无达诂”就是对无作者作品的理解和阐释,即“只有诗,无诗人”,根本不存在根据作者意图进行理解的问题,正如清代劳孝舆在《春秋诗话》中所说:“风诗之变,多春秋间人之所作……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钦欤?盖当时只有诗,无诗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诗;彼人可赓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诗无定指。”③董运庭:《春秋诗话笺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9页。无论是早期还是后来对《诗》的理解都是基于作为诗歌文本的“诗”的阐释,即便是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之后的中国诗学阐释也很少关注作者的意图,所谓“人无定诗,诗无定指”所具有的理解开放性,正是由“诗”本身的存在而非作者的意图所决定的。这一点无疑与哲学诠释学具有相似之处。“在书写中被固定下来的东西已经脱离了它的起源和作者的偶然性,并使它自己自由地面向新的关系。规范性概念,如作者的意义或原来读者的理解,实际上只代表了一个在理解中不时被填满的空白”。④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p.397.文本以自身的存在向所有接受和理解它的人言说,伽达默尔认为我们的理解不会完全受作者意图的约束,而是倾听文本的言说并与作品进行开放性的对话,从而产生一种新的诠释学关系。最后,两者都强调了理解的开放性。“《诗》无达诂”或“诗无达诂”都肯定和倡导理解的开放性和差异性,“赋诗言志”和“断章取义”是一种开放性,甚至是一种可以不顾诗歌完整性的开放性,即便是董仲舒所要求的“从变从义”也包含着理解开放性的维度,而罗大经的“在人如何看,在人把作甚么用”和刘辰翁“观诗各随所得,别自有用”,以及钟惺的“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以说《诗》”等等,则把(诗歌)文学理解的开放性、创造性和差异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伽达默尔说:“文本的意义超越作者本身,这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理解不是一种复制活动,而且始终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如果我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理解,这就够了。”⑤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p.26.可以说,这种创造性的理解活动和只要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理解就够了的诠释学观点,确实暗合了《诗》或“诗”“无达诂”的理解和阐释方式。
两者之间这些“暗合”之处表明人类理解的某种相通之处和某种普遍性,但从理论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非常明显,不同的方面也很多。在此只罗列几个方面,篇幅有限不做深入阐述。第一,“《诗》无达诂”或“诗无达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诗歌的一种现象阐释,它意识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理解现象,尽管中国古代有关于这方面的许多言论,但很难说已经成为了一种理论,更不用说理论体系了。现代西方诠释学则是一种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哲学理论,有支撑其理论体系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和逻辑,有其相对完整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有其逻辑严密的思考问题和探讨问题的方法,有其相互关联而又相互竞争的思想流派,①例如Stanley E.Porter&Jason C.Robinson在《诠释学:理解理论导论》一书中说,至少有六种截然不同的诠释学趋势:浪漫主义诠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诠释学、哲学诠释学、批判诠释学、结构诠释学以及后结构(解构)诠释学。该书除了重点论述这六种的诠释学外,还考察了诠释学现象学、辩证神学和释义学、神学诠释学和文学诠释学。参见Stanley E.Porter&Jason C.Robinson,Hermeneutics:An Introduction to Interpretive Theory,Grand Rapids: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2011。这充分说明西方现代诠释学理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诗》无达诂”命题只是与某种诠释学或某些诠释学的层面有“暗合”之处,不可做简单的类比或随意的挪用。这是单纯的“《诗》无达诂”现象或命题远远不及的。这是根本性的差异,“中国古人的意见往往不成系统,只是在批评的灵感突然彻悟的时刻讲出来的片言只语,然而这些精辟见解往往义蕴深厚,并不因为零碎而减少其理论价值。我们作出这样的比较,并不是说中国古人早已提出了现代西方的理论,只是指出两者之间十分相近。然而相近并不是相等,在仔细审视之下,两者的差异会更明显而不容忽视”。②张隆溪:《诗无达诂》,《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诠释学或诗学(文学)诠释学正是有待于中国学者深入研究和认真阐发的重要课题。第二,“《诗》无达诂”与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理论都突出理解的开放性和差异性,但前者基本忽视了文本在理解中的规定性,而哲学诠释学,甚至包括接受理论在提出理解的创造性和开放性的同时,都强调文本对理解的规定性,与“断章取义”“赋诗言志”和“各随所得”有很大的不同。“在作者、作品和公众这个三角关系中,读者并不是被动的,也不是一连串的反应,而它本身就是历史能量的构成。没有读者的积极参与,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中介过程,作品才能进入一种持续性的不断变化的经验视域”。③Hans Robert Jauss,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p.19.罗伯特·耀斯的接受美学固然突出了读者的创造性作用,但并没有完全忽视文本对理解开放性的规定作用。伽达默尔始终强调读者在理解过程中必须倾听文本的声音。有人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所提出的‘诗无达诂’的文学释义方式对解释者与解释对象之间关系的理解比起伽达默尔的理解来要显得全面得多,也辩证得多。”④邓新华:《比较视野中的中西方文学释义理论》,《国外文学》2001年第2期。这种判断恐怕是很不周全的,甚至是没有根据的。第三,在理解、解释和应用三位一体构成的诠释学事件中,“《诗》无达诂”更多强调的是实践性应用,而这种应用又更多地突出政治伦理方面的教化作用,而忽视了对《诗》本身的本文理解和解释,即便宋明之后的诗学阐释也大多突出“各随所得”,而缺乏完整过程的诗学阐释过程。相反,无论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的方法论诠释学,还是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诠释学,抑或耀斯等的接受美学,甚至德里达的解构理论,都有一套构成诠释学活动的完整“技艺”。
综上所论,“《诗》无达诂”或“诗无达诂”确实是中国传统中的一个重要诠释学现象或诠释学命题,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也体现了从实践应用性经学阐释向文学审美性诗学阐释的转变,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阐释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与西方现代诠释学确有某些“暗合之处”,也有诸多可以相互阐释的维度,但西方诠释学有其自身的传统和逻辑,有非常不同的理解和阐释问题的概念体系。在进行相互比较和阐释时,我们既要深入理解“《诗》无达诂”的中国阐释传统,也应较为完整地把握西方诠释学的问题和逻辑,以避免盲目的对应比较、简单的优劣评价、随心所欲的挪用以及缺乏学理的判断,从而能够让我们在差异性的中西比较阐释中实现某种诠释学的“视域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