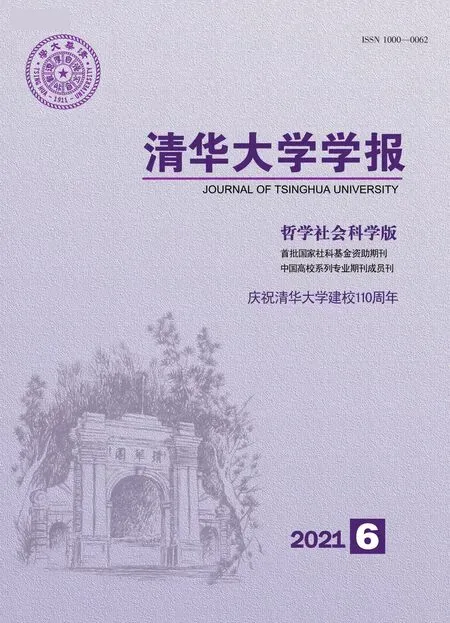神圣地景的兴代:东汉末年疫病下都城文学的发展与文集编纂
吴沂澐
文人如何看待都城与记录时事?都城又如何被写入文学作品中?此为本文最初的问题意识。审视都城景观写入文学作品中所产生的意义,可以发现无论是虚构的场景,或是实际存在的地理景点,已然超越了地理意义,而指向文化意义——都城不再只是地理坐标,而是代表帝国政治、文化的最高影响力,是界定社会文化的符码。文人书写都城景观,亦已跳脱实际建筑物的限制,寓目所及的风景皆是都城文学书写的范畴。他们不只书写地景,更记叙在地景中的活动。而都城文学不同于其他城市或地方书写,正在于这些景观镶嵌在特定的地理——都城之中,这是由政治与文化权威性共构而生的神圣空间,故谓之“神圣地景”。
都城文学不只是记存都城和人文的互动经验,也涉及集体认同与文化生成。文人通过书写都城景观凝练文化共识,强化权力认同,以利团结。从汉代以来,都城文学基本围绕着与帝王有关的景观进行书写,如宫室、田猎,可以说都城(地)、帝王(人)、景观(事)共构为都城文学。都城文学应是围绕帝王气象进行的书写,但在建安时期,许昌显然不能焕发都城文学的写作。建安元年(196),曹操挟天子迁都许昌,两京代表的汉代大一统意义随即中断。而许昌虽是天子所在,却鲜少彰显、匹配帝国威权,期间虽有杨修作《许昌宫赋》,但从现存佚文“入乎新宫”一句来看,似是描写许都宫殿兴建前后之事,且亦无其他共作。此与初平元年(190)迁都长安之时,诸臣作辞共贺返还旧京,通过书写西京共忆昔日大汉昌盛之景,不可同语。反观建安九年,曹操破袁尚后积极营建邺城,一方面藉由兴建新的建筑物复制象征地景,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的游览活动输入都城意义。后者显然是通过文人书写赋予“地景”以都城的意义,从而建构邺城的神圣性、权威性。可以发现,建安时期的邺城虽非名义上的都城,却被赋予“神圣地景”的实质意义。
基于这样的想法,本文聚焦于建安元年迁都许昌以迄黄初元年(220)汉代正式覆灭,此二十四年间神圣地景的兴代问题。曹操既挟天子迁都许昌,为何又营建邺城?邺城如何被刻意制造与再现成为神圣地景?当书写神圣地景的文人因疫病而亡殁,“都城文学”是否中辍?“都城意义”又该如何延续?皆为本文欲论究的问题。
一、邺城作为“代位”的神圣地景
建安初年,曹操挟汉献帝迁都许昌,虽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手段,但考虑两京残破,又欲隐藏其“篡汉”之意,故不能在原本象征汉朝统治的两京上重写成为曹氏的权力象征,此意谓曹操必须寻找新的地景以重新建立新势力。于是,他先是割裂长安的大一统意义,迁都至许昌。其次,他将都城的权力性转移至邺城,剥离天子与都城的关系,使许昌虽具有“都城”之名,实质上与其他城市无异。建安九年,曹操破袁尚后积极营建邺城,企图透过政治、文化权力的集中,使邺城成为实质意义的都城。其具体做法有二:一是凝聚天下才士,重塑权力认同;二是建造模仿帝王别苑的新地景,并于其中行“天子之事”。
据《三国志》卷一五《梁习传》载梁习任并州刺史后,即有计划地削减地方势力,或举荐地方豪族入邺为官,或征召其家丁从军,当“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①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69页。建安二十年,“后(杜)袭领丞相长史,随太祖到汉中讨张鲁。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②陈寿:《三国志》,第666页。此事与《三国志》卷一一《胡昭传》注引《魏略》所载之事相合:“建安十六年,三辅乱,(扈累)又随正方南入汉中。汉中坏,正方入蜀,累与相失,随徙民诣邺,遭疾疫丧其妇。”③陈寿:《三国志》,第362页。扈累所遇的“徙民”即杜袭迁移至邺城的汉中百姓。曹操将各地降臣、遗民聚集到邺城,除是充实邺城人口,④据《三国志》卷一《武帝本纪》载建安九年曹操围攻邺城,“毁土山、地道,作围堑,决漳水灌城;城中饿死者过半”。见陈寿:《三国志》,第25页。更是为了重新编纳分裂的地方势力,防止割据势力复萌,控制地方秩序。
同时,曹操亦将部将家属留置邺城。《三国志》卷一八《臧霸传》:“太祖破袁谭于南皮,(臧)霸等会贺。霸因求遣弟子及诸将父兄家属诣邺,太祖曰:‘诸君忠孝,岂复在是!昔萧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纯焚室舆榇以从,而光武不逆,吾将何以易之哉!’”⑤陈寿:《三国志》,第537页。又同卷《孙观传》注引《魏书》曰:“(孙观)与太祖会南皮,遣子弟入居邺,拜观偏将军,迁青州刺史。”⑥陈寿:《三国志》,第539页。曹操诛袁谭事在建安十年,故二事当在此年。另,建安十二年,田畴吊祭袁尚后,为防曹操疑心,“畴尽将其家属及宗人三百余家居邺”。⑦陈寿:《三国志》,第343页。再据《三国志》卷一八《李典传》载:“‘(李)典驽怯功微,而爵宠过厚,诚宜举宗陈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实郊遂之内,以制四方,非慕纯也’。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太祖嘉之,迁破虏将军。”⑧陈寿:《三国志》,第534页。李典迁破虏将军后,与张辽、乐进屯兵合肥,建安二十年与张辽共破孙权,故徙部曲宗族一事当在建安二十年以前。为了表示忠诚,这些将士家属或不得已或自愿移居邺城,已然暗示着他们近乎人质的身份。
除了地方豪绅、将士家眷外,曹操亦积极招抚文人入邺,建安九年陈琳、阮瑀、路粹皆入邺为祭酒;建安十三年王粲自荆州入邺任丞相掾。另外,曹操接受郭嘉的建议,征辟青州、冀州、幽州等地名士入邺为官,“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渐臣使之,以为省事援属。皆嘉之谋也”。⑨陈寿:《三国志》,第434页。建安十五年曹操下《求贤令》,表明欲天下贤士皆入彀中的企图。不只屯兵、移民、招贤,曹操更以邺城为中心,重整官吏制度。《三国志》卷一《武帝本纪》记:“(建安十八年)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天子聘公三女为贵人,少者待年于国。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为东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①陈寿:《三国志》,第42页。曹操有计划地将北方势力归并入邺城,扩充人力,以邺城为“王业之基”,号令百官,“彬彬之盛,大备于时”,昭示汉末政治、文化的中心发生转移,邺城取代“都城”许昌,成为“代位”的神圣地景。
此外,为了将都城意义转移叠置于邺城,曹操刻意复制地景以承载意义,于是仿造帝王别苑建造西园及三台,呼唤文化记忆。《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记建安十五年“冬,作铜爵台”。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五引《邺都故事》云:“汉献帝建安十五年筑铜雀台,十八年筑金虎台,十九年作冰井台。”②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06页。曹操建此三台,一是军事守备目的,③黄永年指出:“案在此冷兵器的时代,战术上不会有多大变化,因此很可疑从上面所说的弩台等来推测三台的守御作用,当然此三台之高大雄伟绝非彼弩台之可比拟。此外,三台之多窖藏。包括窖藏粟、盐、冰、石炭及财宝。三台之间又可互相交通,也都更有利于长期的固守。”见氏著:《邺城与三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一是设置一稳定的“骋才”场域,模仿汉代都城文学的活动形式,引领文人进行写作。汉代的都城文学基本围绕帝王、宫廷展开,武帝时常召集文人集体作赋,如贺皇太子生而诏枚皋、东方朔等作赋祝颂。又《三辅黄图》卷五《台榭》记武帝元鼎二年(前115)春,始建柏梁台,落成后“帝尝置酒其上,诏群臣和诗,能七言诗者乃得上”。④郦道元注:《水经注疏》卷一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97页。而铜雀台建成时,曹操亦仿效之,《三国志》卷一九《陈思王植传》:“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⑤陈寿:《三国志》,第557页。曹丕《登台赋》序亦提到:“建安十七年春,上游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⑥曹丕著,夏传才、唐绍忠校注:《曹丕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0页。铜雀台及西园的建成,引发此种“同题共作”的写作形式,便是延续汉代帝王召集文人写作以烘托帝王气象的习惯。
然而,既要成为“代位的都城”,只是召集文人群体、模仿皇家建筑和帝王形制实为不足,关键在于神圣地景的认同。这些文人大部分并非长期居住邺城,他们各自带着“地方”的文化印记,或来自两京,或来自荆楚,其人“择曹氏而事”的原因与期待亦不尽相同,或依附强权,或建功立业。唯有对空间具有“同是”的情感,方能自觉归属进新的家国关系,邺城才能够凝聚成“一个国家”的力量。而曹氏父子正是利用这些文人的书写,一方面驯化这群“外来者”,一方面藉此界定邺城的都城意义。曹操刻意复制的地景成为邺下文人聚集游冶之地,也为公诗、散文、歌赋等文学创作活动提供了平台和题材。郑毓瑜指出:“建安文士的侍作品,莫不以彼此共同体验、享受的游戏逍遥、极欢纵意为篇章的主题重心,而与立足于君臣关系、着眼于雄图大业的两汉赋作迥异远别。”⑦郑毓瑜:《六朝情境美学综论》,台北:学生书局,1994年,第178页。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别苑台池并非人人都可以进入,是以排他性塑造的地景,将他者、他地排除在外。曹植《节游赋》便提到:“览宫宇之显丽,实大人之攸居。建三台于前处,飘飞陛以凌虚。连云阁以远径,营观榭于城隅。亢高轩以迥挑,缘云霓而结疏。仰西岳之崧岑,临漳滏之清渠。观靡靡而无终,何渺渺而难殊。亮灵后之所处,非吾人之所庐。”⑧曹植著,朱绪曾考异,丁晏铨评,杨焄点校:《曹植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页。地景的排他性也延续到空间之中的人群,空间的排他性,使此地异于彼处;人群的排他性,使该群体的文化身份高于他者。而掌握、控制空间与群体“排他性”的权力者正是曹操。易言之,铜雀台既是一个被创造的文化空间,也是被选择的政治空间。因此,于其中创作的公诗,正是反映曹氏父子于此地绝对权力的象征。
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曹植为平原侯,与建安七子同聚邺下,①时孔融已逝,仅存六子。不仅是邺下文学活跃的起点,也开启以“游”为主体精神的集会形态。西园游、南皮游留下大量的五言诗作,他们“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②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73页。游宴活动本身并不具有象征意义,而是经由文人间的互动,赋予了空间与行为意义。曹氏父子藉由游宴号召文人群体同题作诗,本身即具有“应诏赋诗”的权力意义。王粲《公》:
昊天降丰泽,百卉挺葳蕤。凉风撤蒸暑,清云却炎晖。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榱。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乐,但诉杯行迟。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见眷良不翅,守分岂能违。古人有遗言,君子福所绥。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③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83页。
二、都城文学的建立与中辍
汉代虽已形成一“文学侍从”群体,但与邺下文人仍然有别。汉代文人迥异于以经术、德行入仕的典型士人,即便身负官职,仍遭讥嘲为俳优之徒,受诏作赋亦被视为“淫靡不急”②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四《王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29页。之事,故文人间不会自觉地组成一文学群体进行创作,而多以“待诏”身份,被动地等待君王“捡选”进行文学活动。且其人的政治地位仰赖于帝王的趣向,因此文学创作主题多围绕于帝王、政治,他们只是大一统意识下的附庸者,致使其创作内容及理论的发展受局限。不同于汉代作为文娱消费的文士,汇聚在曹氏身边的“文学侍从”,大多亲身参与政治和征戍活动。《三国志》卷二一《阮瑀传》载:“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③陈寿:《三国志》,第600页。王粲、刘桢、徐干亦留存行军、咏史之作。他们虽不擅于攻伐治守,但书檄往来、礼乐建设、声威宣扬及树立正统形象却多赖文人之笔,文人亦透过文事,展现其功业理想与忧时之思。当文人普遍获得拔擢而逐渐在政治中取得一席之地,经学在政治、社会文化的独尊地位开始松动,文学进入文化结构,不再是“雕虫小技”,而是可以展现才学、表达思想的流行文化;文人不再是“俳优之流”,而是具有一定政治势力与社会地位的群体。
入邺后,曹氏父子有意识地制造三台(空间)与邺下文人(群体)的排他性,此正是为了凸显文化及群体的“他者化”情况,即区分以建安七子为主的“都城文学”与“其他书写”。除了前举表述特殊君臣关系的公诗外,在以三曹七子为主的“高会”场合,相互唱和的同题赋中亦可见七子刻意建构的权力认同,如《柳赋》为曹丕以建安五年所植柳树为题,感物是人非而作。与之共作的王粲《柳赋》开头即言:“昔我君之定武,致天届而徂征。元子从而辅君,植佳木于兹庭。”④余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第126页。其引《诗经·宫》:“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天之届,于牧之野。”⑤高亨注:《诗经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17—518页。将曹氏父子出征袁绍之事,比于文武伐商,显然将曹氏父子肃清北方的行为,视作“顺应天命”,而非臣子平乱以“彰汉德”“显天子”。陈琳亦和之曰:“穆穆天子,亶圣聪兮。德音允塞,民所望兮。宜尔嘉树,配甘棠兮。”⑥余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第57页。同样将曹氏父子视为“救斯民之绝命”⑦余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第57页。的“皇天之子”,皆一致地形塑曹氏“王权”的正当性。
“被选择”的建安七子成为都城文化的标识,建安七子的文学作品定义了建安文学,形成明确的文学、文化排他性。曹氏父子特意标举七子并非为了加深文化的差异性,反而是为了弭平文化异质性。身为文化转移的作用者,七子的书写在未被选择的他者间,逐渐成为一种“衡文论艺”的指标,促使文人自觉关注七子写作。此种自觉不只是碎片式地表现在谈话评议上,文人间往来书信也常评骘其人其作,曹植《与杨祖德书》提到: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绝迹,一举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者也,前有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①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四二,第593页。
曹植显然意识到不只“自己”关注七子,“他人”也正在“观看”七子之文。这种集体趋向使得文人在有意无意之间,以七子为写作范式或评议标准,故曹植自言“畏后世之嗤余”而不能妄叹,②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四二,第593页。并极力称赞丁廙文章。曹植之言或有其政治考量与文学主张,但也说明当时俨然形成以七子为主的新写作形式。特别是公诗的内容,反复陈述“主人”“公子”爱客而欲使天下归心的企图,巩固以曹操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认同结构,将对邺城的认同扩大为“王权”的认同,使邺城重塑为权力认同的空间,并成为一股意识形态。
都城文学的建构,除了政治认同以外,还涉及其他文化如何看待都城文学的方式。曹氏父子将七子以外的文人“他者化”的行为,使三曹七子的文学自然形成一种边界,若欲藉由文才进入政治结构,则文章的内容表意便不能“滞外”,必须贴近七子的文风,符合表述邺城的“都城意义”,文化差异遂在“入内”的过程中逐渐消融。但邺城的“都城文学”并非仅凭曹氏霸权而确立,建安七子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影响力,正因其人不止是“侍”而已,③《文选》卷二○曹植《公诗》下五臣注云:“公者,臣下在公家侍也。”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第283页。即便该群体形成仍带有依附强权的性质,但其文学写作不仅有“宴”,更具备“游”的个人精神发挥。这些围绕着“游”与“宴”展开的文学作品,“游”象征士人不受现实束缚,精神自由解放的心灵状态;“宴”则是其游园酣饮的活动行为。游园与游心共构成为诗作的主体,使其诗文内容不是只有强权护翼下的逍遥美好,除了目的性的活动记述,更面向社会现实,兼具悲壮苍凉的时代情绪及浮生若寄的情感抒发。《文心雕龙·明诗》曰: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④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66—67页。
贯彻“游”思的赋作,表现情志深远、梗概多气的风格特色,突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使文人既符合群体中的“官属”身份,又能突出“文人”本色。虽然,邺下文人群体的形成到七子俱逝不过六年(建安十六年至二十二年),⑤《三国志·魏书》卷二一《王粲传》载:“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符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显示邺下文学活动的展开,主要围绕于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共聚邺城之时,故以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曹植为平原侯为始。但邺下文人群体的形成,代表文人可藉由文学获得与儒士相比肩的政治地位,文人不再是政权的附庸者,而是引导政治、文化认同的作用者,是使天下文人望风附归的引领性存在。
邺下文人是移植都城意义过程中重要的作用者,被塑造的神圣地景成为其人表意场域,意识形态亦因地景的固有而存在。然而,疫病却打破此平衡。东汉末年连续爆发多场瘟疫。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即遇大疫,据《三国志》卷一《武帝本纪》载:“(十三年)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①陈寿:《三国志》,第31页。《蜀志》卷二《先主传》:“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②陈寿:《三国志》,第878页。《吴志》卷二《孙权传》:“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③陈寿:《三国志》,第1118页。除却战争的损失,曹操军队亦因这次大疫伤亡惨重。又《三国志》卷二《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云:
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雕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④陈寿:《三国志》,第88页。
曹丕立为魏太子时值建安二十二年,可知此“疫疠”,即《后汉书》中《孝献帝纪》及《五行志》所载献帝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这场瘟疫丧亡者甚众,曹植《说疫气》言:“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⑤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52页。曹植的叙述虽带有文学夸饰的色彩,但也反映当时瘟疫的严重程度,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因此亡故。曹植特别指出病者多是穷苦人家,高门大户少有染疫。但从曹丕自言“亲故多离其灾”,便知官宦亦不能幸免。《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载:
(阮)瑀以(建安)十七年卒,干、琳、玚、桢二十二年卒。(魏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⑥陈寿:《三国志》,第602页。
《魏书》强调“疫疠数起”,显示疫情范围不只限于邺城一地,而是多地前后爆发。如王粲于建安二十一年随曹操征吴,二十二年春病卒,很可能就在居巢染病而亡。同行出征的司马朗也是死于大疫,《三国志》卷一五《司马朗传》云:“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司马)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⑦陈寿:《三国志》,第468页。而陈琳《神女赋》亦言:“汉三七之建安,荆野蠢而作仇。赞皇师以南假,济汉川之清流。感诗人之攸叹,想神女之来游。”⑧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968页。陈琳很可能也随曹操出征,而与王粲、司马朗等人一样因疫而死于征途。
建安七子中除孔融于建安十三年被弃市、阮瑀建安十七年病卒外,其余五子王粲、徐干、陈琳、刘桢、应玚皆因瘟疫亡故,邺下文学群体的一时盛况随之凋伤。据《与吴质书》云: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⑨陈寿:《三国志》,第607页。
疫病不只减少人口,更动摇文化,挑战邺城文化权威的地位。邺下文人群体的消亡,不仅表示因文而显的象征性典范的殒落,随着其人消亡,都城文学更面临中辍的危机。即便此前已形成“共同观看”的趋势,但尚未成为稳定输出的书写模式,一旦意识输出(表意)发生断裂,附加在地景的权力、秩序结构,即邺城的神圣性也将随之削弱。为了保持、强化神圣地景的意义,或可以进一步说,为了摆脱生命易逝的问题,寻找使“都城意义”更为稳定而持续的办法,曹丕认为无非著述而已,故编纂文集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借著述传世,以实现生命之不朽、都城文学之不朽。
三、以文集实践“都城意义”之不朽
面对亲友短时间内先后亡故的震撼,生年苦短的焦虑促使文人再度反思立功的可行性与立言的迫切性。若文章可以经国、传世,何苦将时间消磨于犹未可知的建功立业之上?而已丧亡的故人,又该如何使其不被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曹丕认为使已故文人“可复道”的方法即是“都为一集”。“都”为总括之意,意指收集七子之文并为其编集,此“集”显然代表“文集”之意。汉代时已有“文集”的编纂,如:《诗赋略》中个人作品的结集定本,或是史书中文人列传的作品记录。特别是章帝下令集览刘苍作品、丁氏集班昭作品为《大家赞》等集览文稿的行为,反映当时文学已逐渐走向文本化的趋势,皆已不同程度地表现“集”的性质,但大多是基于文献整理、以防作品零散的目的。而曹丕编纂七子文集则是基于“著述传世”企图。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章不朽”的概念,将著述与建功立业共同纳入经世治国的范畴,延续班固以著述阐释王道的理想,向文人指出建功立业以外的经国之路,通过文章著述即可以完成生命的不朽。曹丕“复道”建安七子的同时,也正在复道“都城意义”。
邺下文人群体为曹氏父子建立了一个政治与文化认同的共同体结构,而七子俱逝引起的集体悲伤或是哀时情绪,恰为神圣地景又一次提供共同经验,七子再次成为共同的讨论对象,但不是关注其文学写作,而是从七子死亡蔓延出没世无闻的普遍焦虑。当扬名于后世成为幻想,则此前七子以文学建立权力认同的关系纽带亦将断裂。曹丕提出文学文本化即欲将七子建立的“都城形象”落实为一定式,以此凝定写作形式,使文人共同复道七子文学,延续都城文学。七子虽是都城文学的引领性人物,但无论是口头评议或是文章单篇流传,这种随意性的传播极容易代入“文人相轻”的情感,或是出于政治考量的刻意贬抑,或是透过舆论以提高自己的文学地位,如前述曹植《与杨祖德书》中对于七子的评价正与曹丕相反,此皆不利于系统性输出都城意义。曹丕《与吴质书》也提到:
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词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①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四二,第591—592页。
曹丕藉由文集编纂表达系统性主张,也是透过官方力量推动新的文化流行。此“立言不朽”的观念始于先秦,《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②阮元勘定:《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609页。首以道德,次以事功,末以学问,作为传道于后世的途径。但此“立言”不是指用语言文字表达思想情感的文学作品,而是属于子书范畴,诚如余嘉锡所言:“其发于言而见于文者,皆其道术之所寄”,③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0页。道术为体,文章为用,通过书疏论说以寄托微言大义。而汉人对于著述观念的形塑,则是极力为经学以外的子学、文学开辟立足之地,著述既是“士不遇”的精神皈依,同时也承载个人生命价值。但不可否认,在“以文章显”的价值取向中,汉代文人虽善“翰墨”,仍以“篇籍”为主要写作对象,如东方朔、扬雄、班固等人。曹丕则是强化文学在著述观念中的重要性,透过对“文章”的再定义,转化“立言”概念。建立“经国”与“立言”的直接关系,使“作文章”与治理国事相通,通过“文化事业”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
曹丕《典论·论文》从体裁类型与体貌特色、作家才性与作品风格等多方面理解“文章”,标举文章的艺术形式及表达个人情性的功能,写作内容不是只有讽谕教化,而是涵盖审美趣味与个人情感。既然作品是体现作者才性的成果,何不“务立不朽于著述间”,①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67页。通过文章传于千载,以追求生命价值的永恒。《典论·论文》言: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②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五二,第720页。
曹丕直将“文章”与“大业”相比,以翰墨篇籍等同于千载之功,文章可为治国之用,关乎国家兴衰。年寿与荣辱终归有限,文学却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局限,流传后世。文人无须仰赖史笔记载或凭借高官名位,著述不亚于圣贤之功,是“志士”所当为。立功立德固然可以名垂青史,文章著述同样可以扬名千古,这揭示了文人于建功立业以外的新出路——著述。曹丕所谓“经国”,绝非治理“汉朝”,而是经营以邺城为都城象征的曹魏势力,“国”的意涵可解释为“都城意义”。都城的意义从来不在于地点,而是依托于政治与文化权力的相对集中。唯有大一统王朝,都城与政治权力才能绝对相合,在分裂的政权或是势力割据的情况下,都城(空间)只是一个凝固的文本,因为该地景的表意系统不足以成为绝对的意识形态。一旦表意停滞,即文人不再书写都城,其意义只有萎缩,都城沦为地点,而不具备神圣性意义。所以曹操必须建立替代的神圣地景,使邺城成为一空间文本,以此夺取都城意义。
而曹丕著述观念的提倡,主要是制造影响,凸显其对文学的提倡与重视,其意义有三:一是树立自己文武兼治、立德立言兼顾的“明君”形象。此时距离曹丕代汉不过二年,他迫切需要“复道”都城意义的主要原因,即在于延续曹魏权力的绝对强势。二是反映他对曹植的竞争意识。曹植以善辞赋见喜于曹操,甚至和曹丕共同成为太子的候补人选,又多得文人相助,故当曹丕为太子后,欲掌握文坛话语权,同时笼络文人,遂少发建功立业之言,转而凸显文章的教化力量,宣告文章不朽。此既是与曹植竞争意识的体现,又是对曹植的告诫——务力著述,毋念立功。三是文化取向的示范意义,透过政治力量引导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崇文”的文化倾向,将文学纳入社会文化范畴,也为都城文学注入新力量。曹丕从国事角度肯定“文章”的功能,认为“国之大事”除了礼乐教化与战事武功外,文章著述也是影响国家治乱兴衰的因素,著述范围兼容“翰墨”和“篇籍”。这是延续班固以著述阐述王道的观念,利用子学、文学与经学的关联性,以总结文章的地位和作用。曹丕承继《诗赋略》中强调“诗赋”与“载道”的关系,只是其“载道”的内容更倾向于“个人之道”的表述,“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的主张,脱去文学的经学包装(经训讽谕),重拾经学眼光鄙薄的艺术特征,直面文学所体现的个人精神。但这并不表示“文”与“经”自此分路而行,事实上,支持建安文人申述“个人之道”的思想底蕴即是经学,曹丕利用文人对世乱时艰的共感及事功的向往,化用三不朽观念为文章不朽,既转变文人的价值取向,又使文章符合经学价值的要求。当文学可以不受限于讽、颂功能,而以深情壮志发出为家、为国的烈辞咏叹,“个人之道”亦是证成“都城意义”之道。文集不仅是对文人生命价值的肯定,也是肯定文人可以透过文学表现生命价值、实现经国理想的证据。文集的流传使文人摆落时间、空间的局限,同样地,表达都城意义的话语系统亦超越死亡的钳制,不至于断裂。甚至,当书写都城意义的文人因文集编纂而持续“可道”,都城意义亦挣脱地景的限制,文人成为文化的书写者、作用者,都城意义不必捆绑于固定的地点,只要掌握文人书写,便可以再现都城意义。
四、结 语
都城不只是文学作品中的场景,文人藉由对都城的描写表达其政治理念与生活信仰。而当原有的都城逐渐失落政治、文化的中心性,如何将各地的降臣、文人凝聚为一个新的共同体,则需借助神圣地景的重塑,通过大量的都城书写,重新编派空间秩序。于是,曹氏父子藉由移民措施重新编纳分裂的地方权力,并以复制神圣地景的方式,将文化权力进行空间转移和延续。同时借助邺下文人的书写,将都城的权力、象征意义与邺城连结,赋予邺城“神圣地景”的象征意义,使之取代“都城”许昌,成为“代位”的神圣地景。邺城成为政治、文化的新重心,其“王权”亦因邺城的神圣地景意义而巩固。然而,建安二十二年的疫病,使邺下文人一时俱亡,邺城的“都城文学”面临中辍的危机。为了突破生命转瞬即逝的限制,并实现都城意义的不朽,编纂文集遂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曹丕《典论·论文》将文章视为经国之道,提出翰墨篇籍等同于千载之功的说法,这是对班固著述观念的延续,即将事功与著述同视为“王道化成”的必要条件。曹丕更将文学与子学统归于“文章”之属,转化先秦“立言不朽”观念为“著述不朽”,使文集、史书、子书皆涵盖于“文章”传世的范畴。《典论》与建安七子集的编纂,正是其著述观念的具体实践。而曹丕所编文集和汉代文集最大的不同,在于编集者的主观意识,涉及对文学价值的肯定、文学体裁与风格的认识,以及延续都城意义的企图。西汉已有“集览”的行为,但多为记存而已,即便武帝诏令汇集司马相如的遗作,也只是将其赋作视作增添帝国气象的点缀。但邺下文人则是涉入政治与文化认同的表述结构,表现“我写我城”的自觉意识。因此,曹丕《典论·论文》《与吴质书》在凸显文人与作品互为表里的关系,作品体现才性,观其文,见其人,使文集“可复道”文人。既然文人成为可道者,文学作品中的意识形态也得以延续,便可复道“都城意义”。
神圣地景会因天灾人祸而遭破坏,但经由文人书写的文学地景却可串联过去与现在的情感、政治与文化的认同,延续地景的神圣意义。随着这样的表意方式被大量生产,透过文学文本化逐渐形成模式化写作,都城意义和文学书写相互援引,空间与文化因而发生关联,积淀形成写作类型(文风)。于是,掌握文人,便可以书写地景、重塑地景,即掌握这套表意体系,则神圣地景的固化与否便成为次要。显然,曹丕以文集实践“都城意义”不朽的结果是成功的,从《三都赋》可见一斑。魏立宗庙于洛阳,封五都。严格意义上,洛阳才是曹魏都城。但是离三国不远的左思,却将邺城写入《三都赋》,这是对都城权力的认同,此正源自于建安时期逐步建构邺城的神圣意义。此外,《文心雕龙·明诗》提及建安五言诗,也直接指向邺下文人的诗文作品(二曹、王、徐、应、刘),鲜少关注蜀汉或是东吴等地的作家作品。可以说,曹丕成功凝定了七子为首的文学边界,不仅巩固并延续邺城的神圣地景意义,更是强势地以“中央”文学遮蔽地方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