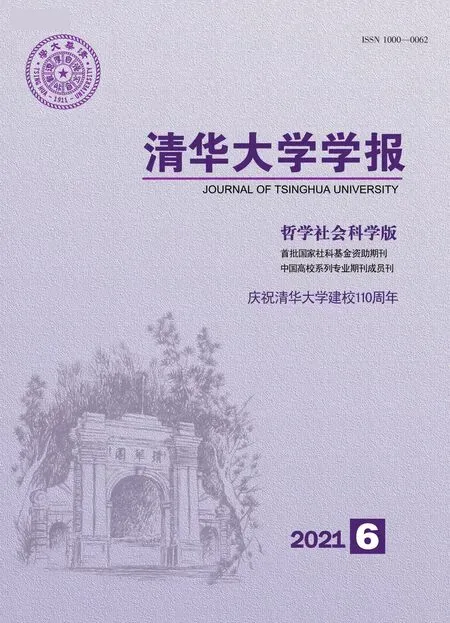胡适、罗家伦翻译的《娜拉》与易卜生在现代中国的接受
刘 倩
序言:被崇尚和被误读的《娜拉》
如果谈到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上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大概非易卜生莫属。茅盾在20世纪20年代回顾几年前易卜生在中国的影响时曾经说道:“那时候,易卜生这名儿,萦绕于青年的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①沈雁冰:《谈谈〈傀儡之家〉》,《文学周报》1925年第11卷第3号。易卜生的很多作品都在不同方面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要数《娜拉》(又译《玩偶之家》)。与此同时,易卜生在中国被接受的过程又充满了误读、曲解和断章取义,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这首先体现在五四时期学界对易卜生的介绍,对他思想的关注远远超过对他艺术的关注,甚至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后者。②赵冬梅:《被译介、被模仿、被言说的“娜拉”——一个中国文学与外来影响的典型个案》,《东方丛刊》2004年第2期,第199—209页。作为“现代戏剧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drama),③Narve Fulsås,Ibsen,Scandinavia and the Making of a World Dram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p.1.易卜生是欧洲现代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源头。④王宁:《“被译介”和“被建构”的易卜生:易卜生在中国的变形》,《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50—59页。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就以其在戏剧和文学上的创新,被欧洲文艺界视为“欧洲先锋主义的典范”(the exemplary European avantgardist)。⑤Narve Fulsås,Ibsen,Scandinavia and the Making of a World Drama,p.1.然而,民国初年的中国学界在解读易卜生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其作品中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元素,①Qi Shouhua,(Mis)reading Ibsen:Chinese Noras on and off the Stage and Nora in Her Chinese Husband's Ancestral Land of the 1930s as Reimagined for the Globalized World Today,Comparative Drama,No.4,2016,Vol.50,pp.341-364;宋剑华:《东施效颦:论中国现代文学叙事中的“娜拉”现象》,《福建论坛》2011年第10期,第44—53页;Wang Ning,Reconstructing Ibsen as an Artist: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e Reception of Ibsen in China,Ibsen Studies 2003,No.3,pp.71-85。很少关注其在人物设置、结构安排等方面所使用的艺术手法,而仅仅强调其思想性。其次,即便在强调易卜生作品的思想性时,民国学者们往往也有所选择,往往只强调其作品的社会意义,尤其是有关女性解放的内容。《娜拉》于是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现代女性解放的先声。然而,我们都知道,易卜生本人后来曾不无委屈地说过:“说实话吧,我现在连女权运动究竟是什么回事还弄不清楚呢?我觉得不过是人间的问题,并不是人间唯一的问题,如果你仔细些去读我的书,自然会了解这一点。”②易新农、陈平原:《〈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回响》,《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第129—140页。而且即便易卜生在《娜拉》中确实表达了对“夫权”某种程度的反抗的话,那么胡适等人则把对“夫权”的反抗挪用为对“父权”的反抗,从而助阵新文化对旧文化的颠覆。③宋剑华:《错位的对话:论“娜拉”现象的中国言说》,《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第122—129页。所以可以说,近代中国学界对易卜生的理解和阐释是建立在误读、选择性接受和有意挪用的基础上的。
那么,中国现代学界对《娜拉》乃至易卜生作品的误解到底起源何处呢?这里面当然有包括时代需要、有意筛选等在内的诸多复杂的原因,但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则是胡适和罗家伦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原著的误读。该译本是转译本,并非从易卜生原文译入,而是译自威廉·阿彻(William Archer,1856-1924)的英译本。作为《娜拉》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胡适、罗家伦译本并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只有很少学者关注过该译本的特点。④邓倩:《娜拉的翻译与重构——以〈玩偶之家〉的中韩译本为例》,《中国外语研究》2018年第1期,第67—71页;石晓岩:《从〈娇妻〉到〈娜拉〉:民初与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创造性误读》,《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156—160页。在将其与英译本仔细对照后,笔者发现,虽然胡适和罗家伦总体来说都保持了对原著的忠实,但却在一些相当关键的细节上有所改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读者对原著的理解。作为《新青年》重磅推出的“易卜生号”的重要内容,这个译本标志着《娜拉》在中国首次问世,决定了当时读者对该剧本的初步印象,对后来的译本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本文从这个译本出发,尝试对《娜拉》在近代中国接受中的误读进行溯源,为易卜生的中国接受研究提供新的资料和不同的视角。
一、新文化运动语境中的《娜拉》
国内最早介绍易卜生和他作品的两篇文章,是鲁迅1908年在《河南》月刊上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鲁迅在文中这样写道:“有显理伊勃生(Henrik Ibsen)见于文界,瑰才卓识,以契开迦尔之诠释者称。”“伊氏生于近世,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假《社会之敌》以立言,使医士斯托克曼为全书之主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⑤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1、79页。1914年,《俳优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陆镜若的《伊蒲生之剧》。1918年6月,《新青年》杂志出版了“易卜生号”专刊,内容包括胡适撰写的《易卜生主义》、胡适与罗家伦合译的《娜拉》、胡适与陶履恭合译的《国民公敌》、胡适与吴弱男合译的《小爱友夫》以及袁振英撰写的《易卜生传》。其中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被傅斯年誉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之一,⑥胡适:《白话与文学心理的改革》,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直接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源头。以上是许多文学史对易卜生在近现代中国影响的描述,我们往往也用这样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来看待这位文学巨匠的跨文化影响。但是,事实上,易卜生在近代中国的影响是更为复杂而多样的。比如,他在普通民众间的影响,和他在文坛上的影响,二者就不可等同来看。
易卜生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普通民众间所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作品的演出密不可分。我们知道,《新青年》等在文学史上有着重大的跨时代意义的报刊,事实上由于其精英主义的倾向,其在近代普通读者身上的影响是很有限的。相比阅读《新青年》上刊登的《娜拉》的剧本,普通民众可能更倾向于去看演出。很多文献记载,当时的许多知名演员,如“新剧同志会”的陆镜若等人,都曾于1914年上演过《娜拉》剧本。①欧阳予倩:《自我演剧以来》,上海:神州国光社,1939年,第79页。也有很多文献显示,著名的春柳社曾经在1914年演出过《娜拉》,由此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的易卜生热推波助澜。然而,根据Xia Liyang等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春柳社很大可能并没有在1914年上演过《娜拉》,而当时真正流行的是《空谷兰》等剧。该剧直到1923年才由北平女子师范学院的女学生上演。而《娜拉》在当时中国民众间的接受也并非一直畅通无阻,有记录显示,有些演出在当时反响并不理想,听众甚至不等到剧终就会离场,因为演出内容缺少审美,而太重视说教。就连中国文学界对易卜生的评价也有多重声音和不同态度。1926年前后,中国戏剧界开启了影响深远的国剧运动,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文学家们批评易卜生的戏剧过于重视说教,对中国戏剧产生了负面的影响。②Xia Liyang,A Myth That Glorifies:Rethinking Ibsen's Early Reception in China,Ibsen Studies,Vol.18,No.2,2018,pp.141-168.正如闻一多所说:“第一次认识戏剧既是从思想方面认识的,而第一次印象又永远是有权威的,所以这新入为主的‘思想’便在我们脑经里,成了戏剧的灵魂。从此我们仿佛说思想是戏剧的第一个条件。”③闻一多:《戏剧的歧途》,《剧刊》1926年6月。由此可见,就影响的结果而言,易卜生在近代民众和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影响都是多样化的,甚至可以说,将他译介到中国的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学家们由于过于推崇其思想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对他的接受起到了反作用。
而就译介的意图而言,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家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推出易卜生的目的就是要借鉴他剧作中思想的力量。在《新文学运动》一文中,胡适毫不讳言:“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④赵冬梅:《被译介、被模仿、被言说的“娜拉”——一个中国文学与外来影响的典型个案》,《东方丛刊》2004年第2期,第199—209页。胡适使用的“易卜生主义”一词可能是受到萧伯纳一篇文章的影响。⑤Qi Shouhua,(Mis)reading Ibsen:Chinese Noras On and Off the Stage and Nora in Her Chinese Husband's Ancestral Land of the 1930s as Reimagined for the Globalized World Today,Comparative Drama,2016,Vol.50,No.4,pp.341-364.萧伯纳在这篇题为《易卜生主义的精髓》(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的文章中也把易卜生视为女性解放的提倡者,⑥Bernard Shaw,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04.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胡适对易卜生主义的理解。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对时人和后人对易卜生的理解都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
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是极不堪的。家庭里面,有四种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作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乐,要安逸,还要体面,所以他要娶一个妻子。正如《娜拉》戏中的郝尔茂,他觉得同他妻子有爱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妻子做“小宝贝”、“小鸟儿”、“小松鼠儿”、“我的最亲爱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给他妻子一点钱去买糖吃,买粉搽,买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标致。做妻子的完全是一个奴隶。她丈夫喜欢什么,她也该喜欢什么,她自己是不许有什么选择的。她的责任在于使丈夫欢喜。她自己不用有思想:她丈夫会替她思想。她自己不过是她丈夫的玩意儿,很像叫
化子的猴子专替他变把戏引人开心的。①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1918年6月15日,第491页。
胡适的分析把《娜拉》的主题引导向了对家庭,尤其是对夫权至上思想的抨击上,由此把易卜生和女权主义联系到了一起。此外,胡适还谈到了个人意志和独立精神的问题,他看重娜拉精神的觉醒,即有个人意志和懂得对自己负责。他甚至敏锐地意识到,在易卜生那里,一个人只要有了自由精神和独立意志,出走与不走,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比如,在《易卜生主义》中,胡适指出,易卜生的《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里,写到哀梨妲嫁人后觉得给别人当妻子、当后母,很不自由,就非常想跟人到海外去过“海阔天空的生活”。他的丈夫知道没法留住她了,就允许她离开家去寻找自由。可是哀梨妲意识到有自由的同时自己也有责任了,就不想走了。她说,有了完全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有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所以,无论是娜拉的出走还是哀梨妲的决定不走,都是自由意志的反映。②刘洪涛:《易卜生〈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四种读法》,《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44页。
然而,《海上夫人》中的“不走”没有在现代中国得到同样的重视,而娜拉的出走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最经典的姿势”。③刘洪涛:《易卜生〈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四种读法》,《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44页。她出走时决绝的态度也成为《娜拉》在现代文学中被讨论、被模仿和被挪用时,人们最关注的内容。《娜拉》往往被中国现代文学界视为女权主义的先声,而该剧其他方面的思想内涵和该剧许多重要的艺术特色都被忽略了。
二、误读的起源:罗家伦和胡适如何翻译《娜拉》
那么,为何中国现代文学界对《娜拉》的接受有上述的特征?这和胡适与罗家伦翻译的《娜拉》有怎样的关系?下面我们来看看胡适和罗家伦到底是如何翻译《娜拉》的。
(一)胡适、罗家伦译本的基本情况
据先前学者和笔者考证,胡适和罗家伦的译本是译自威廉·阿彻的英译本。④邓倩:《娜拉的翻译与重构——以〈玩偶之家〉的中韩译本为例》,《中国外语研究》2018年第1期,第67—71页;Xia Liyang,A Myth that Glorifies:Rethinking Ibsen's Early Reception in China,Ibsen Studies,Vol.18,No.2,2018,pp.141-168。笔者曾与Xia Liyang通信核对过这一结论的出处,Xia Liyang告诉笔者,通过她的考证和比对,也认为胡适和罗家伦的译文是译自William Archer的英译本,笔者在此向她表示感谢。威廉·阿彻是一位苏格兰作家和批评家,他翻译了很多易卜生作品,是最早在英国推广易卜生作品的人之一。他的英译本基本上是在英语世界中流传最广的英译本,也是易卜生作品许多中文转译本的英译本来源。比如,潘家洵在翻译《海德加伯勒》时,在序中就说过:“我还要说明这篇东西是从Edmund Gosse与William Archer合译的英文本子转译过来的。”⑤潘家洵:《〈海德加伯勒〉序言》,《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1—3。在1918年以前,威廉·阿彻翻译的英文版《娜拉》有好几个版本,经过对比,笔者发现胡适、罗家伦的译本与1890年的译本高度吻合,但是在个别不影响主旨的细节上有所出入。因此笔者怀疑二人可能采纳的是威廉·阿彻的其他版本。由于当前资源受限,笔者还未能完全确定到底是哪个版本。但是这些显示差异的细节都非常微小,仅仅是多一次或者少一次称呼,由此可见不同版本的威廉·阿彻译本其实差异很小,故不影响本文结论。总之,本文参照的英译本为1890年的英译本。⑥Henrik Ibsen,ADoll's House:APlay in Three Acts,William Archer trans.,Boston:Walter H.Baker&Co,1890.以下在文中标注页码。
胡适和罗家伦的译本最初刊登在《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6号上,也就是“易卜生号”,于1918年6月15日出版。罗家伦译了第一幕和第二幕,胡适译了第三幕。在该译本的开篇,有这样的题记:“《娜拉》三幕,首二幕为罗家伦君所译,略经编辑者修正。第三幕经胡适君重为迻译。胡君并允于暑假内再将第一二幕重译,印成单行本,以慰海内读者编者识。”①易卜生:《娜拉》,胡适、罗家伦译,《新青年》1918年6月15日,第508页。以下在文中标注书名及页码。当时的胡适才26岁,罗家伦才20岁。从胡适应允暑假内将第一二幕重译的细节可以看出,二人之间,胡适是更为成熟的翻译主力。然而在两人译完该剧后,胡适应该并没有修订罗家伦翻译的部分,甚至我们可以怀疑,两人根本没有读过对方翻译的部分,因为两位译者对人名的翻译都是不一样的,并没有统一起来。比如,娜拉的朋友Christina Linden,当娜拉称呼她为Christina时,胡适将其译为“姬婷”,而罗译为“敦”,是对Mrs Linden进行减省而来。而海尔茂称呼她为Mrs.Linden,罗家伦将其译为“林夫人”。这表明罗家伦误把Christina Linden的姓——林敦——处理为了“姓林名敦”。胡适的处理显然是更为合理的,但他并未纠正罗家伦的译法。
总体来说,同大部分五四新文学家一样,胡适和罗家伦的翻译是相当忠实原文(此处指英译本,下同)的,这和上一辈翻译家如林纾、包天笑和周瘦鹃等人有明显的区别。②Jane Qian Liu,Transcultural Lyricism:Translation,Intertextudity,and the Riseof Emotion in Modern Chinese Love Fiction,1899-1925,Leiden:Brill,2017,pp.46-117.罗家伦使用的翻译语言非常欧化,有时几乎是把英语的句法照搬过来。胡适则更为流畅一些,并且加了很多注释,从这些注释可以看出,胡适对原著的理解是非常深刻而透彻的。但是,二人的翻译在处理一些看似“次要”的细节上,却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而恰恰是这些看似不重要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该剧的理解。
(二)林敦夫人形象的微妙改变
这些误译主要体现在对剧中除了娜拉和海尔茂(该译本作“郝尔茂”)之外的另外一对恋人——林敦夫人(Christina Linden)和柯乐克(Nils Krogstad)——的人物形象和关系的处理上。③石晓岩也提到胡适译本“关于柯洛克和林敦夫人恋爱始末的细节,译本亦多处语焉不详,影响读者对柯、林真诚之爱的理解。总体看来,译本尊重原著,但在局部上下文意义的承接上有明显的失误,使读者不明所以,而这些情节对读者理解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现实与命运的双重悲剧是十分重要的”。此外,他在谈洪深译本时提到该译本也忽略了这个问题。见氏著:《从〈娇妻〉到〈娜拉〉:民初与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创造性误读》,《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156—160页。林敦夫人是娜拉旧日的朋友,在丈夫去世之后,她孤身一人无以为继,听说海尔茂升职当了银行副经理,就来托娜拉请海尔茂帮她找个工作。海尔茂答应下来,打算把曾经有过伪造字据前科的职员柯乐克解聘。柯乐克害怕自己丢掉饭碗,威胁娜拉要将她过去为救海尔茂代替父亲签字的事情透露给海尔茂,然后才有了《娜拉》里那些最脍炙人口的情节——娜拉和海尔茂发生争执,看清了海尔茂的“真面目”,认识到自己在家里不过是玩偶,然后出走,留下那一声响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呯”的关门声。
在中国现代乃至当代文学界,人们对易卜生《娜拉》一剧的关注往往仅聚集于海尔茂和娜拉两人的关系上,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林敦夫人和柯乐克两人的关系对全剧主旨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无论海尔茂还是娜拉,两人一直都生活在浪漫的幻象中:海尔茂心中的娜拉天真烂漫,小鸟一般;娜拉心中的海尔茂会为了她牺牲他自己,会出现奇迹。但当幻象被现实的丑恶——比如出现了一个威胁要揭露娜拉旧日污点的恶人——打破之后,婚姻只能破裂。林敦夫人和柯乐克则恰恰是娜拉二人的反面。他们是知晓了生活的艰辛之后,决定要在一起相互扶持,而不相信浪漫。林敦夫人曾反问柯乐克:“Have you ever found me romantic?”(p.99)(你觉得我什么时候浪漫过?)(《娜拉》,第555页),④这句重要的话在译文中也没有准确翻译出来。林敦夫人对娜拉二人的婚姻洞若观火,在柯乐克回心转意,决定去要回自己寄出的揭发信的时候,林敦夫人阻止了他,因为她认为必须让娜拉走出自我牺牲的美好、崇高的幻想,让他们夫妻俩直面残酷的现实。因为唯有如此,二人才能拥有真正坦诚、彼此信任的婚姻关系。而最终,娜拉和海尔茂的婚姻幻象被打破之后,二人的婚姻只能破裂,这是因为他们无法像林敦二人一样,接受现实的惨淡,去寻找共同的温暖。
在胡适和罗家伦的译文中,由于翻译的不准确,林敦夫人的形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比如,娜拉刚刚和林敦夫人重逢时,娜拉提到自己先前在报纸上看到了林敦夫人丈夫去世的消息,却一直没顾得上给林敦夫人写信慰问。林敦夫人表示理解,娜拉却非常愧疚地说:“我做得太恶劣了。”①除非另外注明,文中William Archer英译本的中文译文为笔者所译。(It was horrid of me.)(p.37)这句话被罗家伦翻译成“我听了都害怕”(《娜拉》,第514页),由此娜拉对林敦夫人的同情和对自己待朋友态度的内疚就消失了。此外,林敦夫人无意间流露出认为娜拉一直生活得无忧无虑的看法,娜拉表示抗议,她说:“You're proud of having worked so hard and so long for your mother?”(p.42)(你服侍你的母亲非常辛苦,时间非常久,所以你感到自豪。)罗家伦把“非常辛苦”译为“小小的受了一点儿辛苦”(《娜拉》,第517页)。这样的改变在提升娜拉的气场的同时,也降低了对林敦夫人劳心劳力孝敬母亲一事的认可。由此,林敦夫人形象所蕴含的积极成分就被减少了。
(三)柯乐克形象的明显改变
而罗家伦译文改变更明显的则是柯乐克的形象。柯乐克在易卜生笔下确实一开始来者不善,但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读者们会意识到其实这个人也有着苦衷。他先前已经完全改邪归正,如今是因为海尔茂要夺走他的工作,再次将他陷入绝境,他才决定铤而走险。当他初次对娜拉说到自己当初为何会从事高利贷时,他解释道,由于自己伪造字据的事情为人所知,所有的大门都对他紧闭,无以为生,所以只能去放高利贷。他说:“I was obliged to grasp at something;and I don't think I've been one of the worst.”(p.57)(我不得不抓住点儿什么,我想我也并非最坏的那个。)罗家伦译为“我不得已去干了点小事。我想也不曾做错”(《娜拉》,第527页)。译文暗示柯乐克自认为放高利贷的事情不是什么坏事,这和原文的意思是有出入的。原文是说柯乐克认为自己并非最狠毒的放高利贷的人,也就是他仍然保持了一些良心,未曾过分欺压过借贷的人。罗家伦的改译降低了柯乐克的道德水准。
两人的对话越来越激烈,柯乐克威胁要把娜拉伪造父亲签字的事情告诉海尔茂。娜拉非常激动,说:
It would be shameful of you!(With tears in her voice.)This secret which is my joy and my pride— that he should learn it in such an ugly,coarse way— and from you!It would involve me in all sorts of unpleasantness.(p.58)
这句话中的“ugly,coarse way”原本是指海尔茂会以如此不堪的方式得知这件事。但是这句话被罗家伦误译为“他怎么可以从粗鲁……鄙陋的你那里得着这消息”(《娜拉》,第527页),由此,“粗鲁”和“鄙陋”被用来形容柯乐克本人了。娜拉作为剧中最重要的主人公,她的视角基本上就是读者的视角,而她对柯乐克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读者对柯乐克的态度。柯乐克的形象就被大大地丑化了。
此时的娜拉还不清楚柯乐克为何会突然找上门来,直到后来海尔茂告诉她,自己要对银行的人事进行重大的调整。这时娜拉才明白柯乐克的困境,她不禁说道:“Then that's why that poor Krogstad——”(p.64)(难怪可怜的柯乐克……)在翻译的时候,罗家伦省略掉了“可怜的”这一修饰语,所以读者无法体会到娜拉对柯乐克是有所同情的,因此无法被娜拉的态度所影响。而当娜拉请海尔茂告诉自己柯乐克到底因为什么事情陷入麻烦时,海尔茂说:“Forgery that's all.Don't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p.64)(伪造字据,就是这样。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娜拉问道:“Mayn't he have been driven to it by need?”(p.65)(他会不会是迫不得已呢?)罗家伦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误译,把娜拉的话译为了“你是不得已”(《娜拉》,第532页),改变了重要的内涵。娜拉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她听了柯乐克先前的自白,也联想到自己的迫不得已,对柯乐克是有所同情的。但恰恰是由于罗家伦的误译,娜拉的同情未能传达出来。
(四)两对情侣关系对比程度的降低
除此之外,林敦夫人对娜拉和海尔茂的婚姻看得非常透彻。在第三幕里,当她告诉柯乐克自己愿意和他重组家庭时,柯乐克非常感动,决定放弃自己的计划,去要回自己投到海尔茂信箱里的信。然而林敦夫人却阻止了他,告诉他自己原本确实希望柯乐克收回自己的信,但是自从来到娜拉家之后,她看到这个家里有很多惊人的事情,海尔茂必须知道这件事。她说:“There must be an end to this unhappy secret.”(p.100)(“必须终止这个令人不快的秘密了”。)这句话非常关键,它显示出林敦夫人杰出的洞察力,即娜拉和海尔茂的家庭表面上非常幸福和睦,却暗藏不可告人的秘密,唯有娜拉把这个秘密的重担与海尔茂分享,两个人打破虚幻的和谐,直面现实的考验,他们的婚姻才是真正幸福的。
胡适虽然准确地译出了上下文,即“海尔茂应该知道这椿秘密借款。他们夫妻两人应该完全开诚相待,这样支支吾吾,决没有开诚相待的日子”(《娜拉》,第556页),但是却省略了这句关于“终止这个令人不快的秘密”的话。大概是他觉得这句话比较重复,便将其融入到前后文中了。但是,林敦夫人的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其实在原作中相当关键,她强调了真正彼此信任的夫妻关系应该是能够容纳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的,不应该将其封锁,成为秘密——这才是“开诚相待”的本质内涵。省略了这句话,实际上降低了林敦二人的情感和娜拉二人的情感的对比意义,尤其是前者所具有的正面的参照意义。
(五)娜拉对海尔茂批评锋芒的减弱
在对娜拉和海尔茂二人关系的直接表现上,胡适的个别译法也和原文有出入,并可能对《玩偶之家》在近代中国的接受产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影响。在娜拉离开家之前,她和海尔茂最后一次谈话,她说自己已经不是海尔茂的妻子了。海尔茂很后悔,说:“I have strength to become another man.”(我有勇气成为一个新的人。)娜拉的回答非常耐人寻味:“Perhaps——when your doll is taken away from you.”(p.122)(也许吧,当你的玩偶被从你身边拿走之后。)胡适把这句话翻译成“只要把你的‘顽意儿’去了,你或者可以改变”(《娜拉》,第571页)。在易卜生的笔下,不仅娜拉在家里被当作玩偶是需要反思的情形,而身为一个大男人的海尔茂仍然需要玩偶(或者说洋娃娃)这个事实,也是值得反思的。有玩偶的男人一直没有长大,因此无法承担责任、无法独立思考、无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所以才有了《娜拉》这部剧中的核心冲突。但是这一层意思在近代中国似乎并没有被人们理解到,人们的关注点都在被当成玩偶的妻子上,为妻子打抱不平,批判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而易卜生对独立思考的强调却往往被忽略了。
为何会如此呢?这恐怕与胡适的译法也有微妙的关联。“顽意儿”一词在清末民初往往指“小东西”“小装饰”,①“顽意儿”:指小东西、装饰品。《红楼梦·第五十六回》:“此刻姑娘们在园里住着,不能多弄些顽意儿陪衬,反叫人去监管修理,图省钱,这话断不好开口。”用来寄托情趣或打发时间的事物。如唱戏、打牌、耍杂技等。《红楼梦·第一一回》:“我们爷原算计请太爷今日来家来,所以并未敢预备顽意儿。”也作“玩意儿”“玩艺儿”。对人、事、物的鄙称。《红楼梦·第六十回》:“那些小丫头子们原是些顽意儿,喜欢呢,和他说说笑笑,不喜欢便可以不理他。”《老残游记·第二回》:“你们此地说鼓书是个什么顽意儿?何以惊动这么许多的人。”也作“玩意儿”。http://www.cihai123.com/cidian/1217147.html,访问时间:2021年6月28日。大男人有自己喜好的小物品其实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大男人如果还像小男孩一样离不开自己的洋娃娃,则是一件非常孩子气的事情了。在易卜生的丹麦语原文中,剧作题目Et dukkehjem很难精准地翻译为英语,最为接近的就是A Doll's House。②易卜生用丹麦语写作剧本,在他的时代,挪威和丹麦最普遍使用的书面语是丹麦语。胡适采用的英语转译本便使用了doll一词,用小孩玩耍的洋娃娃来比喻娜拉在海尔茂心中的形象。胡适把“洋娃娃”译为“顽意儿”,减少了其对“孩童”的指涉,因此很难让读者领会到娜拉对海尔茂的批评的真正锋芒。
除此之外,易卜生原著中许多关于哲学的思考,比如南陔医生的一些言论,在翻译的过程中被具体化了。比如他对娜拉说,自己死了以后,他们很快就会忘记自己的,因为“The absent are soon forgotten”(p.80)(“不在场的就会被遗忘”)。但是罗家伦将其译为“我若不来,你们也就忘了”。(《娜拉》,第542页)南陔医生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他是易卜生用来揭示命运的无常、探索人应当如何面对命运和死亡的一个角色。而译者对他这句话处理的结果,则消解了南陔的深刻思想,使之变成对现实的讨论。易卜生作品中对命运的思考和对哲学的探索在近代中国引起的回响很小,可能也与之有关。
最后,胡适还增加了很多着重号(罗家伦并没有),来强调《娜拉》中的一些内容,尤其是关于海尔茂占有娜拉,把她视为财产,而无法理解娜拉等内容。胡适在强调这些内涵的同时,事实上也无形间遮盖了其他的内容,由此影响了《娜拉》在中国接受的方向。
三、误译对《娜拉》接受的影响
胡适和罗家伦的译本虽然大体上保持了对原著的忠实,但是由于在上述细节上的误译,对《娜拉》在现代中国的接受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易卜生原著的艺术高度被降低了。在原著中,人物的性格是复杂的,是随着剧情发展而发生变化的,而读者对林敦夫人和柯乐克的理解,则会随着娜拉的态度而发生微妙的转变。但是由于罗家伦在翻译时对林敦夫人和柯乐克相关细节的误译或者漏译,这两个人物的形象变得扁平化,而沦为推进情节的工具。娜拉则成为易卜生的传声筒。相应地,海尔茂作为一个成年男人,仍然痴迷并依恋着自己的玩偶,因此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通过批判性的思考来理性看待娜拉所隐藏的事情。这个重要的事实也被忽略了。海尔茂在译作中也仅仅成为了娜拉所要批判和抛弃的对象,而不再是引人深思的、有启发性的人物。
除了人物性格的塑造,原著结构安排上的精巧也由于误译而不容易被人注意到。林敦和柯乐克二人的爱情实际上是娜拉二人爱情的对照。也就是说,原著的结构是双线索的,由两条相辅相成又互为镜像的爱情线索构成。但是在现代中国文学界对《娜拉》的解读中,很少有人提到林敦和柯乐克二人,他们仅仅被作为推动情节前进的无足轻重的人物而看待。
其次,由于《娜拉》的艺术性在翻译过程中被降低了,这更加促使读者们只关注易卜生的思想。而即便在对易卜生的思想进行解读时,人们也往往将其简单化了,只看到其有关“女权主义”的思想,而忽略了他作品中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比如,人们只看到娜拉的出走,和她对海尔茂所代表的夫权社会的控诉,而没有看到林敦和柯乐克二人的爱情才代表了一种很可能是易卜生所赞许的、现实主义的爱情典范。他们是在看清了现实的残酷、接受了自身和对方过去的“污点”之后,决定要直面现实和过往的苦难,结合为家庭。而娜拉二人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过度浪漫主义的、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婚姻,是有问题的婚姻,因此才有了娜拉的出走。所以林敦二人的线索其实是剧作里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我们看到,在现代文学家们对《娜拉》的解读里,和包括胡适的《终身大事》在内的一系列模仿《娜拉》的“出走剧”中,人们只是将娜拉的出走作为典范,而看不到林敦夫人走进家庭的无畏之举。而易卜生剧作中有关哲学的沉思,则因为译者进行了具象化的处理,而很容易被人忽视。
总而言之,作为《娜拉》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胡适和罗家伦翻译的《娜拉》是符合译者自身的主观意图的,而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有意或者无意的误译和漏译则在事实上对《娜拉》在中国的接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对剧中一对次要角色——林敦夫人和柯乐克——的形象和关系的处理,以及对海尔茂的形象、南陔医生哲思的处理,都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促使人们更关注其思想性。而人们在关注该剧思想性的时候,又集中关注了其社会改革的方面,即女权主义的因素,相应地忽视了易卜生思想中更深刻而复杂的内涵。今天的我们当然不是要批判胡适和罗家伦在如此年轻的时候所翻译的剧本,更不是要低估他们通过这部译作所凸显出的易卜生的重要思想价值,而是希望通过梳理翻译文学史上这些看似不甚重要的细节,来厘清文学作品在跨文化、跨语言传播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微妙变化,以及其可能对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
——王忠祥教授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