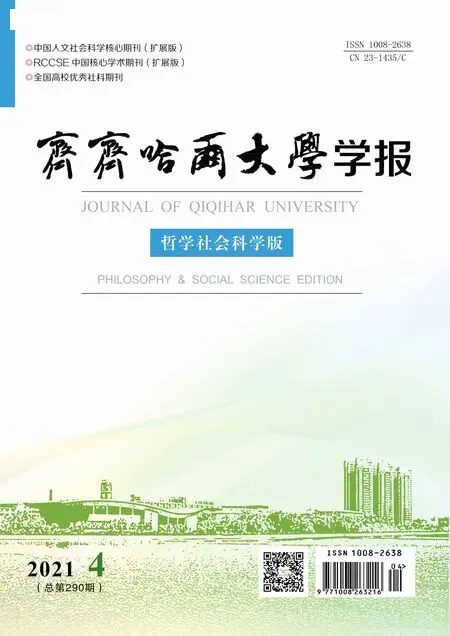“新传记”视角下《奥兰多》立体化叙事表征研究
王 欣,房佳仪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外语系,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维多利亚时期传记作家选择拔高传主人格与记录传主功绩,使得传主“高尚、正直、朴素而严谨”[1]1702的品质成为共性。弗吉尼亚·伍尔夫批判人们用此方式对传主进行模式化的记录,拒绝传记作品如同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蜡像般刻板。20世纪现代主义思潮席卷西方,伴随着伯格森的直觉主义和时空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以及现代心理学等理论的崛起,西方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尝试革新,摒弃传统线性叙事,注重探寻人的精神世界。伍尔夫初次在其1927年发表的《新派传记》中提出“新传记”一词。区别于传统传记,新传记由于小说家群体的加入,呈现出小说的艺术性,注重传主的心理阐释,在保证真实性的前提下,加入作者主体性的想象。这一时期,传记文学来势汹汹。哈罗德·尼克尔森的《群像》集传记与自传于一身,安德烈·莫洛亚主张传记文学是艺术的观点,认为历史应服务于传记人物的书写。因为无法准确把握历史与传主行踪,传记作者不得不进行创造,利顿·斯特拉奇在《维多利亚名人传》中就运用心理视角重塑名人形象。伍尔夫赞赏其为其他传记创作奠定的革新手法,并主张从多角度描写传主“同一张面孔下掩盖的矛盾性格,”[1]1334打破传统传记歌功颂德的教诲作用,更新英雄形象,只有通过立体化的视角观察传主,发挥作者的想象力与艺术创造力,才能“塑造更为完满的统一体。”[1]1334
1927年伍尔夫开始尝试实验自己的“新传记”观,创作出《奥兰多》。她在传统传记的基础上戏谑地加入了小说手法,将历史真实性与小说艺术性融合,实验出一部具有她鲜明风格的新传记作品。伍尔夫并非完全摒弃传统传记形式,在结构上她按照形式排列了前言、正文、脚注、注释、索引以及致谢,书中穿插人物图片,选用的却是自己的密友薇塔和侄女等人的照片,充分显示了对传统传记煞有介事的戏拟。传主奥兰多的选择根据薇塔原型进行虚构似的创造,呈现空间张力与时间韧性。作为男女同体的双性人,奥兰多传奇四百年的人生经历了时代的变迁、自身职业的转变,颠覆和打破了传统传记对于性别和身份的束缚以及钟表时间的规律。伍尔夫使用立体化的叙事方式,将奥兰多形象丰满和生动化,利用多角度叙事和跟随传主心理时间叙事的手法,将作品的钟表时间顺序打乱,将破碎的事件和断裂的时间堆叠,从空间上建立起立体的奥兰多形象和故事情节,追求传主内心真实。
一、性格虚构——人物塑造立体化
传统传记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多以全知视角对传主进行歌功颂德,作者采用看似客观的上帝视角叙述传主的生平,读者只能被动接受在基础事实之上作者对传主的人物设定,导致传主的真实人物性格不能很好地呈现,因而对传主形象的刻画大多统一为具有高尚品质的人或者地位显赫的人,起到教化群众的目的。伍尔夫在《新派传记》中指出,20世纪传主与作者间的关系已发生改变,作者不再是翻阅历史资料的传主忠实的跟随者,“他已然是一位艺术家。”[1]1703作者可以发挥想象力让传主形象多面化立体化地呈现。伍尔夫使用的其中一个手法即运用多视角叙事立体地展现传主的性格。除全知视角外,《奥兰多》中穿插其他人物的心理描写和对话等侧面展示奥兰多的性格,同时也赋予奥兰多第一人称为自己说话的权力。“在想象力丰富的文学中,角色为自己说话,作者并不出场。”[1]30
奥兰多享受自然带来的宁静和思考时间,他躺在家乡的大橡树下感受自然直到号角吹响提醒他要去拜见伊丽莎白女王。伍尔夫描写的奥兰多和女王初次见面场景切换了两方的心理视角。奥兰多通过女王细长和枯槁的手以及淡黄色的眼球判断女王过着高贵威严却孤独的生活。而下一刻,镜头则切换到女王的视角,通过观察奥兰多低垂的深褐色长卷发的头颅,女王断定他是一位天真忠诚的贵族少年,并且在一次又一次的凝视下,女王仿佛看透了奥兰多优雅浪漫的灵魂,因此赐予他爵位和财富。在阅人无数的女王眼中,奥兰多是具有完美品质的贵族绅士,通过切换他人的视角来侧面刻画奥兰多身为男性时的气质似乎更有说服力。伍尔夫对于女王心理活动的生动刻画也突出了奥兰多身为贵族少年时所具有的女性气质,他喜爱自然,热爱诗歌,他柔弱感性,因此女王甚至舍不得让他像其他骑士一样征战沙场。奥兰多的性格因此彰显,同时女王对于奥兰多的评价也通过她个人的心理活动直接呈现给读者。作者的上帝视角隐退,实现角色为自己说话。
奥兰多热爱诗歌,崇拜诗人,他邀请尼克·格林来庄园做客,盛情款待,最后却落得格林针对他隐秘生活发表的讽刺诗,奥兰多经历了爱情和朋友的背叛,对诗歌和名望失去兴致。此时独来独往的状态和性情贴近萨克维尔家族“在家里操持生计撰写日记的理查德夫人。”[2]55奥兰多在家中思考诗歌和名望对于他的意义,其中插入了自言自语的对话,名望对他来说犹如“一件碍手碍脚的镶穗外衣,一件让人憋气的银铠甲,一个遮了稻草人的彩色盾牌”[3]57限制了他。他重新回到自然的怀抱,他想,“多么美好的生活啊”“为什么不现在就享受一下这样的生活?”[3]57显然,伍尔夫不可能深入一个历史人物的内心来获取其当时的情感诉求,即使奥兰多是一位集历史与文学于一身的传主,对于传统传记叙事来说也无法把握其真实性。但伍尔夫选择用间接心理独白方式呈现奥兰多当时的心境,加入了作者的主体性想象,又一次实现传主为自己发声的艺术理论,同时丰富了传记内容。包括奥兰多与格林关于诗歌看法的对话,也增强了传记的可读性,从更加立体的角度刻画出奥兰多身上不同寻常的敏感与诗性气质。
二、心理虚构——叙事方式立体化
1907年,弗吉尼亚·伍尔夫为女性密友维奥莱特写下仿传《友谊长廊》,被视为“一部早期的《奥兰多》。”[4]13在这部小传中,伍尔夫就以轻松幽默的笔触对传记文学进行了实验创作。她赞美真实鲜明的传主个性,并企图还原这种真实。这就需要作者将小说的创造性和文学性加入传记中,发挥想象力,深入传主内心,探寻其心理活动。长久以来,人们对历史的过分关注将线性的钟表时间搬上认识论舞台,“时代”一词的使用也体现了人们对于用时间划分历史的刻板认识。伍尔夫在小说中擅长使用意识流等现代主义写作技巧刻画人物时时刻刻变化的思想和情感,打破传统文学的线性叙事。但基于小说虚拟性的文体,“引入意识的流动、情感的绵延,扰乱传统的线性叙事,并不会影响其虚构的本质。”[5]173对于传记文体来说,加入人物心理的刻画,并以人物流变的心理时间为线索展开叙事则颠覆了传统传记历史性的本质和在时间观上的现实性,从而注入文学色彩。在《奥兰多》中,伍尔夫擅长在奥兰多经历的不同时期和空间内深入其情感变化,同时依据心理时间的流动串联事件,利用小说中时间蒙太奇叙事方式“消弭逻辑时间顺序,将意识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糅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主体的心理世界,”[6]147呈现叙事空间感。伍尔夫试图以奥兰多的心理时间作为事实,在保留传统传记以年代顺序记述传主的方式之外,重点关注其心理活动。不同时代的经历影响奥兰多的个性和思考方式,跟随他的心理活动探索传主内心真实,内心活动又将所有的经历在短暂的钟表时间内串联,呈现新传记叙事的空间感。同时,传记中出现的空间也凝聚传主的内心流变,静止的空间中蕴含漫长的时间流动,推动叙事发展,这都立体化地呈现了传主的个性和经历以及叙事空间。
俄国公主萨沙穿越时代,长久萦绕着奥兰多,萨沙之于奥兰多的意义不断变换,与其说萨沙穿越三个世纪,不如说她存在于奥兰多的脑海中。一连串的记忆才构成奥兰多的内心真实。从叙事学角度讲,故事时序按照钟表时间不断推移,讲述着奥兰多的一生,但伍尔夫打破叙事时序将奥兰多飘忽的思维动态加以展示,实验时序错位。不同时期萨沙给予奥兰多不同人生感悟,塑造其品性,影响其行为动机。这种穿插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无序流动的意识活动削弱了线性时空,虽不能真实呈现现实,“却更接近于个体精神上的现实。”[7]58十七世纪伦敦发生大霜冻,在冰冻的泰晤士河上的狂欢会中,奥兰多第一次遇见萨沙,一见钟情,随后萨沙在两人计划私奔的夜晚背叛他乘船回国。此次爱情的打击让他昏睡七天,再度醒来记忆模糊,在自家宅院开始过起离群索居的生活,并得了阅读和写作的怪病,让他时常以幻象代替现实。这一阶段象征爱情的萨沙扭转了奥兰多的人生方向,使其思索人生的意义。此后,与诗歌相伴的奥兰多时常回忆起萨沙,以其幻象代替真实。伍尔夫在此透露,萨沙的幻象皆为奥兰多脑海中的记忆。伍尔夫认为记忆如同女裁缝将脑海中的无数琐事串联。最普通的动作,也可能搅出古怪和破碎的联想。记忆将奥兰多重新拉回公主面前,让他痛苦不已。而下一秒,奥兰多就被另一张无法辨认的脸所困扰,记忆又将他拉回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奥兰多不断猜测,自言自语中引领着思绪不断变化。当爱情不再,诗歌和名望乘虚而入。诗歌在他人生中种下无法铲除的种子,直到变身为女性。思绪穿越近一个世纪,但钟表却只走了几格。通过这一心理细节描写,伍尔夫深入奥兰多内心,找到他身上诗性气质的来源,而对诗歌无法抑制的崇拜始终保持不变,也从这一角度突显了其双性同体的特质。十八世纪,在奥兰多转变为女性后,她开始以女性的视角思考与男性的相处之道,她观察到采海篷子的男人们,记忆中萨沙的身影再次附身,奥兰多想象着萨沙与男人调情的场景,终于理解她当年的抛弃行为。女性不该被任何人束缚爱情和手脚,她有权利追求一切爱情和自由。奥兰多的意识以女性视角不断流动。轮船驶到两个世纪前的狂欢会旧址处,一切的辉煌和腐朽重现,那里也是她第一次邂逅萨沙之处。这是记忆中萨沙第二次出现。当年伦敦萧条颓废与如今整洁繁荣的场景重合,记忆在上个世纪和现代之中不断摇摆。二十世纪,奥兰多漫步在伦敦,在商店内又一次遇到萨沙,她化身为大公的情妇。萨沙这次似乎与奥兰多一同穿越了三个世纪,但显然此时的萨沙依旧是奥兰多内心无法抹去的形象,她如今只存在于奥兰多的记忆中。不仅是萨沙,对于人近中年的奥兰多来说,任何事物都能将她的记忆拉回不同年代,她在自然、土耳其、印度等等空间不断跳跃。跟随奥兰多的脚步,读者可以有条不紊的穿越一个个世纪,故事时序按照线性空间排列。但跟随她的内心活动,却只能捕捉到跳跃杂乱的记忆,心理时间是意识的流动,心灵时间可以无限拉长也可以浓缩钟表时间。伍尔夫将叙事时序打乱,在不同时期深入奥兰多流变的意识活动——对过去的追忆、对现在的思考和对未来的设想,时空不断交叠,展现了奥兰多意识世界的立体景象。
除此之外,书中还出现多个静止的物理空间蕴含奥兰多心理流变,最典型的是他家乡的大橡树。奥兰多几次回到乡间,扑向大橡树,换取内心的宁静。作为自然空间,大橡树象征着永恒的自然和宇宙时间,奥兰多四百年来几次返回树下,个人的思想流动融于自然之中,心灵的瞬间流入永恒时间,这个空间给予奥兰多精神支撑,因此《大橡树》诗作也是依据这里历时四百年完成,诗作中也凝聚了他一生跌宕的经历与心境,诗作象征的文学空间与大橡树象征的自然物理空间交织,一同展现了奥兰多一生的内心真实。在乡间时,尽管年轻的奥兰多热爱写作和自然,但他觉察到自然与文字无法达成共识,浮躁的心境只有“扑向”大橡树下的土地,心系大橡树,才会感到宁静。这时的奥兰多还未参透人生的真相。在被爱情和友情双双背叛之后,他从伦敦再次返回乡下,烧掉所有诗作,只留《大橡树》。这段时间,他的心灵彻底沉浸于自然之中,思考着诸多问题。“一个人年至三十,即像奥兰多这样,思考时间就会大大拉长,行动时间就会大大缩短。”[3]53奥兰多抛弃名望,“在大橡树下进入心平气和的境界,大橡树坚硬的根须露出地面,让他感到一种内心的安宁。”[3]57一旦涉及大橡树这个空间,奥兰多的思想就会无限延长,因此大橡树是引出他内心真实的媒介。当获得人生感悟后,他将《大橡树》删删减减,文风也从华而不实转向朴实自然,给予自然与文字共存的精神指引。十九世纪,当《大橡树》的手稿再次翻出,上面的勾勾画画如同一件织补物,拼凑出整个人生历程,唯一不变的是他依然热爱自然,他的诗作和自然融合的越发和谐,格林甚至赞赏诗中对于人性、自然和真理的密切关注,并将其出版。二十世纪,奥兰多回到乡间,想起第一次与大橡树相识的1558年,四个世纪过去,给予他精神归宿的大橡树依旧矗立,对自然和世间真理的感悟凝聚在《大橡树》中,出版的诗作虽带来名望,但他要将其埋葬于树下,回馈大橡树,实现诗作只是抒发个人情感和进行秘密交流的意义。自然和文学空间的线索最终汇流,四百年的人生和心境浓缩于诗作。空间不再作为静止的故事背景,同时起到叙事作用,蕴含传主的心理流变,推动传主的故事发展,建立起立体化的叙事空间。
综上,弗吉尼亚·伍尔夫摒弃传统传记对传主歌功颂德的内容和以此教化群众的目的,倡导传记不仅要关注传主的生平等历史性真实,更要适当加入作者主体性想象,丰满传主的品性,立体化探究传主矛盾的心理真实,为传记注入了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