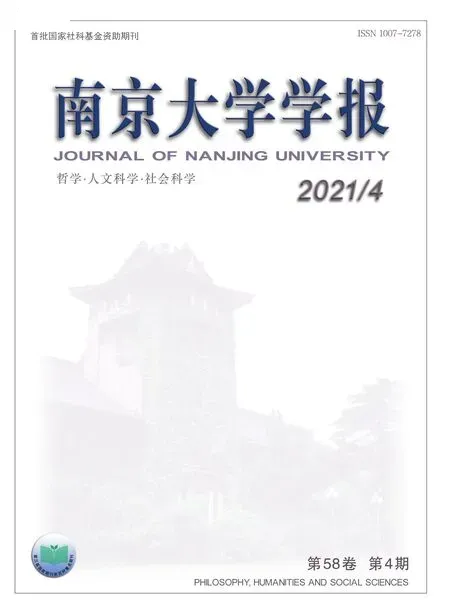融合历史语境的中国哲学阐释路径
孙 伟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101)
“中国哲学”这一术语自产生之日起就存在这样一种争论,即中国哲学究竟是应该用一种基于本土的、历史性的视角来进行研究,还是应该用一种理论的、哲学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前者往往认为中国哲学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文本和特定情境,主张从文本的历史脉络和历史社会的视角对中国哲学进行研究。后者则认为中国哲学本身是一种哲学理论,必须要从抽象理论的高度和形而上的视角来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是哲学的不同形态而已。近年来,随着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和在国际学术界地位的提升,对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成为一个日趋重要的话题。本文拟先对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讨论进行梳理,然后从欧洲哲学史的发展历程来辨析“哲学”这一概念的发展与演变,通过对孔子“克己复礼”思想的分析,尝试提出一种融合历史语境的哲学研究方法,以期解决这一问题。
一、当代学界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
安乐哲(Roger T.Ames)在其《经典中国文本的哲学化:寻求阐释性语境》(“Philosophizing with Canonical Chinese Texts: Seeking an Interpretive Context”)一文中认为,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有两个步骤需要依次进行。第一步就是要使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C.S.Peirce)提出的除了演绎和归纳之外的第三种推理方法,这就是“溯因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对于皮尔斯来说,演绎和归纳都只是从既定的逻辑前提出发来得到结论,不能超越现有的逻辑框架来增添更加新颖的内容。而“溯因推理”则不同,它是从有待解释的观察事实出发,利用背景知识和试探性构想,溯本求源,由结果去推测原因,以寻求和选择最有可能成立的结论。因此,演绎和归纳都只能用来确认一个给定假设的有效性,而“溯因推理”则不仅能够增加归纳推理的内容,而且还能够创造出新的观点,并寻求对经验事实最佳的解释(1)Roger T.Ames,“Philosophizing with Canonical Chinese Texts: Seeking an Interpretive Context,”The Bloomsbury Research Handbook of Chinese Philosophy Methodologies,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Publishing, 2016, p.51.。第二步要做的工作就是“情境化的艺术”(Ars Contextualis)。在安乐哲看来,“情境化的艺术”强调了个体需要与其所处和所构成的情境相联系,而这种情境反过来又构成了这些个体自身。因此,在这种解读方式中,“多”的背后不再有“一”,而实际上有很多具体而独特的“一”构成了它们所处的场域。由于没有了“一—多”和“部分—整体”的区分,这个世界就变成了开放式的,由无数“这个们”和“那个们”组成(2)Roger T.Ames,“Philosophizing with Canonical Chinese Texts: Seeking an Interpretive Context,”The Bloomsbury Research Handbook of Chinese Philosophy Methodologies,p.52.。
余英时也在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坦言其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从整体的观点将理学放回它原有的历史脉络(context)中重新加以认识”。但他同时也承认,“这绝不是以‘历史化’取代‘哲学化’,而是提供另一参照系,使理学的研究逐渐取得一种动态的平衡”(3)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3页。。
与这种“历史化”或“情境化”的观点不同,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哲学应该更强调哲学的论证和思考。如陈少明认为,哲学史论述包含不同层次的论证,如文献考证、文字训诂、史料校核等,但这些问题大部分与思想无关,还不是哲学论证。“哲学论证是要对文本的思路进行分析,分析论题的意义、逻辑的有效性、思想的深度或原创性、表达拒绝或接受的理据。没有这样的工作,只是对古人的言论简单归类,并将其放到现代人熟悉的哲学范畴下,无论是述者还是读者,都不会有哲学上的收益。……在此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假如有改进的可能与愿望,则提出新的论证。”(4)陈少明:《哲学与论证——兼及中国哲学的方法论问题》,《文史哲》2009年第6期。
冯耀明也认为,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哲学思想如果在哲学中是一种理论的话,就必须要在一个逻辑的背景中被理解。历史性的研究方法只在我们寻找事实证据来解释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因果联系时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不事先知道思想概念和范畴的真实意义,我们也无法开展这种历史性的研究(5)Yiu-Ming Fung,“Issues and Method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in Chinese Philosophy,”The Bloomsbury Research Handbook of Chinese Philosophy Methodologies,pp.241-242.。冯耀明认为,与历史性的研究方法不同,包含着概念分析和逻辑分析的分析哲学方法才是研究中国哲学所必需的方法(6)Yiu-Ming Fung,“Issues and Method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in Chinese Philosophy,”The Bloomsbury Research Handbook of Chinese Philosophy Methodologies,p.238.。
除了以上两种观点,还有学者主张将情境化方法和哲学理论研究方法融合在一起。信广来(Kwong-loi Shun)在其《中国思想研究的方法论反思》(“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Thought”)一文中认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策略包括三个阶段:首先,我们必须要仔细考察古代哲学文本的语言和文本细节,并且关注这一文本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样做能够使我们正确理解文本中的关键术语和思想家使用这些术语的独特方式。其次,我们需要分析思想家的观念与当下的我们之间的关联,这其实就预设了他们的观念不仅对他们自己有意义,而且对我们也同样有意义。这种预设是合理的,因为有非常多的人类经验和关注跨越了文化和时间的界限。再次,则是要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更为系统化的哲学反思,并使之与当代哲学观念和框架进行交互性的参与和对话(7)Kwong-loi Shun,“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Thought,”The Bloomsbury Research Handbook of Chinese Philosophy Methodologies,pp.68-69.。
从以上对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简要评述中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存在这样一种争论,即究竟是用一种历史情境的视角去研究中国哲学,还是用一种哲学理论概念和术语的方式去研究中国哲学?这恐怕是中国哲学在继续前行的过程中所必须要回答的关键性问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厘清“历史化”的研究方法和“哲学化”的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从以上的评述中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学者们对“历史化”的研究方法给予了比较清晰的界定和认识,就是将思想的文本置于历史情境之中去理解其可能具有的思想内涵。思想家总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情境之中,而其思想也一定会受到当时所处历史境况和遭遇的影响,因而要准确理解这一思想文本,我们必须要追溯到它的历史根源中去,理解其产生的缘由和根据。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哲学化”的研究方法,学界尚未给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有的学者主张用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有的学者主张用纯粹抽象的哲学论证的研究方法。应该说,这些对于哲学研究方法的描述都比较模糊,或只是哲学方法的某一方面,并不能由此而概括出哲学方法的实质。为了更好地理解哲学研究方法的实质,我们尝试对西方哲学——这一传统意义上“哲学”的真正诞生处——的历史及其演变做一概括性的阐述,以期发现“哲学化”方法的实质,并由此而探讨化解“历史化”和“哲学化”方法之争的一条可能途径。
二、何谓“哲学”或“哲学化”?——一种融合历史语境的哲学
所谓“哲学化”或“历史化”的视角只是本文为探讨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而暂且使用的名称。这样一种截然二分的方法只是一种分析上的需要,并不一定反映这些术语所能指涉的范围。就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哲学”——欧洲哲学而言,从其自身历史的发展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哲学”或“哲学化”本身并不仅仅是一种抽象且形而上的理论建构,事实上,欧洲哲学在现当代的发展已经呈现出思维与存在、抽象与具体、哲学与历史交融的特点。
所谓“哲学”,在其最初的意义上,我们一般将其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从泰勒斯的“水”到赫拉克利特的“火”,这些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都在为这样一个变化莫测的大千世界寻找到永恒不变的“始基”而努力。然而,这些“始基”终究还是感性世界中的事物,并不能真正解决感性世界本身的问题。柏拉图开始力图寻找一个与感官世界不同的“理念”世界。他在谈到美的理念时说道:
它(指美的理念——引者注)首先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并不是在这一点上美,在那一点上丑,也不是现在美,后来不美,也不是与这相比美,与那相比丑,也不是只有这方面美,在别的方面丑,……不在地上,不在天上,也不在别的什么上,而是那个在自身上、在自身里的永远是唯一类型的东西,其他一切美的东西都是以某种方式分沾着它,当别的东西产生消灭的时候,它却无得亦无失,始终如一。……好像爬阶梯,从一个到两个,再从两个到一切美的形体,更从美的形体到那些美的行动,从美的行动到美的知识,最后从各种知识终于达到那种无非是关于美本身的知识,于是人终于认识了那个本身就美的东西。(8)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37-338页。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理念本身是高于感性世界的任何一个具体事物的,它能够指导和规范现实世界的具体事物,是具体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哲学知识’不是要去‘理解—把握’‘真的事物—善的事物—美的事物’,而是要去‘理解—把握’‘真—善—美’‘本身’”(9)叶秀山:《哲学的希望:欧洲哲学的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9页。。柏拉图对哲学知识的这一理解似乎说明,“哲学化”的研究方法强调的是要去理解和把握终极价值本身,而不是这一价值在现实世界中呈现的种种样态及其历史背景。而“历史化”研究方法更强调研究具体的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探究这一概念在现实世界中所表现出的种种样态。但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理念世界既然不同于并且高于现实世界,那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自身呢?正如柏拉图对于“理想国”的设想,绝对的理念如果不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那就只能沦为乌托邦的空想。这种理念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其实就是纠缠西方哲学上千年的一个根本问题,绝对的理念如果要在现实世界中建立一个完全符合理念的现实,那就必然会遭遇困境。
与柏拉图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更强调在经验世界探索普遍必然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但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些分门别类的科学知识并不是最高的理论,“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才是人类最高的认知对象。在他看来,“形而上学”对于理性自身——“努斯”(nous)的纯粹思考能够给一个人带来最大的幸福(10)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21页。。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形而上学中作为最高的存在本体的是推动存在者的第一因,永恒而不动的最高本体通过“目的”来推动存在本体向存在者的转化。
在近代,笛卡尔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也是在努力推动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难题。笛卡尔认为感官世界是变动不居、值得怀疑的,而“我”的理性思考则是不可怀疑的,通过我的理性思考,我能够得知“我”这一理性主体的存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思维和存在统一了起来。但笛卡尔这一论断的问题在于——也正如后来黑格尔所批评的那样——由我的“思”只能推论出“我”这一理性主体的“在”,而无法证明现实世界的存在。
到了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康德力图规范理性的适用范围,认为理性只能认识来自感觉世界的经验材料,而不能超出这一范围认识事物的“物自体”。康德认为,“物自体”这一理性本身的产物虽然是存在的,却不是理性的认知对象,而是道德或信仰的对象。这样,康德虽力图使理性与现实结合起来,却无法使理性突破“物自体”的限制,上升到具有超越性的本体和现实的存在。此后的黑格尔将理性的能力大大提升,使之不仅成为科学认知感性世界的方式,而且也能够在现实世界中自由建构自己的世界。黑格尔认为理性的精神能够使理性从外在现实世界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存在的实体。然而,理性的精神继续前进,继续否定独立存在的抽象思想实体,使之进入经验世界之中。通过这样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理性就完成了自我的发展,而黑格尔的“绝对大全”哲学体系也得以最终建立。
到了现代西方哲学中,胡塞尔开创的“先验现象学”可以说从根本上扭转了西方哲学几千年来的发展走向。起源于古希腊的欧洲哲学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理念或理性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在这一问题上,哲学家们的解决思路大多从理念或概念本身出发,通过概念自身的运动和发展来解决现实世界何以存在的问题。胡塞尔则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他力图将外部现实世界的存在追溯到人的内在心理意识中。胡塞尔通过第一次概念的“悬搁”或“悬置”(epoché),将外在的朴素生活世界提升为一个由科学知识立法的理论世界;而通过第二次直观的“悬搁”,将这个外在的冷冰冰的物理世界内化为人的内在心理世界,“把那种有关世界是自在地、客观地存在的观点还原为世界是关于先验的主体而存在的观点”(11)张庆熊:《现代西方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65页。,这其实也就是胡塞尔所说的“先验还原”的方法。这样,生活世界既不是完全素朴的自然世界,而是具有理性立法的世界;也不是完全抽象的概念世界,而是落实在具体现实的人的直观之中的世界。因而,这样一个生活世界既有抽象性,又有具体性;既有概念性,又有直观性。这样一种思路应该说是将哲学与历史融合了起来,正如叶秀山先生所指出的:
就胡塞尔现象学来说,“过去”和“未来”,都“在”“现时”中“开显”,“历史”也是“活”的“现时”;被“经验科学”“判定”的一切“古人”,仍然“有权”在“人—自由者”的“世界”中作为“自由者”“现身—开显”,“古人”有“可能”“在”这个“自由者”“组成”的“局域—世界”里“复活”,“古人”与“时人”“同在”。没有这一层“关系”,“历史”只限于关于“过去”的“客观”的“科学知识”,而难以发挥对于“现时”的“活的—能动”的“作用—意义”(12)叶秀山:《哲学的希望:欧洲哲学的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第254页。
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哲学自身的发展已经说明了哲学本身研究方法的演变,那就是如何从纯粹哲学的抽象性、概念性,转变为抽象与具体共生、概念与直观共存的哲学与历史视角的交融,而哲学与历史视角的关系,本身也就是哲学史中所体现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一个折射。从这个角度上说,所谓“历史化”和“哲学化”这两个术语的区别使用已经没有必要。事实上,“哲学化”本身就已经蕴含了“历史化”的因素,就“哲学化”所能指涉的内容而言,正如欧洲哲学史的发展所证明的,已经包含了“哲学”与“历史”二重视角的交融。
三、融合历史语境的“哲学”——以“克己复礼”之论争为例
20世纪90年代初,学界围绕何炳棣、杜维明两位先生关于《论语》中“克己复礼”之义解的论战此起彼伏,影响深远。这场论战虽以“克己复礼”为中心而展开讨论,但其所涉及的主题则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问题。让我们先看一下《论语》中的这段话: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何炳棣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礼”的起源要比“仁”早得多,孔子以维护西周礼制为一生重要使命,更因为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才要大声疾呼恢复西周的礼制。孔子“仁”的学说,就是要以仁说把礼全部合理化、意识形态化。也就说是,孔子的“仁”是为“礼”服务的,而不是相反(13)何炳棣:《“克己复礼”真诠——当代新儒家杜维明治学方法的初步检讨》,《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8期。。何炳棣进而认为,孔子的“克己复礼”是针对《左传》所记载的楚灵王之事的具体历史情境而言的,强调了“礼”的外在约束和规范性,而“克己”也是指克制自己种种僭越无礼的欲望,并非杜维明所认为的“修身”之意(14)何炳棣:《“克己复礼”真诠——当代新儒家杜维明治学方法的初步检讨》,《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8期。。
我们可以看到,何炳棣主要是基于历史的立场,从历史文献和情境出发来解释“克己复礼”的内涵。那么,这种“历史化”的解读方式是正确的吗?让我们先深入到孔子思想所发生的历史场景和《论语》文本的思想脉络中,以建立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基本认识。
中国的春秋时期对很多具有怀古情怀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传奇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思想和文明,而春秋时期的社会特点和思想文化传统也直接影响了后来战国时代的思想文化走向。春秋时期是一个古代文化光辉灿烂的时代,从西周承袭而来的礼乐文化,经过春秋时期贵族文化的发扬和传承,演变成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形式(15)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1页。。但在春秋时期,由于宗法制度的变化,原有的以宗族内部分封为主的制度逐渐转化为异姓大夫主政的局面。在这种局势下,原有的以祭祀等礼仪活动为主要职能的官职(如太宰等)逐渐被忽视,而以军事、行政等职能活动为主的官职逐渐得到重视。陈来先生认为:
春秋时代是宗法政治和宗法封建的解体之初,还看不到完整的、新的制度创新的出现。与此相应,一方面,社会生活依然浸润于礼乐文化的氛围之中,……另一方面, 政治生活秩序的“礼崩乐坏”成了春秋后期的特征,社会变迁无情地推动着文化的变迁。……春秋时代的礼仪之辨,表明西周以来的“礼乐”为主的礼文化发展,已经转变为一种对“礼政”的注重。礼之被关注,不再主要因为它是一套极具形式化的仪式和高雅品位的交往方式,人对“礼”的关注已从“形式性”转到“合理性”(16)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01、213页。。
社会和政治的变迁促使着礼的内容的转向。到了春秋末期,这一政治化的转向就更加明显了。面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社会和各诸侯国宗族势力的日益膨胀,孔子斥责了当时鲁国贵族僭越礼制的行为: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
从春秋末年的历史境况来看,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的主张当然有为矫正当时社会出现的礼崩乐坏问题的一面。然而,从更深的层面上说,如果只是对礼乐崩坏的现实进行单纯的指责而不去探究造成这一现实的内在原因,或者基于这一礼崩乐坏的现实而只去诉诸外在的规范,这一混乱的社会现实将很难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因此,孔子颠沛一生所要做的就是寻找到人内心的道德根源,从而建立以内在道德为主导的清明政治秩序。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仁,那就必然不会遵从正确的礼乐制度。因此,人内心中的仁应该是比礼乐更为重要的因素。既然如此,那仁似乎应该在礼乐之前就要产生,因为只有仁人才能创制礼乐流传后世。这一逻辑恰好被接下来孔子与子夏的一段对话所证实。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很明显,孔子非常认同子夏所说的礼乐产生于仁之后的说法。这似乎说明,比起何炳棣先生所主张的礼乐制度先于内心之仁的观点,孔子更倾向于相信仁是人内心本身就固有的。这其实是后来孟子对孔子思想进行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在“礼之本”的问题上,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孔子认为,礼与其奢侈,不如简朴,这就意味着礼的形式并不是那么重要,礼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和促进人的道德情感的发展和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舍弃了人的真实情感而去追逐礼仪的形式,就本末倒置了。
从上述对于春秋时期思想文化背景和孔子思想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思想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背景。正是春秋时期政治生活的“礼崩乐坏”和诸侯征伐的混乱局面促使孔子去重建礼乐文化、拯救世道人心,而其中的核心价值和观念就是由“仁”“义”“礼”所构成的儒家之道。由此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很难与其所处的特定而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剥离。事实上,中国哲学中的哲学思想和作为其载体的思想家总是处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而要理解这些哲学思想产生的渊源和根由,就必须要回到当时的思想传统之中。唯有如此,才能对这些思想有相对准确的认识。因此,对于“克己复礼”这一概念的考察离不开对孔子所生活的历史情境和相关文献的考察,这是对这一概念进行深刻认识的前提。孔子所处的礼崩乐坏的历史时代背景构成了孔子重建礼制秩序的当然前提,而这一礼制秩序的恢复和建立也是为了匡正当时时代和社会的弊病。从这一角度上讲,“克己复礼”当然有克制自己欲望、遵从礼制的内涵。对于孔子来说,“复礼”也就是要用礼来约束人们的日常行为,使其能够在待人接物时容纳他人,更为他人考虑。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清明的社会政治秩序。
从这个角度上讲,何炳棣先生从历史文献和情境出发来解读《论语》,当然有其合理性,而且也是必要的。然而,对哲学思想的历史性追溯并不意味着哲学研究的结束,而恰恰是哲学研究的起点。对于“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的解释也不能仅仅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只去探讨文本本身在其所发生的历史场景中的含义,更应该超越文本本身的历史场景,探讨其蕴含的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哲学内涵。
事实上,“克己复礼”虽有提倡礼制秩序之意,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仁,也就是“克己复礼为仁”之意。“礼”本身就是一种人群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其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要为他人考虑而不能只是一味地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这样,用“复礼”这种外在的方式,人就能逐渐实现自我私欲的淡化,从而逐渐实现仁的最终目的。孔子要实现仁的途径是通过外在礼乐的实践。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人会乐意去从事礼乐的实践呢?人由于自我利益的驱动,很难为他人考虑,因而如何在内心中解决这个容纳他人的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也就是说,礼制本身也要有一定的道德心理学前提才能真正确立。对于孔子来说,人内心一定是有潜在的、可以转化为“仁”的品质。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孔子的这段话如果只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只去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惘,只去思考而不学习就会危险。但如果联系《论语》文本的整体思想脉络,这句话也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解读,那就是——如果人只去追求外在的知识见闻而不返求自己的内心,使外在的见闻成为发掘自己内心智识与良知潜力的力量,那学习就失去了方向,“智识仅如登记上账簿,学问只求训练成机械”(17)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38页。。所以,人学习的知识与其说是一种从外而内获得的知识,不如说是一种为了从内而外激发人心智识与道德力量的工具。对于孔子来说,学习如此,礼乐实践同样也是为了激发内心已有的道德智识,使之得以充分地发展。因而,人内心中已经具有的道德智识——“仁”这一道德形而上本体,就成了人能够从事礼乐实践并接受礼乐教化的心理前提,而人的礼乐实践又反过来促进了内心道德智识的成长和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礼乐都是外在的规范,它必须要有其内在的根源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对孔子来说,这个内在的根源就是仁。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仁”其实就是一个人在心中能够考虑到他人,推己及人,如何对待自己乃至亲人,就应该如何对待他人。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孔子在这里向诸弟子说出了自己的志向,就是对老者尊重安抚、对朋友互相信任、对年轻人关怀爱护。其实无论是子路还是颜渊,他们所说的志向也同样是去除私心,待他人如对自己,只不过子路更加偏重在物质方面与他人分享,而颜渊则在道德方面要求自己待他人如对自己。孔子则更进一步,以对待自己之心来对待老者、朋友和少者。这无非是以自己的公心来对待他人,应用到老者就是“安之”,应用到朋友就是“信之”,而应用到少者便是“怀之”。这便是孔子所主张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之道。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已经为外在的道德原则和伦理规范找到了内在的根源。这一根源便是来自于人们内心的“仁”,也就是去除私欲之后的“公心”,用此心来对待他人便是所有道德规范的最终根据和起源所在。
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此章对仁的形而上境界及其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做了深刻阐述。孔子认为,人如果不能达到仁的境界,就不能安处于困境之中,也不能长久地安处于快乐之中。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能达到仁的境界,人就不能实现自我与他人乃至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有了自我和他人或他物的分别,人就不能安处于外物或外境对自我的限制和约束中,因为这种分别心造成了人与自然和其他人的对立。同样,这种自我与他人或他物的分别同样使得人无法长久地处于快乐的境地。如果没有达到仁的境界,人的快乐无非来自于对其他人或外在事物的追求而获得的满足感上,但这种满足感很快就会消失,因为外界的诱惑会无穷无尽地汹涌而来,人由于某些事物而获得的满足感很快会因为新的诱惑而消失,继之而来的则是新的焦虑。而如果实现了仁这种“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没有了分别心,外物来之则来,去之则去,并不能在心中留下半分,因而也不会产生过于快乐或焦虑的情绪。所以,仁者就会安于仁的境界,智者就会想要达到仁的境界。
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仁”虽然可以看作一种道德的原则,但从更深的本体层面上思考,“仁”也是一种彻天彻地、通贯古今的形而上本体。这一形而上的本体超越了人世间具体伦理关系的束缚,成为一种具有无限性、自足性的本体。孔子的思想虽然产生于具体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之中,但其一旦产生,就具有了思想所独有的时空穿透力和持久生命力。“仁”“义”“礼”这些概念虽然有其特定的时代针对性,但作为哲学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已经超越了孔子所处的时代,一直延续到当下的思想发展进程中。这样,当我们面对这些来自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概念时,就不能只局限于其具体的历史传统中,而要深入分析其形而上的哲学思想及其与当前时代的可能联系。正如陈少明所言:
一方面,古典的观念必须在古典生活经验中理解;另一方面,还可以直接从古典生活经验中提取我们需要的观念。这就是做中国哲学的“中国”依据。……做哲学者,必备的信念是人类无论古今东西,都具有可以共享的经验或问题。只有证明脱胎于古代经验的观念也能有效解释或引导当下的生活,才是具有普遍性品格的哲学工作。(18)陈少明:《“做中国哲学”再思考》,《哲学动态》2019年第9期。
顺着“哲学化”的思路,对于“克己复礼为仁”,杜维明、刘述先等学者不同意何炳棣的观点,展开了一系列的论辩。杜维明认为“克己”这个概念与“修身”的概念密切相接,在实践上是等同的。虽然“克己”也有克制自己欲望之意,但并非意味着“人应竭力消灭自己的物欲”,事实上,“人应在伦理道德的脉络内使欲望获得满足”(19)杜维明:《从既惊讶又荣幸到迷惑而费解——写在敬答何炳棣教授之前》,《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8期。。同时,“克己”并不是强制的禁止或外在的克制,而是疏导和转化。对于“礼”,杜维明认为“礼”本身有“周礼”之意,但也有广义的文化制度与日常生活规范之意,具体到“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礼”应该不是特指周礼,而是一般意义上的礼(20)杜维明:《杜维明先生有关“克己复礼为仁”争论的系统诠释与回应》,向世陵主编:《“克己复礼为仁”研究与争鸣》,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第463、464页。。
刘述先则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何炳棣的观点提出质疑:“何先生似乎还囿于纯粹客观史学的窠臼之内,这种史学观念已经受到严厉的批判而过时。晚近的解释学或诠释学(hermeneutics)指出,先见(preconception)乃至成见(prejudice)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要紧的是照察到自己的成见而希望做到视域的交融(merging of horizons)。”(21)刘述先:《从方法论的角度论何炳棣教授对“克己复礼”的解释》,《二十一世纪》1992年第9期。这就是说,对于诠释学而言,历史文献的研究不能只从客观的、历史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还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创见融入其中。这似乎说明在研究历史文献时,客观历史的视角和哲学思考的视角缺一不可,二者之间需要交融并存。然而,刘述先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更强调了哲学思考的重要性。正如他对《左传》中“克己复礼”的说明,认为这句话是在说楚灵王没有做道德修养工夫克服自己的私欲,因而在乾溪受辱,这恰恰说明孔子是由启发性的角度来做出道德的评论。同时,刘述先认为《论语》中的“克己复礼”明显是讲个人的道德修养工夫,别无异解。这就等于否认了“礼”是指西周礼制的可能性,同时楚灵王等的历史史实对于孔子思想的阐发也没有太大意义(22)刘述先:《从方法论的角度论何炳棣教授对“克己复礼”的解释》,《二十一世纪》1992年第9期。。
杜维明、刘述先等主要基于“哲学”的立场,从“礼”与“仁”的内在关系出发来解释“克己复礼”。这一论战充分展现了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究竟是从历史情境的角度,还是用哲学思辨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那么,对于孔子的“克己复礼”来说,究竟应用何种立场来进行研究呢?
我们可以看到,杜维明并没有否认“克己”所具有的克制、限制自己欲望的含义,但更强调这一过程所带来的积极结果,也就是“修身”。的确,克制自己欲望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人在用自己已有的道德智识来对抗、疏导和转化自身欲望的过程,这当然也就是儒家所讲的修身之意。“克己”与“修身”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但具体到《左传》的具体历史场景中,“克己”很可能是针对楚灵王的行为而言的,更偏重于强调克制人的过度欲望而言,而较少具有修身之意。当然,修身之意在逻辑上也是完全可以推论出来的。同样,对于颜渊问仁这一场景,“克己”很可能更加强调人的道德修身方面,而较少具有历史场景的针对性。
当然,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的历史现实也是《论语》中“克己复礼”这句话提出的真实历史背景。颜渊是孔子最喜爱的弟子,但即便如此,孔子在回答他什么是仁时,也还是主张“克己”“复礼”,强调通过遵循礼制来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进行道德修养工夫。这当然不能说明孔子认为颜渊没有足够的道德自觉性因而不得不诉诸礼制约束,但很可能显示了这样一种状况,即对于孔子和颜渊所处的时代而言,礼制的衰败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而要实现儒家的最高理想——仁,也不得不从当时的历史和社会场景出发,从恢复、遵循礼制开始,才有可能逐渐实现这一最高理想。孔子针对弟子的回答都是根据弟子的禀赋、才性以及当时具体的情境而言的。对于颜渊问仁,孔子应该也是针对颜渊的具体情况而言的。孔子当然相信颜渊凭借自己的天赋和才能,也完全有可能领悟到仁的真正含义。但对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如何通过恢复和遵循礼制来实现仁,才是一个儒者应有的现实关怀。对于一个儒者来说,虽然自己实现仁也很重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让整个社会建立清明的政治秩序,让民众有良好的生活,而这恰恰在于礼制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孔子来说,礼制的恢复和重建正在于像颜渊这样的儒家典范人物的亲身实践和表率,这也就是颜渊后来说“请事斯语”的缘由。
因而,对“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的阐释可以用一种融合历史语境的哲学视角来进行。无论是在《左传》还是在《论语》中,虽然解读的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可以兼顾历史与哲学,用一种融合历史语境的哲学视角来解读文本。
行文至此,我们或许能对何炳棣和杜维明等先生关于“克己复礼”问题的争论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克己复礼”这一概念的诠释而言,一方面要看到这是孔子为匡正当时礼崩乐坏的时代弊病而提出的现实方案,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之下提出的实现良好政治秩序的方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到孔子所要恢复的礼制是为了培养人内心的仁——这一儒家的最高形而上理想,而这一最高的形而上理想对于古人或今人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孔子来说,人如果只是遵从外在的礼制规范而行动,那只是最低的要求,并不是最好的结果。最高的要求应该是人从自己内心的仁出发,主动自觉地从事道德行为。对于“克己复礼为仁”的解读应贯通这一最低要求和最高要求,融合历史情境和哲学思辨两重要素。从这个角度上说,何炳棣先生和杜维明先生的观点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何炳棣先生的“历史化”解读方式没有考虑到哲学思想的抽象性和普适性,而杜维明先生的“哲学化”解读也似乎只是局限于抽象思辨意义上的哲学,没有融入历史情境的视角,因而并没有考虑到西方现当代哲学尤其是现象学的最新进展。事实上,如果现象学本身已经体现了哲学与历史二重视角的融合,那就可以说融合了历史语境的哲学才是解读中国哲学概念和术语的正确方式。
中国哲学的研究需要通过一种融合历史语境的哲学来实现,这就要求一方面用历史性的视角来回溯思想的产生根源和发展历程,认清思想的历史情境因素;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哲学研究来深入思想本身,分析其内在的概念和术语,以形成与古人思想平等而交互性的对话。中国哲学的这种融合历史语境和生活世界的哲学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回应了欧洲哲学几千年来尤其是在现当代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中西方哲学都在努力寻找一条融合思维与存在、抽象与直观、哲学与历史、概念世界与生活世界的研究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