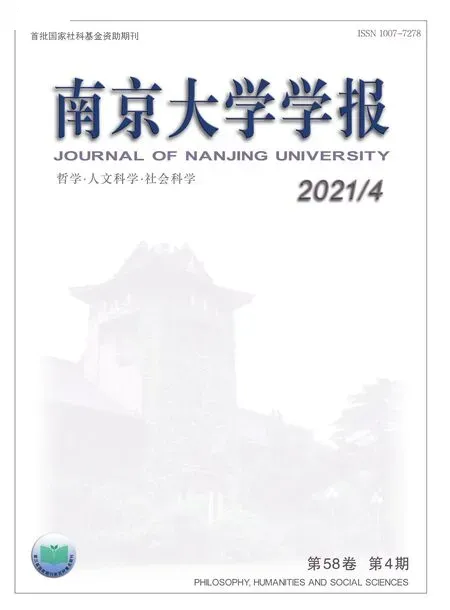从五方五色到五德终始
——论五行说核心之变迁
安子毓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曾经笼罩中国古代社会的“五行说”包含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除“五行”以外,同样也包含了“五方”“五色”“五味”“五脏”等诸多元素。只是因为秦汉以来,“五行”为此理论之核心,故而这一以“五”为名的神秘理论被命名为“五行说”,其他元素皆被视作“五行”之从属。
以此种传统意识为前提,顾颉刚先生曾认为《史记》中刘邦斩白帝子、汉初尚赤、秦国祭白帝等记载与秦及汉初奉水德而尚黑的历史背景相悖,为后人伪造(1)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编:《古史辨》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92-500页。事实上,秦及汉初尚黑之风承自先秦,与“水德”亦无直接关联。参见拙作《“上黑”渊源考》,《史学月刊》2017年第2期。。然钱穆先生却指出,这里使用的理论并非五德循环,而是“方位配五行颜色”(2)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编:《古史辨》第5册,第625页。。
通过梳理先秦史料及考古资料,对比二说,实当以钱说为长(3)除钱穆先生以外,杨向奎、杨权等先生亦同此论。不过,杨向奎、杨权两位先生在文中认为《史记》不存在窜伪的观点则很难成立。除了笔者所考论的秦代史事之外,在西汉后期已遗失的10篇文字在今本《史记》中已被补齐,至于司马迁身后史事更是散见于今本《史记》各篇,皆为显证。仅是前述文字不涉窜伪而已。参见杨向奎:《西汉经学与政治》,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第25-37页;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5-113页;杨权:《论汉初的色尚赤》,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秦汉史论丛》第12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3-353页;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余嘉锡文史论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1-99页;赵生群:《〈史记〉亡缺与续补考》,《汉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以及拙作《李斯“督责之书”系伪作辨》,《史学月刊》2013年第7期;《〈史记〉秦代史事辨疑三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编:《形象史学研究(2013)》,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2-285页。。事实上,钱说称“方位配五行颜色”尚嫌保守,在先秦时代,“五方五色”实为这一以“五”为名的神秘理论之核心。而“五行”出现的时间不够早,加入此体系时间更晚,一度不过是居于从属地位的配角罢了。这一点前贤已有提及。徐复观先生曾指出在邹衍之前的学说只是以“五”名数,并未以“五行”为中心进行附会(4)徐复观:《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488页。。安志敏、陈公柔两位先生在对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进行仔细研究后,指出帛书中明确表现了五色配五方的观念,却并未与五行联系,可见直至此时“五行之说”尚未成立(5)安志敏、陈公柔:《长沙战国缯书及其有关问题》,《文物》1963年第9期。。刘起釪先生的判断更为明确。他举子弹库帛书与《管子·幼官》为例,认为“战国时期楚国所流传关于‘五’的思想还没有和金、木、水、火、土结合起来”,“大概这时还只有五色、五味等和传统的五方观念相结合,后来才发展到和五行相结合的”(6)刘起釪:《释〈尚书·甘誓〉的“五行”与“三正”》,《文史》第7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页。。几位先生所言甚是,然或是因为这些内容并非文章的论述重点,似未引起足够的关注(7)其中,刘起釪先生的文章因其行文简约,未详尽区分具体概念,还引起了一定的误会。赵光贤先生曾以《吕氏春秋》对五德终始说的记载为证,论证五行说并非汉代人的学说。参见赵光贤:《新五行说商榷》,《文史》第1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41-346页。事实上,刘先生本意并非是说战国人不知道五行——“金、木、水、火、土”,而是说这一组元素长期未被纳入以“五”为名的那套理论,更未成为核心。。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此说详论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甘誓》与先秦时期“五行”的含义
《尚书》的《甘誓》《洪范》两篇一般被认为是最早记载“五行”的文献。据此,许多学者将“五行”这一概念的形成上推至商代乃至夏代。这样看来,“五行——金、木、水、火、土”的起源似乎甚早。然细查原文,这一判断并不确切。
《甘誓》云:“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8)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54页。依此记载,“五行”说在夏代初年似已产生。然而,正如梁启超先生所指出的,与“五行”并言之“三正”一般认为是建寅、建丑、建子,分别对应夏、商、周。然彼时既无商、周,何来“三正”?而“金、木、水、火、土”又何以能“威侮”(9)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顾颉刚编:《古史辨》第5册,第350页。?因此,梁先生认为此句当解作“威侮五种应行之道,怠弃三种正义”,至于其细节“固无可考”(10)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顾颉刚编:《古史辨》第5册,第350页。又,《左传·文公七年》有云“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徐复观先生猜测此“三事”或即“三正”,然无确据。参见徐复观:《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474页。。考究先秦时期“五行”一词的含义,可以发现,梁先生的这一推断是比较合理的。
刘起釪先生曾指出,“五行”一词在战国时期有多重含义(11)刘起釪:《释〈尚书·甘誓〉的“五行”与“三正”》,《文史》第7辑,第14-15页。,此说甚是。汉代以来,“金、木、水、火、土”与“五行”几乎成为同义词,被视作五行理论之核心。但这一观念并不能混同于先秦时代的观念,即使在战国后期,甚至到西汉前期,此种指代也尚未在社会中形成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观念。在先秦时代,“五行”与“金、木、水、火、土”的对应关系是游离不定的。甚至连“五”这种分类法在当时都尚未固化。如《左传·文公七年》即谓“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此种分类在《淮南子·泰族训》中犹有余绪:“水火金木土谷异物而皆任,规矩权衡准绳异形而皆施……”
即使在“五”的体系下,这种关系依旧是游离的。“金、木、水、火、土”在先秦的总称并不只“五行”这一种。《左传》中“天生五材,民并用之”一句,据杜预注,五材即“金、木、水、火、土”(1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36页。。刘起釪先生则根据《史记》等书的记载,认为邹衍对此五种元素的称呼为“五德”,而非“五行”(13)刘起釪:《释〈尚书·甘誓〉的“五行”与“三正”》,《文史》第7辑,第18页。。然而在《吕氏春秋》中,祖述邹衍之说的《有始览》称此五种元素为“气”,反倒是不涉及其说的《十二纪》以“德”名之。可见先秦时期此种称呼之模糊随意,至战国末年犹然。
反过来讲,“五行”所代指的元素,在先秦也绝非“金、木、水、火、土”这一种解释而已。《荀子·非十二子》曾指责所谓“思孟五行”。古代学者认为其所指为“仁、义、礼、智、信”(14)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94页。,近代多有学者认为其所指为“金、木、水、火、土”(15)章炳麟:《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页;吕思勉:《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顾颉刚编:《古史辨》第5册,第372页;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编:《古史辨》第5册,第407-410页;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19-130页。余例不详举。。随着马王堆帛书《五行篇》与郭店楚简《五行》的出土,终由庞朴先生考定其所指为“仁、义、礼、智、圣”(16)庞朴:《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的初步研究》,《文物》1977年第10期;庞朴:《思孟五行新考》,《文史》第7辑,第165-171页;庞朴:《帛书〈五行〉篇评述》,《三生万物:庞朴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8-331页。,亦属于道德规范范畴。事实上,以“五行”作为五种道德行为规范的代称,在先秦典籍中是很常见的,远高于指代“金、木、水、火、土”的频率。除了受到指责的“思孟五行”之外,《荀子·乐论》还提出了荀子所提倡的“五行”:“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国矣。”《吕氏春秋·孝行览》则将五种行为规范与“孝”牵合起来,声言“五行不遂,灾及乎亲,敢不敬乎”,体现了以“孝”治天下的思想。此外,《庄子·说剑》又有云:“制以五行,论以刑德。”(17)《说剑》篇思想与老庄思想不类,据学者研究,此篇很可能是楚人庄辛之文被误羼入。参见赵逵夫:《我国最早的一篇作者可考的小说——庄辛〈说剑〉考校》,《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这里的“五行”何指,文中并未明言,但既与“刑德”对举,则其意当亦指道德行为规范而言。
除了指代道德规范外,“五行”可能还曾是星名。《韩非子·饰邪第十九》云:
此非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数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数年在东也。(18)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2页。原文多两个“非”字,不通,据王氏本注删。
此篇所列诸星名,大多不见于《史记·天官书》乃至后世星图,故对于其注释,注家多采取回避态度。文中既已提及“岁星”“荧惑”,则此“五行”非指五大行星甚明。既云“数年在西”“数年在东”,则此星之所指显亦非恒星。而肉眼所见在天球面上运行的诸星中,除五大行星外,最常见的非彗星莫属。古人称彗星为“妖星”,先秦时即已有所谓“妖星占”出现。因彗星数目众多,周期不一,总结规律甚难,因而当时占卜系统中的大量“妖星”实多为术士向壁虚构(19)陈颖飞:《〈孝经雌雄图〉三十五妖星建构考》,《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陈颖飞:《〈河图稽耀钩〉妖星系统考》,《南都学坛》2009年第2期。。且此段文字之主旨又恰在抨击占卜之不足信,与妖星之占卜作用正合。然则此段文字中所列诸星,或当为行星与“妖星”之汇总。若此论不误,则“五行”自当为某一“妖星”的星名了。
综上,可知“五行”在先秦时期有着诸多含义,且多与行为规范有关。《甘誓》中的“五行”实当采梁启超说,以“五种应行之道”为解。
二、《洪范》与先秦时期的经、注格式
与《甘誓》篇模糊其词,难以确据不同,《尚书·洪范》对“五行”的定义似乎就比较详细了: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五行”就此被定义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并和辛、酸、咸、苦、甘五味对应了起来。《洪范》被认为是商末贤臣箕子回答周武王问政的记录,在汉代被推崇至极,成为五德终始说的根基。
然而,从《尚书》成书的过程来看,这一根基恐怕并不坚实。刘起釪先生认为,《甘誓》篇当源于商代,但已为周代太史所改写(20)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2册,第875页。。《洪范》篇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左传》《说文》引用此篇时皆称商书,而其思想近于神权统治,故刘先生认为,此篇核心部分当为箕子所作,写成于商末周初。此篇文字中又多有周人“德”政观,用韵近于西周金文,故其核心以外的部分应是从西周到春秋期间被陆续加入的(21)刘起釪:《〈洪范〉成书时代考》,《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05-1221页。。刘先生此判断当接近情实,对《洪范》篇非一时一人所作的判断尤属慧眼独具。《尚书·洪范》开篇载武王访箕子问政,箕子追述上天赐禹“洪范九畴”: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其后文字则在分释“五行”等“洪范九畴”。对于“初一曰五行”以下这段总纲式的文字,前人多有讨论。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对此总结甚详,指出汉代时有上帝赐禹《洛书》的传说,部分古代学者认为此总纲文字为《洛书》本文,另一些则认为总纲中只有部分文字为《洛书》,其余为禹所添加(22)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3册,第1151-1152页。。
将这段核心文字归之于大禹、《洛书》,固属无稽,但这么多学者将这段文字单列出来甚至进一步细化,背后是有原因的。事实上,《洪范》开篇的总纲和后面大幅的解释,构成了经典的经传体例。这种先列总纲后行解释的写作方法,被后世不少学者借用为著述体例。如《韩非子·内储说上》等篇即为其例(23)《韩非子》第三十至三十五篇皆为经传体例。,而《史记》开创之纪传体实亦有模仿此体例之用意。然而此种体例之原初,却本应是先贤作本经,后学作注疏,本经与注疏不当是同一作者所为。正因如此,才会有将本经之作归于大禹的说法产生。
事实上,古书之流传全凭传抄,若抄写不慎,经、注极易混同不辨。以《大戴礼记·夏小正》为例,其本经与注语即已完全“错糅”(24)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页。为一体。再如传世《逸周书》正文中实已包含早期学者的注解,是以《逸周书》各篇篇名皆加“解”字(25)详见下文第三节。。另外,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篇》,经庞朴先生研究,实包含“经”与“说”两个部分,然而帛书中“经”“说”实已混同。20年后出土的郭店楚简证实了庞先生的这一判断,楚简中有与帛书相同内容的“经”而无“说”,可见“说”的部分实为战国后期至汉初之间的学者所作(26)庞朴:《竹帛〈五行〉篇与思孟“五行”说》,《三生万物——庞朴自选集》,第332-342页。。值得指出的是,《逸周书》与帛书《五行篇》注文总列于全“经”之后,各注文前列出“经”之关键字,以示区分,与《洪范》篇极类,上文谈及的《韩非子·内储说上》等篇亦同此例。可见此形式实为先秦注文之常用模式,与后世更为流行的夹注体例颇为不同。
除体例之外,这段文字的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武王所问,箕子所答,其核心实在“彝伦”二字。所谓“彝伦”,即“常伦”,亦即“伦常”。如果剥离掉汉代经师的故弄玄虚,“金、木、水、火、土”实在难以与“伦常”相联系,更遑论列为“九畴”第一条了。事实上,细察总纲中所谓“九畴”,实多含有行为规范的意味,则所谓“五行”亦当与行为规范相联系方才合理。如上节所论,在先秦时代,所谓“五行”并不单指“金、木、水、火、土”而言,更多的时候,其所指实为五种规范。可见,将总纲中的“五行”释作五种核心行为规范无疑更为合理,所谓“一曰水,二曰火”之类实当为后人之附会(27)事实上,如梁启超、徐复观先生所论,即使是这段文字,亦不过是简单言说五行的物质性质,较之汉儒所附会的种种神秘性亦相差甚远。参见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顾颉刚编:《古史辨》第5册,第350页;徐复观:《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488页。个人以为,此段文字当出自战国中晚期,在《管子》所宣扬的以“五”为名的“五方五色”说产生较大影响之后,邹衍所创以“五行”为核心的“五德终始说”大行其道之前。。由此可见,《洪范》开篇这段总纲性的文字和后面的解释并非一体,其所谓“五行”当亦指“五种应行之道”而言。
此外,关于《尚书》中提及的两处“五行”,刘起釪先生曾提出另一个解释,即五大行星,并认为这才是“五行”的本意。齐思和先生亦曾提出,“五行”之说源自天文学家(28)齐思和:《五行说之起源》,《中国史探研》,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此解释于理亦顺,但在史料上缺乏支持。按此说法,五大行星既为“五行”之本源,自当很早就被纳入五行体系,但究之史料,唯木星在《管子·四时》篇被纳入此体系,却是以“岁星”之名与日、月、星、辰并列,与所谓“五大行星”无涉(29)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42-854页。。除此之外,五星在《管子》《吕氏春秋》中皆不预五行体系。如徐复观先生所言(30)徐复观:《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502页。,迟至西汉成书的《淮南子》方将“五星”纳入其中(31)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8-89页。。以此观之,此说论据似嫌不足,恐难成立。
三、《逸周书》中的“五行”
除《尚书》之外的早期典籍中,《逸周书》亦有不少关于“五行”的记载。关于此书的成书年代,学者争论颇多。综括而言,大致可知该书之撰写从西周开始,到春秋末甚至战国初为止,其主体部分之编定大致在战国初年(32)李学勤:《序言》,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序言第2页;祝中熹:《〈逸周书〉浅探》,《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连龙:《〈逸周书〉源流及其所见经济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唐元发:《〈逸周书〉成书于战国初期》,《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罗家湘:《〈逸周书〉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在此书中,《武顺解》《成开解》《周祝解》都已提到“五行”。然其指代对象颇为模糊,细揣其意,当亦指五种行为规范。然其中《小开武解》的这段记载却看似颇为不同:“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苍,位木;四白,位金;五黄,位土。”此篇文字,学者多认为成文于春秋以前,其内容为周初之事。按此记载,西周以前似已形成了“五行——金、木、水、火、土”。然细读前文,可知并非如此。此文开篇云:
周公拜手稽首曰:“在我文考,顺明三极,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视七顺,顺道九纪。三极既明,五行乃常;四察既是,七顺乃辨;明势天道,九纪咸当;顺德以谋,罔惟不行……”
之后文字则在分释“三极”“五行”“七顺”“九纪”,明见前文才是本经,后文为传语,二者并非一体,其格式与前述《洪范》篇极类。此种解释性的传语在《逸周书》各篇中多有,黄怀信先生指出,这是早期学者的注文。《逸周书》各篇篇名均云“解”,即指此注文而言。这些文字本是早期注解,其后与正文混同难辨,以致后人多有误会各篇“解”字为西晋学者孔晁注释《逸周书》时所加(33)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第81-85页。。这些注解究竟为何人所作,已难考证。黄怀信先生根据书中的用语特色、避讳体例,认为此解为汉朝景帝、武帝时人所作(34)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第85-86页。,或可信从(35)此外,古来有不少学者将《逸周书》的佚篇《月令解》与《礼记·月令》等同,然并无确据。参见杨宽:《月令考》,《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3-469页;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15-617页。今按,《礼记·月令》文字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相关内容略同,铺陈五行体系颇细。从后文将要论述的《管子》之前的五行说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早期的《逸周书》不当出现《礼记·月令》这样体系完备的五行系统。古代学者的这一猜测恐难成立。张小稳《月令源流考》一文对“月令中五行系统为后加”之观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参见张小稳:《月令源流考》,《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
综上,《尚书》《逸周书》提及的“五行”,皆当以“五种应行之道”释之,而难以视作“金、木、水、火、土”这一组合之代称。在其他先秦典籍中,有可能部分成书于西周以前的《易经》《诗经》两书亦未载“五行”等相关概念,对“金、木、水、火、土”的确切记载最早当出现在春秋末年至战国中期成书的《左传》《国语》二书当中(36)主要见于《左传》之《昭公二十五年》《昭公二十九年》《昭公三十二年》;《国语》之《鲁语上》《郑语》。齐思和《五行说之起源》对此搜集甚详,故不赘述。,由此看来,“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形成时间不应上溯得太过久远。
四、五方五色说的形成
如上文所论,“五行”这一概念的产生当不早于春秋时期,且不成其为体系。与之相较,“五方”的概念起源极早——胡厚宣先生根据甲骨文卜辞,指出商代已有“四方”“五方”之观念(37)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外一种)》上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5-277页;胡厚宣:《论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外一种)》上册,第277-281页;胡厚宣、丁声树:《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补证》,《责善半月刊》1942年第22期。。
至于方、色之配,有观点认为史前时代即有(38)冯时:《陶寺圭表及相关问题研究》,刘庆柱主编:《考古学集刊》第1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7-58页。,然似乏确据。在早期的史料中,似仅《逸周书·作雒解》有云:“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亹以黄土。”(39)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册,第534页。其中“青”“亹”两字从其校。关于《作雒解》的成篇年代,刘起釪先生认为此篇当为西周文献(40)刘起釪:《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6页。,黄怀信先生观点略同,认为此篇文字至晚不晚于春秋早期(41)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第110页。。不过,赵光贤先生对文中内容提出了质疑,认为此文为春秋战国时人的伪作(42)赵光贤:《〈逸周书·作洛〉篇辨伪》,《文献》1994年第2期。。屈万里先生则根据上面的引文,认为其内容关涉五行,当为战国之作品(43)屈万里:《先秦文史资料考辨》,台北:联经出版社,1983年,第398页。。今按,目前学界似多赞同刘、黄等先生所论,据此,此篇内容很有可能是西周初年史事的反映,似当为“方”“色”之配的最早记录。不过,正如刘、黄二位先生亦承认的,此篇文字并不甚古,当为东周人所改写——事实上,其笔法甚至较《左传》《国语》更为简易。此外,据相关研究,甲骨文中只有“五色”中的白、赤、黄、黑四色,并无青色。有观点认为,青色在当时很可能被包括在黑色之内。西周金文中出现了“青”字,然其本意并不指颜色,个别有可能指代颜色的“青”字亦存在争议(44)汪涛:《殷人的色彩观念与五行说的形成及发展》,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61-294页。。然则在西周初年,“五色”的观念很可能尚未形成。综上,赵光贤、屈万里等先生的意见似亦难以完全否定——这句关于“方”“色”之配的内容,到底是春秋前之旧文,还是战国改写者所加,尚难完全夯实。虽则如此,综合其他记载来看,“方”“色”之配的形成时间即便不在春秋以前,至迟也不晚于战国初年。《仪礼》云:“设六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45)郑玄注、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10页。《仪礼》一书,古文经学家托之于周公旦,如今几无人信从;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孔子所编定,略近于当今学界观点。不少学者认为此书含有西周之材料,且在孔子以后的流传过程中有增补,要之,将此书成书时间大致定于春秋末、战国初当无疑问(46)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上)》,《文史》第15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7-41页;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下)》,《文史》第1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9页;丁鼎:《试论〈仪礼〉的作者与撰作时代》,《孔子研究》2002年第6期。。细看这段文字,东、南、西、北四方所配之颜色与后世已无不同,唯“中”有歧异。所谓五方是从二维平面角度确立的,而这里则是从三维空间角度确立了“六方”。为了配合“六方”,还特意将相近甚至相同的“玄”“黑”两色进行了区分(47)之所以从黑色中区分出玄色象征天,是因为黑色从先秦以来即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参见拙作《“上黑”渊源考》,《史学月刊》2017年第2期。。
事实上,在早期史料中,“六方”的概念较“五方”更为流行(48)关于先秦时期的“尚六”之风,参见拙作《秦“数以六为纪”渊源考》,《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周礼·春官宗伯》篇有云:“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49)孙诒让:《周礼正义》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89-1390页。《周礼·冬官考工记》则云:“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50)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305-3310页。关于《周礼》之成书年代,学界观点多认为在战国末期,至晚不晚于西汉初年(51)相关诸说在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一书中胪列甚详,此不赘述。彭先生认为此书成书于汉初,成祖明先生则进一步认为此书为河间献王刘德所创制。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成祖明:《论〈周官〉与西汉河间儒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然其中《考工记》一篇与《周礼》其他部分原为两书(52)《隋书·经籍志一》认为是河间献王将此篇补入《周礼》,马融《周礼传》则认为是刘歆所补,参见成祖明:《论〈周官〉与西汉河间儒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相关研究认为其大致当成文于春秋末战国初(53)闻人军:《〈考工记〉成书年代新考》,《文史》第2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1-39页。,略近于《仪礼》成书时间(54)关于这一判断,还有两个旁证。其一,《考工记》笔法较之战国中后期的诸子书颇为古奥,甚是不同。其二,如清人江永与郭沫若先生所考,此书为齐国人所作,在谈及各地特色时,提及的国名颇多,如秦、燕、荆、郑、宋皆被提到,却不言及中原霸主晋国,亦不言及分晋之韩、赵、魏三国。郭沫若先生认为,文中系以“妢胡”代指晋国,以示仇视。今按,田氏代齐前后,晋室已名存实亡,然韩、赵、魏三家尚未为周室正式承认,此地区实无以名之,文中不称晋亦不称韩、赵、魏,而以“妢胡”贬之,当即此种窘况之表现。参见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1-76页;郭沫若:《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天地玄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周礼》这两段文字所记载的方、色之配与《仪礼》完全相同,亦不合“五”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工记》这段文字中,出现了土、火、水等元素,却与“山”并列,显见并非五行之意,更没有与方、色进行搭配。
除了上述六方六色的搭配外,还有四方四色之搭配。《墨子·迎敌祠》有关于迎敌时祭祀的记载,其四个方位与旗帜颜色、人数乃至工具、牺牲皆有对应。不过,此篇据朱希祖、吴毓江等先生考证,为后人伪作(55)吴毓江:《墨子各篇真伪考》,《墨子校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28、1037、1038页。,其年代当不甚早。
此外,大致成书于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间的《山海经》中也有一句疑似与方、色相配有关的文字:“有渊四方,四隅皆送,北属黑水,南属大荒。”(《大荒南经》)
上述几条材料虽已有与现今基本相合的方、色相配体系,却不合“五”数。在早期文献资料中,除前引《逸周书·作雒解》外,《墨子·贵义》中对此亦有暗示:“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贵义》篇据吴毓江先生考证,系《墨子》原文,非后人附益。然其行文较《考工记》简易,其写定时代或当略后于《考工记》,大致定于战国早中期当无大误。这段记载所言,亦为四方四色,然其中四方四色已与天干搭配,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所属,唯戊己无所配,加上戊己所应配的“中”与“黄”,正合五方五色。
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尉缭子》则有云:
左军苍旗,卒戴苍羽;右军白旗,卒戴白羽;中军黄旗,卒戴黄羽。
卒有五章:前一行苍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黄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
此处以中军为黄色,设其位坐北朝南,则左军为东,右军为西,核之原文,皆合方色之配,且末尾又列出五色,其意甚明。
战国中晚期之交的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帛书一幅(56)何介钧、周世荣、熊传新:《长沙子弹库战国木椁墓》,《文物》1974年第2期;湖南省博物馆:《新发现的长沙战国楚墓帛画》,《文物》1973年第7期;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8页。。其四方以图画形式绘有青、赤、白、黑四色木,文中又提到“青木、赤木、黄木、白木、黑木之精”(57)安志敏、陈公柔:《长沙战国缯书及其有关问题》,《文物》1963年第9期;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18-19页。,明确体现了五方五色之配。
综上所述,可知方、色之配至晚在春秋战国之际已基本成型。从这些记载,尤其是《考工记》的记载来看,早期的方、色体系与五行无涉,可知方、色与五行相配之说实为后起。
五、五行与五方五色的相配
如第三节所论,《逸周书·小开武解》所载五行与五色之配当为后人之注释。事实上,以“金、木、水、火、土”并称的五行概念虽然在春秋时可能已经形成,但仅以单独的概念出现,迟迟未与五方五色这一体系相配。
最早将五行与五方五色明确相配的传世文献当为《管子》(58)《墨子·旗帜》有疑似五行配五色的记载:“守城之法,木为苍旗,火为赤旗,薪樵为黄旗,石为白旗,水为黑旗……”其中以“薪樵”配黄,“石”配白,缺“金”与“土”,不知是理论尚未完备,还是为了迁就军事现实。不过,此篇据朱希祖、吴毓江等先生的意见,非《墨子》原文,为伪作,时代当不甚早,五行五色之配亦简略而模糊。吴毓江:《墨子各篇真伪考》,《墨子校注》下册,第1028、1038页。。近代以来,学者对《管子》各篇著作时代颇有争论,上有推之于战国者,下有推之于汉后者,但对其主体部分,学界多认为系战国中后期作品(59)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45-52页。。顾颉刚、冯友兰等先生更进一步指出,此书主体很大程度上系齐国稷下学者所作(60)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0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6-119页。。
在早前的典籍中,虽然也有各种与“五”有关的神秘说法,但不过是一鳞半爪,直至《管子》才形成了颇为完整的体系。因此,此书向来被认为是五行说兴起的标志。之所以发生这一突变,或与齐国之称帝意图有关(61)胡家聪:《〈管子〉中“王、霸”说的战国特征——兼论〈管子〉并非管仲遗著》,《管子学刊》1992年第3期;白奚:《中国古代阴阳与五行说的合流——〈管子〉阴阳五行思想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不过,经细读不难发现,五方五色才是《管子》中这一理论的绝对核心,五行只不过居于从属地位罢了。此书论述五行说的文字主要集中于《幼官》《幼官图》《四时》《五行》《轻重己》五篇之内。其中,《幼官图》与《幼官》除个别字词差异外,文字基本相同,故实为四篇。四篇中,《幼官》与《轻重己》铺陈五方五色体系极侈,却并未提及五行;《五行》一篇则仅言五行与天干等相配,并不涉及五方等诸多元素;将五行纳入这一体系的,似仅《四时》一篇而已。其文云:
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土生皮肌肤……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62)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第842-854页。
东、西、南、北对应星、辰、日、月,而木、金、火、水不过为其所派生的支流元素而已(63)唯“土”为“中”所直接对应,和其他四行对应得并不协调,其前后文字亦诘屈难懂,当为抄写窜误所致。。可见,此时“五行”虽被引入此体系,然而不过是较为边缘的一组元素罢了。
综上,《管子》一书中始言及五行与五方、五色之配,然而四篇涉及五行说的文字中,将五行配入五方体系的仅一篇,其中五行地位又颇为边缘,可见此说在稷下亦未形成绝对主流,尚属草创。由此看来,将五行与五方、五色之配形成的时间定于战国中后期之交当无大误。直至此时,所谓“五行说”名之为“五方五色说”似更为合理。
六、五行相胜说的引入与五德终始说的形成
如前所论,五方与五色相配的时间很早,并且一度处于这一神秘理论的核心地位,五行直到战国中后期才加入这一体系,而且不过是处于分支地位罢了。那么,五行又何以能“庶子夺嫡”,取代五方五色成为这一体系的核心呢?对比前后史料不难发现,其原因当在于旧有的以万物分类为特征的五方五色说向以五行循环往复为特征的五德终始说转变(64)关于以五方五色为核心与以五德终始为核心的两种体系之不同,杨权先生亦有言及,而分别称之为“空间的”系统和“时间的”系统。不过这一命名似还不完全贴切,如五行元素与四季相配亦当属于五方五色系统,称之为“空间”似不协调。两种系统之关键区别当在于一个以万物分类为特征,一个以五行循环往复为特征。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第108-109页;杨权:《论汉初的色尚赤》,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秦汉史论丛》第12辑,第343-353页。,而五行生、胜理论实为这一转变的关键要素。
徐复观先生曾指出,所谓五行生、胜之说并不完全符合逻辑,当系先有五行分类,后有生、胜之说的附会,而非由生、胜之说推演出五行(65)徐复观:《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464页。。此言甚是。相生之说出现及产生影响的时间较晚(66)《管子·四时》以及《吕氏春秋·十二纪》按季节排列五行合于相生的顺序,然未明言。明确的相生记载似首见于放马滩秦墓出土的竹简,墓葬年代应在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左右。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马滩秦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8页。,姑置不论。至于相胜之说,一些观点认为《逸周书·周祝解》“陈彼五行必有胜”为其最早的记载。然此句意颇模糊,其中“五行”解为“五种应行之道”似更为通顺,“必有胜”更是难以解作“相胜”。此后的史料中,《左传》之《昭公三十一年》《哀公九年》,以及《孙子兵法》《墨子·经说下》皆有可能与“五行”有关之记载。不过这些记载或只言片语,或文句不通,其所指是否为“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尚有争议(67)徐复观:《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463页。。即使相信这些记载所指确为相胜之说,由其模糊性实已可见其影响之有限。事实上,即使在《管子》这样一部被认为是五行说里程碑的著作里,也找不到五行相胜的记载(68)《管子》中的《五行》篇欲制一年五季的新历法,而试图突出“五行”的地位。其文中放弃了五方五色等诸多元素,几乎另起炉灶地编排相关元素。然其方法仍是旧有的万物分类之法,并不涉及“相胜”之说。用陈旧方法编排缺乏根基之元素,其影响自然也就远不及铺陈传统“五方五色说”的《幼官》等篇了。。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地葆》当是明确涉及相胜说的最早记载:“五壤之胜:青胜黄,(黄)胜黑,(黑)胜赤,(赤)胜白,(白)胜青。”(69)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1-72页。可以看到,“五壤之胜”实即五色相胜,若脱离五行,这一相胜体系自难以解释。且其《奇正》篇又有云“有胜有不胜,五行是也”(70)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第192-193页。,则“五壤之胜”当即五行相胜之间接表达。根据相关研究,此书各篇实当为数代言兵者从齐湣王时至汉初陆续写就(71)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 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释文第72页;李零:《齐国兵学甲天下》,《待兔轩文存·读史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5页。,其间固当多有孙膑遗教,但亦不免附益之作。《地葆》篇方术色彩极浓,或为战国晚期五行家之附会。
而在先秦传世文献中,明确载有五行相胜理论的实仅战国末期《吕氏春秋》一种而已。其中,《十二纪》已将“金、木、水、火、土”列为“五德”,然仅是如《管子·幼官》一样分类排列而已,并不涉及相胜之说。其说仅见于《有始览·应同》的一小段文字而已。其文言黄帝、禹、汤、周文王分别对应土、木、金、火四气,并声言“代火者必将水”,正依五行相胜迭代排列,五德终始说就此形成。
一般认为,五德终始说出自邹衍(72)《文选》李善注引《七略》有云“邹子有终始五德”。萧统:《文选》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87页。。邹衍本出于稷下,然主要由稷下学者所作的《管子》涉及五方五色理论虽多,却未载此说,甚至在《四时》篇中以“日、月、星、辰、岁”为“五德”(73)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第842-855页。,与“金、木、水、火、土”之说大相径庭。可见邹衍草创此说时,尚未得到稷下阴阳五行家之公认,至战国末年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七、结 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早期“五行说”的核心其实并非五行,而是渊源可上溯至甲骨文的五方观念。五方与五色相结合远在与五行相结合之前,方、色的初步结合及其神秘化意向在《逸周书》《仪礼》《考工记》《墨子》等文献中均有体现,而在出土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一学说发展至战国中后期发生了突变,形成了一套体系完备、具有浓重神秘色彩的理论,体现这一思想的古籍为《管子》。五行在《管子·四时》中首次被引入了这一体系,但并非此理论的重点。直至此时,该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叫作五方五色学说,而非五行说。
直到战国晚期,随着五行相胜学说被引入此体系,五行才喧宾夺主,代替五方五色成为这一体系的核心,最终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五行说——五德终始说。这一理论应创自邹衍,然当时尚未得到阴阳五行家公认。其传世文本首见于《吕氏春秋》,但仅见于《有始览》部分。五行在《十二纪》中地位虽亦重要但还不够突出。此时五德终始说虽已形成,但并未能凌驾于旧有五方五色体系之上,其隆尊地位的形成实在秦汉以后(74)在本文的修改过程中,读到了陶磊先生最近发表的文章。陶先生认为,此两种模式的转换与政治体制变化有关,与五方五色有关的“方位帝”模式对应了联盟、分封政体,与五德终始有关的“线性模式”帝王系统对应了大一统政体。今按,其文将两说的形成时间上溯至春秋乃至商代,似可商榷,然此基本判断当可成立。五方五色说源头虽或与政治体制无关,然其后五方色帝说的流行当与战国中期群雄崛起称王、否定周天子名义统治权有关。而五德终始说的流行则当与战国晚期战争白热化后,“并天下”的思想有关。陶磊:《古史传说与政治文化:对古史传说流变本质之新阐释》,《史学月刊》2019年第5期。,开篇所引钱穆等先生之说确为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