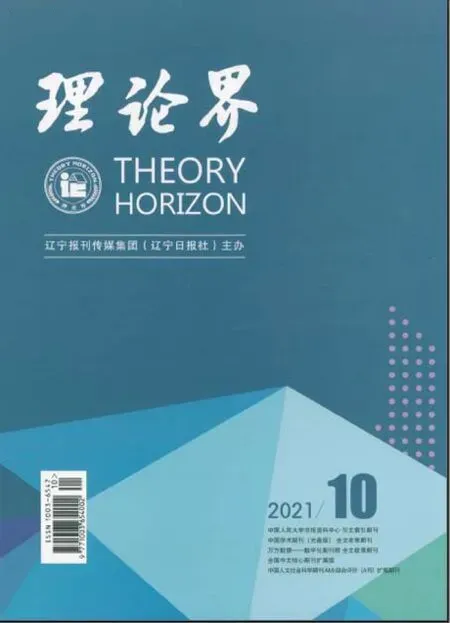党争与苏辙使辽诗文
李昌懋
宋元祐四年(1089)十月,苏辙作为贺辽国生辰使启程前往辽国。此次出使,他随时草就,有诗《奉使契丹二十八首》;返回东京后,又连上《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关于苏辙使辽诸篇,早有前贤注目。概言之,相关研究有三种主要进路:一是以诗文中所述内容,研究辽国各地区社会生活状况。先行研究有孙冬虎《北宋诗人眼中的辽境地理与社会生活》(《北方论丛》,2005.3),吕富华、孙国军《从使辽诗看奚族社会生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1)等。第二种是将苏辙此类作品置于宋奉使诗脉络中加以考察。其中较重要者有王水照《论北宋使辽诗的两个问题》[《山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2期]等。三是通过对本组诗的细读,探讨苏辙本人的契丹认识。这一类研究有《论苏辙的使辽诗》[《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诸葛忆兵《论苏辙的奉使诗》(《江海学刊》,2005.3)等。二者均注意到了苏辙相关诗歌中论及契丹事物时前后笔调的微妙改变。不过,两位论者受制于当代的民族认识,未能在历史脉络中理解苏辙的“契丹论”,因此,对于苏辙的此种“转变”估计得过于乐观。本文拟在进一步讨论苏辙契丹观的基础上,从“党争”这个侧面来回答,苏辙何以持有和表现这样的契丹观。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苏辙在此次使辽前几年党争中的角色。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次年改元元祐;其母高太后听政,重用旧党,实行“元祐更化”。沈松勤指出:“纵观新旧党争每个阶段的初期历史,还可以发现这样‘三部曲’:一是新君即位,改变前政;二是君主或君臣合力,控制台谏;三是利用台谏,击败政敌。”〔1〕在元祐更化中,“较之前一阶段,‘三部曲’的节奏更快,台谏的工具性能和催化作用更显著”。〔2〕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曾置六察司于御史台,使御史与谏官职权分离,专司技术性监察工作,“论事有分限,毋得越职”,〔3〕元丰八年(1085)六月,吕公著进《上哲宗乞选置台谏罢御史察案》,“乞尽罢察案,只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并提出具体的人事安排,提议旧党诸公任职台谏,其中苏辙“可充谏官或言事御史”。八月,朝廷以秘书监校书郎召元丰三年受“乌台诗案”牵连,左迁监筠州盐酒税务的苏辙还,十月,以中旨除苏辙等五人为谏官,经章惇抗议,其中两人改任,而苏辙则顺利上任。
苏辙此番任职谏院,正发挥其善写论辩之文的长处,迭上弹章,对新党人物猛烈开火。他以蔡确为“险侫刻深”,韩缜“识性暴,才疏行污”,张璪、李清臣、安涛等则是“斗筲之人,持禄固位”,更连上三疏弹劾吕惠卿,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吕公著对他的期望。但此时,双方在合作中已经出现分歧的萌芽。苏辙弹奏新党大将章惇时说他“明知光所言事节有疏略差误,而不推公心,即加详议,待修完成法然后施行,而乃雷同众人,连书劄子,一切依奏”。〔4〕这一方面可以坐实新党“阳奉阴违”的“小人”之名,更间接言明于皇帝,自己在“论差役事”上也以司马光为非,但持论光明正大,可谓一箭三雕。仅仅在不到一个月前,他还在反对尽复差役,上《论罢免役钱行差役法状》,然而一旦章惇也开始揭明其反对复役法的主张时,苏辙就立刻站回旧党大队,因人废言,而以倒章为首务。
元祐元年(1086),苏辙为中书舍人,次年,除户部侍郎,三年,转吏部侍郎,四年,为翰林学士,权礼部尚书,并奉命使辽。这一时期,一般认为是旧党分裂,所谓“洛党、蜀党、朔党”党争凸显的年代。然而,关于这一党争的起因、程度和性质,却众说纷纭。宋人文集多以苏轼与程颐在温公葬仪上之龃龉为其滥觞,钱大昕也作此断。后人不满足这种“情节性”过强的解释,于是有所谓“道学—反道学”说、“政见不和”说等。罗家祥认为,蜀洛之争,根本原因即台谏风气的恶性发展,而直接原因,则是苏轼等人触犯了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旧党正宗势力”。〔5〕关于这场争斗的发展和规模,清儒如钱大昕多有认为此一争斗贯穿元祐政局者;〔6〕罗家祥则据旧党内争与新旧党争的交替发展,分元祐为四阶段,一、三阶段是旧党统一压制新党,而二、四阶段则是旧党内争占据主流时期,〔7〕这种分期暗示旧党内各派其实早在元祐之前就已经形成雏形;而王水照、朱刚则提出,元祐四年前,程颐门生为主的“洛党”是依附韩维,而归根到底是受吕公著庇护的;而苏轼一方则更多受范纯仁提携,因此,其时并不存在“洛蜀党争”,而是“吕夷简的儿子”和“范仲淹的儿子”之争。〔8〕至于苏辙出使而返后,他作为主角参加的争斗则是“朔蜀党争”了。〔9〕
前贤诸说,各有所本;为加辨明,正可注意公认为元祐末年党争主角之一的苏辙赖以升迁的本次出使。当指出的是,苏辙的搭档赵君锡,后来被认定是坚定的洛党人物,他生于洛阳一个世代官僚的家庭中,祖安仁,父良规,都曾历任中枢及地方。1091年苏轼因诗有违碍语遭弹劾时,赵曾进言“轼负恩怀逆,无礼先帝,愿亟正其罪”。〔10〕不过,元祐四年(1089)四月,在苏轼被贬谪杭州时,赵君锡却曾经上疏抗救,说:“轼之文……公论倚重,隐如长城。今飘然去国,邪党必谓朝廷稍厌直臣,且将乘隙复进,实系消长之机。不若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则天下蒙福,听其谠论则圣心开益,行其诏令则四方风动,而利博矣。”〔11〕更重要的是,在苏辙“八年中几乎都在为坚持己见而斗争”〔12〕的“回河”问题上,赵也是苏氏兄弟外反对“回河”的“一两人”之一。他认为:“大河不可轻议东回,请亟罢修河司,以省邦费,宽民力”,而在“回河”争论中,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大河天堑是否会因为黄河北向改道而变为契丹南下的通途。苏辙的论点是:契丹“长技在鞍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其“物力寡弱”,因而不可能利用改道后的黄河南下。如此看来,此次出使,不也正是一个让苏辙看一看契丹是否真的“物力寡弱”的好机会吗?
《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中,苏辙题中指明写与副使赵氏的有六首。《赠右番赵侍郎》中说:“霜须顾我十年兄,朔漠陪公万里行。骈马貂裘寒自暖,连床龟息夜无声。同心便可忘苛礼,异类犹应服至诚。行役虽劳思虑少,会看梨枣及春生。”称兄以尊之,骈马而行,连床而眠,并相志以“同心”尽忠王事,只见一副志同道合、融洽友爱之态。当然,这种友爱很大程度上也与羁旅之中两人同怀的乡思乡情有关。无论是去时的“明朝对饮思乡岭,夷汉封疆自此分”(《古北口道中呈同事二首·其二》),还是归时的“汉马亦知归意速,朝旸已作故人迎”(《十日南归马上口占呈同事》),此种心情大概只能说给同行的搭档听吧。不过,如果没有相当融洽的私人关系的话,《赵君偶以微恙乘驼车而行戏赠二绝句》这样的两人之间的戏谑之作是绝不会有的,也不会设想“惊喜开帘笑杀人”这样的调笑场面。苏辙在旅行途中,对于契丹饮食难以适应,尤其不喜奶食,只好以“菜盘”和“粥”来鼓励自己,在归途中畅想:“想见雄州馈生菜,菜盘酪粥任纵横”——疆场无可纵横,餐桌也可聊建功业,然而愿在给赵氏的赠诗中分享此种心情,这就未必不和赵君锡在出使前半年刚刚为乃兄讲了好话,又支持苏氏兄弟的“回河”论点有关了吧——至少在这几首诗里,我们是看不出一点二人失和的征兆的。
一般认为,新党人物在对外政策上,多数持比旧党更为激进的立场,有更为宏大而急切的目标。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四中说:“虽曰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蓟,西不得灵夏,南不得交趾,然三方之在版图亦半为边障屯戍之地。”绝大多数北宋士大夫在原则上认为这三块唐亡时尚为郡县的土地为“失地”,而对王安石等新党来说,则更意图将“收复”失地付诸行动。李焘概括说:“神宗继统,材雄气英,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夏河西专于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籍取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全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1072年,新法派主导下的熙河之战告捷;而变法后宋朝第二个“收复故土”的军事行动,即熙宁九年(1076)因为地理因素与交趾的坚决抵抗而遭到挫折的征讨交趾,也同样有着明显的党争背景:放弃平交政策的动议就来自旧党张方平(《论讨岭南利害九事》)。〔13〕苏轼论及此役,也认为是新党官员“(沈)起实造端,而(刘)彝继之,结怨安南”,归根到底还是安石“求边功”所致。可见,旧党官员在交趾问题上,和在西北方向一样,一直反对边事屡开,主张退让。到元丰五年(1082),五路伐夏以及随后的永乐城之战的惨败,极大地打击了宋神宗支持新法的决心,成为新党“武力收复”政策的第二场大败。在元祐三年(1088)西夏请宋朝将五寨之地归还西夏时,出于旧党的传统政策,苏辙还是赞同司马光的主张,并一同促成了对西夏的“归还”土地。
然而,相比对夏与对越政策中明显的党争背景,新旧党对辽政策上的区别就比较微妙了。王安石尽管有“契丹大而无略,则多隙可承;且并诸国及燕人为一,四分五裂之国也”等对辽“战略蔑视”的观察,却一直反对以辽国为开边的直接打击对象。〔14〕熙宁八年(1075)的“契丹索地”风波中,尽管王安石的作用尚有争议,〔15〕但至少神宗及奉使的新党韩缜(韩维之弟)是主张给予契丹部分所争之地的,不能以王一人态度而断定新党主流态度。而旧党中,同样既有主张退让的,也有反对退让的。
王安石有往辽国方向的纪行诗十余首,多数论者系年于11世纪60年代初期。关于这些诗歌是王安石伴送辽使北返所作还是出使辽国所作,学界有所争论。〔16〕〔17〕〔18〕从这些诗歌中可以窥见王安石的契丹观。对于燕云之地,他有着和所有北宋文士一样的敏感:“尚有燕人数行泪,回身却望塞南流”,“寒雨巧催燕泪落,蒙蒙吹湿汉衣冠”,借燕人之泪而痛恨燕云之不复。不同之处在于,他对北宋以钱帛“和戎”的态度,以及对现实宋辽关系中双方地位的认识。在《河北民》一诗中,他说“河北民,生近二边常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里认为“官家”所为是“事夷狄”已属激进观点;而进一步认定此种做法给边民带来“苦辛”,不像其他许多使北者,把河北边地描绘为一派和平生产,民得其所的景象,则更是发人所未发;和苏辙在《虏帐》中“祥符圣人会天意,至今燕赵常耕农”一句对北宋和辽政策的合理化乃至吹捧相比,王安石显然不曾认为这种政策对于边民是一种恩惠,而只视为一种不得已的现实策略。在《澶州》一诗中安石有云“戈甲久已销,澶人益憔悴,能将大事小,自合文王意”,一方面是对边民“益憔悴”的观察与《河北民》中相照应,另一方面是近乎自嘲式的为朝廷政策的“辩解”——自居“大”和“得道”,同时又暗示日后定当如武王伐纣般对契丹加以征讨;但是这也就依然是承认,现存的关系是一种宋低于辽的不平等关系(像文王对商纣一样“事”之);这种对宋辽关系的认识,也许让他在后来执政时,制定对辽实际政策时,即使有较低的姿态,也可以用宋对于辽原本就属于“(屈)事”的认识来加以合理化。
然而,苏辙的使辽诗文中,是绝不会承认宋辽关系中宋方本就处于略低位置的。在他笔下,自己所承担的任务并非“以大事小”而是“以大字小”。在回朝所上劄子中,他认为契丹皇帝礼遇宋朝是“依倚汉人,托附本朝,为自固之计”,似乎这对关系中,宋是提供保护,具备较优越地位的一方。在诗歌中这种情绪也有所表露,如“虏廷一意向中原,言语绸缪礼亦虔”(《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其四》)。〔19〕同时,他多处流露两国关系中宋在“智算”上胜过辽一筹,从而得到更多实际利益的看法:“甘心吾饵堕吾术,势类畜鸟游樊笼……尔曹饮食自谓得,岂识图霸先和戎!”(《虏帐》)〔20〕这种看法体现了:一、苏辙所理解的宋辽关系完全是“零和游戏”,双方根本利益是冲突的,不可能共赢;二、苏辙在对辽关系中,优先考虑“实利”,在“义利之辨”中,似乎认定对“北虏”并无“义”可讲;三、他不曾对宋在双边关系中的主动权稍加怀疑,并对宋在文化和智力上对辽的优越感大加推崇。总而言之,尽管在策略上他接受和辽方的政治平等地位,但在原理上,他完全不能想象契丹应该具有和宋的对等地位。“朝廷经略穷海宇,岁遗缯絮消顽凶”(《虏帐》),〔21〕苏辙心目中自己的出使并不是一次“文教”之行,而是一次没有硝烟的军事行动(“经略”)。
苏辙契丹观的第二大特点,则是认定契丹所秉之“天性”与汉族人不同,因而绝无“用夏变夷”,在文化上使之接近宋方之可能。由此出发,他认定宋的书籍等文化产品传入契丹,主要在政治上产生泄露情报的影响,而不可能在文化上发生加强双方联系的效果,因此,要加以限制。首先,在“夷汉”之间存在着自然边界,“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22〕在边界北侧契丹腹地,环境如此粗恶:“蓬棘不复生,条干何由作。兹山亦沙阜,短短见丛薄。冰霜叶堕尽,鸟兽纷无托。”他不由得感叹:“乾坤信广大,一气均美恶。胡为独穷陋,意似鄙夷落。”认为“乾坤”本来就未曾给予契丹与中原一样的条件,所以契丹人才“民生亦复尔,垢污不知怍”,这说明了“天工本何心,地力不能博。遂令尧舜仁,独不施礼乐”〔23〕。有论者认为这说明苏辙对“契丹人的同情”。〔24〕〔25〕笔者以为这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是想从本性上说明契丹人之下劣。说“夷性”是出于“天工”,这与王安石对契丹“蔑视”的论述中仅仅是质疑契丹的“智略”形成了对比。在《虏帐》中,苏辙说:“弯弓射猎本天性,拱手朝会愁心胸”,有论者认为这体现了他对契丹人气质的赞美,但“天性”不能“拱手朝会”,这是苏辙完全不承认契丹人有在政治文明上的进步可能性。
因此,我们也就不妨换个视角看待一向被视为佳话的“问大苏”事件。苏辙在《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其三》中说“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在返朝后所上札子中也有提及。苏轼为此曾有和诗“毡毳年来亦甚都,时时鴂舌问三苏”,用孟子“鴂舌”之典,对于辽人蔑视跃然纸上;又曾说:“虏亦喜吾诗,可怪也。”一句“可怪”,正可见他并不认为“虏”内之人有领会他的诗文的能力。吊诡的是,他们却同时认为,这些诗文对于那不能理解诗人的“虏”仍然有不可测的威力,将会“动”之,这种看似矛盾的心态,恰恰足以证明苏家兄弟相信,中原对“北虏”文化上的优越性来自天然禀赋的区别,不能以后天手段逆转甚至接近。
对于燕云汉族人的处境极表“同情”,并借此表达宋人对燕云领土要求的正当性,是几乎所有北宋使辽诗都会触及的题材。在苏辙的奉使二十八首中,有三首(《燕山》《出山》《奚君》)以此为主题,中间不乏同类诗中常见的悲情书写。而“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出山》)、“燕俗嗟犹在,婚姻未许连”(《奚君》)两联中,对燕人“语言”“燕俗”难改,但衣服却已左衽的细致观察,则是更见眼光处。在归朝所上札子中,他论契丹政事三条,第二条即契丹内燕人的处境,并敏锐地注意到辽依赖燕云汉族大族治理汉族人,歧视汉族平民而厚待汉族人豪族的政策。和其他北使相比,苏辙燕人书写中有特色的还有以下两点:一是将奚人的处境与汉人相比较,这种眼光令人想起王安石的论断“并诸国及燕人为一,四分五裂之国也”,是对契丹情况有所深入了解的结果,也反映了与契丹人专事牧业生产相比,奚人尚有一定的农业活动,所谓“奚田可耕凿,辽土直沙漠”(《木叶山》)。二是苏辙的某些言论,似乎在为燕云汉族人如今的“惨痛”处境加以合理化,如《出山》中“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同时他还注意到了其他使人较少注意的“投北南人”群体,《惠州》题下,其自注曰:“传闻南朝逃叛者多在其间。”该诗有句:“会逐单于渭桥下,欢呼齐拜属车尘”,以畅想未来的胜利,与之相类似的还有《燕山》中的“中原但常治,敌势要自变。会当挽天河,洗此生齿万”,把希望寄托在宋朝的“常治”与敌势的“自变”上,总之是因果论和报应不爽,其论倒可以与后世的“胡虏无百年之运”式的自我告慰相参照了。
苏辙在《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其一》中,将北宋铜钱与宋人文集在辽境的广泛流通,并列为“于中朝极为不便”的“北界两事”,他认为宋人文集“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视,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为防止这种后果,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在北宋全境实行出版审查,“惟是禁民不得擅开板印行文字,令民间每欲开板,先具本申所属州,为选有文学官二员,据文字多少立限看详定夺,不犯上件事节,方得开行”,因为“访闻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可见苏辙是认识到,文化交流对于辽方来说是一种“刚性需求”,因此,在流通领域限制这种情况是毫无可能,但他对这一事实的承认无法超过他对契丹的“天性”的认识,以及对契丹的防范和畏惧情绪,还有文化上的保守自大等意识形态因素,于是只得建议“防微杜渐”,在文集的出版这一“生产”环节来控制。
在《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其二》中,苏辙出于辽道宗亲宋的政治态度,对辽道宗作出了相当高的评价,承认他奉行与“朝廷和好年深”的政策,因此,辽境“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但这里所提到的辽国对宋亲善政策的成因,则概括为道宗“颇知利害”,“欲依倚汉人,托附本朝,为自固之计”。另外特别提出的是,道宗在文化上奉行崇佛的政策,苏辙评价该政策:“然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此盖北界之臣蠹而中朝之利也。”这里不仅展现以契丹为敌国,以契丹之害为本朝之利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对辽朝中枢人物在文化上“由夷变夏”可能性的间接否定。苏辙将道宗朝的对宋友好理解为一种“明其利害”的“自固之计”,而拒绝承认辽国可能是出于“义”而友宋,或者是因为在汉文化水平上成长,接近宋朝,故而增加了对宋的亲近感。正像他对契丹境内“问大苏”事件的猎奇态度和防范情绪一样,他无法理解把辽国中枢的对宋态度的文化政治维度,而是先验地拒绝想象“夷狄之国”可能在文化上成长为“诸夏”,因而对辽主的文化倾向,也就更易于注意到“夷狄之君”常见的“佞佛”。道宗在听取儒臣讲经时,对“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坦然态度,和对如今辽国“不异诸夏”的文化自信,苏辙显然是没有听说过,或者听说后也嗤之以鼻,未记录吧。
苏辙这种针对契丹的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态度,还影响到他对高丽的态度。苏辙曾有《乞裁损待高丽事件札子》及《再请禁止高丽下节出入札子》〔26〕主张严格限制高丽使节活动,并降低对高丽使节的接待规格。其主要理由是“高丽之人所至游观,伺察虚实,图写形胜,阴为契丹耳目;或言契丹常遣亲信隐于高丽三节之中,高丽密分赐予,归为契丹”,可见他对待高丽态度的保守正处于他对辽保守态度的延长线上。苏轼的观点,其保守程度之激进则更过于乃弟,就在苏辙使辽同年,知杭州的苏轼就拒绝让到达其辖区的高丽僧人五人进京,并上表反对结连高丽,认为“使者所至,图画山川,购买书籍,议者以为所得赐予,大半归于契丹”。四年后,高丽使者再至时,苏轼再议上表论议,主张:“今来高丽人使所欲买历代史、《册府元龟》及《敕式》,乞并不许收买”,原因是“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而流布于北虏”,甚至连高丽使希望抄写曲谱,都主张予以拒绝。〔27〕〔28〕这是由于认定“虏可以制其使命,而我不能”,从而判断高丽的外交活动受到契丹的影响乃至控制。从两苏对他们想象中受控于辽的高丽的态度,亦足以旁证两苏对于辽国的态度。
在苏辙本次出使的过程中,他与后来被归入朔党的副使唱和不已,托付心思的友好态度,足以印证王水照、朱刚先生所力主的元祐六年之前,洛蜀朔党争的规模与双方的党派意识均未曾充分发育这一观点。而苏辙其他使辽诗文中所展现的“契丹认识”,正和其人及乃兄的高丽认识相互印证,充满种族主义与本质主义色彩,在政治上坚持敌视,在文化上则以为异类,同时并无“用夏变夷”的气度和信心,反而认定其“天性”与中原有异;同时认为宋方在宋辽关系中处于优越地位,这就与新党主将王安石认为宋在双方实际关系中低于契丹,并较少沙文主义态度的契丹观形成对比。故在元祐中期前,所谓旧党内争尤其是体现在对外认识上的政治意识形态领域,还远远没有新旧党争所造成的裂痕明显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