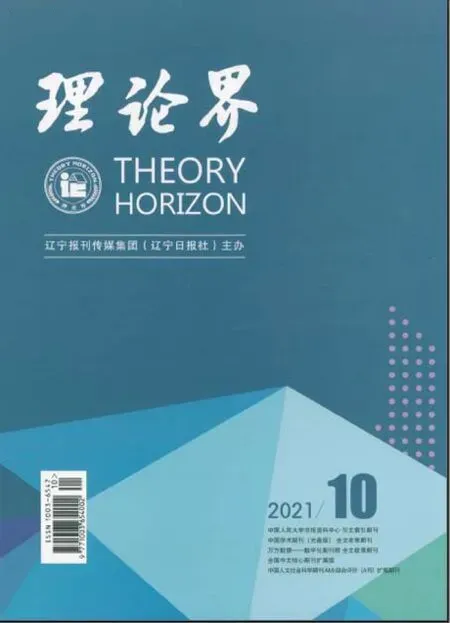《诗品》中“子卿双凫”的问题之争与探讨
蒋惠雯
南朝齐梁时期钟嵘的《诗品》中“网罗今古”“才子”,“凡百二十人”,并以“三品升降”,区分等第。观其品评标准,要以骨气为主、词采为辅。但面对数百年来诸多五言诗家及其诗作,尺度难衡,如何准确透彻地作出评价与分类仍是一项较为困难的工程。鉴于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以及个人审美品位的差异,不见得能对所品对象一概做到允直公正,钟嵘自己也在序中说到自己的标准“差非定制”,诗评价值取向必然存在某些模糊性。因此,《诗品》中除了争议颇大的陶、曹品第是否失宜外,还存在品文不列但序文提及等自相矛盾的情况,激起后世种种猜测与非议。
“夫五言者,首推苏、李,子卿与少卿并称”,〔1〕在探源中国五言诗开端的过程中,往往绕不开苏武与李陵二人,时人将他们之间应答唱和的组诗称为“苏李诗”,两相印证参照、珠联璧合,多被认为是西汉五言诗的起点。“五言始于苏、李”,钟嵘《诗品》序中却撇开苏武,唯独标举李陵为五言诗宗,认为“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品文内亦是将李陵列为上品诗家,苏武诗不入品。这种做法甚异,不免让人猜测钟嵘是否有“尊李抑苏”的倾向。但钟嵘在序文最末列举“五言之警策者”时,苏武又赫然在二十二人之列,“子卿双凫”与“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等诸多名家大作并举,被视为“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苏武的诗作可谓得到了高度评价。如此看来,苏武在五言诗歌史中的地位在钟嵘这里并未完全被忽略。这般准的无依、自相矛盾的品评,难免使人不解,引起后世学者的注意与猜疑,如陈衍《〈诗品〉平议》中谈道:“钟上品数少卿而不及子卿,深所未解。”〔1〕
“子卿双凫”中的“子卿”确然是指苏武吗?若是,为何《诗品》中其他处并未提及呢?是否有可能此处“子卿”指的并非西汉苏武而是另一同字之人?又或许,这里的“子卿”本为“少卿”,只是字有讹误?
一、关于“子卿”其人的论争
关于这一问题的以上种种猜测,前人学者均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与佐证,主要看法分为以下三种。
1.“子卿”即苏武本人
此观点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同,如陈延杰(《诗品注》)、古直(《钟记室诗品笺》)、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等先生在笺注“子卿双凫”时均提到该典故出自苏武《别李陵诗》:“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古文苑》《初学记》中皆有记载。〔2〕其中,《古文苑》载苏武《别李陵诗》全文:“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子当留斯馆,我当归故乡。一别如秦胡,会见何讵央。怆悢切中怀,不觉泪沾裳。愿子常努力,言笑莫相忘。”《初学记》卷十八则仅引前四句。
一旦判定“子卿双凫”中的“子卿”即为苏武,新的问题便产生:“‘双凫’系与少卿赠答之什,何不可以苏、李同品,如秦嘉与徐淑、刘琨与卢谌之例耶?”〔3〕作为和李陵并称的“五言诗”开宗,苏武非但未能与李陵一道被钟嵘列为上品,甚至在品文内都未再被提及。
前后如此自相矛盾,难道只是钟嵘品评的疏忽吗?有其他学者据此不合理之处提出自己的猜想,如杜天縻曾言:“《诗品》不列苏武,此云子卿,恐非苏武字也。”〔4〕即钟嵘提及的“子卿双凫”中“子卿”根本不是苏武,如此一来,苏武不在品内便似乎说得通了。
2.“子卿”乃六朝另一“子卿”
可“子卿”若指的不是苏武,那会是谁呢?梁启超曾提出一个猜测:《诗品序》中“子卿”乃六朝时期与苏武同字的另一人。梁启超的学生徐中舒在1927年撰写《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载《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十八号)时便引述了此番猜测:“六朝时有个苏子卿,而苏武也字子卿。《诗品》说‘子卿双凫’,这个‘子卿’就是六朝的苏子卿。”〔5〕此后不久,许文雨《诗品释》(北京大学出版部,1929年)出版,直接摘录了此段徐氏转述的梁说作为“子卿双凫”的注释。但很有意思的是,许文雨先生在他1947年出版的《钟嵘诗品讲疏》中删去了这一引录,转而补充道:“近人梁任公疑系六朝之苏子卿,羌无征证,恐不可从。”〔6〕中间这段近二十年的时间发生了什么,让许先生对这番猜测的态度有了如此大的转变呢?
梁氏此说颇为大胆,但若深入求证便会发现其中疏漏之处甚多,站不住脚。叶长青在《钟嵘诗品集释·自叙》(华通书局,1933年)中逐条列出理由对此说进行驳斥:其一,诗文用典中,“双凫”向来与李陵、苏武联系在一起,如庾信《哀江南赋》中有“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叶氏据此提出反问:“六朝另有一苏子卿,六朝另有一李陵乎?”其二,苏武《别李陵诗》中的“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与李陵《录别》中“尔行西南游,我独东北翔”以及“双凫相背飞”等句彼此呼应,互为唱和,因此,完全不必质疑苏武与“双凫”之说的关联性。其三,梁启超所谓的六朝子卿,其现存五首诗歌收录于《艺文类聚》《乐府诗集》,文献中皆称其为陈代人,且从未有过与“双凫”相关的诗句出现,那么齐梁时期的钟嵘“何由预知而评之乎”?
尽管叶长青此说并未完全解决“子卿”其人这一问题,但显然对梁氏之说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梁启超身后整理出版的其遗著《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华书局,1936年)中对自己先前的说法做了明显修正:“彼文历举曹子建至谢惠连一十二家,皆以年代为次。‘子卿双凫’句在‘阮籍咏怀’句之下,‘叔夜双鸳’句之上,则子卿宜为魏人,非汉之苏武也。”〔7〕他以钟嵘列举“五言之警策者”以年代为序为由,提出“子卿”应不是西汉苏武,而是三国某人——“窃疑魏别有一人字子卿者,今所传苏武诗六首皆其所作。自后人以诸诗全归苏武,并其人之姓名亦不传矣。”〔8〕索性不再提什么“六朝的苏子卿”,而是假定另有一魏武时期不知名诗人。
即便如此,梁氏所提依据也非全然无可辩驳,“五言之警策者”中并未“皆以年代为次”,如陈思王为三国时期魏人,但仲宣、公干为东汉末年人,然二者列于陈思之后;又如谢灵运为南朝宋人,却排在叔源(东晋)、太冲(西晋)之前。因此,“子卿”的年代没有理由一定在阮籍之后、叔夜之前,“子卿”为魏人之说的根据并不确凿。梁启超自己也清晰意识到了自己主张证据的不充分性:“此说别无他证,不敢妄自主张,姑提出候后之好古者。”〔9〕如此一来,这一猜测便因其提出者未能进一步列出更充分的证据而逐渐被当时主流看法所摒弃了。
3.“子卿”乃“少卿”讹误
除却上述观点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从“《诗品》的逻辑和品评范围”判定“子卿双凫”处“作‘子卿’是明显的错误,这里的‘子卿’(苏武)当作‘少卿’(李陵)”。〔10〕钟嵘《诗品》中提及与称赞的始终是李陵而非苏武。其中,中泽希男(《诗品考》)、车柱环(《钟嵘诗品校正》)、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等学者观点较为具有代表性与探讨价值。
中泽希男《诗品考》中提出“原文为‘少卿双凫’,‘子卿双凫’当为后人妄改”。他列出了两条证据:其一,虽然《古文苑》《初学记》中均收录了“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此诗,但两本书保留的诗名并不同,“《古文苑》此诗题为‘苏武’(《别李陵诗》)之作,而《初学记》卷十八则题为李陵《赠苏武诗》”,这从侧面证明“双凫俱北飞”乃苏武所作并非全然无疑问,也有李陵创作的可能;其二,他发现庾信《哀江南赋》中有“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的说法,由此认为“双凫”这一典故应是与李陵联系在一起的,乃“六朝人以‘双凫’诗为李陵作的一个证据”。
车柱环《钟嵘诗品校正》在中泽希男说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补充,主要理由列为四点:第一,《诗品》三品中皆未列子卿,“于此忽举子卿诗,殊为可疑”。第二,《古文苑》的版本中有“言笑莫相忘”一句,若为苏武所作,勉励李陵“言笑莫相忘”显然是不符合情理的。第三,《初学记》卷十八中所载诗名为《赠苏武诗》,与《古文苑》不同。车柱环认为,《古文苑》之所以将诗列入苏武别李陵之作是因为“子当留斯馆,我当归故乡”为苏武口吻,但车氏提出“子”“我”可能存在颠倒错序,若二字互易,全诗皆为李陵口吻更为合理,于是在接下来一点中他举证证实了自己的猜想。第四,金代王朋寿《类林杂说》卷七中引刘义庆《临川王集》:“陵赠武五言诗十六首,其词曰:‘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我独留斯馆,子今还故乡。一别秦与胡,会见谁何殃。幸子当努力,言笑莫相忘。’”《类林》中明确提出此乃李陵赠苏武诗且“我独留斯馆,子今还故乡”一句可以证“《初学记》《古文苑》‘子当留斯馆,我当归故乡’二句‘我’‘子’二字之错误”。在以上四点理由的基础上,他断言:“则此诗为少卿赠子卿之作,可成定论。而《诗品》此文‘子卿’为‘少卿’之误,亦决无可疑矣。”
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在引用中泽希男与车柱环之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了“少卿之误为子卿”的缘由:“‘少’‘子’草书形近易乱。《〈史记·越世家〉正义》引《吴越春秋》云:‘大夫种姓文,名种,字子禽。’《文选》陆士衡《豪士赋序》李善注引子禽作少禽,即子、少相乱之例。”〔11〕他指出:“《初学记》十八引作李陵《赠苏武诗》,仅引前四句。古氏所引《初学记》,改标题为苏武《别李陵诗》(盖据《古文苑》所改)。”并以《御览》卷四八九、宋祝穆《事文类聚后集》卷四七以及清倪璠注中皆称此诗为李陵《赠苏武诗》为证,〔12〕认为“陈延杰、古直、许文雨之相沿为苏武诗,皆失考也”。
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确有言之成理之处,却未必“决无可疑”。下文将针对上述论据逐一讨论。
二、对“子卿”本为“少卿”的驳斥与举证
首先,记载该诗的文献资料是否存在内容差异,若是,该以何版为准。据车柱环等人所言,《古文苑》与《初学记》中所载诗名有异,《初学记》卷十八中载为李陵《赠苏武诗》,与《古文苑》不同。但笔者考中华书局1962年据古香斋版本排印的《初学记》发现,卷十八“离别”第七中仍引此诗作“苏武《别李陵诗》”,与《古文苑》并无不同。车氏所谓陈延杰、古直据《初学记》引作苏武《别李陵诗》为“或失检,或据《古文苑》标题妄改”,不知据何而来。若是所持版本不同的缘故,恐怕需要更早版本《初学记》比之校对方能确认。退一步来说,即使中泽希男等人手中版本载作李陵《赠苏武诗》且更为古早确切,车氏疑《古文苑》引文中“子”“我”二字颠倒、依诗意将之归入苏武诗中的说法亦未为得实。《初学记》中所引版本的第三、四句与《古文苑》中所引相同,“子”“我”两字位置相同,且《古文苑》所载内容多于《初学记》,可断定前者非本后者所得。既然如此,何以证明《古文苑》有误而《初学记》无误?唐人类书与总集所引中,《艺文类聚》(卷二十九)亦引之归于苏武。车氏所举“我独留斯馆,子今还故乡”的版本出自金代王朋寿《增广分门类林杂说》,成书远迟于《艺文类聚》,安能以后出者为准?总之,从文献学的角度判断“双凫”诗为李陵所作,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其次,庾信《哀江南赋》中的“李陵之双凫永去”能否作为“双凫俱北飞”一诗乃李陵所作之证据。庾信这句其实包含了两个典故,“李陵之双凫永去”化用自李陵《录别》诗中的“双凫相背飞,相远日已长”;“苏武之一雁空飞”则化用苏武《别李陵诗》中的“双凫俱北去,一凫独南翔”,只不过以修辞故,改“一凫”为“一雁”。〔13〕后人常以“双凫一雁”为感伤离别之词,如白居易《与元九书》有曰:“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若能以李陵之“双凫”证双凫诗为李陵作,我们亦可据“苏武之一雁(一凫)”断双凫诗为苏武作。且此诗若为李陵所写,诗中三四句却是“子当留斯馆,我当归故乡”,与李陵口吻不合。日本立命馆大学《诗品》研究班的《钟氏诗品疏》亦云:“或如中氏之所言,‘子卿双凫’为后人妄改。然而,若联系此诗‘子当留斯馆,我当归故乡’句的史实来看,则也许把子卿的苏武设想为作者是合理的。”委婉地对中泽希男的说法提出了异议。
再次,若此诗为苏武所作,结合李陵当时的处境,是否如车氏所说内容存在不合理之处。车氏提出,如果是苏武别李陵之作,绝不当以“言笑莫相忘”勉之。车氏此番言论恐是基于故土情怀、家国之思的观念得出的。但我们结合史料记载来看,苏武这番勉励并无太大的问题。与苏武被俘后因始终不愿投降,遭到匈奴人“绝其饮食”“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等种种折磨不同,李陵在匈奴的生活甚为优渥,班固《汉书·李陵传》记载:“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甚至在汉昭帝即位,“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后,李陵也并未欣然规往,而是“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恐再辱,奈何!’”选择留在匈奴生活,二十余年后病逝。由此看来,对苏武归国,李陵除了故友分别的感伤、故土难回的无奈,也许再无其他意味。苏武希望自己离开后,李陵在平淡无忧的生活中偶尔能想起自己,这与当时李陵的处境并不相悖,车氏所言恐难以成立。
最后,三位代表性学者的意见中也存在逻辑悖论。有些论据是在“双凫”诗为李陵所作的前提下,以假定结论倒推出的结果,并不具备逻辑上的合理性。以王叔岷先生的举证为例,他列举《豪士赋序》李善注引子禽作少禽之例,证明“子卿双凫”中“子”原应作“少”,但这是以“双凫”诗非苏武所作为前提而倒推出来的理由,否则“子卿”本作“子卿”的理由比原作“少卿”的理由更加坚确。“子”“少”相乱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我们如何能确认钟嵘《诗品》中犯了和李善同样的错误呢?
三、苏武未见于《诗品》品第之原因探析
前述种种争论皆因苏武未见于《诗品》品第,使学者怀疑“子卿双凫”中提及的“子卿”是否为苏武本人,然而这怀疑的起因并不坚实可靠。钟嵘是否确未将苏武纳入品文内?这点仍需进一步探讨。
许文雨曾提出这样一种猜测:“逆记室本意,或古诗一品,已包并枚、苏之作欤?”〔14〕许氏认为,苏武虽未被品文单独列出,却是被钟嵘纳入《古诗》中,以另一种形式归入上品内。此猜测并非毫无根据,大致理由如下。
现在为人所熟知的《古诗》,由萧统《文选》中选录的十九首组成,所以又被称为《古诗十九首》。这些古诗非“一人之词,一时之作”,涉及的思想内容也颇丰富,大致包含“逐臣弃妇、朋友阔绝、死生新故”多方面主题。但“古诗”的实际数量远不止此,至少钟嵘看到的便近六十首,〔15〕只因萧统选录时有所抉择,“陆机拟古,间有不入选体。记室举其全,则非有误也。”钟嵘所举数据的真实性应当是可靠的。
那么,为什么说“苏诗或即在仲伟所称古诗中也”?〔16〕
这或许与苏诗宗《国风》颇有关系,“仲伟将苏诗归入《古诗》,盖《古诗》源出《国风》也”。〔17〕上品文内钟嵘未将苏、李二人并列也盖出于此。苏李诗虽以离别唱和互为辉映,但若细分流派,二人诗歌风格仍有明显的不同,苏诗更近《国风》,李陵则源出《楚辞》。明陆时雍《古诗镜》首先提出了苏李诗之不同:“苏武缠绵,李陵简挚。”张玉谷《古诗赏析》亦云:“论其气体,苏较敷腴,李较清折,其犹李唐中之太白少陵二家乎。”相较而言,苏武诗的风格与枚乘更为相似。近代王闿运答唐凤廷问汉唐诗家流派,曾评价道:“汉初有诗,即分两派,枚苏宽和,李陵清劲,自后五言莫能外之。”〔18〕许文雨先生“以体性论,苏、李自异,枚、苏自同”〔19〕的观点与此一致。枚苏二人风格则又与《古诗》“文温以丽”的诗风更为类近,晚近王湘绮曾就此详论道:前者如枚苏、《古诗》,“以‘温丽’称之,上配《国风》”,后者“以少卿怨者之流,附于《楚辞》”。这与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中“苏子卿、李少卿之著,迂曲、凄惋,实宗《国风》与楚人之词”的看法不谋而合。清代刘熙载《诗概》中曾对此观点提出异议:“《古诗十九首》与苏、李同一悲慨,然《古诗》兼有豪放旷达之意,与苏、李之一于委屈含蓄,有阳舒、阴惨之不同。”刘氏谓《古诗》与苏、李诗“有阳舒、阴惨之不同”,这种评价并不完全恰当。《古诗》阳舒,正合乎《国风》之体,确然不错;但苏、李诗风格并不一致,若相比则苏诗阳舒、李诗阴惨,苏诗与《古诗》风格类似,更近《国风》,刘熙载概以阴惨评之并不合理。
上述讨论也仅是就“《诗品》内不称苏诗”这一现象追寻缘由时得出的推论。退而言之,即使推论不成立,苏武未被钟嵘归入品文内的“古诗”,也并不代表着苏武在序中的出现是不合理的,因为《诗品》序与品文标准并不完全一致。
序与品文相异之处主要体现在,《诗品》序对于时代、品第的先后排序并不像品文中那样有意识地强调。品文内“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但序文中举“五言之警策者”时,时序极为随意(上文已略论);品文“以优劣为诠次”分为上中下三品,但序文中“五言之警策者”所举有十一位“中品”,却无“上品”的班婕妤,并不依品界之。易言之,以品文不列而序文及之以为非,虽符合我们的常理,却未必符合钟嵘之“规”,即不能因为苏武未在品文中被单独列出便否认“子卿双凫”中“子卿”指的不是他本人。
四、结语
前人学者从《诗品》篇章架构与行文逻辑、“双凫俱北飞”的诗歌内容与背景乃至字体考辨等多角度出发,结合史料文献,对“子卿双凫”这一典故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证。不论是“子卿”乃六朝另一“子卿”,抑或是“子卿”本作“少卿”,都意在解开苏武未见于《诗品》品第的疑惑。但就上述各家论据的充分性与合理性而言,仍有较大的讨论余地。笔者个人在整理与分析了各方观点后,仍秉持“子卿”即苏武本人的观点,并试图从苏武诗所宗风格以及《诗品》序与正文之间价值取向的偏离这两点出发,探析“《诗品》内不称苏诗”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
笔者虽不同意所引诸家中某些关于“子卿双凫”的解读,但对前人面临学术问题时的审慎态度与热忱追求,深表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