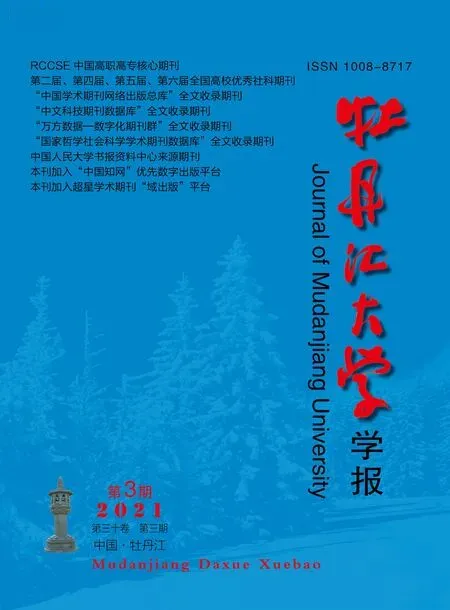从《玻璃城堡》火的意象透视美国的伤痕年代
马丽君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一、引言
美国作家珍妮特·沃尔斯的自传体小说《玻璃城堡》,自2005年问世后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二百五十多周,向世人展现了作者离奇曲折的家庭生活和悲伤痛苦的儿时记忆。记忆中有干燥辽阔的沙漠、破旧散架的汽车、东倒西歪的黑屋子、为上帝所抛弃的寂寞城镇,还有无处不在的漫天的火光。严重损伤稚嫩身体的火苗、熔化心爱玩偶的火焰、席卷旅馆和人群的大火、实验室废弃屋中轰然爆炸将人震飞的烈焰以及瞬间摧毁一家人精心准备的圣诞树的火舌……火腾跃跳动着,充满记忆的空间,萦绕着珍妮特的生活。火的意象消融在热烫的沙漠、高温的岩石、灼热的泉水和纽约透着火光的鲜橘色天空中,共同折射出美国那个离经叛道、迷离彷徨、摇滚疯狂,怀疑抗拒又渴求希望之光的“垮掉”的六十年代。
二、火光中的伤痕年代
荣格认为创作受原始意象影响,而促进原始意象形成的“每幅意象都包含一段人类心理学知识和人类的命运,包含一段人的痛苦史和快乐史。”[1]103神经学家潘克塞普也说过:“共同进化的遗产体现了我们祖先的原始经验,它们在我们的‘记忆程序’的体系中遗留了痕迹。”[1]50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从宙斯处盗取火种,给人类带来了光亮和文明,却也因此遭受天罚,几千年来被禁锢在高加索山悬崖上,遭受恶鹰啄肝之刑。因此在西方文化的原始意象中,火是希望也是痛苦,是光明之源也是地狱之火,纯洁、净化、救赎与惩罚、苦难相伴相生于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中,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着《玻璃城堡》的人物表现和叙事方式。“火”是《玻璃城堡》中的重要意象。“火”是光明的使者,是欲望的喷发,是伤痕年代垮掉派心中的怒火和希望,“火”的出现伴随“伤痕”,同时破旧立新。
《玻璃城堡》中一家五口居无定所,辗转漂泊和流浪。沃尔斯夫妇特立独行,热爱自然,抗拒文明,喜欢刺激和冒险,开着一辆破车带着孩子四处游荡。一家人经常食不果腹,夜宿野外,天地为伴,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他们到过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2]22周游拉斯维加斯、凤凰城、战役山、韦尔奇和纽约,横穿美国各地。一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说走就走,脚踩油门奔驰在美国沙漠戈壁、各大公路和山野田园,这不由让人想起了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运动的信仰声明《在路上》。
《在路上》是“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自传性作品。凯鲁亚克提出了“垮掉的一代”,并用他的作品和行动标榜着美国战后伤痕年代中青年人的惊世骇俗和沉思顿悟。作品中一群颓废空虚、叛逆社会的年轻男女沿途搭车或开车,横越美国大陆,酗酒、纵欲、吸毒和玩音乐,一路游荡,夜宿村落,放荡不羁,荒诞不经,浑噩困顿,消极的表达着自己锐意创新和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以及在战后人心涣散、精神迷茫的荒原上重建乌托邦的渴望。正如凯鲁亚克的朋友霍姆斯所指出的:“《在路上》里的人物虽然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3]23
“火”的意象反映了战后青年为祖国和人类的命运深刻焦虑和痛苦的状态,正如珍妮特将火柴靠近自己心爱的玩具小仙女时的犹豫与忐忑:“我点亮火柴,挨近她的脸。在火光的照耀下,她显得更加楚楚动人。火很快熄了,于是我再点燃一根火柴,这次拿得离她的脸很近很近。忽然,小仙女面露惊惧之色,眼睛睁得好大,这下子我才惊觉,她的脸开始熔化,鼻子已经消失,而原本红嫩欲滴的嘴唇也塌了,变得好丑,好难看。”[2]18火是珍妮特身体的伤疤,也是她伤痕的记忆,更是她心灵痛苦的源泉。父亲告知珍妮特疤痕是她顽强意志的表现,但是珍妮特内心深处却强烈意识到疤痕的扭曲和丑陋,她甚至通过展露伤疤的方式吓退了一个意图侮辱她的赌徒。她无法忘记沉溺于不切实际幻想的父母对她们的不管不顾,小小幼童被迫自己煮食,自己喂养自己,甚至喂养父母。整本回忆录,读者跟随作者“火”的视线,共同遥望着战后青年的焦虑无助与茫然,以及这种无边蔓延的悲伤所带来的痛苦和折磨。
《玻璃城堡》中,火毁灭肉体、面容和房屋,摧枯拉朽般越烧越烈,映照出战后深受战争、贫穷、疾病和种族隔离之苦的美国世态。上世纪美国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面临失业、穷困和歧视,他们在充满幻想和欺骗的淘金梦中横冲直撞,奋进挣扎,直至头破血流。父亲沃尔斯绝大部分的钱和精力都花费在寻找黄金和制造黄金探测仪上,妻儿饥肠辘辘也不管,最后一事无成,如书中战役山和韦尔奇两个小镇一样,为社会所抛弃,成为美国战后不可抹杀的伤痕印记。战役山是淘金梦的历史遗迹,是本地人自嘲为“鬼地方”的小镇。“只有几条街。街上停了几辆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汽车和小货车。”[2]137晒得通红的男人们无所事事,整日聚在“猫头鹰俱乐部”中打牌喝酒赌博。韦尔奇是父亲沃尔斯的故乡。空气沉重、稠密和阴暗,没有下水道,河里塞满垃圾和排泄物。这里自然资源贫瘠,市民落魄贫穷,没有经济来源,大部分倚靠政府救济,没有明天没有未来,浑浑噩噩的生活着。韦尔奇是美国战后经济危机的真实写照,五十年代经济遭受重挫。政府无为,遣散员工、关闭矿场、查封房屋,市民仇恨政府。[2]175同时,种族矛盾严重,白人与黑人关系紧张,奶奶厄玛因为不想看见黑人十五年未出家门。
弗洛伊德说过:“心理群体是这样一些个体的集合,他们把同一个人引入超我,并根据这个共同的成分在他们的自我中相互仿同。”[4]65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经济萧条、政治动荡,战争残酷,人权和道德沦丧,传统价值观念体系崩溃,青年们产生了信仰危机,对传统价值观念怀疑、抗拒甚至蔑视,于是在金斯堡“嚎叫”声中摇滚疯狂,颠覆传统,歇斯底里,奔跑“上路”,成为美国伤痕时代烙印的“垮掉的一代”。父亲沃尔斯身上集合着伤痕年代垮掉派的所有影子。他性格粗犷豪放、叛逆不羁,不修边幅,狂野粗俗,在医院大叫、狂笑和唱歌;满口脏话,叫别人臭小子、王八蛋;[2]13平日混迹于赌场、酒馆和妓院,喝酒、赌钱、斗殴,放浪形骸,洒脱随性。他与妻子亲近自然,远离城市,徜徉乡间,与蜥蜴、秃鹫、毒蝎、土狼和蛇为舞。生活中顺应自然,拒绝捕杀满屋苍蝇,因为苍蝇是鸟和蜥蜴的食物,而鸟和蜥蜴又能喂养猫。沃尔斯厌恶都市,将装满冷气的办公大楼称为“装潢得富丽堂皇的牢狱。”[2]137一家五口自由穿梭,在漫天风沙中飞驰,在暴风雨中狂舞,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睡觉。孩子们成长于自然,赤脚在沙漠中探险,找晶石,寻矿物,猎“怪物”。沃尔斯夫妇反对科技,厌恶文明,不让孩子们嚼口香糖,不用牙膏,讨厌消毒液,认为医学院毕业的都是庸医。大女儿萝莉被毒蝎子蜇伤,不去现代化的医院,而是求助于巫医。
沃尔斯抗拒社会,嘲讽现行体制,同情弱者,反对腐败、黑暗和种族歧视。他自食其力,拒不领取政府部门的救济金,认为救济金腐蚀人心,滋生蛀虫。他反对工会的腐败和强权,认为电工工会为黑社会所掌控,是组织化的犯罪。他与妻子同情贫民、黑人和弱者。他们教育自己的孩子帮助有困难的同学,与印第安人和黑人友好相处,在他们看来“黑鬼”是世界上最难听的字眼,墨西哥裔、纳瓦霍族和阿帕切族与白人没有任何区别。他们自己教育孩子,认为学校死板的规定和管教会扼杀人心。他们有着自己的信念和坚持,不愿卷入世俗,与黑暗同流合污。然而他们超前的思想和理念并不为社会所接纳。父亲沃尔斯对抗工会,查找工会罪证,最终为工会所驱逐,任何工会都不再接纳他;他拒绝政府救济金,自力更生,但家庭重压迎面而来,嗷嗷待哺的孩子和生活的压力让他陷入自卑与绝望;他抗拒城市和文明,反对上流社会,然而孩子们纷纷逃离自己,奔向大都市,住进高级公寓,当上“盖世太保”。他憎恨这一切,意图反抗,因此抬起了打火机,将异教徒崇拜象征的圣诞树(树木)付之一炬,在熊熊烈焰中感受毁灭的快感。
三、火的象征意义
“火”是西方文化的集体无意识,极具象征意义,火是恶,是毁灭,也是新生。西方文学中,火焰是各种妖魔鬼怪首选的武器,是恶势力的标配。如英雄史诗《贝奥武甫》中邪恶的火龙,北欧神话中聪明而又狡诈的火神洛基;法国故事诗《伊万》中邪恶恐怖、嘴里喷出火焰的巨龙。西方传说中的三头龙身体如羊,尾如蛇,口中喷吐着火与腐蚀酸液,所到之处寸草不生。三头龙激发了西方人无穷的创作,出现在美国作家乔治的长篇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中,在大热的美剧《权力的游戏》中也是坦格利安家族的徽章。
火是神物,为宙斯所掌控,是自然神秘之力,不可抗拒,代表上帝的旨意,惩罚罪恶,荡涤灵魂,所以但丁在《神曲》中将异教徒投掷于烈火熊熊燃烧的地狱中接受酷刑,让违背神的意志的暴君恶徒等罪人经受火雨的洗礼。但是,普罗米修斯盗取了火种,给人类带来了希望,“火”最终落入凡尘,沾染了人世间的烟火,慢慢有了人情味,强悍凶猛的火光中透露出新生,让人们感受生命和力量,并传承于文学作品中。哈姆莱特感叹人性美好时,将其形容为点缀着庄严屋宇的金黄色火球;《简爱》中大火毁灭了桑菲尔德庄园,烧死了疯女人伯莎,毁坏罗切斯特的容貌,使其变得又瞎又残,但同时大火也摧毁了贵族名利场,打破了罗切斯特与简爱的爱情围墙,缩短了两人的差距,提供了简爱要求的爱情平等的基础。因此大火过后,简爱回到了罗切斯特身边,迎来新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让悲剧的结局开出幸福之花。在这儿,桑菲尔德庄园的大火就不能简单用“毁灭”来定义,因为没有它,就没有简爱幸福生活的实现,两人也不能共续前缘,简爱无法实现平等的人生理念和终极追求,作者夏洛蒂·勃朗特也无法成全自己对爱情理想的想象。
“火”对立统一的意象深刻影响着西方文学,如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长篇小说《红字》中,“红”是火的颜色,是火的隐喻。它代表了基督教的精神净化和永恒惩罚,是火刑的象征。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两人既是中世纪被施以火刑的异教徒,又是在炼狱熊熊烈火中备受煎熬的两个负罪的灵魂。但同时,火又是爱情之火,是人类的生命之源,是生命、力量、热情和繁衍的象征,没有火,就没有欲望,没有爱情,更不会有人类一代又一代的生命繁衍。
《玻璃城堡》中同样承载着西方集体无意识的“火”的意象。面对孩子们的背叛、生活的压力和现实的黑暗,沃尔斯信念崩裂,浑噩迷惘找不到出路,他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看不到方向,寻找不出切实解决的办法,于是他唯有逃避。他赌博酗酒,混迹于三教九流,流连污垢肮脏的酒馆,经常喝得酩酊大醉,顾不上家庭,让孩子饥寒交迫、衣衫褴褛,甚至还偷盗孩子们辛辛苦苦攒下的前往大城市的路费,为孩子们所憎恨唾弃,而孩子们不满的怒火和仇恨的眼神又进一步让沃尔斯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与失败,更加颓废苦闷,自我放逐。正如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所描述的:“萨尔在东西海岸之间的公路上来往穿梭追梦,发现它很难持续,当他终于在新奥尔良、丹佛、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追上它时,发现它只是一个‘伤心的天堂’。”[3]16一语道破“垮掉的一代”的困惑,在美国战后的黑暗泥沼中砥砺前行,前进、追求,不满、抗拒,然而前路迷茫,看不到方向,困惑绝望,唯有“火光”才能照亮远途:他们疯狂地生活,疯狂地谈话,同时希望得到所有的东西,从不渴求或者谈论平庸的东西……他们像罗马焰火筒那样在夜空中燃烧、喷发灿烂的火焰。[3]18
作品中的“火”极具象征意义。象征是感觉世界的客体,是对深层潜意识的提示。它是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伤痕印记;是战争在美国人民心中种下的残酷记忆;是青年一代价值被否定,理想无法实现的困惑与迷茫;更是垮掉派无力的沉思与愤懑。当抑郁与愤怒激增,超出身体和精神承受之时,必将心生怒火,意图撕裂和毁灭这压印人心的黑暗,因此,《玻璃城堡》中,珍妮特和姐姐萝莉在火中受伤;一家人寄宿的旅馆和爷爷家的房屋在大火中毁灭;珍妮特和弟弟布莱恩在火焰爆炸中被震飞;承载着孩子圣诞节快乐和未来希望的圣诞树在父亲醉酒后的狂笑中毁于一旦。“火”象征着垮掉派心中的欲望和呐喊,灼烧和破坏一切,毁灭黑暗无光的世界。
“火”有毁灭的力量,也有净化和洗礼的能力,它是破坏者,也是救赎者。人类在普罗米修斯的帮助下获得火焰,实现传承和发展文明,火是人类的精神支柱,是锤炼和再生的力量,置之死地而后生,肮脏和黑暗在大火中消失殆尽,新生和希望才能破土而生。因此,珍妮特在大火灼伤身体后战胜内心的恐惧,迷上了火焰,热衷于玩火;暂住的旅馆被烧毁后一家人又开始了流浪,走上新的征程,正如《在路上》迪安对萨尔说:“你的道路是什么,老兄?——乖孩子的路,疯子的路,五彩的路,浪荡子的路,任何路。那是一条在任何地方、给任何人走的任何道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怎么走呢?”[3]15作为伤痕年代的时代先锋,垮掉派青年们憎恶社会痼疾,离经叛道消极对抗,但是他们并非内心无望,脱离尘世,相反,他们内心之火从未磨灭,他们依然充满梦想,破旧立新,渴望着新的理想和人性光辉。
四、结语
弗洛伊德注重创伤经验的研究,认为“对于创伤性神经症来说,其病根就在于创伤发生的那一刻的执著……一个人如果遭受到损伤其生活基础的创伤,他会完全灰心丧气以至对现在和未来都失去了兴趣而永久地沉迷于过去。”[5]255凯西·卡鲁斯将创伤理论运用到创伤文学。她指出创伤“是对一个或几个重要事件的反应,时间上通常滞后,表现为重复、幻想、梦幻或事件促成的思想和行为等形式”[6]。上世纪六十年代是美国战后的伤痕年代,其颓废迷茫和无助的气息深深地刻在美国人脑海中,成为挥之不去的创伤性烙印。《玻璃城堡》正是通过反复的“火”的意象将这特殊的时代记忆展现于读者面前,通过一个离奇曲折的家庭生活影像透视出整个伤痕时代的人物和社会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