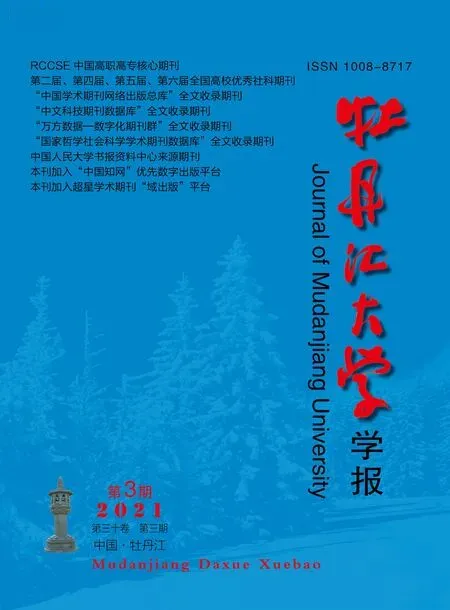当代寻根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建构
张立友
(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经典化”是作品经典地位的确立,指某段时间、范围和标准内的经典建构。《文心雕龙·情彩》一文指出:“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经典被看成重要与关键的借鉴。“典”即常道与准则,《尔雅·释话》指出“典,常也”,意为有示范性与标准意义的作品。西方文学中经典来自于希腊词汇,Kanon,延伸为尺度,后被用于指代包括《圣经》在内的宗教典籍,又被延展为文学经典著作。中西方对于经典的认识都不约而同地指向衡量的标准。历代作家的创作经历一定规则的筛选后,“具有典范性和超越时空审美价值的作品,是一个时代文学艺术成就的标志。”[1]而当一个民族的文学进入异域文化语境,就已经迈上了世界文学经典化的道路。我们有必要“追寻经典的流传学踪迹与光晕,从而为当代文学经典的塑造、祛魅与反魅构建一个较为客观的阐释空间”。[2]
当代寻根小说是走出去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构成。韩少功的《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莫言的《红高粱》、王安忆的《小鲍庄》、阿城的“三王系列”、陆文夫的《美食家》、郑义的《老井》等为代表的寻根作品在海外得到了持续而大量的译介传播,并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这一主题类型作品进入英语世界后,在文学传播赞助人的推动下,被海外读者广泛接受,产生积极影响,确立了经典地位,对外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国形象。这一主题小说是成功走出去的中国故事典型代表。在当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文化对外传播时代背景下,我们考察寻根小说的海外经典建构,有助于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现实路径,提高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成效。
一、文化异质性与世界性的融合
寻根小说在外来影响与本土表达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和融合。寻根作家秉持文化寻根理念,带着现代意识审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文化传统。其本土性体现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与反思,更展现了鲜明的地域特征与民风民俗。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文化寻根故事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传统文化的痼疾与不合时宜之处,以宽容的精神观照原始乡民的生活,展现了边疆民族生活的地域风情和国民性解剖。它们在海外掀起出版传播热潮,赢得国外读者的积极评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与民族精神的书写再现了故事的民族性特质。莫言作品的地域与民间色彩最能打动读者。《红高粱家族》的高密东北乡演绎了神秘的家族传奇,描摹了中国地域传统、生动的民间生活画卷、生命气象。陆文夫、冯骥才、邓友梅等作家从民风、民俗视角讲述中国文化故事,他们的小说受海外读者的称赞。如陆文夫的《美食家》在欧洲一度掀起中国美食文化热。“《美食家》因为其对美食的细致描述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而在海外备受推崇。”[3]冯骥才的《神鞭》中的辫子功夫、邓友梅的《烟壶》中的壶内画技艺、瓷器烧制工艺等展示了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海外读者可从这些作品中读到迥异于他们自身文化系统内的文化信息。从地理书写来看,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中的湘楚文化、莫言的《红高粱》中的齐鲁文化、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隐秘岁月》的藏族宗教文化、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的边疆草原文化、郑义的《老井》《远村》中的山西偏远山村文化、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中的陕西商州风土民情,彰显了洒落于民间的文化传统。这些地域文化描写不仅展示了地理地貌、民风民俗与人物的生存状态,又是对中华主流文化的补充。不同于儒道正统文化,他们所寻之“根”是被遗忘的、边缘化的“非规范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原始文化。然而,书写者并非沉浸于恋旧情绪和死守地方观念,而是从原始文化中寻找精神营养,揭示出人类生存、民族发展之迷与普遍性的人的本质理念,以应对现代发展,重构民族自我。寻根作家从原始文化形态中追寻文化之“根”,汲取营养,进行文化重构。[4]此外,寻根小说中的道家与儒家精神表达也是作品文化异质性之所在。阿城的“三王”系列(《棋王》《树王》《孩子王》)高举道家文化大旗。他主张在传统文化重建中吸收道家文化的有益因素,尤其是《棋王》中的“棋人合一”表征着“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唤醒了中国人对传统的回归,也引领西方读者进入一个不同于西方小说的文化境界。其中的传奇性令西方读者赞叹。儒家的积极入世、自立自强、仁义伦理恪守等思想在海外备受关注。郑义的《老井》与王安忆的《小鲍庄》因此获得英语世界读者的赞誉。“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区别于另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性特征,认识、理解、借鉴中国文化的愿望使得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寻根文学’怀有一份特殊的译介与研究热忱。”[5]寻根文学的民间性与地域性营构了文化异质性,能够调动西方文学审美主体的阅读情趣。他们的求异探奇的欲望将被唤醒。他们将调整自己的心理积淀,接纳迥异于自身文化的新奇对象,从对他者的认知中感受快乐。
如果说文化异质性契合了海外读者文化审美中的求异心理,那么世界性则破除了他们接受中国文学的文化壁垒。韩少功借助魔幻现实主义,书写失落已久的湘楚文化传统,与20世纪70至80年代西方文学的历史书写倾向有很大的相似性。追寻民族文化之根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股世界文化热潮,他的寻根故事理应是世界寻根文学的一部分。他的文化焦虑关切与人道关怀引起了海外读者的情感共鸣。其《归去来》和卡夫卡的城堡一样都是通过荒诞叙事探讨身份认同问题,对人的身份焦虑书写反映了世界性的生存体验。他的《爸爸爸》《女女女》探究的主体性危机,不仅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人的精神面貌,而且也是后现代社会一种普遍性的生存焦虑。莫言寻根作品在海外落地生根,其文学故事的文化思想鲜明地展现了人类的普遍情感和普适性价值。他“努力想使那里(高密东北乡)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6]莫言在一次访谈中阐述了其故事的世界性。“小说表面上是在讲故事,实际上是对于人性的考察。……我在着力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因为写作的根本目的是对人性的剖析和自我救赎。”[7]王安忆的《小鲍庄》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吸收与创新性运用,暴露了“仁义”的堕落,对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批判。其民族性创作艺术不仅给当代中国文坛带来新景象,而且“进一步改变了西方对当代中国作家创作手法的固化形象,唤起了美国研究者们对王安忆作品的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8]。西方学界赞誉这部作品为“寻根文学的经典之作”。阿城的《棋王》固然蕴含着中国民间小说传统,但作品中的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统摄着民间题材。他写王一生对于“吃”和“棋”的执念,其目的在于按照现代性的思维在塑造人物形象,并完成了对人的阐释。这种现代性的思维是作品受到海外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9]
新时期寻根小说的文化批判与民间地域文化呈现凸显了民族文化个性,表达了文学情感共性,这有助于传递中国文学故事的文化特色与调动域外读者的审美旨趣。而海外受众在文化异质性的审美惊奇中体验到自身文化系统的熟悉感,就会增强对中国故事文化思想的认同。文化异质性与世界性的故事构筑了新时期寻根小说经典的特质,对海外读者来说具有一种阅读审美的召唤。
二、汉学家译介与西方学者的多元化阐释
翻译与阐释是新时期寻根小说海外经典化的主要途径。前者是沟通作品与海外读者、研究者的中介,是作品进入异质文化语境传播与接受的首要条件。而后者不仅起到引介中国文学的作用而且使海外读者的阅读进入深层次,促进与深化了作品的海外传播。二者是新时期寻根小说海外经典化的重要赞助力量。新时期寻根小说在海外经典化之路中受到汉学家的青睐。他们在作品译介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葛浩文、杜博妮、艾梅霞(Martha Avery)是他们的杰出代表。莫言作品的译者葛浩文凭借深厚的中国文化积淀,观照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审美期待,运用归化翻译策略,几乎没有留下翻译文学的痕迹,赋予莫言寻根小说的英美经典文学色彩。他的译介将莫言作品带向英语世界读者的心间。他还翻译了阿来的寻根作品《尘埃落定》和张炜的《古船》,推动它们走进英语世界。“集翻译家、学者、批评家于一身的葛浩文,不仅是国际上具有很高知名度的汉学家,也是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他的翻译一定程度上是莫言走向世界的通行证。”[10]兼有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身份的杜博妮是“三王”系列小说的译者。“他的译文是站在中国文学本位的立场上,做出了充分表达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尝试和努力的姿态。”[11]其译本被全球121家图书馆收藏,在海外掀起了“阿城热”。王安忆的《小鲍庄》得到了美国汉学研究者艾梅霞的翻译。汉学家熟谙中国文学、文化,了解西方本土诗学、出版机制、市场运行规律、读者文化心态。从当代寻根小说的海外接受的效果来看,汉学家主导的译入模式无论是译本销量还是读者评价,总体来说都要比中国学者的“译出”模式更加显著,因而更易被广泛地接受。这是一支参与中国当代小说海外经典化的重要力量。
如果说译介是中国文学进入世界的主渠道,那么研究性阐释是维持作品海外传播力的不可或缺因素。西方世界的文化阐释将当代寻根小说纳入到自身的文学视野,不仅传播了中国文学的独特价值,而且深化了读者的理解,激发了他们更多阅读中国文学的渴望。西方本土评论家、华裔学者、本土中国文学研究者等专业读者的文化阐释形成了当代寻根小说海外经典建构力量。韩少功的文化寻根成为西方研究者的关注热点。荷兰汉学家林恪的专著《以出世的态度入世:韩少功与寻根文学》(Leaving the World to Enter the World:Han Shaogong and Chinese Root-Seeking Literature)探究了韩少功寻根小说的道家思想。华裔学者梅仪慈(Yi-Tsi Mei)将韩少功的寻根文学定位在“第四代现代中国作家”的乡村书写,从农民与知识分子身份的变化与逐渐消解的角度阐释他的文化寻根内涵。[12]道家文化思想也是西方学者关注阿城寻根作品的主要方面。澳大利亚汉学家雷金庆注重挖掘《棋王》中的避世与天人合一的理念,同时分析了《树王》中的儒家思想,认为:“阿城意在用儒道文化建构当代中国人的有意义生活,再现了中国性的生存智慧。”[13]加拿大汉学家杜迈可在考察《棋王》后,认为:“儒、佛、道思想构成了中国人世界观的价值基础。”[14]西方人对阿城寻根小说的文化解读显示,他们试图从中国文化中寻求逃离物质主义生活困境的精神慰籍。莫言的寻根小说在英语世界得到了深入的和多角度的阐释,相关学术文章与推介性书评有近百篇。其中《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多次以专栏、专辑、评论等形式刊登莫言寻根寻小说的学术论文。一方面,学者们整体上探究莫言寻根书写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风,破解其对中国幽默文学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一些书评多聚焦,给予莫言很高评价,从“面”上提高其知名度与影响力。《纽约时报书评》《出版者周刊》《远东经济评论》等欧美主流媒体上的评论文章和研究性论文,探讨了《红高粱》的“原创性”审美效果、英雄形象、历史叙事等方面。这些阐释将这部作品推入世界文学,“把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了世界文学的版图上”[15]。对于王安忆的接受阐释来说,西方世界试图从其寻根叙事中寻找当代中国人的民族思维和文化审美,并将其作品置入世界寻根文学家庭中。学者霍华德·乔伊认为:“《小鲍庄》有《百年孤独》的影子,再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主旨,其孤独主题与魔幻现实主义显示作家深入思考中华文化中的仁义,折射出有关人类苦难的探寻。”[16]
海外学者对寻根小说的多元化阐释,传递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艺术特质与文化意蕴,激发了域外读者阅读中国小说的兴趣与文化想象。这推动了寻根小说的海外接受,提升了其传播的力度,助力其经典构建。
三、海外不同类型出版机构运作下的主流化传播
新时期寻根小说进入海外后,受到不同类型出版机构的欢迎。人文与学术出版社、商业出版社、专业期刊杂志参与了作品的出版发行与推介,提高了英译本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它们使得新时期寻根小说走出西方边缘化的社会角落,传播范围逐渐形成主流化、大众化的趋势。海外出版机构在新时期寻根小说的世界经典化中扮演着文学系统之外的关键角色。而相关作品译本在海外出版场域中可以获得有形的经济资本、无形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表征社会地位的象征资本,进而进入经典构建历程。韩少功的《归去来》先由英文《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传播到国外,但反应平平,后被收入华裔学者戴静编译的《春笋: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这本英译中国小说合集在兰登书屋出版发行。随后,该部短篇又被收入华裔学者萧凤霞编译的《犁田、农民、思想家与政权: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其他短篇名作一起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又被收入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选集《一个自己的地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紧跟其后,出版了翻译家张佩瑶编译的包含《归去来》和寻根代表作《爸爸爸》《女女女》的小说集《归去来及其他》。可见,兰登书屋介入《归去来》的传播后,扩大了其影响力。莫言寻根小说的海外经典化获得英美主流商业出版机构的赞助。它是莫言寻根小说海外传播的主渠道,以市场为导向,针对大众读者。国际大型商业出版集团兰登书屋旗下的维京出版社推出了英译《红高粱》。商业出版社在英语世界的读者群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通过针对性的出版选题、成功的推介和畅通的销售渠道,将莫言寻根小说带入海外大众读者的视野,对其作品的海外经典建构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王安忆寻根作品海外出版的形式具有多样化的特色。首部寻根小说英译本《小鲍庄》在美国企鹅维京出版公司出版后,被美国评论界誉为“寻根文学经典之作”,引起了评论界的高度关注。王安忆寻根小说通过出版媒介,在海外广泛传播,进入美国高校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材,被英美学者深度研究,同时通过大众化的出版媒介进入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王安忆成为海外最具影响力的当代中国女作家之一,海外出版机构发挥了关键的建设性力量。
当代寻根小说的海外经典化反映了具有独特艺术与文化品质的当代中国文学在国外被认同与接受的历程。体现本土性的文化异质性与世界性元素使得寻根故事的文化思想更易激发域外受众的阅读审美情趣,而汉学家译介与西方学者的多元化深度阐释、不同类型出版机构的推动促成了这一类型小说的海外认同与经典建构。在这些文学要素与非文学要素的合力作用下,当代寻根小说的海外影响力与思想震撼力得以生成。新时期寻根小说的海外经典化之路对于我们当下提升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力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