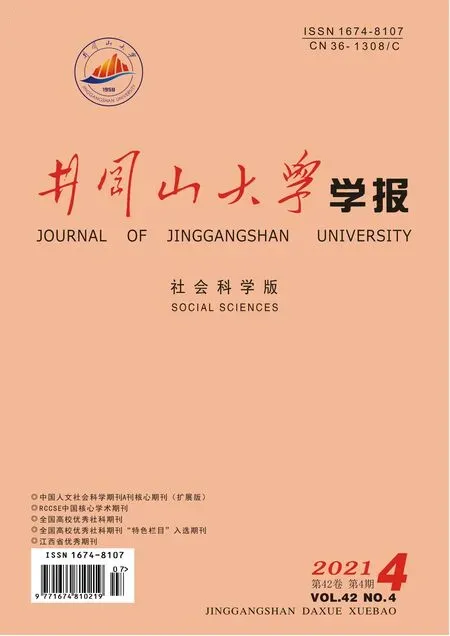论苏区戏剧中“形象政治”的形成及其独特性
许 丽
(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研究中心,江西赣州341000)
苏区戏剧产生于20 世纪20 年代末至30 年代初那个特殊战争年代。尽管从艺术本身来看,苏区戏剧较为粗糙,但它却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发挥过巨大的情感效应。如有学者说:“戏剧是苏区最重要的文艺形式,在文艺大众化、文艺与革命相结合方面做出了卓有成就的尝试”[1]。的确,它一方面服务于苏区的政权建设、武装斗争及土地革命等政治任务,不可避免地与革命意志发生关联。另一方面,它关注艺术形象的塑造与刻画。因此,在苏区戏剧中,艺术形象不是独立的艺术形象,而是融入了政治意识的艺术形象,其中的政治也并非与艺术形象绝缘的政治,而是在艺术形象的把握与体悟中可以获得某种政治倾向或政治观念。如此一来,艺术形象与政治结合为一体,形成了“形象政治”。故此,“形象政治”是苏区戏剧中的重要现象,它的形成及其独特性值得深入探讨。
一、苏区戏剧“形象政治”形成的历史渊源
苏区戏剧承继从民智启蒙到新文化启蒙再到革命启蒙的启蒙思潮。早在20 世纪初,中国戏剧已开始走向人生、走向政治。1902 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呼吁“小说界革命”。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2](P34)梁启超所说的“小说”,包括戏剧。他赋予小说、戏剧严肃的社会启蒙与政治革命的使命,其目的就在唤醒民众,启蒙民智,改良社会风气。1904 年,陈去病等人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并在《<二十世纪大舞台丛报>招股启并简章》中说:“同人痛念时局沦胥,民智未迪,而下等社会尤如狮睡之难醒。侧闻泰东西各文明国,其中人士注意开通风气者,莫不以改良戏剧为急务……吾国戏剧本来称善,幸改良之事兹又萌芽,若不创行报纸,布告通国,则无以普及一般之国民;何足广收其效,此《二十世纪大舞台丛报》之所由发起也。”[3]他们正是看到了戏曲在现实社会中对普通民众的意义和影响,所以希望借助戏曲来开启民智,改良社会,振兴中华。1905年,箸夫在《论开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戏本为先》中说:“剧也者,于普通社会之良否,人心风俗之纯漓,其影响之甚大也。”[4](P60)他也是主张借戏曲以开启民智,移风易俗,进而改良社会。柳亚子、陈去病、天僇生、健鹤等都强调戏剧改良的指向在于民智启蒙,其最终目标是为改良社会,振兴国家。
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形形色色的现代文化思潮,如启蒙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想著作大量译介到中国。而与之相关的戏剧理论也随之进入国人的视野之中。其中的“民主”“科学”思想以及实用论、怀疑论、进化论等理论方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戏剧的观念。他们认为戏剧应是以人的精神、自我的意识、个性的独立自由为核心要义,而这些要义在传统旧戏中是缺失的,故传统旧戏是“非人的文学”,应当受到批判。故此,以京剧为代表的传统戏曲,被视为“非人的文学”的旧文学堡垒,首当其冲遭至无情地批判。如1917-1919 年间,《新青年》发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胡适、傅斯年等人讨论戏剧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中国传统戏曲的思想内容、社会意义、审美价值等多个方面发起猛烈攻击。1918 年 10 月,《新青年》还开辟“戏剧改良”专号。如刊发了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钱玄同《随感录》、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等文章。他们以西方戏剧为样本,以西方戏剧的观念与审美尺度来评判中国旧戏,并且认为只有如此,中国的戏剧才能获得发展的生机。如胡适说:“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5](P310)而当以西方的纯美文学观念为准绳来区分旧文学中的文学性与非文学性时,“文以载道”的旧文学必然要被大加讨伐,被彻底否定了。
五卅惨案的发生,这更大地冲击着中国知识分子已有的思想意识与政治热情。知识分子们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新文化的途径来启蒙民智,这是很难根除中国社会的痼疾,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诚如所说,五卅惨案“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猛省,使他们看到了西方列强‘帝国主义’的存在,也使他们看到了与之并存于商业都会上海的工人们的悲惨状况,随着大多数作家的同情逐渐左倾,一个政治化的过程被调动起来。”[6](P417)这表明随着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进一步认识,这必然引起他们文艺观念的转变。故革命启蒙逐渐取代新文化启蒙,很快成为文艺思潮的主流。这反映在戏剧领域,则体现为由强调戏剧在人性与思想启蒙上的功用转换为突显戏剧在革命启蒙方面的价值意义。革命启蒙,其意图在于是“启发阶级解放意识的觉醒,宣传和鼓动的是为阶级、政党的利益目标而奋斗。”[7](P114)
苏区戏剧正是沿着革命启蒙的道路向前发展。当时由于国民党的恶意宣传,加之苏区民众“未开化”,红军最初驻扎苏区时困难重重:一方面受到国民党反革命的夹击围剿,另一方面一开始没能获得民众的鼎力支持。不少农民将红军视为匪军,避之不及。这样一来,红军在苏区的活动可以说举步维艰,时局极为不利。而更为糟糕的是这一切又给红军军队内部带来不良影响,不少红军战士因此弃军而逃。正是意识到借助戏剧演艺,才逐渐为民众所了解,使他们意识到红军绝非如国民党所宣扬地那般。正好相反,他们是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军队。
二、苏区戏剧“形象政治”形成的现实动力
如果说从民智启蒙到新文化启蒙再到革命启蒙的发展演进,表明苏区戏剧“形象政治”的形成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那么,新中国的构想与实践,则是苏区戏剧“形象政治”形成的现实动力。有学者谈到戏剧在中国革命史上所发生的作用时说:“戏剧并不仅仅是一个装满了众多群众运动武器的军火库中的一种策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隐喻。从土地改革一直到今天,凭借舞台上的公开演出,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在革命中全心全意的形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这些情景下所表达的情感一点儿也不真实,或者是虚假的。人类感情的特殊之处正是其矛盾和顺应的共存;中国共产党这一手段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充分意识到情感的根本真实性,并对其加以利用。”[8]这里不仅说明了戏剧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意义,更在于揭示共产党人在引领时代潮流,把捉劳苦大众的心声方面的自觉意识。共产党人关于新中国的构想与实践正源此而生。
事实上,对新的国家、新的社会的期待与向往,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不少中华仁人志士的共同理想。如康有为就曾说:“既审中国之亡,救之不得,坐视不忍,大发浮海居夷之叹,欲行教于美,又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9](P17)由此可见,康有为有因感国势不振而萌生出到海外开辟“新中国”的愿景。梁启超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展示了他对未来中国的构想,并在《自题新中国未来记》中写下“无端忽作太平梦,放眼昆仑绝顶来”[10](P5428)诗句,抒发了他对新中国的憧憬与期盼。但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都还只是停留在意识层面上的思索,并未付诸于实际当中。到孙中山这里,他开始了“新中国”的革命实践,希冀在“创建民国”与“改造民国”中,为国人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不过,他的中华民国因未充分重视到人民群众的地位与作用,以致徒有其名而无其实。
而中国共产党不仅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新中国”的构想,而且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化,关于新中国的构想不断具体化。如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11](P663)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新中国蓝图,无论是政治方面、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要实现质的飞跃,都要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呈现。首先,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不再受到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的统治。其次,它是自由、繁荣、文明进步的,这完全不同于人民受压迫、受剥削,且又愚昧落后的旧社会。再次,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是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创造者,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与作用。这是它不同于以往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能够得民心,不仅在于他对新中国构想的推进与具体化,更在于它对民心的体察,以“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实践将新中国构想付诸实际当中。从当时苏区的现状看,黑暗统治遍布生活的各个角落、苛捐杂税负担沉重、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人民群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从毛泽东的兴国调查可见一斑。他指出当地的剥削形式有地租剥削、高利剥削、税捐剥削等,而且剥削程度极为严重。如他谈到“当利”这条时,写道:“当一百文,月利五文,当一千文,月利五十文,当一元,月利五分,都拿小洋计算。十个月为期,到期不赎,延一个月死当。月利百分之五,即年利百分之六十,这种剥削非常厉害。贫农、雇农、工人、游民四种人中,进当铺的很多。这四种人,一百家中有六十家进当铺。抵押品,铁器、锡器、银器、蚊帐、被窝、衣服,都要。本区跑到自鹭去当东西的,非常之多,占贫苦群众百分之六十。”[12](P206-207)毛泽东这一调查显示:一是将物品拿去典当是要面临着较大的亏损;二是即便如此,典当却频繁发生,且在劳苦大众中所占比例极高;三是典当的物品囊括了日常生活中的必需物品。这些都表明穷苦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难以为继的情状。而这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土地为少数人占有。毛泽东的调查中还说到:“真正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人数不过百分之六,他们的土地却占百分之八十。……中农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土地却只占百分之十五。……游民百分之二是指完全失业靠赌钱做土匪等为生的一群人,那些半失业的不在此例。”[11](P200)如此一来,劳苦大众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他们要依靠土地生存下来,就只能从土地所有者手中去租,或者受雇于这些土地所有者,因而遭到盘剥压榨也就在所难免了。故此,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艺术形象描述并展现不同于落后现实的未来世界,即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宣传与实践,确证着共产党人对于新中国的展望与想象,这极易逼近民众的内心,引发他们的共鸣与回应。
综上所述,共产党人祈求建立一个与旧中国完全不同的新中国,并在“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实践中确证着新中国的种种可能,这构成了苏区戏剧艺术形象建构的诱因和动力,由此也就有了“形象政治”的形态。这种“形象政治”诱发人民群众对新中国美好生活的想望和追求,从而选择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心甘情愿地支持与拥护革命。美国学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不由地感叹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13](P110)
三、苏区戏剧“形象政治”形成的艺术可能
在艺术实践中,苏区戏剧的“形象政治”集中体现为通过形象对照来突显革命意志。苏区戏剧注重塑造艺术形象,并在艺术形象的鲜明对照中呈现革命意志,这首先与艺术形象的独特功能有关。
其一,艺术形象具有象征功能,因此它可成为革命的象征符号,而通过正反艺术形象的比对则可达到革命意念的传达与渲染。如有学者指出:“政治宣传画常常用插‘镰刀斧头旗’与拔‘青天白日旗’、气宇轩昂的红军‘大捷’与‘獐头鼠目的敌人’溃窜等对举的形象来传达革命胜利的信息。……这些强烈对比的形象却能坚定‘我军必胜、敌军必亡’的信念。”[14]苏区戏剧的艺术形象也基本采取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如《年关斗争》是通过农民与地主的突出比对来突显这两个阶级的尖锐矛盾。农民张三出身贫苦,食不果腹,欠下杨克明、俞麻子、夏波澄三个恶霸地主的债务。在年关的时候,三个地主先后到张三家讨债,将张家洗劫一空。地主杨克明强奸张妻,逼得张妻上吊自杀。地主夏波澄则把张三的女儿抢走了。在被逼无奈,忍无可忍的情形下,张三受到地下党员的启发,提高了觉悟,与广大受苦受难的农民一同发起暴动,将三个地主杀死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显然,《年关斗争》通过农民的“苦”与地主的“毒”,以此说明“打土豪、分田地”的必要与必然。《战斗的夏天》是以查田运动为主题,全剧共分三幕。第一幕工余的闲谈中透露出查田运动的消息。第二幕主要表现反动分子秘密开会商量破坏查田运动的阴谋。第三幕讲查田的收获即冒充贫农的地主苏庆云与冒充共产党员的反动富农陈阿富被抓。该剧中的艺术形象塑造也是以对照的方式来呈现的。如地主苏庆云、反动富农陈阿富等密谋把乡政府主席干掉,教唆丙杀死钟文连家的牛等,表现了他们欺压百姓的种种丑恶行径,揭示了他们自私自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本质。而共产党员谢大发、贫农钟文连等则是全心全意为百姓着想、为民谋福的典型代表。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形象刻画,揭示了当时农村的阶级斗争以及土地革命必然取得胜利的题旨。还有如《父与子》则主要是工人与资本家的形象比照,揭示阶级矛盾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旧世界》《活捉萧家璧》《阶级》《一起抗日去》《地主婆》《打土豪》等剧作也都是通过敌我双方的形象表现,以配合当时的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
其二,艺术形象具有怡情功能,因而通过正反形象的比对可以影响受众的情感选择,并激发他们的革命激情。列夫·托尔斯泰认为艺术即是一种唤起情感、传递情感的过程。他说:“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体验过的感情,而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语言所表达的形象把这种感觉传达出来,使别人也能体验到同样感情”。[15](P60)故此,艺术形象是情感传递的载体。如《义勇军》分三幕,讲述了一名义勇军战士在受到日军袭击后的逃亡途中,受到国民党的欺骗,国军首长要求首先消灭共产党。红军派来的地下工作者向白军战士揭露了国民党的阴谋,说明要抗日反帝,必先加入红军打倒国民党。该剧揭示了国民党真剿共假抗日的丑恶嘴脸,同时也表达出对红军的认可与信任。又如《志愿当红军》讲的是蒋介石对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时一位农民报名参军,但妻子认为“世上几多人呀,怎么偏要你当兵”“你要去当兵呀,我要去离婚”。后在指导员“我帮你砍柴,我帮你挑水,我帮你种菜”的优待军属政策的解说下,妻子认可了“保卫苏维埃呀,人人有责任”的思想,并主动提出“我呀回家去,帮他捡衫衣”。该剧中妇女一开始不同意丈夫参军的心理与情感,这在当时苏区民众身上是普遍存在的。而戏剧真实地将这种情感再现与表现出来,并通过苏区政府的优待军属政策的宣传,以解除民众的后顾之忧,从中可见苏区政府是一心为民的好政府。这使苏区民众从心底认同苏区政府,自愿加入红军队伍中来。《欢送哥哥上前方》套用十送郎的民间曲调,写刘春生报名参军离别时,与情妹妹李兰花依依惜别的情景。这其中既有青年男女之间炽热纯真的爱情,更有对革命的高度认同。这同样传达出苏区群众对“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拥护与支持。其他如《反对开小差》《拥军优属》《位置在前线》《问大嫂》《拖尾巴》《当红军光荣》《快快归队当红军》[16]等剧作都与当时革命战争密切相关,其中的艺术形象都具有怡情功能,故此能唤起民众、鼓舞民众,并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
苏区戏剧借助形象对照来突显革命意志,这除了与艺术形象的独特功能密不可分,还与当时苏区的革命依靠力量有关。当时苏区革命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但农民受教育程度极低,文盲居多。毛泽东曾对苏区进行了实地调查,从他的寻乌调查中可一瞥苏区的大致情况。他说:“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依全县人口说,约计如下:不识字百分之六十,识字百分之四十。”[11](P159-160)这表明,在苏区,男女之间、南北地区之间的受教育程度都呈现出极度不平衡。而且,从他的调查可见,教育基本是有钱人的专利,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等子弟才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则主要是劳苦的农民群众。但这些劳苦大众及其子女则是被排除在教育的大门之外,文盲所占比例极高。1931年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革命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应该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17](P647)此后,还通过了《消灭文盲决议案》,并制定了《消灭文盲协会章程》,以及建立了消灭文盲协会组织等。这都可见苏区政府对于扫盲工作的重视,也可窥见当时苏区中文盲率之高。不惟如此,因苏区闭塞的环境、封建迷信传统等的影响,他们经常游离于政治之外,政治觉悟极低,政治参与意识淡薄。所以,如何将革命思想或革命意识传达给人民大众,并使他们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以及跟着红军翻身得解放的美好愿景, 这是当时苏区最为关注的问题。苏区戏剧正是在形象对照中突显革命意志,通过形象系列的鲜明对比,以一种“寓教于乐”、喜闻乐见的方式,将革命道理寓于其中,为广大的劳苦大众所知晓,并能说服他们跟着共产党走,加入红军中来,为翻身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形象政治”与苏区戏剧的独特性
刘锋杰在《文学政治学的创构: 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一书中提出“文学想象政治论”,他认为文学与政治都是人类的一种想象活动,且在“同为美好生活的想象”[18](P608)基础上达到共生与交融。可以说,艺术形象与政治结合也同样源自两者同为美好生活的想象。苏区戏剧的形象书写通过鲜明强调的对比模式,对政治进行了有效的想象,参与了人的建构和民族国家的建构。这种“形象政治”,除了有艺术技巧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与标语口号式叙事相比,它更为大众化,因而能获得“化大众”的效果。可以说,“形象政治”以其特有的方式极其有力地满足了社会的大众化诉求,从而备受瞩目。而这恰恰赋予了苏区戏剧政治化最为可贵的“审美”特征。但是这样一种“形象政治”的形态,它既不同于苏联艺术中的形象,也与西方殖民主义和话语霸权侵袭下的形象学旨趣有很大不同,从而体现了它独特性。
首先,它有着不同于苏联艺术中的形象的特质。不可否认,苏区戏剧受到苏联文艺思想的影响,但苏区戏剧由于对农民的关注,这使得具有与苏联艺术形象完全不同的表现内容与表现方式。从表现内容看,苏区戏剧所塑造的主要是农民形象,即便是红军战士形象,那也不过是穿上了军装的农民。所以,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的农民的革命斗争及其生产生活成为苏区戏剧的主要内容。而苏联艺术中的形象则更多为工人阶级,这与苏联革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有关。从表现方式看,苏区戏剧因其受众文化水平极低,并且政治觉悟不高,所以它必然要结合当地民间传统,创设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如借用采茶戏、东河戏等民间形式,将苏区地域的“真事”和“真人”加入戏剧中,把“深奥”的革命与阶级理念转化为生动具体的戏剧形象等。而这也使得苏区戏剧形象不同于苏联艺术形象。
其次,它和西方比较文学形象学有所不同。如果说西方比较文学形象学旨在通过形象重构以反抗话语霸权的话,那么,苏区戏剧的用意则更多地体现为在民族危亡时刻,启蒙大众与救亡中国,怀抱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想象。
当然,不可否认,苏区戏剧存有简单化、类型化倾向。有学者说:“中央苏区文艺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合乎逻辑的发展,而是历史变异所催生的文学变形。它逸出文学的常轨而融入政治,最终依附政治,成为政治的一部分。”[19]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当我们面对艺术形象的政治化问题,不可忽视苏区戏剧为我们提供的中国经验。艺术形象与政治都是人们想象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苏区戏剧的形象政治已经表明了艺术与政治在性质与功能上的互文性。两者同是在美好生活的想象基础之上进行形象建构并发挥政治启蒙功能。艺术可以诱发与开拓人的审美想象空间,政治同样可以并且应该建构美好想象空间,从而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