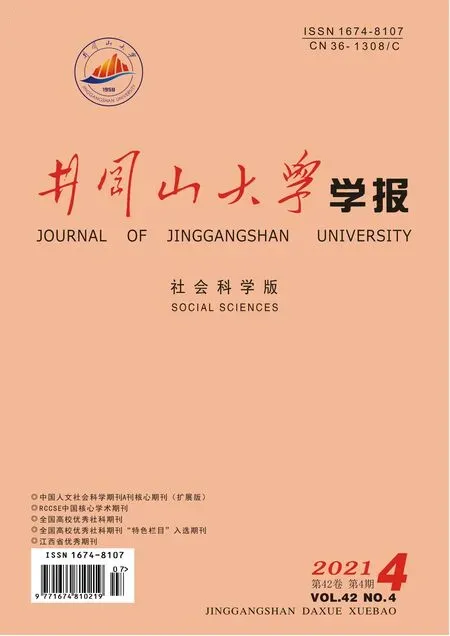论清初剃发令的内涵及实质
陈文亮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江西吉安343009)
清朝入关之后,通过推行剃发令,从身体样貌上重塑了中国人的形象,使得清朝人从身体形象上大大区别于其他朝代人的身体形象。虽然我们对剃发令并不陌生,但是我们常常忽视了剃发令的真正内涵。它不仅包括我们熟知的剃发、易服,还涉及到其他多方面细节。从身体的角度来说,至少还包括了剃须。而从衣冠服饰的角度来说,至少还包括了易鞋。对剃发令内涵的重新厘定,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分析剃发令的真正精神。剃发令并非权力对身体的暴虐,这种理解过于简单化和哲学化了。考虑到剃发令还有更多涉及到胡须、鞋袜等具体细致的规定,可以说,剃发令的本质是清朝统治者对原明朝百姓的满洲化改造。“暴虐”并不是目的,移风易俗、满洲化才是目的。
“剃发令”之名长期以来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并非清朝官方的定名。文献中对清朝剃发令政策的称呼较多。或称为“剃发令”,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云:“江淮间有司或多操切,严剃发令,以施新政,民益走险不顾。”[1](p398)或称之为“剃头诏”,《梅勒章京屯代揭帖》云:“近因剃头诏下,职屡差人谕其遵奉。”[2](p513)或称为剃头之令,如赵开心在给多尔衮的奏折中就说:“如大学士忽传王上有官民剃头之旨,举朝闻之争相错愕。”[3](p761-762)或称之为削发令,《研堂见闻杂录》云:“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处处蜂起。”[4](p268)又或称为“鬄禁”:“鬄禁再设。”[5](p504)或称为“髡令”:“幸而得全于籍令,兼得全于髡令。”[5](p522)
这些文献对剃发令的指涉,都侧重于剃发之上,因为当时人感受最强烈的是剃发。清朝政策推行的侧重点,也在于剃发。但是用剃发令来称呼此项清朝国策,使我们忽视了剃发令的其他内涵。这种简单化理解的后果是让我们容易误解剃发令的实质,而将剃发令看成权力对身体的象征性征服。所谓象征性征服,即将剃发本身作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权力关系的隐喻。这种理解毋宁说是一种诗性的引申,而不是对历史的阐释。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种理解过于主观了。综合考察剃发令的完整内容,我们会发现,剃发令是清朝入关后对原明朝百姓的满洲化改造。
一、理解剃发令内涵的学术意义
剃发令的研究经历了几种不同的范式。1995年,台湾学者吴志铿发表了论文《清代前期剃发易服令的施行》,他在文中总结了剃发令的研究状况:“过去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剃发,且强调满汉的文化冲突,标榜汉人不愿沦为夷狄衣冠的重气节或爱国的表现。大陆方面的研究则充满阶级压迫的意识,强调异民族统治阶层对汉民族被统治阶层的压迫,对于其他满洲本位法令则强调系满汉统治阶层联合对满汉下阶层的剥削。”[6](p169-170)文中明确指出,剃发令的研究,早期集中于对反剃发者民族气节、爱国主义的表现和歌颂。而后期研究中,大陆方面从阶级史观角度,重点在于强调剃发令中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内涵。这种概括是符合事实的,其代表作就是南开大学历史系陈生玺1985 年发表在《历史研究》的《清初剃发令的实施与汉族地主阶级的派系斗争》,该文就比较强调民族压迫下社会政策的形成和推行。而其现实关怀点,就在于多民族国家融合与统一的实践。[7]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是包群立在1991 年发表的《从剃发制度看清朝的民族政策》。[8](p66)从话语和关怀点来说,该文与陈生玺的文章非常相近。
吴志铿提出了剃发令研究的政治象征说。他认为:“剃发、易服虽为不同之满洲本位法令,唯其性质相近,均属满人征服汉人之外在服饰象征,其颁行亦共同进退,故一般均连称并用。”[6](p170)此文的创新性表现在对阶级压迫、民族压迫说的突破。阶级压迫、民族压迫说,未尝没有道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从新的角度挖掘历史事件的学术价值,是大势所趋。换句话说,学术界出现了一种范式变革。旧的阶级斗争、民族压迫范式,已经略显陈旧,而新的研究范式也就呼之欲出了。
吴志铿认为:“透过这些外表的打扮,使人一眼即知其所代表的种族文化,因此,服饰装扮不仅为文化之表征,亦已成为文化精神之象征。满洲的冠服制度是早在入关前即已形成的,随着满族势力的发展与壮大,满人对其冠服发式自必更引以为豪。满族既已统治中国,欲将中国置于其‘王化’之下,使汉族成为顺民,最具意义且最为可行的办法即改变汉人之衣冠发式,强迫其接受满人的衣冠发式。……所以,剃发易服对满清统治者而言,极具形式意义。”[6](p176)政治象征说不仅抛弃了陈旧的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史观,而且建立起了另外一套全新的话语。在这套话语中,占据主角的不再是阶级和民族矛盾,而是政治体、民族、社群之间的交往、战争、征服过程中的一般性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比起意识形态性的政治话语,似乎更加具有普遍性和说服力。清朝征服了明朝,这种现实中的权力关系必然反映在身体和服饰之上。
1999 年,陈生玺在《南开学报》发表了《剃发令对清初的政治影响》。相比1985 年他在《历史研究》发表的《清初剃发令的实施与汉族地主阶级的派系斗争》,这篇论文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了很多。但是其论文的现实关怀点,仍然落在“各民族之间经济与文化的融合以及民族关系的加强”。[9](p14)其现实关怀当然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但是学术范式的更新似乎是不可逆的了。吴志铿为代表的政治象征说,成为了学术界的主流,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比如谈火生的《辫子:政治象征与认同》即其步趋者之一。[10]
学术话语一直在变迁之中,政治象征说发展出了更多的变形。2006 年,张德安在《中国社会历史评论》上发表的《身体的争夺与展示:近世中国发式变迁中的权力斗争》,该文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内——从明末到清末,论证了身体是权力斗争的场域,身体的改造背后,总存在着权力的变换。从身体成了权力关系的被动表现物:“作为社会性的个体,他的身体同样是社会性的。明末清初满洲剃发征服,完全通过对被征服者的身体规范来展示征服者的统治权利,通过政治暴力塑造了中国满汉一家的民族形象。辛亥革命作为一场弃旧扬新的革命,它以排满为口号,要求国民剪掉辫子,改留短发,树立民族新形象。虽然辛亥革命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和带有强种兴邦的美好愿望,但革命党人在实践中却没有把本属私事的发式的选择权留给个人,而是在暴力革命中把衣冠制度的变迁当成一次改造国民形象的政治运动来开展。”[11](p288)
张德安在这篇文章强调了身体作为权力关系的被动表现物。从话语上来说,该文带有了更多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强调了“身体”。其背后是近些年学术界身体史研究、身体话语的兴起,而其所谓的权力,也更加侧重于“微观”表现。我们多少可以从中看到福柯权力学说的影子。更有人直接引用福柯的规训理论来研究剃发令。侯杰、胡伟2005 年在《学术月刊》发表《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认为:辫发成为满族统治者成功征服的标志,也是其拥有广大臣服者的外在表现。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发式问题贯穿了清朝整个历史,展示了权力与身体之间相互塑造的过程。[12]作者在这里似乎找到了福柯权力规训学说最好的历史例证。剃发令研究的政治象征说,其核心要点在于把身体改造作为权力关系的延伸,把身体作为权力展示的场域。然而,福柯权力哲学的本质是对常规权力的批判。而推行剃发令的,并非常规状况下的国家权力。
剃发令究竟是一种政治上的象征性操作,还是基于满洲风俗的移植、对汉人身体形象的满洲化?如果剃发令仅仅是一种象征性操作,那么剃发易服,就只是一个孤立的行为。清朝统治者以及被剃发易服的百姓,所在乎的仅仅是这一象征性行为的隐喻意义:一种抽象的权力关系。但是,将剃发令理解为将原明朝百姓的满洲化策略,剃发令就不只是一个象征性操作,而要求更为全面的、细致的改造。后者似乎更符合历史现实。
本文试图提出这样一种新的观点,剃发令的本质是汉人的满洲化。所谓政治象征说,与此并不相悖。但是政治象征说的核心是权力关系,而满洲化理论的核心则是身份改造。从逻辑上来说,政治象征说中,其象征性行为越是简单,就越有符号性、象征性。而此种象征性行为的选择,本质上是随机的、任意的。就象征一词的定义来说,其本质在于其象征的所指,而不在于符号自身。从满洲化改造的角度来说,剃发本身就是目的。满洲化这一目标,也绝不止于剃发、易服的孤立行为,而必须追求其更加全面、细节化的实现方式。
二、剃发令剃发易服以外的其他内涵
1644 年,清朝入关,定都北京。由于南明的存在,清朝对汉人服饰采取了包容的策略。多尔衮在五月二十四日(6 月28 日)谕兵部曰:“我国建都燕京,天下军民之罹难者如在水火之中。可即傅檄救之其各府州县,但驰文招抚文到之日即行归顺者,城内官员各升一级。军民各仍其业,永无迁徙之劳。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12](p59-60)
多尔衮这段话颇具有迷惑性。这段话似乎坐实了很多人对剃发令的理解,即剃发令仅仅是一种临时性的、权宜性、功能性的政治选择,是为了区别顺逆的象征性行为。但是,从后来剃发令重启的现实来看,多尔衮这段话是违心的。由于南明政权的存在,多尔衮不希望扩大对立面,由此不得已而暂停了剃发令。他通过这段话,来欺骗百姓和官员,让他们相信,清朝并没有长期推行剃发令的意愿,剃发令仅仅是特殊历史情境下的措施。多尔衮有意回避了剃发令的真实目标。
顺治二年五月十五日(1645 年 6 月 8 日),多铎率领清军占领了南京。清朝最大的威胁消灭了以后,多尔衮开始出尔反尔,重启剃发令。顺治二年六月初五(1645 年6 月28 日),多尔衮谕多铎等,令江南军民薙发:“各处文武官员,尽命薙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其郡邑有未下者,或宜移檄招抚,或宜统兵征剿。地方一切事宜,酌议速奏。”[14](p150)六月十五日(7 月 8 日),多尔衮谕礼部曰:“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划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划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此事无俟朕言,想天下臣民亦必自知也。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进章,欲将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该部即行传谕京城内外并直隶各省府州县衙所城堡等处,俾文武衙门官吏师生,一应军民人等,一体遵行。”[10](p151)这段话颇有深意。首先,它声明从前的剃发政策,是战时状态中的权宜之计。当时为了不扩大对立面,所以“不即令划一”,具有很强的折中性、临时性。其次,它表明,对于多尔衮和清朝统治者来说,剃发令有其必然性,而且谋划已久,只不过“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再次,剃发令的逻辑起点是满洲本位。所谓“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皇帝和满洲是君、父,是主导性的,而汉臣、汉族百姓是臣、子,是从属性的。从属性就意味着自身没有独立性、没有本质性。
和多尔衮前面暂停剃发令的命令比起来,这段话才体现了多尔衮的真实意志。多尔衮明确指出,剃发令的颁布并非由于权力的任性,也不是清朝统治者要强加给被征服人民任何耻辱性的标记--至少在多尔衮看来是这样的。多尔衮推行剃发令的理由是,清朝既然得到了这些土地和人民,原来明朝百姓因此成为了清朝人,那么就必须遵从满洲风俗。多尔衮对“清朝人”有一种本质性的理解,即只有遵从满洲风俗、清朝制度的人,才是清朝人。而不是说,你生活在清朝统治下就自然而然是一个清朝人。“若不划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剃发令就是把原明朝百姓改造成清朝人,剃发令是一种满洲化的策略。
从多尔衮的角度来说,剃发令是基于某种合理性假说的决策,而不是权力的随意妄为。剃发不是一种象征性行为,“满洲化策略”不是某种象征性行为就能够实现的,而必须通过更为现象化的,也更为全面细致的多种行为的组合才能够实现。我们结合剃发令的其他内容更容易看出这一点。
(一)剃发令中剃须的内容
周齐曾,字思沂,浙江人,崇祯癸未举人,曾当过广州顺德县令。甲申后,遁居浙江剡溪,自称无发居士。[15](p72)周齐曾迫于压力,不得已而剃发。剃发后作诗曰:“恨不悉除鬓发去,犹留松下一孤身。我来仍唤松为树,未必松呼我是人。”[16](p382)剃发后的自悲自叹情绪在清初人身上很普遍,周齐曾只是其中一个而已。周齐曾虽然被迫剃发,但是仍然认为只有留着全发,才是完整的人。于是他将剃下来的头发收集起来,为之建立了一个墓,称为“发冢”。周齐曾给发冢写了一个墓志铭,铭曰:“谓冢外有全人,已无须无发;谓冢中有全人,复无肉无骨。名则血余,不能化苌弘之碧,见室人而不动,缺常山之节。倘陵谷之不迁,将终古囊云之枕穴。”[17](p453)其中“无须无发”四个字,表明周齐曾不仅剃发,而且剃须。那么剃须是其自愿行为,还是被迫的呢?周齐曾剃除须发之后,自己不复为“全人”。这种抵触情绪表明,周齐曾并不是自愿剃须的。可见,剃须是清朝剃发令政策的一部分。
周齐曾的自悲自叹,是因为他受到了清朝的“象征性”打击吗?从周齐曾的角度确实是这样。周齐曾并不认为自己剃发剃须之后就变成了清朝人,因为他并不认同清朝政权。他感受最强烈的是一种创伤性体验,他受到了“损害”,他不再是完整的人了。这种感受,似乎符合当代学者对剃发令的主流解释:剃发令隐喻着征服与被征服的权力关系。这一层意义,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尤其明显。
但是我们对剃发令本质的理解,应该是从实施者的主观动机来理解,而不是从受害者的自我感受来理解。受害者的自我感受只是剃发令的客观效果,而不是其初衷和目的,因此也不能说成是剃发令的本质。
屈大均,字翁山,广东番禺人,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屈大均同样被迫剃发。周齐曾为自己建了一座“发冢”,屈大均则为自己建了一个“衣冠冢”,用来埋葬自己的明朝衣冠。屈大均有位朋友将自己剃下来的头发收集起来,藏于山中,请屈大均写一篇赋,以为纪念。屈大均遂写了一篇《藏发赋》,有几句是这样的:“猬毛之磔,所恃多頾。衔须不蚤,覆面其迟。魋结者脯,结缨者酰。血余外物,患不成爢。弁髦遗体,以变羌氏。岂甘戕贼,弗欲全归。索头有国,实逞淫威。”[18](p211)又曰:“鬈然既去,何用须眉。拔其下颔,以便射飞。何关神智,唾弃莫疑。”[14](p212)这几句诗句清楚表明清朝剃发令包含了剃须的内容。“猬毛之磔,所恃多頾。”这句诗表明作者已经没有了胡须,因此才会羡慕刺猬有毛。“拔其下颔,以便射飞。”更指出了清朝人剃须习俗,是由于其骑射传统。剃须主要剃的是“下颔”的胡须,以便拉弓的时候,可以将弓弦引到下巴下面,而不会缠上胡须。清朝推行剃发令的时候,将这一习俗推广到中原来了。
屈大均另外一篇文章《长发乞人赞》也提到了清朝剃须的政策。郑成功攻打南京失败后,其军中有人遂流落南京,沦为乞丐。由于没有遵守剃发令,当局将之逮捕。但是由于形似疯癫,旋又将之释放。屈大均称赞他:“人寸我尺,甚称美须。天形无损,只可为奴。一丝华夏,在尔皮肤。”[19](p208-209)意思是:别人只有一寸多的胡茬,而你却能够坦然留着一尺长的美须,保持了身体的完整性。而这种完整性却是以成为乞丐、奴隶为代价的。由此可见,普通男子不仅剃发,还要剃须的。
屈大均作为剃发令的受害者,同样有一种羞辱和创伤经验。但是这种创伤经验,和周齐曾一样,都是来源于清朝强制推行满洲化风俗而来的人格损害。这并不等于说剃发令的本质就是追求这一效果,使剃发成为被征服者的标记。
关于剃须政策的存在,另外一份清朝官方档案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顺治三年四月十五日,直隶真定府晋州武强县人赵高明、赵万银、赵应亨等三人因为头发违式被捕,其被指控的罪名包括:“高明全未剃发,万银、应亨稍剃些须,不遵新式。”[20](p8)可见,剃发令包含了剃须的内容,并且还有规定的、统一的样式,有明确的标准。
清朝时期,来华朝贡的朝鲜人,常常将所见所闻形诸笔端。1803 年,朝鲜人李海应在其所著《蓟山纪程》写道:“男子年二十以前并剃其须髯,二十五岁以后则只剃髯而存须。过三十岁以后则否。”[21](p565)1832 年,朝鲜冬至兼谢恩使使团的书状官金景善来到清朝,写下了《燕辕直指》一书,也提到了清朝人剃须的风俗:“男子二十以前并剃须髯,盖便于弯弓也。廿五以后只剃髯而存须,三十以后则否。”[22](p249)有些人的记载与此略异。朴齐寅认为:“惟髭须则从其年纪而剃之。自四十岁以后则留上须,五十以后则并留下髯。未满四十之人并须髯而尽剃之。”[23](p502)李押则认为:“其俗二十七岁以前皆剪其须,自二十八岁始不剪云。”[24](p208)这些材料清楚表明,清朝人有剃须的习俗。明朝人因为身体发肤、不可毁伤的原因,是不会剃须的。清朝人剃须的习俗是清初推行剃发令时依靠国家暴力塑造的。
1851 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进攻浙江的时候,发布了《檄告招贤文》,声讨清朝“窃据我土地,毁乱我冠裳,改易我制服,败坏我伦常,削发剃须,污我尧舜禹汤之貌。”[25](p125-126)这篇檄文所谓“削发剃须”,将发、须并举,也印证了剃发令之中存在剃须内容。
(二)剃发令中易鞋的内容
我们都知道,剃发令主要包括剃发和易服。我们一方面忽视了剃须的内容,一方面又忽视了易鞋的内容。顺治二年闰六月六日,礼部关于文武官员应用帽顶鞋带样式,规定:“凡民间无织者止许用青蓝布衣,有喜庆事许绢衣,并不许擅用各色纻丝纱罗绸帛。靴筒与鞋□(按:疑为面字)许用纯黑色布。不许用红、黄及杂色绸缎,并不许用云头,犯者以违制论。里衣从便,不在禁例。”[26](pA3-16)
这道命令应该属于剃发令的一部分。因为剃发令颁布的时候,容许衣冠从容变易,一开始侧重于剃发。后来又出台了敦促易服的命令。这道关于鞋子的禁令,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道命令不仅涉及到鞋子的颜色、材质和装饰物,尤其强调了禁止明人常用的云头装饰。这道命令对鞋子样式的规定,本质是用满洲鞋子样式取代明朝样式。剃发令之所以出现侧重点的历时性变化,主要是因为民间抵抗很严重,短时间内无法做到全面改造,因此先从剃发入手。头发一旦剃了,非一两天、一两年就可以恢复,所以百姓护发最坚。一旦实现了剃发,易服也就顺理成章了。而易服之后,再详细规定鞋袜等细节,政策也就很容易推行了。综合来看,清朝统治者在这一政策上是非常严酷而且极为细腻的。
徐珂《清稗类钞》记载,顺治四年十一月,“复诏定官民服饰之制,削发垂辫。于是江苏男子,无不箭衣小袖,深鞋紧袜,非若明崇祯之宽衣大袖,衣宽四尺,袖宽二尺,袜皆大统,鞋必浅面矣。即幼童,亦加冠于首,不必逾二十岁而加冠也。”[27](p6146)明清鞋子样式主要变化体现在:明朝以前,袜皆大统,鞋必浅面。而入清以后,则是深鞋紧袜。深鞋紧袜和满洲衣服的箭衣小袖配套,都是满洲风俗。可见,清朝入关之初,一直坚守满洲文化本位。清朝统治者得到了原明朝百姓和土地,努力从身体形象上将汉人满洲化,从而真正实现他们由外到内的身份转换。
三、重新理解剃发令的实质
剃发令政策并不局限于剃发和易服,同时还包括了剃须和鞋袜方面的禁令。以往,我们对剃发令的研究,有时候片面强调了头发的政治隐喻、伦理内涵和衣冠传统,而忽视了对剃发令在剃发、易服以外的其他内涵。这样做的后果,一方面是把剃发令孤立化了,将剃发令看成一个孤立的事件,无法从更为宏观和本质的角度来看待剃发令的实质;一方面是将剃发令隐喻化了,认为剃发令只是清朝加给原明朝百姓的征服性印记。
剃发令在一定时期确实有分辨顺逆的作用,但是其本质则是将原来明朝百姓从形象上变成(以关外满洲人为原型的)清朝人。所以,剃发令有一种整体性的目标,从整体上改造明朝人;剃发令并不局限于剃发、易服两个方面,明朝人、清朝人的所有差别化存在,都在被消灭的范围。
大而言之,剃发令对人身体的改造,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更大的计划的一部分。清朝自努尔哈赤时期以来,就对明朝制度和文化有较强的戒备心理。而在入关之后,清朝统治者直接接管了明朝土地人民,怎样对待明朝制度和文化,清朝统治者必须立刻做出选择。这是剃发令产生的背景,但其目标并不止于此。比如,汉人的肩舆之制也一度成为清朝的禁忌。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二日(1651 年4月1 日),礼科给事中法若贞奏:“下人犯上,实由等威不辨。今大小诸臣,入朝虽有顶带分别,而燕居衣冠与平民无异。吏胥华服,过于官长,优隶衣饰,同于公卿,非所以别等威也。宜分别贵贱,以防僭滥。兼请复三品以上大臣肩舆旧制,以肃观瞻。下所司议。”[28](p430)这表明,在此之前,“肩舆旧制”是被明令禁止的。
将原明朝百姓从身体形象和服饰上,全盘满洲化的努力,必然也因为执行能力等现实情况而有所打折,比如清朝朝靴则保留了明代朝靴方头的特点。《清稗类钞》曰:“凡靴之头皆尖,惟着以入朝者则方,或曰,沿明制也。而道士之靴亦方其头。”[23](p6206)清初剃发令有所谓“十从十不从之说,虽然客观地描述了某些现象,但并非清朝有意为之,而是由于执行力不足。
从效果上来说,清朝剃发令基本实现了从身体形象上将原明朝百姓满洲化的目标。时人的体验也符合清朝统治者的预期。明末诸生曾羽王《乙酉日记》记载上海一带社会情形说:“毋论贵贱老幼,皆剃头编发。余此时留发初扎起,见人初剃者,皆失形落色、秃顶光头,似乎惨状。甚有哭者,因怕剃头,连日不归。不料家中被贼挖进,盗窃一光。为此即移母亲归镇,锅灶碗杓之类从新备起,如新做人家一般。自此而新朝管事矣,自此而国运鼎革矣,自此而辫发小袖矣,自此而富且贱、贱且贵矣,自此而边关羌调、夜月笳吹、遍地吸烟矣,自此而语言轻捷、礼文删削,另自一番世界、非复旧态矣。即称顺治二年。”[29](p62)
四、结语
从政治象征的角度来说,剃发令仅仅是一种符号、一种政治表态,它本身不是目标,是没有价值的。其所象征的权力关系才是真正的实在和本质。而从满洲化改造的角度来说,剃发易服行为是这种改造的具体表现。剃发行为由此获得了一种“本体论”的地位——它自身就是目的。不过,文化上彻底的反明路线是不可能的。清朝要利用明朝经验,继承明朝制度文化,才能够统治这个庞大的国家。因此,“清承明制”就成了最佳选项。虽然如此,清朝,不管是清初还是以后,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某种反明情结,剃发令是其最为激烈和极端的一种表现。我们在看到清朝满人汉化的时候,也应该看到,汉人存在某些方面的满洲化。这是一个双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