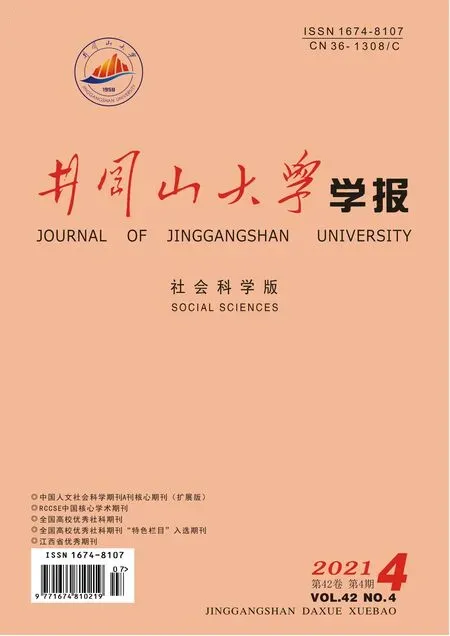宋代“隐括词”的文体生成及传媒因素考察
陈冬根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江西吉安 343009)
当前,宋代文学研究界已经注意到了隐括词,如对隐括词的定义、生成源流、产生原因以及文体特征和文学影响等均有研究。其中,以日本学者内山精也先生和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研究最为深入。两位学者除了对隐括词的概念做了较为合理的界定外,还考察了其生成源流、演变及其在宋代文学史上的影响。这些成果对于后来学者进一步研究宋代隐括体很有参考价值,不仅明确了研究对象,而且提供了文献线索以及研究思路。
不过,笔者发现,在对隐括体在宋代生成原因的考察中,多数研究只关注到其文体试验和文字游戏一面,而没有注意到传媒因素对它的重大影响。换句话说,研究界普遍忽略了宋代社会文化大环境下读者的存在,忽略了审美接受主体对文体生成的催生作用。为此,本文在阐述宋代隐括词生成和描述其文体特征的同时,着重从接受美学和传播学的角度考察了其生成过程中传媒因素的影响。
一、“隐括词”的文体生成
隐括,本作“檃栝”,后被略作“隐括”,其本义为一种矫正竹木的工具,类于规矩,揉曲叫“檃”,正方称“括”。后由其矫正之功能而衍生出“矫正”之义,又进一步引申为“使事物符合规范”之义,其作用对象和使用范围也由具体之物转向人或抽象事物,后来“隐括”被借用到文艺领域。“矫正”一词本身包含有修正、裁剪之意,所以“隐括”自然就有了剪裁、改写之意。此外,“隐括”还有更深一层意思,即“概括”。改写、剪裁之过程必然存在删殳存余之举,即必然有“概括”。意即说,隐括作为一种修辞或写作手法,始终含有改写、剪裁和概括三层意思。这种语料在古人文章中屡见不鲜。如刘勰《文心雕龙·熔裁》:“蹊要所司,职在镕裁,隐括情理,矫揉文采也。”[1](p543)许谦《论语集注考证序》:“是书或隐括其说,或演绎其简妙。”[2]胡光世《春秋提纲序》:“此编隐括诸传,苞举无遗。”[3]隐括逐渐成为一种修辞手法,表示剪裁、改写。如此,隐括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在我国诗文中广泛采用,即被泛化。
当一种修辞手法泛化后很容易成为一种写作手法。在此层面上,隐括作为写作手法,就是对原作进行剪裁、归纳、概括,使其成为一个新文本。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述林正大《风雅遗音》时说:“是编皆取前人诗文,隐括其意制为杂曲,每首之前仍全载本文,盖仿苏轼隐括‘归去来词’之例。然语意蹇拙,殊无可采。”[4](卷二百)此二语例中之“隐括”乃皆为写作手法,其意即是对原作进行剪裁、归纳、概括。同理,当一种写作手法纯熟而广泛地被使用时,它往往将被固化为一种文学体裁。这种情形最典型的恐怕是“赋”,事实上,“诗”“赞”“颂”“骈文”“寓言”“小说”等皆如此。至宋代,则隐括词、集句、嵌字、集药名、集曲名等文体之形成,亦均如是理。概言之,当“隐括”这种手法在我国古人创作中被广泛而娴熟使用时,它将定型成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即隐括体。
隐括作为一个文体术语,第一个明确提出并进行创作的是苏轼。换句话说,苏轼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创作隐括词的作家,所以后人通常视苏轼为宋代第一个创作隐括词的人。而苏轼本人此类创作又以《哨遍》(为米折腰)为始,为其代表作。其词曰: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出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
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内复几时。不自觉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5](p307)
《哨遍》一作《稍遍》。读罢词作,可以发现,这首词几乎就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翻版。其内容与陶氏原作无二致。不过,其形式上有了较大变化,即将陶氏的辞赋改成了宋人擅长的词曲形式。对此,苏轼自己在小序中也作了说明:“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 ”[5](p307)小序不仅交待了此词的创作缘起,同时也说明了本词的创作方式及其隐括对象之来源。故此作通常被视作宋代隐括词之首篇。
这种作品是属于抄袭?还是创新?是有争议的。纵观整个词史或者说古代文学史,笔者认为这是苏轼的一种文学创新。不仅“隐括”手法由来已久,而且隐括词在苏轼之前或同时代即已有之,如刘几(1008--1088)和晏几道(1038--1112)亦进行了隐括词的创作。这说明《哨遍》不是苏轼突发奇想的妄为之作,而是一种在新语境下的文体尝试。不妨先来看看晏、刘二人之作。晏几道《临江仙》词上阙云:
东野亡来无丽句,于君去后少交亲。追思往事好沾巾。白头王建在,犹见咏诗人。[5](P223)
晏氏虽然没有说明自己这首词是否为隐括之作,但熟悉的读者不难看出其明显是对唐诗人张籍《赠王建》诗的改写。于此,对比张诗原作就很容易明白。张诗云:“自君去后交游少,东野亡来箧笥贫。赖有白头王建在,眼前犹见咏诗人。”两篇作品一比较,其“亲缘关系”十分明显。
同样,刘几《梅花曲》也是这样,虽亦不明说隐括,但确实是改写之作。其词曰:
汉宫中侍女,娇额半涂黄,盈盈粉色凌时,寒玉体、先透薄妆。好借月魂来,娉婷画烛旁。惟恐随、阳春好梦去,所思飞扬。宜向风亭把盏,酬孤艳,醉永夕何妨。雪径蕊、真凝密,降回舆、认暗香。不为藉我作和羹,肯放结子花狂。向上林,留此占年芳。[5](P187-188)
刘几《梅花曲》乃改写王安石《与微之同赋梅花得香字三首》(其一)而来的。王诗云:
汉宫娇额半涂黄,粉色凌寒透薄妆。好借月魂来映烛,恐随春梦去飞扬。风亭把盏酬孤艳,雪径回舆认暗香。不为调羹应结子,直须留此占年芳。
对比王安石原作,即可发现问题,即刘作乃隐括王诗而来。如此而论,晏、刘二氏这两首词作,即便不能算严格的隐括词,起码可以说,他们采用了隐括手法作词。
据宋史可知,晏几道比苏轼略微小几岁,而刘几比苏轼年长二十几岁,但也大致算是同时代人。刘几卒于元祐三年(1088),晏几道约卒于政和二年(1112),而苏轼《哨遍》一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就生存时间跨度上来说,晏、刘二氏都有在元丰五年之后创作隐括词的可能。倘使晏、刘二人之作是在苏轼创作《哨遍》(为米折腰)之前,晏、刘二人也可能只是尝试着采用隐括修辞,而并没有清楚意识到他们是在运用一种新的体式创作词。换言之,当时晏、刘二人没有所谓的“隐括词”体之概念。
笔者认为,宋代隐括词创作兴盛亦与晏、刘二氏没有多少关系。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本文更愿将晏、刘二人之作置于苏轼创作《哨遍》之后。这样并不是为了方便对隐括词文体特征的讨论,而是从隐括词这种新兴文体生成的可能性上涉及传媒因素考虑的。此问题将在本文第三部分予以讨论。
二、“隐括”的文体特征
隐括词,是一种形成于北宋的特殊文体。从隐括对象之创作者来看,隐括体可以分作三类:隐括前人作品、隐括同时代人作品和隐括自己的作品。前二者例子自不待言,对于隐括自己作品,苏轼《定风波》(咏红梅)就是隐括自己的《红梅》诗。总体而言,隐括前人作品者居多,隐括同时代作品在南宋较为多见,而隐括自己作品,只有苏轼一例。从隐括对象之文体言,隐括词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隐括单篇散体之文, 另一类是隐括前人诗词语句之作。前类如苏轼的《哨遍》(为米折腰)隐括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黄庭坚《瑞鹤仙》(环滁皆山)隐括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后一类例子随处皆是,不必例举。就此我们来归纳隐括词的几个主要文体特征。
(一)隐括必须有隐括对象,并且其对象必须为名家名篇
不管隐括何人何作,必须有一个隐括对象。隐括作品往往须结合所隐括原作才便于阅读。职此之故,隐括对象通常都是名家名篇,即所谓的“经典”。以苏轼为例,其全部的11 首隐括之作,8 首是隐括前人,分别是隐括陶渊明、白居易、张志和、韦应物、韩愈等,另有2 首隐括同时代人作品以及1 首隐括自己的作品。依次来看,苏轼所隐括作家作品都是当时评价很高或者在苏轼心目中地位很高的作家作品。至于其隐括自己之作即《红梅咏》,必定是他的得意之作。
苏轼之后,宋代诸人所隐括之对象,基本符合名家名篇的定性。这一点很类似今之图书、影像之盗版,其盗版对象均为社会上流行的或知名度很高的作品。典型代表就是南宋林必正,他的《风雅遗音》可谓集隐括体之大成。林氏一生竟创作了41 首词且全部为隐括体,如《酹江月》《满江红》隐括杜甫《醉时歌》,《一丛花》隐括杜甫《饮中八仙歌》,《贺新郎》隐括王羲之《兰亭序》,《酹江月》隐括陶渊明《归去来辞》,《江神子》隐括黄庭坚《题杜子美浣花醉归图》,《沁园春》隐括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临江仙》隐括李白《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酹江月》隐括李白《清平调辞》组诗等。此中,林氏所隐括者绝大部分是名家名篇。即便是有些我们今天看来不是名篇者,可以肯定它们在当时或至少在林必正看来是很知名的作品。
(二)隐括通常是隐括通篇,且必须对原作进行改写
隐括在形式上就是一种浓缩,因为通常情况下,隐括之文总比被隐括之文要简短些(特例除外,如刘几《梅花曲》)。隐括,一般是对单篇概括,少数情况下也有隐括数篇作品。但无论哪种情况,隐括都必须有文辞的剪裁、概括,不能是简单的词句的剪贴。苏轼之隐括词作即如此。事实上,苏轼共有11 首隐括之作均为隐括全篇者。
隐括通常是将原有的诗词文剪裁、改写为词,故隐括体主要就是指隐括词(实际上也有隐括诗)。据王伟勇先生统计,宋代共有136 首隐括词。[6]不过,内山精也先生不认同王伟勇先生所统计的这种广泛意义上的隐括体,他所定义的隐括体是狭义的,“局限于由前人的全篇内容改编而成的词作。”[7](P409)从文体严格定义这一点讲,本文比较倾向于内山精也先生的说法。因为如果仅是隐括前人成句之作,则可以看作是“集句”或者“集字”,甚至仅看作修辞——隐括。如王安石创作《菩萨蛮》:“数家茅屋闲临水,单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予度石桥。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5](P205)词句就分别取自刘禹锡《送曹璩归越中旧隐》、韩愈《南溪始泛》等唐诗。严格意义上讲,这不算是隐括体,而只是采用了隐括手法。
(三)隐括之作必须有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吴承学先生在《论宋代隐括词》中将唐代同谷子的《五子之歌》判定为隐括体的雏形:“我们不难看出,同谷子的《五子之歌》,完全是根据《尚书·五子之歌》一篇作品改编而成的,借改编古人诗歌,来寄托自己的悲愤,并以之讽刺当代的政治,其性质不是集句体,而是近于隐括体。”[8]这里有几个关键词:改变、寄托,表示隐括体必须具备的几个特征,即必须是对原作改写、剪裁,新文本要有作者自己的思想内容或者说情感。如清代江永《礼书纲目序》中说:“尊经之意当以朱子为宗,排纂之法当以黄氏丧礼为式,窃不自揆为之增损隐括,以成此编。”[9]江氏这里使用“隐括”一词时,就暗示了“隐括”是一种带有自己个性色彩的改写,而不是集句,也不是摘抄。
隐括词并非源于唐五代以来的“帖括”。帖括只是摘抄、概括,备于考试,方便记忆,一般是不会也不能带上自己的思想情感的,而隐括则可以。
(四)隐括之作必须协律
从文体生成方式上来看,隐括体要求“以诗度曲”和“以文度曲”,这自与其生成于“以诗度曲”风尚的宋代语境有关。因此隐括词必须协律。如苏轼《哨遍》之《序》:“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既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钺)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又《水调歌头》隐括韩愈《听颖师琴诗》之《序》:“欧阳文忠公曾问余:‘琴诗何者最善?’答以退之听颖师琴诗最善。公曰:‘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5](p280)显然,此中东坡隐括之作是必须就律的。此中,分别说到“度曲”“使就声律”,即是说,隐括之体跟音律密切相关。所以,隐括之体主要形态也就是隐括词,隐括体与隐括词基本是一个概念。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隐括体并不强调其隐括对象的体裁形式,只要作者能将原文改编得符合声律以适于演唱则可。所以,到了南宋后期,隐括体其所隐括对象已经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范围,上至楚辞,下至题画诗,甚至民间曲词如竹枝词之类,无不可施。至此,隐括,不仅成为一种成熟的体裁,甚至成为一种好用的创作方法。
三、隐括体生成中的传媒因素
人们对于隐括体的生成,从多角度追究过它的原因。吴承学先生在《论宋代隐括词》中总结了几个原因:一是唐以来“帖括”文体的影响;二是宋代文人对前人作品的极度欣赏爱好驱动;三是宋人对文体试验的偏好;四是配乐演唱的娱乐需要。吴先生归纳的几点是有道理的,也都是有据可依的,本文也从中获益匪浅。不过,本文觉得似还有某些原因没有说到,还有令人困惑的地方。比如,“帖括”之文产生时间最晚也在中唐,如若隐括体真源自它,那么为什么隐括体直到北宋中期才产生?这似乎不符合文学发展规律。为什么隐括体在苏轼以后突然普遍起来?吴先生在其文中一直没有确切地追究。笔者认为,这些都与传媒因素有关。迄今为止,似还没有学者从传媒因素的角度追问过隐括体在宋代的形成和繁荣。
对于传媒因素对宋代文学的影响,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正是日本学者内山精也先生,他的专著《真相与传媒——苏轼及其周围的士大夫文学》几乎贯穿了这样一条思想主线。他的《苏轼文学与传播媒介》和《苏轼次韵考》等篇对本文具有重大启发。如他在《苏轼次韵考》说:“苏轼生前有数种诗文集经由他人之手编纂刊行,这个可以从苏轼自己的书简及当时的文献得到确认。这些事实喻示着以印刷术普及这个社会现象为背景,苏轼大概能“现实”地切身感受到自己的文学作品的社会反响(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或者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把苏轼看作是最早活用传播媒介的人)。”[7](p375)内山先生这段话具有重大启示意义,第一个注意到苏轼对于传播媒介的有意识关注,这在内山先生《东坡乌台诗案考》一文中也论述了很多。[7](p173-271)惟一遗憾的是,内山先生在《东坡隐括词考》一文却没有从这点进行深究。这恰恰成为本文思考的起点。
苏轼创作隐括体,是在清楚意识到传媒因素的情况下有意识地进行新文体试验。站在今天回顾苏轼一生创作,发现其与传媒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内山精也先生所说,“乌台诗案”可谓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宗文字狱,正是传媒的力量促成了苏轼“乌台诗案”的爆发和升级。(《东坡乌台诗案考》)这场几乎令其丧命的诗案,给苏轼带来无尽的思索。也许在思索过程中,苏轼悟到了自己这次惨祸,不在于自己的诗歌内容本身,而在于新传媒作用下诗作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影响。这样的领悟结果,自然会影响到苏轼今后的所有创作。
“乌台诗案”发生在元丰二年(1079)八月。据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可知,苏轼的《哨遍》隐括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五月,且苏轼对于陶渊明诗文所作其它的和作,最早的也是在元丰四年(1081)九月。也就是说,苏轼对于陶渊明的重新认识,是在“乌台诗案”之后,而其隐括体的创作也是在诗案之后。个中原因,无疑与传媒有关。
第一,苏轼欲借词体这种当时流传最快的文体以传达思想和志趣。词起源于中唐,发展于晚唐五代,兴盛于北宋。苏轼正是生活于词创作较为普及的时代。所谓“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反映的正是“词”这种文体的普及性和广泛性。“词”作为一种新兴传播媒介,深深影响宋代人们的生活,也影响到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甚至生存。我们知道,柳永在相当时期内就是依靠替歌楼撰写歌词为生。尽管苏轼不至于依赖词创作而生活,但不可否认他意识到了词的传播功能。如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所记载: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比栁耆卿何如?”对曰:“栁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郎,按执红牙拍,歌:杨栁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10](卷二十四)
很明显,苏轼非常在意自己的词和当时最为流行的柳永词在大众心目中的位置之比较。尽管诗话言“公为之绝倒”,事实上苏轼当时应该是感到很遗憾的,因为他发觉自己的词不如柳词受大众欢迎。有一事例可以佐证苏轼非常在乎自己词作的传播状况。《词苑丛谈》卷三记载:
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希学柳七。”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11](p51)
表面上,苏轼对秦观的责问是因为秦氏创作学柳永以至于变得低俗,这似乎是堂而皇之的教训。事实上,在严正的教训之辞后面,隐含着苏轼的担忧,即对柳词社会传播影响力盖过自己,以至于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都去学习它,而由此感到不安。这再一次证明,苏轼对于传播因素对创作的作用力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苏轼一生创造多种诗词文体式,都是在充分预设了传媒因素的影响而完成的,并不仅仅是文字游戏。如苏轼曾经创作所谓的“尖叉诗”,并且与王安石反复次韵这些“尖叉诗”。这些“尖叉诗”在文学上到底有多少意义不必追究,但值得注意的是,苏、王反复次韵的整个过程,却充分显示传媒因素在其中起到的重大作用。可以断定,苏、王二人在次韵诗歌时,不仅预设了对方作为读者存在,同时还预设了社会普通读者的存在。因为苏、王二人的诗歌在看似谦逊语言掩护下角心斗智,其目的无非是想让社会读者对自己才智的认同或赞赏。可以试想,如果没有北宋中期传播媒介的发达这一背景,可以肯定苏、王这次诗才斗法是不会也无法进行的。此外,在苏轼的许多诗文中,都出现所谓的“公自注”的字眼,担心别人读不懂或者误读其作,特作说明。这也是证明苏轼创作时存在读者预设的有力证据。
第二,苏轼时代传播媒介之发达为隐括体生成提供可能条件。传播媒介的发达直接扩大了传播范围,也即扩大了审美接受主体,必然带来巨大的传播效应。正如张高评先生所说:“知识得传播媒介,从写本转为印本,不仅书籍制作速度加快,书籍复本流通数量增多,而且对知识信息之传播交流,图书文献之保存积累,皆有革命性之成长。”[12]基于传播的巨大影响,御史何正臣在弹劾苏轼的劄子中写道:“(苏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取镂板而鬻于市者进呈。”所以内山精也先生在《苏轼文学与传播媒介》中断言:“最晚到了北宋中叶即仁宗末期,士大夫在获得过去的多种多样的信息资料时,印刷媒体已经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媒体之一。”[7](p276)这个判断大抵是准确的。
我们应该注意到,苏轼生活的时代,发明于唐代的雕版印刷已经相当成熟,达到了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如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描述道:“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13](p359)这种情形,从宋人大量印制自己的文集这一文化现象亦可印证。自北宋中期以来,几乎所有宋史有传的士大夫都编辑或刊发过自己的作品集子,并且还出现动则上万卷的藏书之家,甚至少年贫寒无书阅读的欧阳修在为官后数年间就能藏书过万卷。这些都足以证明北宋中期印刷媒体的发达。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活字印刷技术出现在这个时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是北宋的毕昇,据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记载:毕昇活字印刷发明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尽管其生年不详,但我们知道毕昇大约卒于皇祐三年(1051),即便毕昇在晚年发明活字印刷术,到苏轼创作《哨遍》的元丰五年,也已经是三四十年以后的事了。虽然没有多少文献记载北宋中期以后到底多大范围内使用了活字印刷来印制诗词文赋等作品,但其被人们关注是肯定的。如此即可断言,苏轼对其作品在社会传播的预设,肯定存在于其创作之前,而“乌台诗案”之祸,无疑加深了他这种意识。所以,苏轼对于词这种无论是在口头还是书面传播速度都极快的载体,重视程度必非同一般。
第三,苏轼“雅”的文学审美观的一种尝试和选择。
从词的创作风格看来,苏轼与晏殊及其老师欧阳修作绮艳词不一样,他不大欣赏温庭筠、韦庄以来晚唐词的恻艳风格,更不欣赏柳永一派走世俗化之路。如对柳永《望远行》上阙中隐括郑谷的《雪中偶题》“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之句,苏轼表示很不满,认为格调太低。苏轼总是试图寻求一种追求格调高雅的雅化之路,事实上他也基本做到了。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一中说:“词至东坡,一洗香罗绮泽之态,寄慨无端,别有天地。”[15](p12)然这种雅化,不能仅仅以诗歌和散文来完成。在词作影响遍天下的现实面前,苏轼意识到还必须借助词这种文体,并在改革这种文体形式过程中贯穿自己“雅化”理想。
考察苏轼词作发现,苏轼通过词走“雅化”之路有两个手段:一是提升词体题材内容,使之与诗文靠近;二是创新写作手法,不再遵循婉约凄恻之调。二者结合之最佳产品,恰是“隐括词”。正如学者孙虹说:“厘清宋词雅化的轨迹,隐括修辞是一个很好的分析视角。”[16]从苏轼《哨遍》来看,内容乃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在“崇陶”氛围浓厚的宋代,陶氏诗文无疑是高雅的代名词。在方法上,苏轼则采用了隐括这一写作手法,在忠实原作的基础上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感。最后苏轼创作出了既满足流俗文化需要,又寄托自己高雅理想和文学思想的作品。
不管后世褒贬如何,苏轼这种作法在宋代得到了极大的认同,并形成一种风尚,由此成就了一种新的文体即隐括词。苏轼以后特别是南宋中后期,隐括之作比比皆是,甚至出现专业化作家。这些,正契合了苏轼对此所作的预设。
如上文已述,在苏轼及其他词人所创作隐括词当中,有一条规律产生即隐括对象必是名家名篇。表面看来,这似乎只是受苏轼隐括陶氏作品的影响而走上“雅化”之路。事实上,在“雅化”因素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促成,那就是传播力量的影响。因为隐括名家名篇有两个好处:一是提高自己作品的知名度;二是隐括作品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不仅能够使读者感到亲切,而且扩大阅读面,增加读者群,从而增加作品的社会影响力。
自苏轼以来,人们创作时头脑中普遍有一个读者预设,即今天所谓的“隐含读者”的存在。隐括名家名篇对于一个已经成名的作家来说,固然不是绝对需要,却也决不是坏事,但对于一个不太知名的词人来说,则显得至关重要了。这从南宋的曹冠、林必正、刘学箕等人的隐括作品目录可以得到明证。
四、结语
王兆鹏说:“一种作品如果改编得成功,肯定会引起读者对原作的关注,促进原作的传播。即便是改编得不成功,它也是一种传播与接受的行为和方式,也有其特殊的功能和意义。”王先生这里正是指隐括体而言,然而他只是注意到了对原作的影响,而忽略作者改编目的和改编之作本身。作家改编名篇名著,更大目标是使自己很快被读者接受,得到社会承认,对于初出茅庐的无名作家尤其如此。至于内山精也和吴承学两先生所说的,隐括词的动机在于交际功能、文字游戏和文体试验,本文在一定范围内认同其理由,但本文更强调传媒因素作用下的读者预设,故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