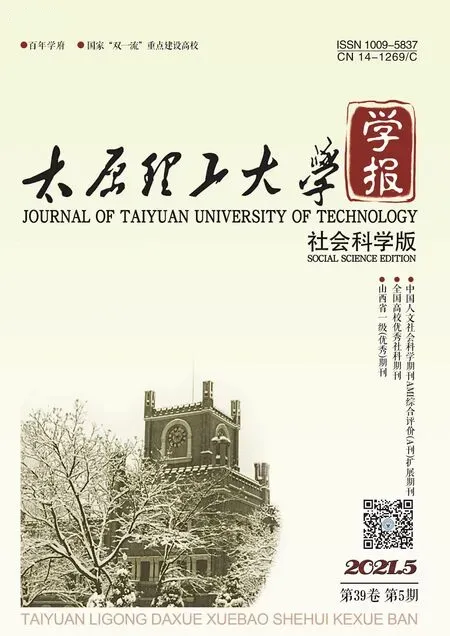“变局中的趋新”:近代士绅国家观念变迁原因探析
——以《退想斋日记》为考察中心
黄 超
(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一、引言
士绅,是传统中国社会中,职掌基层政权的重要组成力量。他们大多数属于已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的乡野籍士人或告老还乡、致仕返乡的政府官员。根据张仲礼的解释,他们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1]。“功名”“学品”等荣誉头衔在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传统中国社会,是政治特权与经济特权结合的集中体现。作为“官”与“民”的沟通中介——士绅阶层,正因为有了“功名”“学品”等的依托,这一群体上可“通达天听,承接差役”,下可“传道孔孟,和睦乡里”。因此,在“万事胚胎、皆在州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中,士绅及其为代表的“绅权”,就成为延伸传统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即使在明清两代,虽然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在以朱元璋、爱新觉罗·胤禛等为代表的明清帝王改造下,已达历史顶峰,然而“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只达县一级”[2]的社会现实,却又迫使明清两代统治者不得不依靠士绅进行管理统治,从而使其在以乡野为代表的广大基层地区形成与正统权力系统既密切相关,又相对独立的“士绅社会”。
近世以降,随着西方势力的漂洋东移,传统中国社会在艰难迈向近代的同时,自身又发生了由表及里的全面蜕变。特别是自甲午中日战争后,随着中国内忧外患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国人逐渐意识到必须打破原有“天下观”的束缚重塑“中华观”(1)关于“中华观”的最早诠释,当属梁启超的“凡遇一他族而立刻又‘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斯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的提法(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四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1-2)。,如此才能最广泛地团结民众,最终赢得国家独立,实现国家的近代化转型。对此,黄兴涛认为,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已不再拥有朝贡体制意义上的藩属国,作为国名的“中国”或“中华”,即便对亚洲而言,也基本失去了华夷观念的歧视含义,而主要成为一个延续性的、单纯的现代国家称谓而已[3]。尽管这一近代国家观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最终成为广大国人的普遍共识,但仍不可否认,它在形成过程中对推动国人的民族意识及国家观念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这一点在处于社会中间阶层的士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以往学界在研究清末民初的士绅阶层时,多将研究的目光聚焦到科举废除与士绅阶层“劣质化”的关系上,旨在阐述在科举废除的时代背景下,士绅阶层因科举仕途受阻,自身与传统社会联系大为削弱,逐渐沦为危害乡里一方的土豪劣绅(2)参见罗晓华所作《科举制废除后的乡村士绅》(《中州学刊》2004年第2期)、罗志田所作《科举制度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杨念群所作《废科举与中国式“代议”现象的消失——科举废止百年后的省思》(《社会科学文摘》2017年第4期)等。。诚然,此类研究将科举废除的时代变动背景与士绅阶层变化紧密结合,具有极强的学理价值,但若将研究的点过多放在“落”而忽视“起”,则未免有一叶障目之嫌。事实上,正如陈旭麓所言,作为“中等社会”的典型代表——士绅阶层,虽然他们身上仍存在着较多的旧时烙印,但他们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起着“破坏上等社会”与“提携下等社会”的双重责任[4]。以辛亥革命为例,根据李国环研究可以得出:正是由于晚清废除了科举制度,才导致一大批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从士绅阶层中脱颖而出。他们在辛亥革命前的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致力新式教育文化事业、创办近代企业、倡导立宪及地方自治,为自己谋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并成为左右清末政局的重要力量[5]。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6]。清末民初的士绅阶层运动,虽是以争商权、开立宪、兴西学等诸多历史事件作为承接载体,但其背后的思潮确是广大士绅突破了“家天下”视野下的臣民观,初步具有了“公天下”的国民观,而这一现象背后也孕育着对近代国家建构的认知因素。因此,系统分析这一变化背后的原因,就成为了解这一群体在“变局”中发挥作用的历史依据。
二、“变局”中的个体世界——刘大鹏情况简述
刘大鹏作为士绅阶层的典型代表,他出生于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卒于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享年八十六岁[7]。纵观其一生,他自幼读学于乡间私塾,受的是传统中国儒家教育,膺服的是“伦理者,维持天下万世之大纲也”[7]为代表的儒家纲常思想,口中诵读的也是“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7]的程朱理学。由此可见,在青年之时,刘大鹏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较深,且具有极强“天下观”认识的帝制臣民。
然而,时代的变化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刘大鹏中举为分水岭,自此以后他的思想随时代的发展逐渐发生了变化。中举,对于科举制度的读书人而言,意味着有进京参加会试的资格,而进京赶考,无疑会扩大刘大鹏的接触面,并使他获得较多的信息,从而为其思想的改变创造外在条件。刘大鹏进京参加会试,时值中日甲午战争的收尾阶段。面对着中国“和议已成,莫能挽回”[7]的悲惨境遇,刘大鹏第一次在日记里表达出了“和则输倭两万万金,且割台湾一岛畀日本,闻之者莫不扼腕愤恨”[7]的民族主义思想。此后,刘大鹏虽然屡试未果,被迫退隐乡间,以开馆教徒为业,但他仍然关心时政,多对一些祸国殃民的事情给予抨击,并笔耕不辍地撰写下了《重修孙家沟幻迹》《柳子峪志》等论著。民元鼎革之际,经地方推荐,刘大鹏相继担任了所在县议会议长、县教育会的副会长、县财政公所经理、公款局经理、县商会特别会董、县保存古物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担任这些职务时,刘大鹏公心处事、施政于民,革除了一些弊政陋习,故而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可。此时他的思想上虽仍不免对革命党有所偏见,直斥其为“乱臣贼子”,并存有“辛亥大变以来,伦常全行破坏,风气亦更奢靡,礼义廉耻望谁讲究”[7]等旧时代印记,但其在主流思想上已逐渐认同了民元鼎革所造成的历史现实,并具有了“蚩蚩之氓,安知中国大局危险以(已)极,不啻燕雀之处堂乎”[7]的近代国家观念。这种情况,即使在日据山西统治时期,也未能有所改变。虽然刘大鹏因自保等缘故,不得不出任伪职,但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暴行,刘大鹏多次在日记里予以记录,并表达出了“恨日军不败,盼红军攻击日军,将日军全部打死”[7]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怀。通过刘大鹏的上述举动可以看出,作为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人物,此时的刘大鹏已不再是对“天下”传统国家观信仰的臣民,而是初步具有“中华”近代国家观认同的国民。因此,正如行龙所言,刘大鹏的一生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痕,既反映了绅士阶层变迁的普遍特征,又突出了内地乡绅鲜明的个人色彩[8]。
三、“个体看群体”——近代士绅国家观念变迁的原因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对于士绅阶层而言,刘大鹏虽是士绅阶层中的个体,但个体思想变化背后必然是群体思想变化的真实体现,而导致群体思想变化的根本在于其所处时代社会关系的变化。梳理刘大鹏“惟籍吟咏以泻一时之感慨”[7]所遗留下来的代表作——《退想斋日记》,可看出造成以刘大鹏为代表的士绅阶层近代国家观念变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华夷易位”:民族矛盾加深是近代士绅国家观念变迁的外在原因
秦汉以降,中国在结束了自平王东迁后长达数百年的分裂混乱局面后,第一次实现了由君权主导下的实质统一,迎来了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大一统帝国”时代。在确立了“大一统”理念的同时,也奠定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观”国家基础。在这个观念下,原本处于中原内地的王朝被视为“正统”,而处于中原王朝以外的部族则被视为“四夷”(3)四夷,即为东夷、南蛮、北狄、西戎(详见〔汉〕戴圣.礼记·孝经[M].胡平生,陈美兰,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105—106)。。双方之间的关系是以宗藩关系为基础的朝贡体系,即“四夷”部族对“正统”王朝提供贡品以示效忠,“正统”王朝对“四夷”部族首领进行册封、厚赏以示认同。通过构建朝贡体系,中国确立了“华夷有别”的外交秩序。此后数千年间,虽然中原王朝鼎革不断、易主频繁,但朝贡体系及其所构建的“华夷有别”的外交秩序却并未受到较大冲击;相反,经过这一体系,中国在维护自身稳定、不断开拓疆域的同时,自身文化也传播到了中国的邻近和周边国家。伴随着这一进程,东亚地区最终形成了儒家文化圈[10]。
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昔日自诩“天朝上国”的大清王朝,在被“轰出中世纪”的同时,自身则遭到了日趋衰落的命运。与此同步的,还有象征其“天朝上国”地位的“华夷有别”外交秩序。面对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及“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11]所带来“华夷易主”的震撼,居于乡野的士绅群体,虽然没有抛弃对“天下观”的信仰,但还是在时代的变迁中加深了对“中华观”的认同,而这转型背后是以一些“华夷冲突”事件为直观感受基础。《退想斋日记》如实地记录了以下事件。
“华夷通商,是天下一大变局,论者归咎于执事,而不必也。夫天下大变,原属天意使然,岂人力所能维持。自通商以来,寇屡犯边疆,中华被害,岂偶然哉?”[7]
“闻太谷城于前二日,洋人埋葬去年被诛之洋夷,所葬之地,乃孟氏之花园,恃势霸占,官且听洋夷之指使,小民何敢抗其霸占田地房。”[7]
“现在法夷蚕食云南广西,英夷蚕食广东福建,日本蚕食闽浙,德夷蚕食山东,俄夷蚕食新疆蒙古,其为中国之患者俄夷为最,以其地与中国毗连耳。俄人不但霸占东三省,一二年中必有并吞中外蒙古并新疆之势,中国若仍偷安,不思自胜之策,徒取西法以求自强,恐岌岌乎不可支持也。尚望当道及早计之。”[7]
“华夷易位”的背后,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综合国力远逊于西方诸国。面对“华夷易位”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动荡,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加深了对被曾视为“蛮夷”的西方列强的痛恨;另一方面也迫使其在“华夷易位”的既定事实下,“开眼看世界”“寻道救中国”。通过刘大鹏的记述可以看出,“洋人”“洋夷”并用,折射出了以刘大鹏为代表的士绅阶层内心依旧残存着的“华夷之辨”思想,但面对“夷”的步步紧逼,以刘大鹏为代表的士绅阶层并非一味地抱残守旧、故步自封,而是在时代的变迁中,萌生了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产生了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想法,并转而催生了以“中华观”为代表的近代国家观念,而这在以视“天下”为“一家之产”的帝制时代是根本不容许的。
(二)“内政不修”:政局持久动荡是近代士绅国家观念变迁的内在原因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百年来的中国革命运动做了精辟概述,并指出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12]。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是近世中国饱受较长时间磨难的重要原因之一。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正逢晚清的嘉道“衰世”,罗威廉就此评价,“除了长期人口压力和失业的担忧之外,还有与朝代衰落相关且众所周知的问题,就是皇帝意志力和监督的失败、官僚的道德及进取心的丧失,以及腐败和乱政”[13]。而鸦片战争后,随着由西方列强主导下的一批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在担负日益沉重的战争赔款的同时,也被迫丧失了司法权、经济权等诸多权利,加之之前未解决的诸多问题,致使整个国家长期处于政局动荡,这一情况即使在民国时期,也未能得到根本的好转。政局动荡,催生出社会的畸形事物,致使匪患、民变、教案成为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对此,《退想斋日记》进行了如实的记述。
“太原一郡之州县官无他政之可办,惟是办理教案,听教民之指挥而已。当此之时,差役四出,恫吓乡民,乡民恐惧,贿役求免,而役遂出无厌之求,闾巷何以能安乎?”[7]
“自变法以来,各行省民变之案接踵而起,又且寇贼纷纷此扑彼动,则是所变之法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然犹执迷不悟,竭力西法而不遗余力,世道之坏伊于胡底哉!”[7]
“杜鹤峰、杨秀三于昨晚来馆,言归化城之乱非由洋教,乃由开垦官逼民乱耳,官军征之,反败于乱民,一切军械及士卒被乱民抢胁者甚多,此其大略也,其详不可得闻也。”[7]
“云南不但有兵争,而且匪祸甚惨,抢掠焚烧无地不然。又加之时疫分为数症:一曰霍乱,一曰白喉,一曰猩红热,一曰红痰;凡此数症一染即死,人民死亡枕籍。春夏之际,唐继尧又入滇与顾品珍开战,伤亡无数。……”[7]
匪患、民变、教案背后的形成因素,既和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积弊有关,又与西方势力的插手介入密不可分。两者虽在引起个别事件所占的比例不尽相同,但都给当时的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以致刘大鹏每每记录此事时,常有“百姓困苦已极”[7]的悲悯,并常怀“迄今仍然,何能望世之治安”[7]的感叹。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素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随着时局动荡的不断加深,传统知识分子为拯救“斯民于水火”,扶正“大厦于将倾”,自身所蕴藏的家国情怀在时代的激荡中不断得以升华。通过刘大鹏的记述可以看出,以刘大鹏为代表的士绅阶层在面对近世中国社会的政局动荡时,自身所蕴含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被极大激发出来,在渴求“望世之治安”的同时,也逐渐在时代的冲击下摆脱了“一家之治”的束缚,形成了“中华观”的近代国家观念。
(三) “变通之道”:履职新政权经历是近代士绅国家观念变迁的时代原因
近世中国,相较于古世中国,不是在其内在发展道路上的循序承接,而是在外力的刺激下的激进跨越。正因如此,中国近世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各种新旧事物、新旧思想杂糅的时代。鲁迅曾对此有精辟的描述,直言近世中国“简直是将几个世纪缩在一时:自松油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枪……都摩肩挨背地存在”。对于广大士绅阶层而言,虽然满腹经纶的才学尚在,但科举制度的废除彻底终结了其“布衣卿相”的梦想。面对现实,固然有部分士绅阶层就此沉沦,但也要看到,大多数的士绅还是转变了其职业模式,并尽量使自己更好适应所处的时代。大到“实业巨子”张謇,小到“乡间夫子”刘大鹏,无一不是士绅阶层发生择业改变的典型事例。对比众所周知的通跨“政商”两界的张謇,刘大鹏的“转变”则具有更为明显的新、旧时代交织的印记。
民元鼎革之际,由于声望在外、能力出众,加之又有当地民众“阖邑之人望予甚深”[7]的期许,经过所在地方举荐,刘大鹏被推举为所在县的县议长,并先后担任了包括县商会特别会董等在内的多种职务。在刚开始担任这些职务时,刘大鹏常以“清代遗民”的身份自居,对革命党抱有很深的偏见,并在其《退想斋日记》中将其所举革命称之为“变乱”。然而随着接触的增多,尽管在认识态度上刘大鹏仍不免有强烈偏见,但在具体施政行动上刘大鹏已逐渐适应了“变局”时代社会的某些需要。在任职期间,刘大鹏恪守“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7]的处事原则,一心为公、任劳任怨,不仅将“电灯”等新鲜事物引进了所在县域,还利用手中职权为民众作许多好事,尤其在维持所在县域商贸稳定上,刘大鹏的贡献尤为突出。
“晋祠堡西之旧路,多年闭塞不通,由於镇人无桑梓之观念,虑不及斯,故不谋重行开辟,宣统三年变乱之日,堡中为通衢,已受往来逃兵之扰累,予即提倡开辟此路,以便南北往来之行人,而镇人置若罔闻,予甚悯之。上年(公元1915年)秋,阖邑商人公举予充商会特别会会事务,迨至腊月,雁门关北贼匪扰乱,警耗日至,予与开路修堡之事,仍然漠不关心,乃于晋祠商界言之,无一人不赞成,因请县长李桐轩提倡监督,亦概然应允。”[7]
“商会会董三、四人主持,撤销本城各号无商会戳记之凭帖,限至四月初一日不容周行,是去日所议者,商人敢怒而不敢言抗,只是说,必起拥挤倒闭之风潮,阖城哄然,予乃禀知县长重开议,将出帖之家招集商会共四十余人,乃议递减之法,以十日为一期,每期撤销十分之一,予倡此议,而众皆赞成,一日始毕,县长又派代表一人监督议场,其议遂定。”[7]
从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中国逐渐从“君主专制”走向了“民主共和”。尤其是辛亥革命后,更是“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14]。而“民主共和”的深入人心,则加速了广大国人以“中华观”为代表的近代国家观念形成。身处期间的士绅阶层,尽管自身存在着难以割舍的旧时代印记,但“变局”新时代的浪潮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以刘大鹏为例,通过刘大鹏的记述可以看出,虽然在他的字里行间中依旧可见对清朝的眷恋(如使用“宣统”纪年号),对辛亥革命的憎恶(如称辛亥革命为“变乱”),但在实际的施政行动上,刘大鹏却懂得利用近代的“民主协商”而非传统“专制强权”的方式处理所面对的问题,其背后实则体现出了“主权在民”“天下为公”的近代民主精神,而这无疑也有利于其“中华观”近代国家观的形成。
四、结语
刘大鹏是近代中国历史演进中的“小人物”,但通过梳理其遗著《退想斋日记》,不难得出:即使是时代中的“小人物”,其自身也有关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深远思考,并具有自身的“中华观”近代国家意识。对此,俞祖华关于历史个体中的人物研究曾有过以下精辟论述。社会转型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一种张力、一种拉锯, 这种张力与拉锯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上体现为新旧交替、新旧杂存、新陈代谢的状况, 而在历史人物的心灵世界则体现为趋时与怀旧、向往西方与回归传统的交战[15]。同样的道理,历史研究者在研究近代人物国家观念形成的课题时,除需研究当时代表人物的思想观念,还应有眼光向下的考量。即将研究视角深入到基层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上与下”的有机结合,从而擘画出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无疑为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来自民间的宝贵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