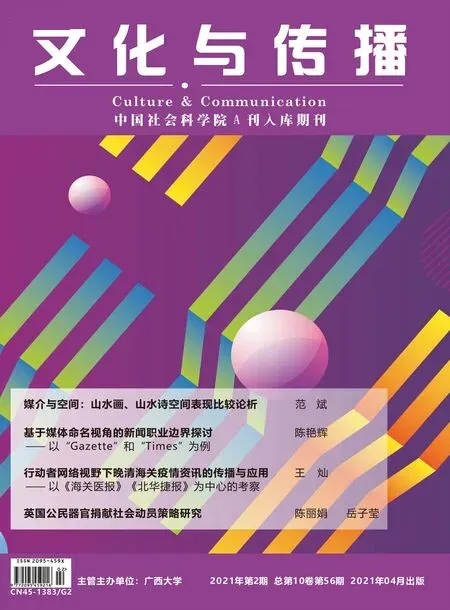圈层破壁、抵抗弱化、走向中心:“粉丝”亚文化主流化转向研究
王伊如
一、引言
“粉丝”一词由英文“fans”音译而来,按照费斯克的界定,粉丝就是“过度的读者”,他们“有规律地、情绪性地投入一个叙事或文本”[1]。詹金斯则指出,仅仅“迷恋、仰慕或崇拜”还不足以指明粉丝的特征,粉丝是主动的消费者,是到处挪用、拼接材料来建构自己文化的游猎式的文本盗猎者,是有勇气争夺文化权力的斗士[2]。传统观念里,粉丝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的典型代表,常常是游离在主流文化之外、对于现实社会持有冲突和对抗姿态的反叛力量,具有边缘性、批判性、反抗性的特质[3]。然而近些年来,在倡导文化趣味多元化的互联网社会中,我们发现粉丝亚文化“亚”的特性不再鲜明。一方面,粉丝群体的抵抗性有所弱化,表现出对主流话语体系的积极拥抱姿态;另一方面,从“为国出征”到“参与扶贫”,从“反对歧视”到“维护平权”,青年粉丝群体主动介入主流社会与公共生活,实现了从边缘到中心位置的进击。本文以粉丝亚文化的这一“主流化”转变为基础,探究其转型背后的动因,以期以更宏观的视角看待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与重塑。
二、轨迹梳理:亚文化与粉丝文化研究
学界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芝加哥城市学派运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城市青年的“越轨”行为进行研究,剖析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为后续亚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战后,以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等为代表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学者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从更深的政治语境中去探索青年亚文化的符号表意,特别是‘仪式抵抗’所蕴含的政治实践意义”[4]。伯明翰学派认为,青年通过风格化与另类符号对统治话语体系进行抵抗,而“支配文化和利益集团则对此进行不懈的遏制与收编”[5]。
8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理论话语的盛行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青年亚文化显现出复杂、多变等诸多新的文化症候。以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所谓的“后亚文化理论”,呼吁打破伯明翰学派的二元对立视角和阶级色彩[6],关注年轻人碎片化、个人化的文化身份建构及其意义价值[7]。在后亚文化研究的视野下,青年亚文化群体无意通过鲜明的风格对抗主流文化,其本身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短暂性、流动性、多样性、虚拟性等后现代特征。
粉丝文化是青年亚文化的典型形态,其研究路径也遵循着亚文化到后亚文化的学术转向。西方粉丝文化研究早期,学者们将大众媒体的消费视作权力斗争的场所,重点关注了粉丝的主动性和抵抗性。他们欣喜地发现粉丝能通过解读文本、转化文本和批判文本来颠覆社会不平等的体制关系,反抗主流意识形态[8]。然而,后期的粉丝文化研究开始注意到粉丝身份和粉丝立场的复杂性。艾伯克龙比认为,面对商业资本以及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侵入,受众的身份建构是复杂且暧昧的。他提出了以“身份”为核心的奇观/表演范式,用以取代伯明翰学派以“权力”为核心的收编/抵抗范式。在这种范式下,粉丝既非完全被动,也非绝对抵抗,而是身兼观看者和被看者双重身份,会通过媒介资源进行想象式表演,建构自我在他者心中的形象,并产生认同进而满足自恋心理[9]。这种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范式的提出对拓宽粉丝研究的视野起到了极大作用。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转型期,在政治环境、文化工业、媒介技术等多种因子的共同作用下,网络文化图谱更加多元且充满流动性,青年粉丝群体不再像过去那般“英雄式”地抵抗主流文化,而是表现为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因此,传统亚文化理论已经无法全面阐释今日粉丝所呈现的后现代表征,有必要站在新的研究立场上,重新审视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下的粉丝文化。
三、粉丝亚文化再审视
(一)圈层破壁:文化交流与边界消融
1.媒介技术与文化互动
费斯克曾指出,粉丝通过持续的文化再生产实践,一方面区隔于主流文化并与之对抗,另一方面挪用并改写主流文化的特定价值观,成为大众文化受众“游击队”中最活跃的佼佼者[10]。过去,粉丝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界限较为鲜明,无论是“粉”偶像明星的追星族,还是“粉”某种文化产品类型的耽美族或动漫迷,都常结成小众化的亚文化部落,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中自得其乐[11]。他们或是拒绝触碰主流文化圈层,或是通过文化再生产抵抗主流文化,圈子和圈子之间壁垒森严,沟通与对话的难度较大。
新媒介技术的社交性特点为粉丝文化与其他文化圈层的接触、对话和沟通提供了渠道,也给予了建构共同话语符号的机会。B站曾经被视为二次元粉丝的“栖息地”,但是伴随着一大批官方媒体入驻,青年粉丝以或被动或主动的方式开始突破自身的文化边界。以《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等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节目在B站大火,充分表明了粉丝群体借助新媒体平台与主流圈层实现了双向的破壁、碰撞和互渗。除此之外,粉丝对于主流话语符号也不再持有全盘抵制的态度,他们常将“这盛世如你所愿”“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等口号挂在嘴边,通过引用官方的宣传话语表达自身情感;主流媒体也逐渐放下身段,接纳由粉丝群体创造的流行词汇诸如“阿中哥哥”“我兔”,以此谋求多元文化认同与价值聚合。因此,通过交流平台的搭建与话语符号的共享,粉丝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不再是伯明翰学派提出的抵抗与顺从、表达与镇压、支配与从属的简单对立关系,而是既有对立冲突,也有协商融合的多元互动关系。
2.后亚文化视角下文化边界的消融
后现代社会语境下亚文化的风格、形式和实践呈现出更大的多元化趋势,粉丝文化的指向性和意义日益模糊,与主流文化的边界也不再清晰。在传统亚文化研究的视野中,亚文化群体具有较高同质性和忠诚度,彼此分享着相同的文化属性和思维观念。亚文化风格具有深刻的内涵,反映着明确的价值观,是一种意义固定和别具一格的符号形式[12]。然而在大众媒介文化的催化下,在偶像泛化的时代背景下,当今的粉丝数量实现了爆炸性的增长,这使得粉丝群体的异质性大大增强。更为重要的是,粉丝还会根据当下需要不断调整自我身份,粉丝内部的每一个个体可能同时属于不同的文化圈层,他们携带着各种各样的文化特质在某一不固定的场所磨合、交融又分离,粉丝亚文化也因此失去了可视性和可辨认性的空间。
传统的亚文化理论是与“前数字化时代”密切相关的,前数字化时代所谓的社群观念使得青年亚文化呈现出鲜明的风格和强烈的集体意识[13]。但是,在互联网“促成的虚拟空间”中,青年粉丝群体更多追求的是个人的精神愉悦与身份认同,强调的是文化交流体验,而非仪式性的抵抗。也就是说,“主流文化本身就已经被分解为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14]。因此,数字化时代主流文化和粉丝亚文化之间绝非泾渭分明,而是处于混杂交织的状态。
(二)抵抗弱化:对主流话语的接纳与拥抱
1.粉丝抵抗弱化的表征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经济改革深入、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促进了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和广泛传播,粉丝文化逐渐在我国落地生根。1992年,春晚小品《追星族》以批判的立场演绎了青少年盲目崇拜偶像明星的现象,并试图以一种诙谐的方式号召青少年群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15],这侧面反映了在当时的主流视角下,追星族是作为“他者”的角色而存在的。2005年,《超级女声》节目的爆火使得粉丝群体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调姿态进入了舆论视野,粉丝们对歌手周笔畅和李宇春等打扮较为中性的选手的追捧可以被视为颠覆主流审美观的一种“抵抗行为”。2010年,韩国组合Super Junior的粉丝为了买到偶像的演唱会门票在上海世博馆聚集并发生混乱,部分粉丝由于过于激动甚至动手攻击武警,这一事件引发了部分网络民族主义者和粉丝的激烈冲突。由此可以看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粉丝往往站在主流话语的对立面,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反叛性和非主流特性。
伴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有研究者认为网络粉丝“谦逊、礼貌、谨言慎行”等形象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粉丝“疯狂、攻击性、缺乏理性”的负面形象[16]。一方面,粉丝团形成了规模化的、有组织的群体性力量,并在追逐偶像的过程中表现出自己大方得体且“正能量”的一面。例如,每当自己的偶像转发“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的相关宣传国家、民族等具有极强意识形态导向的报道时,粉丝们往往乐于接受,并表达对主流话语的附和;另一方面,青年粉丝开始主动向主流话语靠拢,B站的爱国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横空出世,青年粉丝群体在了解国家历史、融合爱国情感的探索过程中不断建构政治主体性,“此生不悔入华夏,来世愿在种花家”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弹幕之一。近两年来,“饭圈女孩”这个原本小众的名词更是变成官方媒体版面上的座上宾,粉丝们将日常的追星实践平移至一场又一场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中,表达了这一代青年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和国家认同感。
2.粉丝融入主流的脉络追溯
粉丝从颠覆、对抗到接纳、拥抱乃至迎合主流话语的姿态转向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首先,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粉丝群体的规模急剧扩大,促进了粉丝亚文化的主流化和大众化。今日的粉丝并非一个严丝合缝的共同体,这也就使其难以形成坚固的抵抗权威的力量。其次,青年粉丝群体生长和浸润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脉络中,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意识形态规训一直以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认知和行动。社交媒体的兴起更是让政府意识到爱国主义教育要“深入浅出、形式多样、生动活泼、注重实效”[17],官方的意识形态部门在近几年的宣传中尝试突破旧有的已然僵化的宣传模式,借助受年轻一代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成功实现了整体性的收编。
再者,今日的偶像由资本一手打造而成,而“根正苗红”成为塑造一个优秀偶像不可缺少的“人设”。嗅觉灵敏的商业力量因此开始积极向主流政治话语靠拢,论证其在“经济效益”之外的“社会效益”。南海仲裁案后,歌手张艺兴把自己Instagram的头像换成包括南海的中国地图,遭到菲律宾网友大量的辱骂。其经纪公司立刻嗅到了这其中的商机,将张艺兴塑造成一个“在海外打拼多年但是由于为祖国发声而遭受网络暴力”的形象,通过唤起网民的同情实现了对明星本人的推广和营销。反过来,艺人是否得到官方认可也逐渐成为衡量偶像影响力的重要指标。由此,主流话语和商业势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筑了互利互惠的共谋关系。在官方发布与明星联动的集体引导之下,粉丝开始用主流化的指标进行自我规约。唯有将自身趣缘认同和主流话语缝合起来,粉丝们日常文化生活的正当性才能得到巩固。
更重要的是,粉丝是不遗余力想要谋求身份认同的群体。今日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青少年粉丝,是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原住民”。现实社会关系的淡漠和长期的数字化生存所造就的“群体性孤独”,使得这一代人形成了不同于既往的情感结构、文化经验和自我认知[18]。迎合主流话语是粉丝实现自身精神诉求的方式,通过接纳乃至拥抱爱国主义、传统文化这些主流价值观,而非固守所谓“小众”的亚文化,粉丝意在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握紧与外部世界连接的钥匙,从而实现高度的情感满足和心理归属。
(三)走向中心:公民意识与社会参与
1.“粉丝公众”的诞生
曾有研究者认为,亚文化群体难以用正式和严肃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生活[19]。这是因为粉丝的主要行动轨迹围绕追逐偶像展开,对于公共事务往往漠不关心。然而,今日粉丝已经形成具有打投部门、宣传部门、公益部门等职能完善的组织结构,无论是普通的应援、打榜,还是更高层面上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实践,粉丝高度的专业化和纪律化,常常令旁观者大为惊叹。疫情期间,鹿晗粉丝24小时内集资66万向武汉地区捐款,并策划输送了大批医疗物资;蔡徐坤参加直播扶贫项目,他的粉丝就把海南的咸鸭蛋买到脱销;美国黑人男子遭暴力执法后,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的粉丝用视频瘫痪了美国警方针对示威者的应用软件,以此表达反对种族歧视的严正立场……诸如此类的事件充分证明,今日的粉丝群体正在突破文化圈层和壁垒,主动介入现实社会与政治生活。
粉丝对于公共参与的态度转向由多种机制所共同形塑。一方面,当前粉丝已经全面参与到娱乐工业的各个运作环节之中,成为偶像事业发展的一块极其重要的拼图。他们不再只是单纯的“追随者”,而是和偶像同处一个利益链条的“合作者”。通过完成诸多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实践行动,粉丝不仅能使自己的追星诉求更加合法化,也能向全社会展示偶像的正面影响力,从而助推偶像的事业发展[20]。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出现消融了政治、追星、游戏、个人身份建构等行为的边界,粉丝们在日常的追星实践中就能较低成本地了解社会事件,获得参与公共议题的机会。例如,“豆瓣鹅组”原是一个谈论明星八卦的粉丝聚集地。然而,粉丝们经常在讨论某对明星夫妻的某一行为时将话题延伸至男女平等、女权主义等方面,这会无形之中塑造粉丝们的性别平等意识,并激励其为维护两性平等而努力。加上新媒体时代的泛娱乐化思潮和消费主义解构了传统政治的严肃性与权威性,粉丝可以不再受缚于传统的价值标准和释放渠道,以更为个性化的方式参与公共意见表达,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所谓的“粉丝公众”的诞生。
2.粉丝公共参与的现实意义
通过某些公开且组织化的集体行动,粉丝不但有可能影响既定事态或事件进程,也有可能从更深层面上改变当代文化、社会乃至政治的某些形态。对于粉丝自身而言,积极的公共参与意味着角色突破和身份转变。就像我们看到,这一群体正逐渐摆脱污名化的形象,从社会的边缘位置进入主流视野、登上舞台中央,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宏观层面上看,粉丝实践的公共意义则体现为对于社会共同体的构建。张玮玉教授在《粉丝公众》一书中提出,粉丝公众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现象。“公众”的意义在“群众”之上,它并非是精神上低等且本质上未开化的群体。在未来,粉丝极其有可能通过与其他公众群体、本土或全球商业力量以及不同层级的政治权利之间的互动构成行动的主体部分。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人可以不受地理位置和社会地位的限制,加入公众的行列,这会为很多要形成公众的个人提供新的视野”[21],粉丝们将自己在长期的追星实践中培养出的爆发力和执行力应用于社会议题,在打造网络社会新的社会共同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2]。
四、总结与余论
在既往的一般意义中,亚文化是一种主流文化之下的次级文化,所追寻的是小众且边缘的文化品格。从历史经验来看,青年粉丝亚文化往往表现出一种对主流话语不兼容甚至对抗的姿态。然而在今日中国的语境下,粉丝文化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主流化”转向。其与主流文化的壁垒不再鲜明,对于主流文化的抵抗有所弱化,并在某些社会事件中展现出了积极融入主流社会的面貌。粉丝文化的流变背后是各种复杂因子的博弈,它不仅关乎媒介与个人情感的变迁,也关乎整体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的重塑。
粉丝亚文化的主流化转向显然能够更好地发挥主流文化的引导力,弱化文化冲突,促进社会认同。但是,亚文化圈层在向主流靠拢的过程也可能会磨灭掉自身的特殊性与灵动性。文化互动与文化融合应当是富有张力与生命力的。对于粉丝来说,需要在开放和坚守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对于社会治理者而言,适当的引导监督与允许文化自治并不矛盾。当粉丝亚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建立在平等与自由的基础之上时,我们就有理由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展望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