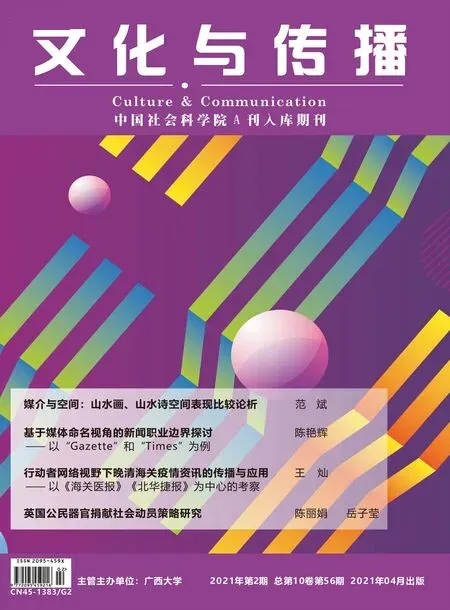民间叙事诗中的二元对立结构分析
——以《双飞鸟的传说》为例
司国庆
民间叙事诗是民间文学体裁之一,是人民大众在民间口头创作和口头流传的、篇幅较长、叙述人生故事的韵文体或韵散结合体的诗歌作品。我国境内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本民族独具特色的民间叙事诗作品,南方如彝族叙事诗《梅葛》、纳西族叙事诗《创世纪》、拉祜族叙事诗《牡帕蜜帕》等,北方如满族“说部”、达斡尔族“乌钦”、赫哲族“伊玛堪”、鄂伦春族“摩苏昆”等。
这些民间叙事诗一般产生于人类社会初期,和神话、史诗、民间传说类似,大多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但侧重点仍以本民族的现实生活为主。“在民间故事叙事中,有递进、环形、对立、插入、重复等多种叙述结构方式,每种方式都渗透着人类传统的认知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其中,对立结构作为一种表现鲜明善恶价值观和思维认知的结构模式,在民间故事中有着广泛的体现,是故事结构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之一。”[1]本文以鄂伦春族民间叙事诗《双飞鸟的传说》为例,分析作品结构中的二元对立元素,进而挖掘文本背后的“深层结构”。
一、《双飞鸟的传说》:一曲动人的爱情赞歌
鄂伦春族属于东北地区满-通古斯诸民族之一,世居大小兴安岭、黑龙江以及乌苏里江等地。在悠久的游猎生活中,艰苦但却瑰丽的大自然赋予鄂伦春人奇特的想象力,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文学、音乐、舞蹈等艺术,如“摩苏昆”(说唱)、“坚珠恩”(叙事歌)、“吕日格仁”(民间歌舞)、“赞达仁”(民歌)等。“摩苏昆”是鄂伦春语,意为“讲唱故事”,一般为单人表演,说唱结合而不用乐器伴奏,语言明白晓畅,合辙押韵,曲调起伏变化不大,具有浓郁的鄂伦春传统文化韵味,2006年被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按照内容性质的不同,满-通古斯诸民族叙事诗分为爱情婚姻叙事诗、传奇生活叙事诗和萨满文化叙事诗三大类[2],其中爱情婚姻叙事诗根据结局不同又分为喜剧和悲剧两种类型。由莫宝凤、李水花讲唱,孟淑珍记译整理的《双飞鸟的传说》属于典型的悲剧型爱情婚姻叙事诗。鄂伦春女孩乌娜季与青年阿什克塔由相识到相爱,在灵巧能干的乌娜季的帮助下,原本家境艰难的阿什克塔一家家境逐渐向好。当二人感情日笃谈婚论嫁时,嫌贫爱富的乌娜季父亲阔力赫依被媒人说动横加阻拦,决心把乌娜季嫁给西山更富裕的八音欠家“酒量小、富态膘、岁数大”的三儿子,乌娜季坚决不从,阔力赫依老头便派家人监守乌娜季。二人想方设法相见并决定出逃,随后被鄂得萨满掐算到并派老龙搅动河水阻隔二人。乌娜季与阿什克塔百般尝试却依旧无法渡河相见,最终乌娜季病重去世,伤心欲绝的阿什克塔也自杀殉情,二人死后怀里飞出一青一白两只鸟儿,飞向高空去寻找最终的自由和幸福……
帕里-洛德理论认为,“在有一定长度的民间叙事演唱中,没有两次表演是完全相同的。”[3]史诗在传唱过程中,尽管部分细节会有所变化,但程式化的主题、典型场景以及句法是相对固定的,一如民间叙事诗中的内在结构。在结构主义学者看来,“同类型叙事性文学作品,无论是从共时还是历时的角度看,其内在的结构(或说‘语法’)是不变的,而变化的只是人物、环境或故事情节等因素。”[4]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双飞鸟”类爱情叙事诗的基本“语法”为:情起—受阻—反抗—失败。这一结构形式在我国古代各民族民间叙事诗及民间传说中普遍存在,如《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与刘兰芝殉情自杀的爱情悲剧,《梁祝》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牛郎织女》中牛郎与织女相隔渺渺天河的爱情悲剧以及《阿诗玛》中阿诗玛被权贵强行嫁娶最终逃离虎口却不幸落水殒命的悲剧等。这类叙事诗不仅“语法”结构相似,而且在文本内部也呈现相似的二元对立矛盾。
二、《双飞鸟的传说》中的二元对立结构
“二元对立”理念最早可追溯至语言学领域。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能指与所指”“历时与共时”“语言与言语”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概念;随后雅各布森学习并发展了索绪尔的二元对立理论并提出“隐喻和转喻”的概念。这一理论转向人类学领域滥觞于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对人类亲属关系和各地神话模式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研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二元对立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方式,最终成为结构主义最基本的结构观念。这种二元对立思维不仅适用于神话模式的分析,也可以用来观照整个文学创作活动,以《双飞鸟的传说》来看,文本中呈现以下几组清晰可辨的二元对立结构。
(一)自由恋爱与家长之命的二元对立
封建社会尊卑等级观念森严,父母对儿女的婚姻大事往往具有决定权,封建礼教更是牢牢束缚了女性的自由意志,“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性成为封建男权社会的一件工具,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自由恋爱成为一种奢望。《双飞鸟的传说》中,聪明灵巧的乌娜季偶遇家境贫寒但年轻能干的阿什克塔,二人在对唱山歌的过程中互生情愫,随后感情快速升温。眼见已经处到谈婚论嫁的地步,然而嫌贫爱富的阔力赫依老头却横加阻拦,“终身大事,父母作主,这是死规矩!”直接导致二人的爱情悲剧。
青年男女与封建家长的对立结构在《孔雀东南飞》与《梁祝》中同样有所体现。《孔雀东南飞》中焦母认为刘兰芝“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要求焦仲卿“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刘兰芝被遣回家之后,也面临父母弟兄的逼迫。最终在双方父母之命的逼迫下,二人毅然共赴黄泉。《梁祝》中祝英台的父母同样因为门第之念而阻止她与梁山伯的自由婚恋,最终导致悲剧。在这组二元对立结构中,年轻男女虽有程度不一的反抗,如乌娜季与阿什克塔决定出逃,焦仲卿与刘兰芝以死明志,梁山伯与祝英台殉情化蝶,但结果全部以失败告终,足以证明封建时代家长势力、权贵势力之根深蒂固,年轻男女的反抗力量之弱小无异于蚍蜉撼树。
(二)善良与邪恶的二元对立
不同于小说等书面文学,人物形象呈现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结构在史诗、神话、传说、叙事诗等民间文学作品中较为常见,这是由民间文学固有的特点决定的。一方面,由于创作者艺术水平的限制,脸谱化的人物更容易塑造,且二元对立的人物性格特征更直观地反映群众喜好。另一方面,不同于小说等书面文学作品多由情节驱动,神话、传说等民间文学作品更多由人物驱动。“格雷马斯从叙事作品的行为主体(角色)的描述及理论基础结构二元对立原则出发,就表达过角色作为行动元的叙事方式。”[5]从善恶对立的人类伦理道德观念来看,青年男女代表了善良的一方,而权贵世俗势力则代表了邪恶的一方。
《双飞鸟的传说》中乌娜季与阿什克塔正直善良,敢于反抗家长之命,尤其是乌娜季,不仅坚决果断,而且富有智慧。在被二嫂看守期间,用真情打动二嫂从而与阿什克塔见面,并机智地留下信物为阿什克塔传递信息。与阿什克塔见面后,她勇敢坚决地提出私奔的建议,相比之下阿什克塔的犹豫更显出乌娜季敢作敢当的风范。出逃之前,她又运用智慧做好物质准备,“她每出去一次,便在怀里掖一两样东西,送到外面人家不在意的草丛里,等太阳老高老高,她也把准备下的东西一样不落地倒腾完了。”一个机智可爱的乌娜季形象跃然纸上。作为对立面的阔力赫依则显得固执蛮横,置女儿幸福而不顾,一心想与富有的八音欠家结亲。在《阿诗玛》中,作为反面形象的热布巴拉更具有典型性。热布巴拉家“花开蜂不来,有蜜蜂不采”,与阿黑哥先后比赛对歌、砍树、撒米、拾种,热布巴拉父子都一一落败但还是一再反悔,并计划放虎害人,最终央告崖神发大水,把善良的阿诗玛卷进旋涡夺去了生命,突出表现了权贵势力邪恶的一面。
(三)人力与神力的二元对立
汤因比认为,“宗教使人认识到人类虽然有卓绝的巨大能力,但也仍然不过是自然界的一部分。”[6]我国北方众多游牧、渔猎民族都信仰萨满教,秉持“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认为萨满是沟通人与神的使者。萨满通常既是氏族内部首领,又兼任医师、巫师等多种角色,具有一定的神性色彩。随着人类社会进程的发展,势必需要逐步摆脱自然的限制、为自然祛魅,萨满形象作为宗教观念的映射,在众多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时常表现为勇士与恶萨满的对立,也即人力与神力的二元对立。
这组二元对立在《双飞鸟的传说》中表现为阿什克塔与老龙的矛盾斗争。叙事诗中乌娜季与阿什克塔正要摆脱家长束缚,决定私奔追求自己的幸福,却被鄂得萨满掐算出来。鄂得萨满随即把消息报告给阔力赫依老头,并请老龙帮忙把河里的水涨满,阻隔二人相见。随后勇敢的阿什克塔与老龙展开了战斗。面对猛涨的河水,二人跃马扬鞭冲进水里,可任凭怎么折腾都无法过河,在与神力的较量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随后二人试图从上游、中游和下游过河,还是因“河水太深”“漩涡太多”“水流太急”无法成功,甚至二人向上游奔跑了九天九夜,依然被洪峰隔断,此时人力依然被神力压制;直至阿什克塔怒火冲天与老龙展开决斗,“直杀得满天雾气升腾,斗得水面巨浪滔天,水中泥沙翻卷,好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最终把老龙杀退到江口。
这组二元对立结构在《阿诗玛》和《牛郎织女》中都有所体现,如阿诗玛逃出热布巴拉家后,同样死于崖神作法兴起的洪水中;而织女则被王母为代表的神力限制,与牛郎相隔天河。在人力与神力的角逐中,既讴歌了人力的英勇无惧,也凸显了神力的强大。从不同人物的最终命运来看,这组二元对立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说明这一阶段的人类作为自然的一分子,还无法真正摆脱自然的限制。
三、二元对立结构的转化、消解及其深层意义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以二分的方式,展示了世界和社会的不断演变的组织形态,而在每一阶段出现的两方之间从未真正的平等:无论如何,一方总高于另一方。整个体系的良好运转都取决于这种动态的不平衡。……正是这一连串的差异推动了整个宇宙的运转。”[7]这种二元对立总是处于某种动态平衡之中,从矛盾建构到消解,还要经历一系列的转化过程,《双飞鸟的传说》中的几组二元对立结构莫不如此。
仅以“自由恋爱与家长之命”这组二元对立结构为例,最初十七岁的乌娜季本是“老两口心间上的肉”,可由于老人偏听偏信西山八音欠家媒人的一面之词,决然反对女儿的恋情,并限制乌娜季的行动,此时这组二元对立矛盾被建构起来。随着情节推进,被派来监视乌娜季的二嫂被乌娜季慢慢说服,转而支持乌娜季与阿什克塔的自由恋爱,为二人相见、出逃提供了契机,此时这组二元对立矛盾出现转换。二人出逃途中,遇到萨满、老龙的阻拦,出逃愿望破灭,最终二人双双离世,这组二元对立矛盾再一次经历转换并最终消解,标志着自由恋爱行为输给封建家长制力量。结合《孔雀东南飞》来看,刘兰芝、焦仲卿二人同样经历了“被逐回家—允诺复娶—逼应他人—以死殉情—死后合葬”,对应这组二元对立结构建构—转换—消解的全过程。
有意味的是,无论是《梁祝》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还是《双飞鸟的传说》中的乌娜季与阿什克塔以及《阿诗玛》中的阿诗玛,他们的爱情故事都以悲剧收尾,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类民间叙事诗的深层结构:虽然“殉情化物”的传奇结尾寄寓了广大人民对自由爱情的美好向往,但在阶级社会中注定无法摆脱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权贵势力的钳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