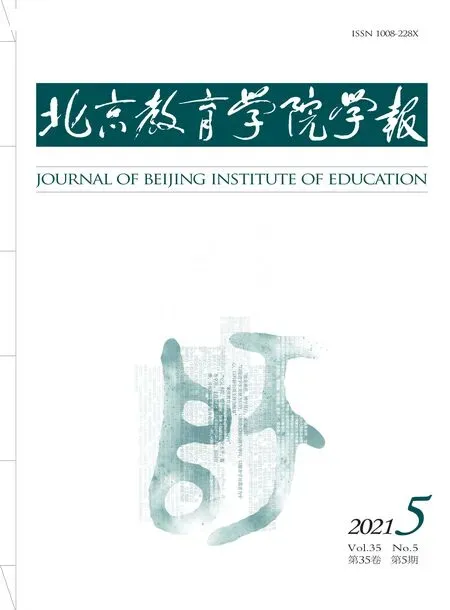高中散文“教—学—考”困局及破解
胡正伟
(国家开放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39)
普通高中教育是在义务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教育。高中语文学科承载着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与核心素养,为学生的自主发展、终身发展奠定基础的重要功能。《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中明确提出“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等语文学科核心素养,需要学生在积极的语言实践活动中积累与构建,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1]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全方位地体现了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应该获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思维方法与思维品质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围绕学科核心素养,当前语文教学实践设计了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等内涵丰富而又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散文是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体量最大的文体,相应地,散文阅读教学也成为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的主要板块之一。师生共同的期待是经由散文阅读教学实践提升语言能力,锻炼思维能力,提高审美品位,促进文化的传承。
在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提升过程中,散文阅读教学实践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使命——生成文体意识、建构阅读经验进而促进读写交互能力的提升。而这需要重视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框架内经典散文文本阅读教学示范性的特质与方法论的功能。否则,散文阅读教学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止于个案教学的偶然性与片面性。在现实的语文学科教学中,尤其是在引入考核评价之后,“教”与“考”形成相对独立的闭环,两者呈现出失衡的态势。学生(同时也是考生)作为教学过程的主体、考核评价的对象,常常陷入“教—学—考”的困局。
一、教师分文体教学意识与学生文体意识的生成
在高中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学习单元常以文体作为划分标准与组合依据。部编本语文教材综合了题材主旨与形式体裁进行单元编排,要求师生在文学教学与文体教学中均能有所收获与发展。基于文体特征开展阅读教学,要求教师能够基于清晰的分文体意识选择经典文本,引领学生在以文本接受为核心的阅读实践中逐步生成相对明确的文体意识。
文体是认知、把握文本过程中的基本概念,其内涵主要指向独立成篇的文本体裁、样式、体制,是创作者用以生成文本的逻辑、技法与惯性。作为规格与体式、惯例与格套存在的文体,呈现出文本基于内容而侧重形式的整体特点。特定的文体类型一般具有稳定的形式特征,这在古代文学视域中尤为明显,例如近体诗、骈体文。即使是在社会日新月异、文体与时俱进的当下,相对趋同的形式依然是文体界分的重要标准。
与文体相关联,在教学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概念是文体意识。宽泛地说,文体意识是指主体在文本创作和接受过程中对不同文体的感受、理解与把握,并发展成为对读写实践的一种能动的再认识与应用。具体到教学过程,教师在一般意义上的文本接受主体的身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向与升华——不仅接受文本,而且引领学生接受文本。当明确的文体意识被引入到教学过程中,教师方能有目标、有步骤地促进学生生成相应的文体意识。
从创作主体的视角,作者会根据具体的题材内容及借此所要表达的情志,选择从纷繁的文本个案中抽象出来的、存储在大脑中的某种文体常态去物化作品,实现特定的写作意图及审美理想。当然,作者常常以某种文体常态作为坐标和参照,一方面遵循它的基本框架和规格,另一方面又进行自由扩张和变异,从而生成与某一文体常态若即若离的具体文本。作为文本接受与文本意义再创造的主体,读者会按照文本所提供的物象、景象、形象或场面等具体内容,运用头脑中先于当下阅读而存在的某种文体常态,去解读、接受包括形式、体制等文体常态在内的文本信息,同时在包括文体变异在内的文本空白处有所发现与领悟。
不夸张地说,文体意识的生成与应用是主体(包含作者、读者)文本艺术思维趋向成熟的标志,是一种深厚语文修养和高超读写技能的体现。文体意识具有较强的导向性,它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读写实践的成效。因此,为了提高文本读写水准,教师需要具备相对清晰、明确的分文体教学意识,在不同的文体教学实践中,选择相对应的经典文本,通过示范性的阅读、写作训练,促进学生文体意识的生成。
二、散文文体特征的别一种认识及其教学实践意义
散文是高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文体。浩如烟海的文本,造成对散文文体概念阐释众说纷纭的局面。本文无意于就此展开思辨。不过,若从散文的文本要素——形、神及二者的关系切入,散文“形散神聚”的文体特征又可能获得另一种审视与认知。然而,对于任一文体而言,有效的文本创作应该都是“神聚”的,一般理解为文本主旨单一明确,深层次可以理解为意蕴、情绪甚至一种心理场的向心凝聚。[2]因此,“神聚”不能视为散文核心的文体特征。相反,“形散”的散文,相较于其他文体,具备了明显的区别性。这里的“形散”,不应仅仅理解为写作手法的自由灵活、语言操作的参差错落等,更应理解为材料取舍的纵横捭阖。经典散文文本总是尝试截取不同时空中的材料横断面予以跳跃性叙写,最终由发散走向聚合,建构起多个材料横断面之间的本质联系。
读者在对任何文本的接受过程中所选定角度与开掘的层次,必然是多维的、开放的。但是,当文本接受作为教学过程的基本环节,其“角度与层次”首先应是相对稳定的。唯其如此,教学方能从个性化、随意化的文本接受甚至文本不可知论的泥沼中脱身出来,具有在课堂上面向全体学生进行解读操作的可能性。笔者以散文《冬天》的阅读作为教学过程的案例。《冬天》是朱自清创作于1933年的一篇回忆性散文,作家运用素朴洁净的文字,在回望人生历程后沉淀生命体验。时至今日,文本承载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对树人育人仍然颇多裨益。虽然“审美鉴赏与创造”等学科核心素养备受关注,但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是毋庸置疑的逻辑起点,也是理所当然的逻辑归宿。然而,教师在《冬天》的散文教学过程中,更应实现对文本个案思想性、情感性这一逻辑处理的超越,进一步向“文体意识的生成与应用”掘进,指向认识论与方法论:在同一文体的经典文本、多个文本接受的基础上,探寻规律,并以规律指导更多文本个案的分析,逐渐引导学生生成日益清晰的文体意识。
叶圣陶说:“谈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会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3]在《冬天》中,朱自清设定了跳跃的三重时空:童年在扬州,青年在杭州,中年在台州。不同的时空中,主体身份与叙事场景在不断变化:作为儿子与弟弟的朱自清与父兄在冬夜白水煮豆腐;作为朋友的朱自清与友人在冬夜游西湖,作为丈夫与父亲的朱自清在冬日与妻子、孩子厮守。三个场景,跳跃腾挪,各自独立。除了朱自清这一人物的恒定与冬日时令的趋同,不同场景中的人、事、物、景互异而毫无交叉。不过,“无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一句话将发散的场景收束整合:人世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弥漫于枯索萧瑟的深冬。整篇文章呈现出一种“文体的完美”样态。
在以《冬天》为核心文本与基本文献的学习活动设计中,教师若能基于明确且辩证的文体意识,便可以围绕散文的文体特征,引领学生经由“形散”走向“神聚”,把握散文阅读理解的规律。
三、散文教学过程与考核评价的平衡与失衡
基于在散文教学过程中生成并不断明晰的文体意识,散文考核评价的旨归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落实。终结性考试作为测定学生学习情况的一种途径,其理想的状态是:命题人围绕散文的文本要素与文体特征进行文本选择、处理和试题命制,考生围绕散文的文本要素与文体特征进行文本阅读并有效作答。来自于语文课堂但不限于语文课堂的多场景学习过程中生成的文体意识,即散文的文本要素与文体特征,作为命题人与考生共有的知识背景成为有效“信息交流”的语境。
深入来说,就作为文本接受的主体而言,命题人与考生同时又是相对于文本创作者而言的另一极。作为文本创作主体的作者与作为文本接受主体的读者,经由文本进行交流,总是在尺度适宜的阅读期待满足与受挫之间谋求一种既有背景认同又有认知差异的动态平衡。换句话说,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往往引入“隐含的读者”的视角,以期创作出的文本能够在预期的范围内为读者有效接受——包含文本要素与文体特征等内涵的文体意识在文本创作过程中就已经成为预设的、潜在的信息交流语境。在文本进入读者视野后,合理的、常态化的文本接受应该是读者秉持与创作者相同的文体意识,即进入由作者预设的、潜在的语境,展开信息交流。
因此,对于散文文本而言,即便接受三个不同主体——原作者、命题人(改编者/读者)、考生(另一读者)的审视,用以支撑不同主体之间展开有效“信息交流”的语境与标准也是相同的,散文阅读试题的信度也是可控的。虽然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任何一个读者视野中的“哈姆雷特”,都只能是北部欧洲的王子而不可能是南部非洲的公主。如此一来,多主体基于散文文体意识围绕同一散文文本展开信息交流,成为散文常规阅读乃至考核评价的理想模式。参照这一模式,散文“教—学—考”形成一个文体意识养成与文体意识应用的闭环,状态是平衡的。
关联至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平衡状态的散文“教—学—考”也正是学科应该追求的目标。学生通过梳理和整合,将积累的语言材料和学习的语文知识结构化,将言语活动经验逐渐转化为具体的学习方法和策略,并能在语言实践中自觉运用。如此,超越单篇作品进而拓宽到相同文体类型作品的文本接受,便具有了更强大、更值得关注的建构意义。教师在有限时空中的教学行为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授之以渔”。
然而实践仅靠模式模拟是不够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更倾向于召唤咀嚼不尽的内涵与细腻驳杂的感受;积极的阅读,尤其是文学作品的阅读,理应呈现更多的开放性并生成丰富的个人体验。[4]故此,文本永远是现实中独特的个案,散文的教学过程与考核评价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复杂的样态:有可能是处于平衡状态的——这应该是主体、常态;又有可能是失衡,甚至是错位的。
兹以《雪野里的精灵》的阅读作为考核评价环节的案例。《雪野里的精灵》是作家李存葆的散文作品,收录于《大河遗梦》。作为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之作,《大河遗梦》中的28篇文化散文及随笔,是李存葆在散文领域精心耕耘的成果。
对当代文坛常见的文体样式,李存葆有着属于自己的认知与定位:在诗歌、小说、剧本之外,散文因其“举要治繁,含宏万汇”“无所不包,无所不亲”,成为“最能让骚人墨客思绪恣意飞驰”[5]的体裁。这无疑是作家在散文创作之初已然生成并在创作过程中不断践行的文体意识。在《雪野里的精灵》一文中,作家截取了三个物象架构文本:多次晋谒的莒县城西定林寺中的古银杏树,70年代在崂山哨所见到的无名花草,90年代在长白山见到的白头翁。不同时空中的材料横断面在跳跃性的叙写中由发散走向聚合,有机地建构起了多个材料横断面之间的本质联系。
不难预想,考生基于学习《冬天》等文本而生成的文体意识,可以在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中,应用于《雪野里的精灵》的阅读实践,实现考核评价对于教学过程的有效验收。
不过,文本接受自身允许的开放度,尤其是文本创作的主观性以及个性化的追求,必然会对“教—学—考”的平衡状态形成挑战。如果仅从创作的角度审视,任何表现形式的文体状态都是可以被接受的,甚至是被鉴赏的。但是,如果进入“教—学—考”的特定情境,从命题的创造性、突破性出发,过度地打破平衡,不免滑入试题偏难险怪的境地,导致考核失去信度,教学过程遭遇否定。以陈峻峰创作的《在春天里观察两只鸟》为例,作家以两只鸟的筑巢作为基本材料不断发散,指向个体生命状态、代际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多个命意。一方面文本提供的材料并非是时空转换中不断跳跃的材料,而是聚合的;另一方面经由文本材料归结出的创作命意却是发散的、离心的。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这是一种写作的自由,无须接受既有文体意识的审视与苛求。不过,当作品进入考核评价环节,作为散文文本在材料与命意之间的关系上与《冬天》《雪野里的精灵》等文本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命意的发散,势必会打破“教—学—考”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考生无法运用既有文体意识精准理解文本,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容易被质疑,考核评价的信度与效度容易被降低以至消解。
教学与考核评价整体呈现出的复杂样态,常常置考生(学生)于进退两难的困局:在课堂上经由教师引领而生成并不断强化的文体意识,在考核评价中可能发挥作用,也有可能失效。
困局深陷一步,则不仅仅是命题人在文本选择与再处理上的疏漏,更是在试题命制过程中与教学过程的南辕北辙。再以进入考核评价环节的徐贵祥的散文作品《穷人树》的试题命制为例。《穷人树》作品由托尔斯泰墓地写起,命意基本指向对托尔斯泰平民化思想转变的崇敬与礼赞。在开篇及文末,作家两次写到墓地“像哨兵一样列队的青草”[6]。命题人就此设问,要求考生分析其内涵与效果。参考答案提供的是如下分析:
第一次,用列队哨兵写(刻画)托尔斯泰墓地青草的整齐,表现托尔斯泰墓地的庄严肃穆、简单朴素,表达了对托尔斯泰的崇敬之情。
第二次,用列队哨兵写(烘托)托尔斯泰墓地青草的刚劲,表现俄罗斯人尽可能保持名胜古迹生态的理念,表达了对这种理念及坚守的敬重之情。
评分标准:两个要点,每个要点3分。意思答对即可(若答形式方面的作用,言之成理亦可酌情给分)(1)详见2015年北京市西城区高三一模语文试卷及参考答案。。
基于同一文本,作者的创作命意被分解为互不相关的两个角度:一是“对托尔斯泰的崇敬之情”,二是“对这种理念(俄罗斯人尽可能保持名胜古迹生态的理念)及坚守的敬重之情”。作为创作主体,作者赋予文本以多个命意是无可非议的,即便是在教学过程中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命题人若脱离或者超越教学过程,对“原生态”《穷人树》文本不加有效处理,甚至放大了其与《冬天》《雪野里的精灵》等文本在文体特征上的差异,用“小众”置换了“主流”,那么走进考场的学生势必无所适从,难以应对:文本到底是用以承载对伟人平民化胸怀的敬意,还是用以传达一种对抗商业化的理念——毕竟材料的发散最终需要指向中心命意。
四、破解困局的可能性路径
受到教学、考核等不同过程主导角色、主体角色差异性影响,破解“教—学—考”困局的路径既是可能的,又是多向的。
在教学过程中,作为课堂教学的主导,教师在学生散文文体意识生成与强化的过程中需要细化且明确教学目标,在学习任务群中设置典型任务,选择优质的教学资源,运用具有经典意味的案例,制订完善的教学方案与路径。同时,适度兼顾散文文本在呈现文体特征时的常态与变异。作为学习过程的主体,学生在课堂内外应把握基于文体特征接受文本的基本规律与方法,并有意识地实现知识与能力的迁移;同时保持开放的心态、灵活的视角去应对多变而互异的文本现实。
破解困局更有效的作为应该发生在考核评价环节。测评与考试是语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就是学生一种特殊的学习过程。语文课程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全面提高,因此,应真实反映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过程与现有水平,准确判断学生核心素养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其原因。就此而言,课程评价与教学之间应形成稳定、有效的反馈机制。课程评价在面向学生与考生之外,对高中语文教学改革应发挥积极的引领与导向作用。因此,破解“教—学—考”失衡的困局需要引入并强化考核评价环节的改革,从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转向关注学生的学习品质。
考核评价的对象是考生,在本质上与学习过程的主体——学生是同一的。从学生到考生,主体需要做的事情不外是将学习过程中积累的散文文体知识与培养的散文阅读能力应用到考试题中,终极旨归不脱离自身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持续提升。但是,在考核评价的诸多方式中,当终结性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上升到主导地位甚至成为唯一形式的时候,考生所面临的形势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话语权从教师转向命题人。就考核评价的主导而言,现实状态是命题人尤其是高考命题人与教师之间分野悬殊。客观且普遍存在教考“分离”,造成高中语文课程评价主体的单一,而非多元;评价方式的失当,而非适当;评价内容的突兀,而非典型。就此而言,课程评价的探索之路相比较于课程教学而言更为任重道远。谋求评价主体的多元、评价方式的适当、评价内容的典型,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此为取向,高中散文“教—学—考”的困局方能得以破解走向平衡,学生的人文综合素质与学科核心素养方能得以有效提升。